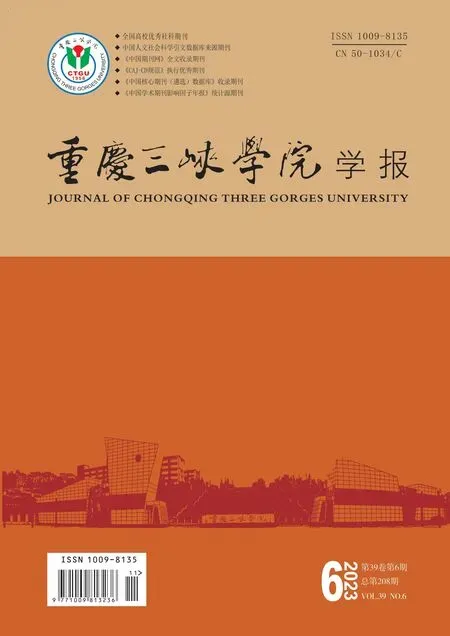汉武帝的通经致用观及对汉代经学的影响
张华林 张梅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说:“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1]56他认为西汉经学家将《诗》《书》等用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处理,此即通经致用,这是两汉经学的基本特色。但此经学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学者将其源头追溯到史官文化与孔子阐发、讲解经典大义之举[2-3],但孔子阐说经典的价值取向偏重于道德人格完善与社会伦常之建构,这与汉人据经义解决社会政治事务的用经理念不同,两者不具有渊源关系;有学者认为汉代通经致用始于陆贾“因世而权行”[4],但陆贾之说较模糊,没有提出明确的通经致用的具体理念与方法等,且其说未被汉高祖采用,更未被武帝之前的学者所接受;也有学者注意到汉武帝通经致用的事例,但对其具体理论主张、实践情况与影响等缺乏系统清理、分析[5-9]。总体上,学界这些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依据经学解决现实政治实务这一通经致用的基本特征讨论其形成缘由,故虽有所论,但多不中的;二是有些学者虽然注意到汉武帝时开始出现的依经决事现象,但没有挖掘出汉武帝有意识提炼出来的通经致用经学理念,也未就武帝对此理念的全面实践作系统梳理,更未论及此理念对汉代经学通经致用特征之影响。
本文的写作目的,便是通过文献耙梳,将汉武帝与汉代经学通经致用特征的产生、形成之关系揭示出来;也借此揭示汉武帝在汉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由此拓宽汉武帝研究的学术视域,突破学界一直从独尊儒术角度讨论“汉武帝与汉代学术关系”的单一视角。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汉代通经致用经学观的形成与汉武帝的明确倡导和全面实践有关,具体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汉武帝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提出,包括“以《春秋》对”和“取之于(经)术”的明确要求;二是汉武帝对通经致用经学观的实践,包括以经决事(涉及治狱、人事任免、军事行动、礼乐活动、治河等)和强调政府官员应具通经致用能力;三是武帝通经致用经学观对汉代经学的影响。
一、汉武帝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提出
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儒家经典被禁止传播。汉高祖本不好儒。汉文帝好刑名,虽有经学博士,仅具官待问。孝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喜黄老而不好儒术,儒生鲜有进者。故汉初儒业不兴。
汉武帝好儒术①《史记》之《孝武本纪》《汲黯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以及《汉书》之《外戚恩泽侯表序》《郊祀志》《东方朔传》等文献皆言及武帝“乡儒术”事。,为太子时曾受王臧、卫绾的儒学教导,所受经学教育与客观现实的需要,使他在统治思想上选择了儒学。建元元年(前140)即位,罢免“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10]156,以王臧、赵绾等经学家为公卿[10]452,初显尊儒立场。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罢《论语》《孝经》等传记博士。建元六年尚黄老的窦太后崩,武帝以好儒术的田蚡为相,于是“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1]3788,他将罢黜对象由法家、纵横家等延伸到黄老道家等除儒家外的诸子百家。元光元年(前134),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10]2523,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不久之后,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兴太学等经学政策相继出台,从制度层面上确保了儒家思想作为刘氏王朝统治思想的地位。
在完成儒家制度化建设的基础上,汉武帝强调儒家经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而不是仅局限于对经书文献与思想的推崇。这种经学理念,被他提炼为“以《春秋》对”和“取之于(经)术”的经学观,要求臣子以经学解决他提出的现实政治问题。
(一)“以《春秋》对”
“以《春秋》对”,指汉武帝要求其臣子依据《春秋》经义处理相关事务。如庄助思念故土,武帝委之以会稽太守;但庄助“数年,不闻问”;武帝赐书曰:“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10]2789要求庄助据《春秋》经义(尊王重礼)对其无视天子的行为作出解释,不允许他用纵横巧辩之辞。据《汉书》本传,“助恐,上书谢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诏许,因留侍中。”庄助以“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回应武帝,即据《公羊传》僖公二十四年(前636)之大义,将君臣关系匹配于人伦关系(移孝作忠),从而促进儒家人伦政教化,并借此推重君权;故为武帝所认可。或许因庄助具通经致用能力,武帝曾令庄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10]2775,“相应以义理之文”应该是与“以《春秋》对”一致,即以经义论政事。
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谋反,武帝命吕步舒以《春秋》决狱。《汉书》载:
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东、江都王皆知其谋,阴治兵弩,欲以应之。至元朔六年(前123),乃发觉而伏辜……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10]1333
“上思仲舒前言”,指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灾”“高园便殿火”,董仲舒据《春秋》“大一统”“尊王”之义,建言武帝消除不正之诸侯王或近臣,确保大一统下强干弱枝的君臣关系,但不被武帝接受,甚至被嘲讽[10]2524。淮南王之谋反,乃挑战中央王权;故武帝诏使吕步舒“以《春秋》谊颛断于外”,即要他据《春秋》经义决淮南王狱,其中便隐含着以《春秋》经学大义昭示、维护至高王权之意。虽然吕步舒据《春秋》经义决狱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上皆是之”的态度,表明他以帝王之尊对以经决事、通经致用经学观与经学行为的肯定与倡导。特别是武帝诏使经学大师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以《春秋》决淮南狱之行为,使此事由个别政治事件的经学处理上升到具有普遍性、权威性的国家意志层面,使吕步舒以《春秋》决事成为具有天下典范的经学理念与行为。
元鼎元年(前116),博士徐偃使行风俗,矫诏当死。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其矫诏之举,徐偃据《春秋》经义为自己辩护,张汤不能诎其义;武帝不得已诏终军以《春秋》义责徐偃,偃词穷服罪。对终军之行,武帝“善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10]2817-2818。武帝所“善”者有二:一是终军据经义处理政事的用经方式;二是终军以此方式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性。而“有诏示御史大夫”,乃武帝向大臣强调终军通经致用的经学行为,是他有意识推尊通经致用经学观的体现。
可见,汉武帝对以《春秋》决事经学理念之提倡是一种自觉的、反复进行的行为。这一经学观念实质上是使《春秋》经学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权力运作与社会事务的处理,这有利于维护与推尊大汉天子君权地位,有利于巩固其统治政权;这应该是汉武帝反复强调“以《春秋》对”的致用经学观的重要原因。
(二)“取之于术”
在元光元年(前134)策问董仲舒等贤良文学的策文中,汉武帝提出了“取之于术”的通经致用观,其文曰: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10]2495-2498
策文中武帝提出了他关注的问题:“夫五百年之间”句策问政权得失兴亡的原因——政权的稳定;“三代受命”句策问其政权的正当性与君权的神圣性;“灾异之变”句策问天人关系,同时也涉及其政权、政策的合法性;“性命之情”句策问人性与教化之道;其余策问治平之道。这些皆是涉及西汉政治根源性与现实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要求文学贤良们“取之于术,慎其所出”。那么“取之于术”具体何所指呢?
对此问题的解答,首先要明确诏书中贤良文学、先圣之业的性质。司马迁道: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11]3788
此言武帝受王臧等人影响,好儒学;文中以“于是”说明“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的原因就在于武帝之好儒,故这群对策的“贤良文学之士”应是一批儒学之士。司马迁接着说申公、董仲舒等代表的儒家经学因此而兴;然后武帝在窦太后崩后,便罢黜百家之言而尊儒术,进一步说明他策问的“贤良文学”应是一些儒家学者。
《汉书·公孙弘传》载元光五年(前130),复征贤良文学,武帝策诏诸儒曰:
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10]2613-2614
文中先说“元光五年,征贤良文学”,而后言“上策诏诸儒”,则贤良文学即“诸儒”。武帝又说贤良文学“习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明君臣之义”正是儒家所长,可知这些贤良文学当为儒者。《盐铁论·相刺》载大夫批评文学之言曰:“所谓文学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术,而姿质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则为人师,用则为世法。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12]282大夫对文学的阐述,也说明他们所习的“先王之术”就是《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学。这可以进一步确定元光元年武帝策问的贤良文学乃儒家学者。
由此可知,汉武帝要求贤良文学的对策需“取之于术”,也即利用经学解决汉王朝政权合法性、正当性等具有根源性与现实性的问题,用经学处理治国与天人关系等问题;要求避免出现“不正不直,不忠不极”等违背儒家价值观的对策内容。他这是昭告天下:经学不应是书斋中的学术,它应该有现实关怀、政治指向性;经学诠释应回应当下的政治诉求。这是将国家政权与经学关联,促使经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国家权力机器行使其文化权力。
由上述可见,武帝对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提倡是明确而自觉的。他提出的“取之于术”要求依据经义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以《春秋》对”,即“取之于术”的细化或具体化,指依据《春秋》经义解决相关问题,这便是通经致用、依经决事,从而促进经学与政治的互动。
二、汉武帝对通经致用经学观的实践
武帝不仅提倡通经致用经学观,还将之用于各种现实政务的处理。这体现为以经决事和重视官员通经致用能力两个方面。
(一)以经决事
以经决事,指依据经义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赵翼已关注到汉人这一用经方式[13]44,但他未论及武帝在这一经学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武帝的以经决事,包括依据经义决狱、人事任免、战争、礼乐活动、治水等。
以经决狱,尤其是以《春秋》决狱,是汉人通经致用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少年时期的刘彻便已有以经决狱之举,据《通典·刑法四》:
汉景帝时,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论杀防年父,防年因杀陈,依律,杀母以大逆论。帝疑之。武帝时年十二,为太子,在旁,帝遂问之。太子答曰:“夫‘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与大逆论。”从之。[14]4275-4276
对于陈防年杀继母案,廷尉依据律令,以大逆罪论处。这一判定是基于母子伦常关系而定。但《仪礼·丧服》有“继母如母”之说,刘彻认为此说恰恰表明继母与亲母有别;之所以服继母之丧与亲母同,乃缘于继母与父亲之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当陈防年继母杀其父之时,便已断绝两人夫妻关系,也就断绝了她与防年间的继母子关系。因此防年之杀母事不宜以大逆之罪论处,只能判之为普通杀人罪。对此判决,景帝予以肯定。如此事属实,则武帝年少时便具通经致用之能力。此后他使吕步舒以《春秋》决狱,使终军据《春秋》义决徐偃矫制之罪,鼓励兒宽、张汤以经决狱,乃至在董仲舒老病致仕之后,命张汤至董仲舒家问其得失,促使董仲舒著《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15]1612等等;皆是对少年时期以经决狱之延续与发展。在武帝的倡导下,汉代逐渐形成以经决狱之风。
在一些重大人事变动上,经义为汉武帝提供了经典支持,使其更具正当性和神圣性。这包括据经义废立皇后、封皇子等重大政治活动。
元朔元年(前128)废陈皇后立卫皇后一事,武帝下诏: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10]169
诏书所引《易》文出于《系辞下》;所引《诗》文为逸诗;二文皆强调变更的重要性。在经典支持下,武帝废陈后而立卫后,并废除孝景后三年以前狱讼及逋贷,为其内外政治变革打下基础。
元狩六年(前117),武帝据经义分别册封刘闵、刘旦、刘胥为齐王、燕王、广陵王,三篇策文皆为武帝自制①《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司马贞索隐:“按《武帝集》,此三王策皆武帝手制。”则此诏当出于武帝之手。。如封齐王策曰:
于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乎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11]2567
此文仿《尚书》诰命体而作,其话语、思想也与《尚书》《论语》有关。如“封于东土”出自《尚书·康诰》之“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惟命不于常”语出《康诰》“惟命不于常”。“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语出《论语·尧曰》之“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化用《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保国艾民”用《康诰》之“用保乂民”“用康保民”等。这些被称引、化用的经典话语,其原初语境中的仪式性、神圣性,以及册封者——天子的希冀、勉励、告诫等思想情感,皆通过武帝策文得以再次转化为神圣行为与思想范型。故汉武帝此举不仅从文体上取法《尚书》,更是据《尚书》以行分封之事;而汉代依据《尚书》行封建诰命,也当始于此。
对匈奴的用兵,是武帝一朝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经学常为其行为提供强有力的经典支持。如元朔二年,卫青等出击匈奴,取河南地为朔方郡,筑朔方城。武帝益封卫青之诏曰:
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10]2473
这虽是追记之辞,但阐明了武帝用兵匈奴的原委。“薄伐猃允,至于太原”语出《小雅·六月》;《毛诗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三家诗皆同。诗言匈奴内侵,周宣王对匈奴用兵,将之驱逐出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语出《毛诗·小雅·出车》之“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武帝引用时省略了“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句。《毛诗》以之为周文王时诗,《盐铁论·徭役》亦然,而《汉书·匈奴传》则以之为周宣王用兵猃狁之诗[10]3744。武帝也以此为宣王时诗,与《六月》同,皆言对匈奴用兵事。武帝据此《诗》文对匈奴用兵,乃比附周宣王伐猃狁之事,将自己置于历史和现实的道义高度上,并借诗以形塑自己中兴之主的形象。
随着国家进入盛世,武帝希望能制礼作乐,兴复礼制,以巩固社会秩序与统治。故他常据经义以制礼作乐。如元鼎五年(前112)立泰畤于甘泉,武帝诏曰:
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内惟自新。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望见泰一,修天文禅。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10]185
所引《易》文见《易·蛊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齐戒必自新,临事必自丁宁。”[10]186武帝据《易经》先甲、后甲之日以斋戒、祭祀。此逸诗和《周易》皆为武帝行礼之依据。
“以《禹贡》治河”,也是汉人代表性的用经方式之一,始为汉武帝所提倡。元封二年(前109),瓠子河决,武帝亲自主持塞决口。采用塞、导二法,双管齐下,说是“复禹旧迹”,实本《禹贡》以治之。[16]818太始二年(前95),齐人延年上书言治河之策,武帝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10]1686他拒绝了延年的治河方略,要求坚持“大禹之所道”。程元敏评论道:“‘大禹所道’道,《禹贡》所载之故水道也。……大禹所道、所治、所导者,故亦《禹贡》所载故水道也。”[16]818即此武帝据《禹贡》以治河。
汉武帝对通经致用的实践,所关涉者以政治事件为主,反映出其通经致用之政治取向,这也影响到相关经学诠释的政治性取向。其所涉及经学文献则包括《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仪礼》《论语》等群经文献,说明武帝对通经致用的要求是从经学整体层面而言的,而不是只针对某一门经学予以强调。
(二)重视官员通经致用的能力
汉武帝不仅自己以经决事,他还注重政府官员通经致用的能力。这体现在他对公孙弘等以经术缘饰吏事的官员的重视以及对部分儒生因不能通经致用而被疏远或罢免的事件上。
公孙弘曾习《春秋》杂说,元光五年(前130)拜为博士,“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11]3574。公孙弘以儒术缘饰吏事,即是以经术处理政务。《汉书》载元朔三年(前126)诛主父偃事:
上欲勿诛(主父偃),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10]2804
杨树达曰:“诛首恶乃《春秋》义,见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公羊传》。弘本学《春秋》,此弘传所谓缘饰以儒术者也。”[17]435此言公孙弘据公羊学定主父偃“首恶”之罪。班固曾说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10]1160,当即依据《春秋》之义管理下属官员。武帝对此大悦,擢左内史,元朔三年迁御史大夫,元朔五年晋丞相封侯[10]3593。通过褒扬其通经致用行为,成为天下典范,必然促进通经致用观在整个社会的传播,故《史记》说此举使天下学士“靡然乡风”[11]3788。
兒宽也因长于通经致用而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书》本传载:
兒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兒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10]2628-2629
《尚书》学者兒宽于元朔三年为廷尉文学卒史,为廷尉张汤所排斥。后因参与一疑奏的写作而被张汤和汉武帝认可,特别任命兒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结合《汉书》所言:“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10]2639可知兒宽、张汤采用的“以古法义决疑狱”,应是以《尚书》《春秋》等经义决狱①经义决狱,出程元敏《汉经学史》:“决狱比附古义,即经义。”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135 页。,这正是武帝所提倡的通经致用,故超迁之。此文还反映了两点:一是兒宽以经决狱的行为,得到张汤与汉武帝的认可与推广;二是其时“儒生与文史法律之吏,择术殊途,及宽、汤进用,由是引儒生以补法官,援古义以断今狱”[18],反映汉代以经决狱、经法结合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部分汉家自有制度的形成过程。伴随着秦汉统一时代的来临,人民和统治阶级都渴望在思想上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归属。因为,只有共同理念下形成的统一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才能确保大汉帝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19]。
董仲舒也倡通经致用,最具典范性的是以经决狱[15]1612。即便是他已致仕,朝廷大议,武帝常遣张汤就问之。董仲舒解决问题的方式则是据《春秋》等经义以决事,即“动以经对”,这与武帝提倡的“取之于术”“以《春秋》对”的用经理念与方式一致,故为武帝推崇。
汉武帝重视公孙弘、兒宽、董仲舒的共同点,是“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反之,部分儒生官员因缺乏通经致用能力,被武帝疏远或罢免;前者如《鲁诗》学者申公因缺乏解决实务能力而最终被“免归”。后者如武帝令博士诸生制作封禅之礼,然诸儒拘于《诗》《书》而不能灵活运用,制礼不成;武帝以诸儒无能,尽数罢黜[10]2631。这从反面表明他对官员通经致用能力的重视。
武帝对通经致用的提倡与实践体现在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使得经学从各个方面与政治相结合。这使经书文献由以前的儒家学者所看重的经典知识与历史文献上升为具有国家法典地位的治国理政之大法;经学大义对王朝行政事务的参与使其王朝政权与权力获得了经学的支持。这使经学与政权形成了相互支持与成就的态势;经学为皇朝政权的权威与合法性提供了学术保证,皇朝政权对经学的支持使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由此确保经学在汉代国家学术中的独尊的地位。同样,这也使经学不再是纯粹的学术存在,经学阐释必然要关注现实,对现实政治进行回应;现实政治的变化也自然会影响到经学学术形态与思想内容。
三、汉武帝通经致用经学观对汉代经学的影响
在汉武帝的提倡下,在董仲舒、公孙弘、兒宽等的响应下,通经致用得到两汉君臣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接受,成为汉代经学的基本特色,渗透进社会各个方面。下面从汉代帝王对武帝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接受与汉人对通经致用的实践两方面略作论述。
(一)汉代帝王对武帝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接受
武帝之后的两汉帝王多接受并提倡通经致用。如汉宣帝“循武帝故事”[10]1928,延续了武帝的通经致用观,如甘露元年(前53)召开的平《公羊》《穀梁》同异之经学会议上,宣帝要求参会经学家“各以经处是非”,这是对汉武帝提出的通经致用观与实践方式的延续。汉元帝好儒,其行多据经义;如元帝初元元年(前48)朱崖反,贾捐之反对元帝出兵,元帝责问捐之反对行为到底合乎哪些经义,其实质就是“以经处是非”或“以经义对”。成帝也接受了这一经学观念,如建始四年(前29)策问天地之道、王者大法、取人之术等问题时,明确要求对策者“各以经对”[10]2673。王莽则将通经致用发展到极致,以致“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10]1179。光武帝言行常以经为据,如据经义罢免诸侯王等[15]61。汉灵帝也要求大臣以经义对策[15]1998等等。
这些文献表明汉武帝所提出的通经致用经学观,为两汉帝王所接受,且以帝王之尊,以身作则,依据经学处理如废立皇后、罢免封赏大臣等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事务;而且要求大臣也当依据经义处理各种现实事务,依据经义为天子策问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由此逐渐形成汉代经学的政教实务特色。依据经义处理现实事务,也是汉人用经常态,相关文献材料大量见载于两汉文献中。
(二)汉人对通经致用的实践
汉武帝在汉代影响极大,是汉人心目中功德最大的四帝(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之一;应劭甚至说武帝“攘夷辟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矣”[20]49,以其为百王之冠冕。在武帝对通经致用的提倡下,在此后的汉代诸帝王的响应与号召下,汉人从各个方面落实以经决事的通经致用观。
如武帝曾依据经义废除陈皇后,此后汉代帝王妃后之废立,也多有据经义而行者,如光武帝据《关雎》废郭皇后[15]406,汉顺帝据《春秋》之义立梁商之女为皇后[15]439,曹操据《关雎》要求废除伏皇后[15]453,等等。
武帝据经义废立皇子的用经方式,亦为后世所接受。如光武帝据《春秋》义废太子刘强,立刘阳为太子[15]71;和帝邓太后据《春秋》义立刘祜为太子。霍光等据《诗经》《尚书》等立、废昌邑王刘贺[10]2945,并据《礼记》立刘询为天子[10]2947,经学直接参与大汉皇子乃至天子的废立,为其提供经学理论的合法性支撑。
武帝据经义开展对外军事行动,此后的汉代君臣也常据经义讨论或开展军事行动。如宣帝时萧望之据《春秋》之义反对对匈奴用兵,并为宣帝所接受[10]3279。元帝初,珠崖反,上欲大发兵击之,贾捐之据《诗》《书》《春秋》之义反对出兵,并为元帝接受[10]2831-2835等等。这些皆反映出经学在汉代军国大事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武帝曾据《禹贡》以治河,此后,成帝时许商也据《禹贡》治河[10]1689,哀帝时平当、贾让亦倡此说,而王莽及后汉诸帝也多有据《禹贡》治河者[16]819-823,如此形成皮锡瑞所谓“以《禹贡》治河”的通经致用现象。
在武帝影响下,汉代诸帝也重视任用明于经术大义的公卿大臣,并以教育、仕进等各种措施与政策保证对通经致用之士的选拔;而经学之士也自觉贯彻以经决事的理念,最终形成汉代通经致用的经学思潮与特征。
故被学界视为常识的汉代通经致用的经学形态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产生和广泛流布与武帝的明确而反复的倡导直接相关。武帝不仅提倡通经致用的经学观,并以身作则,将之用于实践。特别是武帝开创的这种经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学术生态被汉人普遍接受之后,汉代经学的通经致用特征、汉代经学政教实务特性便被确定下来,而持续了两千年的传统经学由此才真正得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