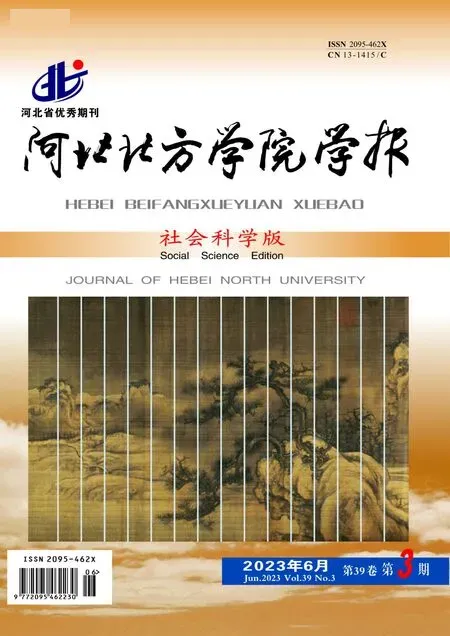民族播迁视域下魏晋南北朝汉羌农牧交融探析
高 凌 云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民族大迁徙导致各民族不断接触,进而形成民族大融合。该时期,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向中原迁徙达到了一个高峰,其内徙的原因多种,内徙促进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融。下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播迁为研究中心,探讨羌人迁徙过程中农牧文明之间的融合,以期对北方农牧交融史有所裨补。
一、羌族的播迁发展概述
魏晋之初,羌族主要在凉州、秦州、雍州和益州等地迁徙发展,羌人频繁迁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的需要和经济文化的吸引等原因。下文主要探讨这几个地区的羌族与中原民族发生接触后产生的迁徙与交融。
(一)凉州地区
汉末魏晋时期,各地割据势力强盛,凉州地区战争不断,西北地区的豪强欲逐鹿中原,能耕能牧的羌人自然成为其招揽对象。《三国志》载:“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1]491为了恢复经济,时任金城太守的苏则实施了一系列招抚政策,“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1]491。苏则招抚羌人部落,还亲自教给羌族百姓耕种知识。由于苏则体恤民情,东汉末因战乱外逃的羌人和塞外意欲迁徙的羌人都向金城郡迁徙,金城郡的人口不断增加。该时期羌人的迁徙除因招抚政策之外,统治阶级带领羌人作战也是原因之一。《三国志》载:“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1]491可见李越反叛时,苏则带领羌人平定了李越叛乱。魏文帝黄初年间,“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1]476。酒泉苏衡反叛,与羌豪等胡族联合攻打边县,一同被时任雍凉二州刺史的张既带兵击破,塞外西羌感受到了张既军队的威势,率两万余人投降,迁入凉州。此后,凉州和秦州的人口被魏蜀两国不断掠夺,两国之间的战役不断,该地区羌和氐等族的人口在两国之间反复迁徙。如正始八年(247),“(郭淮)进讨叛羌,斩饿何、烧戈,降服者万余落”[1]735。正始九年(248),蛾遮塞等“屯河关、白土故城,据河拒军。(郭)淮见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据白土城,击,大破之”[1]735。综上可见,在曹魏与羌人的接触中,因战争投降依附曹魏的羌人多达上万人。羌人的武器、粮食和劳动力可为魏蜀充实人口和发展生产力,给魏蜀争霸提供物质和人力保障。随着羌汉不断交融,凉州地区获得一定的发展。十六国时期,许多西北的王公贵族打着护羌校尉的旗号统治羌人,他们把羌人编为军队,带领羌人征战,或者强迫羌人修筑宫殿、开拓田地和种植谷物等。护羌校尉雄踞凉州及河湟一带,依靠羌人的力量称霸一方。
(二)秦州地区
秦州各郡的羌人也是各割据政权积极争夺的对象,羌人随各政权势力的消长而辗转依附于不同政权,与中原民族不断发生接触。太和二年(228),“蜀大将军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1]94。天水、南安和安定3郡中有不少羌人参与了反叛,响应诸葛亮的军队。同年,郭淮“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1]734。魏将郭淮在袍罕击破陇西著名羌族首领唐蹏的军队。太和三年(229),诸葛亮攻取了魏国的武都和阴平二郡,郡内众多羌人归附蜀国。姜维辅政时期,其对羌人更加信任和重用,羌人也为蜀国北伐作出了巨大贡献。蜀延熙二年(239),“辅汉将军姜维领大司马,西征入羌中”[2],姜维西征进入秦州南安郡。正始元年(240),“蜀将姜维出陇西。(郭)淮遂进军,追至强(羌)中,维退,遂讨羌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1]735。郭淮在陇西打退蜀将姜维后,招揽3 000余羌人到关中地区,以充实关中地区人口。蜀延熙十七年(254),姜维攻破徐质,“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1]1064,姜维将这部分羌民迁至益州。十六国时期,羌人也多次被动迁徙。如太和元年(328),刘曜在洛西被石勒打败,其子刘熙率文武百官逃亡,当时武都、扶风和始平各郡羌人皆反叛响应刘熙。咸和四年(329),“石虎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3]2475,石虎率军在河西等地击败诸羌,并强制15万氐人及羌人迁徙至司州和冀州。建平元年(330),“秦州休屠王羌叛石勒,石生与休屠王的侄子擢共同击败休屠王羌”,石生击败秦州反叛的氐人和羌人,并“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3]2475。西秦政权统治期间,如建义二年(386),“南安秘宜及诸羌虏来击国仁,四面而至”[3]3113,羌人也不断主动或被动迁徙至秦州地区。由于西秦实施压迫羌人的政策,羌人多有反抗。元嘉八年(431),西秦灭亡后吐谷浑据有其地。总之,魏晋南北朝期间,羌人在秦州的迁徙活动较为频繁,主要群落是宕昌羌和邓至羌。
(三)雍州地区
魏晋时期,雍州的辖区大致是关中地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写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可见,自羌人内迁后,魏晋时期,羌人在关中人口中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三国鼎立时期,由于各割据政权实力相当,故各政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羌人迁徙的记载较少。晋惠帝元康六年(296),郝度元、冯诩、北地马兰羌以及卢水胡联合起兵,冯栩太守欧阳建被打败,北地太守张损被杀。同时,赵王伦“刑赏失中”,其亲信孙秀滥杀羌人数十人,导致羌人和氐人联合反叛。秦州和雍州等地的羌人和氐人也纷纷响应。直至元康九年(299),晋朝才镇压了叛乱,这次关中各族民众的起义使西晋统治阶级意识到处理民族矛盾问题的重要性。晋元康年间,自然灾害和战争不断,秦州和雍州等地的羌人和氐人等各族人口共10余万开始不断向蜀地迁徙。西晋政府出兵镇压,并下令让这部分民众返乡,这是关中羌族向西南进行的一次较大的迁徙。十六国时期,羌人多次随割据政权流徙,如石勒将“巴帅及诸羌揭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3]2728。前赵灭亡后,后赵政权攻占秦陇各地,石虎“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3]2745。大量氐人和羌人被迁徙到司州和冀州。东晋太元十一年(386),“苌自安定引兵会硕德攻统,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之者二万余户……九月,王统以秦州降于后秦”[4]。王统降于后秦后,姚苌“迁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3]2967。北魏建立后,雍州等地的羌人纷纷归降北魏。关中地区的羌人先后被刘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和北魏所统治,不断流转迁徙于各政权统属辖区之间。
(四)益州地区
据《西羌传》载:“秦献公初立(前384年),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5]2857魏晋以前,因秦献公开疆拓土,羌人为躲避战乱,大量南迁到了益州西北部地区,这些羌人属于河湟羌人一系。魏晋时期,北方政权更迭频繁,羌等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迁徙,益州地区政权也积极争取氐和羌等族的力量,如蜀汉施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民族政策。魏晋时最活跃的羌人生活在汶山郡,汶山郡统治羌人的行政建制非常严密。西晋初,汶山郡的羌人部分移居至成都平原附近的都安天拭山一带。西晋末年,李特集团进入汉川和茂县等地区,因其对羌人的统治政策较为温和,羌人迁徙较少。南北朝末期,羌人在益州不断发展,势力范围已经发展到益州西北部。
二、汉羌文化的双向互动
羌人大规模的迁徙致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等多种文明在不同地域内交往、交流和交融。下文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维度来考察汉和羌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政治维度
随着内迁羌人逐渐增多,中原王朝对羌族的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已经遍布青、幽、并和冀等州,中原王朝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内徙的羌人,继续设置护羌校尉等官职,但该官职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国时,“以(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1]739。《晋书》亦载:“秦州,魏始分陇右置焉,刺史领护羌校尉,中间暂废。”[3]435这一时期,羌人内迁规模越来越大,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管理羌人,护羌校尉之职开始由职权更大的州刺史兼任。此外,还设有典属国等地方民族管理机构。中央政府设置在羌人聚集区的校尉官职及其他管理机构的作用是巨大的,既巩固了中央政权在羌人地区的统治,又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加快了羌向封建化过渡的进程。羌族自东汉以来就开始随着各政权的更迭不断迁入中原,一直到西晋末年,羌族前后经历了汉、魏和晋王朝的统治,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已经发生变化,到后秦时已经趋于完全汉化。后秦的职官制度沿用了前秦的政治体系,包括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后秦在建都长安之后,中央官员的设置逐渐趋于完善,设置有相国、太宰和太尉等官职。到姚兴统治时期,中央管理制度已趋于完备。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设置了州、郡和县三级制。在军事制度上,受魏晋时期的影响,施行了兵户制度、“护军”制度和“持节都督”制度。后秦在选拔人才方面,也融合了汉、魏和前秦的制度,主要采用察举征召与考试拔擢相结合的方式。姚兴继位之初(396)就下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3]2977,其后又“命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3]2984,可见姚兴时期继续发展察举制度。在十六国中,后秦属封建制度体系比较完备的国家之一,基本上已成为吸收了汉文化的封建政权。
(二)经济维度
汉羌交流促进了中原王朝边地经济的发展。从东汉年间开始,内附巴蜀地带的羌人逐渐增多。这些原本属于游牧经济体系的少数民族逐步进入农耕地区,为了充分利用羌人力量,蜀地当时设置了专门管理羌人的机构,用以管理羌人矿产开发和牛马饲养等;羌人开采的铜铁等是制作兵器和农具的重要原材料;羌人放养的牛羊是生活的日需品;羌人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蜀地的开发和发展,影响了中原边地经济的发展;羌人的生产方式也逐渐发生转变,羌人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三国志》载:“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1]734可见,关中地区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存在羌人自耕农。《后汉书》中的记载证实河西地区羌人逐渐转化为自耕农,“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硷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5]267。这是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对该地征收田租和口赋的规定,说明该地区自耕农和中原一样需要缴纳田租和口赋,羌人原有的原始社会式的组织结构逐渐解体,逐渐走向汉化道路。后秦政权统治期间,“有计划的徙民近二十次,迁徙的人口粗略估计约有二一万户左右”[6]。后秦君主之所以将大量人口迁入相对稳定的关中地区,主要还是为了发展该地区农业。此外,姚襄屯于盱眙时曾“招徕流人……劝课农桑”[3]2979。后秦政权采取一系列发展农耕文明的措施,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融合,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断更新,中国北方的农耕文明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迈进。
(三)文化维度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大迁徙,羌人文化逐渐影响到了中原民族。在早期民族还未大融合之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还保持着各自的传统。正如《博物志》所云:“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膻焦也”[7]可见胡汉民族生活方式差异较大。胡族的饮食加工方法主要是炙与炮。《搜神记》卷七载:“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泰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8]羌族最引以为傲的美味就是“羌煮貂炙”。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民族杂居,胡汉食物加工方法逐渐融为一体,魏晋时“羌煮貂炙”已经在社会中相当流行。《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牛马羊等牲畜的饲养方法、兽医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其中很多技术和方法都来自羌族。羌人的畜牧业生产技术、牲畜品种以及一些农产品在迁徙过程中随之传入中原地区。羌是游牧民族,羌人的饮食也以牛肉、羊肉、乳和酒为主,这也影响了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在迁徙过程中,羌人的生活方式等也发生转变。《魏书》称:“牧养犛牛、羊、豕以供其食。”[9]由此可见,早期的羌人饲养牛羊等为食,还没有发展农业。内迁之后,羌人的游牧文明逐渐发生变化。《西羌传》记载,护羌校尉贯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收羌禾稼”[5]2883。可见,到了汉朝时羌人的农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可收获大量小麦。到后秦政权时期,《晋书》载:姚兴“自安定如泾阳,与(苻)登战于山南,斩登。散其部众,归复农业”[3]2976。羌人内迁后,逐渐接受和发展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水平越来越高,他们到关中后已经谙熟农业生产之道。此外,羌人的宗教信仰等均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旧唐书·党项羌》言:“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10],可见党项羌最初保持着原始的崇尚天神等宗教信仰。内迁之后,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羌族逐渐接受和信仰佛教,特别是北魏灭后秦后,在北魏统治下,很多羌人信仰佛教。
三、汉羌农牧交融的思考
人口的频繁迁徙促进了地域间的互动与发展,加速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
(一)融合是汉羌民族发展的主线
伴随迁徙,汉羌民族间的正统观念、家族观念和习俗道德观念等逐步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族大规模的迁移活动推动了地区民族的多样性,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生活环境。居住格局发生变化后,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羌文化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汉文化也随着羌文化的融入而转变。自东汉以来,羌人虽迁徙至关中地区,但仍保留自己的部落组织,没有改变聚族而居的状态。直至西晋末年,羌族部落仍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部落组织逐渐被破坏,羌汉杂居,各族的语言风俗、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相互渗透影响,羌族逐渐接受中原先进物质文明,最后认同华夏文明。匈奴、羌和氐等少数民族都相继建立过政权,北方汉族地区相继出现过十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羌族几乎有着跟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与汉族长期接触后,少数民族开始主动接受农耕文化,有意识地吸收和学习中原文化制度。北魏孝文帝统一北方后,极力推行汉化政策,使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发展程度更高。
(二)汉羌交融具有阶段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补充兵员和劳动力,经常招抚和强迁氐和羌等族入居中原,内迁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频繁接触。由于民族间具有差异性,民族交融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起初,由于汉羌生活习惯有较大差别,羌人仍保持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因此汉羌融合过程中出现隔阂。汉族统治者往往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和剥削政策,如在凉州汉羌杂居地区,“受方任着,又非其材……侵侮边夷……妄加讨戮”[3]1444。各级官吏肆意掳掠羌人,导致民族间产生冲突,进而引发民族矛盾。西晋末年,许多少数民族开始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少数民族为了适应中原地区新的生存环境,主动接受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学习汉族文化、重用汉族世家、崇尚儒学和劝课农桑等,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也随之缓和。北魏统一北方后,统一了政治制度和赋税制度,学习中原传统文化,消除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在生活习惯和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差别。随着汉羌民族的杂居共处,民族间文化上逐渐产生认同。文化认同推动“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加快了农牧文明的融合。
(三)“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必然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1]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形成对流态势,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出现了多个政权分裂和对峙的局面。汉族和羌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皆呈现新景象。政治上,中原民族对羌人管理方式发生转变。中原王朝为了管理诸多羌人,不断完善对羌族的管理体制。经济上,羌族不再“所居无常,依随水草”[5]2896,逐渐向定居演变。文化上,羌族建立后秦政权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推行儒学教育,向“华夷同风”转变,丰富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碰撞,双方互相吸收彼此的文化精华,使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频繁,推动了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相互交流。汉羌民族接触过程中,羌族在不断吸收汉文化之长的同时,还保留了本民族特色,并对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呈现出思想文化双向互动的交融发展趋势。民族间文化相互交流,促进了民族的重组与融合,双方向具有越来越多共同性的方向发展,增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各民族间的认同感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评《产品包装设计( 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