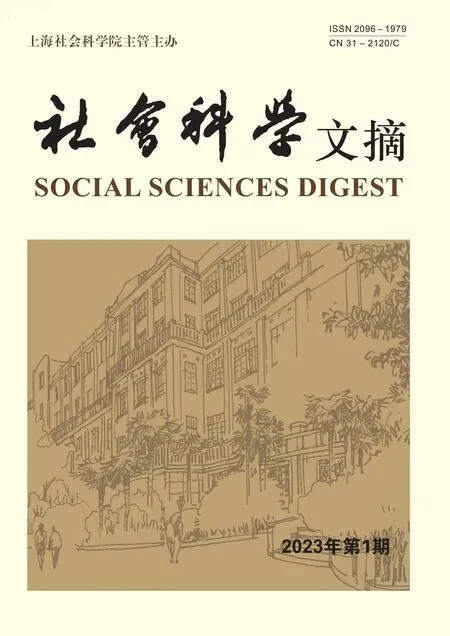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神思”范畴的译释
文/戴文静
20世纪以来,在西方文论话语垄断的世界文论场域中,如何有效彰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成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中亟待探究的主题。由此,探赜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在世界语境中的译释,检视理论“他者”与“自我”的跨语际对话,成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
“神思”是中国传统文艺构思论的重要范畴。东晋玄言诗人孙绰在《游天台山赋序》中曾提及他写天台山赋时的“驰神运思”状况。南朝刘宋时期,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从绘画创作视角分析了神思活动。西晋陆机在《文赋》中也对其做了生动的描述,但直至刘勰,才正式将“神思”作为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使用。他将“神思”论视为创作论的首要问题而作专篇论述,这是前所未有的。《神思》因此受到国内“龙学”界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神思”因与西方艺术想象和虚构诗学存有潜在关联,也倍受海外学者关注。然而,要实现国学与汉学双向有效的互识与互通,有必要由“神思”英译辩难的交锋处切入,通过探赜其所夹缠的意义踪迹及内在逻辑,澄明译释中的“误读”。
《文心雕龙》范畴“神思”英译引发的学术思考
“神思”在《文心雕龙》中共出现三次,均在《神思》篇内。首先,考察关涉《文心雕龙》“神思”范畴英译的13部文献:施友忠、黄兆杰和杨国斌的三部全译本(以下分别简称“施译”“黄译”“杨译”);杨宪益、戴乃迭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节译本(以下简称“杨戴译”和“宇文译”);刘若愚(James J.Y.Liu)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以下简称“刘译”);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以下简称“梅译”)、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和张泰平(Taiping Chang)主编的《东方学手册》(Hand Book of Oriental Studies,以下简称“康张译”),以及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邵保罗(Paul Yong-shing Shao)、赵和平(Heping Zhao)、李敏儒(Minru Li)和马劲松(Jingsong Ma)的博士论文(以下分别简称“吉译”“邵译”“赵译”“李译”“马译”)。
接着,辨析英语世界的译解分歧。从语义结构而观,主要存在复合、偏正、并列三种译解。三个译本(梅译、杨戴译和杨译)将“神思”视为复合词,征用西方概念进行整体迻译;另有七个译本(施译、黄译、刘译、吉译、邵译、赵译和马译)将其译解成“神”修饰“思”的偏正短语,主要有三种表达:Spiritual thought, Spiritual mind和Intuitive thinking;此外,三个译本(康张译、宇文译和李译)分取“文之思也,其神远矣”之意,硬译拆分“神”“思”二字,以Spirit Thought这两个并列名词译解“神思”。从语义内涵而观:“神思”应合而论之,整体译为“Inspiration”(灵感)“Fancy”(幻想)还是“Imagination”(想象)?或者分而解之,“神”应译为“Spirit”(精神)还是“Intuitive”(直觉)?“思”应译为“Thinking”(思索)“Thought”(思想)还是“Mind”(心理/心灵)?以上英译是否合理?哪些是正解?哪些又是误读?
为此,本文将以上英译分歧进一步归结为两大问题:第一,“神思”的语义结构应为复合、偏正还是并列?第二,如何定义“神思”的语义内涵?下文将从语义结构和语义内涵两个维度澄清“神思”义界,分判译释。
“神思”语义结构的义界阐析及译释分判
“神”是“神思”的核心。《文心雕龙》中“神思”之“神”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限定“思”,将其定性为内心的精神活动;另一方面,它暗含“思”具有奇妙、深不可测的魔力特质。正如钱锺书所言,“神”有二义:“养神”之“神”,乃神之第一义也。而谈艺者所谓“神韵”“诗成有神”“神来之笔”,皆指《文子·道德》所谓上学之“神”,即神之第二义。事实上,“神”的这种双重性正是英语世界各类译释“神思”语义结构分歧的焦点。刘勰在《神思》篇中主要论述的是“神”的第二义,即艺术构思的形象思维活动。但他也并未忽略“神”的第一义。他认为创作者只有在神气旺盛、精力充沛之时,才可能进入神思的审美高潮阶段;如精神过于疲劳,情绪低落或气衰力竭,则无法进入。针对“神思”的不同阶段,刘勰的观点也各有侧重:在论述“神思”运行前提时,他坚持“形神并重”,认为“神思”不可脱离人的精神而独立存在,人的形体对精神有决定性作用,需以“气”养“神”,这时取“神”之第一义。而在论述神思运行的审美机制时,他赞同“重神轻形”,强调神思运行时,有超越形体之外与天地之神合为一体状态,即“精义入神”,这时取“神”之第二义。由此可见,“神思”是创作者“顺乎自然”的归依体验和“无远不至”的高峰体验的融合体。
“神思”之“思”含有“诗人之思”和“诗思之发”两个层面。前者指诗人创作前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形象思维密切相关;后者与“取境”有关,涉及诗人之“思”所产生的具体之“气”在体内的运行,以及化为具体的语言文字和节奏旋律,直接影响作品的风格体貌和高低优劣。因为“神思”之“思”虽以论述“诗人之思”为主,但也关涉“诗思之发”,涵盖以上两个层面。综上所述,涵涉艺术思维全过程的“神思”包含上述“神”之二义和“思”之两面。
反观英语世界“神思”的译释,康张译、宇文译和李译均采用并列结构译解“神思”。李敏儒认同宇文所安的译法,指出这里的“神”为主语,“思”为谓语,“神思”的语义重心落于“思”上,强调“思理为妙”,将“神思”视为一种居于形体之内,且与西方形象思维或想象相类的精神活动。然而这只能表达出“神”之第二义和“思”的第一层含义,无法涵盖广义“神思”所指。采用偏正结构的施译、黄译等七个译本表达的语义重心落于“神”上,通过以“神”饰“思”,呈现出“思”之“神”性,基本抓住了“神思”的语义重心。因为“‘思’与‘神’是二而一的,‘思’就是精神的思虑活动,也就是‘神思’”。事实上,受刘勰“擘肌分理、唯务折中”有机论创作思想的影响,广义“神思”涵括人的精神现象和思维活动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就语义结构而论,广义“神思”译释为偏正或复合结构都是相对合理的。
“神思”语义内涵的义界阐析及译释分判
“神思”这一范畴,意在分析审美意象的创造过程。狭义而言,它主要论述艺术思维过程中的想象活动及其特征,即“神与物游”。广义而论,则是指整个艺术思维过程。首先,文思应注重外物感应。这里“感属于外物,应属于内心,所以一方面要积学、酌理、研阅、驯致;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内心的虚静,俾能随时应物”。因为虚静是“神思方运”的前奏,而“积学储宝、酌理富才”是保持虚静的致力之方,“研阅穷照、驯致怿词”是保持虚静的加工之法。如《神思》篇所言,创作者只有“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保持虚静状态,才能调畅其气;只有当创作者处于“气足神旺”的最佳精神状态,“神思”才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狭义的“神思”是指“神与物游”。它涵括“物感”说和“情观”说,是“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在创造中情感运动的双向展开。它既需以物为主的“随物宛转”,也需以心为主的“与心徘徊”;既要强烈情感向物象渗透的“情往似赠”,也要运用理性自觉对物象进行虚构创造的“兴来如答”,是物我融合的统一体。其间创作者的感情移出与移入同时进行,主观性情和客观自然冥合无间。而广义的“神思”则并非纯粹“游心内运”的心理现象,它还与客观现实生活有着必然联系。“神思”是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通过“辞令”的驱辞遣句得以呈现。由此可见,“神思”经由形内的准备、构思和形外的表达构成,是由“实在之物”推及“虚构之意”再到“征实之言”的过程。《文心雕龙》中“神思”范畴当取广义,是一个融合了形内、形外、虚形、实相、主观、客观、感性、理性等诸多要素的有机整体。
厘清“神思”的语义结构和语义内涵之后,反观英语世界译释场域中“Inspiration”(灵感)“Fancy”(幻想)“Imagination”(想象),哪个词与“神思”本义更为接近呢?
首先,辨析“神思”与“灵感”(Inspiration) 的异同。通过分析可知,“灵感”只是想象活动的一种能力,类似于“神思”中的“情会”,但并不等于广义的“神思”。梅译以“灵感”译解“神思”,易使读者产生以偏概全的误读。
再辨“神思”与“Fancy”(幻想)的异同。事实上,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神思”与“幻想”都有很大差别。首先,创作者在“志气”和“辞令”这两个要素上的总体表现趋于稳定。相对而言,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和情感两要素则总是处于常变状态,因为不同情境所引起的情感总是不同。因此,“神思”的过程包含变与不变两种因素,这与“幻想”只接受基本图像的机械过程相异。其次,“幻想”的对象是虚构的,而“神思”却明确要求创作者在“积学储宝、酌理富才、研阅穷照、驯致绎词”这样“博练”的基础上“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由此可知,杨、戴的“幻想”之译与“神思”本义相去甚远。
“神思”是否等于“想象”?事实上,“神思”与“想象”相类,但不完全等同。两者相通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神思”之“思”不仅含有传统意义上思维、思索之义,还具有神不可测、万能神通的特性。后者可使创作主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想象力的发挥是在对象不存在的情况下,直观对象的现实存在。就此层面而言,“想象”与“神思”相类。第二,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传情达意,无论“神思”还是“想象”都有强烈的情感参与。
两者的差异在于四个方面。第一,“神思”直接关涉当下经验;而“想象”的发生是即兴选择经验元素并加以非理性的任意组合,非直接关涉当下经验。第二,“神思”侧重心物交融与应和,通过明心见道,还原自然道体世界;而西方浪漫表现论则强调“想象”是心灵的创造性功能,它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第三,“为文用心”所进入的心物情境关系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即“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一元宇宙观是一致的;而“想象”则建基于二元宇宙论基础之上,处于对立事物间的张力之中。第四,“神思”具有“神与物游”的自然性和自发性,因此,“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而“想象”必须通过心灵的力量,来克服主客对抗和物物对抗得以重新创世,具有人为性。“神思”不能与“想象”等量齐观,前者的外延明显大于后者。神思包括“神与物游”和“意与言会”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指物的意象化,后一阶段指意象的语言化。而“想象”的发生仅集中于前一阶段。
英译世界“神思”译释误读背后的学理反思
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译者,大多数处于低语境交际关系中。他们先天具有与目标读者文化背景相近、文化语境差异较小的优势。他们信任读者的接受能力,译释时无需进行跨文化想象,也不必以更多的信息填补目标语境的不足。为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间的差异,译释时他们往往采取迻译的文化策略。如此,“译”的成分远超“释”;相较之下,处于高语境交际关系中以英语为外语的华裔译者,寻找与目标读者共同语境的难度更大,为取得理想化的接受效果,他们只能在自身知识辖域内对预期读者作跨文化想象和语境建构。较强的交际欲求使他们具有更强的解释倾向,更重视目的语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准确性及规范化,力求译本在风格和结构上趋近目的语文化。因此,他们更多地采用解释性翻译策略,如此,“释”的成分远超“译”。当前汉学研究已从纯翻译走向了翻译的后世,即译释结合的文本细读研究。因此,上述两类译者在方法论上应相互补益。
此外,为减少译释所产生的误读,译者应避免直接征用西方概念,这种文化简化主义的操作会使“神思”的特殊语境一般化,进而使其演变为西方范畴的一种低劣变奏。广义“神思”是“由多种含义构成的场域,任何一种含义都可以成为这种诸多含义所构成的场域中的一个焦点。因此,要规避西方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单义性阐释,跳出怀特海所说的‘完美词典谬误’的窠臼”。尊重中国文论范畴的语境多义性,尽力接近范畴本义及其逻辑关联,采用语境化译释法即音译(Shen-si/Shen-ssu),使广义的“神思”原型得以再现。与此同时,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采用多重定义加以译释,如用“Daemonic/Intuitive thinking”这样涵涉广义“神思”的“神与物游”与“神用象通”两个阶段的译释,使“细目在场”,以还原“神思”本义。
反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海外译释,充满了主体对话的学理选择和价值省思。“神思”译释关涉中西文论话语体系内脉,其中因选择性接受而产生的“误读”既是两种文论体系张力中的摩擦焦点,也是其异域接受过程中的典型症候。通过对这些焦点的研判与反思,窥见其后隐蔽的深层逻辑理路:这种选择性接受所遮蔽的是西方“以世界为方法,中国为目的”汉学研究途径,即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归根结底这样的“世界”还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英语世界。后理论时代,应“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将中国和欧美视为多元世界的构成要素,摆脱“西方为方法”的囿限,用中国的材料研究中国的思想,以中国传统言说方式音译其名,并尊重其内在逻辑,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采用多重定义加以译释,才能更为精准、全面地把握其内涵,以此反向启益中国文论海外传播,有效深化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本土建构及海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