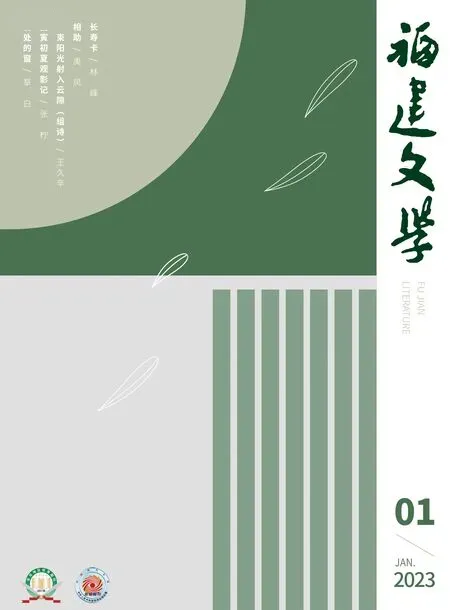致敬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
——读汤伏祥散文集《过往》
潘新和
恋旧与怀旧不同,怀旧跟年龄有关,恋旧则未必与年龄有关,多是一种秉性。《过往》所写旧事,不是怀旧,而主要是恋旧。论年纪,伏祥刚跨进中年门槛,怀旧还早点;恋旧无论早晚,即使小孩也会恋旧。恋旧之人多重情。
伏祥上我的写作课,距今已27 年。他喜欢写作,在同学中算是佼佼者,小有名气,但在校时我与他交往不多,认识而已。他毕业后我们倒熟络起来。他年节时常来探望,茶不喝,水果不吃,就坐坐聊聊,这么多年从未间断。大老远的,叫他别来,微信问好就成,他不听。有事请他帮忙,不论办得到办不到,总想方设法、竭尽所能……还有他工作之余仍坚持写作,出版了好几本书,让我这曾经的写作教师感到欣慰,从而更拉近了心理距离。我从教几十年,素有联系的、亲近的学生不少,像他这般重情、贴心的不多。
伏祥重情,恋乡便顺理成章。他来自农村,《过往》所写多家乡旧事,可视为恋乡之作。他读初中就已离家寄宿,后来读高中、大学,工作,离乡渐远,在福州已二三十年,早成“城里人”。令我惊讶的是,他的“过往”仿佛时光倒流,倒流到与我竟无代差。我大他二十多岁,我经历的他知道,我没经历的他也知道。他对家族、家乡往事的了解,似与年龄不相称。
他笔下所谓的“过往”,说自己的很少,多是前辈、亲朋的。不知他怎么了解那么多陈年往事,有“十八岁见二十四代”(福州俗语,意在嘲讽“小大人”,此处反话正说)之感。除了自家外祖父、祖父、叔祖父、姑婆、堂曾祖、三太婆等,连邻居、发小的家人(见《三个女人》),地主、长工、寺庙住持、教徒、乞丐、疍民、酒鬼、热血青年、工艺美术师、残障人士,都在他的视野内。连他工作后的家乡事,他也了如指掌,这大大出乎我意料。我为纪念先父写过家史,对父母已觉所知甚少,遗憾颇多,写祖父更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深知追溯“过往”不易,何况叙谈百味人生。我在闽北“插队”多年,按说对农村也不陌生,但说实话,像《过往》这样的书我写不出来。
我一向觉得伏祥不擅交际、不善言辞,看来这是偏见。他少小离乡,农村孩子的秉性依旧,质朴、腼腆、谦卑,无伶牙俐齿,亦非“自来熟”。重情义自有好人缘,于亲朋故旧,想必他是另一副讨喜模样,这也是一种天赋。在《三个女人》中他写道:“这三个都上了年纪的老女人是一家人,是我发小的亲人。小时候,我常常在她们家玩耍,与她们熟悉得很。也不知道是不是性格所然,我小时候就十分喜欢与老人交谈,听他们讲过去的时光、过去的故事。”一个小娃喜欢与别人家的祖辈交谈,这种“忘年交”是不是很神奇?这只有一种可能,他很可爱、懂事,在乡人眼里是好孩子、好听众,直到长大成人,仍心意相通。偶尔回乡探亲,故情犹存。随便串串门,树荫下,小板凳一坐,眯眼憨笑,无须开口,便能听到熟悉的掏心窝的娓娓絮说——这是对他恋旧的回馈,《过往》是他对乡亲的反哺。
恋旧,是就其表层心理而言。就其深层心理看,是对底层人人生的悲悯。他写的多是农民,哀其不幸,悲其苦痛,感同身受,他与他们有天然的心灵感应,始终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的家乡是闽东福安一个不起眼的临江濒海村落,吉光片羽的日积月累,给它以丰厚蕴蓄与时空纵深。他不用刻意于宏大叙事,散点透视、移步换景、交错比对中就能折射出光阴流徙中的人生际遇、时势兴替、命运浮沉。土地、家族、苦难、死亡……这些世代沉淀的意念,植根于作者的精神血脉,构成乡村文化的景深。在农村,土地便是一切,是农民的梦想,是他们养家糊口、立足社会之本。但土地梦带来的并不都是财富、荣耀,在社会转型、家族矛盾、生存竞争等冲撞、磨难中,难免有人身与时舛,走向没落与死亡,为推陈出新献祭。伏祥作为农家子弟,对农民生存处境、困境深有感悟,浓烈的故土情愫赋予他沉郁、悲楚的文格。
赖以为生的土地,是中国农民的梦。“我常常想,在中国农村,那些最朴素的农民,默默地把自己奉献给了土地,他们勤勉而又不失机敏,朴素而又不失梦想,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是什么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守护大地,让他们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死?也许是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因子给了他们力量,给了他们对土地的赤诚之心。曾祖父经过自己的努力也有了不少田地,这是他引以为豪的,也是祖父、叔祖父为之珍惜的。”(《愿他远行时有诗书》)这个梦,是他的曾祖父、祖父、叔祖父的,是地主的,也是雇农的,总之,是全体农民的,一做几千年。为了这梦,他们孜孜矻矻、吃苦耐劳,交替扮演各种角色。经历了20世纪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追求的土地梦不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这一切似乎戛然而止。但人活着就得吃饭,土地情结就还在。总有人始终心系土地。“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死”,是过往农民的宿命。如今,土地情结渐消,越来越多的人离乡谋生。千年土地致富梦在未来会怎样,是伏祥留给我们的思考。
土地梦,让农民为土地而生、而死,是昔日农耕文化的动能。靠田地生存繁衍,创造美好生活,需强壮劳动力。男丁,是强壮劳动力的接班人,也是维持家族存续、兴盛的源泉。本书中专门谈到“顶祠”,我首次看到此词,顾名思义,以为是指祠堂里可顶门立户、接续香火的人。看来我的理解不完全对。《顶祠》中是这样阐释的:“顶祠,这是个生僻的词语,在字典里估计是找不到的。但这个词,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村里人讲起,或者说它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是祖祖辈辈绕不开的字眼。我的父亲就‘顶祠’给了我的叔祖……顶祠就是过嗣。”中国人讲究传宗接代,有的人是为了福泽绵延、光宗耀祖;但急需劳动力的农村,如果没有男丁,意味着田地无人耕耘,土地梦的终结。该文结尾:“他们顶祠来顶祠去,无外乎就是留了个名字在族谱上而已,或者说,再久远些,谁还记得这些呢?”这表明伏祥已解迷局,有所开悟。城乡界墙已坍塌,农村迅速城镇化,既无须以田地为生,传宗接代观念亦随之淡化;城市少子化,甚至不生育——随着农村向着城市的移民潮的到来,顶祠,以至宗祠、族谱会消亡否,这是伏祥予我们的又一个思考。
农民命运与土地深度捆绑,他们的喜怒哀乐,寄寓于土地。但土地带来的欢乐不少,苦难也不少,因而,表达对底层生存的同情、悲悯,成为《过往》的主旋律。“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不过是士大夫对田园生活的诗化憧憬,自我陶醉的幻象。在过往的农村,“桃花源”是缺失者的奢望。
从土地获得回报,并不取决于付出——甚至不知将获得什么,这就是土地梦诡异之处。诚如《三个女人》中所说:“她们的丈夫这辈人,甚至更远的祖上,有了积蓄,能想到的似乎只有购置田地,仿佛只有有了田地,日子才算富有,才算安稳。但谁能想到,这反倒让他们尔后承受了人生的悲苦呢!”世事轮回、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极而衰,也许这就是“天道”。
伏祥书写农村生活,或是受潜意识驱使。农民,是社会中的基础阶层。他没当过农民,但在田间劳作过,耳濡目染,对农家最为关切,不吐不快。
死亡最难写,伏祥对写死亡“情有独钟”,他的不俗想象力可见一斑。想象中有哲思,是伏祥的追求。如果说同情苦难是小慈悲,那思考死亡则是大悲悯。他的叙说,几乎篇篇有死亡,各种“死亡”纷至沓来。农民,是最应给予临终关切的群体,伏祥的书写,便是为了唤醒这种关切。
生来干脆,死时怎么就这般折磨呢?大姑婆生命最后的几年,她是否懊悔我不知道,但她定是责备那口气息怎么就老在她的咽喉打转,让她经受这样的折磨,让她体味如此的苦楚呢!(《姑婆》)
生来干脆,死时受折磨,这是人皆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一。上苍不公,好生难死;苦难至死方休,苦难过后是解脱。这是上苍的“好生之德”吗?又或是对苦难的补偿?“好死不如赖活”其实未必,我认同“赖活不如好死”。伏祥借大姑婆的心思,说出普遍的人生悲情:生不由己,死也不由己。
他坐在木椅上,垂老得像厅堂里的大钟。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儿子搬来了这么一个大钟,说是外面买来的,属于有些年代的货。那可能是一种安慰,在这样一座乡下的木屋中,放上这么一个老钟,似乎是搭配的,但显然,他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儿子告诉他,偶尔可以看看大钟,有点时间概念,但他觉得无所谓时间了,大钟准与不准,都无所谓了,不就是消耗多余的时光吗?(《欠情》)
以老钟类比老人,极为契合,堪称神来之笔。儿子买来老钟,也许一是出于孝心,二是贪便宜,能省则省,系农家节俭美德,三是心想垂老的父亲用不着知道精确的钟点。不想歪打正着,这老钟正好触动了父亲此时此境的心弦。时钟是生命力的隐喻,人生与时间息息相关。濒死之人,生命之烛将熄,将与时光合一,化为永恒,因而无所谓时间准否,只是等待,等待生命之钟停摆。老钟失准而隐喻精准,贴切地刻画出临终者心态。
写死亡,难在死者无语,生者未知;逝者长已矣,生者要面对,死亡是人生最后一道坎。因此,写死亡,写各种各样底层人、普通人的死亡,是临终关切、终极关怀,是大悲悯。康德曾说,想象是“主观的重生”,“无目的而合目的”。苏轼评柳宗元《渔翁》诗时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在超验状态,凭主观拟测写死亡,而且试图有哲思——“合道”,这需灵性、智性想象力。这是难以企及的,而伏祥已显示出他的潜力。
读罢掩卷,一幅幅久违的农村图景栩栩如生。时代在进步,农村已脱贫,正步入衣食无虞的小康社会,伏祥给“过往”立此存照,无疑将给年轻一代颇多启示与警醒,让他们懂得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福祉,努力为后世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本书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