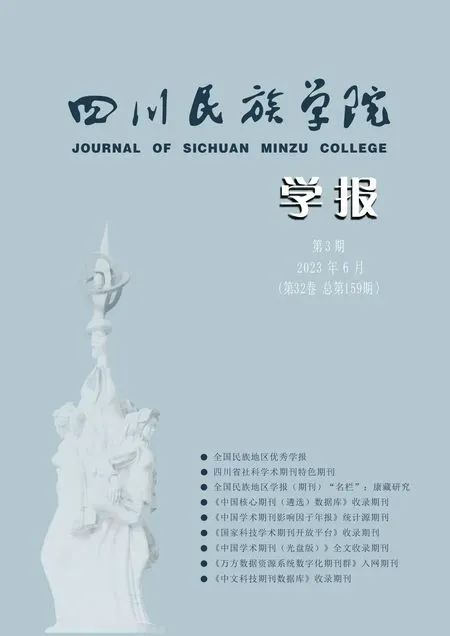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的艺术特征
王庆贺 王 潇
(①湖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恩施 445000;②中南民族大学,武汉 430074)
在清水江流域,苗、侗、汉等众多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特殊的区域文化。最直观的表现便是苗、侗等民族的刺绣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交融痕迹。如在苗、侗等民族的传统刺绣中存在许多共同的技法和纹样,从而形成共同的视觉形象符号。不过,受自然、历史、贸易等因素影响,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为施洞型、凯棠型、西江型、柳富型等多个刺绣类型,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苗族民众通过一系列繁琐而有序的工艺,绣制出具有浓厚民族性特征的刺绣作品,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内化为苗族刺绣的基本特征。
一、清水江流域苗族及其刺绣工艺概述
在清水江流域,有大量苗族聚居,其先民由湘西沿沅水上游的清水江进入贵州地区[1]。山水的阻隔和环境的差异造就了苗族群体内部语言、服饰、习俗的差异。当地苗族的住房以干栏式建筑著称,房屋整体被分割为堂屋、火塘、卧室和圈舍等多个功能区。当地曾盛行“姑舅表婚”的习俗,即舅家儿子拥有优先娶姑家女儿的权利。该地区的传统社会制度以“议榔”为核心,“理老”“寨老”“议榔”和“神明”四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制度分支构成了当地的制度文化体系,是苗族社会调整人际关系的基础和柱石。
清水江流域苗族的文化丰富多彩,不仅有《古歌》《开亲歌》《刻道歌》等歌文化,还有板凳舞、芦笙舞、斗牛舞等舞文化,亦有剪纸、织锦、银饰、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该区域还流传着《苗族史诗》《贾词》《议榔词》《民间故事》等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此外,当地还有春节、祭桥节、姊妹节、四月八、吃新节、鼓藏节、苗年、芦笙节等种类繁多的传统节日。清水江流域盛行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的传统,其中枫树、蝴蝶、葫芦、姜央等形象表现了清水江苗族民众浓厚的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当地苗族又通过剪纸、刺绣、银饰等传统手工艺表达其文化心理。
在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按照技法、纹样等方面的差异分主要有施洞型、凯棠型、西江型、柳富型等刺绣类型。其中施洞型苗绣以台江县施洞镇为中心,该类型刺绣以破线绣技法著称,纹样多与蝴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民族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凯棠型刺绣以凯里市凯棠镇为中心,该类型刺绣工于打籽绣、堆绣技法,纹样多反映当地“蝶母崇拜”的观念。西江型苗绣又分为台拱式和雷山式,其中台拱式刺绣以台江县台拱镇为中心,该类型刺绣以辫绣为主要技法,纹样多为龙凤、蝴蝶等吉祥图案;雷山式苗绣主要分布在雷山地区,该类型刺绣主要使用邹绣技法,纹样与台拱型大致相同。柳富型刺绣以剑河县柳富村为中心,该类型刺绣以锡绣著称,纹样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并通过抽象的几何形进行呈现。
在清水江流域,刺绣不仅是实用的艺术,亦是苗族民众审美情趣的表达,同时也发挥着仪式的功用。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还拥有独特的区域性特征,其刺绣艺术是再现性与表现性的结合,是具象与抽象的共用,刺绣创作讲求整体观念,纹样主题呈现生活化特征且各民族、各类型刺绣纹样表现出明显的互鉴与共享。
二、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对再现与表现结合艺术原则的体现
再现与表现是艺术呈现的两种方法,再现是艺术品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表现则是艺术品对艺术创作者的主观情感与意境的表达。弗思认为:“艺术品是人类经验、想象或情感的结晶。艺术品的形式表达和处理,能够唤起我们特有的、以审美情感为基础的反应和评价。”[2]田自秉认为工艺美术不同于绘画等艺术,绘画以再现为其艺术手段,工艺美术则以表现为其艺术手段,表现特定的艺术情趣和格调,即表现创作者的精神世界。[3]两人都更加强调艺术,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表现性。不过,对艺术品的品鉴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再现或表现,而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作为手工艺术的代表,中国传统刺绣工艺是写实与写意艺术的集合体,即表现性与再现性的统一。刺绣的纹样选择及技法运用,都是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有意识之结合。尤其是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工艺是集体情感、价值观念与创作者自身审美情趣的反映,是刺绣创作群体主观意识的物化形态,因而具有很强的表现性。同时,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中有大量纹样源自客观现实,是日常生产、生活及自然物的忠实反映,因而包含着再现的客观现实成分。
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纹样中包含着真、善、美的美好意念,是刺绣创作主体内心原始本能的向往与表达[4]。清水江流域的苗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着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英雄人物崇拜的传统,特别是对枫木树、蝴蝶妈妈、鹡宇鸟、水牛、祖先、张秀眉、务冒席等充满敬仰与赞美之心。苗族刺绣中大量使用蝴蝶妈妈、鹡宇鸟、枫树、张秀眉、务冒席等纹样,实质是对该区域内苗族民众信仰观念、崇拜观念的物化表现,是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表现性特征的直观体现。甚至苗族刺绣中还有姜央、雷公等人物形象的刻画,这是苗族绣娘们依据《苗族古歌》、苗族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资料所进行的纹样创作,是对清水江流域苗族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资源的符号提炼与我在表现。表现艺术追求朦胧抽象的情调和意味,因而十分注重形式美。即各种形式因素的有规律组合,形成某些共同的特征和法则,包括色彩、线条和对称结构等。[5]清水流域的苗族刺绣对色彩的搭配、纹样的选择和纹样结构的设计都十分注重形式美。尤其是施洞地区的用于装饰苗族盛装上衣的刺绣,更是有着严密的结构和精巧的纹样搭配。
同时,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与当地苗族同胞的生活关系密切,是当地苗族民众日常生活的再现。作为民间传统手工技艺,苗族刺绣所表达的主题通常围绕着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因而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中,不仅有大量折枝花、鱼、鸟、蝴蝶等写实动植物纹的使用,还有对日月星辰的客观表达,甚至还有田间劳作(耕牛图)、接亲婚嫁等生活场景的记录,体现了浓郁的写实性和地方性特征。
不过,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的再现与表现之美是互相离不开的。绣娘们通过表现性纹样和再现性纹样的搭配,使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呈现出再现与表现的和谐之美。
三、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对具象与抽象共用艺术原则的体现
具象与抽象是艺术创作中常用的两种表现手法。具象艺术是指艺术的形象与自然对象基本相似的艺术,抽象艺术的形象与自然对象的外观偏离。具象艺术中的艺术形象具有可识别性,如近代兴起的写实主义和超写实主义艺术,其作品的外部形象都与自然对象相似。具象艺术的表达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的工艺美术作品中。如欧洲原始岩洞壁画、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壁画。再如中国敦煌莫高窟的岩洞壁画,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石雕造像,中国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等,都属于具象的、写实主义的艺术珍品。抽象艺术则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有精神地张扬。西方现代抽象艺术并不主张“再现现实”,而是从客观现实中抽取精神意义,使用平面几何图形以及各种不规则形状的组合,形成“不可视”的画面主体[6]。黑格尔认为所谓的抽象应分为具体的抽象和抽象的抽象两种。具体的抽象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抽象的抽象则意味着从一个对象中抽取出它与意识的一切联系,抽取出一切感觉印象以及特定的思想后所剩下的东西,这无异于完全的虚无。[7]
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艺术中,有大量具象纹样的运用。当地苗族刺绣中有大量源自苗族日常生活的喜鹊、蝴蝶、梅花、折枝花、鱼、鸟等纹样使用,是对自然物的写照及对生活的记录。并且,在具体的纹样造型中,刺绣艺术的创作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们运用最精美的工艺技法,最切合的刺绣原料,力求所得图案的活灵活现。同时,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中亦有大量基于自然物的抽象图像(即黑格尔所说的具体的抽象)和高度抽象的几何纹,甚至还有一些臆想的纹样造型。如鹡宇鸟的图像造型是基于日常生活中公鸡的形象进行的艺术创作;再如苗绣中大量牛身龙、蛇身龙、蚕身龙、鱼身龙、狮体龙、双体龙、叶身龙、花身龙、鱼尾龙、马尾龙、牛角龙、凤头龙、鸡头龙、蜈蚣龙、人头龙等众多变形龙纹的使用,实则苗族刺绣艺人将心中的龙形象与生活中众多动物抽象、融合的结果。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中的几何纹样同属于刺绣艺术的抽象化表达。当地苗族刺绣中,既有三角形、四方形、十字形、米字形等几何图形按照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方式进行排列,亦有多个不规则几何图形遵循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进行搭配。同时,当地的苗族刺绣图案中还有大量臆想纹样的使用。如“务冒席”“姜央”“张秀眉”“龙”等纹样的使用。张秀眉与务冒席被视为苗族的抗清英雄,姜央则被视为苗族的祖先,龙在苗族社会褪去了权力的隐喻,没有了张牙舞爪的外部形象,而是以憨态可掬的形象示人,象征风调雨顺、农业丰收[8]。
四、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艺术折射的整体观
艺术与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格罗塞认为:“艺术的起源,就是文化起源的地方”[9]。文化对艺术的形成及艺术的表现内容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艺术的认识不能仅限于艺术本体的分析,还要拥有整体观的视野,即对艺术形成、发展背后的环境、文化等因素进行细致地分析。同时,艺术的表现力不仅在于对局部细节的精致打磨,也要对艺术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巧妙地设计。因此,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艺人们在打磨细节的同时也力求整体的和谐美。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整体美,艺术的整体观就是建立在对艺术品的这一整体美的认识基础之上。[10]65艺术的整体观,要求艺术作品成为这样的浑然一体,其美不在一字一句之间,而在其整体的气势之中[10]66。中国的艺术不只是为审美和娱乐所创造的,也不是为了表达其独特性和个性所存在的,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认同中的表征系统,也是人们遵循其所表征出来的符号和文化象征来规范自己行为的一套教育体系和文化传承体系等。[11]
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的整体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刺绣品具有明显的文化隐喻功能。即该区域苗族刺绣所传递的内容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是对所处文化系统的表达。二是刺绣品的创作过程中讲究整体的和谐美,即纹样的构图、色彩的搭配及技法的选择都不只是表现局部之美,更是为表现整体的和谐美。首先,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具有文化隐喻的功能,它所表现的内容与其所处的自然生境和文化生境存在必然的联系。如当地刺绣中枫树、水牛、蝴蝶妈妈、鹡宇鸟、张秀眉等纹样的使用。枫树、水牛既是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同时,苗族社会的枫木崇拜、水牛崇拜传统给予枫树、水牛纹样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蝴蝶妈妈、鹡宇鸟纹样隐喻了苗族民众祖先崇拜的信仰观念。张秀眉、务冒席等纹样则是反映了苗族同胞英雄崇拜的文化心理。
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艺术的整体观还表现为纹样构图、色彩搭配及刺绣技法的和谐美。该区域的苗族刺绣长期以来形成了固定的纹样构图和搭配惯习。其中台江、施秉等地的施洞型苗族刺绣常采用三接式或二接式的刺绣构图方法;纹样间的搭配也逐渐形成惯习,如蝴蝶妈妈纹与鹡宇鸟纹,张秀眉纹与务冒席纹、人驭兽纹,龙与凤纹,喜鹊与梅花,梅花与树枝,蝴蝶与花朵等;服饰、背带、鞋面等同一刺绣归母品上各个部位的刺绣主体纹样基本相同。如革一、凯棠地区的刺绣上衣中衣肩的主体纹样与衣袖、衣襟等处的纹样相同,如果衣襟部位的主体纹样是蝴蝶,则衣袖、衣肩、衣领等部位通常也是使用蝴蝶作为主体纹样,并以鸡宇鸟纹、水涡纹、折枝花纹等相配。凯棠型、台拱型、柳富型苗族刺绣的纹样构图及结构则表现为另外一种特征。
五、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纹样主题的生活化
苗族传统刺绣滋生于广袤的乡土社会,带有极强的乡土性、民间性和朴拙性。刺绣艺术的诞生空间给予刺绣浓浓的乡土气息。作为苗族刺绣的创作者,绣娘们皆是土生土长的劳动妇女,她们制作的绣片主要是为家用,这就使得她们的刺绣作品受市场的影响较小。各族刺绣艺人在生活的感触下进行艺术实践,创作了大量反映生产生活场景及自然万物的刺绣纹样。在图案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她们的艺术灵感多源于日常生活。她们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将常见的事物进行合理的艺术想象,并将这些想象进行表达,创作出了具有生活化气息的刺绣作品。山中花木、林间鸟兽、水中虫鱼、空中云雀、苍穹中的日月星辰等自然物;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节庆习俗、民间信仰等精神生活都是她们创作的素材。绣娘们通过变形、夸张和巧妙地处理,用手中的针线勾勒出一幅神态生动、充满活力的图案[12]。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的刺绣艺术,都是她们生活场景的反映,是生活与审美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满足自身生存的真实需要而创造,旨在追求美满生活,抒发美好的理想,表达内心的向往与祈愿”[13]。清水江畔的苗族绣娘们喜欢以江中的游鱼、溪畔的虫虾、池塘的青蛙、田间的水牛等常见动物为刺绣创作的素材,因而上述区域的苗族服饰中常有鱼、虾、青蛙、水牛等纹样;台江革一,凯里凯棠一带居住在山岭地区的苗族绣娘们,常喜欢用山间的鸟兽、丛中的蝴蝶、路边的花草作为刺绣的蓝本,这些地区的刺绣常用喇叭花、飞鸟、蝴蝶等动植物作为衣着装饰。生活化的艺术特征使南方少数民族传统刺绣千姿百态,充满乡土气息。台江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民间故事:古时候,有一个苗族青年在山上打了一只漂亮的锦鸡,就把它送给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这个姑娘仿照锦鸡的模样来装扮自己,把自己的发髻梳的高高的,就像锦鸡的羽冠;把衣袖留的宽宽的,就像锦鸡的翅膀;仿照锦鸡的尾羽做了长长的褶裙。姑娘通过这番装束更加美丽动人,使得那个青年更加爱慕她了。[14]146这则故事说明苗族刺绣艺术的设计灵感与日常生活存在密切的关联。不过,除了对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生活常见自然物的描绘,南方少数民族刺绣中还有各种反映民族历史、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及节庆习俗的刺绣纹样。
清水江流域苗族传统刺绣源自生活,并通过妇女们的双手,反映在各种纹饰和制作技巧上。因生活习惯和自然环境的不同,装饰纹样及其制作方法也充满了地方性色彩,这种因地而异的艺术特色,是以自然条件来区分的,其中,山与水的区分较大。[14]154清水江两岸的施洞、旁海、凯里、湾水一带苗族,因交通便利,在长期的文化交往中,汉族对其影响较大,因而该区域的服饰图案色彩鲜艳,且多采用汉族地区流行的折枝花纹样。凤穿牡丹、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等汉族地区常用的吉祥纹样也深受上述区域苗族民众喜爱。制作方式多采用破线绣、打籽绣、挑花等刺绣技法。因而该区域的刺绣呈现细腻、柔美的艺术风格,是秀美清水江的完美呈现。雷山、台江、剑河等地的靠雷公山一带多使用辫绣、邹绣等制作方法,纹样则以二龙戏珠、龙飞凤舞等大块图案花构成,且多以深绿为主色。该区域的苗族刺绣具有粗犷的艺术风格,与雷公山满眼青绿相得益彰。同时,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生活习俗、民间文学、宗教生活等给予各民族的传统刺绣工艺千姿百态的艺术表征。
六、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纹样的交融性
刺绣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苗族刺绣艺术特征是苗族民众生产、生活的艺术化表达。在清水江流域,各民族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实践,促进了各民族刺绣纹样的互鉴与借用,进而使苗族抽象呈现出各民族刺绣间的交融。同时,各区域的民众通过一个个基层市场进行着频繁的经贸往来,进而促进了纹样的跨区域传播,并出现地域间的纹样共享。此外,刺绣艺术亦是思维的物化表现。苗族传统社会保留的对自然界的原始想象促使苗族刺绣中存在不少表达苗族民众原始观念的纹样,这些纹样多通过动物与人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复合,表达特殊的文化内涵。
(一)各民族间的刺绣纹样互鉴
苗族刺绣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具有生活性特征的艺术。清水江中上游的苗族刺绣纹样多来自日常生活,有一部分源自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社会习俗和宗教生活。不过,苗族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断进行着相互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反映在刺绣艺术中则是各民族刺绣纹样的相互借用。笔者所带领的调研团队在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黎平县、台江县等地的苗族、侗族刺绣调研时,清晰地发现苗族、侗族刺绣间的借用现象。在黎平县岩洞镇的岩洞村,我们调研团队发现绣娘的跨民族流动引发流入地的刺绣变革。黎平县岩洞镇的岩洞村本是侗族聚居区,1960年,来自从江县贯洞镇的苗族绣娘陈白兰远嫁至此。陈阿姨精于剪纸和绣花,在岩洞镇做起了卖剪纸的生意。当地侗族妇女见其绣花精美,便纷纷买她剪好的花样来绣,同时还学习她带来的破线绣绣法(1)岩洞地区的刺绣以数纱绣为主,辅以贴花和平绣。。2005年前后,机器介入刺绣的制作,加上当地人找到了侗族的传统刺绣花样,岩洞地区的围腰又改绣侗族的传统花样。可见,拥有纹样创作能力的剪纸高手在各民族刺绣纹样借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多个地域间的刺绣纹样共享
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源自乡土社会,村落为刺绣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刺绣的发展与村落空间内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苗族传统社会,村落之间因地缘、血缘、姻缘和业缘(主要是以“赶场”为目的的经济往来)建立了相互交叉但又层次分明的村落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婚姻圈的划定依据服饰、语言、习俗的异同;市场圈的范围则以水陆交通为触须。在村落共同体内部,服饰的款式,刺绣的技法、色彩和花样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并通过乡规民约的方式得到有效地遵守,同时通过民间文学的方式得到固化。不过,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通婚限制条件的减少,经济市场圈的扩大,村落共同体表现出了较强的伸缩性,甚至各个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区隔逐渐模糊,相互之间文化借用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作为族徽标志的刺绣,因共同体间的频繁互动难免会出现相互借鉴与共享的现象。剑河县革东镇的苗族服饰换装验证了上述假设。
据苗族剪纸国家级传承人姜文英(2)姜文英,女,苗族,49岁,苗族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娘家为台江县老屯乡岩脚村,2003年搬家至剑河县革东镇,并在此地卖剪纸,2005年,剑河县城由柳川镇搬迁至革东镇,姜文英的剪纸生意愈加红火。介绍,革东地区的苗族原用红绣作为衣服的装饰。2000年前后,五河、施洞等地的刺绣流入革东地区,当地妇女觉得施洞绣花精美,就将其用于衣着装饰。2003年,姜文英等专职刺绣剪纸的艺人来到革东,她们不仅带来施洞型刺绣的剪纸花样,还将破线绣等技法传授给当地绣娘。从而加速了当地服饰的改装。2003-2010年期间,姜文英的工作室每年能够卖出一两百件“施洞衣”,此外还有大量的剪纸花样流入革东,最终出现“施洞衣”代替“红绣衣”(3)不过革东镇的每户苗族家中一般还会留几套自己传统的红绣衣,在去柳川等穿红绣的亲戚家走亲时要穿红绣衣。的现象。可见,刺绣艺人的流动引发刺绣纹样及技法的传播,基层市场则为纹样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所需场所。剪纸艺人将刺绣花样拿到基层市场上售卖,绣娘们依据买来的剪纸花样制作刺绣作品,剪纸艺人与绣娘在基层市场辐射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刺绣纹样的共享空间。
(三)不同纹样之间的复合
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艺术的独特性表现为绣娘们常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对刺绣的单体纹样进行解构与重构,设计出众多具有创造性的复合型纹样。如施洞型、台拱型、西江型等苗族刺绣经常将动植物纹样进行分解,萃取其关键要素,再对萃取出的多个纹样要素进行整合,形成新的纹样形象,创造新的纹样结构。常见的纹样复合分为两类,一是动物纹、植物纹之间的纹样复合;二是动物纹(包括人)之间的纹样重构。动植物纹复合最具代表性的是蝴蝶纹与花纹的组合、喜鹊与梅花的共用等。蝴蝶纹与花纹的交融、叠加,形成花中有蝶、蝶中有花、亦花亦蝶的多变形象,构成蝶恋花的装饰纹样。喜鹊与梅花纹样的结合也通常出现在清水江中上游的苗族刺绣当中,构成“喜上眉梢”的文化隐喻。动物纹样之间的复合在当地苗族刺绣中同样常见,这类纹样的代表是千变万化的龙纹的使用。在苗族民众看来,龙为蝴蝶妈妈所生,并通过鹡宇鸟的孵化破壳而出。龙与人类、雷公、水牛等互为兄弟。在苗族地区,龙没有权力与地位的文化隐喻,因而被广泛应用在服饰中。同时,苗族绣娘们根据自己对龙的理解建构了千姿百态的龙纹形象,并通过龙与其他动物的结合,形成龙首牛身、龙首蛇身、龙首蚕身、龙首鱼身、龙首狮身及双体龙、叶身龙、花身龙、鱼尾龙、马尾龙、牛角龙、凤头龙、鸡头龙、蜈蚣龙、人头龙等众多变形龙纹。龙纹与其他动物纹样通过纹样要素的解构与重构,表现出苗族刺绣艺人们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折射出她们众生平等、万物共存的世界观。
七、结语
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是苗族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总体来说,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拥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其一,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是再现与表现的结合。当地刺绣中有大量源自生产生活的纹样,是苗族民众现实生活的再现,同时,苗族刺绣是民众集体情感、价值观念及审美情趣的表达,具有很强的表现性。其二,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是具象与抽象的共用。当地苗族刺绣中有大量具象纹样的使用,这是对自然物的写照及日常生活的记录。同时,在当地苗族刺绣中有几何纹、复合性纹样的运用,这是对自然物与臆想事物的抽象与整合。其三,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创作讲求整体观念。苗族刺绣品中所表达的文化隐喻无不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同时,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在纹样搭配、整体构图及色彩选用上十分注重和谐之美。其四,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纹样主题呈现生活化特征。当地苗族刺绣纹样多源自自然界及日常生活,是生活化的表达。其五,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刺绣还呈现出与周边民族刺绣互鉴与共享。具体表现为各民族之间刺绣文化的交融,区域之间刺绣纹样的共享及纹样之间的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