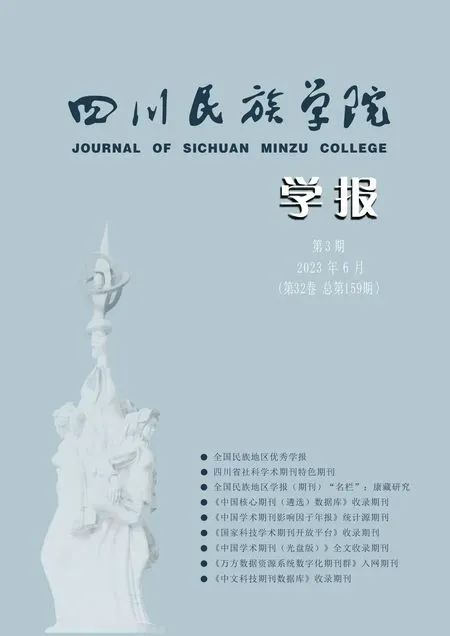“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
吴宇晴 吴秀云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2)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新特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39。走中国式民族问题解决的“正确道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的历史承继。其中,“从历史传统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2],“大一统”思想蕴涵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智慧。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围绕多方面、多维度展开,既从本体视角出发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发展,也从历史维度深入研究其生成逻辑,并着眼于当前民族工作实践进行实践维度与价值维度的探析[3],但较少学者从“大一统”思想出发,进一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逻辑。因此,通过揭示“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进而明确其价值逻辑、推进其实践逻辑,有助于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新时代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一、“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大一统”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我国传统国家治理经验的思想精华,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传统。因此,从历史源头、内生动力、情感旨归三个层面揭示“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有助于厘清“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流关系,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大一统”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源头
中国历史是一部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理想的历史,“大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才是异态[4]。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格局最初见于周王朝,《诗经·北山》有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但“大一统”一词最初见于战国晚期儒学经典《公羊传· 隐公元年》的首篇《春秋》:“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6]其中,将“王正月”释为“大一统”,但西周式“大一统”在春秋时期早已难寻踪迹。随着西汉政局稳固、儒学复兴,大儒董仲舒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7]认为“大一统”合乎天地之道、遵循古今之法。在隋唐时期,统治阶级变革了传统官僚体制,创建了科举制、三省六部制,以及相对成熟的文官制,这些制度在宋朝进一步完善,为维系我国传统“大一统”格局输送了大批政治人才。到了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则重视边区管理与民族规治,形成了各民族“大一统”的融合格局,进而缓和了中原同外族的民族矛盾。在中国各大王朝的时代更迭中,“大一统”思想虽发生了历史流变,但其追崇统一、崇尚整体的价值内核已逐渐为中华民族所内化,生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大一统”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
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能够明确“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2]。“大一统”思想萌发于西周“大一统”的伦理基础、稳固于秦汉“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完善于隋唐宋“大一统”的官僚机制、发展于明清“大一统”的民族融合,已内化为各民族的政治信仰与社会共识,生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大一统”思想作为团结各民族的情感纽带,虽历经千年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一方面“大一统”思想的包容性激发了其生命力,“大一统”思想能够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相融合,并以符合各民族利益、贴合各民族文化、融合各民族特色的治理方式加深其内在的思想联结,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大一统”思想的认同感强化了其感召力,能够增强各民族的自觉意识,使各民族自觉进行心理联结,进而形塑各民族的政治品格,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大一统”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旨归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民族认同,核心内容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8],这种“认同”从属于对“大一统”格局的认同,其本质仍是服务新时代“大一统”格局的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源于“大一统”思想,并汲取了“大一统”思想的情感内核,“大一统”思想之“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共同”具有内在的情感联系。其中,“大一统”思想之“一统”主要强调客观层面的“一统”,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共同”则是吸收了“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意蕴所延伸出的情感共识,更加强调心理层面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当代诠释,既丰富了“大一统”思想的时代内涵,又依托其强大的认同力进一步巩固了新时代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服务于新时代“大一统”格局的思想建设,回归于“大一统”思想的情感系统。
二、“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
“大一统”思想具有价值导向性,其中“天下一统”的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儒家一统”的文化观、“华夷一统”的族群观[9]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蕴,从国家、政权、文化、民族四个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价值指向,要求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认同,进而巩固新时代多民族“大一统”格局。
(一)从“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到对伟大祖国的强烈归属
“天下一统”的疆域观意指我国地理疆域的完整性及治理状态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继承“天下一统”理念的历史基础上,更加注重从国民心理层面,提升中华民族对伟大祖国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主要体现在国家认同上。当前,以国家认同为心理基础建构国家合法性是深化我国“大一统”格局的必然举措,而“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够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10]。国家“政治秩序”或称国家治理秩序作为稳固我国“大一统”格局的坚实地基,不仅是新时代强化国家合法性的制度设计,还是维系各民族国家认同的制度安排。但全球化的发展虽带来工业化加速与城镇化推进,但也引发了资本化扩张,极大地影响了巩固中国传统“大一统”格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部分民族群体出现身份认同的不协调,以及部分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信念等地域传统的包容性弱化。因此,为改变为这种局面,要求不能仅仅局限于“天下一统”理念所强调的客观层面的国家统一,而应深入到各民族的心理层面,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对伟大祖国的归属感。
(二)从“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到坚持党领导的强大共识
“王权一统”的政治观意指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政治形态的稳定性及政治权力的集中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演化于“王权一统”的政治格局,汲取了“王权一统”理念的积极内容,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局限于客观层面政局与政权的稳定集中,而是更加强调心理层面的政治信仰与政治认同。在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演进中,我国政权最终实现了从“王权”到“民权”的历史转向,“民权”即公民的政治权利,最初在现代意义上对“民权”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即政治革命,但由于中国历史与中国人民的坚定选择,最终将彻底实现“民权”这一伟大的政治使命落于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进行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中国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中华民族的政治信仰更加坚定乃至凝结为坚持党领导的强大共识。在新时代新起点上,这种政治共识必将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共创历史新成就的磅礴力量,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从“儒家一统”的文化观到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
“儒家一统”的文化观意指我国思想意识的凝聚性以及文化传统的整合性。“儒家一统”理念将儒家文化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儒家文化烙上政治色彩,因此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便承担起政治教化的重要任务,但居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高位”并非真正能够使各民族在心理层面达到深切认同与真正接受,因此儒家文化经中国千百年的历史“扬弃”,其思想精华最终熔铸于各民族“共同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1]。中华文化在中华各族人民传承创新的历史实践中“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12],沉淀着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意味着各民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真正接受,既充分诠释了“大一统”思想的文化导向,又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力量。现今,面对文化虚无主义引发的多重认同危机,应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注入文化力量,进而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从“华夷一统”的族群观到团结各民族的坚定信念
“华夷一统”的族群观意指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性以及少数民族的团结性。“华夷一统”理念为清朝所倡导,但其形成演进却历经多朝更迭,如先秦时期所萌生的“华夷之辨”观念、汉代所强调的“华夷首足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盛行的“华夷”皆正统之论调、宋代所形成的“礼别华夷”之观等,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化中,最终于清朝完成了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的时代转向。同时,“华夷一统”理念作为古代统治阶级提出的民族治理理念,更多地强调各民族在客观层面上的和谐团结如没有战火纷争、民族矛盾等,往往缺乏从心理层面强化各民族情感联结的思想意识。因此,为巩固多民族国家、处理多民族问题、发展多民族关系,要求不断增强团结各民族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族团结视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3],民族团结以“生命线”的天然形态联结着各族人民的社会交往,极大地拉近了各族人民的心灵距离,这种坚定信念也将转化为各民族间牢固的“生命联结”,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应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4],从而真正实现以民族团结促民族进步,以共同奋斗促共同富裕,最终以民族团结为战略基点巩固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三、“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在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实践中,“大一统”思想以国家发展与民族进步为基准不断调适,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辉煌成就。面对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应加快国家治理创新进程、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弘扬中华优秀治理传统、提升民族区域治理效能,不断凝聚、引领、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巩固多民族“大一统”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秩序。
(一)加快国家治理创新进程、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思想蕴涵着朴素的国家治理观,要求通过制度治理链接法律、技术、人民、全球等多主体治理,进一步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根本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大一统”思想强调制度的完善性是古代“圣王”的治理追求。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失误教训时,指明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5],中国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是巩固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保障,因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根本就在于坚持制度治理。其中,依法治国作为制度治理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基本方略,新时代坚持走依法治国道路,必须以“良法”促“善治”,在法治轨道上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与现代化[16]。在数字时代,数字治理已成为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当前将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以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管理为主线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进而打造数字政府已成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但数字治理本质上仍是人民治理,以人为主而非以技术为主,人民借助数字工具不断强化国家治理效能,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提升我国全球治理效能,增强我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入场券”,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发展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着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实现良性互动,进而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17],“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我党百年奋斗经验的第一条,要求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制度创新、提升制度自信,不断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群众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的辩证统一[18],我国通过制度设计,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共识上升到制度层面,确立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7]。一方面,要求深化制度优势推进制度创新。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重点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全面落实党的组织安排、系统深化党的统筹规划,坚持从制度设计层面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从制度执行层面强化党的战略决策,从制度反馈层面优化党的政策落实,结合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创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制、健全党的反腐机制、深化党的斗争意识,进而形成科学的制度安排、完备的制度结构、有效的制度耦合[18],真正在制度层面做到“两个维护”。另一方面,要求在制度创新中提升制度自信。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实践创新中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创新党的领导制度执行机制、提高党的领导制度执行力度、强化党的领导制度执行效能,实现治理效能的社会积淀、力量勃发与真实反馈,进一步将其效能优势转化为制度自信,同时当制度自信作用于社会主体,能够自动对外输出政治认同,使各民族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有助于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新时代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三)弘扬中华优秀治理传统、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文化土壤,是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桥梁,必须坚持以科学理念为指导探索科学方法,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历史传承,在“两个结合”中推动创新发展,在数字时代加快跨域传播,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兴则国运兴,中华优秀治理传统承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7]。首先,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必须强化其“辩证意识”“价值意识”“体系意识”“功能意识”以及“融合意识”[19]等科学理念,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提炼提纯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多重价值,充分发挥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多元功能,科学完善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传承创新体系,不断推进中华优秀治理传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次,在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历史传承中,应不断优化中华优秀治理传统教育体系,打造专业化教师团队,将中华优秀治理传统融入大中小幼的思政教育中,助推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入脑入心,实现“三全育人”。再次,在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时代创新中,既要将中华优秀治理传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要将中华优秀治理传统同时代精神相结合,实现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时代创新。最后,在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跨域传播中,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新优势,拓宽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传播空间,重塑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话语体系,培育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传播人才,不断提升中华优秀治理传统的传播效率。
(四)提升民族区域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思想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区域治理智慧,最终会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内核,新时代必须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多民族治理,进一步团结各民族力量、提升民族区域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问题处理模式的伟大创造。”[20]当前,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成为新时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要求。其一,在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多重冲击时,应结合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其个性化民族自治模式,进而提升民族区域治理效能。其二,应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始终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指导,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轴,与时俱进地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法律法规。其三,为更好地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应建立健全民族自治权力监督体系,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体制,提升民族自治机关的治理能力与权利意识,破除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优化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结构,打造觉悟高、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新时代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其四,应在弘扬社会主旋律的现实前提下充分吸收各民族特色,创造出为各民族所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借助精神产品生成情感链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五,应从思想意识层面深化各民族的认同感,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区域治理效能,以治理效能的强化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四、结语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既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能够以其历史逻辑明确价值逻辑、以其价值逻辑推进实践逻辑。新时代以“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高度重视“大一统”思想的时代价值,注重从客观层面的“一统”深入到心理层面的“认同”,不断完善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治理体系,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认同,助推新时代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系统优化,进而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1]58奠定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