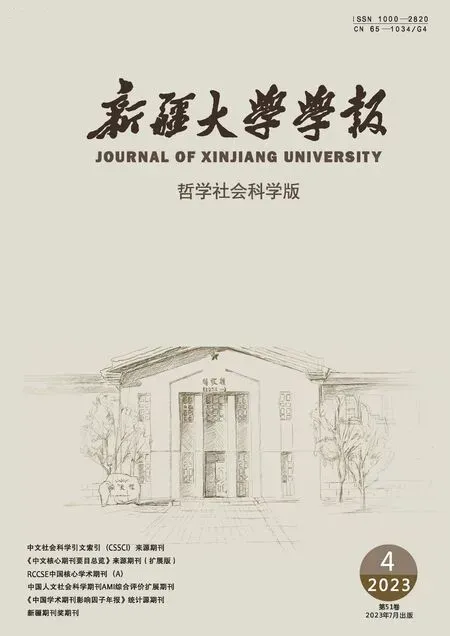西部哨所“喀格勒克”语源、语义考*
玉努斯江·艾力,潘勇勇
(1.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克拉玛依市委党校,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喀格勒克”一名至晚在7 世纪后期已见于文献,很可能在9世纪中叶回鹘迁入塔里木盆地南缘时已开始使用。波斯和察合台文文献作“哈尔噶里格”(qarghaliq),《钦定西域同文志》中的“哈尔噶里克”为该名最早的汉译形式,此后还曾出现“哈尔哈里克”“哈哈里克”“哈拉噶里克”“哈赫勒克”等译名。该地名的由来与其战略位置和民族演变密切相关,最初仅用于指代位于今叶城县乌夏巴什镇和皮山县克里阳乡之间的军事要塞及附近村落。后来随着人口增长,该村落居民迁居今伯西热克乡东南部并形成“喀格勒克”回庄。因人口和商业等因素,其部分居民又迁居今“喀格勒克镇”,使成为当时辖属叶尔羌较大的村庄,也指其附近地段的名称。光绪八年(1882),设叶城县,县驻“喀格勒克镇”后,“喀格勒克”逐渐指代提孜那甫河流域即今叶城全境的名称。
一、“喀格勒克”一名的几种解读
“喀格勒克”一名,在清代之前文献中出现次数并不多,主要见于清代初中期相关文献中,如《钦定西域同文志》《西域水道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新疆图志》《西陲要略》等史籍以及部分察合台文文献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钦定西域同文志》中有关“喀格勒克”一名的解释:“回语,地多林木,群鸦巢焉,即所有以名其地。”[1]上述记载曾被前人多次引用,并以此为基础对“喀格勒克”一名的语源及语义进行了探讨。经笔者收集,现今有六种不同的说法:
1.喀格勒克一词源于“Kalghuluq”,意为“留下来、住处或好的留处、停留”,据说此地曾是土地肥沃、水资源充足、人民富裕、热情好客的新开垦之地,因此吸引了周边众多劳动力到此打工谋生,因而被命名为可以留下之意的“Kalghu”,并逐渐成为该地的正式地名。①第1种说法为访谈所得,口述者:麻木提·阿尤甫,退休教师,叶城县吐古其乡,访谈日期2019年8月22日。
2.哈尔噶勒克,为qarGa(乌鸦)附加字尾—liq,而成qarGaliq 之音译,义为乌鸦之地、乌鸦的,今新疆叶城县治。②参见刘义棠《钦定西域同文志校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4页。
3.喀格勒克一名是从“Qarluq”(葛逻禄)一词演变而来的,意为“葛逻禄人的活动或居住处”,因为当时生活在包括今喀格勒克镇的叶城范围内的主要居民是以葛逻禄及其近亲的其他部落为主。
4.喀格勒克一词源于回鹘语“qarighligh”,该词由“qarigh”和“qiligh”组成,有“向王国缴纳赋税”“王伯克们的领地”或“王伯克们收赋税之地”之意。
5.喀格勒克一词源于“qaghanliq”(可汗国、国家),意为“可汗土地或公地”,因为国家被认为是整个汗族的财产,“汗”(qaghan)即“国家”。①第3、4、5种说法均为访谈所得,口述者:苏里坦·马木提,退休教师,莎车县一中,访谈日期2015年4月16日。
6.喀格勒克由回鹘语“qaraghuluq”一词演变而来,为“城堡、堡垒”之意,历史上这里是北通莎车、东与于阗、西与蒲犁、南与西藏、拉达克(克什米尔)必经地。之所以被命名为“喀格勒克”,可能与此地是军事哨所和边防重地有一定关联。②参见叶城县地名委员会《叶城县地名图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
以上是笔者所见有关“喀格勒克”一名的语源及语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说法,反映了部分研究者对历代今叶城境内民族构成与演变的关注。但上述研究似乎忽略了一些细节问题,如,有的极为重视该名与现代语言中的某个对音词之间的简单相似之处,进而确定其语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除第六种“源于“qaraghuluq”(城堡、堡垒)”说法外,其余均为民间传说和推测,并无可信的依据。第一种说法,“qalghuluq”与今叶城现代维吾尔语称呼“qaghiliq”虽有相似之处,但无法解释其向“qaghiliq”转化的过程。“Qalghuluq”一词由动词辅助体“Qal”和词缀“ghuluq”组成,表示舍不得离开之意。此外,“ghuluk”像其他构词词缀quluq//guluk一样,加个别动词词干,构成表示动作对象的抽象名词。如,“korguluk(苦头、不幸、厄运),tartquluq(苦难、苦楚、痛苦),qilghuluq(做为、该做、该为、可干的、可做的)”[2]等。显然,ghuluq//quluq//guluk与名词附加后缀“liq,lik,luq,luk”有明显区别,后者为地名相关的专有名词,表示某人生于何地或何许人。再则,叶城在清代初期译写“哈尔噶里克”(qarghaliq),“r”音尤为突出,而“qalghuluq”中无“r”音。
第二种说法“qarGa”(乌鸦)与今“qaghiliq”(喀格勒克),同样两者词根相同,读音也相似,但原本语义完全不同。前者语音变化不明显,尤其是有关近代文献中均以“qærgha”形式出现,说明其“r”音的脱落在书面语中不突出,却表现在口语中,如qargha→qagha,不过后者(qaghiliq)中的名词附加“liq”,很可能与后人记忆中原有语义关联。这样就有理由认为,上引《钦定西域同文志》中对“喀格勒克”的解释,以口语语义即民间传说为主,并未足够重视该名文化内涵的传承问题。之后,部分历史地理学家多参考《钦定西域同文志》,《西域水道记》也沿用“qargha”(乌鸦)之说。牛汝辰先生赞同此说,并称:“本县辖境汉代为莎车、子合国地,北魏为渠沙、悉居半、朱俱等国地,唐代为沮渠、朱俱波地、明叶尔羌。……叶城县的维吾尔语称呼为喀赫勒克,意为乌鸦之地。”[3]笔者认为此观点不仅缺乏语言学方面的探析,而且对该词是否适合作为地名缺少考量。然而,就乌鸦形象而言,人类接触鸟类学相关科普知识之前,视其为不祥之物或废墟、悬崖、厄运、贪婪的代名词。这一特征在民间表现得较为突出,叶城也不例外。如,流传在叶城的一首童谣中有这样的描述:一群乌鸦叫着哑哑,飞着向柯克亚悬崖,想吃东西抢着牛粪,心黑肠带着厄运。既然今叶城境内的人未把乌鸦当作神鸟和图腾,为何自豪地称其为“喀格勒克”,这亦很难理解。除了叶城外,新疆别处都可见无数的乌鸦,但为什么只有叶城因“乌鸦之地”而命名为“喀格勒克”呢?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同样是一种民间推测,缺乏历史文献的支撑。
第三种说法“qarluq”(葛逻禄)与今“qaghiliq”(喀格勒克)的发音相差甚远,同时很难解释从“qarluq”到“qaghiliq”的语音演变过程。另据叶城土语语音特点,其分为山区土话和平原土话,山区土话基本保持原貌,如辅音r发音很清晰,r的脱落比平原区少。③参见吐拉买提·艾木都拉《现代维吾尔语叶城土语词汇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这对最早以平原区“喀格勒克”雏形发展形成的叶城来说,其原有名称“qaghiliq”与“qarluq”在词根和构词附加成分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如,由含“qar”(雪)和形容词附加成分的“qarluq”(葛逻禄)一词,表示“雪地人或住雪山的人民”[4]之意。目前,新疆地区还保留着与历史上葛逻禄人活动关联的一些地名,如哈剌鲁山谷(qarluq ghol-哈密)、喀勒克(qarluq-新疆疏勒)村、喀尔勒库木(qarluqum-新疆疏勒)村。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帕哈塔其、额鲁特、木巴拉克、阿屯萨依、舒尔其等地区也有以哈剌鲁(Qorluq)和哈剌鲁克(Qorliq)命名的村落”[6]238等。可见,上述这些地名基本上保留“qarluq”一词的原型,从中无法看出其与“qaghiliq”关联的语音变异现象。
第四种“qarighligh”和第五种“qaghanliq”说法与今“qaghiliq”(喀格勒克)之间无任何关系,从对音上看,两者均为抽象词汇。尤其是“qaghiliq”(喀格勒克)源于“qarighligh”的说法很难成立。据研究,回鹘语中并无与“qarighligh”对称的相关词,只见于“qarigh”和“qiligh”(qareligh)一词,前者为“年迈、老年人、老人”,后者为指“一种税”或“开支和花费”,而不是什么“缴纳赋税或王伯克们收赋税之地”之意。另外,回鹘语中还有与“qiligh”相同含义的词语,如,basigh,birim,irt,qawïd,qodghu,tüdün,umdu等,①参见李经纬《回鹘社会经济文书辑解》下册,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532、586页。均指9世纪末至14世纪在吐鲁番地区收取的各种赋税。同时,在回鹘语中真正与“领地”“赋税”关联的并不是“qarighligh”一词,而是“inčü”(彩邑、封地)和“salïgh”(捐税)②参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4、275、280、289、298、299页。两词,因此,笔者认为以上说法显然缺乏文献依据,不能说明问题。对于“qaghiliq”(喀格勒克)源于“qaghanliq”说法,同样无可信依据,因为现有的语言学材料中无法找到“qaghanliq”到“qaghiliq”的相关音变实例。该词由“qaghan”和附加成分“liq”组成,虽然前者指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首领普遍使用的官职称号,但其关联的地名并不多见,最为典型的是隋末唐初建在今吉木萨尔县护堡子古城之内的可汗浮图(qaghanbut)城。据研究,“可汗浮图城的名称为复合名词,可分解为‘可汗’与‘浮图’两个部分。其中“可汗’之称,显然与城的性质密切相关”[6],然而“浮图”一词,也就是“‘浮屠’正与bodo,boddo,bouda 相当”[7]。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城存在时间不长,不久就因天山北坡东路民族构成的变化又替换北庭之称。我们从中可以得知,与“可汗”相似之类地名的出现,该地区的性质与某北方游牧民族在此地是否设过统治机构或活动有关。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qaghanliq”说法,仅仅只是一种推断和猜测而已,故不能成立。
第六种“qaghiliq”(喀格勒克)源于“qaraghuluq”(城堡、堡垒)观点,尽管未考证该地名沿革、语音变化及具体出现时间等,但在理论上似乎更具可信性,即认为之所以叶城被命名为“喀格勒克”,与“其军事哨所和边防重地有一定关联”。笔者赞同此说法,不过还需对其进行进一步地考证。
二、基于考古与历史文献学对喀格勒克历史沿革的考证
据《汉书·西域传》“西夜”条,叶城早期居民属蒲犁、依耐、无雷同类,“与胡异,种类羌氐行国”。1976—1977 年,塔什库尔干境内香宝宝古墓从侧面反映了包括叶城在内其附近地区居民的构成。公元前174 年,“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8]卷96,3884。说明塞王南迁后生活在今叶城(喀格勒克)境内的居民并不是单一族群构成,也有属于不同族群的群体。叶城西汉时为西夜,后分属西夜和子合,同时与附近莎车、于阗等国,积极参与摆脱匈奴控制的斗争。据《汉书·郑吉传》,公元前60 年,西域都护府建立,“治乌垒城,镇抚诸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叶城等地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东汉初叶城并入莎车,光武建武九年(33)莎车王康卒,“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西夜王”[9]卷88,2923。94 年,西域各地内属,东汉统一西域。
三国时叶城为西夜,被疏勒兼并,据《三国志》记载:“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犂国、億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脩国、琴国皆并属疏勒。”[10]东晋时叶城仍属于疏勒而称“子合”,南北朝、隋朝时改名为“悉居半”或“朱俱波”。据《魏书·西域》悉居半条记载:“悉居半国,故西夜国也,一名子合。其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在于阗西,去代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来献,自后贡使不绝。”[11]《通典·西戎五》“朱俱波”条云:“其人言语与于阗相似,其间小异。人貌多同华夏,亦类疏勒。”[12]可见,5 至6 世纪时包括今叶城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亲密的朝贡关系,并原名“西夜”“子合”,后被“悉居半”或“朱俱波”一名取代,同时居民构成也发生明显变化。另据考古调查显示,1999 年9 月至11 月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喀什地区叶城县和莎车县境内发掘了一批晋唐时期的古墓葬,共14 座,其中在今叶城县宗郎乡群艾山亚村共发掘墓葬10 座,从中收集了颅骨标本4 例。经张全超等人研究认为,从墓地出土的人骨形态观察来看,该墓地组颅骨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的基本特点。群艾山亚组与山普拉组及阿拉沟1 组等代表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的古代对比组聚为一类,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较为接近,同时这一结果与根据颅面部形态观察的结论完全相符。①参见张全超、陈靓《新疆喀什地区晋唐时期古代居民的人种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71页。这一特点证明,6—7 世纪今叶城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古代居民在体质类型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原“西夜”“子合”居民,已不再是汉代时单一的“羌氐”构成,而是以杂有地中海类型为主的居民和羌氐民族构成,两者已逐渐融合。
唐朝统一西域后,分别于640 年和702 年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护府下设都督府,其中今叶城之地属于疏勒都督府。《贾耽四道记》云:“于阗……六百二十里至郅至满城,一曰碛南州。”[13]笔者认为郅至满与悉居半、朱居槃或朱俱波为同名异译。唐朝对西域的管理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力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从而推动了今叶城等地一些新兴城镇的涌现。据考古调查,1990 年8 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组在今叶城宗朗乡和洛克乡境内先后发现几座唐宋时期的考古遗址,其中在宗朗乡境内发现冬俄孜、阿哦遗址,最后的普查报告指出:冬俄孜遗址位于宗朗乡冬俄孜村境内,“在现在乡中学附近。此地维吾尔语又名库木夏海尔,译成汉语即为‘砂子城’之意”[14]52。“阿哦遗址位于宗朗乡阿哦村境内,在吾鲁吾斯塘河的西侧高台地及其北侧的倾斜坡地上。……我们在遗址上采集到少量的陶片,均夹细砂,陶色有黄和赭色两种,基本手制,在口沿或颈部有轮制痕迹。”[14]52洛克乡境内发现郭大木、马江敦遗址,普查报告中指出:“郭大木遗址位于叶城县洛克乡郭大木村东约500米左右,在卡尔瓦斯曼吾斯塘河东岸第一台地的边沿,……地表布满了红色陶片,我们采集到陶片、铁碴、钱币等物。”[14]53这进一步证明,唐宋时期在叶城东中部包括今宗朗乡和洛克乡境内已经出现了几座城镇,其中宗朗乡境内的冬俄孜、阿哦遗址具有一定的规模,居民很可能过着定居生活。这一情况在公元7 世纪初途经此地的玄奘记述中更为突出:“斫句迦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坚峻险固,编户殷盛。山阜连属,砾石弥漫,临带两河,颇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寔繁。”[15]这说明,当时玄奘所见到的“朱俱波”还译写“斫句迦”,是丝绸之路南道重要城镇之一,其境内居民农牧业灌溉水源主要依靠今提孜那甫河和叶尔羌河。对此黄文弼先生指出:“居民沿河两岸而居,村舍相续。据说:此地甚早即有居民,称为奇盘,故山亦以奇盘为名。……奇盘山势莽平,土阜起伏,居民咸散布于山阜中,以畜牧为业,兼营耕植。”[16]可见,叶城棋盘乡地形特点与玄奘记述颇有相似,同时斫句迦(朱俱波)城地理位置应相当于今棋盘乡及附近区域。
龙朔二年(662)吐蕃势力开始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直到866 年其势力退出西域之前,部分吐蕃居民陆续迁入叶城在内的于阗等地,并丰富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吐蕃统治结束后,一些吐蕃人继续留居叶城,逐渐融入当地居民中。这一点在今叶城境内吐蕃时代保留的一些地名中表现得更为明确,如瓦勒瓦、格仍拉、许许、许来、博隆、尤隆等。9 世纪30 年代末,漠北回鹘人因内乱和外族入侵,诸部纷纷西迁,其中一部分迁居到于阗王国所控制的新福州及其附近的叶城一带。这次迁徙为叶城原有居民注入新鲜血液,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交流,逐渐融合。北宋时期叶城先属于阗,后属喀喇汗政权,虽然这一时期有关叶城的记载较贫乏,但20 世纪初在莎车县郊外发现的一批文书中反映了当时莎车及其附近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构成。在农村地区私人土地占一定比例,但也盛行土地买卖或把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从中还不难发现,当时生活在叶城等地的居民日常生活中使用回鹘语、用回鹘文拼写自己的语言,后受宗教因素等原因逐渐用阿拉伯文拼写自己的语言,“这个传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如14 世纪以来的察合台文,流传至今”[17]。其境内的主要民族以回鹘为主,还有其他民族,如塔吉克人和被回鹘化的坎察克、桃花石人等。
喀喇汗政权后叶城属西辽。“西辽王朝对其归并地域的城乡居民的所有权没有作任何改变,特别是耕地,仍归居民耕种,……居民缴很轻的税,每户纳一个狄纳尔。不久,百姓兴旺,牲畜肥壮。”[18]元朝时叶城属别失八里行尚书省管辖,后为察合台后裔领地,但一直受朵豁剌惕、巴邻、楚剌斯等蒙兀儿部的管理。后来,这些部落受当地文化影响,从游牧走向定居,逐渐融合于近代维吾尔族当中,今叶城境内的巴仁(原为baarin)、洛克乡的莫尕拉、棋盘乡的木尕拉(moghalla)村等地名均为上述部落与当地居民融合的见证,不可能与成吉思汗名将木华黎后裔有关。因为从读音上看,“莫尕拉”和“木尕拉”为“moghal”(蒙兀儿)一词的复数,而木华黎为“muqali”的音译,二者无任何相同之处。
明代时叶城属叶尔羌汗国,据研究,“汗国中期以后除把归并的吐鲁番、察力失(焉耆)作为封地外,又从阿克苏、叶尔羌、和田等地区分割出库车、哈尔哈里克、哈拉哈什、克里雅等作为封地。受封者主要是汗的儿子和兄弟,也有孙子,他们称为总督”[19]。可见,叶尔羌汗国对所属的土地按大小分为几个分封地区进行统治,并把受封者称为总督。大约在叶尔羌汗国第四代统治者“马黑麻时叶城从和田分割出来,按照惯例,他把叶城赐封给了其弟羽奴思速檀管理”[20]。16—17 世纪中后期和前期中亚纳克什班底教团“黑山派”和“白山派”势力传入叶尔羌汗国,为扩大各自的影响广收门徒,壮大势力。从此,相互对立的这两个派别展开激烈斗争,企图控制汗权,最后导致汗国灭亡。叶城长期为黑山派和卓活动范围,社会经济倒退,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755年,清朝讨伐达瓦齐平定准噶尔,1757—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至此,清朝完全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包括叶城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再度与全国运行在同一政治轨道上,叶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清朝采取“因俗施治”政策,在南疆实行伯克制度。据《西域地理图说注》记载,当时叶城隶莎车(叶尔羌)府,“叶尔羌旧有土城一座,约六里三分余,……城内旧有回目居住子城一座,约二里五分余,今为驻扎官兵,并设仓库内。该属城村二十九处”[21],其中今叶城境内有哈尔哈里克、塔克布依、库库雅尔、霍穆什千、玉拉里克、舒铁、伯什里克、英格奇盘等八个回庄,而“塔克布伊,在库克雅尔西北二百里,有小城,东北距叶尔羌城三百里”[22]423,指今叶城柯克亚乡西北“五条河谷:帕赫甫、楚克苏(Chukshu)、布龙(Bulung)、玉龙(Yulung)以及桥甫(Chop)”[23]202。霍穆什千(亦写呼木什恰特为“芦苇村”之意,均为“qumushkant”音译),指今依提木孔乡、恰尔巴格镇、铁提乡、吾吉热克乡、夏合普乡、依力克其乡范围,其辖属有26 村,其余的分别指今西合休、柯克亚、乌夏巴什、棋盘、伯什热克、喀格勒克镇等地。而《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除上述村庄外,又提到沙图、贝拉两个村庄。沙图,“在呼木什恰特东南二十五里,逾叶尔羌支河至其地,西距叶尔羌城二百二十里”[22]424。笔者认为,沙图很可能指今叶城萨依巴格乡萨亚特村,贝拉位于今洛克乡博热村。1882年,设叶城县,治叶尔羌(莎车)回城,1884年,新疆建省后移县治今喀格勒克镇,因为喀格勒克镇原属叶尔羌回庄,县名仍沿用叶城。
三、“喀格勒克”的语源和语义
前述叶城西汉时为西夜,后分属西夜和子合,三国时又为西夜。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东北到都护治所五千四十六里,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8]卷96,3882-3883。《后汉书·西域传》载:“自于窴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西夜国,一名漂沙,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9]卷88,2916-2917以上内容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是同一个区域不同地点的描述,尤其是“西夜国,一名漂沙”,应指“子合”一地,不可能是“西夜”别称。因为今叶城柯克亚乡境内有与“漂沙”同名的普萨(pusar)村,另外《后汉书·西域传》中“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的记载,为探索西夜、子合方位可提供重要线索。“所有这些地方都必须在叶城附近去寻找,这一点是清楚的,因为皮山即今天之古玛(Guma)是可以肯定的,而由此往西的路,必须通到现在之叶城地区。”[23]197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西夜很可能位于叶城平原区,子合位于其山区境内。还应指出的是,古代叶城别称“西夜”“子合”与“喀格勒克”之间虽有传承关系,但很难理解其向“喀格勒克”的演变情况。
关于“西夜”“子合”与叶城南北朝、隋唐时另一别称“悉居半”“朱俱波”和“朱俱槃”,余太山先生指出:“西夜[shien-jyak],与塞[sek]视为同名异译,故西夜亦得为种族名。”[24]117“悉居半[siet-kiapuan]与‘子合’[tzie-hep]为同名异译。二者与本传另处所见‘朱居’[tjio-kia]均为čakukalka 之对译。”[24]126笔者认为此说虽甚有创意,但却忽略了地理方位地考证。《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八云:“裕勒阿里克,在波斯恰木南七十里,有小城,东北距叶尔羌城三百里。由是西南为汉西夜国地。”[22]422这里的裕勒阿里克是今叶城县乌夏巴什镇下辖行政村玉勒艾日克村,因此,汉西夜国地理方位在叶城县中部以及附近地区。如,今叶城洛克、依提木孔乡都有与“西夜”音译更相似的斯也克(siyäk)村,当然这对西夜与塞(sek)视为同名的说法更实际些。另外,“朱俱波”或“斫句迦”“在《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作遮拘迦,《月藏经》又作遮居伽,《南史》又作周古柯,皆来自čakukalka,为梵文化的字尾。又回鹘文《玄奘传》残本作čäkük”[25]。上述叶城不同时期的译写,如“悉居半”“朱驹波”“朱俱波”“朱俱槃”“斫句迦”或佉卢文、藏文、梵文中的“čugupa”“čugopa”“čakukalka”均为今叶城境内的棋盘(čupan)的另一译写,其中回鹘文中的“čäkük”是梵文“čakukalka”的缩写,不可能是“喀格勒克”(qaghiliq)一词的最初形式。F.W.托马斯指出:“喀格勒克绿洲(叶城)位于于阗的西部。……有趣的是,在《于阗国授记》和《于阗教法史》中都提到了这个名字的藏语形式。在《于阗国授记》中,我们读到了一个相对较晚时期的于阗国王尉迟(Vijaya),书中只提到他名字的动态部分。他娶了朱居磐国王的一个女儿,名叫殊度迦。殊度迦为她的妹妹阿罗汉·阿输迦斯拉建造了左雨囊伽蓝寺,这座寺庙是受到阿婆佗神和瞻葩橘多神的保佑的。《于阗教法史》中提到一个地方叫南牟没(mona),在那里,早期的于阗国王(yol)提议建造一个堡垒,作为朱俱波(Bcu-gun-pan)肖像的宝座,它保卫着俱善城(Dge-ba-tan)及其片区的要塞。”[26]以上记载虽为传说,有其不可置信成分,但其中心内容,即早期于阗国王在朱俱波建造一座堡垒提议之说,为我们探索“喀格勒克”语源和语义提供重要线索。说明了喀格勒克堡垒的建造很可能与于阗佛教文化对其周边传播背景有关,即当时今叶城一带一段时间属于阗国势力范围。
但应当指出的是,“叶城”在和田出土藏文麻扎塔格,a,¡¡¡0013 文书(d)中亦出现“Kha-ga-pan”形式,文书中云:“送呈朱俱波(Kha-ga-pan)官邸(diwan):忙若的陈述书(一般的问候后)去年听到说人坏话者的诽谤后,我已辞职去塞俄(She-vo)。然后我的……一个孙女出生了,在聂噶(Gnyag)也有,……去年我叔叔尚杰热的仆人麦鲁的额兹(Na-zigs),佣金说好是七钱(zo),在朱俱波(Khaga-)……在木木(Dmu-mu)等待,且从七钱涨至14钱。查封……。”[27]222这里所说的“Kha-ga-pan”,显然是指“喀格勒克”(qaghiliq)的最初形式,但不可能是“朱俱波”(čugopa)的等同对译。对此F.W.托马斯又指出:“音节pam,可能意为“路”,又见于Klian 之旧名(Kilpam 或Gilpam),它可能在于阗以西的相同地区。奥·斯坦因爵士认为此地就是现在的卡尔噶里克(Karghalik 或Kokyar),看来就Kha-ga-pan 之名来说,事实上已看到这个名称的最古老的形式。”[27]221可见,“喀格勒克”一名源于“Kha-ga-pan”一词,从词形构成看,由名词“khaga”和附加词“pan”构成,但在和田塞语中与“khaga”语义上相仿的对称词相对甚少,说明“Khaga”一词很可能是“khye”的音变形式,khyesa(喀什噶尔)一名在藏文文献中的另一别称“Gahjak”形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中不难发现,“喀格勒克”(qaghiliq)一名与西域大多是古老地名如Khye→Khaga,Khyeso→Gahjak,Khyeso→Kashgar,Kilpam→Kilyan,khaga→karghu一样,经过语音演变过程。据此可以推测,“khye”与“Khaga”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语义对应关系,然而“喀格勒克”(qaghiliq)虽有源自于“Kha-ga-pan”,但其语义仍保留“khye”之含义。据《和田塞语词典》,“khye”为“城堡、要塞”之意。①See Harold 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76.另外,上引附加词“pan”不完全表示“路”之意,有可能与“喀格勒克”(qaghiliq)名词后缀“ligh”(luq/liq)一样表示地点、场所。在和田塞语词汇中有与pan相似的一词,如vana,意为“居住地”。②See Harold 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383.该词又以vank 形式出现在古代亚美尼亚语,意为“被遮盖的地方、寺院”。③See Sten Konow.Saka Studies.Oslo:Glückstadt and Hamburg,1932,p.192.当然这与上述于阗佛教文化对其周边地区传播背景相合。
关于“Kha-ga”与“kargha”的演变过程,F.W.托马斯指出:“无论r 或者送气音(h 音)的词尾变化,两者都不妨碍我们对此文书的研究。看来,《大事记》26年(鸡年)即公元697年(第72行里),很可能记载了此地的另一名称Cu-gon-pan,见朱俱波(Ce-dog-pan)使者前来致礼。史料的日期是没有问题的,而名称上只需调动一个元音的位置,使之为Ce-dgo-pan,后者对于吐蕃人来说,相当接近他们早期与卡尔噶勒克接触时所记录的发音。”[27]221笔者认为这里的朱俱波虽为指棋盘,但Ce-dgopan 应为“喀格勒克”的另一别称,据此可知,当时吐蕃人入居叶城时,按照藏语发音特点又把“喀格勒克”称呼为“Ce-dgo-pan”(喀格半)。由此可以看出,“Ce-dgo-pan”似是目前文献上所见到的“喀格勒克”一名最早的译写,更确切些说是指“Khaga-pan”之讹写。不过“Kha-ga-pan”与“喀格勒克”(qaghiliq)之间也同样存在语音变体现象,但后者不仅保留原有的语义外,还按照回鹘语构词特点以附加词“ligh”(luq/liq)取代“pan”,可将其理解为此处有“烽火台、哨所”之意。这一演变情况在成书于北宋时期的《突厥语词典》中也出现,其文称“karghaligh-卡尔阿利格。怛逻斯城附近的一个城堡的名字”[28]卷1,549。看似该城堡不在我国境内,但其对“Kha-ga-pan”向“喀格勒克”(qaghiliq)的转化过程,也可以提供间接作证。同时该书中又收录与“qaghiliq”词根“qargha”有关的“Karghu”“Karghuy”“Karghči”等三个词条,均解释为“烽火台”“守卫、堡垒守卫者”[28]卷3,237-238。该词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还有“qaravulhana”“qaravul”“qaravulluq”“qorughuči”“qorulgax”等几种变体。可见,原为表示“要塞、堡垒”的“Kha-ga-pan”(喀格半)在回鹘人迁居后被“qarghu”或“qargha”一词取代,后来在11世纪时以“qarghaligh”形式出现。但这种变更只是一种原名和语义的保留,确保了该地名的稳定性。这一点在叶城土语部分词语音节中的元音u,o 替换a 现象中可见一斑,如,oghul→oghal,otun→otan,polo→pola等,这样自然将“qarghu”变成“qargha”。另外,由于r 音的脱落和又再加名词附加分lugh/ligh/liq 而最终演变qarghaliq(qarghu→qargha→+luq/liq→qarghaliq→qarghiliq→qaghiliq)。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于阗国在今叶城县乌夏巴什镇和皮山县克里阳乡之间以建造了“Khaga-pan”命名的一座要塞,无疑是考虑加强防御能力和扩张势力范围,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边境要塞和哨所功能。后来由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向喀什噶尔和莎车转移,叶城变成靠近边境即和田和喀什噶尔之间的边缘地区。元明时期叶城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变成名副其实的边境地区,清朝对叶城包括塔克布依在内所有地区的有效管理,使叶城社会得到进一步安定,成为守护西部边境的前哨。这一点在该名北宋至明代时期出现的“qarghaligh”“qarghälyq”“qarghaliq”音变形式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清朝治理新疆前期,该名因口头中r 音的脱落,演变称“qaghiliq”,为此在民间其语义也就自然说成为“乌鸦之地或乌鸦很多的地方”。《钦定西域同文志》《西域水道记》等清代部分典籍中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况。与此同时,叶城及周边原本为“烽火台、哨所”之意的一些地名,同样经口语变化,其语义均说成与乌鸦关联的地名,如喀尕买里(qagha mahalla-原为烽火台村,现说成乌鸦村),喀尕贝格(qagha beghi-原为烽火台边果园,现说成乌鸦果园),喀尕博依(qagha boyi-原为烽火台边的村子,现说成乌鸦巢边村),喀尕阿格孜(qagha aghizi-原为哨头村,现说成乌鸦嘴之头村)等。
四、结 语
叶城西汉时为西夜,后又为子合,其“悉居半”“朱驹波”“朱俱波”“朱俱槃”“斫句迦”等别称均为今叶城境内棋盘(čupan)不同时期的译写。“喀格勒克”(qaghiliq)一名,源于“Kha-ga-pan”,“Khaga”很可能是塞语“khye”的音变形式,为“城堡、要塞”之意。该词首次在唐武后神功元年(697)的文献中以“Ce-dgo-pan”形式出现,另外,9世纪30 年代末,回鹘人迁居该地后被“qarghu”或“qargha”一词取代,至晚在11 世纪时以“qarghaligh”形式出现。在语义上与“Kha-ga-pan”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后按照回鹘语构词特点以附加词“ligh”(luq/liq)取代“pan”,并保留原有语义“要塞、堡垒”基础上增添“哨所、烽火台”内容,以明确此处是“有哨所(要塞)、有烽火台的地方”。这正是当时叶城战略地位的进一步体现,尤其是清代前期中国近代国家版图奠定后,其演变为西部边境的哨所。18 世纪后期,由于在口头中r 音脱落,“qarghaligh”最终变成“qaghiligh”或“qaghiliq”,这样原本表示“哨所、烽火台”语义的“qarghaligh”一名因语音的变化又在民间中说成为“乌鸦之地或乌鸦很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