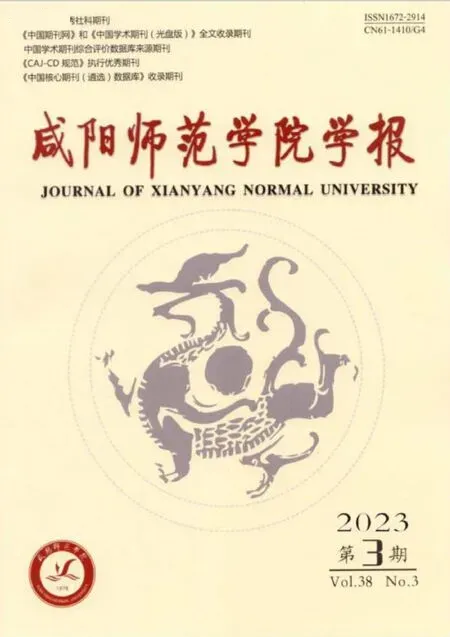《正蒙拾遗》的思想特点及其关学定位
魏 冬,韩师悦
(西北大学a.关学研究院,b.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正蒙拾遗》是明代中期关学代表人物韩邦奇对张载《正蒙》进行解释的一部作品。韩邦奇(1479—1555),明代陕西朝邑县(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境)人,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继王恕、段坚、周蕙等人之后,与吕柟、马理同时而齐名的重要关学传人。该书作于韩邦奇四十岁时。在此之前,韩邦奇已经研读《正蒙》二十余年,并曾因“张子《正蒙》无注”而著《正蒙解结》,用来解释《正蒙》中难以理解之处。后来,他陆续看到了兰江张廷式的《正蒙发微》和长安刘玑的《正蒙会稿》,认为该书兼取两者之长,故焚其稿。《正蒙拾遗》则是韩邦奇在《正蒙解结》之后因“近来《大全》《三注》及《会稿》注释者颇多,但张子大旨,似未全得,中间二三策,尚欠详明”①韩邦奇《性理三解》之《正蒙拾遗》卷首,见韩邦奇著、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上册),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本文凡引用《正蒙拾遗》均出自该书。而作的。由于明、清关学阵营中直接诠释张载之学的著作并不多见,而该书篇幅不大,但对张载思想有继承遮护且富推阐创见,故而对研究明、清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关系,研究《正蒙》学思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该书版本流传较少,传述作品罕见,所以本文对该书的主要内容、思想倾向、理论定位等情况予以简要介绍,以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先导。
一 《正蒙拾遗》的思想主题
与刘玑《正蒙会稿》对《正蒙》全文进行逐字逐句解释或全面概括章句旨意的解释方式不同,《正蒙拾遗》选取《正蒙》中的部分条目作以解释,这也是其之所以叫“拾遗”的由来。那么,这一著作表达出怎样的内容呢?通过对《正蒙拾遗》诸篇内容的提要,可以看出该书的基本主题。据本文统计,《正蒙拾遗》的解释涉及《正蒙》十七章内容,共对《正蒙》九十例文句作了解释。其每篇解释条文数及主要内容如下。
(1)《太和篇》。15 条。本篇主要内容有三:(1)高度评价张载。韩邦奇曰:“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所谓“气坱然太虚”是“非横渠真见道体之实,不敢以一‘气’字贯之”,“客感客形”是“横渠灼见道体之妙”,“以死为常,以生为变”是“横渠真见造化之实”、“爱恶之情,同出于太虚”是“横渠酌见性命之真”。(2)阐释天人性道。提出“太虚无极,本非空寂”“太虚未动,本至灵之气”,“幽明聚散,如环无端,幽即是明,明即是幽,但形不形耳”。提出“气未可以言道,由‘气化’可以言道矣”,认为“性道,一物也。存之于心,谓之‘性’,寂然不动者是也;发之于外,之谓‘道’,感而遂通者是也”,且曰“‘坱然太虚’,不是‘太和所谓道’”,主张“天地万物,本同一气。其成也,皆小而大,未有陡然而大者”,“天地亦有老时……亦以渐而没”,“今已到未字上,以后渐渐一代不如一代,天地将老,乃欲挽而为唐虞、三代正午之治,难矣!”并就气化而论人之生死,认为“吾生,本气之聚”,“气之未聚,吾之常”,“今死而散入无形,得吾本然之体也”,“何曾亡乎?”就气化而论人性,认为孟子性善论乃是“言人性固有欲,然万善皆备于性,非谓‘全无欲’也。”(3)批评诸儒之非。认为“宋儒于《中庸》解人道则是,于《易大传》解天道则非”“于《中庸》解天道亦是,而独于解《易》则非”,批评了宋儒以“道为太极”“谓‘天地非由积累而后大’”等观点。由上可见,本篇是韩邦奇关于天人性道等哲学思想的集中表述。
(2)《参两篇》。4条。本篇重点阐发了对天地结构、运行的基本认识和天文历法的计算方法。其最大特点是绘制了“天体度数之图”“日与天会之图”“一月月与日会之图”“一岁月与日会之图”“天日月运行总图”“闰月定时成岁之图”,以展示其天文历法思想,并节录了王蕃、蔡沈、张衡对天体运行、浑天仪制作的论述,“以便读《正蒙》者之考验制作”。本篇是韩邦奇天文历法思想的重要文献。
(3)《天道篇》。2 条。提出“学者造道之妙”是“不待言语形象”,但“若夫垂教于世,言象岂可已?”并感叹“天下之事,惟正为难守,最易眩迁。世之君子,不为死生利害眩迁者易,而惟不为名节道义眩迁者为难”。本篇重在论为学处世。
(4)《神化篇》。4 条。本篇与《太和篇》内容相应,提出“德为体,道为用”“德,天之性也;道,天率天之性行也,一于气而已”“蒸郁凝聚者,气之发用也。浩然湛然者,气之本体也”的观点,并赞叹“横渠洞见造化之实,异于世儒所见”。
(5)《动物篇》。2条。本篇亦与《太和篇》内容相应,从魂魄、五行方面扼要论述了气的变化和普遍性特征。
(6)《诚明篇》。3条。本篇亦与《太和篇》内容相应,提出“性是天之性,太极之理,体也;道是天之道,天率天之性,一阴一阳之迭运、化育、流行,用也。然皆实理也”。认为张载提出的“气坱然太虚”这一观点,是“自汉、唐、宋以来,儒者未有见到此者。是以不惟不能为此言,亦不敢为此言也”。与《太和篇》对孟子人性论的探讨相应,明确提出了“人之生,欲与善、气与理同受,但晓悟则欲在先而善在后”的观点。批评宋儒,认为“其谓‘下愚可移’,直自诬耳”,“看不透孟子之意,故多强释。于文义似矣,验之人,其实非然也”。
(7)《大心篇》。1 条。提出“内是心,外是耳目。心之明,由耳目之闻见、讲习、讨论之类”的观点。
(8)《中正篇》。1 条。针对张载“洪钟未尝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的观点,提出“洪钟本有声,圣人本有知”,并评价说“张子本意,谓圣人之教,无偏主,无预定,随人所问而答之。洪钟则扣有轻重,声有大小也。但其言抑扬太过”。由此亦可见韩邦奇非完全盲从张载,而是自有主见。
(9)《至当篇》。4 条。顺承张载“金和而玉节之则不过,智运而贞一之则不流”的观点并作出解释,提出“独立不惧,一家非之而不顾,一国非之而不顾”的人格观、“义流则非义矣,仁过则非仁矣”的仁义观和“终日乾乾,而凶惧可免”的处事观。
(10)《作者篇》。2条。认为张载提出的“以知人为难,故不轻去未彰之罪”是“千古大臣爱惜人才、养明养度之法”,对舜、汤、文、武作了扼要评价。
(11)《三十篇》。1条。承继张载“伏羲、舜、文之德不至,则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的观点,提出“麟至而夫子之文显于万世矣”。
(12)《有德篇》。7 条。提出“约信不可不谨,依人不可不择”的处世观,认为张载提出的“宵有得”是“指知而言,非谓‘夜气’也”。提出“本有其实,但无征,亦不可言。虽言,人不信,则人将效之为妄诈”“蔽固之私,一生于心,必形于外,岂可欺天而罔人哉”“因言不当而触乎人,人归罪于我焉”的观点,对汉高祖、昭帝作了评价。认为谷神不同律吕,“谷神皆随人之所呼而应,不能别有所应。律则一律为君,而倡之则六声应矣”。
(13)《有司篇》。2条。论述了夏、商、周三代助、贡法之不同。提出“治世赏罚明当,乱世赏罚颠倒。君子公于众也,小人便于己也”的观点。
(14)《大易篇》。25条。提出“看张子之易,当别着一眼看。若拘于平日之见闻,安能得其意!”吸收早期所著《易学启蒙意见》的主要观点,对《周易》的基本旨意、卦性、卦变、卦占原则有集中的讨论。解释了乾、坤等几个卦的卦辞,辨析了张载与朱熹易学在具体解释上的不同,可见其在易学上并不盲从张载和朱子。其解易多引申历史人物,借易评论了周公、汉高祖、高贵乡公、文天祥、李密、王世充等人物。同时,本篇与《太和篇》论题亦有相应之处,提出“太极,未尝无也。所谓‘无’者,万有之未发也;所谓‘有’者,有是体而无形也;‘未尝无之谓体’,太极也。”论述了气的聚散、隐显与生死的关系,提出“阴阳之气,聚而为显,万有之生也。阴阳之气,散而为隐,万有之死也。一幽一明,形而可见,故曰‘象’。一推一荡,是造化之妙,为万有之所以聚散者,孰得而见之,故曰‘神’”的观点。
(15)《礼器篇》。3 条。认为“君臣之际,其可畏哉!大臣之责,危疑之际,其难处哉!”提出“惟人主降辞色以诱之,则下情始得伸。上下之情既通,则谗毁不敢入”“谗毁不行,君臣孚信,上下交而德业成,令闻广誉,施及万世矣”的观点。评论了周公,认为“蔡子曰:‘公岂自为身计哉?亦尽其忠诚而已矣’,得周公之心矣。”本章重在论述君臣关系。另对卜、占之法有简要介绍。
(16)《王禘篇》。4 条。重点论礼,并就古今差异,提出“安可泥古而不酌之今哉”的观点。
(17)《乾称篇》。10 条。与《太和篇》相应,提出“‘虚’字为‘无极’字,‘神’字为‘太极’字,‘虚而神’,正是‘无极而太极’”,“‘性’是太极,寂然不动者也;‘不息’是造化,发育流行、感而遂通者也”,“造化发育,自其流行而言为‘道’,自其流行之妙而言为‘神’,自其流行之代谢循环不已者而言为‘易’,其实皆一而已”,“天地间,惟气为交密,虽山川河海,草木人物,皆气之充塞,无毫发无者”的观点,认为先儒对于张载“形聚为物,形溃反原”观点的争议,“是乃在册子中窥造化,不曾回首看眼前造化之实”“语其推行为‘道’,正乃‘太和所谓道’。古人未有如此说者,故多妄意于空寂之中”。同时批评佛教,认为“释氏亦窥见些子造化”,“将驱天下之人,使之为善,然欺之也”,“圣人之教以诚,释氏之教以伪。夫感人以诚,犹惧人之不从,况伪乎?”又认为“佛氏以死为归真、生为幻妄,亦只是主客之意。但‘幻妄’字便有个无用的意思”,“殊不知天所以为天,以其用之不息也”,所以“佛氏之教亦穷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邦奇在本章不但提出“自益益人,固贵不已其功,然须优柔有渐,间断固不可,急迫亦不可。此为学之要法”,而且对《东铭》作了解释,提出“《西铭》是规模之阔大处言天道也,《东铭》是工夫之谨密处言人道也。先《东》后《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圣贤之学,言其小极于戏言戏动、过言过动之际,无不曲致其谨,推而大之,则乾坤父母而子处其中,盖与天地一般大也。此《西铭》《东铭》之旨”,认为朱子独取《西铭》,失横渠之旨矣。
结合以上各篇的主要内容,可将《正蒙拾遗》的所论大致归结为如下五个论题:(1)天人性道:内容最多,思想性最强。以《太和篇》为主,在《神化篇》《动物篇》《诚明篇》《乾称篇》有所体现。(2)修身处事:内容较多,思想较为突出,以《乾称篇》为主,在《天道篇》《大心篇》《中正篇》《至当篇》《作者篇》《有德篇》有所体现。(3)易学历史:学术性强,内容较多,主要体现在《大易篇》《三十篇》《礼器篇》。(4)天体历法:学术性强,内容最多,限于《参两篇》。(5)礼乐制度:学术性强,内容较少,主要体现在《有司篇》《王禘篇》。由以上可以看出,韩邦奇在哲学、天学、易学、礼学、史学等各方面的观点于《正蒙拾遗》中都有所体现。《正蒙拾遗》是其思想学术表述较为集中的一部著作。而其中对天人性道、修身处事两个主题的探讨,则构成《正蒙拾遗》哲学思想的主体内容。
二 《正蒙拾遗》的思想倾向
韩邦奇门人白璧曾如是评价韩邦奇:“苑洛先生天禀高明,学问精到,明于数学。胸次洒落大类邵尧夫,而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少负气节,既乃不欲为奇节一行,而识度汪然,涵养宏深,持守坚定,躬行心得,中正明达,则又一薛敬轩也。”[1]1767其中“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一语,正可见韩邦奇在道体论方面对张载思想之继承发展,而《正蒙拾遗》正是韩邦奇这一思想特质的具体体现。通过《正蒙拾遗》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出于自家的生命体认和理性抉择,从而认同、赞扬、回护和阐发张载《正蒙》中关于道体的基本观点,正是《正蒙拾遗》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倾向。而这一倾向,乃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韩邦奇对张载极为认同,评价极高。自宋以来,理学家虽然对张载有所认同,但并未提高到超过程朱、直接孔子的地步。《正蒙拾遗》与之不同,其评价张载则曰“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评价《正蒙》则曰:“横渠《正蒙》多先后互相发明,熟读详玩,其意自见,不烦解说”(《正蒙拾遗》篇首),篇中又多次评价张载观点,数曰:“横渠洞见造化之实”(《正蒙拾遗·神化篇》)、“横渠真见造化之实”“横渠灼见道体之妙”“横渠灼见性命之真”(《正蒙拾遗·太和篇》),从对造化、道体、性命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张载见识的不同一般。韩邦奇又说张载“气坱然太虚”的观点是“非横渠真见道体之实,不敢以一‘气’字贯之”(《正蒙拾遗·太和篇》),“自汉、唐、宋以来,儒者未有见到此者,是以不惟不能为此言,亦不敢为此言也”(《正蒙拾遗·诚明篇》)。此中用一个“不能”、两个“不敢”,不惟道出韩邦奇对张载识见高明的信服,亦道出其对张载造道之勇的钦佩,由此可见韩邦奇对张载的服膺认同,非同一般。
其次,韩邦奇还阐释张载学说,提出自己创见。韩邦奇不仅高度评价张载和《正蒙》,而且通过对《正蒙》主要命题的揭示阐发自己的思想主旨,这是韩邦奇思想的主要创见之处。张载主张“天人合一”,韩邦奇基于对张载这一主旨的体认,不仅明确提出“吾读《正蒙》,知天人万物本一体也”[1]1358,把“天人万物一体”作为正蒙的思想主旨,而且明确提出“学不足以合天人、一万物,非学也”“学不足以一天人、合万物,不足以言学”[1]1358,把“一天人、合万物”作为自己为学的基本宗旨。韩邦奇还根据张载以气为本的思想特征和崇尚圣人的价值取向,提出“以天为气,志为圣人”的基本观点,这也是韩邦奇对张载”天人合一”论在宇宙论和价值论上统一的概述。在具体的解释上,韩邦奇承接张载,提出“张子曰:‘太虚无形,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又曰:‘知虚空即气,则无无。’察乎此,则先儒所谓‘道为太极,其理则谓之道’,老氏所谓‘无’,佛氏所谓‘空’,不辨而自白”[1]1358。众所周知,张载虽然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知虚空即气,则无无”等观点,但并未明确提出以“气”统一万有的观点,而韩邦奇则在对张载关于“太虚”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太虚无极,本非空寂”“太虚未动,本至灵之气”(《正蒙拾遗·太和篇》),而且更明确地说“天地万物,本同一气”,并具体阐发了关于气的存在状态是“通一无二”,天人万物的演化是“其始也,先有生,后有成;其终也,先消成,后消生”渐进的历史观。张载认为“爱恶之情,同出于太虚”,韩邦奇则明确提出“人之生,欲与善、气与理同受”(《正蒙拾遗·诚明篇》)。这些观点,将张载思想的气论特征进一步明确化、清晰化了。更为重要的是,韩邦奇基于对张载思想的认同,更为深入地探讨了天人性道的问题,不仅就性道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提出“道一物”的观点,而且就性道的存在状态作了区分,提出“存之于心,谓之‘性’,寂然不动者是也;发之于外,之谓‘道’,感而遂通者是也”(《正蒙拾遗·太和篇》)。基于此,韩邦奇还提出天有天之性、人有人之性,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道,然两者本质相同也。这也是从性道角度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推进和深化。从此可以看出,韩邦奇天人性道观其实是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发展,是《正蒙》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除此之外,韩邦奇在《正蒙拾遗》中还继承了张载天学学统,在《参两篇》重点阐释了天文历法并归之于“考验制作”,这也是张载关学注重自然科学、崇尚实践学风的具体再现,与纯粹注重义理和道德践履的其他正蒙注释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
其三,为了遮护自己对张载思想的理解,韩邦奇还对诸儒佛老进行了批评。首先,对朱熹独取《西铭》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韩邦奇认为,张载的《东》《西》二铭是相互支撑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西铭》是规模之阔大处言天道也,《东铭》是工夫之谨密处言人道也。先《东》后《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只有从《东铭》所主张的功夫论出发,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而“与天地一般大也”。故而“朱子失横渠之旨也”。韩邦奇对《东铭》的重视,突破了朱学偏重《西铭》的风气,对全面理解和继承张载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对诸儒的天道观提出了批评。韩邦奇批评了诸儒以“太极为道”“以理为道”的观点,提出“太极是不动时物,是理,道是动时物,安得以太极为道哉”!他还批评诸儒以“天地陡然而大”的观点,认为这只是“在册子中窥造化,不曾回首看眼前造化之实”,由此可见韩邦奇对张载注重考察现实学术态度的继承。其三,韩邦奇还继承张载辟佛老的观点对佛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在韩邦奇看来,佛教虽然对造化有一定的认识,也有导人为善的价值取向,但却没有看到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是大道的基本内涵,因此否定现实生命、否定现世生活,“乃诚而恶明者”也。“夫感人以诚,犹惧人之不从,况伪乎?”,“佛氏之教亦穷矣!”蔡尚思先生曾高度评价韩邦奇对佛教的这一批评,“韩邦奇批评佛教最中要害,既正确也痛快。直到近代的章太炎都似不知此说;即使知道,也未能起来反驳”[2]403,可谓真知灼见也。
需要注意的是,韩邦奇虽然认同张载,但并非盲从。在《正蒙拾遗》中,韩邦奇曾有几次对张载与他人观点的评述,以见其理性的认知态度。如针对张载“太和所谓道”和孔子“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提法,韩邦奇虽然认同张载的观点,但也指出“正蒙‘所谓’字,不如孔子‘之谓’字为的确,此又圣贤之别”(《正蒙拾遗·太和篇》)。再如针对张载和蔡沈的五行观,韩邦奇则认为“蔡子之说较稳实”(《正蒙拾遗·参两篇》),并不盲从张载。再如针对张载“洪钟未尝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的观点,韩邦奇提出“洪钟本有声,圣人本有知”,并评价说张载“其言抑扬太过”(《正蒙拾遗·中正篇》)。还有对张载“又有义命,当吉当凶、当否当亨者,圣人不使避凶趋吉,一以贞胜而不顾”的观点,韩邦奇明确提出“此节非《易》之本旨。夫《易》者,见几趋时,审力合道,以求万全,乃圣人之妙用,义命不足言也。横渠以‘吉’‘凶’二字,恐学者既不见几矣。及当其时,乃为偷生脱死、趋利避害之谋,故示之以此,以为未尽易者之防”(《正蒙拾遗·大易篇》)。由此可见,韩邦奇对张载思想所持的理性态度。虽然如此,韩邦奇对张载思想的整体认同是可以肯定的,《正蒙拾遗》最基本的思想特征,就是在理性抉择的前提下对张载思想的接受认同和开拓创新。
三 《正蒙拾遗》的思想定位
如上,《正蒙拾遗》最基本的思想特点是认同、继承和推阐张载思想。那么,如何评价《正蒙拾遗》的这一思想定向呢?窃以为,只有将《正蒙拾遗》置于相应思想视域下比较,方可看出其理论的价值,并对之做出合适的定位。在此,仅从韩邦奇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明代当时整个思想潮流两个维度,对《正蒙拾遗》的理论特征予以定位。
其一,从韩邦奇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正蒙拾遗》是韩邦奇思想历程的转折点,是其哲学思想的巅峰之作。根据韩邦奇的生平史料,他早年的学问基本出于家学,而以对朱子学的研究为主题。如韩邦奇在二十岁左右完成的《蔡传发明》《禹贡详略》都是以朱熹弟子蔡沈的《书传集》为蓝本,阐述其《尚书》学的著作;二十五岁完成的《易学启蒙意见》则是以朱熹与蔡元定共同完成的《易学启蒙》为蓝本,阐发其易学的代表作;三十七岁完成的《洪范图解》则是以蔡沈“洪范九畴说”为本,力求《尚书》学和《易》学贯通之作。蔡元定与蔡沈为父子关系,同出于朱子门下,故为一系。从此可见韩邦奇早年之学与朱子学的渊源。同样,在韩邦奇的早年著作中,虽然可以看到韩邦奇对朱熹卦爻法的改善,但对朱熹并没有激烈的批评,对张载也没有论及,故而其基本藩篱仍属于朱子学。与之相反,在《正蒙拾遗》中,韩邦奇则或明或隐地对朱熹的观点提出批评,却对张载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张载思想表示了高度的认同。这表明通过《正蒙拾遗》,韩邦奇思想已经实现了从推阐朱子到归本横渠的转变,所以《正蒙拾遗》是韩邦奇思想历程的转折点。再通观韩邦奇的所有著作,除了《易学启蒙意见》用“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圣人之心,浑然天理”两图表示了其“阴阳、五行、万物,不在天地之外,阴阳有渐,无遽寒遽热之理”基本宇宙观,并在《正蒙拾遗》中进一步用文字阐发,以及《苑洛集》卷十八《见闻考随录》中有零散的对《正蒙拾遗》思想深化的论题外,在韩邦奇的其余著作中基本都没有谈及对天人性道等哲学主题的认识。所以,把《正蒙拾遗》看做是韩邦奇著作中哲学思想的代表作,看做是其哲学思想的巅峰之作,看作是其思想转折的代表作,是完全适宜的。
其二,从整个明代关学的思想潮流中来看,明代关学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受当时整个理学思潮的影响,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主流的思想形态;另一个方面是受张载关学学风的影响,注重“以礼为教”的传统。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明代以及此后关学传承的基本底色。但从整个明、清思想倾向而言,普遍对张载自身思想体系的传述不甚重视。以对《正蒙》的注释为例,整个明、清时代,关学学者中也只有刘玑的《正蒙会稿》、韩邦奇的《正蒙拾遗》、吕柟的《张子抄释》等几部。在仅有的这几部对《正蒙》思想传述的著作中,刘玑的《正蒙会稿》相对于韩邦奇的《正蒙拾遗》早出,其重在传述本义而疏于创见;吕柟的《张子抄释》相对于韩邦奇的《正蒙拾遗》晚出,其也以抄为主,所谓的“释”,也基本在于点名段意,创见性亦有所不足。而韩邦奇的《正蒙拾遗》则以其对张载思想的高度认同和推阐创见最为突出。因此,可以将其作为明、清关学能传述《正蒙》之学的重要代表作。而韩邦奇不仅因能传承关学“以礼为教”宗风而与吕柟、马理等人并列关学干城,而且也因为这部著作,在张载思想的直接传承上拥有了更高的地位,清人刁包谓:“韩先生远祖横渠,近宗泾野,其学得关中嫡派”[3]卷一○○,这正是后世学人对韩邦奇关学特质的精当评价。因此将韩邦奇定位为关学阵营中能“发横渠英声”的学人代表,也就无所置疑了!
如上所述,韩邦奇的《正蒙拾遗》探讨了天人性道、修身处事、易学历史、天体历法、礼乐制度等多方面内容,体现了韩邦奇在理性抉择的前提下对张载思想的接受认同和开拓创新,是韩邦奇思想从“推阐朱子”到“归本横渠”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也是其思想学术表述较为集中的一部著作,更是明清关学能传述《正蒙》之学的重要代表作。韩邦奇“其学得关中嫡派”的地位,因为其能传承关学“以礼为教”宗风和此书对张载思想的继承推阐而得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