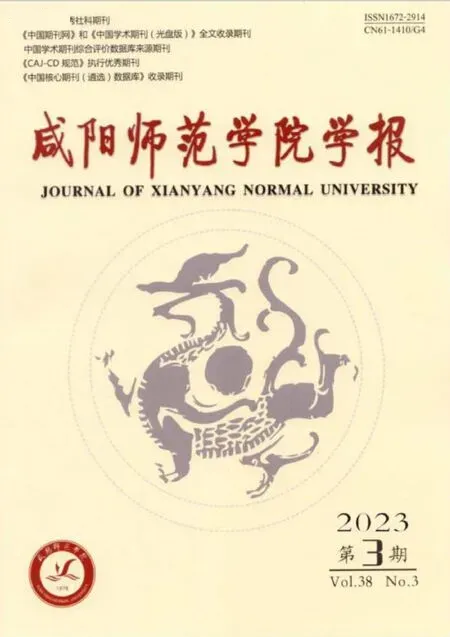以法正名:《商君书》“正名”思想研究
施阳九
(上海商学院,上海 200235)
春秋末期,“名”已成为探讨礼制或刑书的概念。它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表政治身份及其内容,一是指事物的称谓及其意义。在“正名”主题最初的探讨里,主要是以表政治概念的“名”为核心。直至战国中期,随着“变法”“历物”等思潮的发展,表指称事物及其意义的“名”才成为“正名”主题的重要范畴。
商鞅及其后学正处于“正名”两重向度在战国中后期乃至秦初的发展阶段,他们对“名分”“法令之名”的探讨亦是整个先秦“正名”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过去对《商君书》的研究基本都在法家理路中探讨,本文欲以“正名”思想的发展脉络为背景,解析《商君书》对“正名”相关问题的回应。
一 “正名”两重向度及其在《商君书》中的展现
据考证,《商君书》是由商鞅及其后学历经大约两百年编撰而成[1]191-204。此书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2]2。虽然各篇的写作风格与体例有异,但其思想前后较统一,有着清晰的思想沿承与发展脉络。其中,对“名”的直接表述以及相关“正名”思想的阐发,集中于被考证为战国末期至秦始皇统一天下阶段的诸篇①据学者考证,《商君书》各篇的写作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战国中期:垦令、境内、农战、战法、立本、兵守、开塞、君臣、立法等,这几篇被认为由商鞅所作。(2)商鞅之后至秦昭王时期:更法、说民、弱民、赏刑、徕民、慎法、外内、去强等。(3)战国末期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时期:算地、错法、壹言、靳令、修权、画策、禁使、定分等。可参见黄效《〈商君书〉各篇的作者、创作时间及其成书考》,载《管子学刊》2021年第1期;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特别是被认为最晚出的《定分》篇[3]129-136。如:
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今先圣人为书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4]145
在该段文字中,“名”既有表政治名分,也有表法令之名。前者涉及的是政治权力与秩序的运作,后者触及法令之所谓的解释,属于事物指称的确定性探讨。但无论哪一种“名”,其“正”都离不开《商君书》的“法”。从孔子正式提出“正名”以来,正名分与正名谓一般属于不同问题意识的“正名”向度。可在《商君书》里,这两重向度似乎被统合于它的“法”思想之下。
为了更清晰地解析《商君书》的“正名”思想,有必要先对这两重“正名”向度及其问题意识予以简要梳理。
“正名”一词最早出现于记载了晋文公施政纲领的《国语》中,但“正名”思想主题的开启是以《论语》“必也正名乎”章为标志的。因为前者的“正名”只是确定社会各等级所能享有的食禄,而后者则是“治国之本”[5-6]。对于孔子的“正名”,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其“名”是表政治身份及其内容的“名”,还是关于事物称谓认知的“名”,这将直接影响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理解。
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认为此“名”是表政治身份及其内容的“名”,此类“名”包括名号、名字、名位、名分等,区别则在于其立论的依据及方式不同。古文经学家根据《春秋》与《左传》所记载的史事认为所正之“名”乃“世子之名”,而今文经学家则脱离史事,依据公羊学“以王父命辞父命”的正义原则来解释作为政治身份的“名”本身应该如何确立[7]。不过,从民国开始,不少学者以西方逻辑学重新解释战国中后期的名实论,并基于此把孔子的“正名”纳入其中。这里,有的以意象与意指、或称谓与定义概念来解释名实关系,如胡适[8]40-41、冯友兰[9]72-73等;有的则从逻辑学的概念、判断与事物的本质属性来分析名实论[10]175-176。近年来,有学者希望以思想史的视角来重读孔子的“正名”。于是,以曹峰[11]109-114、苟东锋[12]为代表的学者区分了孔子“正名”之解释史与孔子“正名”原处于的思想史阶段的不同,并在探源了“名”内涵之变迁的基础上重新选择了表政治身份及其内容的“名”:“孔子的正名说与早期名学的名分义是一脉相承的”。
各解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地,但以《论语》以及孔子所处的时代而言,其“正名”之“名”本身的语义应该是清晰可释的。在《论语》里,除了正名段落外,其余五处“名”不外乎以下三种意思:人或物的一般称呼(不涉及语言认知的反思);表名声、名望;表政治身份及其内容的名号、名位、爵名或名分①《论语》其余五处“名”分别是:(1)《阳货》:“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名”即表一般对象称谓。(2)《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称者,铨也,衡也,等也。《荀子》有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在当时,常以“称”相言的不是名声、名望,而是表政治身份的“名”。君子厌恶的是一辈子都没有做出与自己所处之名位或名分相称当的事。(3)《子罕》:“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依据达巷党人与后文孔子言六艺来看,此“名”是名声、名望之义。(4)《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里所成的“名”具体是指君子之名。孔子认为,君子有君子应该做的事,主要是仁与礼,换言之,为仁与循礼就是君子的名分所在。因而,此“名”应归属名分之名。(5)《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里的“名”与《老子》“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中的“名”类似,即因功德之大而无法给予任何与之相称的名位。。由于孔子是在回答“为政奚先”时提出了“正名”,所以“名”的意义应该明确为表政治身份及其内容的“名”。
这样的“名”不是一个单纯的称呼,而是一个关乎是否拥有合法政治权力的身份证明。在周礼中,只有拥有如此的“名”才能够运用政权、祭祀权、族权以及财权[13]。“名”的效力保证在于王有着征伐的权威。但在孔子的时代,“王”的权威衰落了,就算明晓名分权责,不遵循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其用意并不是要确定“名”所对应的权责,因为僭越并非因权责不清导致,而是要让僭越政治权力的现象被约束。正如牟宗三指出的,“孔子言正名,主要目的是在重典礼乐,重整周文之秩序”[14]63。重整的关键并不是所谓的名实权责的相符,而是建立有效的约束力,即内在的道德约束。孔子认为,在约束力之下,“名”的权力下达与执行才会得到保证,言事、礼仪、刑罚都将顺利地被执行与遵守[15]892。
虽然《论语·子路》中的“正名”不是在讨论名实相符的问题,但孔子确实已经涉及礼制中名物相符与否的问题。比如,斛之名所对应的斛之形制或实际用途出现了不符的情况[15]412。与此同时,在郑国,较早于孔子的子产因推行“铸刑书”而引发了以邓析为代表的“辩刑名”。从“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16]488的记载来看,刑名的辩释与运用在刑书公布于众之后变得纷乱起来,如何确定刑名的意义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春秋末期这两条思想史脉络几乎是平行发生的,它们共同开启了以事物指称义之“名”为核心的另一重“正名”讨论。
在战国初期,虽然礼崩已无法挽回,但孔子提出的“正名”及其相关问题,即政治秩序为何失效、应该如何有效建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如何得到有效运作等,则成为了战国时代的共同思想主题。尽管诸子没有直接用“正名”一词来点题式探讨,但都不约而同地参与了孔子“正名”的思考与回应。此外,有关指称事物之“名”的讨论也愈发多了起来。不过,依然以孔子“正名”讨论为主。比如,墨子虽然提出以“取”的概念来探析“名”之意义的确定性[17]687,但其论述的核心依然是以兼爱与尚贤来回应政治权力与秩序的问题。
到了战国中后期,指称事物之“名”因“变法”与“历物”思潮而得到了更丰富的思考。前者需要通过确定“名”的含义来清晰解释法令与新制度;后者则以指称事物之“名”为切口,展开对“物”的思究。这为战国后期的名实、言辩、名法等思想的发展与兴盛提供了现实实践与理论储备。而“正名”的新向度也在此阶段得到了发展,其基本问题意识是如何确定“名”的意义。
综上,先秦“正名”两重向度各有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其考察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末期,这两重向度的考察一般都是分开进行的。但从《商君书》的《定分》篇来看,商鞅及其后学的“正名”似乎并没有各自讨论,而是在其变法思想下,将这两重向度予以了统合。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正政治名分还是正法令之名,皆以旧制与新法的讨论为基础,两者的理路逻辑是一贯统一的。
二 对儒家“正名”方法的批判
儒家的“正名”方法是援仁入礼,即把周礼解释为基于人本有的内在之仁而外化了的道德践履。通过对“仁”的体认与实践,人们就能够内在约束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遵循其他名位给予自己的职责。这样,周礼得以恢复,名分将重新拥有效力。其实质是用内在道德来约束周礼的施行。对此,商鞅及其后学予以了反驳。
(一)反思亲亲之仁爱
《商君书》的批判切入点是儒家的亲亲之爱。商鞅及其后学没有否认过人具有亲亲之仁爱这样的自然倾向,也从未像道家那样去否定仁义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其质疑的是,仅仅顺从亲亲之仁爱这样的自然倾向并外化建立相应的制度就一定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吗?他们认为不能。理由有两点:
第一,亲亲之仁爱所能导向的并不一定是可以平天下的无私之善。属于战国中期篇目的《开塞》有曰:
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4]51-52
这里描述了三个社会阶段,即亲亲而爱私的上世、崇尚贤者教化爱人的中世,以及设立明确等级制度与禁制的下世。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世似乎都是在前一世的不足之上发展而来的,而其中最为“不堪”的恰恰是儒家理论的基础——亲亲之仁爱。
按照儒家的解释,人之爱亲是天生而有的自然倾向,礼就是顺此建立起来的。对此,商鞅学派并没有否定。他们认为,在最初之时,没有什么宗法礼仪,男女媾和繁衍后代,孩子只知母不知其父。即使如此,亲亲的仁爱已经存在了。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虽然爱自己亲人这个倾向是人人皆有的,但所爱的对象、结果、方式却是特殊有别的。这意味着,亲亲其实是一种基于普遍自然倾向的“私”爱。在现实里,当人们遇到各种事物时,基于私爱到底是导向爱更多的人,还是导向自利之恶呢?与儒家认为爱亲就可以顺利把爱推及他人不同,商鞅学派认为,世人会把私爱视为目的,甚至把私爱作为行事原则,而这将极大可能地产生自私的恶。如果儒家无法把亲亲之仁爱从逻辑上自恰且必然地推及非亲之他人,那么以亲亲之仁爱为基础的礼又如何能有治理天下的自信呢?
第二,仁义只能够自我内在约束,即使形式化为礼制,一旦出现“非礼”时,也只有众议谴责而已,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属于战国末期篇目的《画策》指出: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4]113
仁人能够仁爱他人,仁爱他人是仁人自觉主动的行为,可仁人并不能用仁爱去要求别人必须仁爱他人。因为仁爱这种自然倾向只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约束力,不具有外在强制力。如果把仁爱作为一种必然要做到的要求强加于他人,要求他人也必须爱人,这不就是道德绑架吗?世人自然不会认同。此之谓“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既然仁义本身有如此之不足,那么基于仁义而形式化的礼就是一套建立在自觉主动性之上的松散的制度,是不能必然地达到“正名”重整政治秩序、恢复政权效力的目的的。
不过,《商君书》从未彻底排斥仁义,只是认为仁义不应该直接成为政治制度本身的构成环节,应把仁义排除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与执行判断之外。同为战国末期篇目的《靳令》有曰“仁者,心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商鞅及其后学应该是认同仁义之于社会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通过仁义这种品性,可以调节社会的各种关系,尤其有助于君、臣吏、民三者关系的融合。但仁义的施行应该有限度,即不可悖于最高权力者所制定的政治规定,只有以“力”平天下之后,才可“述仁义于天下”[4]82。
(二)重审人性
儒家“援仁入礼”的理路有一个重要缺陷,即仁义本身是否拥有普遍有效性。当孔子之时,对仁的理解多以“爱”为主。但“爱”是一种情感,是不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有效性的。既然如此,如何能基于情感而建立稳固的制度呢?或许在孔子之后,儒家也意识到了仁爱本身的这个不足,所以他们越来越重视一个概念,即“性”。儒家开始把“性”作为仁爱的牢靠根据,并认为人性中的向善自然倾向才是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
虽然其他诸子对援仁入礼总予以不同视角的批判,但儒家希望通过人的内向性来论证外在制度之有效性的理路,却被后世诸子所接纳,他们纷纷加入了探讨“性”的行列,且以此来建构政治秩序。《商君书》亦是如此。
商鞅及其后学并不像道家那样关注天下万物的“性”,他们所关注的只有人性。但与思孟学派秉持人性善且“同然”又不一样,他们认为,人性的内容非常丰富,但能够成为政治秩序基础的,则需要结合“时”予以选择。
对于人性,《商君书》进行了重新审视,讨论主要集中于战国末期的篇目,其内容大致有两方面:
第一,人天生所拥有之“性”的内涵,并不像孟子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向善的道德之性,还有趋利避害、知学、求欲等等。《算地》有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4]45
第二,圣人与民在日常中所展现的“性”似乎并非同然。也就是说,趋利避害、向善、知学、求欲等等都属于“性”的范畴,不过,并不是所有人在现实中都必然地展现出“性”的所有内容。民之性主要表现为趋利避害,即使是知学、欲求或遵循某事物也因利害而起。与民不同,圣人则像离娄拥有超越常人的敏锐视觉、乌获天生就有能举起千钧之重的非常力量一样[4]126,其所展现的“性”可超越趋利避害而达到绝对的“善”,比如“必信之性”[4]113。需要注意的是,圣人并不等同于君主,“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4]110。
正是基于这种两分的人性观点,《商君书》需要考量政治秩序建构的人性基础到底是两者兼顾,还是只选其一。
《画策》有曰:“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治理天下需要必然性,而非或然性。而其“必然性”需要“人性”,但不能只依靠人性:因为“人性”虽是天生而有的,但只是具备必然的可能,而非现实必然如此。现实的“必然”还需要“必为之时势”。“势”指所要借助的外力。在《商君书》里,治理天下所需要的“势”就是“民之情”或“国俗”:“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4]62-63
《商君书》指出,当时的“民之情”“国俗”已不同于过去,诸国以力相争得利是总时势。而民众的自我意识越来越突出,更加敢于表达与追求自己之所欲所利[4]56。大多数人并不否定等级社会,但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方式来获得社会的高等级及其相应的待遇,而非只以出身世袭来决定[4]20,11,111。此外,政治上公私不明、官吏体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税赋徭役漏洞大、农垦不足等亦是困扰统治者与百姓的亟待解决的问题[4]85,133,6,7。
基于这样一个趋利的时势,且政治制度最终的施行者不是圣人,而是王、官吏和百姓,其“性”的主要表现为趋利避害,所以,商鞅及其后学最终选择只以“民之性”作为政治制度建构的人性基础。如此,不仅能够有效地化解诸多政治难题,也能让百姓更加自愿地遵循制度,“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4]59。
综上,由于个人内在仁爱的自律并不能必然保证社会最终导向善,也不能使政权得到必然的效力,所以,商鞅学派认为,儒家的援仁入礼其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礼崩的问题,达到“正名”的目的。在重审人性、考察时势之后,他们指出,只有彻底改变旧有的政治权力的组织构成方式,建立一套基于趋利避害之人性的新制度,才可以彻底解决礼崩所产生的各种政治问题,才能让各等级的“名”再次拥有效力。
三 以新“法”正“名”
《商君书》对“法”的变革目标就是对“法”进行修正、变更及创新,使“法”成为全国统一、至上的明文规定。《商君书》中的“法”与过去的“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新“法”的特征
“法”,刑也。刑者,罚辠也。西周以前有“殷罚”,主要内容是对“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等行为予以惩罚[18]1899。在过去,“法”实质是一种秩序运作的辅助性规定,只有当人们背离了礼,“法”才会起作用。然而,《商君书》的“法”不是辅助性的,而是关涉政治权力之获得、运作、分配的根本性制度。其重要特征如下:
第一,获得政治权力的重要方式不再是宗法,而是军功与官吏仕途。这种新的权力获得途径,不仅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还能够推动当时民众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国家富强的价值实现中。
第二,明确权力结构及其权限。新“法”的权力结构是由上至下的“君主—官吏/官爵—民”。
就君主而言,其权力是至上且不可分享的,“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4]82。其权力之至上性现实表现在三方面,即君主对官吏之执行权与解释权的授予权、君主对官吏的赏罚权[4]132,61,以及“法”的制定权[4]83。
不过,君主的权力虽然至上,但其权力的运用依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不可凭权力随意修改“法”[4]66;二是权力行使必须无“私”[4]84-85。区分“公私”是商鞅及其后学不断强调的一个重点,“私”的内容大致有五个方面,分别是:涉及宗亲、姻亲的人伦关系[4]51;大臣家中君主无权任意干涉的私人关系[4]60;官吏的利己违法行为[4]6,16;百姓个人的各种行为或价值[4]18;民间通过辩说、议论等方式表达的各种有关政治的观点[4]68,104。“公”则是指“法”规定的所有权力与规范。比如《壹言》“上开公利而塞私门”,此“公”是指“法”所规定的获得权力的各种途径,“私”是指卿大夫等大臣所能给予的门客利禄。
就官吏而言,其设置与权责都应依据“法”的规定,“为法令,置官吏”[4]140。特别的是,商鞅学派认为,由于新“法”条例数量不少,且涵盖领域众多,要让官吏体系良好地运作起来,就需要设置一个关键官职,即“主法令”。其权责是:准确地让官吏执行法令以及让所有人知晓法令。如果其他官吏或民众前来咨询某个法令之“所谓”,主法令不仅要有问必答,而且要依据咨询者所遇事之缘故有针对性地进行解答。
如果说一般官吏拥有执行法令的权力,那么主法令在受命于君主后将实施法令的解释权。解释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不仅有利于降低官吏体系的腐败问题,亦能提高民众的公平感。犹《定分》所言:“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4]144当官吏与民众都知法、守法,社会秩序与国家发展目标都将可以顺利实现。
第三,君主应该有监督官吏的责任,并应赋予民众监督的权力。《禁使》有曰:“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保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监。”商鞅学派指出,只有利害关系相异的双方才能够有效地实施互相监督。君主自然不希望看到自己授命的官吏贪污腐败,所以君主监督官吏是可行的。此外,虽然民众可能会欺瞒君主,却会监督官吏是否违法渎职,因为民众与官吏正好是管治者与被管治者的关系,双方的利害关系相异,所以,民众之于官吏的监督亦是有效的。
综上,如果说过去的“法”一般是指规定了社会行为规范的“刑法”,那么商鞅及其后学所要建立的新“法”的性质则发生了改变,乃一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比起传统的礼制,新“法”对于权力的构成、分配,权责的规定与具体运作都不再以亲亲尊尊为基础,也不由各种礼仪来呈现。新“法”的权力由下而上集中于君主,并以严苛的惩罚来保证各级权力的有效展开。如此,有关政治秩序及其效力的“正名”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二)在新“法”中正“名”
如果说春秋时期子产铸刑书、邓析辩刑名,只是就刑法的形式与内容予以有限范围内的改变与讨论的话,那么《商君书》则是要彻底建立一套新的权力组织方式。虽然亦曰“法”,但此“法”的内容已经远远大于过去的刑书,是对政治权力秩序的规定。由于新“法”需要明文规定且颁布于众,所以作为法令构成要素的“名”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正是如此,《商君书》触及了“正名”的语言认知向度。
在《商君书》的新“法”里,“名”有三种意思:
第一,有关户籍的名册[4]17。此“名”只作称呼,不表达更多的意涵,“名”的字面意义与其名所谓的对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这种“名”,无关正名与否。
第二,“法令之名”,即“法”中的各条例与规定。法令之名就与名册之名不同了,它们有着明确的意义指向。即使没有解释法令的法官,通过法令之名本身的字义,亦可理解。比如,“无宿治”这条法令之名,从字义来看,就是没有或者禁止隔夜治理。但法令之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的意义是在“名”本有的意思的基础上,由最高权威者赋予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同样以“无宿治”为例。“无”一般有两义——没有或者通“毋”表禁止。由于一“名”有两义,就会产生歧义。如果是“没有隔夜治理”的话,可以理解为官吏工作需要的时间很长,没能在第二天给出处理方案;如果是“禁止隔夜治理”的话,那么意思可以是官吏不应该隔夜治理,要么当天处理,要么认真讨论研究过几天再给出解决方案。可见,“无宿治”这个法令,由于“名”本身具有歧义,所以整条法令就会出现意义纷乱,非常不利于法令的执行。不过,这种歧义在新“法”中得到了解决。因为所有的法令之名都将由最高权力者予以明确的意义规定,并且由主法令向各层官吏与民众明确告知。正如《定分》有曰:“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可以说,与邓析之时相比,法令之“名”的指称义已经被最高权威明确规定,不用担心其意思有分歧。即使出现分歧,法令之名的解释权也最终由君主决定。此即正法令之“名”。
第三,名分之“名”。礼制中,名分之名一般有两类:一是以血缘人伦为基础的名分,比如父、伯、叔,嫡子、庶子等;一是官爵名分,比如诸侯、卿大夫、士等。礼制中的名分之名其实就是社会、家庭或政治身份,而每个身份都意味着将拥有相应的权力与责任。不过,由于商鞅及其后学是把宗法血缘与政治权力分离的,所以新“法”所涉及的几乎都是官爵名分。
在《商君书》里,名分之名与法令之名一样,都有着明确的指称对象及意义。不同的是,法令之名的意义尽管有歧义,却还是可以从“名”的字义中直接呈现出来。但名分之名的意义是无法从“名”本身的字义体现出来的,而是由各名分的权责来赋予的。比如,“君”这个名分之名所蕴含的意义,并不是“君”本身字义所赋予的,而是由新“法”中君主所拥有的各种权责来充实的。与儒家不同,商鞅学派对名分之名的理解完全把德行排除于规正名分之外。也就是说,个人德行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外在条件,并不会决定名分之名的所谓对象及其蕴含的意义。君之所以是君,臣之所以是臣,不是由其德行决定的,而是由新“法”规定的各名分的权责决定的。各名分的权责就是名分之名之所以为此“名”而非他“名”的依据所在。犹如《定分》有曰:“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
此外,在《商君书》里,名分之名还多了一层意思,即事物的名分,类似于当今的所有权。其《定分》有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4]145为何一只兔子在跑,会有一百个人同时去追,而市场上售卖的兔子,即使挂满了市场,也不会有人去拿?因为市场上的兔子为某个商贾所拥有,而奔跑的兔子并不归属于任何人。事物之名分所涉及的问题其实很重要,比如,为何以某种方法获得的事物就可以属于自己?如何让他人也能够认同这事物是属于自己的?这些问题既无法用仁义道德来裁决,也不可能因地宜约定俗成,只能通过“法”来明文规定,由最高权力及其惩罚制度来保障实施。
不过,无论是哪种名分,都是由“法”来确定名分的权责,权责决定了名分之名的意义为何。这亦是《商君书》中的正“名”。
四 结语
孔子的“正名”问题是政治向度的,其问题意识是如何重新确立各“名”的有效力,其“名”表政治身份,涉及政治权力。在《商君书》看来,儒家的援仁入礼无法解决“名不正”的困难。在反思仁爱、考察时势、重审人性的基础上,商鞅及其后学提出了新的“正名”方法,即建立新“法”。通过权力组织关系的重塑、各名分权责的确定、严苛惩罚规定的确立,确保既不会发生“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等臣强主弱的现象,也能够让“愚智遍能知之”,从而保证各“名”的权责效力、执行与遵守。
此外,由于新“法”的制定与运作都离不开法令条例的解释与执行,所以又涉及了以确定指称之“名”意义为问题意识的语言认知向度的“正名”。不过,《商君书》对“名”的意义之确定是通过外在的政治权力来实现的,并没有从“名”本身所蕴含的规定性来探究,也没有涉及对名实关系的思考,更多的是现实实践中的应用。
可以说,在《商君书》里,先秦两重“正名”向度问题皆因其“法”的建立而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