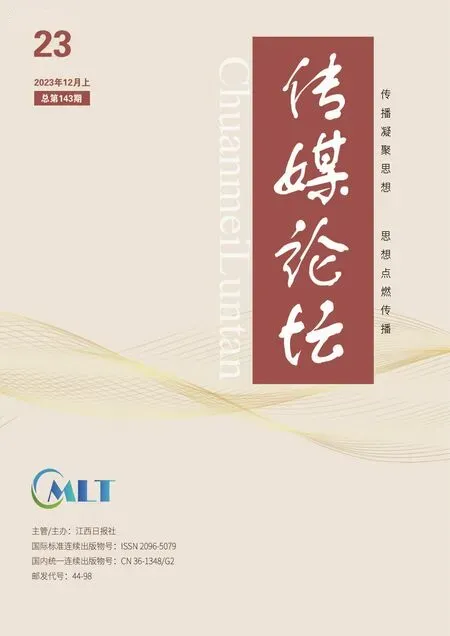数字影像赋能乡土文化:内在机理、多元表达与振兴路径
程 文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所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然而,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剧烈变迁,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遭到侵蚀,乡土文化正处在被人遗忘的境地。回顾人类文化发展史,媒介形态和信息技术的更迭深刻地影响着文化传承发展的形态与方式。在现代进程中,影像作为新兴的视觉媒介,已经成为乡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城市移民群体的乡土记忆,也构建着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广袤的乡土社会孕育着悠久的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是指根植于广大农村地区的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涵盖特定区域的民风民俗、文物古迹、沿革变迁等有形的文化,亦包括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无形的文化”[2]。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乡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乡土社会不断受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乡土文化面临解构、异化甚至消失的现代性危机。就文化自身的传承而言,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当前农村教育在教学内容、方法以及价值观念上都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实现个体的现代化与社会化为目标进行教化培育,培养离开农村的城市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加之,在城乡二元差异格局下,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谋生,农村正在走向“空心化”,导致由亲属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乡土文化彻底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守护乡土记忆,传承好乡土文化,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命题。
在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以数字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也在逐渐崛起。正所谓“一图胜千言”,相较于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获取信息,人们更愿意通过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感知现实世界。这一现象标志着在日常信息传递中,具体形象的影象比抽象概括的文字更易被受众所接受,即社会文化传播转向视觉化。“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实际上是通过复杂的视觉活动而建构起来的”[3]。在新媒介时代,数字影像可以重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数字影像成为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媒介,它不仅能通过影像实践活动再现乡土社会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像主客体互动关系来拓展、创新、重构乡土文化。
二、数字影像赋能乡土文化的应用逻辑
自19世纪以来,影像技术先后经历胶片影像时代、电子模拟影像时代。而20世纪以来,第三次影像技术革命兴起,电影、电视、DV以及新兴的网络视频等各种影像的制作与传播全面迈入数字化,将传统的以胶片、磁带为载体的模拟影像转为以数字文件为介质进行记录、储存、传播。
(一)空间逻辑:以影像记录的逼真性复原乡村空间
乡村和城市是人类聚落空间的不同形式。乡村空间由村落、民居、院落及公共空间等构成,是一种明显区别于现代城市的具有特定边界的地域范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乡村空间与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相互渗透,成为乡土文化得以存在的载体,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具有感化教育功能。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传播媒介,数字影像以声音和画面组成的表意系统能够直接记录现实世界的空间状貌和逼真地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视听综合、时空一体的表现方式使得数字影像具有其他任何艺术和技术无可比拟的复原能力,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感知空间的范围,甚至是联结、重塑空间。数字影像通过对许许多多实体乡村的影像记录,建构出一个庞大的虚拟乡村空间,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边界开始模糊。城市向往乡村成为当前社会影像受众普遍的代偿心理。
(二)情感逻辑:以影像语言的审美性传承乡土文化
作为一个时代的视觉印记,影像以其特有的方式完成对社会现实的想象与构建。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所言“影像是被投入意义的现实”。在让·米特里的美学观念里,影像最初属于知觉层面,即影像本身,是现实片段的物象再现。按照特定的语言表达规则,影像转换为符号,符号再经过审美创造具有诗意,即影像成为艺术。
影像通过可看的画面和可听的声音来抒情言志,通过屏幕上的艺术形象使人们获得思想熏陶、情绪感染和审美愉悦。影像创作者的风格和能力都会影响最终呈现的视觉效果,进而影响受众对客观现实的感知。“艺术家不仅是生活的探索者,也是崇高精神财富,以及那种独特的诗意美的创造者。”[4]优秀的乡土文化影像创造者总是在真实书写的底色上,描绘乡村生活中蕴藏的诗意和情感,守护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人文情怀。
(三)主体逻辑:以影像传播的互动性增强身份认同
随着多媒介融合发展,数字影像的传播形态呈现多元化:一是以影院为代表的大屏幕公共领域;二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小屏幕私人领域。两种形态并行不悖,甚至大多数情况呈现出多屏传播与社交互动的媒介传播新态势。
电影、电视大屏成为优质数字影像作品传播的主流渠道,选择与家人朋友集体观影,探寻审美与情感的共振是影视的魅力所在。在急遽变化的现代社会,社群在个体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个体建立情感联结的需要。而影院作为社交活动的载体成为寻求集体认同和情感共鸣的理想场所,不再满足于浅层的影像奇观化消费需求,而是在群体共情中感受乡土文化的影像魅力,回望故乡、寻根乡土成为越来越多的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同时,乡土文化以影像为文本实现全网跨平台覆盖,在影像传播过程中创作者与受众在新媒介空间中实现多维互动,点赞、评论、收藏、转发等一系列行为已演进为充满仪式感的网络社区互动规程。多屏互动传播打破以往电影、电视线性传播的局限,实现数字影像受众因“屏”而聚,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增强身份认同,重拾乡村文化自信。
三、乡土文化影像化传播与传承的多元表达
乡土文化影像的创作者扎根大地,用影像描绘广袤的乡间一隅,书写着乡土中国优美宜居的外在风貌以及和谐共生的思想意蕴。根据创作主体以及创作观念、方式的不同,乡土文化影像可以分为复制式、纪录式和参与式三类。
(一)为国修志的复制式影像
复制式影像主要指利用影视手段对具有重要价值的乡土文化,尤其是正被破坏甚至濒临消亡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地记录。其表现手法追求客观、真实,排斥艺术效果渲染。复制式影像记录的核心是要达到对乡土文化的真实反映,重视对乡土文化中公共性活动及其动力的记录和探寻,为未来保留当下具有现实和历史价值的乡土文化影像资料。
复制式影像多是由学术研究机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主导进行摄制,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有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中国记忆”影音文献项目等。这些项目以“为国修志”为使命,通过影视技术手段对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节日、史诗演述、非遗项目进行系统性地拍摄记录,目的在于抢救与挖掘濒危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制式影像的文献价值将不断递增,成为相关学者开展研究工作的第一手影像文献。
中国节日影像志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地采用影音技术记录传统节日文化的国家级文献工程。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传统节日可以弘扬具有家乡特色的乡土文化。但在社会的发展中,传统节日文化在农村地区有逐渐淡化的趋势。为了反映社会发展中的节日现状,中国节日影像志以“真实、客观、完整”为基本原则,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拍摄完成200多个节日,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积累宝贵的影像资源。以春节为例,中国节日影像志共有二十多个项目组进行记录拍摄,如《甘肃环县红星村春节》《北京郊区村落的春节》《湖南花垣机司村苗族春节》《山东曲阜三峡移民春节》等,以多维度视角构筑中国最古老最盛大的春节影像志。
(二)诗意表达的纪录式影像
纪录式影像是指以乡村乡土及其文化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影视作品,包括纪录片、新闻片、宣传片等影视体裁,由电视台、影视公司、传媒机构制作,并通过电视等媒体面向大众播出。以乡土文化为对象的纪录式影像数量众多,其中尤以纪录片深受广大观众熟悉和喜爱,如《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美丽乡村》《中国村庄》等,成为普通观众了解和获取乡土文化的重要渠道。
系列纪录片《记住乡愁》堪称乡土文化纪录片的典范之作。该片以“关注古老村落状态,讲述中国乡土故事,重温世代相传祖训,寻找传统文化基因”为宗旨,用充满艺术感的镜头和诗意性的表达展现传统村落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悠久醇厚的历史文化,让每一位离开故土的游子都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导演张曙丽在创作手记中说:“当我们向前奔跑的时候,别忘了回头看看来时的路;当我们仰望浩瀚的星空,别忘了星星就在脚下。”观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过程,宛如一场对“美丽的乡愁”做出深情的回望和凝视的时光之旅,让身处在都市中的人们重新认识当下美丽乡村的富饶与幸福,彰显出乡土文化意蕴和时代价值。
与复制式影像相比,纪录式影像更加注重当下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一部热播的乡村纪录片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一个媒介热点甚至是以超乎想象的热度进行裂变传播,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受到无数拥趸的追捧。以《记住乡愁》为代表的纪录片,通过故事化呈现、诗意性表达彰显出纪录式影像助力乡土文化自信的强大价值,在传播乡土文化的过程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成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消解“现代性乡愁”重要的历史见证。
(三)自我赋权的参与式影像
参与式影像是指农村社区居民拿起摄像机记录、传播自身周边的乡土文化影像。“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5]成为参与式影像最著名的一句宣言。虽然影像早已渗透到乡土文化的各个层面,但影像的使用依然存在不平等的一面。在过去,乡土文化的传播者通常是记者、导演、学者等城市文化中的精英阶层,他们介入到农村社区,凭借话语阐述和媒介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乡土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他者”传播。但随着DV、相机、手机等影像工具的极大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新技术为广大村民搭建起一个开放、平等、自由的乡土文化传播平台。
参与式影像在国内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精英对广大村民的发起文化赋权,以云南社区影像实践为典型代表。21世纪初,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郭净教授在云南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区影视教育”,“利用影像的方式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乡土知识传承”[6],后发展为旨在培训中国西部地区广大农牧民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和传承乡土文化的“赋能”公益行动。第二阶段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极大普及,对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新青年实现技术赋权为代表。随着短视频行业成熟,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年活跃在自己生长的乡村热土上,拍摄了海量的乡村美食、田园风光、传统技艺、历史掌故等多种多样的素材,并借助各大短视频平台进行分享、互动。新时代的乡村青年以数字影像为媒介为家乡代言,唤醒大众乡村记忆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对乡土文化的身份认同和形象建构。
四、数字影像赋能乡土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从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历史中的乡土中国正在迈向新发展阶段。以数字影像赋能乡土文化,以乡土文化滋养乡风文明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时代之义,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需求。
(一)以数字乡村为依托,建立乡土文化集体记忆库
用数字影像保留乡土记忆,是信息化时代大力推进乡土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为指南,创新发展乡村数字文化,推动乡土文化资源数字化。系统梳理乡土文化谱系,从地理和历史两个维度开展村落民居、古建遗存、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名人传记等多方面的数字影像采集与制作,尤其是对濒临消失的乡土文化开展抢救性记录和永久性保存。
推动乡土文化数字化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数字文物资源库”,建立以数字影像为核心,集文字、图片、音频多文本为一体的乡土文化集体记忆库。以厚重的人文关怀、强烈的纪实风格影像传播乡土文化,展现传统乡村的山川地貌、人文历史、风土人情。
(二)以自我赋权为理念,增强居民主体性保护意识
乡土文化的传承应以农村社区原居民为主体。在“人人都是影像生活家”的媒介时代,乡土文化在社区影像的介入和影响下呈现出生动的变化过程。社区影像倡导将摄像机由外来者手中传递到社区居民手中,赋予本土居民参与乡土文化发展的权利。以社区影像为力量,彰显本土居民作为创作主体的个性表达,培育和提高本土居民的文化觉悟和文化自信。
建立社区影像制作与传播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居民群众在乡土文化上进行自主保护、传承、教育的积极性。借助政府、高校、社会等多方力量,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的影像素养。在参与社区影像的过程中,能够让村民重新认识本土本乡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进一步增进农村居民的文化认同,引导更多的乡土人才扎根故土,赋予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以文化空间为载体,打造吸引用户的视觉体验
作为农村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文化空间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重要桥梁。乡土文化空间的设计与营造,不仅要布局合理、和谐美观,适宜开展多彩的文化生活,更要充分拓展其内在功能,彰显乡土文化之美。
充分利用和拓展现有文化空间,如文化礼堂、村史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和设施,引入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结合实景空间、全景影像、三维动画,构建乡土文化VR/AR展示装置系统,通过视听化、艺术化的影像语言再现乡村生活,打造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的乡土文化体验场域。这些举措打破了文化传播在时间、空间、频次方面的限制,更加生动地展现乡土文化的魅力与活力,有利于形成对乡土文化的整体性感知。
(四)以网络技术为驱动,实现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播
以5G网络建设为契机,为乡土文化传播构建多维度、立体化传播矩阵。依托数字乡村建设,以手机为“新农具”,以网络技术为“新农资”,借助互联网平台,打破传统电视台、电影院播出时单向线性传播的局限,实现乡土文化影像差异性、延续性、互动性传播。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乡土文化传播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抖音、快手、B站等短视频平台传播乡土文化,实现多终端、立体化的融合传播,让更大的受众发现身边的乡土文化之美。以影像为力量,释放乡土文化潜能,产生更多的乡村网红,让更多的意见领袖为乡村发声,避免在“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代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流失。同时,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小红书、豆瓣等平台进行分享与评论,实现乡土文化影像的跨平台二次传播。这些传播手段不仅推动乡土文化影像的多元发展,促进乡土文化受众群落的形成,更能将乡土文化从固有的文化圈层带入大众视野,有利于缩小城乡文化领域的“数字鸿沟”,构建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
五、结语
媒介传播方式的迭代让文化传承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乡土文化的延续随着现代媒介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数字影像作为媒介已融入当下乡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对“以影像为媒,各美其美”的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传承的物质形态基础。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背景下,厚植乡土文化,让新时代的乡村建设保有难能可贵的“土模样”,成为身有所栖、心有所依、人人向往的和美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