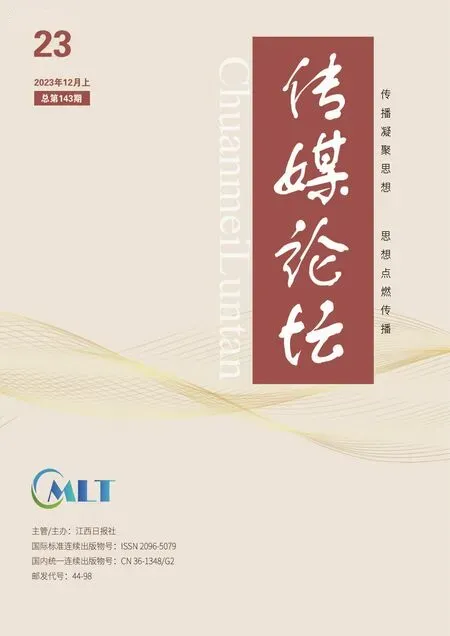人工智能时代提升朗诵能力的路径探究
李 飞
人工智能合成音在当下的应用比较广泛,技术日趋成熟,逐渐打破了之前语言机械单一,缺乏语气和语流的技术壁垒。这对播音主持教学也带来了着极大冲击。面对技术的革新,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朗诵技能。因为朗诵艺术凝聚了播音主持专业有稿播读中的核心技巧。结合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提高朗诵的语言技巧,面对AI智能合成音的挑战。
一、理解稿件,寻找情感依托
对于稿件的理解,大的方面可以从文章的写作背景、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写作风格,文章的主题等方面切入。小的方面,要对文章中的借代、隐喻、用典进行细致的分析,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
如李清照的词中常出现“黄花”一词。在朗诵她的词时就需要了解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个人的人生境遇,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情感依托,为情真意切的表达做准备。以《醉花阴》为例,结尾三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进一步明确她因别离而相思,因相思而憔悴。此词写于崇宁二年(1103年),是她嫁给太学生赵明诚的第二年,由于丈夫“负笈游学”,加之重阳佳节,对丈夫有着浓浓的思念。除了词人的丈夫在佳节远游,因为她的父亲李格非身陷朝廷党派斗争,她与父亲也不能相见。这一年,她的父亲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由于朝廷党争激烈,其父“元祐党人”的罪名也株连到她身上。多重心事的交织,让诗人憔悴不堪,也倍感孤寂。易安巧妙使用了“珠帘”这一带有阻隔感的意象,让西风卷起珠帘,惊窥到帘中人已消瘦如斯,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更加强烈;使用“瘦”字时,不直说人之瘦,而是与节后即将不断衰萎的黄花对比,人比花瘦,情感力度也更进一层。通过深入理解文章中的核心词语,明白其深意,理解作者的境遇,这样在朗诵中才能有情感依托,调动起播讲欲望。
二、通过联想想象,引发情感共鸣
在全面理解稿件的基础上,在朗诵时,还需要演播者通过想象,将一个个文字符号变成活动连续的画面或场景,设身处地地感受文本作者所处的环境,理解文章想要传达的情感意图,这样更能调动自己的情感,实现朗诵者与文章作者、演播者和朗诵作品的共鸣。
而这些共鸣,通过声音的呈现,让听者也能通过想象,身临其境地走入文本内容所营造的场景当中,和朗诵者一起置身情景交融的境界,领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意蕴。如李白的《清平调·其一》对杨贵妃花容月貌般的美丽的描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作者没有直接描述杨贵妃的样貌,而是借云朵联想到她飘逸华美的衣裳,更有一种风姿绰约之美。对于她的容貌,作者借牡丹卓尔不群之姿赞叹其国色天香之貌。因此这种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者运用借代和比喻来描绘传达,这就需要朗诵者和听者一起运用想象联想,进入诗人营造的意境。
又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四句诗中不带“孤寂”一词,但写出了在寒冷寂静的环境中,一位老渔翁竟然不畏严寒风雪的专心垂钓的形象。老渔翁的身影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这也映射了作者的心志。在朗诵时,只能通过想象和联想来体味作者的这种人生况味,走进这种寂寥、孤寂之至又不失追求和等待的心境。通过联想想象,借助于意境的营造,最终实现朗诵者和听者在情感上的共鸣。
三、运用节奏技巧,提高语言的感染力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这样论述:“艺术家往往倾向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1]各门艺术的艺术传达方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制作方法和表现手法,这使得艺术技巧和手法在艺术传达中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2]
朗诵艺术是情感、声音与气息的融合,也需要运用艺术技巧和手法,将文本的内容和其背后的情感传达出来。在面对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带来的冲击时,朗诵的声音想要具备生命活力,亟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解决节奏平的问题
经过对稿件的理解,通过想象联想激发起极强的播讲欲望,但如果没有恰如其分的语言技巧,这些情感通过单一的声音外化出来,仍旧不具备感染力,缺乏生命活力。艺术技巧的运用像盐溶于水,有味无痕。
要彰显朗诵的生命活力,打破朗诵中容易出现的“读书腔”“念书调”,需要我们掌握声音高低和文本内容的配合,如“百炼成钢”一词,声音形式会高而强一些,而词语“花红柳绿”则显得低而柔一些。同样是低而柔的“晓风残月”,气声会多一些,相对偏虚,情感偏冷。
又如当代作家张永枚的《斧头之歌》,在关于抗美援朝期间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中,“白色的羽毛。云,白色的鸟群。”这句话一共出现了三次。根据上下文的内容,“白色的羽毛。云,白色的鸟群。”这句话的三次出现需要运用不同的声音形式进行演播。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开头部分。因此,在朗诵时,选用陈述的语气,声音相对柔和,情绪波动不大。在它第二次出现时,是在一位朝鲜阿玛尼被敌人炸死后,当志愿军班长看到老妇人的血流了一地,想到她对志愿军深深的爱和无私的帮助,愤恨地说道:“雪,是白色的羽毛吗?云,是白色的鸟群吗?不,雪是漫天凝结的泪花。”在该处朗诵时,“云”和“雪”的声音比较急促,以偏强的实声为主。这句话第三次出现,是在“斧头以顽强的生命在班长手中飞舞砍呐,朝敌人砍去!美制的钢盔栗子壳一般地裂开。斧头在杀杀的歌唱,一首复仇之歌。带血的斧头,冒着热气。敌人的尸体,纵横在脚下。班长屹立在战友们中间,手里紧握着老妇人留下的斧头。”这个叙事段落之后,结合上文,此时朗诵的语气是一种释然的,悲壮的情感交织。因此,在朗诵该句话时,声音音高稍强,与第二次的表达相比,语速稍快一些,声音稍显明亮一些,但情绪是悲壮的。
在语速上,要轻重缓急进行结合。根据语意和作者情感的变化,让语言节奏赋予变化。如读到《口技》:“遥闻深巷中犬吠,便有妇人惊觉欠伸,其夫呓语。既而儿醒,大啼。夫亦醒。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又一大儿醒,絮絮不止”时,语速要舒展。而到了“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众妙毕备……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语速达到全文里最快的部分。通过抑扬顿挫的节奏之美,让真挚的思想感情更加完美和谐地呈现出来。
(二)要解决情感单一缺乏主次之分的问题
一篇文章作者在写作时就注重叙事的主次之别,有的内容三言两语简单概括,有的洋洋洒洒成百上千字细细描绘。因此,我们在朗诵时要依托文本,将情感进行浓淡、轻重的区别,而不能字字用情、句句着力。在语言表达上做到,准确、鲜明、生动。例如《白杨礼赞》:“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根据语意不难发现,重点句子是“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这一句,在朗诵该句时就需要情浓而声高,语速稍微偏快。
又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虽然细腻描写了与父亲分别的场景,但纵观全文,重点内容是作者两次感动落泪的地方。分别是:“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和“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有了对文章的主次把握和情感浓淡的区别,语言才会更加丰富生动。
除了以上两点,想让语言表达技巧更接近完美,还需要在朗诵之余,练习基本的语音发声,让吐字圆润舒展、富于变化,掌握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语气、停连、重音、节奏这些语言表达中的内外部技巧。最终达到恰切的思想感情与尽可能完美的语言技巧的统一。
四、真情实感贯穿朗诵创作始终,彰显声音的活力
情感是艺术构思和创作不竭的动力,艺术家只有在炽烈情感的浇灌下,才能完成艺术创作。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这样解读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内在生命和灵魂,没有审美情感就没有艺术。著名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认为:“音乐是不借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的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的空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动着的血液。”狄德罗也同样指出了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3]。朗诵作为语言艺术也亦是如此,它的音韵之美,它的意境之悠远朦胧,直击人心的情感冲击离不开创作者炽烈真挚的情感。
例如,作家臧克家在《有的人》一文中,总结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的选择和归宿,以此来歌颂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尚节操和精神。正如诗中所写:“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朗诵该作品时,朗诵者需要深切感知作者对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和腐败统治者的深恶痛绝,和对鲁迅这样像野草一样甘愿奉献的仁人志士诚挚的爱和发自内心深处的赞扬。同样都是活着,一个充满着作者的鄙夷和否定,一个流露着作者的赞美和歌颂。作为朗诵者,也需要像作者那样有着发人深省的情感的迸发,用真情实感来传达作者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心声!
让朗诵向生活汲取那些亲切真挚、鲜活动人的情感,才是有声语言的创作源泉,我们积极的人生态度、丰富的生活情感、主动的内心体验才是有声语言的源头活水。“让朗诵映照生活”,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可以使我们“思接千里,触类旁通”,就可以使我们打开心灵,张开触角,在朗诵中学会感悟、在生活中学会欣赏,学会为“真、善、美”感动,学会为“假、恶、丑”愤怒、用诗文培养自己“审视美的眼睛”和“辩音律的耳朵”、更重要的是用朗诵培养自己“健康而湿润的心灵”。在朗诵创作中,需要在艺术体验、艺术构思、艺术传达中将真情实感贯穿始终,始终秉承“传情达意,心口如一。”
例如,在朗诵当代诗人艾青《光的赞歌》这篇歌颂光明、鞭挞黑暗的政治抒情诗时,需要理解作者对于光明的解读,正如诗中所写到的:“每个人的一生/不论聪明还是愚蠢/不论幸福还是不幸/只要他一离开母体/就睁着眼睛追求光明。世界要是没有光/等于人没有眼睛/航海的没有罗盘/打枪的没有准星。”诗中除了对光明的赞扬,也有对害怕光,制造黑暗,维护黑暗势力的人的抨击和斥责。作者在诗中这样斥责道:“但是有人害怕光/有人对光满怀仇恨/他们占有权力的宝座/一手是勋章、一手是皮鞭/一边是金钱、一边是锁链/进行着可耻的政治交易/完了就举行妖魔的舞会/和血淋淋的人肉的欢宴。”
真情实感的拥有,需要朗诵者在演播时,多一些“童真”,少一些功利。如明末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里所倡导的,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欲望。即文中所说的“童子者,人之处也;童心者,心之初也。”[4]又如作家林语堂在四十岁生辰所写的自寿诗中表述的:“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拥有一个“童心”才会让情感更加诚挚和纯真,才能通过鲜活的声音将情感传递出来。
音色承载着质感,呼吸承载着生命,言语承载着精神。切切实实地让受众感受到传播主体和他们是同质的肌体,是亲切的灵魂[5]。唯有如此,我们的声音才真正拥有了生命的活力,我们的朗诵才不会畏惧科学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压力,让有声语言散发着不朽的生命活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