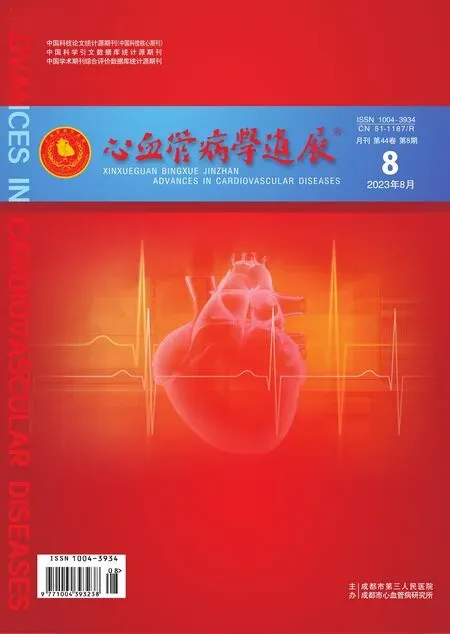女性乳腺癌相关性心房颤动的研究现状
杨仙 陈芸霖 殷跃辉, 易鑫 杨敏 崔犇
(1.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院,重庆 400010;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重庆 400010)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影响了全球2%~4%的成年人[1]。2020年GLOBOCAN报告[2]显示,乳腺癌已经超越肺癌成为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病例数约占同年女性新发癌症总数的1/4。随着人们对肿瘤心脏病学兴趣的增长,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女性乳腺癌患者AF风险高于普通人群,但二者之间的联系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既往研究[3]提示,AF的发生可能与恶性肿瘤的治疗有关,如手术、化学治疗(化疗)和放射治疗(放疗)等,以及二者的共同危险因素和病理生理途径。此外,女性是AF-CHA2DS2-VASc评分中的危险因素之一,乳腺癌的高凝状态会使缺血风险进一步增加,但恶性肿瘤本身的代谢紊乱及抗癌药物的使用会增加出血风险,使此类患者的缺血及出血风险难以预测。目前,乳腺癌合并AF患者的抗凝策略尚无定论,仍是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难题。
1 流行病学研究
乳腺癌和AF的共病率正逐渐增加,女性乳腺癌确诊后会表现出更高的AF风险。以色列北部的一项队列研究[4]表明,新发乳腺癌在诊断后的前90 d内发生AF的风险增加(调整后HR=3.40,95%CI2.06~5.61)。D’Souza等[5]报道了丹麦早期乳腺癌患者的AF发生率在乳腺癌确诊后6个月~3年呈增加趋势。Guha等[6]对85 423例年龄≥66岁的美国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发现,乳腺癌诊断后新发AF的发生率在30 d为0.6%(95%CI0.5%~0.7%),6个月为2.1%(95%CI1.9%~2.4%),1年为3.3%(95%CI3.0%~3.5%),而非乳腺癌组新发AF年发生率为1.8%(95%CI1.6%~2.0%);而且,该研究中乳腺癌组的AF患病率(14.5%)远高于年龄≥65岁女性一般人群(8.5%)[7]。一项中国上海的单中心研究[8]纳入了706例乳腺癌患者,其AF患病率为2.97%,高于中国一般女性人群的1.70%。由此可见,女性乳腺癌与AF在流行病学上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 乳腺癌相关性AF发生机制
2.1 共同危险因素
2.1.1 年龄
高龄是AF不可逆转的主要危险因素,AF的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可能与高龄引起心肌纤维化及窦房结功能减退有关。乳腺癌的发病高峰多在绝经后,高龄也是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因素。一项基于人口的癌症数据分析[9]对全球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了评估,发现中国乳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在2000—2012年期间均明显上升。高龄是乳腺癌和AF的共同危险因素,可能在乳腺癌患者AF的发生中起着潜在作用。
2.1.2 肥胖
一项荟萃分析[10]发现,体重增长和较高的体脂率增加了绝经后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其中雌激素受体阳性亚型与肥胖相关的证据最强。肥胖也是AF发生的危险因素,肥胖的存在会引起炎症、左心房扩大、心肌脂质增加、间质纤维化、电活动传导减慢及异质性增加,导致自发性和诱导性AF增加[11]。持续的肥胖可能通过影响瞬时外向钾电流和L型钙离子通道的表达,引起心房不应期缩短[12],导致心房电重构而诱导AF。
2.2 病理生理途径
2.2.1 炎症
恶性肿瘤本身是炎症聚集体,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等炎症因子均存在于恶性肿瘤中,其可能通过调节心房电生理变化及心肌纤维化等,诱导心房电与结构重构,触发AF。另外,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是乳腺癌微环境中最突出的细胞类型,是介导肿瘤炎症的关键,可通过激活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介导促炎信号释放,诱导心肌纤维化[13]。而且,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炎性小体激活的触发物(如肽聚集物、氧化线粒体DNA)以及其引起的氧化应激和细胞质钙水平的增加均与AF特别相关[14]。因此,炎症是乳腺癌和AF的共同病理生理状态,乳腺癌的炎症状态会促进AF的发生。
2.2.2 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是肿瘤发展和化疗反应的重要表现,可能导致肿瘤患者新发AF的风险增加。髓过氧化物酶是一种促氧化酶,可通过诱导心肌纤维化而诱发和维持AF。另外,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是心肌超氧化物产生的重要来源,其活性过高时,活性氧生成增加,通过介导氧化应激,改变钾、钙等离子通道活性,诱发心房氧化损伤和电生理重构,增加AF易感性[15]。
2.2.3 自主神经系统
心脏受到丰富的自主神经支配,其中位于心房的心脏固有神经与房性心律失常密切相关。自主神经系统激活时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释放肾上腺素,通过蛋白激酶A信号通路,激活蛋白激酶A,进而影响钠、钾、钙等离子通道,引起心房电生理变化,诱发AF[16]。另外,β肾上腺素能刺激可增加Ca2+/钙调蛋白结合,激活钙调神经磷酸酶,通过改变基因转录,诱导肥大和促纤维化基因表达程序,导致心房结构重构[16]。因此,乳腺癌中可引起自主神经系统激活的因素,如疼痛、发热、感染、紧张情绪等均可通过上述机制引起心房结构和电重构,诱发和维持AF。
2.3 肿瘤相关治疗
2.3.1 手术
手术是乳腺癌患者发生继发性AF的常见诱因之一。Guzzetti等[17]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表明,与非肿瘤手术的患者相比,接受乳腺癌手术的患者AF患病率增加(2.0% vs 0.6%)。Guha等[6]对乳腺癌患者进行的队列研究表明,与局部肿块切除术等简单手术相比,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等复杂手术具有更高的AF发生风险。手术诱发的心肌离子通道相互作用、高炎症水平、过度氧化应激及术后低氧血症都可能是术后AF的潜在机制[18]。
2.3.2 化疗及靶向治疗
心脏毒性可能是癌症患者抗癌治疗最显著的不良反应之一,乳腺癌患者多见于顺铂、环磷酰胺、吉西他滨、曲妥珠单抗等。顺铂的心脏毒性主要在于DNA损伤,其次还可能诱导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引起钠、钙等离子稳态改变,促进炎症反应,诱导心肌纤维化[19]。环磷酰胺与顺铂类似,另外其还可通过激活p53和p38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途径,导致心肌细胞凋亡、炎症和肥厚[20]。吉西他滨也与新发AF有关[21],这可能与心肌细胞中高能磷酸盐化合物的耗尽导致的缺氧有关[22]。曲妥珠单抗是一种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乳腺癌治疗的关键。一项基于诸多临床研究的荟萃分析[23]证实曲妥珠单抗增加了乳腺癌患者AF的易感性。在小鼠模型中,曲妥珠单抗改变了DNA修复和基因表达,促进了心肌的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诱导心脏毒性[24],触发AF。
2.3.3 放疗
放疗是肿瘤患者发生AF的另一危险因素[25]。暴露于电离辐射会增加血管水平发生炎症的风险,促进心肌纤维化,且电离辐射会以剂量依赖的方式增加心力衰竭和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25],以上都是AF的既定危险因素。Guha等[6]对乳腺癌患者进行的队列研究表明,植入放疗在AF发展中比束放疗风险低,可能是由于放射质粒植入乳房后的心脏剂量较低。
2.3.4 止痛治疗
癌症晚期通常需使用缓解癌性疼痛的药物,包括非甾体类抗炎药物(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NSAID)和阿片类药物,这二者都与AF发生有关。Chokesuwattanaskul等[26]研究了NSAID与AF的关联,表明使用NSAID的患者比未使用NSAID的患者AF发生风险更高,这可能是因为NSAID阻断了前列腺素合成,通过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扩张血容量,增加左心房压力,导致心房结构重构;通过肾远曲小管排钾减少,引起高钾血症,增加心肌细胞复极异质性,导致心房电重构。Lee等[27]进行的回顾性研究表明,使用吗啡的乳腺癌患者AF发生风险明显高于未使用者,但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阐明。
因此,乳腺癌相关治疗(手术、化疗、靶向治疗、放疗、止痛)可能会通过上述机制诱导心房电和结构重构,增加乳腺癌患者发生AF的风险。而且它们之间的共同危险因素(年龄、肥胖)及病理生理状态(炎症、氧化应激、自主神经系统紊乱)也可能是乳腺癌患者发生AF的重要机制。
3 AF合并乳腺癌患者的抗凝治疗
抗凝治疗是AF治疗的基石,在乳腺癌合并AF患者中也不例外,但目前缺乏指导恶性肿瘤患者AF治疗的具体指南。尽管如此,《2019 AHA/ACC/HRS心房颤动患者管理指南》的最新报告[28]提出了,与所有AF患者一样,肿瘤背景下的AF患者若男性CHA2DS2-VASc评分≥2分或女性≥3分,建议长期抗凝。《2022 ESC心脏肿瘤病学指南》[29]支持上述建议,并进一步完善了此类患者的抗凝建议,仍参照《2020 ESC 心房颤动诊断和管理指南》[1],当男性1分、女性2分时,也必须考虑长期抗凝;但抗凝药物的选择需根据个体化病情而定。
3.1 维生素K拮抗剂
华法林是临床上广泛使用的维生素K拮抗剂(vitamin K antagonist,VKA)类抗凝药物,也是预防AF栓塞事件的主要抗凝药物。Connolly等[30]进行的INVICTUS研究表明,在风湿性心脏病相关性AF患者中VKA比利伐沙班导致的心血管事件或死亡的复合发生率更低,且没有更高的出血率,再次证明VKA是瓣膜性AF抗凝的唯一选择。但VKA始终存在局限:(1)华法林主要通过细胞色素P450酶系统代谢,凡能影响该途径的药物和食物均会与华法林产生相互作用,影响抗凝效果;(2)华法林治疗窗窄,国际标准化比值必须维持在2.0~3.0,需频繁监测,依从性下降;(3)肿瘤患者易出现恶病质、肝肾功能障碍、化疗后恶心呕吐等,都会影响抗凝效果;(4)出血问题,尤其是在转移性疾病中。
3.2 低分子量肝素
长期以来,建议合并静脉血栓栓塞的肿瘤患者优先选择低分子量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LMWH也常用于住院AF患者的抗凝治疗,但LMWH对AF患者卒中或全身性栓塞的预防疗效尚未确定,其使用仅基于其在静脉血栓栓塞中已被证实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9]。《2022 ESC心脏肿瘤病学指南》[29]建议存在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15 mL/min)、非维生素K拮抗剂口服抗凝剂(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NOAC)药物-药物相互作用、血小板计数<50 000/μL的AF患者,可考虑选择LMWH。但LMWH是针剂,需每日2次皮下注射,不便于长期使用,依从性低。
3.3 NOAC
NOAC包括Xa因子抑制剂(艾多沙班、阿哌沙班和利伐沙班)和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达比加群)。
ENGAGE AF-TIMI 48试验[31]的亚组分析比较了艾多沙班与华法林在活动性恶性肿瘤合并AF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在1 153例新发或复发的恶性肿瘤(胃肠道肿瘤、前列腺癌、肺癌等)合并AF患者中,高剂量艾多沙班(60 mg,每日1次口服)比华法林在卒中、系统性栓塞、心肌梗死的复合终点中更有优势。ARISTOTLE试验[32]评价了阿哌沙班与华法林的疗效和安全性,对1 236例合并有活动或既往肿瘤病史(前列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的AF患者进行的亚组分析显示,在AF合并活动性肿瘤患者中,阿哌沙班比华法林能更有效地降低栓塞、心肌梗死和死亡的联合终点,出血风险也明显下降。ROCKET AF研究[33]对利伐沙班和华法林进行了综合分析,合并肿瘤(前列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的AF患者使用利伐沙班和华法林的疗效和安全性与非肿瘤患者相似,抗凝疗效不劣于华法林。达比加群是目前临床批准的唯一一种可逆结合凝血酶活性位点的直接凝血酶抑制剂,但RE-LY研究[34]没有对AF合并肿瘤患者进行亚组分析,故无法评价其在AF合并肿瘤患者中的疗效。
在恶性肿瘤患者的静脉血栓栓塞治疗中,NOAC具有与LMWH类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更优越的便利性[35-37]。而且,NOAC是乳腺癌合并AF患者在辅助激素治疗期间进行抗凝治疗的一种有效和安全的选择[38]。因此,NOAC不仅是AF抗凝的新宠儿,也将成为乳腺癌合并AF患者预防全身栓塞事件的新选择。
NOAC也存在劣势。(1)NOAC的代谢途径依赖于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系统(达比加群、艾多沙班、阿哌沙班和利伐沙班)和CYP3A4型细胞色素P450(阿哌沙班、利伐沙班)[39]。而许多化疗药物是P-gp及CYP3A4的抑制剂或诱导剂,二者联用会影响抗凝的疗效或安全性[40]。例如,他莫昔芬是一种用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药物,可以抑制CYP3A4和P-gp途径[41],与NOAC联用可能增加出血风险,应避免联用。(2)NOAC的肾脏清除率各不相同,达比加群为80%,艾多沙班为50%,利伐沙班为35%,阿哌沙班为27%[42],因此肾功能不全会影响NOAC的吸收和代谢,使NOAC的药物暴露增加,加剧出血风险。《2022 ESC心脏肿瘤病学指南》[29]不建议肌酐清除率<15 mL/min的患者使用NOAC。(3)血小板减少也应得到重视,通常与化疗、骨髓肿瘤侵袭等有关。因此,在使用NOAC时应密切监测血小板水平,当血小板计数<50 000/μL时,应避免使用NOAC[29]。
综上,对于女性乳腺癌合并AF患者而言,瓣膜性AF患者抗凝的唯一选择仍是VKA;而非瓣膜性AF患者可根据病情首选NOAC,尤其是亚洲人群[43];如果存在严重NOAC药物相互作用、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血小板减少或NOAC不能耐受时,则慎用NOAC,优先考虑VKA或LMWH;无论选择何种抗凝药物,其治疗方案都应实现个体化。
4 AF合并乳腺癌患者的其他风险
乳腺癌不仅增加了AF的发病率,还增加了AF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6]。(1)女性是CHA2DS2-VASc评分的危险因素之一,乳腺癌的高凝状态及抗癌治疗使缺血风险进一步增加[6,44],导致合并乳腺癌的AF患者卒中风险增加;(2)乳腺癌及抗癌治疗引起的心脏结构重构,不仅会诱发AF,也会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27],而且AF本身也会诱发心力衰竭,增加死亡风险;(3)女性的QT间期比男性长,抗乳腺癌治疗(他莫昔芬、CDK4/6抑制剂等)会进一步延长QT间期[45],更易导致长QT综合征或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增加死亡率。
乳腺癌增加了AF患者的抗凝风险,恢复并维持窦性节律至关重要。但乳腺癌患者合并很多延长QT间期的因素,如激素治疗[45],而胺碘酮等抗心律失常药可延长QT间期,因此AF的复律药物使用受限,同时其他可延长QT间期的药物的使用也受限。
5 小结与展望
女性乳腺癌与AF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仍需更多研究深入了解其潜在的病理及分子机制。同时,临床医生应更加重视乳腺癌患者发生AF的风险,以便尽早诊断和治疗。另外,抗凝作为AF治疗的基石,在AF合并恶性肿瘤的综合管理中也是重中之重,CHA2DS2-VASc评分和HAS-BLED评分均未将恶性肿瘤作为危险因素纳入AF相关评估,因此未来需要开发新的缺血及出血风险评估工具,以考虑到恶性肿瘤共病的风险,指导抗凝治疗。目前此类患者治疗存在许多矛盾,更需要多学科专家(包括肿瘤学专家、心脏病学专家和血液学专家等)合作明确相关诊疗指南,指导临床治疗,改善疾病远期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