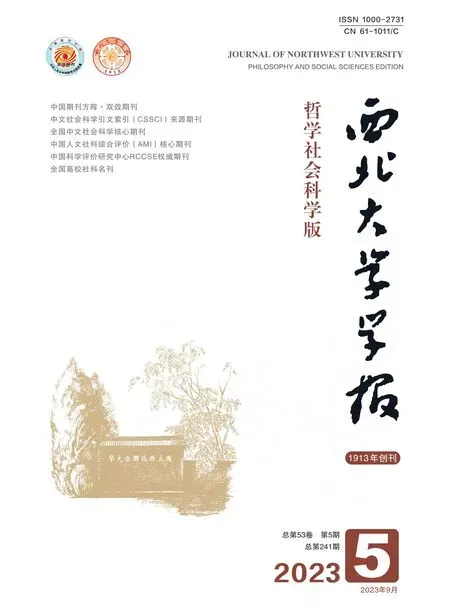“玩”与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变迁
刘 欣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以物为具身经验对象的审美活动,即本文特指的物审美活动,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蔚为大观的“美物体系”,其虽是长期留驻于中国古人生活中的坚实存在,却始终未能有效进入以审美观想为核心内容的古典美学研究视野。作为此现象的重要表征,传统文化中的“玩”范畴以其所代表的与物亲和的感性活动,从审美内涵的日臻成熟与影响范围的挪移、拓展方面,典型而集中地体现了上述物审美活动曲折的价值突围过程。对“玩”的审美价值定向中几个关键性历史节点的考察表明,尽管人们常以“玩”为象喻强调文艺审美体验的精神自由性,由此忽略其作为审美活动的独立价值。但事实却是“玩”并非文艺审美领域的边缘范畴,其作为传统审美文化的及物向度与身体脉象,对中国古典美学经验特质的形成具有十分关键的奠定、扩充意义。
一、“玩好”:先秦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阈限
“玩”者何义?《说文解字》云:“玩,弄也,从玉,元声。”[1]6又云:“弄,玩也,从廾持玉。”[1]53“玩”与“弄”同义互训,最初均指对玉的近身赏鉴活动,通过摩挲这一触觉动作,人对玉的诸种感官经验被充分激发,玉的质地、纹色、声音等形式因素随之获得细致品味。历史地看,古人所“玩”固然不限于玉,但“玩”本身作为一种与物亲和、令人愉悦的感性活动,却始终葆有丰富的审美意蕴,且因与对物的感受直接相关,其甚至常以名词形式直指供人近身赏鉴的“审美精品”[2]2。
“玩”作为物审美活动的发生,源于我国早期社会生产力与造物艺术的长足发展。先秦时代的“玩好”,即指以玉石、犀角、象牙等原料精工制作的珍贵器物和饰品。据《周礼》记载,这些物品最初尽皆收归天子专享的“玉府”,因此其仅合法流通于上层贵族的“式贡”体系,所谓“职贡不乏,玩好时至”[3]1160,即指“玩好”是国家秩序——“礼”的一种呈现方式。然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期,“玩好”制售跃出礼制束缚并走进权钱阶层的日常生活,后者不但以“玩好”为乐,更将这种悦人耳目的奢侈品作为结交、应酬之物,由此给国家秩序带来巨大危机。也正是基于此,管子视“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4]95为国之“六攻”,而圣君明主则“犀象之器,不为玩好”[5]118“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6]155,于是,从君臣之仪的象征到频繁引发祸乱的不祥之物,人们在政治层面逐渐明确了此后封建时代国家秩序与“玩好”的长久对立关系。
事实上,由于与物亲和的感官体验极易调动人之本能欲望,造成人心迷乱乃至行为失范,因此即使就个体来说,先秦思想家对“玩好”的耳目愉悦也充满警惕。对儒家而言,沉溺于物极易毁伤自我健进的君子修为,《尚书·旅獒》“玩物丧志”之说即表现了儒家以健进为德、节制“玩好”的价值取向;对道家而言,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反对“丧己于物”,“玩好”于人的声色悲喜均有碍其精神澄明,故“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7]62;相比之下,墨家更坚决抵制不中民之利的逸乐活动,不但强调造物时“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8]90的基本原则,甚至把营造“玩好”的巧术贬斥为“拙”。可以说,先秦诸子对“玩好”的排斥态度大都隐含了节欲、尚俭的价值导向,这种态度既孕育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情境,又符合艰困民生的现实要求。
总体来看,从早期“式贡”体系的礼制约束,到之后的政治、伦理等诸多层面的警惕与批判,“玩”作为一种与物亲和的感性活动在先秦时期并未得到充分肯定。不过,这并未掩盖其与审美活动的潜在关联,《国语·楚语下》记载,面对晋赵简子鸣其佩玉的炫示,楚使王孙圉回应:“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9]557,楚国并不以此“哗嚣之美”[9]558为宝。这便表明,尽管“玩”以其造就的诸多风险而常被排斥,但其终究还是与一种低层次的“美”相联系。事实上,“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10]343。由于“玩”以物为直接对象,这便使其调动并历练了人的视、听、触等多种感官,具有对人之感性需求的巨大满足作用,也正是出于对这种以物的直接经验为核心的感性生命活动的申张,有论者指出:“所谓‘玩物丧志’的‘玩’,本来就近于某种审美陶醉的境界。”[11]
二、“玩”与“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播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并未阻碍中外贸易交流的活跃发展,域外珠玉宝器经陆、海丝绸之路大量输入,为这一时期的玩好消费提供了可能。史载河间巨富王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馀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12]144-145需要注意的是,彼时玩好多属上层门阀士族的奢侈享受之物,玩好的政治伦理规约均已废弛,其悦人耳目的装饰娱乐作用突显。《颜氏家训·勉学》即载,梁朝全盛时期,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驾长檐车,“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3]140。而对于此现象的潜在危害,文人阶层早有深切痛斥,陆机《辨亡论》追述东吴亡国之兆:“明珠玮宝,耀于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14]699鲍照《芜城赋》慨叹豪华都市广陵城因变乱而昔日风光不再:“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5]2687这些作品均以古鉴今,延续了先秦以来人们对玩好之弊的历史反思,同时亦是对当时上层门阀垄断社会财富、大兴奢靡之风的强烈警示。
不过,从思想取向看,魏晋以来“尚通脱”、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精神,经郭象“物各自生而无所出”[10]26的阐释,社会文化由尊礼法的“致用”型向越名教的“自娱”型转变,已属时代精神转捩之必然。也正是基于此,尽管文人阶层深切痛斥靡费物力之“玩”,“玩”的对象却仍以婉曲姿态向文人生活迁转,这也使得彼时之“玩”开始与艺术建立积极联系,且其作为物审美活动的正面价值定向,更典型、更集中地存在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中。
首先,尽管时有对玩好之弊的现实反思,但在魏晋南北朝倾向“自娱”的文化氛围中,文学仍为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表达空间,而“玩”本身,亦开始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活动被书写。陆云曾在作品中频繁记述其适意的“玩物”生活:“蓬户惟情,玩物一室”[15]26“幽居玩物,顾景自颐”[15]65。而从彼时的咏物赋看,由于其铺陈对象早已从楼台殿阁推及蒲扇、囊镜、案几、乐器、文房用具等,因此文人之“玩”亦多体现为对日常物的审美关注。如嵇康的《琴赋》,即生动描述了时人摩玩古琴、抑扬徘徊的陶醉状态,以至连作者亦沉迷其中,“长而玩之”[5]1319。当然,鉴于魏晋以来崇好自然的审美风尚,文人所“玩”亦向自然物推展,陆机《叹逝赋》:“玩春翘而有思”[14]138,以“春翘”为可玩之物,显示不仅日常物,山川花鸟等自然景观亦可触手成春,以其声色之美成为被表现和近身感受的对象。曹摅《答赵景猷》之“俯玩璇濑,仰看琼华”[16]45,更将“玩”融入俯仰自得的天地审美境界,由此彰显出物审美活动借助文学想象与文学表达所焕发出的积极意义。
专注于“物”、对“物”进行穷形尽相的摹写,本是历经两汉、直抵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的一大方向,而“玩”作为一种满足人之感官欲望的方式,在其中则充当着深入引导作家发现、重视个体体验的重要功能。这种与物亲和的感性活动在文学中的价值显现,使得以物象追摹为能事的审美心理,扩展至近身之物触发的更具纵深感的审美心理。此不啻为艺术视野与审美观念上的一大进步,其结果是不仅开拓了新的文学题材,更预示并加速着人们对审美本身更为丰富的理解。
如果说文学作品中的“玩”体现出文人以镜像反映方式对物审美活动的婉曲肯定,那么把作品本身作为赠答酬谢的手边玩物,更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一种积极呈现。陆机《文赋》即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14]17,其看似以物状繁杂喻文情多变,实则以互文笔法陈述文之为物的观点,即如后世杨明所释:“此注以上句言文,下句言外物。文章亦万物中之一物,凡物则各有其体貌,二句混言众物,不必严为区划。”[14]17-18而从彼时著述来看,将文与物相联系,由此突出文的物质性外观、体貌、声色,并非偶然之见,以至其在南朝刘勰那里获得了经典总结:“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绎方美。”[17]518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物观文,以文为物,强调文学作品首先具有物质性构成,是供人“玩绎”的感性物件,已成为该时期颇为流行的文学观念。
事实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文人普遍关注文之为物的感性愉悦,从不讳言“玩”文的乐趣。陈琳在《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中言道“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喜笑,把玩无猒”[5]968,其在《答东阿王笺》中更称誉曹植文章的巨大魅力,以至使其“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谨韫椟玩耽,以为吟诵”[5]968;刘琨在《答卢谌》中谈及读卢谌赠诗的愉快感受,称其诗作令人“执玩反覆,不能释手”[5]2082;萧统在《答晋安王书》中也描述其收到晋安王赠诗后,沉迷于斯,以至“吟玩反覆,欲罢不能”[5]3064。在这里,“把玩”“执玩”“玩耽”甚至“吟玩”,均突出强调了诗文作品以其物性因素与人建立的亲体关系,而诗文带给人的审美愉悦就生成于对这些物性因素的直接感觉之中。也正是基于对文学活动中这些物性因素的肯定,文以物为体现,物以文的面貌出场,成为彼时文人突破历史壁垒、彰显其文艺观念变革的一种重要叙事策略,在此“玩”文的时代,文与物交叠融合,一起构筑了文人阶层极富感性特质与现实情味的文学世界。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定向具有显著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受上层权钱阶层崇奢竞豪的氛围影响,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在政治与伦理层面并未跳脱先秦玩好审美的基本价值定位,并因此受到历代广泛批评;另一方面,在该时期文人生活和文学空间中,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的积极价值却得到初步肯定,彼时文人注重作品物性存在的事实,也体现出相关物审美活动的价值承托作用。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的自觉”背后实际亦潜藏着“物的自觉”,无论是“以文写物”,抑或是“以文为物”,“玩”范畴在文学中的频繁现身,均体现出以往备受贬斥的物审美活动在文学领域的间接表达,从历史效应看,这种间接表达不但启发后世文人继续于文学领域,尤其在山水园林、闲适生活的诗意描绘中,以婉曲方式实现物审美活动的正面价值定向,更为后世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领域的价值突围提供了可能。
三、“适情”与“尊生”:宋明之“玩”与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凸显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以来,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通过向文学领域的价值播迁,以婉曲方式肯定了其自身价值,那么有宋以来,清玩的出现终于使物审美活动以雅致之姿向文士的现实生活全面渗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代艺术的品类格局与整体面貌,有学者由此认为:“把握‘玩’是理解宋代艺术的一个关键。”[18]224
以清玩为标志的物审美活动在宋代勃兴,固然有赖彼时商业繁荣与先进的造物技术,但从时代文化来看,则首先源于宋代文士“追三代之遗风”“补经传之阙亡”[19]2的博雅好古精神。在一代文宗欧阳修带动下,彼时文人玩古之风炽盛,古器作为几案尤物已是其摩玩欣赏的重要对象。李清照、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谈赏玩古器之趣:“得书画、彛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20]257在这里,历史遗物的质、形、纹、色固然重要,但多识的“博物君子”已不满足于对器物形制的表面娱乐,而是力求以古物为凭借,追慕历代先贤的精义神采。正如南宋朱熹所指出的,儒家艺教需借助“玩”的中介圆融作用,通过适情之玩使人返诚至乐,以至“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21]75。事实上,就玩古而言,这种精神追求已是如此,彼时博雅好古之士已不耽溺于钟鼎彝器的感性外观,而是“玩其文而既其实”[22]93,并循此进入理想的道德人格境界。
此外,宋代文人自然求真的旨趣,使得清玩不限于人工,所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23]11,便体现了彼时文人力图使山水风物进入日常生活的审美理想。苏轼便曾记述其用饼饵从孩童手中换来的美石,其石温润如玉,“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24]1986。《云林石谱》则记载了苏轼钟爱的雪浪石:“色灰黑,燥而无声,混然成质。其纹多白脉笼络,如披麻旋绕委曲之势。”[25]196从表面看,“玩石”的愉悦源于自然物颜色、光泽、形式产生的视觉张力及其引发的心理节律。不过,文人亦在对自然物的赏玩中超越物本身的限制,由“物”至“物之理”,从而达到对于天地之理的把握,正如苏轼所说:“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24]367这表明,对宋代文人而言,“玩”也是一种穷其物理的认知方法,正是在对自然物的赏玩中,天地之理最终落实于人心,天成之物也便成为文人们于平常处冥想宇宙的神机。
概而观之,清玩与儒学尤其是理学融洽互补,为宋代文士生活注入了活力。在这里,“物物而不物于物”[10]360的价值追求,使“玩”呈现为雅致的审美活动,进而成为宋代艺术文化的重要标识。不过,由于宋人将“适情”作为“玩”的尺度,倡导儒家观念在相关物审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这便决定了“玩”在宋代虽以亲物的审美活动为形式,却反对与物交接的过度沉浸。苏轼即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24]356由此,“玩”实际便成为一种独特的修养方式,其目的乃是使人自由愉悦地进入理想的伦理或认知境界。鉴于“玩”与文人的精神取向紧密结合,以其代表的物审美活动也便局限于文人圈层,一如有学者所说:“这‘玩’不是一般的玩,而是以一种胸襟为凭借,以一种修养为基础的‘玩’。”[18]224
与宋代不同,明代尤其是晚明商品经济繁荣,使社会呈现出“工商皆本”的早期现代特质,而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亦突破文人圈层束缚,向更广泛的市民阶层扩展。孙枝蔚《埘斋记》即记载:“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26]1144画家杜堇的《玩古图》更是生动再现了时人颇为风靡的披玩古器的典型场景。此外,彼时所“玩”的物品范围亦突破了文房清供的局限:一方面,古物的稀缺性与当下巨量需求的矛盾,使时人放弃了单纯以古为贵的玩好风尚,其审美眼光投向更易获取的同时代器玩。沈德符即指:“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27]653。另一方面,明代市民阶层的地位提升以及世俗文化的活跃,使得以往隐没于底层生活的凡俗器物,也成为可供赏玩之物,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闲情偶寄》中均设“器玩部”,其直言“粗用之物,制度果精……亦可同乎玩好”[28]227。这种开阔的审美视野,也使得“玩”作为物审美活动在明代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中均占据了突出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物,尤其是长物已成明人衡量生活质量与审美品位的普遍尺度。
除了上述显见的诸多变化,明代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在其广泛流播过程中,也逐渐呈现出深具时代色彩的价值侧重。众所周知,晚明文化重视现世的感官享受,但其内在旨趣却是对人之生命存在的尊视。也正是基于此,彼时之“玩”亦深具生命关怀趋向,所谓“一切药物补元,器玩娱志,心有所寄,庶不外驰”[29]2,即是说通过器玩怡养心神,其效与药物相同,皆合于尊生之旨。在这里,“玩”并非对感性欲望的放任,而是以器物带给人的感性愉悦为寄念,力求达致身心皆得、怡生安寿的理想生命状态。而从具体来看,此理想生命状态的获得,十分典型地体现于彼时之“玩”的具身化体验特征上。
首先,亲和性。“玩”是手、眼、耳、心等器官综合运用的亲物体验,其突出特征是手对物的触觉把握。这种对触觉的重视,尤其体现在时人对“手泽”(即包浆,亦称胞浆)的迷恋。李渔便曾言道:“宝玉之器,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28]227周高起评宜兴壶:“入用久,涤拭日加,自发暗然之光,入手可鉴。”[30]81张岱谓其水中丞:“虽戕口,不起羞。虽折足,不覆饣束。点点滴滴,毋忘手泽”[31]394。在这里,突出“手泽”之于器玩的重要意义,正因唯有经“手泽”的直观触觉表征,人才得以越出空间限制并与物建立全方位亲体关系,在此亲体关系中,器物褪去了创制之初的“贼光”与“火气”,以其润泽使自身成为人之感性活动的确证,进而成为人之生命意趣的直接投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手泽”而引发的人与物的亲体关系,甚至也成为人与人跨越时空的情感纽带。陈洪绶晚年作品《品砚图》,即描绘了三位老者摩挲故友遗物的场景,在画面中,好友生前手泽浸润过的砚台,焕发深邃沉郁的色彩,这种色彩乃是逝者生命的独有印记,生者则在对砚台的摩挲怀想中,以自己之手实现与逝者生命的切近,由此,人与物的亲和也通向了人与人的亲和。
其次,交互性。“玩”作为物审美活动,不是人对物的单向度的审美把握,而是通向人与物的对话、交感与授受。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自述:“余得一枕,用哇哇手持荷叶覆身,叶形前偃后仰,枕首适可,巧莫与并。”[29]545在这里,枕之造型需考虑人体感受,其“巧”处便在于物与人的呼应契合,即器玩以其合乎人意的感性形式吸引着人的手与眼睛,隐含了对人的温情约请,体现为向人的敞开和召唤,作为回应,人对器物的赏玩则是发现这种约请并欣然应约的过程,且“人们通过给予器物所要求的而从中得到乐趣”[32]63。在此过程中,审美活动的主客二分状态被消弭,延传既久的距离式静观体验变成了饶有趣味的动态体验,人与物互渗共生,实现了“在我”与“在他”的融合。
最后,创造性。“玩”即手的游戏,作为一种突破传统距离化赏鉴模式的物审美活动,其总是伴随着对物的更为丰富、也更为彻底的审美发现。正如梅洛·庞蒂对康德手是“人的外部大脑”[33]400的阐发和强调,通过手的探索,沾满青绿古锈的青铜器,润泽如玉的各式瓷器,雕镂繁缛多姿的金银器乃至纹理细密的家具,都不再只是以悦目的色相示人,人对物的感受因手的参与而复归于三维空间,诚如古人对玩玉场景的生动描绘:“色似琼酥白似银,摸着灵泉随手生。”[34]32在这里,手对玉的感受引发了手对灵泉的绝妙感受,由此获得的审美快感已不局限于印象式的、无法深入感受对象的审美观想,而是以触觉、视觉、听觉等诸感官的协同参与,释放心灵的潜能,充分唤起情感、想象力的综合运动,由此产生出激荡个体全部生命活力的审美愉悦。
总体来看, 宋代文人风气与明代市民阶层崛起, 均促进了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在传统文化中的正向价值塑造。 而宋明之“玩”从“适情”向“尊生”的价值重心位移, 则大大推动了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从高雅形态向市俗形态的转化, 如果说宋代文人以修养为凭借, 更侧重清玩之于人的精神愉悦, 那么明代文人以及彼时广泛的市民阶层则更侧重器玩对个体身心状态的养护价值。 也正是这种尊养生命的价值追求, 使得“玩”通向不惮与物同流的“快活”“清福”与“真乐”, 使得人不必极尽手段与物欲博弈, 而是探索并实践着一种涵化物欲、 力求在对物的切身感受中寻求情感愉悦、 精神自由的日常生活美学。
四、“玩”与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美学意义
以“玩”为代表的审美活动,因其与物亲和而常被赋予煽动欲望的消极意义。由此,儒家以载道名义将物纳入政治伦理视野,指认“心赏而目娱,手以为嬉,丧志大矣”[35]28。而道家亦提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10]303,由此反对与物相靡,克绝“五色”“五音”“五味”乃至“难得之货”的物欲纠缠,力求通过超越物的感性现实世界进而达到“游心于物之初”[10]379的自由之境。
与上述思想倾向协同并进的,是以“感物”为主的传统审美观念,在该观念中,“心”为美的发现、创造和感受的关键,“物”是“心”的诱发体与媒介,所谓“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36]494,审美活动即主要以观想方式指向主体的精神化育。这便意味着“感物”的审美过程虽伴随生理机制的运行,但本质上却是一种心理转换,实现这种心理转换的先导是人的感觉器官,但其却无刻不受“心”的统摄,即“心居中虚以治五官”[37]366“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4]265。在这种以心统摄、制约五官,进而引领对物的审美感知的机制中,“物”的面目始终是模糊的、片面的,其通常处于审美活动的起始但又边缘的位置,审美主体所能标定为审美对象的物,也只是物适应人的精神要求的某些方面,物作为直接而完整的审美对象的意义恰恰被遮蔽了。
不过,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发展中,与物亲和的审美活动却从未止息。事实是,封建礼制与思想控制愈发僵化,愈有清晰鲜明的个体意识与感性诉求以“玩”的方式显露,在“玩”的审美体验中,物不再只是某种中介性存在,而是具有自身的生命召唤结构,其决定了“玩”的目的不是用我去改变物,而是让我投入物,使我的感性生命在物的召唤下得以实现。
当然,这种以“玩”为契机对人之感性生命的实现,也充分显示出审美活动与身体的本有联系,以及中国古人对审美之身体根基的深刻把握。事实上,历史上诸如玩心、玩味、玩咏、玩索、玩讽、玩耽、玩读、玩绎、玩华、玩赏、玩阅、玩适等颇具审美色彩的精神活动之所以与玩相关联,便已昭示这些活动并非超然于身体之外,而是内在于身体之中,其愉悦体验和人的生命欲望的满足息息相通,正如有学者所说:“由于一切审美经验都奠基于身体,所以也不妨说审美经验是一种整体性的身体经验。”[38]不过,亦需指出的是,承认审美活动的基底在身体,并非意味着“玩”与审美意识无涉,而是强调物在审美意识生成中具有直接作用,强调物经审美意识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和力量,由于在“玩”的审美体验中,审美意识、身体快感和冲动本就无法分离,因此这种体验从来就不是意识与物的外在关联,而是人之身体与外在世界的充分交融。有鉴于此,作为审美范畴的“玩”,实际代表了一种审美理想,其将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39]354,将物作为其直接对象,由于客观之物具有多方面感性特征,因此“玩”实际力求把各种愉悦感受融为一体。明代袁宏道即称其毕生追求的器玩之乐为“真乐”,因其“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40]221,故这种对物的审美把握,已不局限于“橱窗式”的审美观想,而是把诸感官经验纳入同一美学框架,同时实现心理和生理感受的交汇统一。由此,整体协同的物审美活动提高了审美愉悦的强度与效果,通过提升身体的体验、感知能力,“玩”最大程度地达成了个人快乐、幸福之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中,“玩”范畴不但以其对感性生命的贴入实现了审美活动中人与物的融贯,而且其对当代美学研究亦具重要价值。众所周知,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便是以能动身体消解既往美学身心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强调审美活动中的身体非仅物质性肉身,而是主动且富有创造性的生命机体。由此出发,美学对审美经验的研究势必指向具身现实,并着力探究身体与外在环境的互动共生,这也意味着将美学从有关审美的知识性讨论中释放出来,通过将抽象思维中受动身体还原为生活中鲜活能动的身体,新的美学将超越抽象的美和狭隘的“美的艺术”,成为一种调动人之全部感觉的“及物”美学,并最终指向人之身心和谐的审美化生存。事实上,从“玩”范畴在古典美学发展中的价值突围来看,其力求将审美活动落实于与物交接的现实生活之中,这种“及物”的审美活动不但为中国古典美学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身体进路,更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现代性转型中发出了审美价值变革的先声,由此对当代美学的思维转换与价值转向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凡此种种,皆表明以“玩”为代表的传统物审美活动具有超越其生发环境的巨大潜能,其理应成为当代美学研究中具有文化承续性的理论依托与实践例证。
更值得关注的是,从文化现实看,当今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探索在给当代审美文化注入活力的同时,也造就了诸多新的美学问题:一方面,当今社会媒介符码泛滥造就的“超现实”处境,使人疏离于现实之物,以新媒介为依托,人与物虚拟的共同在场造就了一个日趋平面化的世界,满足于媒介化生存的人们,亦满足于对物的新的“橱窗式”审美体验;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市场经济的普遍商品化趋势,虽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庞大的“美物体系”,但商品的现实消费又往往使人沉溺于物,在这种消费中,具有创造性的完整身体常被具有再生产价值的欲望化身体所取代,物的丰裕表象之下则是物的具身经验的缺位与贫乏。而恰恰是在这方面,“玩”以其与物亲和、身心合一的审美旨趣为解码此类问题提供了传统理据,在传统文化中,“玩”以其与物亲和的具身体验超越了“钝汉”“庸奴”对物的夸示性消费,其不但有利于从审美观念上纠正时代文化对物的符码化、欲望化偏执,更以其与时推展、不断臻于圆熟的物审美活动,实现了对活的身体经验的感性回归,作为可资参照的实践范例,其终将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临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