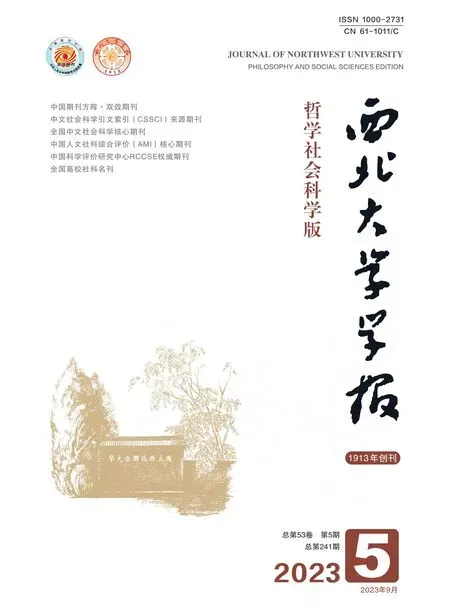20世纪中国文学里情感的公共性维度
——以海外汉学的研究为中心
刘毅青,张 欣
(1.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00;2.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包含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审美经验的总结和阐释,其诗学观念和相应的审美范畴也会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作品和观念的选取和分析体现出来,而研究者的评判视角和评判标准会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纷繁态势,这就涉及对其判断标准进行再次检视和考察的问题。“在历史与文学的辩证关系中,解读者的阐释限度应受到相当程度的警惕。”[1]夏志清也曾指出:“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2]332当不同的研究者对他者的判断结果,或是其自身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得出的结论产生质疑和思考之时,便是检视其话语公共性的动因。
从文学公共性的指涉方式来看,其意义突进有着两重典型路径。一则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媒介渠道将知识分子的声音转化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的声音,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和批评空间,如李欧梵所语之“铁屋中的呐喊”,文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缔造一种共通的想象,介入公共空间,以此发掘文学借由文字与叙事等建构传导的力量。另一重路径则偏向于内部话语更新的方式,学人通过个体意见表达的方式使其观点进入文学场域,借以影响或改变现有的批评研究标准,这样一种使其话语获得合法性的论辩过程,亦是其追逐公共性的体现。此种多重话语参与文学场域的建构行为,促使研究视点多样化的演进过程,本身也是拓宽文学公共空间、激活文学公共性的有效增益行为。海外汉学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或隐或现地体现出公共性的视角、方法和追求,在其“有情的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亦体现出公共性的维度。故而在公共性的问题视域中,探讨情感以不同姿态体现公共性的多元面向及其外围的文化根系,可以对其研究本身进行再次反思和开拓,并观照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建构问题。
一、何谓“公共性”及“公共性”何为
将海外汉学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放置在中国的文学公共领域中进行公共性探索,则需对与此议题相关的概念有所理解。一般而言,文学公共性诞生于一定的文学公共领域,因此,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往往影响着生发于其中的文学公共性的表现模式,中国的文学公共领域以及生发于此的文学公共性有着自身的特点。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发生的变革,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公共场景不同,中国的公共场域主要集中在“报纸、学会和学校等文化场域”(1)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载《史林》2003年第2期,第77-89,123-124页。。其中的主体也“不再是朝廷法令或者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3]4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参与感与日俱增。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伊始的先驱,多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和身份,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以“美学话语”和“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入世的手段,与“启蒙”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现代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启蒙与革命的公共空间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带有与生俱来的公共性特质。
在文学的公共领域内,公共性的实现与个体及个体差异性的存在密切相关。“公共性的重要特点是差异性和共在性的统一”[4],作为文学研究主体的人,拥有不可剥离的社会性,因而其审美阐释话语虽以个人意见的方式进行表达,但社会历史的因素亦伴随其中,影响其审美判断的立场和方式。因此,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研究往往具有一种公共性。“犹在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性引起私人政治批判的争议,最终完全被取消之前,在它的保护之下,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前身的文学公共领域已经形成。它是公开批评的场所,这种公共批评集中在自己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5]34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文学公共领域具有公开性、私人性、交流性和批判性的特点,承担建构主体性的功能。此中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相关,二者并非隔绝的对立状态,而是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6]34。这个包含着无数个人的公共空间也就意味着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因为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聚会场所……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6]38。世界如她所形容的“桌子”一样,让人们既聚集在一起,又不至于倾倒在他人身上,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人们在同一空间内围坐周边,从不同的角度分享各自的经验并进行协商,则意味着观念的独立性及输出方向的不同。这便可以推导出公共性的本质是无数视点和方面的交流与沟通。因此,人们在同在情况之下的“个体差异”是公共性得以形成的前提保证。故而公共领域并非生产出全然相同的共识,而是作为一个分歧意见的集合地,诞生于此间的“公共性”也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结论,而是指向围绕问题对象而展开的多面向探索。
自20世纪50年代起,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桌子”周围就多了一重域外的声音。夏志清基于“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理念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撼动了尘封已久的现代文学史言说框架;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等从不同角度显明了文学史某些被误解或被遗忘的角落;王德威、胡志德、米列娜等学者在现代性视角下对晚清及五四文学关系的勾勒;奚密的《现代汉诗》、耿德华的《重写中文》以及罗福林的《中国报告文学》对文类文学史的构建等等,诸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因其独到性和差异性获得参与中国文学公共领域构建的权利。总的来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理路是对审美标准差异化思考后提出问题的过程,其直接对象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思考主体为个体研究者。但研究者初始时期的思考成果,只能呈现为一种对审美标准的个人理解,要想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甚至改变现有研究标准的话语,则需使其思考成果进入公共领域,获得公共性,这个过程便是阿伦特所主张的公共领域的“自由争胜”[4]过程。
在此过程中,“有情的文学史”因情感的介入及其对现代性认知的挑战而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学史。比如,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建构,以情感穿梭于现代文学“史诗”叙述的“暴力”之中,在“情”与“史”的对话中弥合了历史大一统书写下的缝隙;李欧梵在情感的问题视域中将个体话语、道德伦理、国族愿望及种族主义结构在一起,于“浪漫一代”的文学史叙述中钩沉历史隐而不见的细节;刘剑梅在对“革命与情爱”这一创作主题近百年的历史言说中,发掘情感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游离形态,在情感与革命的互动语境中挑战既定的文学史认知并展现出新的历史视野;李海燕以作为“心灵革命”的情感突入现代中国的社会想象,情感以感觉结构的方式塑造情感共同体并推进主体认知,使文学史的叙述突破“精神文明导向”的辖制而更具真实性。
由此,情感作为一种审美评判方法进入中国文学公共领域并获得言说的公共性。情感本是源自于人基本的、原始的表达需求,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主观性等非理性色彩,但在文学公共领域内流通的情感是经意识加工后的审美经验,具有情感主观性与表达理性的双重特征。“情感的共享是深刻而又意味深长的,在任何普通的单独情感中获得的共同原则的分享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7]61情感在不同时期或借由充满个体理想主义的话语表述,或通过能够联结自我与他人的情感共同体等多种路径释放审美经验,在公共权力与个体之间建构起一个相对自由独立且融合理性与感性的公共空间,其存在是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之一。但这个空间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写日期”或“大叙事”的遮盖下若隐若现,未能得到系统化、学理化的认知与阐述。从发现的角度和实际的意义来说,海外汉学家们以情感为方法介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并使之获得公共性之时,便在客观上不断刺激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空间增殖和意义转变。
故而,情感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创作题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讨论对象,还可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美学问题,来透视其本身所代表的审美评价体系的合法性及效用价值。情感本身是否具备公共性以及其作为方法是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具备公共性,是应该认真检视的问题。海外汉学家将情感作为理论方法的缘由,已有学者归纳为三点:其一,是海外汉学家论述的“抒情传统”已在学界引起对话的冲动,可进一步促使中西方学术话语的交流;其二,是在情感视野中中国社会里的个人和国家,可解除简单的对抗关系而获得多重样态;其三,是研究范式转变的要求,“逸乐作为一种价值”的理念催动情感正面价值的浮现(2)参见余夏云:《以“爱”的名义讲述:李海燕〈心灵的革命〉》,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第179-189页。。海外汉学家以情感为视点,在文学公共领域通过多种方式使其获得部分真理进而获得公共性,正如其表述和获得过程的多样性一样,其将情感作为一种审美评判话语进入文学场域后,以与既有审美理念对话的方式获得公共性,亦呈现出公共性的多重面向。
二、情感作为传统:中国“抒情传统”与公共性
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话语构建,从陈世骧对“抒情”的现象描述,高友工对“抒情美典”的本体阐释与建构,到王德威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相关联,“抒情传统”成为一种构建与西方文学相异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独特方式。围绕其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多有批评质疑的声音。
有学者指出,汉学界的抒情传统理论构建,将“兴”“怨”等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概念与西方的启蒙、革命等意识形态内容进行内容置换,使抒情化作个人之情,使其主体性的追寻,付以隔绝群体的代价来实现,与外界形成紧张关系,“一切抒情都沦为远离听众、缺乏微言相感目的的自我吟唱,公共性被完全剔除了”[8]。汉学界抒情传统的追求,在西方话语的简单化约下,丧失了抒情话语的“相与之情”这一公共情感维度。还有学者认为陈世骧和高友工专注于传达主体情感经验和形式美感的抒情传统建构,实际上是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影响的文学主张,以主体情感的自由抒发和表达来定义文学,过度地发挥了康德美学中的主体性维度,这种基于纯粹个人经验的情感抒发,很难实现美学的公共性和政治潜能(3)参见苏岩:《公共性的缺失:“抒情传统”背后的浪漫主义美学反思》,载《名作欣赏》,2015年第16期,第40-44页。。南帆在《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一文中同样指出,以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为重要倾向的抒情传统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后期出现,致力于打破儒家“诗教”的浪漫主义文学和“五四”起塑造了一个新型抒情主体,冲破了文学风格与个性的限制,代表着抒情的新生力量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话语建构。海外汉学家中国抒情传统诗学所建构的抒情主体则无法有效地参与这种公共性活动,显示了其公共性面向的缺失(4)参见南帆:《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第5-18页。。
可见,关于“抒情美学”公共性的质疑,多围绕于诟病其“抒情”的自足保守及因剥落公共性而无法真正参与公共领域而展开。但若我们以公共性的视点审视“抒情传统”话语建构本身,便可发现,一方面,“抒情美学”的构建显示出其与“公共性”的疏离。陈世骧和高友工等抒情传统的阐发者都将主体情感的抒发当作抒情的本质所在,抒情美学所要探寻和建构的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抒情主体,因其对个体情感经验的推崇而存在于一个审美超越的世界中,文学的公共性被隐匿不见。此时的抒情美学更偏向于一种用于解决现代性冲突的想象性诗学,而刻意与“公共性”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抒情美学”又有着“公共性”的特殊面向。这一点在王德威探讨“抒情传统”与现代性关联时的论述中得到充分印证,我们可以重新回溯海外汉学家对于“抒情传统”的建构话语来分析其公共性所指。
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9]2。他肯定中国人的“诗”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体现出的抒情性,将“抒情道统”贯穿中国文学(5)参见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载《陈世骧文存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高友工则将抒情传统塑造成一种中国文化认知的体系,形成中国审美文化中的抒情美典,抒情主体通过“内化”(internalization)和“象意”(symbolization)的方式保存“自我现时的经验”。但这种自我经验并非纯然的与外界隔离的状态,因为高友工所定义的抒情,“不仅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种主题、题素。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属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10]83。虽然他所探索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内向(introversive)价值美典如何克制外向(extroversive)美典的问题,但也依然着意于这种内向美典如何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意识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在此,抒情主体并不是存在于超验世界的生命个体,其对自我经验的诉求和保存,必然沾染社会的氛围。尤在个人、文学与社会的冲突状态中,这种担负价值、理想等意识形态的抒情,往往带着强烈的政治气息和批判意识,成为在文学公共领域的另一种声音。
在王德威的相关论述中,“抒情传统”如何进入现代的问题,也即抒情美学在现代文学公共空间中的合法性和生长空间问题,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抒情”与公共性的关系被论述得更加明确。在分析梁宗岱、宗白华和沈从文对抒情现代性的创造性观点时,他发现了三人抒情理念中现实的被动呈现意味。他们以抒情的方式来描绘中国现实,“模塑人类情感无限复杂的向度”,“将内在和外在的刺激赋予音象”,便可“因应任何道德/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11]40在此,“抒情传统”着意强调的“音乐性”,不再单单指涉语言文字的艺术化特征,而成为一种试图消解世变与诗情之间尖锐矛盾的方式,这何尝不是抒情美学之公共性的另一重维度?此外,他在回溯了朱自清、周作人和闻一多的“诗言志”观后指出:“诗歌——或文学——的光谱因此包括了言志、缘情、纪事的维度,进而指涉了私人和公共领域的互动、知识议论的呈现和历史记忆的形成。”[11]35由此,“抒情”并不局限于第一感觉的主观浪漫,也不单一指向个人的封闭系统,而是以“持续深入到知识分子和文人历史意识闳域”的方式,将个体话语引入公共空间并形成互动,参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建构和延续。
进入20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一个很难令人联想到抒情的时代”[12],但在波澜壮阔的 “史诗”叙述中,“抒情”又与现时的文化前景产生了何种关联,如何产生公共性,则是王德威意欲找寻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他将“抒情”的概念回溯到古典的词源学中,与西方的“lyrical”概念进行对话,发现中国的“抒情”蕴含着“发愤以抒情”的一面,隐藏着抒情主体的历史动机并掺杂着种种政治因素,中国的抒情诗学是具有复杂性和分歧性的。王德威选取沈从文作为史诗时代抒情声音的代言人。沈从文在其早期的作品当中,已于乡土抒情的笔端下注入了种种历史感伤的情绪,他所主张的“抽象的抒情”便是以艺术的方式对现实经验作出回应,是知识分子担负自身责任的一种方式,他“希望借这样一个‘抽象的抒情’的形式,来面对历史的暴力,强调即使个人处在时代的风暴里,也仍然有他自为的可能性”[11]103。而后,“事功”与“有情”的历史观,让沈从文于“大历史”的叙述洪流中,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有情”的历史叙述者,将他与其他中国人的思想与想象以情感的方式记录下来,沈从文所谓之情是一种“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13]13他在生命后期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便是其在“有情的历史”观下参与文化建构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王德威在何其芳与冯至以“死亡与重生,自我与群体,腐朽与动力”为主题的诗作中,也发现了于20世纪中期中国文化政治的迷魅之中流露出的抒情主义。在他看来,二人彼时的创作之所以还能够引起此时的审美感受,并不是因为其对自我改造和主体构建的成功,而应归功于诗歌在叙述裂缝中透露出的抒情话语,它“提醒我们诗人的语言充满曲径通幽的游离性;诗人的本命就是偶开天眼,看见并铭记不可见的事物……追根究底,所谓的‘抒情性’是一种意在言外、另有所思的‘旁白’(aside),或现实话语的灵光乍现”[14]。正因如此,何其芳在筑“梦”的国度与现实间的穿梭回望,冯至在其“蛇”意象中进行的“死与变”的想象,构建了二人诗歌“重生”视景中最为生动的章节。
根据时序线索的推移,在论及抗战时期及之后的抒情转向时,王德威为“抒情”加上“红色”的前缀,显明“抒情”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以探讨革命的与抒情的、诗意的、浪漫的情怀之间的张力。在论及二者关系时,他说到:“没有抒情,革命的豪情不足以成为个人生死相许的寄托。没有抒情,革命群体无从还原主体个别的意志——哪怕这‘个别’的意志只是一种伪托。这是革命之所以为革命的审美喻指的一刻。”[11]139故而,革命的话语中是必然掺杂抒情的底蕴的。“抒情传统”在这里的面向显然发生了转变,“抒情”从传统诗学里延承的“兴”与“怨”,不仅仅是在审美观念上的无限延伸,而成为了在宏大的革命诗学之中,个人或群体情致得以释放的出口,是人在革命感召中本真情感的表述渠道,“抒情”并不拘囿于狭小的个体空间,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参与“当下此时”公共活动的能力。
据此可以发现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抒情传统”的表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话语在不同情境中有着很强的理论适应性,从陈世骧、高友工至王德威,显示出一条由关注内向性的美学话语拓展至建构与意识形态批评相关话语的发展路线。“抒情传统”本身作为一个研究视点,可视为不同于“启蒙”与“革命”外的另一种“意见”的提出,正是这些“意见”的显明与自证、沟通与交换,才构成了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真正意义。正如王德威所言“抒情论述是一回事,而为何以及如何采取抒情姿态,论述抒情,才是问题所在”[11]13。在主流大叙事之外,对另一种史观的向往促成“抒情传统”召唤,“这一召唤的本身便已经饶富政治意义”[11]6。“抒情传统”在话语演进的过程中,逐渐跳脱了审美超越的前提,或以表现或以批判的方式介入历史情境,又或以“文化认同”(6)参见刘毅青:《作为文化认同的抒情美学传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1-105页。的方式参与文学公共领域的秩序建构。其在文学场域的发生和成熟,正是因为其持续性地提供了一种“较佳论证”进而获得了“差异”的合理性,而在文学公共领域中,“差异”正是“公共性”的应然之维。
三、情感作为结构:情爱谱系与公共性
阿伦特曾这样表述:“我们注意到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才能幸存下来。比如爱情(不同于友谊),爱情一旦公开展示,就被扼杀或变得黯然失色了(‘决不要试图去讲述爱/爱从来无法讲述’)。由于其内在的非世界性(worldlessness),爱情如果被用于政治的,例如用于改变或拯救世界,就变成虚假的或扭曲的了。”[6]34但她在其早期著作《爱与圣奥吉斯丁》(7)《爱与圣奥吉斯丁》(Love and Saint Augustine)是阿伦特博士论文的英文版,由Joanna V.Scott和Judith C.Stark编辑整理,于1996年出版,德文原版名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Der Liebesbegriftbei Augustin),1929年首次出版。中,也曾表达了其对爱情的世界性的关注,承认爱的公共性意义。这种对于爱情的具有张力的解读,在海外汉学家这里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某种连接。
斯坦福大学的李海燕将“情爱”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她将情感放置在个人与社会、文本与环境中的研究方法,便将情感由一种固态的历史和文化的常数转变为语言和文化的动态研究资源,揭橥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可塑性和流变性,从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层面给予情感更多学术视野的关注。她将现代主体与现代政治群体等多种对应关系与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时刻相结合,通过情感在具体文学情境中的转化再现,使得情感成为一种文学研究理念并在文学场域中具备了参与公共场域的公共性。李海燕认为“情感话语不仅是内心情绪的表达与表现,同时也参与了社会秩序(再)定义和自我与社会形式(再)生产的发声实践。关于情绪的言说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谈论情绪,而总是涉及某些其他的东西,如身份、道德、性别、权威、权利和群体”[15]8。情感在这里成为一种构建个体和集体身份的话语,构成了脱离启蒙话语遮蔽后重新审视文学表现的一个审美评判体系。在此,情感一方面在不断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具备公共性意义,另一方面又通过其所获意义形成一种情感范式,再次参与现代主体的思想构建。那么,在这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中,情感同时作为构建的主体和客体,其具备“范式”性的公共意义后,对人的思想的共性感召是否建立在差异性消解的基础之上?作为公共性基础存在的差异性的削弱,是否会引发其话语公共性的失效?情感公共性的获得是否有其他方式并产生何种价值?
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借助雷蒙·威廉斯所提出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进行分析。“情感结构”是指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现实生活给人们带来的一种普遍的认知经验和感受,他将社会意识的定型称之为“沉淀”(precipitated),在鲜活的时代经验中,情感是溶解在其中但未完全定型的部分,是复杂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情感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和确定性,作用于人们活动中最微妙和难以捉摸的部分,是独特而鲜活的生命经验。它“不是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感受,而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16]141。“在流行的感觉结构和同时代的文学对它的运用之间存在着连接,这种连接对文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作为整体的文化其内部的各种真实关系——其意义甚至比各种制度还来的重要——变得清晰了。”[17]78正因如此,“情感”作为一种审美评价话语,具备了厘清文学发展及窥视其内在真实的学理依据。相比外在的政策宣传及主导性权力话语,文学在形象建构的过程中与“感觉结构”互动所形成的情感话语流,在分析社会文化体系时更具可靠性和真实性。
情感结构还体现出“流动性”和“溶解性”的特质。威廉斯认为:“大多数现行艺术的有效构形都同那些已经非常明显的社会构形,即主导的或残余的构形有关,而同新兴的构形相关的(尽管这种相关常常表现为原有形式当中出现的改形或反常状态)则主要是溶解流动状态的感觉结构。”[16]143李海燕在将“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作为一种新的视角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亦发现情感结构在与中国具体的社会经验及个人经验结合时所体现出的流动性特征,勾勒出其由“儒家的感觉结构”至“启蒙的感觉结构”,再到“革命的感觉结构”这一脉络谱系。
“情感”与“结构”的结合作为一种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方法,成为一种新的审美分析路径,可观照基于情感的主体与意识形态的信念之间的张力,以及在情感中心下的概念性与社会性议题。比如在李海燕以“情爱”为介质与鸳蝴派对话的过程中发现,鸳蝴派小说以“爱”的名义所结构的小说,大多树立了一个比爱更深远、更崇高的追求目标,它可以是儒家话语体系下的某种传统美德,也可以是与国族愿望交织在一起的家国理想。“把超越爱情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包围性叙事溶于一炉,从而使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一切热烈追求共同指向的一个不容质疑的终端。”[15]96这似乎与五四时期“自由恋爱”呼声后的终极欲望有着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鸳蝴派小说的现代性追求并不以“断裂”与“诀别”为基础,相反,他们在一种普遍性情感的隐喻中建构起一种“儒家的感觉结构”,包含着对传统孝义秩序的遵从与维护。
而在观察五四及五四后期有关主体性和社会性的论争之时,“启蒙”这一话语表述除去口号标语的激进意义后,也被内化为一种感觉结构,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同时期主体的基本行为和终极道德选择。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有关“自由恋爱”的呼声,就不单单地指向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其深层话语实则是与家庭和传统的诀别意识,呼唤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出现,要求个体的身份必须凌驾于一切特殊性的束缚关系。李海燕将身处这种“自由恋爱”中的浪漫主义情人称为“一张擦拭干净的白板(tabular rasa)”[15]102,对于人类群体形式的全新想象便可以在此种存在关系中展开。在这些“浪漫主义”文本中,作为修饰“恋爱”一词的“自由”,从一种象征性修辞,逐渐向社会领域突进,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迷惑性及多重权力产生纠葛。爱情在此也化为了一种政治化的象征,代表着五四批判精神中的自由、平等和权利欲求。“爱情”这一带有私有性、偶然性色彩的行为,在此与自由相结合,成为了一项抗争父权意识形态和家庭礼教的反叛性事业。
但是,情感结构在与支配性的社会性格相对应的同时,亦会体现出与任何一种可识别的社会性格并不完全相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被“共同理想”所忽视的内容,它们不仅存在,而且构成一种时代“情感结构”中不容忽视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普遍的支配性性格下,其他的社会性格也是暗流涌动,甚至引发时代的各种现实冲突。在诸多五四作家自觉地以“爱”之名书写叛逆性宣言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将爱拉回日常生活轨道的尝试出现。比如1923年张竞生在一场爆发于公共空间的“桃色”丑闻中发表的“爱的定则”,便是将“古老守旧的儒家婚姻模式”和“浪漫主义爱情婚姻理想”作为共同抨击的对象,使爱情脱离了那种抽象的、压迫的原则和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肯定了其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存在价值,使其成为一种“平凡的生活善”。由此,李海燕在众多上演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恋爱”的故事中,发掘出现代主体在“爱情”之名裹挟下“追求崇高”的目的与包括社交和性交在内的所谓“尘世之爱”(earthly love)的获得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这使得“爱情”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存在成为一种悖论——对私人领域内“尘世之爱”的渴求与公共领域内“浪漫之爱”的追求不能两全。这种对于“爱情”的公私欲望的冲突与理想的差异,实际上也映射了社会转型时期主体构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除了这种在一时期同一感觉结构召唤下引起的共同表现外,作家基于个体经验的思考、判断及表现也是各不相同。例如,李海燕于启蒙情绪的向往下对自由爱情的一片讴歌中,发现了鲁迅所开启的唯物主义式批判。鲁迅在《伤逝》中割裂了“爱情”与“自由”的普遍联系,爱情不再如五四高潮时期那般以自由为名义,而成为一种“迷醉的心灵状态”,站在了自由的对立面。涓生和子君在获得了爱情之后,一个陷入传统家庭失去了心灵的自由,一个则失去立身之本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爱情自由在失去经济自由的保障下失去了存活的空间。对于爱情自由的评判,是因为“他绝对无法原谅自由恋爱的乌托邦理想,也无法原谅持续鼓吹恋爱自由的愿景而无视其内在的冲突及其与生活现实之间矛盾的那些人,他们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就是在恶意操控轻信而易受影响的青年”[15]126。可以发现,情感的感觉结构引发的文学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它既可以是对崇高的、自由的浪漫之爱的追求,也可以是对爱情虚伪承诺的一种反拨,当然,前者是占支配性的主流情绪,后者则是作为与主流思想不相为同的另一种声音。
爱情作为一个创作的母题,与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的现代转型息息相关。正如她所言:“中国都市中心的文化居民,几乎无人可以公开表示,自己的社会经验与关系的质量,不跟话语场中爱情的起伏兴衰绑定在一起。”[15]298因此,李海燕将爱情视为一个问题,承认其稳定存在并否认其恒常的固定形态,在具体的历史使用领域中探讨其现代性的经验维度。情感作为感觉结构,一方面在不断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具备公共性意义,形成具有支配性的话语力量影响个体和群体的主体建构;另一方面,允许其他经验依旧拥有存活的空间和表达的可能,构成公共领域中的另一重差异性话语,其主体性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
四、情感作为表演:情爱主题重述与公共性
这里所使用的“表演”并不限定于传统的艺术表现概念中,而是指一种将文学活动中的行动表现、对话交流及意义重构方式等因素综合考量的分析方法,意在探寻程式化意义表达方式之下话语的生成、异变和表现机制,以及戏剧性、及时性、突变性等表演独有的特征。
李欧梵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找寻到了他们对于情感的表演痕迹。他以情感作为切入视点分析苏曼殊创作时,发现了情感的悖论式戏剧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失意的苏曼殊在其作品中却常常被两位不同性格的女性同时迷恋,“一个脆弱温柔,一个热情主动,但又同样忠贞及愿意自我牺牲。”[18]67苏曼殊在国外出生,并未受过完整的中国文化教育,但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使得他对女性专一的传统美德“投入了无限的情感因素”。而当这种想象在西方文化的入侵下濒临幻灭之后,他则痛愤道:“衲敬语诸女同胞:此后勿徒效高乳细腰之俗,当以‘静女嫁德不嫁容’之语为镜台格言,则可耳!”[18]67在他的小说中,爱情成为表演的舞台,用以展现“模范情感”和“爱的追求”,但在现实中,他却“被爱情的肉体部分——欲海——所征服”[18]69,情感从私有隐秘性情感的狭小认知中解放出来,与时代话语和传统文化产生交流,于此,情感作为一种表演方式,成为在公共领域中获得发言权和阐释力的关键词,用来解释时代过渡期中一种普遍的“倦怠、骚乱和迷惑”情绪。
这种对于爱情的“演说”和“表演”及至左翼文学时代的作家郭沫若和蒋光慈这里则更加明显。“郭沫若的多愁善感是表面而不真实的,是为了公开展示而并非私人情感。”[18]189蒋光慈在爱情故事和革命斗争的矛盾书写中,更是将爱情这一人类的私有情感与革命话语通过戏剧化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诸多小说作品中,爱情常作为革命的对立物而出现,共产党人常会为了革命而牺牲爱情。李欧梵并不完全赞同如夏济安所说的“蒋光慈坚持在关于革命的故事中加入‘爱情’,是为了清足他个人的情感需要。理想女性的爱情,和革命理想一样,是蒋光慈一生追求的目标。”[18]222相反,他认为蒋光慈从不让爱情在革命中扮演积极正面的角色,恰恰是因为他在现实世界中对于爱情的专注,“他渴望爱情、人间温暖和一个不错的家庭,却为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欲望而惭愧。因此,他太急于描绘革命,并强调应该把革命放在浪漫爱情与孝道之上”[18]223。蒋光慈的文学实践并未忠实于个人的情感经验,相反,他通过戏剧化的反讽书写方式,以情感的表演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孤独受难英雄”的形象,在爱的浪漫的基础上,于革命的书写中不断证明自己并完成自己的使命感建构。
即便如此,由他开启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已将爱情赋予了革命的激情。刘剑梅将这种“革命加恋爱”的文学想象视为一种“表演”,“革命”和“爱情”这两个概念在“表演”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不同的含义。爱情成为一种“劝说”的工具,一种影响和改变思想的方式,充满了感性的力量,营造一个能够使人们释放焦虑与激情的表演空间。正如刘剑梅所说,爱情在此“并不是简单地传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同时也制造了社会和文化认同,也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化实践,而这一实践又反过来不断补充或者改变马克思主义启蒙大众的原初意图。”[19]36及至左翼文学时期,爱情话语一方面延续了五四的浪漫传统,代表人对主体精神的追寻;另一方面掺杂了阶级意识,用以反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于此,情感成为一个公开的表演空间,用于展现五四流传下来的爱欲探寻与青年人心中的革命热情的双重追求。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身份和认知焦虑,使得他们虽然尝试着将自我形象与集体形象融合,并将革命寄于爱情之口,但个人情感和革命要求之间的不协调,使他们始终处于一种“个人兴趣与国家需要、革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中,在争取与放弃、融合与抗拒的姿态中左右摇摆。故而,情感的表演虽在概念层面生效,但在具体的情与欲的叙述中并不成功,其在实践层面的失败正提示着那些犹疑在两性情感关系和身份定位中的左翼作家,虽然言必及政治、革命,但依然徘徊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并未真正完成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身份及心理转化。
除此之外,作为表演的情感还具备话语颠覆力量。若将情感放置在上海这样一个“既有‘重’的关于国家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左翼革命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想象,也有‘轻’的关于娱乐、消遣、颓废等都市日常文化的想象”[19]152的公共空间里,则可打破传统的“进步与颓废”的二元对立模式,发现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情感的表演在不断复制和循环的过程中建构起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左派原初的目标——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受到上海都市各种不同文化的牵制,与颓废的资本主义都市生活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关系”[19]154。这打破了很多文学史家对写作“革命加恋爱”题材的作家身份的共同想象,即这些作家都拥有较为一致的政治和革命追求,为一种“共同历史”进行总体性叙述。在刘剑梅看来,虽然当时革命的潮流已浩浩荡荡,但这些居于上海的现代派作家却将“令人兴奋的革命景象转变成心理符号和充沛的色情幻想……一道色情的街景,喧嚣而诱人”[19]155。比如,施蛰存延续了“革命加恋爱”创作主题的小说《追》,便在上海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展示了情的诱惑和性心理冲动与革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男主人公将自己的情欲与革命幻想夹杂在一起,经常感到“暗示腐败堕落的力量能够与革命的力量相抗衡”[19]161。只有当他遭受到背叛时,此前的情与性的心理斗争才真正转变为政治战争,那种充满激情的革命话语被一种带有不确定性和杂糅性的情感表演所替代,“暗示着革命意识形态如何界定内部与外部、资产阶级和工人、堕落与革命,也同时暗示着保持那些概念被明确界定的困难”[19]161。同样隶属新感觉派阵营的作家刘呐鸥和穆时英则将这种情爱与革命的混杂性表现得更为清晰。刘呐鸥总是将革命的叙述归置在一个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被压迫的情感序列之中,欲望的压抑与放纵取代了阶级斗争的紧迫性成为被书写的主要对象,性魅力甚至成为革命欲望的驱动力,“‘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完全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色情游戏”[19]168。这与左翼作家的创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将革命话语所带有的进步主题和言说语境置换为一个“沉醉于性的色情世界中”,因而,这种谐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描写,只能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暧昧态度,而非批判精神,这与他所言称的暴露资产阶级腐朽和腐败社会危机的主观意愿并不吻合。而穆时英则在革命与情的纠葛中呈现了人的生存境地的多重矛盾,作为都市“漫游者”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主体哀叹物质主义和伪善入侵的矛盾,显现出现代性对人的分裂,证明了“不论是革命还是爱情,都不能使一个人摆脱现代危机,或者摆脱存在的危机和痛苦,都不能为现代人提供出路”[19]177。此时的情感,不再能提供左翼作家笔下那般美好的幻想和热烈的激情,反而,它和革命话语一起对“进步的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自省。
加之消费主义文化的刺激,“革命加恋爱”的创作主题不断偏离理想发展模式。比如张资平在此流行主题下的创作,虽然披着左翼思想的外衣,但仍难挡他对“消费文化”的真实关注,甚至在向人们说着:“所谓革命和爱情都是那么脆弱和不切实际,根本没有办法抵御都市物质生活的诱惑。”[19]180-181所以,他更倾向于用情欲、性游戏或其他都市景观来满足处于消费时代的大众需求,反过来说,这种写作方式又进一步刺激了“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的传播与接受。同样,叶灵凤对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双重迷恋,使他总是将自己应和大众文化趣味的“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创作伪装成政治宣传,他用充满诱惑力的情欲表演不断干扰政治语言的严肃性和道德感,用以讽刺革命与爱情相结合的文学写作现实。可以发现,张资平和叶灵凤在“革命加恋爱”的外壳下,书写的都是远离社会现实、娱乐大众的作品,与严肃的社会批评基本没有任何关联,更与初始“革命加恋爱”想要营建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
刘剑梅通过梳理“革命加恋爱”这一创作模式中情感的表演方式在传播途径中的不断变化和多元存在形态,向我们说明革命文学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化政治。既往的文学史家们所描述的那个革命话语超过一切的文学世界还有很多缝隙等待填补,情感的表演并没有被淹没在革命的大叙事之中,相反,它们通过上述这些作家对于商业化、通俗感、都市生活和个人理想的描绘中显现出来,共同参与着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这些正提示着我们,不能把情感的表演行为从革命文学的研究中孤立出来,情爱话语作为与革命话语并存的概念,在复杂的文化政治环境中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公共性,展现出与传统认知中“进步的现代性”相抗衡的力量,体现出中国现代性的另外一面。
五、公共性的反思与批判
宇文所安曾自谦道:“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20]这谦逊之词却提示着海外汉学家观点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其以“不同角度”观察文学之时,看到了什么固然重要,但“如何看见”是其身处不同社会文化场域对中国文学研究作出的更为重要的贡献。在这个“看见”的过程中,看见的内容和“看”本身的意义都值得分析探讨。海外汉学家以或遥看或近观的视角提出的“新问题”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正是以提出新的研究议题或改变旧有文学评价标准的方式共同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中。在此过程中,这些议题在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意见”交互的方式逐渐问题化,其初始之时的学术立场、学术理念及方法同其观点的表述一同成为研究与反思的对象。
这种反思于公共性的视野中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范围内行进。在空间维度,海外汉学家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以“意见”的方式穿梭在所谓“内”与“外”的交换空间中。具体来说,这种交换是在两个层面完成的。一方面,海外学者提出的研究问题和观点作为一种“意见”进入国内学界,其“意见”因蕴含部分真理从而成为国内学者们的研究资源和方法借鉴,是为“意见”的突入过程;另一方面,当其“突入”形成一定影响,便会引发国内学界以此为中心议题的更多“意见”的发声,形成另一轮“意见”的讨论与交互,是为“意见”的融入过程。在此“突入”与“融入”的交互过程中便形成或扩大了文学公共空间。而在“众声喧哗”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或可借用公共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完成。从上述对“意见”交互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海外汉学家将某种审美话语赋予公共性内涵,进而获得合法性进入公共视野之后,其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再独属于自己,而进入一种对话式的话语建构过程中,成为一种公开的议题,其话语公共性及合法性面临新一轮的检视与阐发。
在时间维度,由于文学本身是语言、情感与形象等因素与一时代之意识形态、历史意识等的融合体,文学之中隐含着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因而文学研究既有对文学历史和经验的研究梳理,也有着解决新的文学与文化问题的担当与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汉学家的研究问题也应放置在历时性的线索中进行考察,其在一时期内获得公共性的方法和角度在另一时期是否还具有效性,是应被纳入整体性视角进行考量的问题。职之是故,反思其话语的适用性及等值问题成为公共性视域下的重要命题。
以前文探讨过的中国“抒情传统”为例,便可较为清晰地看出具体研究议题在公共性的驱动下逐渐问题化的进程。当“抒情传统”作为一个议题进入国内学界之时,便成为一种具有评判标准性质的存在。各方学人将其作为方法介入本土文学研究时,将其所蕴含的美学观点与本土经验相结合,与中国现代诗歌、散文、小说、影视艺术等产生了关联性表述(8)将“抒情传统”与中国多种文类建立关联的研究主要包括:将中国散文“言情”与“言志”的内涵拓展至“抒情传统”的范围中来,以期使散文摆脱西方文学传统的羁绊而展现中华民族特有的风骨与神韵(参见陈剑晖:《论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第1-9页);结合对电影艺术形式和特点的分析,将中国电影中呈现诗化风格的类型(相异于擅长戏剧表现的“影戏”),纳入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视野之下进行讨论(参见宋杰,徐锦:《抒情传统下的中国诗意电影》,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4-14页);将玛莎·努斯鲍姆提出的“诗性正义”和中国 “抒情传统”加以历史地和跨文化地比较,证明中国电影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与他国审美领域及电影语言的可交流性,以期形成一种全新语境下的中国电影“共同体美学”(参见饶曙光,刘晓希:《抒情传统与诗性正义: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叙事伦理》,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16-121页);关注“抒情传统”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双向影响(参见韩松刚:《抒情传统与新时期小说叙事》,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第80-85页);探察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参见苏文健:《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以张错为中心》,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29-140页)。,并将其作为问题中心用以评价分析现代文学作品(9)参见颜水生:《抒情传统与小说的文体实验——欧阳黔森创作论》,载《南方文坛》2020年第5期,第185-189页.马宏柏:《端木蕻良小说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第144-151页。。可见,“抒情传统”作为一种审美评价话语,在由“外”入“内”地逐渐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场域的过程中,其本身因“移植”而带来的异质性在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中不断被修正。
而“抒情传统”作为一个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具体观点在文学公共领域进行“意见”交换时,也伴随着进一步反思,与其他“意见”产生张力式阐述,不断弥合其理论缺陷并获得新的话语生命力。例如有学人将鸳鸯蝴蝶派小说《花月痕》中“情之所钟,端在我辈”的哀情叙事看作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的开端,用以弥补王德威在“抒情”谱系建构中对民初“哀情”时代的遗漏之憾(10)参见张蕾:《花月痕之“痕”——兼论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第176-193页。。还有研究者在探寻废名小说与“抒情传统”之关联时,将中国“抒情传统”与文学母语的特性相联系,认为废名情、文相生的诗学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境界化叙事,在召唤“抒情传统”的同时,创化了母语文学的象、境、言统一的现代传统(11)参见杨经建:《“抒情传统”的新质与母语文学的“创格”——重论废名小说》,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44-153页。。在此,“抒情传统”在问题演进的过程中获得了与汉语言直观化思维相联系的另一重阐释空间,其理论话语得到进一步扩充。此外,季进还将夏志清文学史写作中包含着对普遍人性与人情关切的“优美”理念视为“抒情”的另一种发掘路径,“故国的抒情”成为他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史诗”叙述之外“第四种可能”的情感动力,他对宏大有序的“文学共和国”的探求正隐含着在当时冷战背景之下超越对抗的抒情性。由此,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被视作一种在世界视域下进行的满溢抒情性和充满文学自信的跨文化实践(12)参见季进:《“抒情传统”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2期,第205-211页。。由此,“抒情”之音不仅鸣声于现代文学抒情与时代的律动之中,而且成为一时代学人的情感结构,在学术场域亦有回响,抒情美学的话语辐射范围随之发生改变。
如是,作为“意见”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问题,在公共领域获取公共性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话语体系不断被检视并和来自其他视角的“意见”协商的过程。这种个体与场域的辩证关系类似于奚密理论架构中的“Game-Changer”(改变格局者)[21]27,但若以Game-Changer强调的革命性、颠覆性的力量概括海外汉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之嫌。因此,毋宁将海外汉学家看作为一个个“Game-Participant”(参与博弈者),每个人都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身份由Game-Participant 向Game-Changer趋近,在充满竞争性的game(博弈)中期望其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获得更多change的可能与力量。但在实践中,change的箭头是双向的,它不仅指向他人,也指向自己。换言之,在公共性的视域中的反思和改变也是双向的,海外汉学家的话语体系在追寻公共性的过程中,既对已有的评价体系产生冲击,又需在新场域中不断修正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