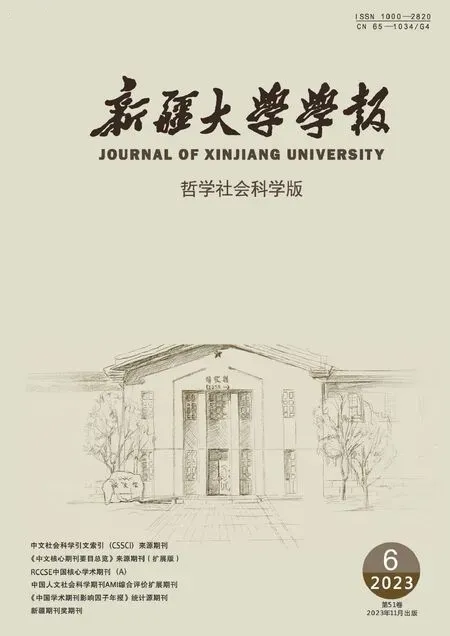以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法理学依据
——基于儿童保护与朴素正义的覃思*
陈轩禹,韩 丰
(1.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5;2.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令人瞠目的校园欺凌案件被频繁曝光,公众对校园欺凌表现出了一种掺杂着关注、热议乃至焦虑的情绪反应,这根源于校园欺凌的危害引发了人们对子女和下一代群体健康成长的隐忧,并演进为对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强烈期盼。校园欺凌是“一个紧迫的社会、健康和教育问题”[1],欺凌严重损害着受害者的健康①受害者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健康问题,表现出诸如睡眠障碍、尿床、腹痛、孤独、自卑和对人身安全的高度恐惧等临床症状,进而引发自杀意念。See Peter K Smith and others.School bullying in different cultural: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520.和学业成就②欺凌会降低欺凌双方的学业表现和教育回报率,被欺凌者的学业成绩往往低于其他没有经历过欺凌的学生,他们更有可能逃学,甚至完全辍学。See Brown S,Taylor K.Bullying,education and earnings: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8,Vol.27,Iss.4,pp.387-401.。欺凌行为亦会增加欺凌者和“欺凌—受害者”(bully-victims)们实施暴力行为甚至犯罪的可能性③欺凌者在青春期和成年后滥用毒品、学业成绩下滑、实施暴力的风险会增加,犯罪倾向会增强;受到欺凌后又欺凌他人的“欺凌—受害者”们则更倾向于从事违法行为和反社会行动。See Smokowski and others."Bullying in School:An Overview of Types,Effects,Family Characteristics,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Children&Schools,2005,Vol.27,Iss.2,pp.101-110.。自2016 年起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校园欺凌防治的规范性文件,展现了我国政府坚决治理校园欺凌的意志和决心,新时代的欺凌治理已经从“政策议题”逐步过渡为“法律命题”。
然而,以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学术性讨论在踌躇满志之时戛然而止。近年来,鲜有学者探讨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必要性和实施路径。法律上有关校园欺凌的防治内容仅一笔带过,未作出具体部署。本文认为,这归因于学界和实务界在不经意间淡化了用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本质原因和法哲学逻辑。当谈到“通过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必要性”,现有研究多为模糊地提及欺凌是对权利的侵犯,应予约束;抑或声称法治是域外校园欺凌治理的优选策略,④参见熊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凌〉报告》,《世界教育信息》,2019 年第32 期,第73页。应予效仿。学界就是否进行校园欺凌立法争论不休,却跳过了法律为何要介入欺凌防治这一最基础的论证逻辑。法学界对校园欺凌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其他学科又难以触及法律治理的本质,这导致学界探索法律治理欺凌的具体实施路径(专项立法抑或完善法律、侧重学校防治抑或司法介入)踯躅不前。因此,有必要对以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本质原因和法哲学逻辑进行剖析。
站在法理学的角度,校园欺凌在微观的个体层面是对权利的侵犯,在宏观的社会层面则是一个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已有研究仅从侵权法角度指出校园欺凌所侵犯的民事权利,却忽视了更加本源的儿童人权保护问题。就社会问题而言,现有研究也轻视了校园欺凌的特殊性,未能解答民众要求使用法律严惩校园欺凌的内在原因。面对校园欺凌的真实危害,人们逐渐意识到当道德偏差已然、现实造就校园欺凌恶果,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启动法律治理机制时,更需要理性的分析、行为的规约与观念的指引,而不仅仅是朴素的道德谴责与情感表达。因此,本文将先从个体层面论述欺凌对儿童权利的侵犯和学生校园保护的法治需求,再从社会层面剖析人们对欺凌所表露的朴素正义价值与法治诉求,进而明确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动因本源。
二、呵护儿童成长的必然要求
“欺凌是剥削”[2],是对儿童基本权利的侵害和对人权的践踏。人们对欺凌越来越关注,部分原因是“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3],与欺凌作斗争的核心需要源自于对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视。青少年享有其作为国家公民的一系列权利,类似学校这样的组织机构有责任维持学生在学校内所享有的人权标准。①See Dupper D R.School Bullying:New Perspectives on a Growing Probl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93.正如丹·欧维斯反复强调的,“让孩子在学校感到安全,免受同龄人欺凌或欺凌所隐含的压迫和反复、蓄意的羞辱,是一项基本的民主或人权”[4]。权利视角也有助于将法律干预校园欺凌的范围扩宽到那些容易产生敌对环境的行为当中。
(一)维护儿童人权的法治需要
在人权问题上,《世界人权宣言》第26 条第2款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1989 年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一步阐明了儿童所享有的权利,例如“公约”第16 条规定了儿童的隐私、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第19条规定了儿童不受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凌辱、虐待,第29 条则强调教育儿童的目的应当是培养其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②1991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决定”,从此该公约成为中国认可的国际公约。“公约”第16 条规定:“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第19 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第29 条规定:“缔约国一致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法律应当作出规定以确保学校能够保障所有学生的人权。
一般来说,现代法律所关注的人权聚焦于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就生命健康而言,校园欺凌会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基于学界对欺凌行为攻击性和侵犯性的共识,欺凌意味着故意伤害另一个人或造成其痛苦,欺凌者被认为比受害者拥有更加显著的力量。这种攻击性行为会重复出现,并引发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抑郁、孤独、社交焦虑、学校恐惧症、自卑等问题与被欺凌有着密切关联。③See Solberg M E,Olweus D.Prevalence estim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with the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Aggressive behavior,2003,Vol.29,Iss.3,pp.239-268.在欺凌环境下受害者会受到“公约”第19 条所述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虐待或剥削”,其安全和福祉所遭受的威胁违反了“公约”规定的保护要求。政府有责任依照“公约”制定方案以纠正这种不公正的欺凌现象。
就尊严而言,校园欺凌贬低青少年与生俱来的尊严。“尊严”通常被解释为“一个人得到了重视和尊重”,而“与生俱来”则意指“作为某个事物自然的或基本的部分而存在,不能被移除或改变”[5]。论语有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尊严本身的价值要比尊严所带来的人们活动所能产生的其他价值高,在最基本的道德层面上,不侵犯一个人的尊严比提升一个人的尊严更为重要。欺凌给欺凌者带来的快感,多来自于欺凌行为对受害者尊严的践踏与侮辱。对欺凌者而言,攻击与伤害受害者并不是其最终目的,他们更多地是通过欺凌贬低他人尊严,以此得到自身心理层面的满足。在无限制的校园欺凌所带来的羞辱中,相关主体的尊严都已丧失殆尽。尊严的维度要求社会为维护尊严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提供保障,①尊严的其中一个维度包括极低的社会地位以及过分地从属于他人,这就包括不受同伴欢迎的学生。参见托马斯·博格、李石《阐明尊严:发展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正义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第19-22页。法律应当对损害尊严的校园欺凌行为加以制止,这也符合“公约”第28条有关学校保护儿童尊严的规定。②《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学校执行纪律的方式符合儿童的人格尊严及本公约的规定。”
除了关注校园欺凌对个人的侵犯外,以儿童为中心的人权视角有助于将治理校园欺凌的注意力转移到由欺凌所导致的“敌对环境”上。有关“公约”第29条所述教育目的的官方评论指出,“学校环境本身必须反映出自立、和平、容忍、两性平等的自由和精神”[6],允许恃强凌弱或其他暴力和排他性做法的学校显然不符合第29条的要求。尽管“公约”没有提供任何执行机制,但基于“儿童与成人平等享有人权”的基本价值,“公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框架,在这一框架内,校园欺凌被认为与儿童人权保护所需要的尊重和安全的教育环境背道而驰。根据“公约”的精神,各组织(如学校)有义务维护人权标准,这将给予学校充足的法律依据用以防治校园欺凌。同时,侵犯人权的行为性质更加恶劣,将校园欺凌认定为侵犯儿童人权的行为,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们对预防和治理欺凌重要性的认知,也能够克服在使用法律方法减缓校园欺凌严重性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更加有助于关注欺凌动机和那些通常被忽视或被低估的欺凌形式,例如恶意散布谣言、网络欺凌、基于外貌、社会地位、嫉妒、个性和个人特质的欺凌等。③See Woods S,Wolke D."Does the Content of Anti-Bullying Policies Inform us About the Prevalence of Direct and Relational Bullying Behaviour in Primary Schools?"Educational Psychology,2003,Vol.23,Iss.4,pp.381-401.法律和政策倡导是齐头并进的,二者都是迈向公平、人权保护和学校免受欺凌困扰的必要条件,④See Michael B. Greene, Randy Ross."The nature, scope, and utility of form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prohibit schoolbased bullying and harassment".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HAMILTON FISH INSTITUTE ON SCHOOL AND COMMUNITY VIOLENCE,2005,pp.91-100.只有当我们为不可剥夺的人权而战时,学校中不公平的欺凌行为才不会盛行。
(二)救济保护与错误行为矫正的现实要求
将法律引入校园欺凌治理,主要是依靠法律的强制性、稳定性、权威性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呵护其健康成长。在人权视角的铺垫下,结合校园欺凌的特殊性和实际危害,可更进一步地明确以法律治理校园欺凌将为欺凌双方带来何种益处。
对于欺凌者而言,法律治理能让欺凌者的错误行为得到遏制和矫正。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校园欺凌是促使和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⑤早在1994年就有研究显示,欺凌者比他们的同学更有可能被送上少年法庭,被定罪判刑,成年后他们的孩子也存在更多的攻击性问题。See Hazler R J."Bullying Breeds Violence.You Can Stop It!".Learning,1994,Vol.22,Iss.1,pp.38-41.这种极易引发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必须得到遏制。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已然证明欺凌危害严重的客观现实下,很多学校受制于固化思维,往往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校园欺凌及其危害,导致处理结果较轻、处理方式单一、威慑性不足。有学者将欺凌问题归因于法律治理与惩罚滞后所导致的青少年认知与行动的失衡,而并非其自身的道德沦丧。⑥参见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治理的跨学科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2-23页。法律的威慑性可以有效解决学校回避处理和惩戒较轻的问题。根据最基本的正义原则,施加给欺凌者的惩罚应当与其不法行为相称,法律手段的威慑性既包括对欺凌者的直接惩罚,也包括法律对学校和个人的负面评价。完善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的教育惩戒措施,完善赔偿性民事责任、惩罚性行政和刑事责任,让欺凌者感受到对惩罚的恐惧,将有助于矫正不良行为、减少欺凌行为、预防犯罪行为,使其尽可能地回归健康有序的校园生活。
对受害者而言,法律能够通过司法诉讼等程序起到妥善的救济作用,促使受害者摆脱校园欺凌的负面影响。不同于普通的校园伤害行为,校园欺凌既是对受害者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更会危及欺凌双方的心理健康与精神状况,引发受害者“恶逆变”⑦通俗地说“恶逆变”是指受害人转变为了加害人,即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遭受违法犯罪行为侵犯后,在不良心理的支配以及其它因素的推动下所导致的反向变化,从被害者的角色向加害者转化。参见王临平、赵露娜《防止未成年被害人恶逆变》,《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3期,第23-25页。风险。如果校园欺凌行为得不到有效处理,那么受害者将难以获取救济并从伤害中得以恢复,欺凌双方和旁观者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也会因不公正的处理而受到负面干扰。将法律程序引入欺凌治理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以侵权法为核心的民事赔偿虽然不能提供彻底的救济,但也能够给予受害者一定程度的慰藉。侵权法应当关注所有对于侵害事件的回应,正如埃伯斯坦所说:“自愿损害他人的人,即使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也在以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自己目的的意义上获利了,因此他必须赔偿。”[7]侵权法的目的是公正的赔偿与吓阻,因此欺凌者必须要为自己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这可以通过完善针对欺凌损害特殊性的赔偿方式来实现,例如增加精神损害赔偿。另一方面,法律可以通过金钱赔偿以外的其他方式满足受害者的心理救济需要。除赔礼道歉外,发挥修复性正义的作用,例如引入修复性司法的方法,通过法律制定相关的程序性要件予以妥善安排,在物质补偿的基础上,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和群体评价。
三、对民众朴素正义诉求的法治回应
上文已述,从微观的个体层面上看,校园欺凌是对儿童权利的侵犯,需要法律介入以保护儿童健康成长。那么,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说,校园欺凌是如何成为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并要求法律介入呢?这或许与人们朴素的正义诉求密不可分。欺凌危害的严重性和欺凌者们不怀好意的恶劣行为触动着人们的内心,引发人们源于道德良知的朴素的正义情感。朴素的正义观是人们普遍认同且具有共识性的正义观念和思想,是最直接的感受与价值判断。在朴素正义感的驱使下,严惩欺凌者、打击校园欺凌行为成为民众面对校园欺凌时的直接要求。为了回应人们这种由欺凌危害所引发的基于朴素正义感的价值判断和惩治诉求,法律应当在校园欺凌的治理中有所作为。
(一)民众对欺凌所表露的朴素的正义情感
校园欺凌是攻击性行为,兼具道德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的双重性质。从行为学和心理学角度,人的攻击性是一种本能,表现为搏斗、厮杀、威吓、欺凌。弗洛伊德等人认为,欺凌者的攻击性源于人的“破坏性”“好斗性”本能,利用攻击性行为,欺凌者“宣泄自我的情绪,找到存在感,获得自信和力量”[8]。同时,校园欺凌是由人的权力占有欲引发的随附行为,这与权利根源理论所认为的“实施欺凌行为的个体有着强烈的控制感及权力欲望”[9]相一致。
那么,在涉及校园欺凌的攻击性行为时,为什么人们会对此呈现强烈的反对态度,并力求予以干预和消除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所具有的朴素的正义观对欺凌行为的错误性作出了价值判断。较为典型的例证是,在朴素的善恶观影响下,每当恶性欺凌事件被曝光时都易引发社会公众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①参见张婧《法意与民意: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价值蕴涵》,《犯罪与改造研究》,2020年第11期,第2页。、严厉打击欺凌行为、将欺凌“犯罪化”处理的强烈呼声和官方主流媒体对欺凌行为“零容忍”的呼吁。②自2019 年以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次发文提出对校园欺凌要“零容忍”,同时从各媒体客户端下的评论区可以看出,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新闻事件的热评多集中于呼吁严惩犯罪青少年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尽管刑法学界并不都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正确的,但民众尤其是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有切身感知的人却不以为然。当欺凌等违法犯罪事件未被公众所知或未发生于自己身边时,人们又会从性善论的角度给未成年人投以关怀和善意的目光。
朴素的正义感是人们内心中对正义最本能的期待。“它往往指那些出于人性需要的、无须政治意识形态渲染的对正义的渴望和行为。”[10]我国社会中的正义观念是一种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正义观。这种法律规则之外的善良正义,源于道德良知、民众情感和经验法则。道德良知的基础在于道德内心的觉悟。知善知恶是为良知,人们为了免于“良心谴责”而约束自身行为,并因恻隐之心或良知而理解社会的道德与正义。民众情感反映着人们所秉持的正义价值,是对善良与公正的崇尚、对恶行与虚假的否定,是朴素的民众感觉。它来自于“社会中一般成员所共有的整套信仰与情感”[11],并且这种意识在无形中被奉为评价社会行为的是非标准,不能被冒犯。经验法则是“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有关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为社会中普遍常人所能体察和感受”[12],具有社会认识的共有性和公信力。
基于朴素的正义感(一种自然法秩序),鉴于欺凌的严重危害,怀有道德良知的公民会认为校园欺凌是不道德的错误行为,欺凌者是“坏孩子”,民众情感渴望欺凌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惩戒,并逐渐形成“校园欺凌十分严重,需要严厉打击”的潜在意识。出于经验法则,人们也会认为欺凌者的不良行为需要通过惩罚等方式得以矫正。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所说的那样,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未能受到他人善待的人们而言,道德范畴的评价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被欺凌者的喜怒哀乐和因欺凌所遭受的痛苦在人们心中引起共鸣,尤其会引发为人父母的恻隐之心。那些被媒体披露的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在无意间触动着人们的心灵,促使民众在对校园欺凌作出善恶判断的同时,希望欺凌问题能够通过合乎正义的方式得以解决。
同样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当被欺凌者们的诉求难以通过司法裁判或其他官方程序解决时,他们会采取求助于帮手或自扮为正义使者的公开或秘密的“报复”行动,寻找时机报复欺凌者。就受害者而言,大部分未成年人尚处在身心发展阶段,法治教育的薄弱和学校救济制度的缺失使其未能掌握正确的欺凌处理方式。在少年眼中校园欺凌乃是霸道的强势一方恶意地对弱势一方实施的伤害行为,强势的欺凌者那漆黑的恶意将赤裸裸地暴露于受害者面前。对于被欺凌的少年来说,伺机报复欺凌者既是其反抗欺凌的方式,也是试图解决欺凌行为的办法。正所谓,通过报复让那些冒犯你的人和因为你被欺负而讽刺挖苦你的人感受到与你曾经相同的屈辱和痛苦。①参见〔美〕威廉·伊恩·米勒《以眼还眼》,郑文龙、廖溢爱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不管是自卫还是报复,“只要能实现侵害成本的有效内化,且符合对称性、回应性和相当性,‘以暴制暴’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就能获得公众的理解甚至同情”[13]。然而这种“以暴制暴”的手段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破坏性和残酷升级的必然性。这就要求应当以法律的规则之治应对校园欺凌行为,以避免从公力救济转向私力救济所引发的暴力性事件。
(二)法律治理是对人们朴素正义感的应然回应
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是对校园欺凌的危害和民众朴素正义观的法治回应。建立法律治理体系,依靠法律的指引、教育、预测、强制作用促使校园欺凌的防治落在实处。在校园欺凌的相关立法中吸收情理因素,让法律与我国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相结合,达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在校园欺凌案件的法律实践中,尊重朴素的正义感,充分考虑情理因素,对欺凌案件中的“动机”“手段”“结果”等因素进行具体分析,认真考量欺凌各方的综合情况,从而给予相关主体合法且合理的惩罚与救济,达到相对公正。完备的校园欺凌法律治理制度能够从以下两点回应民众对校园欺凌的担忧和惩治诉求。
第一,通过法律制度的设置可以提高欺凌防治主体对校园欺凌危害性的认知,针对性地缓解欺凌诱发因素,从而遏制校园欺凌行为以逐渐消除民众对校园欺凌频发的隐忧。一方面,通过补充和调整现行法律,对家庭责任、文化传媒进行引导,使家庭切实地履行教育与监护职责,减少媒体传播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改善社会环境因素。另一方面,通过专项立法对校园欺凌的常规防治工作进行制度性规定,要求学校做好教育引导和预防工作,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和互动机制,满足学生的依恋、奉献、投入、信念需要,减少引发欺凌行为的个体不良状态,预防欺凌发生。
第二,通过法律治理能够更好地发挥法的惩罚、威慑、救济作用,回应民众的惩治诉求。在校园欺凌发生后,欺凌双方理应受到合法且公正的对待。一方面,通过完善综合性法律强化公检法机关在校园欺凌治理中的作用。施以欺凌者合法的惩戒,给予受害者充足的救济,使人们感受到欺凌案件处理中的公平正义。在法律报应正义的制定法秩序下,规训和惩罚基本上与义务属于同一类型。“它与其说是一种被践踏的法律的报复,不如说是对该法律加倍的重申,以至于它可能产生的矫正效应不仅包括附带的赎罪和忏悔。”[14]应当依据欺凌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所涉及的法律性质对欺凌者施以惩戒,满足被欺凌一方对正义的渴求。另一方面,完善学校防治所依托的专项法律,授予学校处理校园欺凌的权力,明确教育惩戒权和具体措施,让学校在以道德教育为主要手段以求达到长善救失目的的基础上,做好应有的惩教工作。学校具有保护学生身体和精神安全的义务,通过法律规定学校在欺凌防治中的权责,既能为学校有效管理学生提供基本根据,又能“为诉讼争议发生时司法认定责任提供重要的法律指引”[15]。强化学校的一线防治作用,让校园欺凌的预防及事后处理更加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