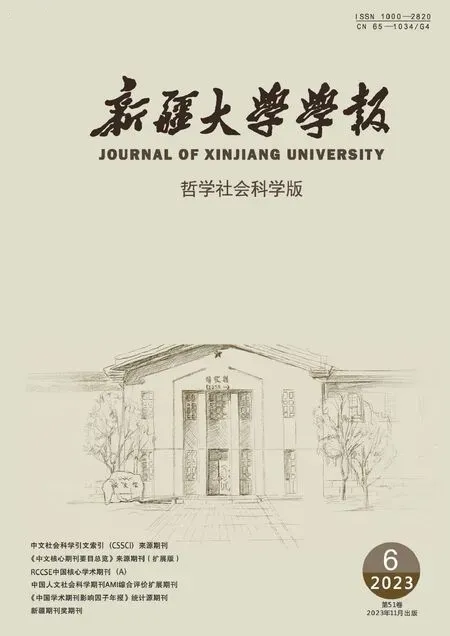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用机理与优化路径*
黄巨臣,苏 睿
(兰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前瞻性地提出了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2],这为今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方向和遵循。有鉴于高等教育在农村发展中具有的关键性地位与作用,且在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内涵与功能已经得到了极大延伸与拓展,作用和服务范围早已超出教育的领域向产业、组织、文化等纵深挺进,有必要将其视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2022 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方案……有计划开展教育……组团式帮扶”“支持办好涉农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3]等内容,肯定了高等教育在国家战略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角色,乡村的发展、建设以及治理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参与、支持和服务。那么,应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亟待研究的前沿议题。
从目前学界相关成果看,国内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主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阐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汪三贵认为,二者有效衔接的内涵是“涉及体制机制、政策落实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有机衔接”[4]。(2)探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与逻辑。涂圣伟基于自身经验提出,二者有机衔接应重点关注扶贫产业、扶贫资产利用等领域。①参见涂圣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8期,第2-12页。白永秀、苏小庆等学者以为,有效衔接的逻辑分为两个方面:在理论逻辑上,链接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实践逻辑上,是实现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拓展”。①参见白永秀、苏小庆、王颂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人文杂志》,2022 年第4期,第50-57页。(3)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与挑战。叶敬忠和陈诺从宏观层面分析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包括:城乡资源要素分配和流动的不平衡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以及衔接上的计划脱节、基础较弱、驱力不够等。②参见叶敬忠、陈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顶层谋划、基层实践与学理诠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0-16页。(4)总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措施与路径。左停、李颖等指出,除了要发展农村经济产业外,还要“以落实防贫保障为基础、以夯实发展基础为前提、以构建长效机制为关键、以强化志智双扶为根本、以衔接乡村振兴为目标”[5]等路径来推进。
上述成果聚焦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逻辑、问题以及路径等方面,并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为本文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高等教育这一重要的视角和内生因素。事实上,要真正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不仅要依靠外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从功能上看,高等教育正是作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力量和要素而存在,其以各种类型的参与形式和手段来精准服务农村社会建设,激发广大农民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更深层次来看,激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都直接或间接涉及高等教育因素。例如,农村人才资本水平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能力优化和农村社区的治理水平提升都需要依靠各类高等职业教育培训和高校专业技术人才下乡等来实现。
因此,开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时,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理论逻辑、作用机理、存在问题及其路径优化进行系统探讨。
二、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在赋能中增能
赋能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概念最早出现于20 世纪70 年代,由美国学者所罗门(Soloman)在《黑人赋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区》中提出。她通过研究当时美国黑人工作情况来揭示出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以通过寻求赋能来减少他们的“无权感”,即赋能是一个增加个人权利的过程。③See Soloman B B.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8.随后,该理论被大量运用到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教育学等领域。Conger 和Kanungo 研究发现,给那些不受重视的普通企业员工配置一定管理权,能有效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自信心。④See Conger J A, Kanungo R N.The Empowerment Process: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Vol.13,Iss.3,pp.471-482.Riger 在后续研究中提出了新观点,认为不能仅关注赋能过程,还要注重个人和群体对资源的实际获得占有。⑤See Riger S.What’s wrong with empowerment.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93,Vol.21,Iss.3,pp.279-292.Rappaport 则对该理论的适用对象进行了拓展,提出赋能不仅仅发生在个体和群体之中,同样也存在于组织、社区层面。⑥See Rappaport J.Terms of empowerment/exemplars of prevention: toward a theory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87,Vol.15,Iss.2,pp.121-148.Chadiha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指出赋能与资源、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赋权及其带来的各项权力、权利、资源等来改善当前处境,提升生活品质。⑦See Chadiha L A,Adams P,Biegel D E,et al.Empowering African-American women informal caregivers:a literature synthesis and practice strategies.Social Work,2004,Vol.49.Iss.1,pp.97-108.通过对赋能理论含义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赋能不仅仅是指个人、组织、社区等获得的外在帮助和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在的支持来实现内在能力的发展。赋能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个人、组织乃至社区在社会资源稀缺与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下,他(它)们的处境是不利的,但通过外部帮助可以改善。这符合国家和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根本价值追求。
在中国具体情境下,这种假设与理念也为高等教育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正当的“合理性”根据,使得高等教育在发挥自身价值与功能中成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性力量。从这个层面上的意义去理解,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中的重要探索,赋能取向已成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一种模式。更进一步看,乡村振兴领域中的高等教育本身是作为一种“权力/权利”“机会”与“资源”而存在,其参与和服务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赋能乡村发展的过程。需要指出,与西方赋能理论内涵指向所不同的是,中国乡村发展视角下的高等教育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多重意涵与价值:外部权力/权利、资源、机会的获取、内生发展能力的强化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既要给予外在的帮助、支持和服务,更要以此来激发个体、组织和社区等内在发展的动力与能力,最终在赋能中实现增能,走向共同富裕。这就是蕴含其中的基本立场和理论逻辑。
三、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作用机理
高等教育与其它阶段的教育相比,更具实践性和效益性。通过高等教育的力量可以更精准地赋能农村基层各个领域和各类要素的发展。乡村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基层组织执行能力提高与农村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因素和核心环节,下面将从个人、组织与社区这三个维度来阐述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现实机理。
(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增强与农民素质提高
人力资本积累与增强是国家和社会得以繁荣发展的核心动力,农村的发展同样遵循该定律。作为关键资源要素的农民,既是被高等教育关注的对象,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论断已在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得到证实。例如,广为人知的一个研究案例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通过对美国农业资源利用状况开展调查,发现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农民可凭借自身掌握的知识技术实现对有限资源的高度利用,进而获取更高经济回报,并最终得出结论——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农民个体更能应对农业技术环境的改变,也更知晓如何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①参见马丁·卡诺伊《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170页。从人力资本视角看,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传统的村落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对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促进农民科学文化知识与素质的提升,掌握基本的现代劳动生产技能;可以增强农民获取和利用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能力,“将人的地位从单纯的经济资源要素提高到资源运用的主体”[6]以及帮助他们发展内在能力,进而获取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以改善弱势地位。例如,自2018年山西省开展“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工程以来,忻州市繁峙县的农民通过参加地方政府和高等职业院校联合举办的“专业知识技术培训班”,不仅获得了自身生产活动所需的技术技能,接触到了网络直播营销等电商知识,拿到了技能考核证书,而且这些职业技能培训显著提高了广大农民创造财富的能力。经过一系列培训,2022年,繁峙县金山铺乡农发村村民已掌握了肉牛养殖繁育技术,建立起电商销售渠道,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有效巩固了前期脱贫成果。该村“目前户均养殖7 头牛,人均收入2.6 万元。村集体收入现在超过百万元,养殖肉牛超过2 000 头”[7]。可见,经由高等教育提升后的农村人力资本,将对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生深远影响。
(二)高等教育、组织动能与政策执行能力强化
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期,为确保深度贫困地区的持续脱贫、脱贫成果的巩固拓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国家已陆续出台涉及产业融合发展、村民易地搬迁、科技教育下乡等不同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来保证上述目标的如期实现。更进一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而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又在于农村基层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基层组织将来自顶层的国家治理需求与底层的群众发展需求有机整合为一体,并能动性地根据具体情况和问题性质的差异做出迅速的应对”[8]21,有力保障了“政策资源在农村社会的有效运行与分配”[8]21。在当下,高等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活动主要表现为地方高校深度嵌入并服务乡村,展示出了明显的组织优势和知识优势。现有研究已经证明高校与农村组织之间的交流越多,社会关系越紧密,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供需匹配程度越高,“高校人力资本在农村行政组织、农村经济组织间流动,促进了高校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扩散,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9],进而增强了农村基层组织执行政策的能力。例如,从2015年开始,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禄峒镇6 个贫困村建立帮扶关系,服务队成员下村70余次,开展了55期讲座,涵盖了国家政策宣讲、党务村务工作技术指导等。其中,所帮扶的思侯村“村两委”组织建设取得较大成效,尤其在执行上级“促进消费扶贫”政策方面,村干部在管理能力和执行方式上有了大幅改进,主动与外界企业、高校等商谈合作事宜,创新多种产品销售形式。仅2020年年初,与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签订的采购额就达45.94万元。2020 年4 月,思侯村入选广西《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典型案例选编》。①参见人民网《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建助脱贫,产业促发展》,网址:http://gx.people.com.cn/n2/2020/0930/c390645-34328889.html.访问日期2022年6月1日。可以认为,地方高校嵌入乡村的过程,同时也带来了资金、人才、技术、知识等资源要素,特别是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的专门业务培训,提高了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赋予了基层组织发展的新动能,进而强化了政策执行能力。
(三)高等教育、制度改进与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蕴含着改进现有制度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要求。相关研究表明,制度优势与治理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完善的制度能够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②参见夏茂森、朱宪辰、江玲玲《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特区经济》,2011年第10期,第157-158页。基于高等教育参与和制度改进的协同关系分析,制度的改进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源于知识进步。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与农村各项现存制度不断磨合、融合乃至对其进行改进的过程。再者,当代的高等教育“它承担着广泛的公共义务,包括:走出校门……以及尽力密切学术团体与地方的重要联系”[10]。其中,“把推动制度改革作为组织本身的一项计划”[11]是高等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内容,更被当作是其社会服务职能的应有之义。例如,为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纠纷,广东财经大学受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办公室委托,派出专家组对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石鼓镇深冲村进行调研帮扶(该村现有流转土地1 755.6 亩,占全镇土地流转总面积的5.95%)。通过面对面访谈、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调查后,学校专家组对该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以及出现的利益纠纷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专家组研究提出了一套流转对象明确、流转信息透明、流程步骤规范的利益分配制度,并向省委汇报获得了支持,进而有效解决了深冲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租价标准模糊和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村庄社区的稳定和谐。③资料来源: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石鼓镇人民政府。故而,“专家下基层”“科技特派员”等形式的高等教育参与,能为农村各类制度的完善提供必要帮助,进而更好地提炼农村脱贫的典型做法经验,将之体系化和制度化,还可健全农民利益分配和权益保障机制,从而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水平。
四、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多重困境
赋能理论关注如何给予个人、组织与社区足够的权力/权利、资源以及机会等支持,恰恰也是当前高等教育在参与乡村发展中关注的三个重要层面,而期间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样是通过个人、组织与社区的情况表现出来。
(一)个体困境:农民个人主体性的缺失
高等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保障,但一些农民缺乏主体性意识却阻碍了高等教育对农民个体的赋能,进而导致他们无法真正实现内在能力提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首先,“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小农经济尽管促进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衍生出安于现状、守旧求稳的思想观念”[12]7。在这种思想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不少农民不仅不会主动了解获取国家出台的各类惠农政策信息,而且对正在实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行动也不愿参与,这反映出农民未意识到自己就是乡村建设的“主角”。其次,在不少乡村建设行动中,“农民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被动……去参与或卷入。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而有一定的普遍性”[13]。当前,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已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一些肩负定点帮扶任务的农林类、工商类以及高职类等院校已经在逐步开展专门提升农民职业技能的短期培训、职业培训和学历教育。然而,一些地方出现了“被动性参与”,即:农民参加各院校开展的某项职业技能培训是为了获得培训资金补贴,而非基于自身的长远发展需要考量,“对接受自身综合素质能力等发展性的教育与培训缺乏主动追求的精神”[14]231,且2020 年一项针对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120 位农民职业培训的实证研究显示“仅有5.2%的人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94.8%的人没有参加过,调查群体的农民职业教育参与度低”[14]230。此外,高等教育参与乡村建设的服务体系与农民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与偏差。“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地区性和持续性等特点,农民对培训内容的个性化需求非常强烈”[15],而一些院校在实际的服务过程中为尽快完成任务和节省人力、物力成本,对有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训练需求的农民识别不够精准,忽视成人学习特点和农业生产规律,采用的培训手段单一,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参与的主动积极性。
(二)组织困境:基层组织的功能性衰弱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功能表现出了以弱化和涣散为主要特征的衰弱,已影响到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的实现。首先,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定位的模糊。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以及各类政策、资金等资源的大量进村,农村公共性事务急剧增加且变得日益复杂,使得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疲于应对,在进行乡村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公共性定位愈加模糊。这种公共性定位的模糊主要表现在:按照《中国共产党乡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16],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年修订)则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17],“但在实践运行中两者却存在模糊交叉地带,而且在实践中,村党组织以及党支部书记的政治地位要比村委会及村委会主任更高一些”[18]。在实际的资源分配、管理和使用中,村党支部也经常参与其中,成为事实上“掌权人”。此做法不但引发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会导致资源管理配置不当,进而弱化农村基层组织原有功能的作用。其次,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发挥方式的偏差。事实上,高等教育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内含三重目标: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②推动乡村振兴;③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前两个目标是为第三个目标服务,而目标的实现既涉及高等教育各主体力量本身的组织优势与条件基础,也涉及高等教育所提供的资源得到合理使用。这意味着单纯依靠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难以独自开展和完成上述公共事务活动。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其它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校等主体通常被排斥在外”[12]7,集便民服务、专项整治以及日常事务执行于一身的“村两委”基层组织,因大量承接任务使得原有依赖于内部人员和资源的管理方式遭受到冲击,从“专而精”转变为“泛而空”,致使组织功能日益涣散。
(三)社区困境:农村社区治理的低效能
当前,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低效能问题日渐突出且已经成为困扰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农村社区所获得的赋能性服务支持还远远不够。首先,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换言之,农村中的广大民众所获取和享受的服务,并不符合自身的实际需求以及获取的难度较大。“随着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日益扩大、多元的需要与规模不足、质量不高、不平衡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凸显。”[19]就高等教育力量嵌入并服务乡村发展的实践情况而言,高等教育的赋能与服务供给主要是通过各类院校及其相关的教育组织机构来实现。由于大多数提供服务的高等教育组织和机构均有自上而下的考核,其服务方向和重点往往更偏向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所关注的内容,习惯于遵照上级指示保守执行,难以实现对社区的深度嵌入和均衡覆盖,甚至是对如何在“乡村建设中自主、有效发挥自身功能缺乏研究与探索,社会责任意识、社会公益意识、自我发展意识均有所局限”[20],实则表明了专业性服务能力不强,进而导致对农村社区的服务赋能不够,削弱了社区治理效能。其次,农村社区获得的制度供给不足。高等教育服务乡村发展的重点主要还是在人才、技术、资金等层面,对涉及制度政策上的支持和建设还相对不足。例如,浙江省乐清市象阳镇桥前村和王家店村的“村规民约”以“从夫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为根据,以制度规章的形式把侵害农村妇女权益的情况“合理化”,致使那些准备出嫁的、已出嫁的、离婚回村的妇女无法享受应有的各项土地权益待遇。①参见袁艳《浙江一些地方“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合法权益》,《浙江日报》,2010年1月14日,第15版。直至今日,这些情况都未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而作为对接象阳镇乡村建设的具有法学专业优势的院校也并未充分发挥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对那些存在问题的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和完善。高等教育力量对乡村发展在制度层面专业性知识和技能供给的不足,可能会影响乡村社会治理的长治久安,稀释前期农村社区的治理成效。
五、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优化路径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高等教育赋能乡村建设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境。赋能理论认为,为保证个体、组织以及社区能够有效改善不利处境,获得所需的资源与机会,应注重通过多种形式给予他们所必需的支持和帮助,包括知识、技能、资金、机会等。而为了解决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困境,同样需要在个人、组织和社区层面来予以突破。
(一)深化高等教育赋能农民主体发展的内生性
内生性是保证农民个人发挥主体性的关键,以深化内生性来提高主体性是切实可行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广大农民主体性意识不高实则是内生性不足的反映。国家和政府希冀通过政策与资源倾斜来保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的实现,但如果忽视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民特征,就容易导致政策失灵。因此,有必要深化高等教育赋能农民主体发展的内生性,既要融入乡村社会,更要融入乡村社会农民的发展需要之中。
首先,高等教育融入乡村社会的内生化,扭转农民传统思想观念。要打破广大农民安于现状、守旧求稳的思想观念,需要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在充分了解并对地方乡村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不足或落后之处进行批判性扬弃的基础上,赋予其以新时代内涵,“让农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文化心理等与现代化相衔接、相融合”[21],以此带动引领新思想观念的生成,帮助农民树立起“开拓进取”“自立自强”“知识致富”的新观念。在此基础上,参与乡村建设的各高校、科研院所等高等教育力量应对参加培训学习且表现优异的农民进行重点表彰宣传,以此提升荣誉感、自豪感和获得感。同时,在表彰中要致力于让农民意识到知识和技术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让他们从内心自主认同和认可参加各类培训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鼓励更多农民参与,规避单纯物质奖励和资金补贴等手段带来的弊端。正如西奥多·舒尔茨所言:“改进穷人的福利的关键性生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22]其次,高等教育融入农民发展的内生化,精准对接农民实际需求。高等教育在服务农民发展中,应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并根据农业生产规律和农民生活情况,因地制宜、因需制宜地开展个性化、精准性助农活动。在前期,面向对接服务的乡村进行大规模调研,广泛收集农民的意见与需求。在后期,根据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以农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目标,设计符合农民需求的服务内容,采取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开展活动。通过以上措施,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二)提升高等教育赋能基层组织建设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农村基层组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所要遵循的内在逻辑。在组织建设视野下,要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弱化和涣散的功能性衰弱困境,主要还是在于发挥高等教育作为乡村公共性建设者的作用,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定位和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发挥方式的科学性。
首先,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定位。将高等教育自下而上的介入与以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要求相结合,督促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为代表的农村基层组织分别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 年修订)、《中国共产党乡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对各自性质、功能和目标的规定,找准定位,清晰划分二者的职能边界,特别要注意不能把村委会视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末梢”或是“兜底”角色,而要将其当作是法律意义上的农村基层自治性组织。高等教育研究平台、智库、院校等应自觉将现有的人才、组织等优势转化为可供农村基层组织发展需要的现实举措,适当引导它们进行组织性质、组织理念、组织目标的再认识和公共性建设,从而使得组织的功能定位更为聚焦,遏止组织功能的涣散。其次,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发挥方式的科学性。帮扶高校应将“农村基层组织发展”作为一项课题进行研究,建立驻村工作站等科研与实践平台,借此培育农村基层组织的公共性,积极吸纳其他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校等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形成“事务共商、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成果共创”的多方协同格局。基于此,可建议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把一些非核心事务交予其他组织来协作完成,这不仅能提高办事效率,也能保证自身组织核心职能的有效发挥,避免陷入功能涣散的境地,从而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强化高等教育赋能乡村社区治理的专业性
加强和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是早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的关键。面对因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和获得的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社区治理低效能困境,一些学者提出打破困境的关键在于增加资源总量投入或优化制度环境,进而改善现有状况。但即便如此,乡村建设中社区治理的低效能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合理解决。究其原因,以往措施和对策均未涉及社区建设的专业性层面。在高等教育赋能语境下,专业性体现为高等教育主体利用自身专业性优势向特定农村社区提供服务和产品(制度)的综合素质能力。
首先,强化高等教育对农村社区所提供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涉农类高校、高职院校、高教科研平台和智库等应增强自身的服务意识,既要树立起服务乡村建设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公益意识,还要做到精准对接农民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教育现实需求,提升各类服务的可获得程度和可覆盖范围。尤其是肩负帮扶任务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借助教育评价改革契机,完善社会服务评价机制。服务乡村的方向和重点除了要关注上级部门和领导重视的内容,也要回应社区内部农民群体的期盼,建立起以“满足农民需要+提升治理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倒逼各高等教育主体专业性服务能力的提升,保证所服务社区农民享有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次,强化高等教育对农村社区制度的供给。此处的“制度供给”并不是指由服务乡村建设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提供新的规章制度,而是指在农村社区原有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协助进行再设计和优化。当前,农村社区的现行制度规定不仅多是宏观性的原则表述,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规定的内容明显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格格不入,损害了特定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高等教育作为服务乡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和义务运用自身专业性知识技能优势来对关切农民利益和诉求的领域开展协助制度修订工作。从科学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专业角度出发,明确社区中的村规民约等制度章程“倡导什么”“摒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后要承担何种后果”,推动农村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切实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支持。
六、结 语
时至今日,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关心的大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接续推动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以高等教育赋能来增强乡村农民主体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执行能力以及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效能,可以帮助个人、组织和社区获得更多发展的权力/权利、能力、资源和机会,改善现有处境。可以认为,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是特定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特色模式,也是一个重视高等教育赋能农村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诚然,需要承认的是,囿于案例资料收集的难度,本文更多的是从学理角度对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依据逻辑、作用机理、面临困境与优化路径作出论述探讨,在经验考察和案例呈现上还有待深化挖掘。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收集和补充更多的案例素材,以支撑和验证高等教育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作用机理是如何发生和运作的。同时,在本文已有理论基础上,可对乡村农民个体、组织以及社区等赋能对象或要素作进一步探究,讨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互动情况,以推动理论的本土化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