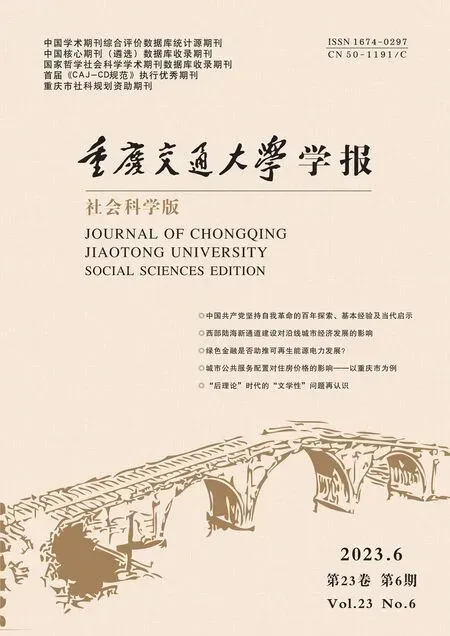物·空间·神话
——托卡尔丘克《衣柜》的叙事创新
覃 才, 苏仲乐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它的叙事主体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变迁中,虽然已经从热奈特所说的“口头叙事者”和“书写叙事者”[1],演变成凯瑟琳·海勒所说的具有后人类特征的“口头叙事者”“书写叙事者”及“电子人叙事者”的转变[2]。但当我们仔细甄别小说叙事主体的转变时,发现其在主体性划分上表现出的相对不变性,就是“长期以来,人们主要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划分叙述者类型(有些作品偶尔采用第二人称)”[3]。这就是说,在人类历史演进中,小说艺术的叙事主体虽然明显地产生着从“极端人格化”(主体依然是人)到“极端框架化”(主体为人工智能框架)的变化,但常用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不常用的第二人称依然是小说中约定俗成的叙事者代称[4]。小说艺术的这种“变”与“不变”,在叙事层面上引出的是小说一直存在的发展瓶颈和创新探求问题,因为小说叙事的每一次进步,都推动小说的整体发展[5]。对小说叙事发展瓶颈和创新探求的关联,詹姆斯·伍德在经典著作《小说机杼》中表示,“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小说虽然不乏心血来潮的自我更正,却始终难逃非议,人们总是指责小说僵化了:情节像一套现成的护具,而所谓的‘冲突’、发展、顿悟、场景、对话等等,无非陈词滥调,现实主义的透明,纯属自欺欺人”[6]序言7。在技术时代,由人物、事件、情节及时间等要素构成的小说叙事,它的吸引力和张力不仅远远落后于声音与图像的叙事(如音乐和电影),还越来越提不起读者的兴趣和欲望。在我们所处的技术与媒介时代中,小说叙事的瓶颈、僵化其实已经反向性地让小说叙事创新与发展,不可思议地成为一个牢固的共同体和需要重新思考的现实问题。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1962—)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授奖理由是她的小说叙事“运用观照现实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观察入微又纵情于神话,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独创性的散文作家之一”[7]。其实,托卡尔丘克小说表现出关于小说叙事的新方法与创新,是她一直探索的“第四人称讲述者”。在小说叙事层面,她所追求的“第四人称讲述者”可以说是“不仅搭建某种新语法结构,而且是有能力使作品涵盖每个角色的视角,并且超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到更多、看得更广,以至于能够忽略时间的存在”[8]。纵观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她所探寻的这种“第四人称讲述者”显然不会机械地停留于小说艺术约定俗成的第一人称“我”、第三人称“他/它”及第二人称“你”,而是在约定俗成或是已成为传统的“三大”人称之外的“第四人称”。托卡尔丘克认为,只有不同程度地跳出传统化的“三大”人称叙事,我们才能在阅读小说的新感觉中达到小说、现实及人生意义理解的时间同一。当然,从写作规律来看,每个作家的写作存在初期、成熟期及未来的晚期阶段性,托卡尔丘克的“第四人称”叙事显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根据她的实际情况,她的“第四人称”叙事大致上是在成为专职作家(1997年)后形成的。托卡尔丘克1997年出版的小说集《衣柜》(也有译《橱柜》)恰好呈现了她的这种实践。总体而言,托卡尔丘克小说集《衣柜》包括《衣柜》《房号》《神降》三篇小说,这三篇分别对应着物的叙事、空间叙事及赛博格程序的神话原型叙事,它们在内部编织上可以说是既独立又一体地构成她对“第四人称讲述者”的一个形象描摹。即在叙事层面上,物叙事、空间叙事及赛博格神话叙事,是托卡尔丘克探寻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之外的“第四人称”叙事的表现形式,也是当代小说叙事创新的重要探索之一。
一、物叙事
在从原始到现代的历史变迁中,人类创造了神话、悲剧、史诗、叙事诗及小说等文体。从类型特征看,人类早期创造的神话、悲剧及史诗,它的叙事主体主要是超自然的“神”(上帝);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叙事诗和小说虽然还有“神”的踪迹,但也慢慢让位于建构了相应理性和主体意识的“人”;在20世纪末到当下,技术和媒介的强势兴起已然展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物”主导性。不能否认,“物”是非常古老的。这种古老之物只要我们稍微想一想那些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的诸多自然之物就能够明白。同时,“物”又是非常新的。这种“新”是我们每个人肉眼可见的各种技术之物(产品)的制造、购买、使用及更新淘汰。当下我们不难发现,在新与旧的物及物的文化包围着、主导着人时,曾经至高的“神”和在几个世纪中自信满满的人,越来越陷于“物”编织的虚无与无意义的牢笼。即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科学的兴起把人类推向了专门学科的隧道。人越是在知识上进步、前行,就越不能清楚地看到整个世界或者是自己”[9]2。
物是实体性的,并且一直如此。相对神与人的时实又时虚,实的物就有它自身的稳定体系。我们能够发现,在物(符号)主导的时代,包围、主导着人的物越来越“具有代人行事的能力,也可以说是建构社会意义的能力”[10]4。在这种明显的“物”趋势、“物”时代及其形成的“物”文化积累之下,“物”叙事的形成可谓既自然又合理。大体而言,在“物”时代,小说中的“物”叙事实际上就是融情于物,让物等同于人,创造我们习以为常的“人”的叙事之外的“物”主体表达,达到以物观己身、以物观世界的独特叙事效果。在《物体系》一书中,让·鲍德里亚大致将人类认识的物形成的叙事能力概括为有用的功能性、拟人的情感性及有意义的文化性。在鲍德里亚看来,有用的功能性是物的自然属性,也是物的价值体现(物追求有用)[11]67。拟人的情感性是指“物体是以一种拟人的方式(anthropomorphique)存在。人和形成其环境的器物因此是在同样的一种肺腑与共的亲密感中发生关联(依照同样的比例关系),仿佛器官和人体”[11]29。意义的文化性则是表明技术之物的创造、品质定位及价值(即意义)需要“在一个文化意识形态中成立”[11]40。生活在物与物文化主导的世界中,我们能够理解与亲历物的功能性、情感性与文化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因需要某物或某物的功能时,去购买某物(即有用性)。在日常的孤独与虚无中,一些物能够像一个朋友或亲人一样给予陪伴与抚慰(即情感性)。我们居家所用之物、随身携带之物更象征着我们的品位和信仰(文化性)。
在技术时代,虽然无法估计的“物”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生活,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在另一层面上生成与我们所处世界的问题(异化、虚无、间隔等)。虚无与无意义可能只是时实又时虚的神或人的事,实体的物应该一直是它所是的样子,并且一直是有用和有意义的。即作为身处由物及物文化主导的时代中的人,在感到孤独、寂寞、恐惧、虚无及无意义之时,我们既能够在日常所购、所用、所带的物之中找到慰藉,又能够在“实”的物之中找到稳定的意义。这种情况发生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去理解物,最好是把物理解为平行或等同于人的存在。托卡尔丘克是理解与呈现如何以平行或等同于人的视角,重新发展和定义先于人类存在或由人类创造的物,并以此建构人与物之世界的完整性的作家。
作为一位批评家与读者,詹姆斯·伍德表示他“喜欢读那些由断章、警句、哲学论文组成的书,读那些游走在小说、自传和批评之间的作家——尼采、佩索阿……这类作家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很直接、很私人、很当代”[6]序言9。从对物的精深写实和瞬间虚幻来看,托卡尔丘克明显就是伍德所说的这么一位很直接、私人也很当代的作家。托卡尔丘克的这种特征是建立在她对物世界的勘探与强调、对现实世界存在问题的发现,以及对这些现实世界问题解决之道的探寻之上。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温柔的讲述者》中,托卡尔丘克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讲述危机:我们每个人都通过屏幕与应用程序感知真实世界,但每天收到的却是各种不真实性、不确定性[8]。这种导致我们精神世界与价值导向的不真实性、不确定性,不仅平添活着的人严重的虚无与无意义情绪,还催生我们关于真实世界存在缺陷与问题的思考。作为用小说讲述世界的人,托卡尔丘克在作品中解决人与世界问题的方式,就是用第四人称性的“物”来讲述人及人类所在的世界,这种独特的物叙事能够让她和读她作品的人更清晰地看清自己与世界。在小说《衣柜》中,托卡尔丘克不仅将物视为等同于人的一个他者,还展现物叙事有用的功能性、拟人的情感性及有意义的文化性特征。她这种对“物”的“第四人称”处理,起到以物的形式叙述自己对个体、时代及世界的另一种理解与思考的作用。
在技术时代,物的有用性、功能性被广告与媒介突显。因而我们决定购买某物,动因是这个物对个人或家庭有用。小说《衣柜》中,托卡尔丘克和她的R先生之所以前往距他们新家很远的二手商店购买衣柜,是因为他们刚搬进一个新家,都觉得这个新家需要一个衣柜。这种对衣柜(即物)的需要,突显的是物对人和家的有用性。衣柜一方面能够放置托卡尔丘克的裙子和R先生的西装等衣物,另一方面则与这个家中的其他家具、物品排列组成一个全新的关系整体。这些都是物是有用的功能性体现。托卡尔丘克和R先生刚搬进新家,马上去二手商店买衣柜,并花了比衣柜还贵的运费把它弄回家。在此,我们看到由“物”(衣柜)的有用性驱动的叙事及产生的人物行为之形式。
托卡尔丘克认为,有用的功能性只是物的一个自然、技术属性,这种属性虽然能够给人带来方便,满足人的需要,但似乎并不能解决人与世界的本质问题。她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在心理与精神维度上赋予物以拟人的情感性。她表示 :“我写小说,但并不是凭空想象。写作时,我必须感受自己内心的一切。我必须让书中所有的生物和物体、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一切事物,穿透我的内心。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都必须非常认真地仔细观察,并将其个性化、人格化。”[12]104在强调“第四人称”叙事的托卡尔丘克看来,她本人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与她平行或等同的他者。在小说叙事中,对这些他者,她都会“温柔”以待。这种温柔以待的具体做法是赋予她之外的他者拟人化、情感化的言说权利和特征。在总结自己小说中这种物叙事特征时,托卡尔丘克称之为将物(包括她本人之外的一切)“人格化、共情以及不断发现相似之处”[12]104的温柔艺术。如在托卡尔丘克背靠衣柜而立时,人格化、共情化的物让她发现:作为人,她忙碌、常感脆弱,并且短暂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作为物的衣柜,却可以永远完美地作为衣柜和物本身,具有超出脆弱、短暂的人的完美。在使用衣柜门内侧的小镜子时,托卡尔丘克也时常感到她本人、镜中的身影、衣柜及挂在柜中衣架上的衣物等是一个“物体系”,在这个相同的“物体系”时空中一切都没有差别,因为它们构成一个超越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的同一性存在。在此,我们看到“物”与人相齐是托卡尔丘克理解个人、时代及世界的一种“温柔”视角,也是她进行“物”叙事的温柔方式。
如果只是将我们身边之物和所处世界之物进行拟人化、情感化叙事,并在这种拟人化、情感化叙事之中发现人与物的相似之处,但没有进行更大意义的提升,显然不能解决人与世界的本质虚无问题。在技术时代,人与世界存在的空间与能量不能给我们安全之感或时常让人失望时,物及其衍生而出的物文化会生成一个具有弥补性的能量场域。很多情况下,这个能量场域能够弥补人与世界能量的缺失。托卡尔丘克的物叙事就是在物及形成的物文化空间中,为人类与世界建构稳定、可靠的能量(意义)场域。在《衣柜》中,托卡尔丘克不仅认为衣柜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域,还能给她和R先生一种稳定且有永恒性的意义。她表示她和R先生去家具市场亲自挑选的旧衣柜(把衣柜运回家的运费比衣柜还要贵)在家中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因为无论现实的世界怎样,她一钻到这个衣柜里面,就能忘却时间、季节、年份,就会感到深入生命本身的舒服与安全。在她的家中,这个有限的衣柜不仅是她自己的心安之所,她和R先生一同钻进去时,她们的心安之所就变成相对现实世界的可靠之地。在这个可靠之地中,他们真切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每个时代的所有小说都与自我之谜有关。一旦你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存在,一个角色,你就会自然而然地面临一个问题:什么是自我?如何把握自我?这是小说作为小说所奠基的基本问题之一”[9]23。在托卡尔丘克看来,人类世界除了人自己,还有无数个平行或等同于“人”和“我”的物。在个体越来越失去重量与重要性的技术时代,物恰恰是个体之外的“人”与“我”的重要性弥补与意义映射。托卡尔丘克以一种特殊的“温柔”进行物叙事,这种“温柔”就是在她自己及人之外,发现人格化、拟人化和情感化的物。这种物是真实的物,同时也是与人相似、相等的物。它们有用、温柔且有意义,这种有用、温柔及有意义正是现实的人与世界所缺失的。因而,对它们的强调与突显,就成为一种不错的小说叙事创新与建构人和世界意义的方式。
二、空间叙事
物只要一经创造或生产,就成为空间中的物。如果人也算一个物的话(托卡尔丘克就将人当作有味道、颜色及色彩的物),人类的世界不仅是由各种各样的物构成,它本身还是一个囊括各种各样的物,并且是有相应限定范围的空间。作为生活在或大或小空间中的人,如果不明白空间对我们的影响与制约,就不能正视人本身的问题与寻找自我的意义,更不能明白人与世界的共同体关联。对人类迈入的这个既是现实又是想象的空间化世界,亨利·列斐伏尔曾经指出的“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13]问题,既将人与社会生产的价值、意义引向“空间”的生产,同时又强调我们所处的“人类世”已然具有了空间叙事的意义属性。《房号》是托卡尔丘克小说集《衣柜》的第二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托卡尔丘克以首都饭店客房服务员打扫房间的空间叙事形式,表达了空间对人和人的世界(包括国家、文化、信仰、价值观等)的意义建构方式。简要言之,在托卡尔丘克看来,容纳人和物的空间(即小说中的房间),既是人与物的容器,它将人和物限定在一个空间场域内,也让人与物在这个空间场域内展现其构成和代表的意义。她所探索的空间叙事作为具体人称(我、你、他)之外“第四人称”叙事类型之一,就是以全能的空间对人和物展开关联想象与意义生成。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传达意义、运作权力关系、建构自我人格”[10]6的物,还是有自主性的人,都被空间化了。就此而言,在空间叙事层面上,《房号》中的每个酒店房号既代表居住的空间(即房间),也指现代人与世界的空间性意义。
在《房号》中,200号房间是第一个出场的房间。对这个空房间,客房服务员从皱巴巴的床单、凌乱的被子及乱扔的垃圾的空间状态中嗅出客人昨晚的辗转反侧与早上赶时间的苦涩味道,却不能立刻判断客人是男或女。在服务员流程化地开展更换床单、被子,清扫地毯、卫生间,处理烟灰缸、垃圾桶里的垃圾等环节后,这位已经离开的客人是男是女逐渐明了。如果是男的,她只需要整理床,擦掉镜子里残留的倒影,抹去房间里心不在焉留下的气味,再扔掉垃圾桶里的垃圾就行。如果是女的,她打扫起来就更麻烦。因为对相对于男人,女人会下意识地把房间当成自己的家。为此,她除了常规清理外,还需要处理女房客可能留在房间中的某种“思念”——洒在地毯上的爽身粉、玻璃杯和烟嘴上不经意间的印子,以及卫生间(浴缸)里的欲望和狼藉,等等。这些都是女房客给房间(即空间)制造和遗留的专有麻烦。此外,从她的经验判断,女客人从不留小费,留小费的一般是男客人。显然,在对男女房客性别的判断中,托卡尔丘克呈现了200号房间这一空间的能指与所指意义。
224号房间是住了一段时间的日本夫妇。这对夫妇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去参观博物馆、景区或看演出,客房服务员来打扫房间时一次也没有见过他们,但她一进门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甚至如临圣坛的感觉。小说中,这对生活规律的日本夫妇除了让客房服务员感到惊讶和钦佩,还让她产生很强的不适感。这种特殊的惊讶、钦佩及不适,是这对日本夫妇每天早出晚归,但她每天上午来打扫房间时面对的情况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洗漱台,一个水滴印子也没有的镜子,地毯上没有他们掉落的黑发和碎屑,没有任何指纹的电视旋钮,以及像是没有睡过一样的被子和枕头等。在这个房间内,客房服务员不仅感觉不到除了自己之外的人的味道(即只有酒店本身的味道),还时常产生打扫过这个房间又来打扫的错觉。通过对224号房间“整洁”、没有味道的空间叙事,作家一方面在无形之间表达她对不在场的日本夫妇的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含蓄地讲述日本人自律的身份特征与国家公民形象。
226号房间住着一位阿拉伯男人,客房服务员是从房间中摆放的阿拉伯语护肤品、行李箱、书籍上看出的。同时基于房间中还没有使用痕迹的卫生间和厕纸,猜测这位客人是半夜从机场打车到饭店的。227号房间也住着一位男人,与刚入住226号房间的阿拉伯男人不同。227号房间的男人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并且在这里的每天都过得不快乐。因为每次只要一进他的房间,积了很多烟灰和烟头的烟灰缸、洒在桌面或地毯上的果汁、装满各种空酒瓶的垃圾桶,以及还剩一两口酒的玻璃杯等,都让房间散发着这个男人昨晚幽闭而悲伤的味道。还有镜子前摆放的除皱霜、粉底、顶级芳香水、腮红、眼线笔等化妆品,表明他是一个注重身份与场合的人,也表明他害怕老去或处于非常糟糕的精神状态中(用化妆来掩饰糟糕)。在227号房间,客房服务员每次打扫和整理凌乱的房间,就像护士一样安抚这个客人的混乱。
223号房间住的是几个年轻的美国人,也是客房服务员最不愿打扫的房间。因为她的每次打扫都在嗡嗡作响的CNNI频道播报中见证如出一辙的混乱,并且还需要在这种“嗡嗡作响”和混乱中把地毯上的烟头、截成两段的铅笔、被踩扁的牙膏、新衣服商标及床上剥了一半的橘子等扔进垃圾桶,把歪倒在衣柜里的枕头和乱放在沙发上的东西复位,把那些只写了地址但还没有写祝福语的明信片整理好,把挂在空调出风口的内裤和袜子放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等等。总的来说,在打扫这几个年轻美国人的房间时,作家的空间叙事与表达不仅以客房服务员身份认知的形式说明当代美国的强大、自信,也担忧美国年轻一代的放纵、自大及未来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因而,每次客房服务员打扫完这几个年轻美国人的房间,都不由产生在门口抽根烟和平复内心的冲动。
在酒店中,客房服务员对自己负责打扫的房间可以说具有无限的权力(彻底的空间复位、清除上一房客的味道等),但偶尔也有权力失控的时候。这个失控时间是小说中所写的:门把手明明挂着“请即打扫”的牌子,但客人却在房间中。229号房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房间。其实从平时对房间的暂时性拥有角度来看,客人与客房服务员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如果二者同时出现在房间中,就会出现一种相互干扰的犹豫与尴尬状态。如果两人都在房间里,两人对房间(空间)占有的冲突可能会让房客和服务员有相应的紧张或不适。在这次打扫工作中,客房服务员即是如此。她不仅先入为主,感觉到坐在电脑旁的男房客正在刻意或不自觉地观察自己,还觉得现在自己穿的保洁制服、黑色平底鞋、围裙及腰上挂着一大把钥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在房间中,工作中有些出汗、疲惫且衣着不洁净的客房服务员,更是不由地产生一些自卑和不自在。这种客人和客房服务员的空间冲突与尴尬叙事,显然是作家对229号房间的空间意义塑造,即在两人都暂时拥有支配权的空间中,虽然两人是平等的,但这种尴尬的空间冲突破坏了他们既有的生命状态与信心,构成他们对生命的短暂怀疑。
228号房间住着一对瑞典老夫妇,也是客房服务员要打扫的最后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基本什么也不用打扫的房间,但与224号房间每天外出看景点和演出的日本夫妇不同,这个干净和整洁的房间弥漫着生命的“晚期”意味。客房服务员看到这个房间中的一切东西,像这对瑞典老夫妇一样都在它们该在的原位上,即洗漱台上的手巾、牙刷、牙杯、漱口水、芳香水等都整齐地在它们的位置上,没有混乱与慌张。在他们的房间中,没有感受到空气里遗留的关于人的噩梦、激情的味道。从房间空间的整齐、干净度来看,这对瑞典老夫妇与224号房间的日本夫妇相差无几。但与自律、奔走在不同地点、体验世界之大与神奇的日本夫妇不同,这对瑞典老夫妇只想他们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给他人与世界造成麻烦,他们静与慢的人生状态直接表现为房间缺少生命的气息。这对瑞典老夫妇房间中摆放的已经写完的瑞典语日记本尾页,《圣经》一书摊开到《传道书》部分(主要段落写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已有的事,后必再有”等内容)也说明这点。为了给这弥漫着人生晚年气息的房间补充一点人的生气与活力,客房服务员刻意把她一身的疲劳、汗水和生命的味道留给228号房间和老夫妇两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白了托卡尔丘克所讲到的每一个房号及其对应的房间,其实都是由人与物构成的整体性空间。小说《房号》清楚地呈现了作家对空间和空间叙事的把握与形态描摹。按照作家的理解,空间叙事具体涉及的空间可能只有十几或几十平方米的房间,但这个空间却超越人和物,具有国家或世界的意义指向。托卡尔丘克呈现不同国家的人住在这些房间里,就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中,他们对待物品和空间的方式展现着他们的身份与所接受的文化观念。在《房号》中,作家以房间中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的客人来喻指人的一生(青年、中年及老年)如何度过才有意义,并回应着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
三、赛博格神话叙事
物与空间很多时候是一体的,甚至具有一种超出人类范畴的全能性。这种全能性就像一个他者,构成另一个“我”或人类全体。当我们从“我”“你”“他”的叙事角度来看,物与空间构成的他者明显超出“我”“你”“他”的叙事维度。从托卡尔丘克强调的“第四人称讲述者”的内涵来看,物与空间的叙事导引出的他者应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在他的全能性话语讲述中创造人、物、空间及世界,并赋予他所创造的一切以不变的意义。全能的上帝在《圣经》中出现,他的创世之举是世界的原型,也是一种神话。托卡尔丘克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技术虽然给我们的生活与世界带来难以置信的改变,但由于“我们的身体与五千年前的人类别无二致,我们的思考也同我们的祖先一样”[14],我们在技术时代的命运和世界依然与过去相连,即有过去的原型。因而,基于神话的过去与技术的当下,托卡尔丘克以赛博格程序的神话叙事形式,建构她对传统的具体人称(我、你、他)叙事之外的“第四人称”叙事。总体而言,托卡尔丘克的赛博格神话叙事主要以《圣经》为原型参照,即让《圣经》中上帝创造人类,用洪水毁灭人类,又再次让人类新生的原型在赛博格程序上重复发生,并检验效果。我们理解的人、物、空间及世界的价值,就在这个赛博格程序上被神化般地“迭代”和重新赋予意义。她的这种赛博格神话叙事既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论小说与小说家》所说的文学创作整个进展过程具有的“循环往复的趋势”[15],又是一次另辟蹊径的创新。
小说集《衣柜》的第三篇小说《神降》中,托卡尔丘克以电脑程序可以无限模拟、无限宕机重启的赛博格世界为场所,演绎技术时代的人与世界和过去的历史相似性、反复性,并寻找她认为的技术时代中人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身处和看到正在衰老、崩溃及毁灭的人类现在世界(城市),计算机天才D在他能够编程与改变的赛博格程序中创造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赛博格世界里,D就是上帝。但在现实世界中,D是个只靠社会补助度日的计算机编程人员,他待在房间里,并且长期坐在电脑前。房子的窗户和电脑的屏幕是D对人类现实世界与网络赛博格世界的对位性理解。计算机工作者在电脑前久坐会眼睛干涩、难受,这时候他们会站起来看看窗外。D也是如此,眼睛难受了就站在窗口处看看城市。但窗外城市表现出来的衰老、破旧、虚幻,并没有给他放松眼睛与平静内心的感觉,如窗外城市中汽车尾气和尘土混杂的阴霾天空,街道上同样疲惫的涌动人群,对面老砖房楼下停靠的褪色汽车及楼中窗户后偶尔移动的人影,都表现出城市与D同处的间断、模糊及没有逻辑性的现实。城市虚无、被掏空的瞬间和本质性感觉,让D产生人类和城市已死的原型,即在D看来,房子窗口呈现正在衰老、崩溃及毁灭的城市既是现实,也是最好的赛博格世界的设计原型。
基于现实世界原型的逆向思考,D在他所用的名为“创世纪”电脑程序中设计了一个充满和谐秩序、发展方向明确及有巨大未来延续可能的赛博格世界。人类的现实就是现实本身,没有模拟和“宕机”重启的机会。但在赛博格世界中,由D建构和模拟的人类现实,可以有改进和重新来过的机会。为了探索一个和谐、明确、连续的人类世界,D在他的程序中先是建立小部落、小城池,再建立大城市和国家,并在沿海地区建造船厂、港口,与其他地区和国家交流……他让人类沿着从原始到现代、从小到大的轨迹发展。作为赛博格世界的上帝,D所创造的城市看上去是朝着理想的状态发展,但是计算机程序本身的可控性与自主性催生的赛博格世界,其实与现实世界有同样的定律,即两个世界中的种族或国家之间存在相互侵略、战争(资源优化)。在计算机可控性与自主性之间,赛博格人类与人类现实世界同样有秩序与不秩序、和谐与不和谐的相同点。在失望又疲惫之时,D像《创世纪》中上帝用洪水毁灭他所创造的世界那样,“向自己的城市投入了风暴、大火、洪水、鼠潮和蝗灾”[12]58,放弃了这个程序。
像《创世纪》中上帝毁灭自己创造的城市之后,D又得到一个叫“半边生活”的新程序,他想以此重新创造一个年轻而有希望的世界。为此,他对“半边生活”建模。第一天,他先是在“半边生活”创造出“元”海洋,用漂浮的氨基酸合成单细胞的蛋白生物,然后是陆地上最早的两栖动物。第二天晚上,D又创造了“有四肢、鸟一样的脸和没有瞳孔的眼睛”的人类。但对为寻找食物发愁、时常感觉恐惧及有混乱人生的人类,他非常不满意,所以D释放洪水和火雨,毁灭了他们,并重新创造一些人。此后,D不再以任何方式干涉“半边生活”中的人与世界,只是按部就班,让程序运行,就像上帝在洪水过后也让人类与世界自行发展一样。然而,只是一根烟的时间,“半边生活”中的人类就发生好几次为了金钱、女人、权力的大战。战争的结果是人类流离失所,世界毁灭,“半边生活”游戏结束。电脑程序询问D“是否重新游戏?是/否?”之时,D选的是“否”。
很显然,世界与人一样充满着原型的重复性(过去与现在的对应),《神降》以能够无限重复的赛博格空间的“朋克式审美、全息地图技术等等古人无法想象的现代元素”[16],让过去的世界与人在现代才有的电脑程序中重复、对位着,以突显两者的同与不同、好与坏。D选择结束“半边生活”游戏,不是放弃在这个程序中创造理想世界的想法,而是对这个程序重新编程。经过一周的努力,D创造了一个能够“包含一切维度的无穷无尽的数值”的“无”,并将“半边生活”程序升级为“半边宇宙”。这个“无”一开始是一个不分光明与黑暗的混沌,在之后的大爆炸中产生四大力量,再之后是时间、空间及物质的形成。看到完美的“无”的产生、爆炸、分离过程,D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永远是好的,或许最好的人与世界的状态,可能就是他当下所处的现实与城市的正常衍化状态。因此,他对“半边宇宙”程序什么也不做,任由它运行,想看它最终会形成怎样的世界。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作为这个世界的模型,奠基于人类事物的相对性与模糊暧昧。”[9]14《神降》中的D或者说作家所处的现实世界、赛博格世界及神的世界,无疑呈现世界模型的相对性与模糊暧昧。在这一意义上,《神降》是与《创世纪》互文性的小说,托卡尔丘克正是试图在电脑程序的赛博格世界中演绎上帝创造人与世界,又毁灭人与世界,再更新洪水之后的人与世界的神话原型,进而思考当今所处的现实世界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神降》中,计算机天才D即是作家与上帝,他在电脑程序中创造多个世界,也看到多个世界中人与世界的诞生、繁衍及毁灭。“半边宇宙”是没有运行完的程序,这个喻指现在活着的人类和带着问题运行的世界,它们都在等一个结果。
四、结语
小说是人创造的艺术,主流的叙事形式表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构成的“人的叙事”。在世界文学中,“人的叙事”的每一次改进都是小说艺术的重要发展。当下,“人的叙事”得到极大强化,与之相对的是它的突破空间也越来越小。为此,托卡尔丘克主要探索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之外的“第四人称”叙事,以对“人的叙事”进行突围。小说集《衣柜》是托卡尔丘克探索“第四人称”叙事的样式“深描”。在《衣柜》篇中,托卡尔丘克大胆勘探平行于人或等同于人的物的功能性、情感性及文化性叙事,在第一、第二及第三人称的叙事略疲软之时,她建构的“物”的叙事一方面显露现代人与世界本质的虚无与无意义,同时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物及其物文化的温暖深入时代与人心。《房号》所写的首都饭店二层七个房间及其所住客人,突显的是一种空间叙事与意义生产。作家通过打扫房间的客房服务员、房客和房间之物的空间关系,讲述空间对现代人和物的另一种说明。可以说是七个房间所住的或自律,或放纵,抑或是从容的人,他们共同构成现代人不同年龄段生命状态的象征,即这七个房间中人与物构成的空间意义,让我们深刻思考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才有意义与价值。《神降》基于《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人与世界,再用洪水毁灭人与世界,进而更新人与世界的原型,通过赛博格空间来演示人与世界有可能像游戏一样,可以不断被创造、毁灭,又可以重新来过(游戏结束重新开始)。但在这种重复中,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人与世界才是好的。整体而言,托卡尔丘克的小说集《衣柜》是以物、空间及神话为形式,建构她所认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鲜活、完整、实体的“第四种讲述者”,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在另一层面上肯定她这种叙事创新具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