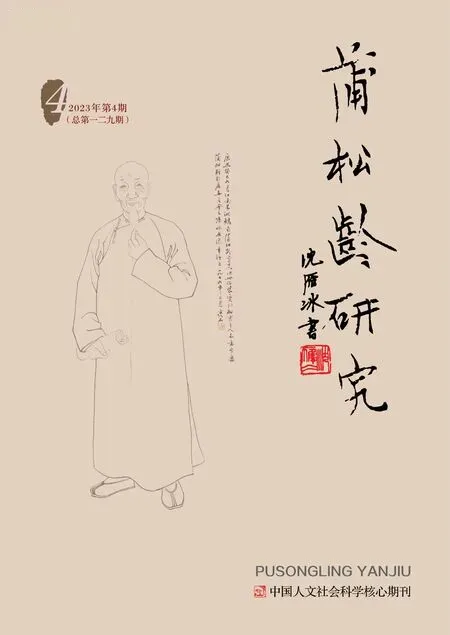康熙十二年蒲松龄与唐梦赉同游泰山说质疑
张洪玉
(淄川博物馆,山东 淄博 255100)
袁世硕先生所著《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一书对蒲松龄的生平事迹与著作情况做了较为具体细致的考察,为聊斋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蒲松龄与唐梦赉》一文有这样一个观点:“有可能这年(按,指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龄亦曾与唐梦赉同游泰山。只是尚无佐证,不敢遽然论定。”[1]131后袁世硕、徐仲伟二先生合著的《蒲松龄评传》,于第五章《文章憎命·缙绅门下》记此事与以上观点又有不同,认为唐梦赉确曾邀蒲松龄同游泰山(说见下)。后来的研究者论及唐、蒲交往,必言二人于康熙十二年(1673)同登泰山、观日出一事,俨然已成定论。笔者的看法与袁世硕、徐仲伟先生不同,认为唐梦赉登泰山在康熙十二年(1673)的冬天,蒲松龄登泰山则在某年的七月,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龄与唐梦赉同游泰山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今据相关史料爰作考证,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康熙十二年唐梦赉的登岱之行(上)
康熙十二年(1673)冬,唐梦赉因踵与释元玉的旧约而有泰山之行。其《志壑堂诗集》卷一《登岱集》有自记云:
余己亥以前旧咏,如《环山亭稿》《庐岳游记》及长安诸什,一夜起,挑灯于酒炉边尽焚之。庚戌奉讳以后,益复无作,故牢桑之役,未有只字……自癸丑《登岱集》以后七八年,复存稿。”[2]30
据此自记可知,唐梦赉登岱之事发生在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是集有《登岱同祖珍禅师》《黄华洞题壁》《宿普照兰若赠死菴》《泰山歌》《看日出歌》《凤翔冈放歌》《普照寺和珍公韵》七题十首,皆作于其游泰山期间。由这一组诗作,可以知道唐梦赉游泰山不仅见到了释元玉(字祖珍)其人,而且曾题壁黄华洞,居停普照寺,放歌凤翔冈,并与释元玉多有诗歌唱和。该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落木萧森出虎溪,诸方喔喔听荒鸡。”(《登岱同祖珍禅师》)“石桥霜径与林通,古屋寒烟礼大雄。”(《普照寺和珍公韵》)从诗作所反映的时序来看,其登临泰山,正当树叶落尽、板桥结霜、屋宇烟寒的严冬时节。
台湾明复法师编《禅门逸书》续编第八册,为释元玉的《石堂全集》。其卷八为五言律诗,中有《癸丑冬同豹喦太史踵泰山旧约,宿翔凤冈》三首,其一云:
昔有天门约,俄经十五年。寒崖兹与踏,晚景倍同怜。
绝顶裾堪曳,高山调莫传。人间忧乐事,俱付白云边。[3]378
唐梦赉《登岱同祖珍禅师》亦有“三生支许约同登,瓢笠虽闲尚让僧”句,《宿普照兰若赠死菴》有“新知看竹迷萧寺,旧约听泉过薜萝”之说。从释元玉与唐梦赉诗可知,唐梦赉此次登岱,是为践与释元玉十五年前的旧约无疑。
释元玉(1628—1695),唐梦赉僧友,字祖珍,号古翁、古菊、死菴,别号石堂老人,江苏南通人,俗姓马氏,辞婚出家。天童嫡派临济宗大师释道忞(字木陈,又作木澄,号山翁,晚号隐道人,清世祖赐号弘觉禅师)再传弟子,为金粟释本昇(字天岸)和尚法嗣。
唐梦赉与释元玉记释本昇友善,两人之间有诗歌往来。此时释本昇住持山东青州法庆寺,释元玉乃本昇座前侍者。释本昇有《天岸昇禅师语录》(释元玉记录)二十卷,见于屈映光、蔡运辰编《中华大藏经》第二辑第一百○四册。卷十九《偈》有《复唐梦赉太史》七言绝句五首,题下注:“次韵。”其一云:
飘飘仙客骨如梅,鹤立风前玉一堆。
欲问生前真面目,须将心眼著寒灰。[4]43335-43336
释元玉师祖道忞和尚曾于顺治十六年(1659)入京,顺治帝召于内庭万善殿说法,赐封弘觉禅师。其时释本昇随往,元玉留青州,摄法庆院事。唐梦赉此时于青州法庆院初识释元玉。道忞南还,本昇返归法庆寺,释元玉始受记莂于本昇,乃辞青州法庆院事。此后次第开堂于邹平白云寺、泰安普照寺、沂水资庆寺等禅院,立戒坛于长山於陵(今属马尚镇)之大悲庵、淄川之慈寿寺。
释元玉与唐梦赉十五年前的“天门之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逆推,应在顺治十八年(1661),也就是唐梦赉与释元玉相识的第二年。唐梦赉撰《泰山普照禅寺祖珍和尚塔铭》曾记此事,见于释元玉《石堂全集》卷首,其文曰:
世祖皇帝召天童弘觉老人于万善殿说法,以其主青州高足天岸禅师从,留祖珍公于青摄法庆院事。余是时盖初识祖公于弘觉翁南还。天岸师反法庆,公始受记莂于天岸师。乃辞院事物,将衣钵西往,禁足清源。久之,来往长白山之白云禅寺数载,受请住泰山之普照兰若,遂结茅终归老之计。[3]31
《石堂全集》卷首有张肇昌《序》,记载了他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冬与唐梦赉、释元玉论道事。张肇昌,字樵岚,山西泽州人,例贡,时任泰安州同,代理知州,为泰山八散人之一。因得地利之便,张肇昌与释元玉游处最久,并为《石堂集》作序。其《序》中有云:
泰山之阳有普照寺,荒废且久。有五琅释氏祖珍禅师飞锡来,止之。荒者修,废者举,居然为泰山一名刹……余于庚戌夏来倅奉符,欲得可与论文之儒与之友……无何饮公方外香茗,遂过访焉……辛亥春,余假摄郡篆……至癸丑冬,同豹岩唐太史复亲道履,谈多世务,公(按,指释元玉)辄津津不辍……[3]3-4
张肇昌虽是例贡出身,又是地方官员,但雅好文会。他与文僧释元玉过从甚密,二人时常“对坐山堂,茶瓜竟日”。唐梦赉是饱学之士,精通儒学与二氏之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往来不离纱帽侧”,满腹治国理政之策,人称其有救时宰相之才。唐梦赉的到来,无疑让张肇昌非常欢喜。唐梦赉得遇张肇昌也是相见恨晚,云:“日者策杖泰岱,窃得窥其容止:翛翛玉立,士元诚非百里材也。”[2]198后来张肇昌著《囊馀录》,唐梦赉为其作序,赞其“镆邪利器,行且将脱颖而出”[2]198。
二、康熙十二年唐梦赉的登岱之行(下)
康熙十二年(1673)夏,清廷诏修各省通志。山东巡抚于是檄令各州县修志呈送,以备省志采录。是年夏,淄川知县请唐梦赉、毕际有、袁藩共修邑志。毕际有、袁藩负责采集基础材料,唐梦赉任总纂。乾隆八年《淄川县志》卷七《艺文志·文》载毕际有《县志旧序》云:
迨康熙癸丑之夏,邑奉上檄,索志甚急……而吾邑自癸卯以来,志未修者阅七十载。时高念东先生方谢病家居。先生海内通儒,屈国史笔润色邑乘,直发蒙振落耳。乃习静避嚣,不自为之,与唐太史济武交折简于余相劝勉。邑使者元纁再及门,余不能终辞,乃请以太史董其成,而余与袁孝廉松篱执其役。遂同集于念东先生之候仙园,商榷讨论者十日,受成命而返。已乃孝廉来就余家,相与键户石隐园中,同几共砚,字订句考,讹者正之,阙者补之,凡例条目,悉为更定……其有文献阙征,疑难须质,则询之太史,赫蹄往来无虚日。孝廉有句云:“菊蕊从知今又破,藕花曾及见初开。”则历时可知已……书成送邑,邑录送省。[5]24下-25下
从毕际有《序》可知,康熙十二年(1673)奉檄修志,上官索之甚急。唐梦赉、毕际有、袁藩先在高珩候仙园商讨十余日,毕际有、袁藩随即西移到西铺村毕氏石隐园中整理基础材料,唐梦赉则在候仙园中主持纂修事宜。
袁藩《敦好堂诗集》卷三详细记录了修志全过程,其诗有《候仙园》《留别念东先生次原韵》《立秋夜》①按,该题接排此处不妥。是年七月二十五日立秋。《敦好堂诗集》由袁藩自己编订,其去世后,长子尊父遗命,将诗稿交与毕际有,请其帮助印制。彼时毕家财力不济,已无力为其刻印,只好抄录两份,一份自留,一份付与袁家。说见《敦好堂诗集》卷首毕际有序。该年立秋较晚,可能是毕际有觅人抄写时,按常理将《立秋夜》一诗移置于前。《石隐园雨中》《石隐园夜坐》《七夕归途》《秋日感怀次毕载积先生韵四首》《陆砚歌为载积先生赋》《西归雨甚》《七月望日》《挽王西樵吏部》《答唐济武太史用来韵》《述怀时客石隐园修邑志》《修邑志成,别载积先生东还》《将赴之莱,行青州道中有感》《夜行胶东道中》《平度州宿家信我兄学署》《将入都门,过毕载积先生。雪中夜饮绰然堂,兼订邑志》《龙山道中》诸作。
袁藩《述怀》一诗题下注“时客石隐园修邑志”,诗云:
摊书常是一床满,为客忽惊九月来。菊蕊从知今又破,藕花曾及见初开。秋林叶落灯前雨,旅梦虫吟石上苔。已近重阳归未得,雁声愁绝向人催。[6]30-364
袁藩这首诗,说他们一心埋头修邑志,紧张得无暇他顾,连物候都忘了。还未及赏荷,转眼已是菊花破蕊的暮秋时节了。此诗之后,即《修邑志成,别载积先生东还》《九日诸公偕妓登山,赋此寄讯》二题。这说明重阳之前,邑志初稿已成,众人可以稍稍放松一下了。唐梦赉《志壑堂诗集》卷二《锦秋白岳集》也有《邑志成有感》七言律诗二首,其一云:
从来四十已称翁,短鬓萧骚绿镜中。旧友凄凉犹我在,古人检点与谁同。惊心白骨宜高卧,过眼黄花耐晚丛。碧海石龛留旧室,微名何必祀黉宫。[2]34
此后袁藩有莱州之行,月馀而返归淄川。之后,其《敦好堂诗集》卷三有《将入都门,过毕载积先生。雪中夜饮绰然堂,兼订邑志》一诗。据此可知,袁藩自莱州归来后曾与毕际有修订邑志,此时虽是初冬时节,已经降雪。此次修订邑志,可能是唐梦赉完成编纂之后,交由袁、毕二人作最后的文字校订。此后,袁藩便游幕京师去讨生活了。邑志校完交稿,再加上行前制装,唐梦赉的登岱之行,最早也将到仲冬了。
笔者发现,蒲松龄游泰山在某年的盛暑七月(说见下)。而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二十二日,新城王士禄卒,唐梦赉闻讯后曾前往吊唁。《志壑堂诗集》卷二《锦湖白岳集》,有《将吊王西樵,即泛舟湖上。小憩阳春馆中,闻刘峄巄家梨园吹笛》七言律诗二首,中有“渔舟歌发蓼花时,策策西风掠鬓丝。跨鹤不闻高士驾,炙鸡动与故人辞”句。王士禛《蚕尾续文》卷十三《墓志》,有《敕授征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喦唐公墓志铭》,中有“甚至先兄考功之丧,先生哭寝门极哀”。[7]833此可证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下旬唐梦赉尚在淄川,且曾去新城吊唁王士禄。
唐梦赉出游,不同于今人旅游,因为交通便捷,可以来去匆匆;古人出游要放下缠身的俗务,似闲云野鹤般随兴而为,而且往来都需要较长的时日。唐梦赉游览淄川邻县的长白山尚要七日,游崂山要月馀,游吴越要五个月,游泰山,践十五年老友之约,或需月馀。又,淄川邑志修纂至此已历七十馀年,其事头绪纷繁,况且“邑奉上檄,索志甚急”,这年的七月众人一心扑在修志上,连当月开放的荷花都无暇去欣赏,更不用说去游览泰山了。
袁藩的诗作按时间先后排序(《立秋夜》除外),从候仙园商讨修邑志始,到邑志修讫赴京师途中,中间也没有记载一同修志的唐梦赉出游登岱的文字。
种种迹象表明,唐梦赉登岱时在仲冬。而袁藩自胶州归来不久就已降雪,此时从淄川去泰安,经青石关、莱芜一线因雪后封山已不能通行,只能走经过济南的官道。此条线路三百七十馀里,往返就要十一、二日(说见后文)。而泰安州州同张肇昌公务缠身,能与唐梦赉在泰安期间相处甚得,也绝非三两日就能处得如此熟络。假设唐梦赉在泰山驻足五六日,那么整个登岱之行前后要近二十日,若是初一启行则可,若启行不是初一,可能连出吊王士禄之事都会错过了。这年的七月,唐梦赉能放下淄川七十年一遇的修志公务去登岱访友吗?唐梦赉七月出游,于情于理皆不合。
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来说明。这是一篇小说,常规的教法是从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讲起,笔者选择的是将小说的标题切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小说标题可以切片成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三个元素,既交代了主要人物形象及其特征(形象),高度概括了林冲风雪之日在山神庙手刃仇人的主要事件(情节),又渲染了环境气氛,奠定了文章的感情基调。从标题切片分析,切口小,可供挖掘的意义却深。
而到康熙十二年(1673)的冬天,毕际有、袁藩校订邑志完毕,身为总纂的唐梦赉要再作最后审定,然后“书成送邑,邑录送省”,他才能卸下修志的重担,有闲暇之心制装出行。唐梦赉诗、释元玉诗、张肇昌《序》与毕际有《序》、袁藩诗、吊王士禄事相与印证,皆可证明唐梦赉登岱一事发生在康熙十二年(1673)的冬天,而不是这年七月。
目前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康熙十二年(1673)冬天,唐梦赉为践与释元玉十五年旧约而访友泰山。期间他曾登临泰山,宿于岱顶所设官署中。次日四更即起,至日观峰,见“天宇穹窿,白云满地,已而鸡声唱彻。东望白云中,火焰堆起三峰,初如红榴乍吐,渐高云气始赤。叠锦拖绮,变现万状;朱盘轮囷,去天渐近;白云渐消,山峦村落渐出而世界现矣。”[2]360唐梦赉又作《看日出歌》记述他所见到的骇人心目的日出景象,载《志壑堂诗集》卷一《登岱集》,诗云:
日观峰头看日出,闻鸡蹴起不暇沐。凌空一杖坐单椒,但见阊阖深锁云填谷。此时羲和睡正酣,龙宫高挂扶桑毂。少时海东散微霞,山脚明河类拖玉。赤城烂熳色渐骄,粘天横练千层绿。同游大叫真奇绝,朱镜谁家忽出匵。一时倏变珊瑚钩,喷焰三角红髻蹙。此时只在平地白云中,却隔海天尺五六。须臾全现丹砂盘,虞渊一跃涌天腹。[2]31
唐梦赉和蒲松龄,在游泰山的过程中都看到了日出。那么他们看到的是同一次日出吗?或者说,他们是一起登临泰山看到的同一次日出吗?
三、蒲松龄没有与唐梦赉一同登临泰山
蒲松龄确曾登过泰山,这有《聊斋诗集》中的《登岱行》和《聊斋文集》里的《秦松赋》为证。
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龄集》,在《聊斋诗集》卷一有“姑附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之下的部分诗作。路先生在卷一癸丑《又寄孙树百,兼贻鲁坛》诗题之下加按语云:
按:以下各诗为张序五卷本第一卷所编订之目次,然未注年代,兹考之亦未得其究竟,因亦不能移于他处,姑附于此。[8]495
邹宗良先生在《二卷本〈聊斋诗集〉探考》一文中考察云:“路编《聊斋诗集》卷一‘姑附于’康熙十二年癸丑的诗作,1962 年8 月第1 版的《蒲松龄集》包括《又寄孙树百,兼贻鲁坛》在内共收入四十一题六十一首,路大荒先生误称‘五十八首’;至1963 年10 月《蒲松龄集》第2 次印刷时,路先生复据《聊斋偶存草》补入十二首,共得七十三首。”[9]260
蒲松龄的《登岱行》七古一首就包括在这七十三首“姑附于此”的诗作之中。既然路先生说其底本张序五卷本“未注年代,兹考之亦未得其究竟”,那就说明这七十馀首诗作的写作年代并未确定,研究者是不能把这些诗作认定为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诗作的。
袁世硕先生在《蒲松龄与唐梦赉》一文中,关于蒲松龄是否与唐梦赉同登泰山一事有如下表述:
显然,蒲松龄是登过泰山,登泰山也必凌绝顶观日出。《登岱行》便写到观日出:
瑶席借寄高岩宿,鸡鸣海东红一簇。俄延五更黍半炊,洸漾明霞射秋谷。吴门白马望依稀,沧溟一掬推琉璃。七月晨寒胜秋暮,晓月露冷天风吹。顷刻朝暾上山觜,山头翠碧连山尾。
与唐梦赉《杂记》之记述颇相似。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里,《登岱行》正系于康熙十二年。那么,有可能这年蒲松龄亦曾与唐梦赉同游泰山。只是尚无佐证,不敢遽然论定。[1]130-131
袁先生认为蒲诗《登岱行》有明确的作期,即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因而与唐梦赉登岱的时间正好是同一年,这为他们相约一同去登泰山提供了可能性。但上文的考察说明,《登岱行》恰好正是因为不能确定具体的写作年代,才被路大荒先生“姑附于”康熙十二年(1673)之下的那七十三首诗作中的一首。因此,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登岱行》一诗作于“某年”,而不能确认它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也就是说,唐梦赉在康熙十二年(1673)仲冬为践与释元玉之约而去泰山一事是可以确认的,但说蒲松龄在同一年也去了泰山,并且写下了《登岱行》一诗,这究竟是不是事实却是难以确认的。
再者我们在上文的考察中确认,唐梦赉去泰山的时间是在这年的仲冬。但上面所引的蒲松龄《登岱行》里却有这样的诗句:“七月晨寒胜秋暮,晓月露冷天风吹。”这说明蒲松龄去泰山的时间是在盛暑的七月,但因为身在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泰山之上,所以他发出了“七月晨寒胜秋暮”的感叹。至于是哪一年的七月,因资料阙如,不好论定。一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的仲冬时节登岱,一是在某年的七月登上泰山,就算是假设蒲松龄在同一年的七月登岱,也与唐梦赉登岱相差了四个月,“有可能这年蒲松龄亦曾与唐梦赉同游泰山”的看法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正因为同是登岱,但唐梦赉和蒲松龄登岱的时间不同,时令有别,袁先生对于蒲松龄与唐梦赉同登泰山一事,亦因“尚无佐证,不敢遽然论定”。由于蒲松龄与唐梦赉同登泰山一事在时间上无法统一,难以坐实,所以笔者认为,他们两人在康熙十二年(1673)同登泰山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2000 年,袁世硕、徐仲伟两位先生合著的《蒲松龄评传》出版。其第五章《文章憎命·缙绅门下》记蒲松龄、唐梦赉登泰山事,与袁先生《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中的观点又有不同:
康熙十一年(1672)……次年七月,唐梦赉要去登泰山,为了不感到孤寂,又邀蒲松龄相陪伴。蒲松龄那年在王家坐馆,但不好拂唐大缙绅的美意,他在当地是有很高的名望的,好在泰山距淄仅百里之远,往返不过五、六天,也就征得馆东的同意,随着去了。[10]90-91
袁、徐二先生提出的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唐梦赉邀蒲松龄一同登岱之说,不知其所本,亦不知因何与袁先生前说相异。袁、徐二先生认为,唐梦赉登岱因感到寂寞,遂邀蒲松龄同往。事实是唐梦赉此行的目的不为登岱,而是访友。因为旧日的僧友元玉驻锡于泰山之阳的普照寺,唐梦赉践昔年的旧约前来相访,所以他不会感到“孤寂”。
唐梦赉会不会邀约蒲松龄与他一同登泰山呢?笔者的看法是不会。从《志壑堂集》的相关记载看,唐梦赉出行阵仗很大,不像蒲松龄那样“一仆一骑,别无伴侣”,其随行者有侍从、苍头、厨子、车夫、马夫、保镖等等,并且保镖都配有火铳。康熙十六年(1677)唐梦赉南游江浙,由淄川张氏家族的张绅和柳灿东(名不详)侍从;康熙十九年(1680)南游江浙,由其外甥许静修侍从前往;康熙二十一年唐梦赉邀友人登近在咫尺的长白山,由浙江少年才俊吴陈琰侍从。当时蒲松龄的馆东毕际有亦应邀同往,但蒲松龄却无缘此行,毕际有的侍从者是其妻侄王广铨(字次公)。毕际有出游回到西铺村,蒲松龄曾在《重阳,王次公从高少宰、唐太史游北山归,夜中见访。得读两先生佳制,次韵呈寄》诗中慨叹“李郭仙舟望亦难”。而且,由唐梦赉发起,淄川诸多文人参与的“载酒堂唱和”“五亩园倡和”等雅集活动,蒲松龄也只能作诗遥和。以蒲松龄的身份地位,他是没有多少机会参与到唐梦赉的社交圈子里的。唐梦赉出游,如果没有蒲松龄的馆东同行,让蒲松龄侍从随往,于情于理,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袁、徐两位先生关于“泰山距淄仅百里之远,往返不过五、六天”的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彼时淄川去泰安州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淄川南行,经青石关、和庄、莱芜到泰安的小道,约二百四十馀里;另一条是出淄川西行,经王村、明水、济南、长清到泰安的官道,全程约三百七十余里,康熙十九年唐梦赉南游走的即此线路。这两条路,皆不是袁、徐两位先生所说的仅有“百里之遥”。莱芜一路地处在群山之中,山高路险,行动缓慢。特别是益都县颜神镇与莱芜交界处的青石关,关北路险难行,即便是晴和天气,也须手脚并用才能攀爬到关前。康熙十二年(1673)袁藩自胶州归来,与毕际有再次修订邑志时天已降雪,一旦大雪封山,莱芜一线便已不能通行。走济南一线,全程约三百七十馀里。即便沿途唐梦赉不居停访友,一行人每天赶路七十馀里,时值冬日,昼短夜长,积雪不化,五六天的时间,大概只够去泰安单程。
综上所述,袁、徐两位先生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支持的情况下,说唐梦赉邀蒲松龄在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同登泰山,所言诸事皆与事实不符,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值得关注的是,袁先生原来“不敢遽然论定”之事,后来竟已然成了“定论”,不少研究者言及唐梦赉与蒲松龄之间的交往,必谈二人偕从登岱之事。如袁世硕先生主编的《蒲松龄志》云:“(蒲松龄)也曾随唐梦赉等游览山水,东去崂山,南登泰岱。”[11]28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附录《蒲松龄年谱》云:“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三十四岁……七月与唐梦赉等人登泰山,并作诗《登岱行》七古一首。”[12]总3377刘秀荣、刘婷婷《聊斋俚曲论纲》云:“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龄34 岁……是年……七月与唐梦赉等人登泰山,作《登岱行》七古一首。”[13]14马振方先生《〈聊斋志异〉面面观》云:“十二年(1673)……七月又曾登游泰山,作《登岱行》。”[14]10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当年路大荒先生因张序《聊斋诗集》五卷本卷一没有编年,而“考之亦未得其究竟”,将包括《登岱行》在内的七十三首诗作“姑附于”康熙十二年(1673),后来的研究者则未作考证,因循其说,将蒲松龄登岱一事坐实为康熙十二年(1673),并明言是受唐梦赉之邀,与唐梦赉一同登泰山。现在该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改正这一错误结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