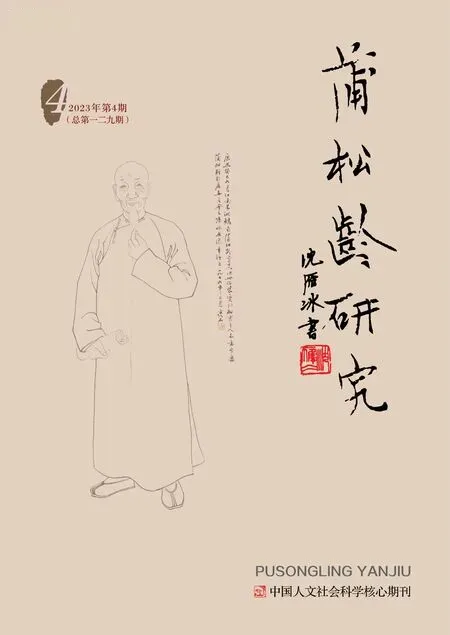《醒世姻缘传》“农民”考
——兼论明代吏员参充制度
贾海建
(绍兴文理学院 学报编辑部,浙江 绍兴 312000)
《醒世姻缘传》既是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1]855,为我们认识明代社会提供了生动的图景和丰富的细节。《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明水镇的里长乡约风闻侯小槐因娶汪为露之妻暴得横财,便借纳监之事向侯小槐索要五十两银子。讹诈不成后,里长乡约恼羞成怒,将侯小槐举报到县中去纳监。侯小槐向县官辩解称,自己是种田农夫,无力上纳监生,并且“一字不识,似盲牛一般”。县官却说:“因你不识一字,所以报你纳监。若是认几个字,就该报你做农民了。”虽然侯小槐“使了六十两银子,寻了县公相处的一个山人说了分上”,免除了纳监之事,但乡约仍然不肯放过他,又要“举报农民”。对于此回的“报你做农民”“举报农民”,读者多会有所疑惑,为什么做“农民”比纳监更可怕?“这监生不(还)止于倾家,若是被他报了农民,就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若赔了,倾家不算,徒罪充军,这是再没有走滚。”[2]571-572在明代,农民除了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外,还有什么特殊的内涵呢?
一、《醒世姻缘传》“农民”歧说辨析
现有的《醒世姻缘传》校注本以及相关的小说语言词典皆未对第四十二回中的“农民”进行注解。法律史专家郭建在谈到书吏特权时引用过《醒世姻缘传》的这一情节,认为“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是农民应承担的差役,而侯小槐“原来开一个小小的药铺,是个市民”,乡约借清查黄册之际,试图将他划为农民,以使其承担繁重差役,从而达到报复的目的[3]71。明代户口主要有民、军、匠、灶等籍,后来为了征派税役和市场管理的方便,确也出现了铺商注籍制度,所注之籍称之为“商籍”或“铺籍”[4]116-127。不过,侯小槐投状请求免于纳监时,特别强调自己“世代务农,眼中不识一字,祖遗地土不上四十亩,无力援例”,因此,侯小槐本当就是民籍中的农户,换句话说,《醒世姻缘传》中“举报农民”与户籍划定并无关系。以古汉语研究见长的赵红梅、程志兵曾对《醒世姻缘传》中“农民”的内涵做过专门探讨,指出该“农民”实为“粮长”的俗称[5]92-94。“粮长者……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6]1899,其职责主要是催征、解运钱粮。明中期以后,赋税繁重,农民逃亡现象加剧,政府常责令粮长补足赋税钱粮,因此,粮长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重役。如果将《醒世姻缘传》中的“农民”理解为粮长,在逻辑上也讲得通,但与相关史实不尽吻合:
首先,从制度的设计上,编佥粮长的标准虽多有变化,但考虑的主要是田地、丁额、家资之多寡,对是否识字没有特别的要求。《醒世姻缘传》中县官提到,纳监可以不识字,但“做农民”需要“认几个字”。其次,粮长的主要任务是征解春秋二税,政府也会委派其“拟订田赋科则,编制鱼鳞图册,申报灾荒蠲免成数,检举逃避赋役人户和劝导农民努力耕种并按期纳粮当差等”[7]1。而《醒世姻缘传》“做农民”需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却未提及征解钱粮这一导致粮长破家亡身的苦役。再次,明代粮长有“乡储”“万石长”“公正”之别名,但现有史书、笔记、方志等文献中尚未发现粮长有“农民”之俗称。
综上,《醒世姻缘传》中的“农民”既不是指农夫或农户,也不是指粮长等里役。值得注意的是,除《醒世姻缘传》外,其他小说作品中也出现过此种特殊的“农民”。《西洋记》第五十六回,张守成解释为何半路出家时说:“弟子自幼儿习读经书,有心科举,后因五谷不熟,不如草稗,却到我本县去纳一个前程。是个什么前程?是个办事的农民。渐渐的当该,渐渐的承行。当该、承行不至紧,就看见公门中有许多不公不法的事,是弟子发下心愿,弃职而去……”[8]729清初拟话本《二刻醒世恒言》下函第五回《黑心街小戏财神》讲述一个发生在明朝山西应州府的故事,主人公淳于智文不成武不就,“舍了文武两途,只有一个作吏。这淳于智也思量去作吏,只是山西旧例,都要有家事的才好纳农民,加纳两考,如无本钱,也进不得衙门。这淳于智家里,只有四堵壁子,还是租着人家的,破了不曾修好,那里得个银子去纳吏”[9]131。由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农民”在官府中做事,与吏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契合了《醒世姻缘传》中当了“农民”就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的职责范围。不过,如若想要真正明确“农民”的含义及其与吏员的关系,还需从明代吏员的参充说起。
二、吏员参充与“农民”的产生
明代选人三途并用:“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6]1715吏员俗称外郎,“是由国家任用、在吏部注册、地位低于官的公职人员”[10]39。明代吏员的参充主要有佥充、罚充、纳充三种途径。其中,罚充指官员、进士、举人、监生、生员等犯错或久学无成而谪充为吏,典型的如弘治年间乡试第一的唐寅,在会试时因受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而被贬谪为吏[6]7353。由于罚充之吏员与“农民”关系不大,并且明中叶以后罚充为吏的规定渐次废止,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佥充与纳充两种形式。
佥充即政府强制性地从当地百姓中征派吏员。吏员本质上带有役的色彩,因此也被称为“吏役”。明代佥吏事例规定,民户有二丁、三丁者一丁充吏,四丁以上者,即使有“一丁或为官、或充生员,及有一丁充吏后,有司又佥其一丁充吏”的情况,也不可以优免[11]400。乾隆《吴江县志》在总结明代役法时云:“明役法有四:曰选役,曰编役,曰长役,曰赋役。”[12]435其中吏员即为选役:“选役者谓其才力堪中,有犯则除名。”[12]439也就是说,吏员虽属役之一种,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也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参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元代奸贪猾吏祸国殃民的前车之鉴,提出吏员“惟以农人役之”[13]402,从而成为有明一代吏员佥充的成法定规:“凡佥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但曾经各衙门主写文案、攒造文册及充隶兵与市民,并不许滥充。”[14]147对于不许市民参充吏员的原因,朱元璋解释道:“其市井之民多无田产,不知农业艰难。……有等无籍之徒……其心不善,日生奸诈,岂止一端,惟务构结官府,妄言民之是非。此等之徒,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哪有厌足。”[13]327-328因此,农民身份成了明初佥充吏员的必要条件,佥充之吏员又被称为“农吏”。如《咒枣记》中萨真人转世西河县,“忽遇上司明文,着各县耆老保取子弟俊秀者,充取农吏。西河县的耆老就保了这个萨君”,被佥拨在刑房为吏[15]17。“保取子弟俊秀者,充取农吏”即佥充吏员。
由于吏员佥充与农民身份的关联性,“农民”一词在明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王同轨《耳谈类增》指出,明初时“吏称农民”[16]253,即“农民”是吏之别称。不过,“吏称农民”仅见于《耳谈类增》,即使这一说法记载无误,也当只适用于明初,此时,佥充吏役者考核合格即能收参成为吏员。随着纳充吏员政策的推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纳充即通过纳物或纳银获得参充吏员的资格。明代吏员捐纳之风肇始于景泰年间[17]75-81,最初只是由于西部边地连年战争,在四川等个别地区实行以筹措军饷。成化以后,或因救灾备荒,或因大工筹饷,甚至以“处钱粮以裕国用”[18]322等宽泛的理由,在全国范围内广开吏员捐纳事例,并逐渐演变为常规定例,随之,纳充也取代佥充成了吏员来源的主要途径。关于纳充吏员的程序,嘉靖年间曾任吏部尚书的许赞说:“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写字……考称者,照纳银司府州县令典等项,挨次参充,不中者降参着役。”[19]1370许赞所谓“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的说法,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捐纳吏员者纳银之后还要经过考选及候缺,而在成为正式吏员前即被称作“农民”。不过,尽管明朝中后期纳充已是吏员的主要来源,但在名义上佥充仍是吏员参充的“正途”,纳充吏员需“援例”实施,一事一例,一般都有一定时限或钱粮额度,超过时限或捐纳的钱粮达到一定数量即行停止。如弘治六年(1493),保定等府水旱虫疫连岁相仍,为救荒开捐纳吏员等事例,“俟麦熟停止”[20]1560;嘉靖十八年(1539),工部请开纳监生、吏农等项事例,“诏从之,限三年止”[21]4770。因此,纳充吏员盛行并成为主流后,佥充这一形式并未消失,而佥充者同样也要经过考选及候缺,在成为吏员前也属于“农民”。嘉靖年间《广东通志初稿》就明确记载了“农民”包括“纳银农民”和“考选不纳银农民”两类[22]216,并且这与嘉靖七年(1528)吏部的规定也相吻合:“凡农民选取良家子弟取具保结,教令习学书写,讲读律例等书,转送巡按衙门定立等第……前纳银听参人役,送考堪中者,于农民考中数内挨次参用。”[22]215可见,选取者(佥充)与纳银听参者(纳充)在获得吏缺前皆是“农民”,许赞对“农民”的解释并不全面。
关于“农民”及其与吏员的关系,万历年间《东里志》的说明或更接近事实:“初辟于有司谓之农民,至授职事乃谓之吏。”[23]135也就是说,明代将初参吏员尚未考选者,以及初次考选或捐纳定拨后候缺吏员者称之为“农民”(下文提到的“农民”皆指此而言,如无必要不再加引号)。另外,由于吏缺少,候缺者众①候缺者中既有佥充、纳充之农民,也有吏员转考、起复者等,其人数往往是吏缺的数倍。,佥充或纳充吏员者往往不能立即补缺充吏,因此,农民又被称作“候缺(听缺)农民”,甚至存在“纳银三十年未拨”[24]624的情况。如此一来,农民不再只是佥充或捐纳吏员者的一种过渡性身份,而成了衙门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群体。
三、农民的地位及职责
一般来讲,无论是佥充还是纳充吏员,农民皆是其必经阶段,因此,“报农民”可看作是“报农民以充吏”的省称。明代吏员三年一考,“三考满,四考勤,而定以杂职,九品、八品、七品等第,而授之冠带,又分各衙门办事。六月毕典,给引回家,谓之省制。候选期至,行文起取至部,高者授以京卫或外卫,经历司七品、八品等官。”[23]135因此,吏员考满选官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异路功名”,如上文提及的张守成(《西洋记》)、淳于智(《二刻醒世恒言》)皆将参充吏员作为前程出路。即使考虑到存在“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25]106的情况,但做了农民、吏员可获得赋役上的优免,并且“庶人在官者”的身份也让吏员有了舞文贪贿以取利肥家的权力,因此,“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吏胥”[26]105。既然如此,为何《醒世姻缘传》中报农民会令侯小槐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呢?
从农民的前途来看,理想的状态是成为吏员,并在三考满后入仕为官。但此过程极为艰辛:“在外农民守候一二十年方得挨参,又有上司比较、钱粮未完、查盘考察等项问革,丧家失业者十常七八,给由到部者十仅一二。”[27]37即使能够到部,还需“分拨各衙门办事。辰入酉出,动经数岁,其有去家远者囊橐空竭,无人供应,遂致沿街丐食,廉耻道丧”[28]169。同时,传统观念中吏员身份低微,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捐纳吏员的盛行,“纳银听参吏员不谙刑名行移,不通楷书算法。既以纳财为出身之阶,必以贪财为营家之计”[29]621,吏员社会危害性凸显,致使“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30]401。即便有幸为官,这些出身吏员的官员也常被蔑称为“奴才官”[31]387。因此,普通百姓多将参充吏员看作是苦差,甚至“指为垢辱,百计求脱”[32]841。尤其是“北方州县吏役绝少,甚有求一二人直印管库而不可得者。每报农民哄动闾阎,诚恐有司奉行不善,翻为良民之累”[33]205。
同时,农民“未有前程之名,未沾斗粮之惠”[34]527,成为正式吏员之前需要长期候缺,甚至没有机会“转正”,其地位还远在吏员之下。沈鲸《鲛绡记》第十出《谋害》中讼棍贾主文“相交的是六房书吏,使的是笞杖徒充。外郎称我阿叔,农民叫我公公”[35],虽是自我吹嘘,但借此也可看出农民地位之低:外郎即吏员称其“阿叔”,农民则更低一级,称其为“公公”。更为重要的是,明代农民不同于清代的“挂名书吏”,仍要在官府中“办事”。如淳安县“农民旧例上班”,即每天都要到衙门点卯待命。海瑞任淳安知县后,革除了农民上班的旧例,但“遇有差遣……挨次轮流,不论差之繁简久近”[36]43。《牡丹亭》第八出《劝农》县吏上场云:“承行无令史,带办有农民。”[37]40这也说明,农民虽然尚不是正式吏员①对于此处的“农民”,以往学者皆将其理解为农夫,而未留意到“农民”在明代还有其他的含义。结合文本及历史语境,此“农民”当指候缺农民。,但也要在衙门中应差办事,帮办或实际承担了吏员的诸多差事。并且,委派给农民多是“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等苦差。以管库为例,这一差事不仅要负责支解钱粮,有时还需“供县官衙用、堂食诸用以及办礼、办酒席”[38]67。《醒世姻缘传》第十七回,晁思孝在任通州知州时,“在那库吏手里成十成百取用,红票俱要与银子一齐同缴,弄得库吏手里没了凭据,遇着查盘官到,叫那库吏典田卖舍的赔偿,倾家不止一个”[2]229。可见,管库绝对是一项高风险的差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倾家丧身。而一些地方则革库役“以候缺农民领其事,谓之库农”[38]66,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乡民对报农民畏之如虎了。《醒世姻缘传》中乡约勒索侯小槐不成,报其纳监,侯小槐请托免纳后,乡约“仇恨愈深”,所以要举报侯小槐做人人畏惧的农民,以泄心中之愤。
四、报农民与纳司吏
《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魏才打听到乡约要举报女婿侯小槐做农民,立马给其支招:“火速的刷括三十多两银子,跑到布政司里纳了司吏,就可以免纳农民。”[2]572按照许赞“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的说法,侯小槐纳司吏,在纳银后、正式参充吏役前实际上就是农民。同样是农民,为什么侯小槐想方设法逃脱被乡约举报农民,而自己却又主动纳银做农民呢?
如上所论,农民是候缺之“准吏员”,“凡各衙门起送农民本以学法令、办文移”[22]217。因此,农民与吏员的来源及参充程序基本重合,也有佥充和纳充两种形式(官员、士子等罚充为吏者不称农民)。佥充农民的基本程序是:地方乡约、耆老推举符合条件的“良家子弟”,取具保结,经由州县吏房,“每半年一次,起送赴司府,转送巡按衙门考选”,考中者挨次参用,不中者发回为民[39]410-411。纳充的基本程序是:朝廷开捐纳事例,纳充者到布政司援例纳银或捐物,行文本县取具保结,按照所纳吏员行头免考候缺,或者与佥充农民一起送巡按衙门考选,考核合格者按照所纳吏员行头候缺,“不中者,发回习字。其累考不堪者,年终类奏,查照义民事例,冠带荣身”[39]411。《醒世姻缘传》中所描述的侯小槐纳司吏的过程符合纳充的基本程序,并且也补充了一些史书未载的细节:
侯小槐……同了魏才来到省城布政司里递了援例状子。三八日收了银,首领行头,正数二十两,明加四两;吏房诸凡使用,去了五两。行文本县取结,乡约里排、该房书吏,去了四两;心红去了五两;来往路费,做屯绢大摆、皂靴儒绦,去了二两多;通共也费了四十多银子。[2]572
既然侯小槐通过布政司纳农民充吏以逃避报农民,那么乡约要举报的“农民”应是非纳银农民,即佥充农民。前文提及,吏具有役的性质,佥充吏役本是地方的职责之一,纳银充吏盛行后,佥充这一途径也未完全消失,仍可以“因吏缺而报农民”[40]429。同时,明代各级衙门吏员额有定数,但候补的农民却“不限以数”[41]149,滥佥农民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州县官吏常借报农民需索钱财,如万历年间山西兴县知县陈□□“佥报农民共报四十五名,每名密送银一二十两不等”[42]604;天启年间四川大邑县报农民,全县共一百四十名,知县翁九升“每名索银一两免纳”[43]279。另一方面,佥充之农民,“初佥杂役,役满参缺”[44]212,在参充吏员前,要先在衙门应差做杂役,所以一些州县“在答应诸人,则不止祗候之民皂,而又报义民以充官;不止侍奉之门厨,而又报农民以妆吏”[45]979,这也正是《醒世姻缘传》中说“报了农民,就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的原因。
捐纳农民充吏则有所不同。关于《醒世姻缘传》中侯小槐纳司吏,吴晓龙《〈醒世姻缘传〉与明代世俗生活》解释说,纳了司吏,侯小槐就成了衙门里的人,乡约便不敢再找麻烦(报农民)了[46]39。此种解释并不符合小说的原意。侯小槐之所以纳司吏,并不是说司吏的身份可以让乡约畏惧,而是纳了司吏自然就免除了佥充农民之役。《明会典》载:“国初令有司设司吏,许各保贴书二名。其后定设掾史、令史、书吏、司吏、典吏,后又设提控、都吏、人吏、胥史、狱典、攒典……正统元年,裁天下吏员,每房止存司吏一名、典吏二名。”[14]124虽同是吏员,但“司吏承掌该房之事,典吏分投典管”[47],司吏是典吏的上级,并且明朝中后期诸多州县的司吏支取俸禄,典吏却没有①参见周瑛,黄仲昭《重刊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 页;王心修等《(嘉靖)天长县志》卷二《人事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6 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 年版。。不过,《醒世姻缘传》中所谓“司吏”与之不同。侯小槐所纳为“首领行头,正数二十两”,“吏员行头,俱以食粮多寡为称。如在外布政司通吏谓之大二石五斗”[48]384,“首领行头”即地方司或府经历司、照磨所等首领衙门典吏,在捐纳吏员时,“各司、府首领并州县吏员银二十两”[21]6810。而地方司、府首领衙门不设司吏,只有典吏,并且,布政司、按察司等中的司吏常以书吏称之[24]652。因此,《醒世姻缘传》中魏才口中的司吏,是相对于州县吏员而言,泛称布政司、按察司等省级衙门的吏员,具体来讲,就是省级衙门中经历司、照磨所等首领机构的典吏(首领行头)。
明代的经历、照磨等首领官多由监生、吏员出身者选任,“以秩卑为上官所轻弃,甚则部民得以事倾之”[49]857。《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三回,骆校尉就曾极力劝阻狄希陈做府经历这样的首领官:“你做了首领,就要叫人老爷,就要替人磕头,起来连个揖还不叫你作哩。……只是那没日子过的人,别管他体面不体面,做上这个官,低三下四,求几个差委,撰几两银子养家。”[2]1096不过,首领衙门虽然冷淡,但捐纳吏员所需银两少(二十两),与司府州县六房中的吏员相比,事简人闲,即使是农民也是照所纳首领行头候缺。而州县佥充之农民,经过巡按考选后,大多数会被下拨各州县候缺,候缺期间(时间可能会很长),需要充当杂役。因此,对于纳吏避役者来说,捐纳首领行头无疑是上佳之选。如嘉靖年间湖广按察司首领衙门吏员“止有七缺,前后纳银农民将及三百人”[24]652。如此之多的候缺人数,说明很多人并非为了充吏,而只是为了避役。行文至此,《醒世姻缘传》中侯小槐为逃脱被乡约举报农民,而选择捐纳农民就有了合理解释:乡约所佥报之农民,多需先充杂役,并且大概率会考拨在州县候缺,面临着被委以管库、管仓等苦差的危险;捐纳首领吏员后可能也要先做候缺农民,但做首领衙门农民及吏员的风险较低。因此,侯小槐两害相权取其轻。
结语
“小说家叙述时事,必须牵涉其背景。此种铺叙,多近于事实,而非预为吾人制造结论。”[50]6因此,在文学价值之外,小说的史料价值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醒世姻缘传》中乡约为报复侯小槐试图举报其做农民,以及侯小槐通过捐纳首领衙门吏员摆脱危机的情节,即为探讨农民与吏员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农民既有“纳银农民”,也有“考选不纳银农民”,是明代对初参吏员尚未考选者,以及初次考选或捐纳定拨后候缺吏员者的称谓。明朝中后期,捐纳成为吏员的主要来源后,“考选不纳银农民”已沦为与“门子、屠沽、菜佣”类似的杂派[51]3578,百姓畏之如虎,而贪官污吏则借机将报农民当作敛财索贿的“登垄地”。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能襄助相关小说情节的理解并澄清一些错误认识,同时对明代吏员参充制度研究的深化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