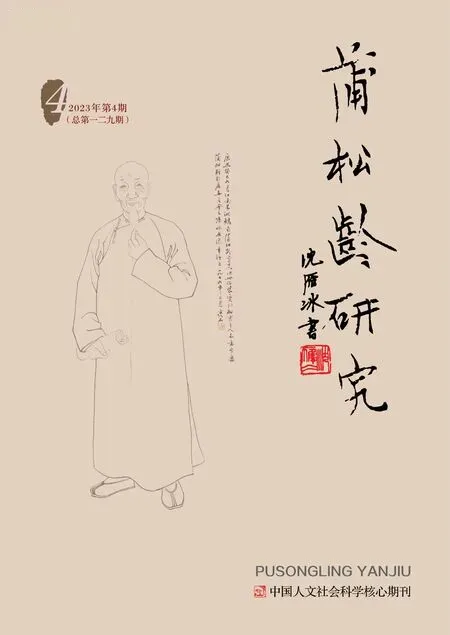关注灾害学与文学、民俗关系研究
——《明清灾害叙事、御灾策略及民间信仰》感言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灾害,作为存在状态异常的集合概念,恒在且无可回避。人类许多民族都有对于灾害的丰富感受、认知和诠释,从神话到民间故事、文学作品都有着多种多样的记录、想象,而古代中国更有着在世界上罕有可比的“荒政”制度、文献与赈灾实践经验。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相关的文献、民俗资源,更是为今天如何认识、应对和总结御灾策略,提供了宝贵资料,使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灾害学”学科成为一门“显学”,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先生及其团队,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灾害、御灾文化记忆、政策制订与民间御灾经验总结的多学科探索中,民俗信仰研究是一个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方面。民俗无往不在,而御灾民俗信仰更是支配着明清朝廷荒政的具体措施筹划及其地方官员“执行力”的操作、民间救助与应灾诸环节。那么,如何将灾害、御灾民俗资源最大限度地搜罗、调动起来,就充分体现出民俗学的包容力。这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清灾害叙事、御灾策略及其民间信仰》(中华书局2022 年12 月版),就体现了明清民俗信仰研究与明清小说、野史笔记文献等多学科较大幅度的结合,具有超现象性、跨学科性、整体性、实践性强四个特点。
首先,是灾害叙事研究的超现象意义。这在导言部分多有谈及,亦即灾害叙事与明清御灾民间信仰的精神史意义。包括历史事实中观念元素,传闻小说藏蕴的灾害民俗价值认同,其民俗叙事行为本身。通过对明清若干灾害的描述,探讨灾害、应灾民俗记忆、民俗观念,勾勒明清灾害民俗发生的若干精神史脉络。既理性地认识到灾害祭禳活动的迷信、超现实想象性质,又能历史地看待和辩证地进行价值判断。
其次,是对灾害的种类划分与认知跨学科性实施。该著部分地借鉴灾害学的归类,将明清灾害划分为九大类。其中有许多都是属于御灾故事与神秘崇拜结合的,如水灾及其民间信仰归因,强化了蛟龙崇拜、“许真君”信奉,水神职责也被赋予到“金龙四大王”“黄大王”形象上,以及治水能臣栗毓美的神化等。旱灾与帝王罪己,地方官求雨,求雨功效在此大于勤恳敬业。清官能臣也运用巫术仪式求雨,灵物崇拜多与求雨有关。佛教的咒龙求雨发展为打骂龙神,而驱除旱魃有了替代方式,女性求雨是佛经故事的世俗化。而蝗灾,可被柳神有效遏制。治蝗带有人治观念和伦理性,清官所在之地而蝗不集。将柳神理解为秀才,说明清初民俗之于柳的亲和感,体现了生态保护思想及柳崇拜观念。至于雹灾有突发性等特点,古代史书把雹灾政治化阐释,将其对应到政治悖谬导致的天气阴阳相激。继而民间认为冰雹是神人在空中播洒,或高山上那些神化了的虾蟆、蜥蜴、龙等所吐。雹灾传闻体现了龙崇拜“先结构”存在,人们了解雹灾是洪水前兆,想象宝物驱雹[1]。瘟疫,明清人想象中的病魔形象,有服饰古怪的童子、鸭子、怪人等。御病传闻有送药神使、特效药、抗病法新发现等。一方面承认人力救助,另一方面又恐惧天命鬼神,而鬼神救助往往即人力救助的变形延展[3]。
该著的跨学科性,还突出地体现在将民俗记忆、小说文本与晚清告灾新闻图画的结合。按说,这后者属于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范围,且属近现代领域。“流民图”作为摹状苦难的传统传播模式,无须文字的瞬间识记,摹状灾情呼告的“铁泪图”,每幅告一灾,寓意丰富。如《河南奇荒铁泪图》劝赈书,图画是以具体生活细节展示灾荒的可怕情状,图画上往往配有主题词及情况说明文字,与灾情歌谣等呼应。而表现官员实地赈灾,民间自救互助的图画,如吴友如等主绘的《点石斋画报》,不仅关注、追踪灾民真实生活,提供舆论和社会力量支援被灾者,直接进行募捐广告宣传,还每多诉诸直观画面展示受灾、逃灾的情状,揭露不合理御灾、趁赈灾横行不法现象,提供疗病御灾之良策。赈灾图画对唤起中外人士多阶层、多层次、多方法地赈灾,取得巨大收效并持续久远。著作在数千幅图画中,对有关灾害表现的作品精心拣选,同相关载录结合,对其新闻传播等价值研究,增大了应灾工程及其相关民俗现象的理解深广度,图文呼应,特色突出,具有较大的创新价值。
其三,是与前揭联系的整体性眼光。该著不仅描述明清灾害的民间信仰,更重视民间御灾、赈灾等一系列方面,特别注意到地方官员多方式的“匿灾”(瞒灾)、侵赈等罪恶现象的民间记忆载录,结合古代尤其明清以来丰富的“荒政”文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该著整体性还在于,努力探究多种灾害之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如该著揭示出明清灾害言说,多呈现水旱叠继,二者或连年发生,或同年降临,导致被灾者信仰乱象、心理异化及应灾行为失常。水灾则多因风灾而至,两者都带有局部性与突发性。而“三大自然灾害”(水、旱、蝗)往往彼此连带发生,“旱极而蝗”,持续旱灾,植被遭损,蝗灾易生。涝灾则不利于蝗,大雨可灭蝗于初萌,等等。干旱也与瘟疫的持续时间多呈现正比;旱涝之灾也不免造成水质破坏、卫生条件愈加恶劣、腐尸不及掩埋、饥民流动等,加速疫病传染,而且疫情具有季节性[3]。因而明清小说中常写灾后饥寒困苦,夺命的多为因冻饿体弱所染各种疫病。管理、救助不当,赈济过程中也易发瘟疫,善举在执行中办了坏事。对于这些赈灾弊端、多灾交织及其因灾派生的诸多连带关系,该著也做出了可贵的探讨。
这里,从该论著对于瘟疫、御瘟民间信仰予以介绍。从主题学角度梳理相关材料,也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眼光,所谓古人云“大灾必有大疫”,瘟疫等流行性疾病,恒久且普遍地危害于人。该著揭示出明清人们的灾疫推因:所谓人间瘟疫,往往由某种或多种自然灾害衍生或加剧。这样,那些自然灾害就不免带来了“次生灾害”。相关文献载录,谈虎色变,人云亦云,由于医学发展局限和神秘思维影响这些描述其实并不确切,但却的确是彼时人们的真实想法,于是今天也就不妨碍从民俗角度探讨,获得有益于当代御灾心理、想象复杂性探索的启示。
其四,关于灾害神形象梳理的多样化、个别化并重,体现出一种互补联系。通常,人们对于旱魃(民间的打旱魃、打旱桩等)、水神等探讨较多,该著则除了瘟神、疟鬼形象与特效药叙事等,还讨论了雹神李左车、雪神滕六、驱蝗神金姑娘娘、刘猛将等。更重要的是注意灾害之间的关系,并设立了专章。应该说,这是先前较为少见的。当然,多种灾害的发生有必然性也有随机性、偶然性,这些联系虽然存在多发性,也未必都每次验证,但这一探索无疑是必要的,有利于进一步追索如此叙述的深层原因、思维路径。
在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人心目中,病魔形象尤其变得多样化丰富化。如服饰古怪的童子,如青衣人驱赶的鸭子,如巨头赤发金目的瘟神形象,如“以身试瘟”的那位“姓温”的应试书生,等等。著者能尽量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并且适当补充精选的小说、野史笔记中的相关材料佐证,并在此基础上阐释推因,虽然不能说都那么充分,但的确体现出多种民间信仰在明清告灾、御灾体系的纷杂而又富有规律性、实用性的组合。这一具有众多“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前科学时代的民俗心理的反映。
瘟神疟鬼形象描述的复杂多样和叙事过程中,具有众多不确定性,表现出明清人还未搞清楚瘟疫等恶疾的源头,难以准确想象出瘟神疟鬼确切形象。应灾心理的感受、思考,其实是艰难困苦中进行的,由此民俗想象得以发扬,看得出记述者们也是在努力探寻瘟疫的生活真实。如黑格尔论述印度神话时指出的:几乎一切东西……甚至动物都被假定为梵天化身,“于是那似乎要规定自身为个体性的东西立刻就又消失在普遍性的云雾中了”。但这就是一种历史真实,也是文学书写的民俗现象,小说中的描述往往还更接近当时人们的真切感受。
其五,该著有说服力地描绘了明清民间抗灾医疗活动的一幅幅民俗场景。这是民间记忆中的被灾者如何及时疗治,医药经验与神秘崇拜的综合运用,也包括抵御病魔来袭的相关传闻:这里有上天派来神秘使者送灵药;这里有具备医学经验的“博物者”——智慧老人指示对抗传染病的特效药。论著指出,故事传播者基于这样一种可以说中外历史上见惯不惊的大瘟疫惨痛结局,明清人接受的暗示是某种神秘因素在主导。大量的多种来源的事例都在无可置疑地宣示,遭疠疫而获救者的幸运,是由于自身做了善事,体现出高尚的道德。于是这些成功免于灾难的故事,建构了族群伦理与灾害伦理结合的体系,维护了以伦理教化为中心的社会人文生态。关于瘟疫的叙述多数带有题材的选择性,这一点有悖于明清社会不存在抗瘟特效药的历史真实,但却成为相关故事丛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热点。其他如水旱蝗灾等的应对也是如此(但对于雹灾、雪灾缺少应对也是情况属实,同时说明古人在突发灾害面前的无奈)。论著搜集的民俗资料非常丰富,断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朝廷提倡之类先前的成说所能解释的。我们赞成论著的汇聚新资料、多元阐发的学术践行态度。
抗灾另一个关注点是从信仰角度看待各种灾害、禳灾活动。如,民间如何叙述避灾、驱疫鬼与送瘟神。在本土文献依据下,该书补充了弗雷泽对于巫术禳灾、驱疫活动的了解,这些仪式活动已在相当多的中外学者论著中成为定论,如日本田中一成对戏剧祭祀、禳灾的研究,但该著没有驻足于此,而是注意到民间对“疫鬼行踪”与活动规律,是如何理解,如何御灾防患未然的,这才是明清御灾民俗理想最期盼的。这些故事的魅力就在于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过路的鬼使神差被及时拉拢的故事,有的是瘟神梦中提醒的故事,还有民众、僧道、官员结成联盟携手共同御灾的故事,同时展现出驱“瘟神”过程中决策、官民合作的重要。而相比之下,那些“急来抱佛脚”式的功利性祷告常不生效。相关故事中,还展现出佛教与道教咒语融会,而“接触巫术”又与“相似巫术”并用。在其他诸如水、旱、蝗三大灾害的防范、抵御活动的民间叙事中,该著也注意到民间信仰的这些实用性、混杂性的特点。
其六,对于明清应灾、赈灾活动的思考。明清野史到小说所批评的被灾者坐等施赈、骗赈、冒赈等恶习及相关的灾荒民俗心理,向来罕有研究者触及,关注同时能结合恰切的案例加以分析,呈现出该著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除了对于朝廷勤政恤民、清官能吏期待与侵赈冒赈情形的民间惩治方式——冥间审判、报应等,该著专章论述了赈灾过程中,民间的“闹赈”“索赈”“趁灾敛财”“骗赈”与纠集团伙外出“逃荒”等恶习。这就打破了先前僵化、单一的研究模式,似乎在赈济活动中,只有施赈一方伴随权力私用出现的“侵赈”“冒赈”“造灾”等恶政劣行,而是更为全面地审视赈济过程中发生的受赈弊端。如将灾情造假、养蝗蝻以骗赈:“每于山坡僻处,私将蝻种藏匿,听其滋生,延衍流毒,等应差扑捕之时,蹂躏田畴,抢食禾穗,害更甚于蝗蝻。”以至于清代诗歌中愤愤不平、多所揭露的:“闭粜乃恶富,闹荒亦奸民。奸民何为者?一二无赖人……众人米未粜,奸人已千缗。众人腹未饱,奸民酒肴陈。”将赈济物质中饱私囊。又例如晚清小说《老残游记》形象展示的,水灾时部分灾民为了等船每天送馒头,送馍馍,“许多蹲在屋顶上不肯下来”,担心换了地方“就没人管他吃”这种消极待赈现象,等等。这都是伴随灾害降临,赈济施行时经常发生乃至导致“次生灾”的弊端、顽症和痼疾。如果研究者单纯地从某一种文体来看,就容易得出单纯地评价某一个诗人、作家、作品,某一种文体如何反映现实、写实、体恤民瘼等结论,但如果置于灾害学、御灾民间信仰等多角度、跨文体来看,可知这其实有一个对于骗赈、冒赈、闹赈等赈灾恶俗发声,镌刻、传扬移风易俗、建构更为公平、合理的赈灾民俗的大问题。于是研究论著便接地气,具有针砭赈灾过程中种种弊端的补弊纠偏作用,也体现了著者力图将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的使命感。
该著字里行间体现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但从明清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各级官员的综合素质、受灾民众应灾行为等体现出的社会赈济状况,想达到这样的美好愿景,当然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奢望。因而该著也较为注意储水储粮备荒、“换工自救”、赈粥救危过程中的诸多技术性因素,正是这些宝贵的民间御灾经验救活了那些行将成为饿殍的被灾民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种文本载录的饥民急于果腹、“久饿贪食”的教训,以及赈粥过程中如何处理年轻女性尊严的问题,小说、野史笔记中这些看似细微末节的吉光片羽,其实正是宝贵的御灾“民俗记忆”,它们往往可以补明清朝廷赈灾文件——“荒政”文献的不足,以其生动鲜活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较为接地气、具有在地性关注的,还有该著引述的那些地方志,虽然可能有不准确、神秘色彩或未必是原创的,但毕竟是彼时凝结下的当地耆宿载录,体现出民俗学与地方史的结合,使得有关灾害过程、受灾状况等有了相对真实的留存,论著为此显得更加厚重。
由上可见,该著“十年磨一剑”,的确具有民俗、宗教、文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灾害学研究有重要实际应用价值。
此外,该著注重了应灾、御灾的实践性特征。如对地震前鸡犬等动物预兆活动的总结,从天象与飞禽水兽状态预测大风、洪水等。灾兆有时甚至需要仙道之士的及时提醒,于是神仙崇拜的明清持续性发展、泛化的丰富性,就成为该著的一个值得肯定的优势。该著还彰显了小说描写的植树抑洪、储水备旱、节粮节水、推广外来多产农作物等,如此“国计”乃为“民生”之大事,这是多么重要的御灾民俗记忆!该著强调,明清民间助赈讲究不伤害被灾者自尊,维护被救助者的“面子”,这也值得倡扬、践行。捐赠、助赈,本身也是一种应予肯定的侠义精神,需要发扬。该著充分肯定了明清多灾多难社会背景下的“侠客想象”,认为侠与清官联盟的最大成效,莫过于灾荒之际帮助清官惩贪济民。而士绅助赈、仙道救急的民俗观念,亦明清诸多超时空神秘故事流传的主要动因[4]。至此,御灾民俗研究的当代价值可见。
总结明清灾害、御灾叙事的认识价值与文化观念,亦有着重温灾害民族记忆的心灵反映与警醒当今的现实意义。灾害不仅瓦解人类社会,也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有效率地应灾御灾并逐步提高应对智慧与能力,人类也会更理性地、全面地敬畏自然。清代曾利用灾害文化,反思避灾的伦理原因。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灾害、受灾和避灾的民俗记忆总结,可成为一种应灾的必要教材。“灾时社会心态”使人们亲和力增强;灾害叙事往往也成为灾害主体宣泄痛苦,呼唤正义的渠道。讲述灾害酷虐与御灾有效的民俗记忆,无疑能使人们痛切地认识到良好生态环境及其保持的重要。
作者对于先前多所忽视的小说文献中蕴藏的民间信仰,已经关注多年,这方面的梳理选材尤其突出了主题学理论方法的优势。二十年前,刘卫英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得到导师陈洪教授的支持,李剑国教授的表扬。可以说,宝物信仰研究是她的学术准备。如何将民间信仰与明清小说文献结合,将零散的个别作品体系化,梳理出谱系,本来就是学术上跨域、跨文体结合的民俗史、文化史现象,却被20 世纪中叶以来的学科分工强行划出了各自疆域,基本思路也不免因此受到限制,在许多具体研究中体现出来。而事实上,顾颉刚先生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初即找出了本土的主题学思想,他在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找出了宋代郑樵(1104—1162)的《通志·乐略》中这一较早的主题学思想:“《琴操》所言者何尝有是事?琴之始也,有声无辞,但善音之人欲为写其幽怀隐思而无所凭依,故取古之人悲忧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响从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声而已。”下面的这一段话,早已因被顾先生较早引用而更为有名,并辗转流播得到人们更多地引用:
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间,而其事亦有记载。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琴操》之所纪,又其类也。顾彼亦岂欲为此诬罔之事乎?正为彼之意向如此,不说无以畅其胸中也。
前段时间看到有一种说法提到“西方主题学”,这种“贴标签”是文化虚无心理作怪,不仅完全无视顾颉刚等人的研究,也无视了既有的更早的本土学术传统。由这部论著可以看出,到了明清以降,特别是俞樾等人,不论是时空视野、跨文体还是经典之作的解读,都已然成形,那时西方的一些相关理论还没有传入。后来的20 世纪80 年代初,海峡对岸的英文教授陈鹏翔先生的《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也对上引顾颉刚的话转引过,放到显赫位置,极为推重顾颉刚先生的这一跨文学、史、音乐史、民间故事史的贯通性探讨。而在本文所评这部论著中,我们看到的也是文史互证为基础,适当吸收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而更多是本土材料的充分运用,不能归功于“选择性失忆”语境下的所谓“西方主题学”。
灾害的地域性,也是该著的一个关注点。大概是由于生活与工作的原因,该著的两位著者关注灾害、御灾民间信仰的视线、运用的材料较为偏重北方,特别是华北。书中所列雹灾信仰,就偏重在山西这一多山的地域,也的确是雹灾频发且易于发生的地区。至于水旱之灾,偏重在黄河流域和中原、西北;风灾,偏重在西北、华北,而兽灾则分布地区较广,等等。
该著视野开阔,广泛吸收、引用了古代文献与国内外多学科成果,如《中国荒政全书》等卷帙浩繁的史料、地方志,如法国魏丕信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英国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美国艾志端的《铁泪图:19 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日本森正夫的《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荒政和地主佃户关系》等国外研究成果,又如多部明清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文献的御灾描写评述,更吸收了国内灾害史学等众多研究成果,而又能补充丰富综合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方面“接着说”,尤其在特定灾害、御灾信仰的沿波讨源,甚见功力。
两位著者有着丰厚的学术积累,对古代社会的灾害叙事有着整体性、专题性结合的学术观照。特别是能对不同灾害的关联性、动态性研究,不仅对以往灾害民俗研究的学术范式有所超越,也对人类思考有效控制当下世界性的疫情、自然灾害,更有效率地应灾御灾,做出某些预案,有很好的多学科借鉴价值。虽已60 万字,但一些地方如能展开一些,会更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