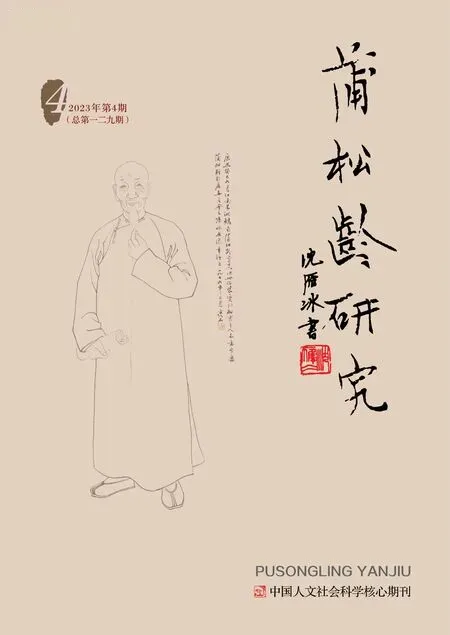《聊斋志异·放蝶》人物本事与创作寓意考辨
聂廷生 王 东
(1.淄博第六中学,山东 淄博 255300;2.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中学,山东 淄博 255154)
《聊斋志异·放蝶》是一篇记叙真人真事的短文,主人公如皋县令王生是明末济南府长山县张坊村(今属淄博市周村区)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长山县志》《济南府志》等有传。多年来,聊斋学界对王生“放蝶”本事作了大量的考证与分析,并对王生的生平交游等做了一些研究,但仍感到有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史书上记载“性简静”的王生为什么会做出“放蝶”这样“放诞”的举动,其思想性格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又如,蒲松龄写作《放蝶》仅仅是因为好奇志异吗?他对王生的态度与写作寓意又是如何?本文拟结合近年来地方文史研究中所见到的资料,谈谈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在以往的《放蝶》研究中,人们大多是沿袭了何守奇“风流放诞”[1]1459的观点,认为王生是一个“好奇尚异”“荒唐政务”“放诞怪异”的官吏。这固然有其道理,但这一观点,显然又与《长山县志》《济南府志》王生“性简静”的记载大相径庭,颇为抵牾。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有的学者认为:“《长山县志》对他有‘性简静’的评价,或许道听途说,传闻异辞,‘放蝶’之说有所夸大亦未可知。”[2]55既指斥史书方志记载的不够真实严肃,又认为“放蝶”记叙是夸大不实,这样一来矛盾倒是消解了,但也将王生和“放蝶”从历史和小说中彻底地抹去了。窃以为此法并不可取,因为大量的记载又证明“放蝶”实有其事。因此,如何全面正确地了解王生其人其事,是我们解读《放蝶》的关键。
陈际泰(1567—1641),字大士,江西临川人。崇祯七年中进士,十年授行人,十三年奉旨护送已故相国蔡国用灵柩回乡,次年于济宁途中染病去世,年七十五。著有《读易正义》《太乙山房文集》《已吾集》等。陈际泰与王生交往较多,不但为王生诗集作序,还写有《和王子凉〈潜岳解〉》《与王子凉》《〈潜岳解〉跋》《隘山斗说》等多篇诗文。陈际泰《王子凉诗集序》说:“山东王子子凉,其奇,吾目中无有也。其学,发源于《山海经》《穆天子传》《考工记》与类于三者之书。其术,出于老庄,一字复人所过,若服上刑。”①陈际泰:《已吾集》卷一《王子凉诗集序》,《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93 册。陈际泰认为,“奇”是王生最为显著的、总的特点。下面先从“其学”“其术”作一点解释分析。
济南东南诸峰有黔娄遗迹,叠石为垒,槁灭高山,著书四篇曰《黔娄子》,明道家之用。山斗虽未见其书,然其书日在目也。今读陈子之文,犹是也。顾陈子之道,颇广有黔娄之高而去其隘,山斗有其隘而去其高,故自名隘也。子其为《隘山斗说》。
陈际泰认为,山斗山之精灵所生之士,以“子凉”为其别字,“凉”是其天性。“凉”之本性与其外在高峻之形相适宜,既有保持石之本质、拊摸感受到的“凉”,又有垒石为高山、攀登而上所感受的“凉”。太行、上党虽然是石之山,而且高峻,但上有州县,数十人登临而上如在平地,反而感受不到“高与凉”了,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了“隘”(狭隘)。王生以自己的“隘”为缺点,但是“不隘不足以为高,不隘不足以慕黔娄”,由此可知,他是在以隘为自誉,揭示了王生保持其“凉”之本性、“隘”之外行与追求高洁、仰慕黔娄之间的内在关系。陈际泰在文末又提出了对王生的郑重忠告:现在你考中了进士,正为“天子贵重之臣”“作天下之幹”,则当自去其隘,而“黔娄诚不足效”,希望他由此而改变自己。特别有意思的是,陈际泰将这一忠告委婉地表达为是王生自己想要改进缺点的审慎的“自断”。至于这是否是王生请其解说“隘山斗”的本意,我们不好臆断,但这几句话的确表达了陈际泰认为王生的这种人格追求和处世态度在现实的仕途生活中是不太适宜的。陈际泰此文当作于崇祯十三年下半年,即王生考中进士刚任如皋知县之时。《隘山斗说》应该是陈际泰这位在人海宦波中浮沉了几十年的老人对王生的深切忠告,而王生此后的仕途之结局似乎也被他不幸而言中。
不可以句疴长幅,效人口动石上读。奇字古文忧师俗,神契命诀亡深笃。越歌道谣丧奇酷,穆传天问失诘曲。大靡经言僵渊穆,寻绎微径得禁谷。胡然而天获单复,爰有山斗山黔生□。精种在下积而育,世绵千祀具生福。②陈际泰:《已吾集》卷十四《诗杂文》,清顺治李来泰刻本。
明代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模拟袭古,墨守唐音,在反对台阁体空洞无物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背离了抒发性情反映生活的正途,在诗体上更加推崇近体。后来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击下,虽已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对明末清初的诗坛仍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状况下观照王生的诗歌就会发现,他远离当时诗坛潮流,不趋新,不务时,形式上“无近体”,内容上“抱黍离之悲”①《长山东街王氏世谱》第三册,民国四年(1915)续修本。,在诗歌审美趣味上显示出反对主流、不合时俗的个性特点。
有黄极淑者,如皋民也,惯大言。市廛人憎怨,以他事不相目,合讼之令,凡十余人。缙绅先生或怜之,畏令不敢请,莫可如何。极淑知一旦死尔,及对时,问何业,曰画。极淑实不能解画,但解工人之所谓画。令即欲见其画,则出之怀中。令大称赏,属巾服宾礼,而笞其讼者十余人,又判金各千两,谢讼极淑罪。人人空壁立,本无一有,乃膝行哭极淑所乞命,穷极,令乃肯已。其所为多类此。然卒以是小不理于人口,败去云。
在这一案件中,市井之徒黄极淑因为爱说大话(“惯大言”)而被十余人联名告到官府治罪,缙绅“怜之”也无能为力。谁料想,审案时黄极淑又积习难改,“大言”会画画,以此赢得了县令王生的好感,不但没有治罪,反而让那些告状人挨揍重罚。诚然,说大话、爱吹牛,固然令人生厌,但毕竟是无伤国计民生、无害他人生活的琐细小节,而那十余名告状者因为看不惯就讼至官府,妄想假借县令之手治人重罪,致使黄极淑吓得要“死”,看来这十余名告状者也不是些善良厚道宽容之辈,实乃无事生非之徒。县令王生似乎对这些无事生非的闲人们也没有好感,识破了这些人的阴谋伎俩,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借机对这些人略加惩治,让其受笞重罚,“膝行”哀求。
另外一件事是为邵潜题匾。邵潜(1581—1665),字潜夫,自号五岳外臣,江苏通州布衣。万历间诗人钱谦益亟称之。此人性格孤僻,侨居如皋,卒年八十五。尤善《文选》,工诗,于周秦两汉书无所不学,精篆籀,善八分书,最工文字学,有《皇明印史》。据《如皋县志·邵潜传》记载,邵潜迁居如皋时,县令王生“式其庐,署其门为‘寓公庐’”,亲自参加了邵潜寓所落成仪式,并题写了“寓公庐”匾额。由此可见,王生对于性格孤僻而富有才学的人还是非常敬重的。
材料一:
(王)山斗生,字子凉,崇祯丙子科举人,庚寅科进士,任南京如皋县知县。公天性渊默,莅官未久即去之。归田以后,殚心著述,如《怪石居文集诗集》《四书文集》均先后锓版行世,旋毁于火。仅余稿本二册,为五古二百首,其目自“一游”至“百游”,“一遁”至“百遁”,今已无从搜辑。惟《四书文》三十余首为陈大士诸公所评定,尚存贻楷手。公抱黍离之感,遗命不求人作碑识,是以轶事无传,其散见周栎园《书影》、钮玉樵《觚賸》、蒲柳泉《志异》诸书者,仅雪泥指爪耳。配吕氏。子一,之琴。①《长山东街王氏世谱》第三册,民国四年(1915)续修本。
材料二:
材料二引自卢兴国先生所著《邹平进士录》。卢兴国先生是滨州市文史馆特聘馆员,著名地方文史专家,研治文史数十年,对邹平当地的家族谱牒、历史人物、地方文献、民间故事、乡野传说等都极为熟悉,著有《邹平名门望族》《邹平进士录》《邹平乡贤录》《邹平碑刻集注》《袁紫兰家族》等著作。他所说的王生嘱咐后人“不剃发不穿满服,不做清朝臣民”的家族遗训是对王氏家族调查访问中得到的,应该是较为可信的。而这一点又和材料一《家谱》中的“公抱黍离之感”相互印证,说明王生的政治态度是拥明反清的。社会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常识”具有“多重实在”的特点,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时可能更加贴近史实。
材料三:
《张并叔允抡、王子凉山斗生》(节选)
张其淦
子凉旧县令,散髻兼斜簪。饵鹿向竹坞,调鹤来花阴。问君胡能尔,
所思在云岑。幸有谷音传,一篇珍璆琳。所以怪石集,巍然留至今。①张其淦,撰,《明代千遗民诗咏》三编卷三,民国时期出版,年代不详。
材料三节选自张其淦撰《明代千遗民诗咏》三编卷三,民国时期出版,年代不详。赞颂了明末遗民王生佯狂避世(“散髻兼斜簪”)、志向高洁(“所思在云岑”)、寄情诗文(“幸有谷音传”),名传至今。这首诗更是写出了王生的遗民形象和情感态度。这几则材料都表现了王生政治上不从清政、留恋亡明的思想倾向。钱海岳在其《南明史》卷八十七列传第六十三中也将王生列为明之“遗臣”。
二、蒲松龄《放蝶》创作寓意考辨
“从本事到故事,不但是实事的移动与改易,且存在处理经验事实的故事策略,即在特定话语主导下或不同话语的竞争关系下,哪些被列入‘不可叙述之事’,又采取怎样的叙述视角达成这一目的,其实存在话语介入层面上的‘看不见的手’,此即吴宓所言:‘殊不知人生至广漠也,世事至复杂也,作者势必选取一部以入书,而遗其他。即此选择去取之间,已自抱定一种人生观以为标准。’(《论写实小说之流弊》)。”[5]因此,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去探究作者的创作匠心和态度寓意,在材料的去取、情节的铺排、文字的表达中去涵咏体味,或许方可求得作者的真心。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去研读《放蝶》,我们发现以往人们对《放蝶》的解读,无论是古代冯镇峦“儿童之见”的讥讽、但明伦“不惟戕物性,且坏法律”的批评,还是现在一些论者的观点,都与蒲松龄《放蝶》所展现出来的丰富内涵有着极大的差距。下面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来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材料的选取。据赵羽先生《〈聊斋志异·放蝶〉本事考证》,较早记载王生“放蝶”本事的应该是李长祥的《王子凉传》。李长祥(1610—1673),字研斋,四川达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明亡后,李长祥积极抗清,与郑成功、张煌言等屡仆屡起,抗节不挠,是清初南方著名抗清人物,著有《天问阁文集》,《清史稿·遗逸》有传。李长祥为王生作传,是将其引以为同调的。《王子凉传》有关“放蝶”部分如下(方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李长祥的《王子凉传》,是一篇比较规范严肃的人物传记,以历史的视角,叙事务求真实。在点明人物的籍贯和性格之后,文章详细叙述了王生罚鹤、罚蛇、罚猫、罚蝶、输蝶的过程及原因,重在突出人物为官之道的违反常规、不徇常法,甚至给人以喜怒无常、朝令夕改的感觉;同时也采用反复手法突出了王生“居官喜节廉,不畏人”的处世态度和倔强性格,写出了他与众多官员自私贪婪的显著不同。而蒲松龄的《放蝶》对于性格、罚鹤、罚蛇、罚猫等内容都通通略去,只是简要地保留了王生的籍贯及“罚蝶”“输蝶”的主要信息,而且比《王子凉传》做了更为细致的描述:“每听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审理案件时,严格地对照着大明律令去判定犯罪的轻重,但处罚的方式却极为奇葩,不是罚钱罚粮、罚劳役、罚入狱,而是罚缴纳蝴蝶。放蝶时“堂上千百成群,如风飘碎锦”,用“风飘碎锦”来描写千百成群的蝴蝶在县衙大堂上下翻飞,艳丽迷人,如片片碎锦在风中飞舞。以简洁而形象的笔墨写出了县令王生的不同常道。蒲松龄这样处理材料的去取,除了更能紧扣题目、线索集中、重点突出,也与他的叙述视角相关。蒲松龄的《放蝶》是一篇传奇小说,采取文学的视角、审美的视角,叙述务求幻化,其重点是在写出由“放蝶”而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和人物的结局。如果说李长祥是将“放蝶”作为一个重点事件来写,那么蒲松龄则是将“放蝶”作为整个小说的起因来写。另外,在“放蝶”的原因上,李长祥只用一句“性喜鹤”写出由鹤而蛇、而猫、而蝶的一系列故事,而蒲松龄则是连这一句也懒得去说,这自然引发我们的思考:蒲松龄为什么不写县令王生罚蝶的原因呢?进士出身、身当壮年、贵为县令的王生,真的是像冯镇峦所讥笑的那样是遏塞自然、了无生趣的“儿童之见”,或者如同但明伦批评他这是在“戕物性,且坏法律”?一般而言,作者对某些内容不写,是因为不必言说或者不可言说。不必言说,是读者能够不言而喻,但是三百年来人们仍在各说各话,可见不言并没有自喻。不可言说,自然是指后果严重,招惹灾祸。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巨变的时期:明朝在多年的党争、阉祸、农民起义、清军大举进攻的多重打击下,走向灭亡;清朝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开始了对中原及全国地区的全面统治。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时事变异、人心不稳,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之中。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作家的“写”与“不写”自然也就多了一份时代政治的因素。“即此选择去取之间,已自抱定一种人生观以为标准。”李长祥是积极抗清的晚明之奇杰,蒲松龄也有着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对王生的复杂性和叛逆性有着更多的了解与认识,因此,他们能够从其怪诞的举动中,看出内心的迷茫与彷徨,精神的苦闷与痛苦,行动上的抗争与无奈,带有着更多的理解同情。所以,“此处无声胜有声”,不写反而是最高明的写法。
情节的铺衍。“蝶仙警告”以及“直指使呵责”两个场景,李长祥《王子凉传》、钮琇《觚剩》、龚炜《巢林笔谈》等著作都没有,这是蒲松龄的精心创造,以志怪而传奇,也是《放蝶》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立意不同于其他著作的关键所在。蝴蝶遭受“虐政”,自然前来问罪,但蒲松龄对此的描写却别有一番韵味。蝶女“衣裳花好,从容而入”,突出其雍容华贵,神态安详,所施惩戒也是“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即先让其受到风俗教化的小惩罚,态度平和,语气舒缓,显示出蝶仙醒世救人的菩萨心肠。衣裳的“华好”,步态的“从容”,离去的“回翔”,既突出了蝴蝶的物性神态,又与其醒世菩萨心肠的情感色调相一致。而面对突然而至的直指使,王生遑遽而出,与妻子闺房戏乐时戴在头上的素花却忘了摘下来,于是遭到直指使的严厉诟骂。“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这一细节,既是蝶仙“风流小谴”的具体细化,也写出了王生生性浪漫的另一方面。堂皇的县衙,严肃的气氛,面对决定其仕途命运的直指使,平日散漫的县令此时正遑遽不安,战战兢兢,而王生头上一朵闺中戏乐的“素花”更是使这紧张的气氛陡然增加了滑稽的色彩、温馨的色调。按理说,要照应“先受其风流之小谴”之“先”,自然应该再写其“后”的惩戒,即后来遭受的罢官。但蒲松龄没写,故事在“罚蝶之令遂止”中戛然而止,自然也包含了不愿让王生遭受更多的失败与折磨,同情之心也流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