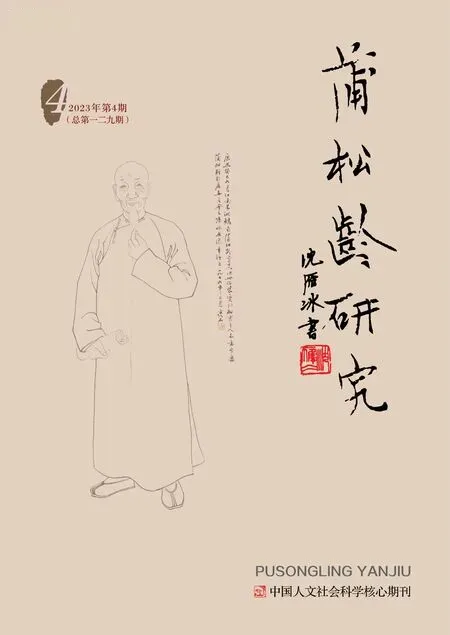《聊斋志异》中“墙”的艺术意象浅析
王小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艺术意象是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其产生是主体思维及情感活动的结果,更是主体内在情思和外在物象的统一。它与具体的生活物象相关,但却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1]657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有言:“《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2]130在蒲松龄的小说中,市井街衢、天上地下以及时空之外的幻境异域,往往一键切换,让人来不及觉察,便跟着主人公入幻出幻了。作为高明的小说家,蒲松龄的行文构思自然是有设计的,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屡试不爽的高招,那就是巧用“道具”,比如主人公的榻、仙人的物件、突如其来的云雾等等。本文要论述的“墙”即是聊斋故事中最常用的道具之一,在蒲松龄笔下有着近乎文学符号的意义。“墙”,本意是砖、石或土等筑成的屏障或外围。《说文解字》释义:墙,垣蔽也。《释名》:墙,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如《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桑。”古文中,与“墙”近义的字还有“垣”“壁”“堵”等。社会生活中,墙关系到人们的人身、财产的安全,是人与人、家与家、城与城的物理边界。“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墙又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这时的墙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3]116-118本文不谈“墙”的社会功能,单就“墙”作为“主题道具”在《聊斋志异》文本中的构成与意蕴进行简单论述。
一、幻境的入口
熟读《聊斋志异》的人都清楚,蒲松龄掌握着他的“聊斋宇宙”,时常要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开启一道“任意门”,为他们打开幻境空间,推进故事情节发展,也为读者开启全新视阈。如同设计中的转场或电影里的蒙太奇,要借用一些设计学理论或技术手段,甚至借助人的视觉差效应,从而达到一种移步易景的效果。蒲松龄选择了“墙”作为文学叙事的媒材,把这个原本只是在建筑物中面积够大、够平整的组成部分变成他的舞台,用文字设计布景,为他的情节构建、意象表达以及读者的文学接受服务。
说到《聊斋志异》中的墙,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画壁》中的墙,那是一面画满精美壁画的墙。男主人公朱孝廉客居京都,与同伴偶然路过一个寺庙,看到庙里的壁画,“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①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皆据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 年版,后文不再标注。他“飘”进壁画中,如愿遇到了垂髫仙女,两人幽会,被其他女伴发现后,垂髫仙女被梳起发髻。其后,金甲神的搜捕、仙女的逃遁、朱孝廉的困局,一系列戏剧冲突在壁画里的“世界”次第上演。蒲松龄把这面壁变作屏幕,但只呈现给读者,朱孝廉的同伴孟龙潭是看不到的。壁画外,同伴找不到朱孝廉,茫然不知所以。老僧洞若观火,“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归?’”同伴这才发现“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老僧再呼,(朱)“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出了幻境的朱孝廉与局外人一同再看向壁画,先前拈花微笑的仙女“螺髻翘然,不复垂髫矣”。蒲松龄让主人公心动身动“飘”进墙上壁画,瞬间把平面的画面变成主人公幻游的立体空间,再以主人公的视角向读者转述他在幻境中的经历,又以壁画外的人的旁观呈现其出境。叙述视角的巧妙切换让壁画里的内部空间和现实中的外部空间微妙关联,又彼此分明,最终以小说之外读者的全景视角完成对朱孝廉奇遇的见证。
蒲松龄赋予了他的文字不可思议的画面感和空间感,使这篇小说有如一件充满作者审美意识的艺术作品。寺院的壁画多是佛教题材,有意思的是,在蒲松龄的笔下,这面满绘精美壁画之墙成为一道“幻由人生、幻中有真”的隐喻之门。“朱孝廉的白日梦,导与随喜的老和尚则心知肚明,甚至是这场有声有色白日梦的设计导演者。”[4]31此文学接受的结论自然要归功于总设计师蒲松龄的匠心独运,把这面“画壁”作媒介,用文字作“幻”,以无意中所切合的艺术场景设计理念,既使得主人公畅游“内外之境”,也使得读者由原本的艺术接收者成为艺术的共同参与者,一起走入“幻境”,最终将这件“跨界”作品交付给一代代的读者接受和批评。
另一篇小说《寒月芙蕖》里也有一面神奇的墙。故事写了济南一个有奇术也颇有些性格的道士,要答谢经常宴请他的官员,地点是大明湖的天心水面厅,时间是隆冬。众人赴约,“则空亭寂然,榻几未设,咸疑其妄”。道士只说他需要借官宰们的僮仆一用,“道人于壁上绘双扉,以手挝之。内有应门者,振管而起。共趋觇望,则见憧憧者往来于中;屏幔床几,亦复都有。”这面墙是道士就地借的,是其法术的掩护,也是他的道具。道士又给这面墙装置了一个新的道具,他画了一扇门,敲门会有应者,开门隐约可见“里面”有人有家具。若说众人通过两扇小门看到的是道士的幻术,那么门内传递出来的美味佳肴却是真的,“既而旨酒散馥,热炙腾熏,皆自壁中传递而出”。道士提前嘱咐僮仆们不要与“里面”的人说话,于是传递酒菜时,“两相受授,惟顾而笑”。这个细节既魔幻,又充满趣味,蒲松龄用一面真实的墙、一扇由虚而实的门,连接“里面”妙不可言的幻境和外面众人的现实空间,建立起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关联,也给读者以奇妙的阅读体验,进而对作者的意旨产生共情。
小说后文,众官宰酒足饭饱,有人感叹如此佳宴只可惜不是六月天时,便很快有僮仆禀报“荷叶满塘矣!”众人推窗远眺,“果见弥望青葱,间以菡萏。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面,荷香沁脑。”这时,蒲松龄用水面亭原本的“窗”代替了之前的“墙”。他借众人的视野,把水面亭的空间和湖面一笔相连,形成一个可观可感的“反季节”空间。这个空间有真实的成分,在场的人可进入,但目之所及的莲叶菡萏却全是虚的。官宰派人采莲,明明“遥见吏人入花深处”,却皆空手而归,只道莲花可望不可得。最后道人一句“此梦幻之空花”作结,小说宛若中国画创作的最高境界,笔断意连,余韵悠长。
《莲花公主》中,蒲松龄则是通过一道道墙把男主人公窦旭和读者带进幻境,即莲花公主家的宫殿实景。窦旭第一次入幻时,“从之而出。转过墙屋,导至一处,叠阁重楼,万椽相接,曲折而行,觉万户千门,迥非人世。”层叠繁复的建筑物是宫殿的气派,也符合蜂巢的构造特点,后文中读者会知晓莲花公主的族群是蜜蜂。无独有偶,1992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制作的同名水墨动画片《莲花公主》,对这段文字的视觉呈现堪称神来之笔,影片中段模拟书生的视角表现了进入蜜蜂王国的过程,强烈的“电影性”扑面而来。全片时长10 分钟,这段长镜头有近30 秒钟。与蒲松龄原文一样,画面通过窦旭的视角来呈现,让观众一路跟着直行、绕行,穿过千回百转的江南园林式的洞门、花窗、回廊,来到宫殿深处,而这也是窦旭梦境的深处。
蒲松龄用文字营造出来的美学空间和艺术张力可以给其它艺术创作门类,尤其是空间艺术场景设计以足够的创作底本和跨界灵感。这里,我们还是着眼于蒲松龄小说写作中对“墙”的运用。蒲松龄以现实世界的建筑物的墙为媒介,以笔墨勾勒巧妙“布景”和“转场”,不断构建适配故事情节的幻境场域,从二维到三维一气呵成,让书中人物与这个空间共同完成作家布置的任务——成就小说主旨,引发读者的审美愉悦和情感共鸣。
二、读者的屏幕
“墙”在《聊斋志异》中的运用还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看上去更贴近它本身的功能,但在蒲松龄的笔下却有了更深的况味。《劳山道士》中,青年王七向往修道成仙,前往崂山求学。入了师门,却只是日日打柴,王七受不了苦,打算一走了之,就在这时,他见证了师父的法术。“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有个客人说这样的良宵应该有嫦娥来助兴,“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墙壁和发光的纸月亮本是二维平面,蒲松龄让活生生的嫦娥仙子从墙上“月宫”飘下来,又让道士与客人移席幻境,“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这一来一去,实现了二维平面向三维空间的切换。宴席尾声,光线暗下来,师父独坐,客人已渺,“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蒲松龄起笔出人意料,收笔轻巧利落,瞬间恢复常态境地。墙还是那面墙,只是贴了一张圆形的纸罢了。
在之后的小说中,墙还有妙用。王七到底是吃不消苦,要回家,临走求师傅传授穿墙术。在道观的墙边,师傅面授机宜,王七“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回到家后呢?“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同样的操作,家里的墙把王七“撞”倒在地,给了他额头上一个鸡蛋大的包,原因自然不是此墙非彼墙,而是他早忘了师傅的告诫“归宜洁持,否则不验”。这两面用来助推剧情的墙,蒲松龄只是以它验证超自然的法术,也就不必费笔墨切换视角、营造场景,只需要写男主角的行动和结果。与之前奇妙的月夜宴饮一样,后文中的墙依旧是读者欣赏故事的妙趣与寓意的屏幕,如同蒲松龄精心设计的主题剧场。
还有《褚生》一篇,男主人公之一顺天陈孝廉灵魂出窍,跟人去逛李皇亲园。李皇亲园实有其处,指明武清侯李伟的园林,又名清华园,接文中的“水肆梅亭”之语,小说中当为李伟之孙李诚铭在帝京城南建的李皇亲新园。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其在北京城南,“以水胜”,还有“长廊数百间”。游园结束,陈孝廉回味同游歌女的诗,“过长廊,见壁上题咏甚多,即命笔记词其上。”他知道了离魂原委,再去李皇亲园,只见题诗还在,“而淡墨依稀,若将磨灭。始悟题者为魂,作者为鬼”。蒲松龄巧借旧时读书人爱在墙上题诗的习惯,以壁上题诗证明主人公灵魂幻游,又以诗句的“若将磨灭”渲染他的离愁,以及人生荣华易逝的幻灭感。蒲松龄让这面墙记录主人公字迹,又让它“淡墨依稀”,仍旧是给读者一面屏幕,却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其中况味见仁见智。
《梅女》写书生封云亭与蒙冤而死的梅女的两世情缘。女鬼梅女初次出场是在白天,通常民俗传说鬼是不能白天现身的,蒲松龄为了故事情节合常理,同样巧用“墙”来讲故事。封云亭白天在寓所休息,“见墙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画,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动,亦不灭,异之。起视转真,再近之,俨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环秀领。惊顾未已,冉冉欲下。”蒲松龄让女主角先以影子现身,在日常环境中墙自然是最合适的背景。身影由浅淡变清晰,逐渐显现出悬梁自尽的少女模样,见封云亭似解其来意,“影居然下”,向封求助,“诺之,则灭”。后来的情节发展中又有鬼妓顾爱卿的加入,她的来去也需墙壁,“以指弹北壁,微呼曰‘壶卢子’,即至”,天亮“入北壁隙中而去”。某典史听说封云亭有鬼友,请他帮忙打听阴间亡妻之桥段,不料封云亭“叩壁而呼”唤出的顾氏,正是典史亡妻,接着阴间老鸨、梅女逐一登场,原来典史就是昧心受贿使梅女蒙冤自尽的贪官。一连串的冲突让小说变得更好看,自然离不开蒲松龄对“墙”的灵活运用。此时的“墙”作为屏幕的功能是单向的,并不呈现墙的内里所代表的阴间,它只负责让阴间的鬼自由出入,带着她们各自的“故事”进入男主人公和读者的视野,如果直接从地下“冒”出来,或是从门外进来,总是少了些文学意趣和神秘感,也浪费了蒲松龄以文字构图造型的艺术造诣。
三、志怪的帮手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到自己的创作初衷:“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5]29《聊斋志异》中确有不少篇幅短小的故事纯属志怪之作,这类作品里,有一些直接让“墙”承担关键任务,如同传统戏剧里的“戏胆”。“‘戏胆’是传统戏剧的一个概念。简言之,是在一个曲折的戏剧中,出现某一物品(如《锁麟囊》中的囊,《拾玉镯》中的玉镯)或某一事物,对情节发展起特殊作用。”[6]439
《单道士》中的道士会隐身,避险时仍以此脱身,蒲松龄妙笔生花,让道士利用“墙”顺便玩了一道实景遁形术。“单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挝,城门顿辟。因将囊衣箧物,悉掷门内,乃拱别曰:‘我去矣。’跃身入城,城门遂合,道士顿杳。”这里,蒲松龄只是三言两语描写道士的幻术,却让二维平面瞬间变三维空间,幻术结束一切如常,墙还是那道墙。《宅妖》中,长山李公家的宅子常有怪事。这天,屋里又多了一条春凳,李公伸手一摸,凳子一下子变软了,“四足移动,渐入壁中。又见壁间倚白梃,洁泽修长。近扶之,腻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时始没。”原本是起保护、遮蔽、间隔作用的墙壁,成了让人害怕不安的怪异事物的藏匿处。《美人首》更加惊悚,一些商人住在京师的客栈里,“舍与邻屋相连,中隔板壁;板有松节脱处,穴如盏。忽女子探首入,挽凤髻,绝美;旋伸一臂,洁白如玉。”众人当她妖怪,捉她,她就会缩回去,但隔壁也看不见她的身体。又是墙壁上呈现的古怪,好在众人合谋砍下了这颗脑袋,没有为美色所诱,否则可能就是另一章《画皮》了。这篇也是蒲松龄以“墙”作关键道具的专属志怪之作。《商妇》中,小偷隐藏到某商人家打算行窃,商人妻独自在家,“既而壁上一小门开,一室尽亮。门内有女子出,容齿少好,手引长带一条,近榻授妇。”商人妻用女子给的长带自缢了,“女遂去,壁扉自合”。壁上的小门、神秘的女子、一场匪夷所思的命案,蒲松龄借助墙壁推动悬疑感,省却了很多笔墨。当然,在这篇同样主打志怪的小说中,蒲松龄不忘给小偷一笔人性之光,写他挺身而出给被冤枉的邻居作证,如实交代了那一晚的所见,这是蒲松龄平民意识的自然体现。
这类故事大概率是蒲松龄道听途说得来,又以小说家的“惯性”和天分,随手记之,随手略微修饰渲染,满足了很多偏爱猎奇说怪的读者,也满足自己姑且聊之姑志之的“黄州意”。
结语
“墙”是蒲松龄小说中独特又巧妙的一种艺术意象,如我国古典诗词中的“红豆”“芭蕉”“杨柳”等一样,既是客观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元素,又凝结了艺术创作主体的生命意识和审美理想。在蒲松龄笔下,“墙”是他构建奇幻之境的入口,给予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以“穿梭时空”的能力;“墙”是他链接读者与文本的屏幕,使得艺术的接受者们有心神入境、感同身受的体验;“墙”是他生活经验和文学造诣的外化,我们更可以透过这些真实的艺术意象,感知到隐匿在一个个故事背后的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蒲松龄。
《聊斋志异》还在创作期间就被手抄传播,乾隆三十六年(1766)青柯亭本刻印出版后,各类版本和一代代点评者、校勘者、仿作者以及各种改编和跨门类、跨学科的相关艺术创作层出不穷,充分印证其跨时代的价值,同时它也会不断有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解读和“再创作”。从艺术意象构成的角度解读分析《聊斋志异》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发现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更多的可能,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更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