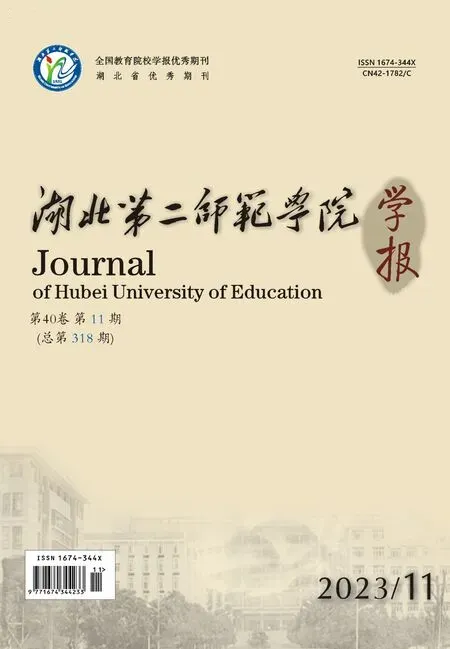GPT-N:“人机联袂”对生命教育的深度挖掘
刘沃奇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
一、“人机联袂”是否打造出新的生命体
人类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问题已达半个世纪之久,进入21世纪以来更呈现如火如荼、愈演愈烈之势。最近甫一问世就火爆全球的ChatGPT 更是令人既惊且恐,茫然不知所措。“AI究竟是不是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再次旧话重提,成为新一轮街谈巷议的“焦点”。针对这个莫衷一是、迟迟没有定论的问题,绝大部分人都给出理性而干脆的回答:AI暂时还算不上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只有极少部分人会情绪化地认为“AI就是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之所以先抛出这样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目的是从生命哲学的视域出发,深入探究人与AI的关系,即: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支撑下的数字时代,人机的交互、嵌套与融合是否会诞生出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说一枝独秀的“技术”本身无论如何发展都很难成为一种“生命”,那么“身体—技术”“人机联袂”或如唐·伊德“三个身体理论”[1]中所说的“技术身体”就很难说它不是一种“生命”了。特别是当“技术”与人的身体及其意识不再有任何“间隙”,其本质关系已呈难解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假如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心力衰竭患者在接受了外科医生的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术后,又起死回生了,那么他的后半生就不再仅仅属于他自己了,那个永久性植入他体内的心脏起搏器也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AI了,这种“人机联袂”所共同打造的身体就将成为一种崭新的“生命”形式。
从这个角度说,AI究竟是不是一种新的生命,端看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嵌入、介入生命并使之延续和进化?只要它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因为它的“存在”而促进或改变了生命进化的路径和进程,就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当然,要论及ChatGPT 及其相关智能技术还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存在”,本文将从现象学——本体论和技术哲学的角度加以梳理。
二、ChatGPT的真相:“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
回顾ChatGPT 的发展历程,可追溯到2015年,当时Google 的研究员发表论文,首次提出机器学习技术中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深度双向长短期记忆(LSTM)。这正是“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技术的开始。LSTM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翻译领域都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其计算复杂度高,耗时长,不能满足实时应用的需求。时隔三年,OpenAI 的研究人员又提出一种基于Transformer 模型的预训练技术——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该技术可以更快地训练深度神经网络,并可以更好捕捉语言特征,从而提高机器学习模型的准确性和精度。直至2022年底,OpenAI研发的ChatGPT便横空出世。
如果只把ChatGPT看作“能与人类对话”的机器人,技术进步的迹象似乎并不显著。毕竟siri、小度、小爱之类工具技术,都可以提供“聊天对话”服务。ChatGPT的“魅力”更多还是技术上的“进化”,其中“大模型”是关键词。
何为“大模型”或“小模型”?AlphaGo就属于“小模型”,只能用来下围棋,至于象棋、五子棋等都不会。其中的底层技术是类似的,但如果要让AlphaGo下象棋或五子棋,还需要给它重写代码、并重新训练。“小模型”不仅需要大量手工调参,还需要给机器喂养海量标注数据,这拉低了人工智能的研发效率,且成本较高。但“大模型”则不同,它是通用的。ChatGPT 的应用场景很广泛,既可以写邮件和文案,还可以写代码、写诗、画画、作曲,甚至可以写论文。
如果说互联网引发了一场“空间革命”,智能手机引发了一场“时间革命”,那么,ChatGPT引发的将是一场“思维革命”或“意识革命”,因为它将改变人类的旧有思维模式,并由此重塑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在ChatGPT之前,人类是孤独的思考者,面对人类文明几千年积累的巨大图书馆,只能想办法提高检索效率。而现在图书馆里多了一位管理员,它包罗万象,逻辑清晰,回答神速,并能综合所有已知知识为人类提供思考路径及行动方略。如果说以谷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在“寻找问题的答案”,那么ChatGPT就直接跃升到了“自主完成任务”。
这场“意识革命”的关键词就是“训练深度神经网络”,ChatGPT之所以亮相即封神、爆火、出圈,就因为它在“人圈”外匪夷所思地说起了“人话”,这便是“深度神经网络训练”的结果。这不禁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话:Man acts as though he were the shaper and master of language,while in fact language remains the master of man.[2]如此冗长的一句,译成汉语既简捷又明朗:“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
这正是本文的题中之义——“人机联袂”对生命教育的深度挖掘将产生不可预料的多义性,“人机联袂”后的生命再也不是“人机联袂”前那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存在”了,他们成了一个谁也离不开谁、彼此共生共进的“新生命共同体”。人在滔滔不绝地说话,或机器在喋喋不休地言语,二者都属神经正常,不足为奇。问题是一旦机器开始说“人话”,并反过来影响和重塑人类思维和意识的时候,一场真正的革命就锣鼓喧天地开始了。所谓“革命”,就是革除“旧命”,生出“新命”。
当然,ChatGPT甫一面世就有人立刻宣布它“翻车了”,因为它无法克服“井喷式”咿呀学语阶段的啰里吧嗦、同义反复、内容虚假、张冠李戴、乃至恶言恶语、胡说八道、带有偏见和三观不正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然而,ChatGPT 再神再火,也不过是一款受制于数据集质量之高下的人工智能聊天程序。目前的ChatGPT 是从GPT-3发展而来的,可以称之为GPT-4。随着该项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进化,那些严重问题就会在未来的GPT-N身上被一一解决。
在GPT-N一次次学习说“人话”的进程中,那些逐步升级、越来越繁复多义的“人话”,终有一天会超越“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生命的任何一次大的进化都必须是超越自身能力之上的一次努力和挣扎。“人机联袂”就是这样一个共生共进、互相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恰恰是“生命教育”的本义。
三、“人机联袂”与“进化大戏”
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以后,“人机关系”已成为技术哲学、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等持续关注的话题,最近几年在教育学领域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议。
相关专家给“人机关系”取了很多新的名头,诸如“人机协同”“人机协作”“人机共存”等等。本文作者更偏爱“人机联袂”的叫法,因为它寓有人机“同台共情”“双主联袂”出演智能时代一场大戏的引申涵义。当然,这也是人类在进阶人工智能之前所能勾划出来的一个较为理想的前景。本文借用“人机联袂”这个称谓论及当下人类发展及其相关教育实践,也有展望未来之意。
更重要的是,ChatGPT的横空出世给早已预备好的“人机协同”“人机协作”“人机共存”这些名头涂上了一丝苦涩意味。之前的AlphaGo还算明火执仗地在围棋大赛中演绎了“你死我活”的戏剧冲突,可到了ChatGPT这里,AI已经开始跟人类友好地聊天对话了,而且还自带碎碎念和吐槽功能。在新一轮的“人机关系”中,它虽然比之前显得更谦逊了,也更亲和了,但是仍然给人类全体都带来了一种莫名的惶恐和焦虑。很多人认为长此以往,一旦ChatGPT发展出了更高级的意识,人类的主体性是否会面临“异位”——即“主客倒置”的危险?
这样的担忧实属大可不必。人工智能毕竟只是人工—智能,它终究还只是人类理智的“造物”,是人类为了克服自身的局限并用以延伸一己欲望的功能性产物。它不过是“人类进化”这场大戏中的一颗新星罢了。既然人工智能是跟人类“联袂”出演,就整出“进化大戏”来说就不该有“你我”之分,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人类生命”的一部分,人类“联袂”AI共同占据舞台或片场的C位。
至于如何给它命名,那将是后世人类的事情。甚至后世的人类还叫不叫自己“人类”也都是一个有待观望和商讨的问题了。正如今天的我们称自己为“人类”,却把我们的祖先叫做“猴子”。假如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真的研发出时光机,令时空穿越成为可能,我们回到浑身是毛的古猿面前,拿着一张现代人的照片问他:他是猿吗?猿一定会摇头否定。果然告诉他这是“人”,而且在未来的时日里,你将跟照片上的这个“人”联袂演出一场“进化大戏”。古猿人一定会惊恐万状地再次摇头否认,说他是他,我是我,这“人”只让我感到惶恐和焦虑,浑身冒大汗。
这既是一场演出,也是一次演化,只有登场先后之分和时间长短之别而已。譬如在“围棋战”那个短暂的片场当中,一直瑟缩在角落里的AlphaGo经过多次试练与鏖战后,终于一点点步入C位,站在人类进化史的聚光灯下。悲乎?喜乎?
悲欣交集也。喜忧参半也。这正是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所要阐明的一种“赛博进化论”态度,他基于数字时代所描绘的那三个连绵不断的“身体”,恰恰是人类历史在生命进化过程中的不断更新和迭代。
在2002年出版的《技术中的身体》一书中,唐·伊德第一次对人类的身体做了三个有趣的区分。国内学者杨庆峰将其归纳为“三个身体理论”,即:物质身体为第一身体,文化身体为第二身体,技术身体为第三身体[3]。
唐·伊德所说的“物质身体”是指本能的、本源的、非理性的肉身。“文化身体”则指由人类文明演变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身体维度,是文化的产物。“技术身体”是指从物质身体到文化身体延伸而来的“第三身体”,唐·伊德将其作为数字时代背景下的人类身体,并赋予其“赛博空间”的虚拟性质。“三个身体理论”继承了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肉身理论”、以及福柯的批判现象学,适时地将“技术身体”作为“第三身体”单拎出来,用以阐述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现实及其大数据技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最新变化。人类鉴于唐·伊德本人自己也承认“身体一”是源自梅洛·庞蒂的“肉身”,因而“物质身体”一词显然不能准确概括“肉身”之真正所指,所以本文将以“本源身体”代替它。同理,既然唐·伊德的“第三身体”特指数字时代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人类身体,用“技术身体”来概括它的内含也带有极大的歧义性和暧昧性,因此本文决定用“数字身体”代替它。
“三个身体理论”的建设性意义有两点:第一,在于它的“三位一体性”,即从“本源身体”发展而来的“文化身体”以及“数字身体”是一个毫无间断的有机连续过程,几乎很难找到“三个身体”之间的严格界限与分野,亦即没有真正的“间隙”,它们是一体的,延绵不绝的。第二,是指“三个身体”之间的互相遮蔽与覆盖,以及更进一步的彼此忽略与否认。比如“文化身体”对“本源身体”的悲剧性打压与限制,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时代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教育体系无所不用其极的“自责机制”。再比如唐·伊德本人所认为的“数字(技术)身体”不具备“涉身性”,因而与“本源身体”失去了有机的连接。
如此矛盾的“分裂性认知”正好体现了今天的人类对待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的偏颇态度。究其原因,就因为人类对“数字身体”的审视缺乏现象学本体论的视野,忘记了思索数字时代的“本源身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至少有一点今天的人类早已达成共识:我们地球人无一不是从其他动物演化而来的,即发展至今的任何一个人类个体的生长,无不携带着生物进化过程中所有的基因密码,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又不断地形塑着生命基因,在这种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中也渐渐形成了生物与自然之间紧密的生命连结。
因此,探究任何生物的现世存在,都不应脱离其漫长的进化史。正如达尔文(1859)本人在《物种起源》中曾经写到的那样:“如果有人能证明所有现存器官不是由无数的、渐进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理论就彻底崩溃了。”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二百万岁的原始人、以及由此上推的各类“动物祖先”,他们在漫长的进化中一直化整为零地潜藏在“本源身体”当中。亦即是说,“本源身体”才是这场“进化大戏”中永远的大咖和主角,尽管它庞大而隐秘的身影时不时会被后世的“枝叶缤纷”和“喋喋不休”所遮蔽与覆盖,但它终究是永在的,不死的,它才是人类进化史这出长河剧中永远处于C位的、当仁不让的大主角。
四、“人机联袂”与“深度神经网络互侵”
当前,AI的“深度学习”能力越来越对我们人类的思维意识构成“催逼”之势,特别是ChatGPT的出现,“深度学习”已经演变成“深度神经网络训练”。这个词猛然听上去虽然不明白在说什么,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也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这不禁让人想起2016年3月,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时留给人类世界的那段苦涩记忆。
一个再也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棋类AI诞生后,世界棋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冠绝天下的AI成为人类棋手们别无他选的最佳老师,它非但可以在每次比赛之后帮你复盘研究败局,还可以让你在完全弄不懂AI为何要这样下棋的情况下,通过死记硬背AI的决胜“棋谱(标准答案)”而打败其他人类对手。
此种“教与学”关系的演变和逆转,同样让人欢喜让人忧。悲观者以为,从此以后人类把子对弈这件事就成了一项异常枯燥而乏味的活动,因为棋手一开局都按死记硬背下来的AI的套路展开,它因缺少变化而失去了汩汩流淌的生命气息;乐观者则认为,棋类AI在挑战人类智商的同时,也为其打开了一扇视野更阔大、更明亮的窗口,人类由此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以及“千变万化”才是生命进化的根本“内驱力”。这不也正应了我们中国古代经典《礼记·学记》所说的“教学相长”吗?“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为了学习AI的下棋思路,我们人类棋手向AlphaGo求教,它的意识便慢慢进入我们的意识,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吗?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们,我们的意识也不再是原来的意识,而是我们与AI的混合体、综合体,具有双向融合的特征。
由此出发,我们再回顾一下ChatGPT的“深度学习”——即“深度神经网络训练”,既然它是一款“对话聊天程序”,这种“深度神经网络训练”就绝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双向的、彼此嵌套、互相影响的“洗脑”活动。正如现如今的人类棋手都要追随AI的下棋思路一样,我们人类在与ChatGPT气氛融洽的“友好交谈”中,难道就一点新东西都学不到、不发生任何改变?倘若我们能够反向细加思量,是否会从中瞥见“深度神经网络互侵”的潜在苗头?正是这个“互侵”或“互嵌”,才构成“人机联袂”的本质性存在,难道不能断言它不是一种新的生命体?
这不禁让人再度揣摩海德格尔的那句至理名言:Man acts as though he were the shaper and master of language,while in fact language remains the master of man——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
“以哲学为背景的技术实践,需要以哲学的视角来思考技术的本质。”[4]事实上,面对在“人机联袂”讨论中出现的各种博弈与冲突,国内已有相关专家学者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并适时提出了颇具远见的“联袂方法论”。为实现当下“人机关系”的共在共生,促进教育技术沿着和谐有序之路发展,于英姿和胡凡刚认为,有必要从存在主义视域出发,以“联袂价值论”彰显“人机共生”的存在意义,并以“联袂过程论”剖析人机“共在共生”的种种真实形态,从而构建人类未来教育的新图景。[4]
另有学者刘钊和胡凡刚认为,在“人机联袂”的境遇中,教育的目的应该超越纯粹的价值实现,转而重点培养能进行生命意义审思的人。为达此目的,教育也必须借助“人机联袂”的技术条件,“将真实境脉与虚拟境脉有效整合,通过充分的信息交互引发主体对多元生命意义的体悟与融合”。[5]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技术更是一种解蔽方式。“惟当我们让目光停留在这个基本特征上时,现代技术的新特质才会向我们显示出来。”[6]这才是所谓的“解蔽之域”,亦即“真理之域”。
五、数字时代的生命教育
人所共知:教育学即人学,人学就是生命哲学,而生命哲学又是“生命教育”的核心和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命教育就是生命哲学的现世伦理体现。“生命教育”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在1968年提出的。他认为,“生命教育是一种以提升学生的精神生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7]而“精神生命”又为何物?它是作为“肉体生命”的对立面被提出来的吗?显然不全是。在杰唐纳·华特士看来,“精神生命”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特质,或者该叫“天赋异禀”,它也像“肉体生命”一样具有特定的生长周期。如果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具备了某种异于他人的天性,生命教育要做的就是不断发现并挖掘他的这份天性。
正如中国古代经典《中庸》一文开宗明义阐述的那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教的关系即是人之天性与教育的顺承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道”,它指的就是人类拥有“肉体生命”这一天命的同时,也顺应天道予人的“精神生命”。所以,“人道”是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生命意义,也就是对“精神生命”的不断更新迭代。由此,生命教育即可理解为先天生命与后天教育的无缝连接,即“本能生成”+“主动进化”,这恰与西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生命哲学”不谋而合。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是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他继承了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思想的核心,认为世界的实在和本源既非精神,亦非物质,而是一股连绵不断的“生命之流”,是生命的“创造冲动”;整个宇宙都是由这个“生命之流”和“创造冲动”派生出来的。“绵延是生命本质的体现,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和把握生命存在的绵延,生命是一种向上的冲动,生命的本质是创造。”[8]
这句话中涉及到三个关键词:“绵延”“直觉”“创造”,充分体现出“生命”的三个特质。“绵延”是生命特有的存在方式,“直觉”则通往本能和本源,“创造”则是一切生命的终极呈现。因此,世上万物,无时不在流动,无时不在绵延,无时不在创造,无时不在进化。在这场绵延不断的“流变”中,过去包容在现在里,并且向未来“持续地涌进”。在这种连成一气、宛如大河奔流的过程里才有生命的永恒性,它永远是生机勃勃,奔腾不息,绵绵不绝。“生命冲动”无时无刻不在进化,即创造自身并迭代更新。这种进化不是从同质向异质的过渡、或单纯同质的相加和累积,而是纯粹的“质”的创造过程,是“质”的不断飞跃。为了区别于斯宾塞的机械的进化论,同时也为了反对达尔文主义用物质的机械组合和外部力量的选择来解释生命的进化,柏格森把他的生命进化称为“创造进化论”。
虽然“绵延”是生命本质的体现,但想在现实生活中准确把握这种绵延状态却绝非易事。帕格森强调,必须通过“直觉”深入到生命的最深处去体味延绵不绝的“生命之流”,才能探知生命的本质和真相。“直觉”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是一个举足轻重、至高无上的概念,它是同理智相对立的一种思维,人只有具备了这种“直觉思维”才能真正摆脱自身与外界的利害冲突。反之亦然,只有成功摆脱了自身与外界的利害冲突,人才能真正拥有“生命直觉”。“所谓直觉,就是一种共感(sympathie),通过共感我们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对象中那独特而又无法表达的东西融为一体。”这就与现象学的“本质还原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
在帕格森的生命哲学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理智”,它是作为“直觉”的升华而不是对立面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类具有本能和理智两种精神活动方式,其中的“理智”代表了生命进化这一方向的最高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理智”高于本能,而是指二者把握“实在”的方式不同。意识越是理智化,物质就越是空间化。“理智的特征就是天生不能把握住生命。”[9]
柏格森虽然批评理智迂回在事物的外部,无法直达实在把握“绵延”,但他并不断然排斥理智。他认为理智是对事物关系的认识,有助于人适应环境、维持生存、确立主体性。所以,柏格森的“直觉论”与传统的“直觉论”并不完全相同,它并非指单一的天赋本能,而是指本能与理智的有机融合和互为补充。
如同直觉一样,本能也是一种“共感”,是本能者与其对象或环境的一种“同频共振”,主要表现为本能者之于对象和环境的天生认知与后天适应。人类因本能而存在,但因理智而进步,缺一不可,偏执于任何单向的一方,都是对生命的误读,对教育的误导,因而也就阻碍了生命的进化与生长。人工智能及其ChatGPT的诞生,首先是理智的进步,但“人机联袂”产生的新生命形式则是一个与“本能(本源身体)”相连接的过程,这才可以被视为生命的“绵延”。
在《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生而为人的意义》一书中,迈克斯·泰格马克对人类的终极未来做了大胆畅想,从近未来直到万年乃至亿年以后,从“可见的智能”潜入“不可见的意识”,重新定义了“生命”“智能”“意识”等概念,并澄清了常见的“人工智能误解”。他将生命的进化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生命1.0、生命2.0 和生命3.0。人类的生命已经走过了1.0生物阶段和2.0文化阶段,接下来生命将进入“自我设计”的3.0科技阶段——人工智能与有机体生命整合而成的阶段,即“人的技术对生命的进化进行了干预。”
泰格马克的“三个生命阶段理论”与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如出一辙,虽然面世迟了15年,但比后者更加讨巧和微妙,也带有更强烈的生命哲学意味。他所说的“生命3.0”,就是指“人机联袂”进入高阶的终极生命形式,即由“深度神经网络互侵”步入“深度神经网络共融”,这才是“学习”和“教育”的最高境界。
六、结语
综上所述:“AI究竟是不是一种新的生命”确实已成为一个没有多大讨论价值的问题了,因为AI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介入或嵌入我们的生命,并开始以某种隐而不见、匪夷所思的方式改写着生命进化的路径。它已经演化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就因为此种生命是“一个既能保持自身复杂性,同时又能进行复制的过程。”[10]
“人机联袂”技术是对生命哲学及其生命教育的一次大力拓展和深度挖掘,它正在将人类的生命从“被动进化阶段”推入“主动进化阶段”。即从“深度神经网络训练”到“深度神经网络训练互侵”、再到“深度神经网络训练共融”都是对人类思维意识的一次次刻意改写和升级。这既是“意识”的升级,也是“记忆”的演化,进而也该被视为“生命”的进化。只要“可见的智能”潜入了“不可见的意识”、并对其实行了有效的干预,那么新的“生命”就一定在酝酿,新的世界也即将诞生。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教育、生命哲学、生命记忆和生命进化都可被视为同义词。所以,人类及其亲手发明的人工智能(AI)大可不必将彼此看成“异己”或“异类”,更不该如惊弓之鸟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数字时代的“人机联袂”最好被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角色扮演游戏(Cosplay)。在这样的认知下,“人机联袂”更像是一种“数字孪生(Digital Twin)”,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演化出神秘的“生命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