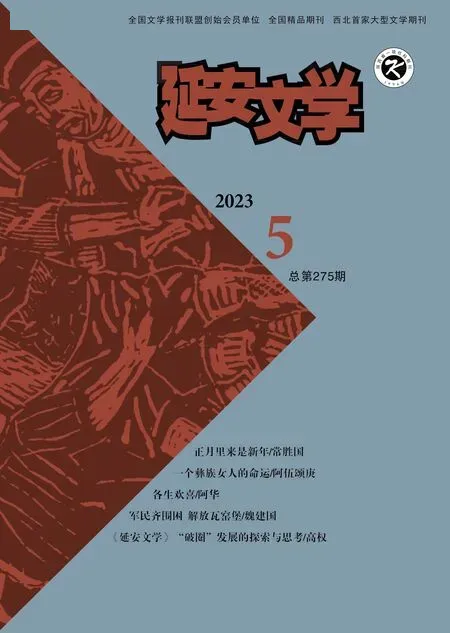出 家
施佩清
一
很怪,桥建在那里。
怎么看都很奇怪。
仅仅是为了连接南北两个乡,一条三十米不到的河道,要用到这样高大骇人的钢材结构,怎么看,都很奇怪。
李里即使站在距离那里很远的地方也能一眼就看到桥架上的弧形拱背,那样远远的,亮着救生衣一样的橙色,漂浮在远处的天空中。
“怎么建了那样一座桥”以及“什么时候建了那么一座桥”……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在心里开口好几次,不知向谁询问。问题抛到母亲这里,她只说:“不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猜这座桥是为了城市扩大而建,在南边那个即将开始发展的城市里,来了打印店、写真店、电影院,还要建楼盘、建中学、建小学……李里上过的小学,即将要搬到那里去了,不用像小时候一样,穿过老街,路过柳树、枣树,经过澡堂,沿着高高的河岸往前走上好远好远……
这个问题,原本问父亲更合适,他年轻时候是卖货郎。从前他的口头禅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在李里家的饭桌上,饭菜冒起的白烟中,外面世界在父亲的描述之中如同海市蜃楼,被李里大筷夹起,狼吞虎咽到肚子里去。父亲低头划亮火柴,在烟雾升腾的后面,李里看见父亲眯着的眼睛,他说起那条河的由来,父亲说,它叫“胥河”。知道是哪个“胥”吗?父亲的食指点在桌上,想了想,落不下第一笔,最后说就是“伍子胥”的“胥”。
然而现在李里再问起来,他是什么也不知道了,父亲就是在这样的遗忘中,越来越显出老态来。
头顶上的葡萄架子是父亲四十来岁时架的,是父亲带回来的外来物,据说是外面的品种,比本地的葡萄更大更甜。葡萄种在院子的南角,置了足有一张床大的地方,不是就地挖的土,而是从外边铲了回来自己架高的。那时候父亲正当年,和李里如今差不多的年纪。春天里,父亲穿着白色背心,用扁担挑了两个旧簸箩,一前一后,从田边运土,一筐一筐倒下,在院里的角落堆成尖尖的小山,用铲子打平后,又夯土砌砖。李里拿着铲子,提着一桶水跟在父亲后头,看到他一扭一扭甩着黝黑粗壮的大臂,屁股均匀晃动,那滑稽的样子——李里在后面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不知他在笑什么,在前面骂了几句,也笑起来。
几年后李里多大了?应该还在上小学。小学的末尾,他坐在夏天的院子里,头顶上是绿油油的葡萄叶子,青葡萄胆颤心惊地在阳光下悄悄剔透,阳光穿过叶与叶的罅隙照到庭院的地下。走过时如同置身水底,斑驳的光影如游鱼流动,树影如藻荇交横,温柔起伏。他们仰头,看见明亮的叶子上不时有麻雀飞过的身影,它们走动,小小的爪在竹架上轻轻地试探,发出微弱的“沙沙”声响。何时鸟头突然在叶间攒动一下,眨眼间鸟喙已回,那盏葡萄的一只灯泡就熄灭了——一颗刚刚亮起的害羞的葡萄。
于是父亲用废弃的茅草扎了稻草人,让它戴上那只破绽开来的旧草帽,穿上一件破布衫,蓝色的粗布料子,也是父亲淘汰的装束。这只稻草人成日背对阳光,双手与身体呈一个十字,沉默地抵挡鸟儿的侵袭。
葡萄越来越大,父亲每日归来,放下扁担与簸箩后,就脱了汗衫,来院里放井水洗脸,喝一海碗凉开水,止了汗,等到尿意上来,解了裤子“唰唰唰”地去墙边灌溉葡萄树。
盛夏里他们全家看葡萄成串,上过波多尔液后不久,它们生长得越来越着急,不久就紫里泛青,一串串葡萄拥挤着,越来越沉地吊在了头顶上。葡萄树体的枝干不过一拳粗细,竟也支得起满园的果实。李里紧张又欣喜地仰望,眯着眼睛挑选。父亲赤膊了上身,架着简易的木梯,叼着烟站在上面,像是一个富有的国王清点臣子的进贡。父亲不时歪头与李里确认,选择比较,然后才将那把又黑又沉的大剪子伸过去,李里随着上面人的动作挪移,伸高菜篮……“咔叭”一下,父亲利落地剪下一串沉沉的葡萄,弯腰把它们小心地放进篮里。等到菜篮提不起来,李里就以双手支撑举高,凑满一篮子,放到井水里去浸……
如今父亲就坐在这满院的竹架下,在葡萄撤场后的空落落的庭院里,晒着太阳。
它们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枯萎的,李里找不到与此有关的记忆,也许是几年前,也许是十几年前,自从父亲身体不好就没人侍弄它了。李里也过了期待葡萄成熟的年龄。母亲不是养花养草的人,原先葡萄生长的土壤换上了一簇绿油油的小葱,头顶的葡萄藤早已晒干掉光,一阵风过,“咔咔咔……”排排竹架就颤巍巍地在风中冷地哆嗦一下。
父亲坐在午后的阳光里,忧心忡忡,又一次说起他的梦来。
那是一个陈年的梦了。
在父亲的描述里是个大雪天气,他用小时候给李里讲民间神迹一样的语气,带来冰天雪地中的回声。父亲光着脚往前走着,穿着他那件早已丢失的黑色棉袄,是他冬天卖货时候用来克风的那件。四野里一个人都没有。在早晨四五点钟的光亮里,父亲往前方走着,梦里的声音指引他向东,向东,他就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着,每一夜,每一场梦,父亲在雪地中远行……寻找那座小庙。
冬日阳光温暖,然而终究是冬日的阳光,温吞吞的暖意浮荡在李里的眼皮上……李里感到困倦,有一搭没一搭的,他问父亲,母亲是什么想法?
“随他去。”她的嗓音仿佛在风雪中远远吹来,在他们耳边擦过。
父亲已经决定了,他说,这次叫李里回来也是因为这件事。父亲是固执的,他的固执里带着长途跋涉之后的艰辛疲惫,卷挟着冬日的云雾低低地从远处的田野掠过。
父亲说,我肯定要去那里的。
再考虑考虑吧,李里说,或者再打听打听,是不是有什么说法?
父亲拒绝说更多了,如果儿子不能陪同,那么他就一个人上路。
李里想了想,半天才说,无论如何,得有个目的地吧。
到了就认得了。父亲说完,久久地沉默了。
……
李里侧头看父亲时,他已经睡着了,可能夜晚少眠,不足的部分就要由下午来补齐。他的头发如同猫的胡须,根根惊醒,雪白稀疏,头皮也开始泛白发粉,像婴儿皮肤一样的颜色。父亲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老得没了力气,没了精神,只剩下固执,与日俱增的固执。
二
李里是第一次走得这么近看这座桥。下面栏杆是蓝色,上面的高架是橙色。它这样的新鲜时髦,带着十七八岁的年轻颜色站在这里,对比两边河岸破落的旧房子,像个完全的外来者。是哪个粗心的城市孩子遗漏在此的一块积木也说不定,旧河道提心吊胆地戴着这个巨大的不属于自己的帽子,别别扭扭地站在了这里。
李里点了支烟。
晚上十点多钟,乡里家家户户早已闭门不出了。路灯只亮了几盏,又被行道树的影子挡下不少,照不亮半条街,远远看去,一阵亮,一阵暗,纱帐一样的昏黄后面是无限的黑暗……只有桥上是全亮的,可能是新建的缘故,桥墩向上打着灯,穿过了漫漫的黑夜,笔直地向上扩散,与高架边缘向下探照的灯光穿插,一来一回的黄色光芒中,擦出些缱绻的意味,连浮荡的灰尘都清晰可见。然而河面是黑的,更远处,黑水像铁一样凝住了。只能看见桥墩上钢的骨架被光凛冽擦过,纵横交错,疏疏朗朗,看得人发冷。
原先那座石桥又短又粗笨,但也知道在底下一边各辟出一个桥洞来,方便叫花子在洞里安家。夏天洞口拉上了旧粉花的帘子,一到晚上,里面就透出烛火的亮光,等到冬天,蓝色的被褥取代原先的薄布,抵挡风口,堵得严严实实,只看到影子。每当李里上学下学,总要看看桥洞的装饰,帘子换过几次,却从没看见过里面的样子……
杨梨就是在那座石桥上走过来的。她是一个漂亮如狐狸般的女孩,有狐狸一样的眼睛,狐狸一样的娇媚,狐狸一样的神秘……然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小学时候了,李里想如果再见到,他可能都认不出她了。
当晚杨梨如狐狸一般钻入他的梦境,醒来后除了旧时学校的窗户轮廓与黑板阴影模糊的浮现,李里什么也不记得了。他只感觉到暖暖的,梦境里,他们似乎是相爱的。
家里的老座钟“铛—铛—铛—铛—”地划亮黑暗,四点的钟声奄奄沉没下去后,母亲中断的呼噜声又跃跃欲试地拉响了。母亲说自己是个从不做梦的人,李里从小到大,确实也从未听她说过做了什么梦。对母亲而言梦境这种东西不存在,睡眠就是上下眼皮闭合,夜夜鼾声,页页空白,醒了就醒了,干脆明亮。而父亲的梦是忙碌的,父亲的梦境中有无穷无尽的呓语,李里留心听了会儿,窃窃如耳旁风,像是某种失传已久的方言,父亲就是用这种方言和梦中人长长地交谈着,打听询问着他要去的目的地。
李里在半睡半醒之中,辗转反侧,他已经很久不和父母同睡一室了。与圆子分床后,李里总是一个人睡,他惯常失眠,一到深夜,就像赤身裸体睡在时间的防空洞中,婴儿一样蜷缩着身体,时间的风吹彻在头顶,他总觉得冷。如今回到少年时自己的这张小床上,罕有的,在覆盖着时间的香灰之下,他找到一点余温。李里一动不动地储藏着这难得的温暖,他想这或许是关于杨梨的梦境带来的。
许久不见了,将近四十,她应该早已结婚生子。李里依据不多的一点记忆拼凑出一个成年的杨梨,他在父母起床之前的一个小时里竭力虚构出一个与她有关的假想。她为他出轨了,他在某间窗帘紧闭的房间之中覆在她的身体上,他试图与她对视,可是这么多年,他早已忘了她的长相了,他从来也没敢认真看过她的眼睛。她会伸出一只手蒙住他的视线吧。李里把手盖在眉毛与鼻尖,眼皮在温暖的黑暗中颤动着,他放轻了呼吸,将这想象进行了许多次,许多次……但无论如何,他的身体像是一座死火山,一点反应没有。
当钟声在疲倦之中敲响五下时,清晨降临了,没一会儿,他听见母亲在黑暗中打了一个好大的哈欠,拖着睡眠的尾巴,她摩挲着从暖烘烘的被窝里坐起来,窸窸窣窣地穿衣服,一件一件。父亲不久也醒了,他一醒就要够床底下的痰盂,李里等待了好一会儿,才听见父亲的喉间轻微地颤动一阵,像是小小的一声埋怨,“呸——”他吐了一口痰。
父亲的声音浸透了早晨蓝色的静默,雾霭沉沉,今天是个雨天。
“因为是雨天,所以晚上走路走得很吃苦,挑着担子跑了半天,发现在原地打转。”父亲与李里坐在堂前,两人看着纱窗外的雨,风来一阵,雨就细细密密地被吹落一阵。
雨天没法出行,一出去就是泥泞,飞虫一样的小雨落在人脸上,湿湿的睫毛,模糊的视线……如果要走,也等一个晴天再走,大概是哪里知道吗?
往南京?芜湖?郎溪?宜兴?还是往哪里?总要有个地方吧?
都不是,在东边,看到了就知道怎么走了。
父亲抱着暖水袋,看着屋外阴雨的天空,他的目光好像已经丈量了雪地,赤脚走在干净冰凉的白色大地上,四野空无一人。
母亲去打麻将了,李里一时沉默,家里静悄悄的,有猫在屋顶爬过,瓦声轻动。卧房里老旧的钟声敲响在父亲的脚下,“铛——”是半点的钟声,意犹未尽的暂歇,在这震荡里他看见父亲一步一步,在雪地中越走越远。
母亲直到四点才回来。她打了一把巨大的花格子伞,喜笑颜开,这是在南边赢了钱的表示。她胖胖的身体在积水的院子里跑过,脚尖一颠一颠快跑了几步后,母亲气喘吁吁地走到廊下,甩一甩伞面,让它花朵一样开在地上,拍拍身上的雨珠,走进来,母亲说:“我听人讲了一座寺。”
她听人讲了一座寺。
建在桥的南边……
她是在棋牌室听说的。她把父亲的梦与颓然归于迷信,她们打麻将的人那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母亲举了几个他们知道的人名。之后比起远行,李里觉得这是更方便可行的,他们问父亲的意见。他这一辈子跑遍各乡,听说了太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已流进他的血液成为骨肉,他永远是宁可信其有的。
三
清晨五点钟,李里开车打桥上过。
在这座巨大的桥架下,钢管平行斜出,根根竖立,纷纷乱乱,向挡风玻璃倾轧下来。
父亲坐在后排,循着以前的习惯,他的肩上挑着两簸箩满满的记忆,它们太重了,沉沉地压得他开不了口。母亲同样在后面,她要欢快得多,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她向李里提前透露她要许的愿望,一二三四,条分缕析,最重要的是希望李里的妻子——圆子,早点生孩子,上天保佑,一个大胖小子,那她就什么也不用烦啦。
李里没有打断她的这些幻想。
他觉得自己是不被那些愿望所容纳的,神、佛、菩萨,容纳不了他,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他不信,也不能相信。关于这一类的印象,于李里,是阴影一样的存在,是十五岁那个冬天的早晨,是脚下这条路,是在一年一次“出菩萨”的早晨,同样是他因为梦见杨梨而遗精的早晨,是他站在请神的队伍中挥动旗杆的清晨,杨梨站在他的身边。
队伍里有中年男女,也有像他们一样的青年男女,不论年纪,脸上都搽了红红的胭脂和口红,个个举着高高的彩旗,怀着对以后人生顺利的愿望加入进来。从他们乡出发,途径周围各乡,热热闹闹地迎神送神。
“呜哩啦呜哩啦”,唢呐吹成的调子起头,“庆庆呛,庆庆呛”的钹声跃跃欲试地终于打起来了,乐器的震颤声音随着纷乱的步伐,在拥挤的人群中流水一样地滚动起来,两边围的都是人。喜气洋洋的笑脸簇拥着这支又长又窄的鲜艳队伍,那欢闹的人声与音乐一样,也与队伍里男女腰间的腰带一样,绿得耀眼,红得绮丽。
人们的脑袋一排排传递向后转看,远远地,看见远处镂空的小轿子过来了,由儿童扮成的“菩萨”化了唱戏一样的浓妆,目不斜视,看着前方。轿子下面,四位穿着黄衫黄裤,头上戴着滚红边黄缎帽的汉子,“呦呵,呦呵”地喊着口号,颠着轿子往前走,后面盛装的队伍慢慢地跟了上去。
李里的眼前掠过两边各色的面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拍巴掌的,大声喊话的,举着小孩的,划火柴点烟的……
他被音乐与热闹还有青春期的躁动所鼓动,有那样多的话呼之欲出,蓬勃旺盛,而杨梨是那样难以取悦,为了逗得她的一点笑,他就大放厥词,调侃队伍中的人,路边的人,滑稽的装束,最后他嘲笑神……他说了那么多的字与标点,咽了那么多的唾沫,口干舌燥,杨梨才勉强转头对他笑一笑。后来他把自己和她都说累了,等到周围村落全部绕遍,回到乡里,他筋疲力尽地看杨梨回到她母亲身边的时候,后面的中年男人意味深长地告诫他说:你讲了那么多不敬的话,是要被责罚的。
你会被责罚的。
李里就是在那一刻感到自己落入了人生的诅咒,他在长久的絮叨之后感到对自我的厌烦,这种厌烦让他感到这天是杨梨在他生命里设下的一个埋伏,比起被神诅咒,他更觉得是被杨梨诅咒了。多年后,他已想不起杨梨的长相,却还是能够清楚记得那年那人的那张脸,又黑又瘦,一张干巴的男人的小脸,意味深长地洞穿了他的从前与未来。这张脸后来与为他诊断的男科医生高度重合,他也是这样意味深长地向他宣告他的“性功能障碍”,他在那一刻久违地想起多年以前。原来暗示早已埋伏于此。
什么寺要建在岛上?
如烟如雾,人们看见蒙蒙细雨中的小岛,都放低了声音,等远远划来的小船。
父亲在冷风中任由雨丝飘落,他抱着这一天都要寡言的固执等待着,生怕有谁惊扰了这层结界。母亲早早与旁边的妇女聊起天来,她们用交换秘密一样的声音交换愿望。
李里与母亲一同将父亲扶上了船,加上船家,凑齐了九个人才慢悠悠地向岛上划去。天上的小雨细如灰尘,李里撑伞遮住自己与父亲,而母亲自己遮一把。船上的人都如同考试临近的学生一般静默。只有两个青年男女小声地说:“这船不要钱倒是挺好。”被船家听见了,喜气洋洋地说:“渡有缘人呐……”
于是在这雨丝飘打的河面,一船人像是成了诺亚方舟上的幸存者,都默默裹紧了身体里的温暖与心愿。不过五分钟,他们一个扶一个小心翼翼地下船。
“诺亚”开口:看着给船费,不论多少,全看心意。
有人给五块,有人给十块,李里给了二十。
“去吧!”母亲劝李里,“来都来了,进去拜拜。”
李里搀着父亲跨进了门槛。
寺是新建的,毫无疑问,还有重重的新漆味道。画栋飞甍,一切仿古,刷成朱红色,扁扁的一大间,中间开着大口,一进去就是神像。他们遵照僧人的指示,先磕头,再去旁边一间封闭的小屋里请愿。人是要一个个进的,堂厅里如考场一样安静。磕完了头的人就静静地站在小屋门口排队。到父亲时,他以一种虔诚的神态阻止了母亲的搀扶,也不要李里的陪伴,自己进去了。之后是母亲。
轮到李里时,他掀开帘子一看,里面端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蓝色羽绒服,戴着老花镜,见有人进来就一脸严肃地放下手机,口中默念了一句什么,然后递给李里一个本子,让他照着前面人写的抄。李里拿起笔,看到父亲端端正正的名字下面,是母亲歪歪扭扭的名字,他跟着写了名字,后头又画上了100 的字样。
“一百元。”男人说完,从底下掏出一个透明的钱箱,里面已有不少红色的钞票,“或者微信支付宝也可以。”钱箱上贴着一绿一蓝两个二维码。
“必须要给吗?”
“不能骗佛的啊。”男人头也不抬,拿起手机。
李里出去了。
除了他,父母都交了一百,这让他有点恼火,想到一些忌讳,终究又闭了嘴。
母亲倒是乐观,她安慰李里,也安慰自己,求个心安,哪里还不花这两个钱?
父亲尽管觉得上了当,却再没说什么。回去之后他就小病了一场,他这两年本来就缠绵病榻,母亲不以为奇,她是强壮有力的,她有那样令人羡慕的精力,上午洗衣服做饭,下午打麻将,晚上看电视,夜里鼾声震天。
雨下了三天,父亲就病了三天,因为头昏与梦境的双重折磨,他在夜里发出低低的叹息。
李里走不掉,他在电话里对圆子说,再等等吧,或者钥匙我先快递给你?
圆子知道他心情不佳,于是也没打电话再来催。
父亲躺在床上,李里在房间里陪着,他尊重父亲的节俭,灯总是关着。房间里的木门,米缸,电视,床,木桌,板凳,座钟,拖鞋,窗架,插销……在灰暗中拖着长而潮湿的影子,它们来自多年以前,有的是父亲卖不掉的陈货,有的是父亲在进货那里带回来的处理品。一样一样,一点一点,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拼凑出了家的轮廓。
父亲那两只装小百货的大簸箩至今吊在卧室屋顶的吊钩上,从前里面放了木梳、纽扣、歪歪油、顶针、鱼钩、红手绢……为了不落灰尘,晚上父亲回来后,总是用两块粗布小心地盖在上面。旁边放着褐色的磨得发亮的扁担,它的中间有个大大的黑色斑点,轻微地拱起,像是一个脸上有着胎记的丑陋老人,默不吱声地靠在墙角。天还未亮,李里起床刷牙时,它已经随着父亲出去了。而今两只簸箩还在等待主人随时将它们解放下来,一前一后地把它们挂在扁担两边,穿透晨雾,从清晨出发。
里面早已空空如也,李里看看它们,又看看房间的各个角落,他没有看到那个老扁担。
父亲在专心听外面的雨声,秒针“咔嚓,咔嚓”地擦动着小小的步伐,一个钟好长,分成六十个分,拆成三千六百个秒,三千六百个“咔嚓”。
母亲在外面厨房叮叮当当地拿缸子,择菜,煮饭,切肉,往烧热的油锅里倒油——“哗啦”一声,世界喧腾,湿漉漉的炊烟在雨中袅袅散开。
父亲浑然不觉。
饭桌上母亲问李里:这两天生意忙吗?圆子一个人顾得过来吗?
那间卖二手手机的店铺归了圆子,离婚协议书已签,接下来他和圆子要分房子,分车子,分财产,清点许多东西,幸好没有孩子,倒也省事。李里面对这些无穷无尽的烦恼说:“城里的生意不打算做了。”
父亲的目光落在李里的肩膀上,半天没有说话,只是用鼻子轻轻地呼了口气出来。
四
李里是在桥上遇见杨梨的。
开始的时候他还没认出来,因为长相大不同了。
她胖了好几圈,穿了一件鹅黄色的收身羽绒服,腰间的肉一圈两圈地鼓囊出来,她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两边脸颊被太阳晒得通红,虽然脸胖了很多,年轻时尖纤的下巴也圆润了,但那种漂亮女人才有的,眼角上扬时漫不经心的风流神态还是让他认出了她。
李里当时正从桥的南边过来,为了把房子钥匙快递给圆子。回来走到桥中间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胖女人杨梨。她正在用家乡话和人寒暄,旁边站着个不耐烦的男孩子,高高瘦瘦的,后来他猜是她的儿子,因为面孔,尤其是眼睛,双眼皮一模一样。
李里原本应该像自己少年时那样故意在旁边磨蹭一会,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因为直到十米开外了他才反应过来那人是杨梨。
毕竟是将近新年了,虽然不是逢着会场,但一日一日,街上渐渐热闹起来,去了外乡的人回来后先上街,本地人为置办饭菜也要上街。街上的小摊贩抓住这一年一度的商机,卖春联、卖炸串、卖绿植、卖棉花糖……什么都卖。人们哪怕什么都不买也乐得逛一逛,上一次街,要遇见多少个熟人,谁碰着谁都像是碰见一个惊喜。李里转了转,最终买了几张“福”字和对联回去。对比以往的价格,他觉得肯定是买贵了。
春联父亲以前是卖过的,就在他们乡里,父亲在街上摆了一个小摊,卖对子和“福”字。李里正值少年,从镇上中学放假回来,就要在街头看店,不是怕有人偷,是因为联子轻,要用砖头磕,用夹子夹,一不小心就会被吹上街去,他要跑着捡回来。不停有同学认出李里,小学的,中学的,远远地对他笑一笑,或者走近了打个招呼。人家的目光在一地的红色春联中检阅过去,父亲看他们打招呼,知道是他的同学,就冲对方笑笑。李里觉得很难为情。
不忙的时候,父亲给李里钱买东西吃,或者劝他去街上逛一逛;忙的时候就顾不上了,他会嫌李里找钱太慢,拿错了东西,踩到了红纸。骂得多了,李里就沉着脸坐在凳上,人家问他对子多少钱,他故意一声不吭。母亲在饭馆里帮厨忙碌,等到下午两三钟客人少了,才匆匆给他们送来饭菜,他和父亲把三只温热的铁缸子凑在小矮凳上,一人捧一个碗,把菜夹到碗里就着米饭往嘴里塞,他们和冷风比速度,慢一点饭菜就要凉。肚子茫然,前一刻还饿得咕咕叫,下一刻就被胀得滚圆。要是有人此时来问价可太不识数,父亲放下碗给人拿春联收钱的工夫,饭菜就凉透了,冰冷的饭菜吃下去口舌一颤,喉管冰凉,不管不顾吞到肚子里,成了个冷疙瘩。
父亲后来说,他的胃就是这样吃坏的。
李里等母亲从棋牌室出来,两人一起往家走。母亲不断地遇见熟人,和人招呼,让他叫人,回答他们自己在城里的活计与经营,是男人的话还要发烟。关于父亲在街头卖货的记忆一次次浮现,一次次地被打断,最终被抛在身后。
李里回头看看,人群中早已没有杨梨的身影。
父亲并没有因为新年的临近而振奋,他竭力让自己靠着枕头从床上坐起来。隔壁人家的亲戚不时造访,来到院里七嘴八舌聊天,吃瓜子。这些闲谈和冬日炉火一样,暖烘烘地洋溢在即将到来的节日气氛中。父亲也流露出对这种热闹的向往,隔了一堵墙,这七个八个他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为他带来远方大雪的消息。偶尔外面也传来母亲的声音,几个女人聚在一起聊天,哈哈大笑。
隔壁院里没有人的时候,李里的家也就空旷起来,尤其周边人家喊吃饭,喧闹的声音从堂前溢出,红烧鸡的香味飘散到他家的时候,寂寞就更加具体而全面地降临。母亲是毫无所知的,不外出的时候,她就在院里坐着,不同于父亲对大雪的等待,她享受着冬日的温暖。
“暖冬真好啊!”她的身体在阳光下渐渐热乎起来。罩褂子脱了,棉袄也脱了,不敢再脱毛线衣,然而她说腿热得直痒,又把棉毛裤推到小腿以上,大冷天的,胖乎乎的腿上起了白白的屑。
李里看得一冷。
父亲摇摇头。
“嘶哈——”母亲挠着自己的腿,阳光下白色的皮屑在空气里慢慢扬起来,如同小小的雪,和灰尘一起,漂浮在空气中,久久不下沉。
父亲不说话,双手放在腿上,脊背微微驼着,看得出了神。李里想,杨梨是不是也会这样?当她老的时候,她也会像他的母亲一样,邋遢地当着自己儿子的面把腿抓出一道道白色的痕迹,像打了一层痱子粉似的。
他在久久的怔忡之中问自己,如果他成为杨梨的丈夫,他会情愿和她在此共度一生吗?在脚下的土地上,和一个胖胖的,早已没有过去风韵的杨梨,这样的一个杨梨……他不知道为何,想与她在此共度余生。
五
李里梦见了桥。
一座奇怪的桥,他跑到外面一看,这座桥好像列车的轨道,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每隔五百多米,也许一千多米,就有一个UFO 一样的银白色圆盘漂浮在空中,这道弧线过山车一样地向远处蔓延去,圆盘在每个圆弧的顶端出现。他又跑到桥下,感觉奇怪而茫然。
醒来他嗅出晴天才有的清冷味道,幽蓝而新鲜,他睁开眼睛,在母亲熟悉的呼噜声中,在声音低伏的片刻里,他辨出父亲吃力的喘息声。他不可避免地预感到父亲又一次听受着远方的召唤,在空无一人的凌晨,在大雪铺就的路上,气喘吁吁地向远处跋涉,寻找他说的那座庙。
醒来,父亲果然又说起梦里的雪。
“也许是心理作用”,他说。
也许是迷信,母亲说她去找了算命的。
悬而未决。
恢复了一些体力,父亲又一次坐在了阳光里。
“等你的身体再好一些吧”,李里说,“等你身体再好一些我带你出去。”
父亲急不可耐但无可奈何,冬日即将过去,天气预报里说,今年南方部分地区可能无降雪天气,而春天快要降临。在后面的日子里,母亲计划了去南边,去远亲家吃喜酒,去城里看灯会……那些热闹的事情拥挤着排列在后面,一眼望不到边。
次日他与父亲四点多就出发了。凌晨四点多的田野,李里许多年不见了,而今就在道路两旁,被风拉扯模糊,向后倒退。路上几乎没有车,因为怕错过路口,李里开得不快,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悄悄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春天。
感觉并未开很久,至于某一处时父亲让他停车。接下来的路不便开车,一路的泥沙,崎岖不平,两边树干凶狠地伸出枯死的枝杈。李里把车停在路边,扶着父亲下了车。父亲因为久不出门,又长期吃素,走不了百米就要停下来在路边坐一坐。李里站在旁边点了支烟抽,天空还是暗的,但已有渐渐明朗之势。父亲一起身,李里就去扶他。但走了不过百米,父亲又低头找一找,找个地方坐下来,他说:“等一等啊,歇一歇。”
早晨的风,从田野深处路过田垄,拂过水面,掠过树杈与荒草,吹拂过来,带来茅草与大地的味道,新冷的空气顺着胸腔把五脏六腑都搜刮了一遍,带走身体好不容易储藏的一点薄温。在风声与草声中,李里看见父亲的脊背低低地耸起,又轻轻地落下。父亲像是跑了许久许久了,才这样剧烈地喘气,然而放眼望去,田野是如此的枯燥,残酷地重复着,一片片,连接着一模一样的草野,向遥远的尽头延伸推进。李里眯着眼睛,只能看见毛绒绒的蓝色地平线,遥远的,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地平线,而太阳即将升起。
等他们走到天空彻底亮了,李里回头望去,只觉得触目,他一眼就能看见来时的那条路,甚至他那辆黑色大众也能清楚看见。它平静而无声地等待着他们。
“回去吧!”他对父亲说,“一大早,也没吃饭。”
父亲不作声。
他又问:“路对吗?”
父亲不如先前那样笃定了,他抬起浑浊的眼睛望着这片草野,茫然如孩童,很久之后他说:“不对嘛,怎么走到杨家圩来了……”他的视线在空旷的田野上晃来晃去,目光之所及好像他已经全部用脚步丈量与踩踏过。
他说,和梦里不一样,没有下雪,认不清路。
最后他们用了双倍的时间又走回车上。李里提出背着他走,父亲开始不肯,后来就不由他肯不肯了。背上的人干瘦,分量全压上来也不感觉到沉,好像只有可怜的一点点。李里没有背过小孩子,但他感觉自己现在就背了一个小孩子,轻飘飘的,到车边他把父亲放下的时候,他感觉父亲又瘦小了一些。
“等雪天吧!等下雪了再说。”李里对父亲说。
父亲沉默。这场雪遥远得看不到迹象。
已经午后,回去的路上父亲默默向外看,行驶间李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他唯一与父亲出门卖货的那一次。午后,他跟在他后面,在一个陌生村子的巷子里七拐八拐,巷头巷尾响彻着父亲吆喝卖东西的声音:“梳子啊,剪刀啊,收头发啊……”阳光热辣,生意寥落,偶尔有人路过。父亲在这里坐了一阵,等了一阵,又绕了一阵,一毛钱没有赚到手……那一次,回去路上,父亲也是这样的沉默。
李里加快速度,脚踩油门,一路飞驰往家里开。
到家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家中照例没有人,空落落的院子,空落落的堂前,他们坐在家里吃备好的午饭。
父亲面前两碟菜,一碟素油青菜,一碟腌菜豆腐,他早已习惯,怀着一颗失落的心,吃得很仔细。
李里以前看电视,古装剧里演到最后,总有人要出家的。有女人剪了头发说要做姑子,也有男人剃头说要做和尚,三千烦恼丝,仿佛一入佛门,人不生不死,又亦生亦死,成为了第三种状态。他那时觉得索然,以为人一出家总会给故事留下些空旷的余味,好像这个人既没有死,但与生的关系也不大了。
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父亲有一天也要走上这样一条路。
下午两点钟,钟声回荡于堂前,父亲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李里身边,茫然看着门外,在分分秒秒地老去。他们因思想不同生生分出两个空间,各自被迎面而来的风暴吹袭。但父亲并不知晓,或者知晓了也不作声,他就在轰轰隆隆的波轮洗衣机的声音里,轰轰隆隆地被时间敲打。李里不知看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