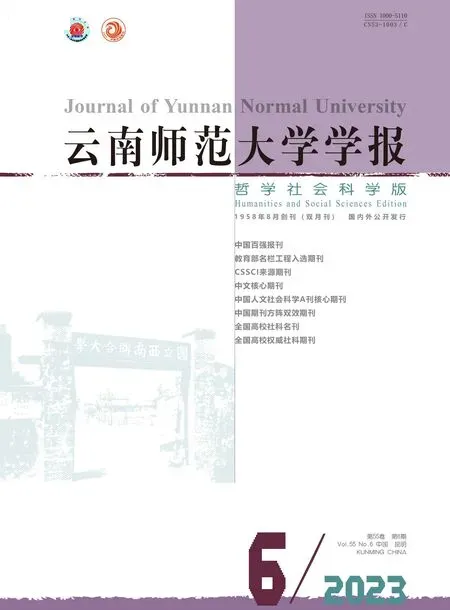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动物伦理:以法律间张力重塑部门联动机制*
孟令法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重庆 400067)
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社会实践来看,文化主管部门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本质上的非遗保护工作并非文化主管部门的独立行为,而是以文化主管部门为重心,结合其他相关机构乃至社会组织及其成员为辅助的多元行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下称《操作指南》)第三章“参与《公约》的实施”就对以专家、专业中心、研究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构成进行了功能确认,而中国则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非遗保护原则,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1)在下文中,凡出现《非遗法》,即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使用“非遗法律法规”时,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内的一切涉及非遗保护的法律法规。)第一章“总则”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和第九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法条中得到更明确规定。不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还是《非遗法》,其对非遗的概念定义以及类型划分均表明,非遗不只是一类文化表现形式,也关涉社会结构状态与自然生态环境,“动物问题”便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伦理关切。
小引:问题的提出
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广,不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还是《非遗公约》缔约国,愈发意识到不同类别非遗代表作(2)在教科文组织层面,遗产项目的前置修饰词为《代表作名录》,而中国则为“代表性项目”,故在后文中,凡属国际层面的使用“遗产项目”,凡属中国实践则使用“代表性项目”。项目的彼此互涉,而包括“动物使用”在内的一系列“横向问题”(transversal issues)被推向前台。“动物问题”并非保护非遗一开始就有,也不是《非遗公约》通过后即被关注到,而其“导火索”则来自2014年(9.COM)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下称政府间委员会)对中国所申报“彝族火把节”的审查。由于节日中的“动物角力”被质疑“是否符合尊重不同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敏感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且被认为带有一定“娱乐性”的动物使用传统“如何促进不同敏感社区间的对话”,则成为政府间委员会决议(Decision 9.COM 10.12)将之“退回”,并要求补充信息以在下一评审周期提交审查的核心原因。虽然这一结果与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对遗产外交的干扰和影响相关,但其显然促进了人们对动物使用类非遗实践的反思。近年,中国学者如李旻旻(2015)、孟令法(2016)、林海聪(2016)、夏循祥(2017)、陈爱国(2018)、温士贤(2018)、陈红雨(2019)、周跃群(2019)、龚真和刘璐瑶(2020)、刘爽(2020)、郑智和王昱璇(2020)、杨宇星(2021)、姜中其(2021)以及珊丹和刘嘉晖(2021)等不仅立足中国非遗保护实践分析动物使用带来的文化困境,还借助国际非遗保护经验为中国非遗保护建言献策;而以Gustavo A. María(2017)(3)Gustavo A. María, Beatriz Mazas, Francisco J. Zarza & Genaro C, Miranda de la Lama, Animal Welfa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f Spanish Citizens Towards Bullfighting[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17,(6).、Wojciech Dajczak(2021)(4)Wojciech Dajczak, Dariusz J. Gwiazdowicz, Aleksandra Matulewska & Wojciech Szafrański, Should Hunting as a Cultural Heritage Be Protected?[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 juridique, 2021,(34).、菅丰(2022)(5)菅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幻影[A].雷婷,译.周永明,王晓葵.遗产(第五辑)[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153~177.以及Lyne Letourneau(2023)(6)Lyne Letourneau & Louis-Etienne Pigeon. Questioning Customs and Traditions in Culinary Ethics: the Case of Cruel and Environmentally Damaging Food Practices[J]. Food Ethics, 2023,(7).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也就本国实际探讨了特定动物使用对发展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直接影响。
尽管从非遗保护角度勘察动物伦理已成学术热点,但非遗作为一类为“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所共享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总和,其活态传承性决定了其保护策略的动态性。换言之,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非遗保护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的非遗认识以及保护手段必然是发展的,因而包含动物使用的非遗实践也随着相应案例的出现,必然走向理念更新、政策创新和方法革新的道路。不过,上述学术成果虽极为重视本土个案,但这种以描述为主的行文风格既缺乏对本土非遗保护政策的检讨,也未关注国内外相关事件或案件的历时性变化。更重要的是,相较于2003年正式开启的国际法非遗保护,动物的国际法保护不仅兴起较早且更为全面,(7)如1946年的《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whaling,我国于1980年9月24日缔约)。1971年的《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我国于1992年1月3日缔约,同年7月31日生效)。1973年的《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我国尚未缔约)。1973年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1980年12月25日我国缔约,1981年4月8日生效)。1979年的《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我国尚未缔约)以及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我国1992年6月11日缔约,1993年12月29日生效),等。但现有研究基本没有涉足这一领域,甚至连本土法律都未提及。然而,作为一项文化行政工作,非遗保护需要法律保障,但非遗并非独立的文化事象,因而也要关注包括动物保护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法规对非遗保护的辅助甚至决定性作用。那么,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名录》和中国“四级名录体系”(8)在《非遗公约》框架下设立的两个名录和一个名册,一般简称“《〈非遗公约〉名录》”(the Lists of the 2003 Convention),包括《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简称《急需保护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表作名录》)和“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简称《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四级名录体系”即我国在非遗保护过程中设立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的简称。都有哪些典型性动物使用类非遗实践,我们又该如何审视《非遗公约》《操作指南》及中国非遗法律法规等所设定的列入标准及其与“动物保护法”的关系,则是本文所要重点梳理和探查的问题。
一、动物伦理与非遗保护:作为法律关注视点的国际文化事象
在追溯非遗保护作为国家文化工作的兴起时,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之指向日本对“无形文化财”的保护,而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民俗版权”之争则为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逐步走向21世纪初叶诞生的“非遗”奠定了“对象”基础。换言之,最初的非遗保护或许更加青睐口头传统,但“民俗”(folklore)的能指和所指或内涵和外延显然为其概念及分类的国际法定性提供了标准参照。正如上文所言,尽管《非遗公约》下的《〈非遗公约〉名录》,以及以中国“四级名录体系”为代表的缔约国非遗清单,都以“代表作(性)”的前置定语修饰非遗,但不可否认,这些“遗产项目”不仅互相关涉,且涉及领域极为多样,因而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已然不止于非遗法律法规一个面向的“保护”,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其他国际法和国内法。人们过于重视非遗的社会文化属性,忽略其作为社会生活之组成部分的自然生态特征,这无疑为非遗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在特定缔约国出现刑事案件。
立法保护非遗早已成为国际共识,而针对《非遗公约》得以出台的基本过程,巴莫曲布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9)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J].民族艺术,2008,(1).一文中进行了详细梳理。尽管这部国际法的订立经过了相对漫长且艰难的国际辩争,但一经宣布就得到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的积极响应,甚至影响到各缔约国对本国同类法律的修订或制定,而中国非遗法律法规的确立过程即是典型。(10)孟令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A].周永明,王晓葵.遗产(第一辑)[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111~135.由此可见,非遗保护作为一项国际文化行动,其立法活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践行。在笔者看来,以《非遗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和以中国非遗法律法规为代表的国内立法实践,从法律角度界定了非遗的概念及类型,指导了各缔约国及相关文化机构的非遗保护工作,规范了各级各类非遗实践的认定标准及“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理念”(巴莫曲布嫫的总结)。不过,“法律往往不能对相同事项作出统一的规定,有时法律只能规定一般原则或者作出一般规定,具体内容由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补充或作出具体规定”(11)朱福惠,刘心宇.论行政解释形式的制度逻辑与实践图景[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换言之,单一法律文本虽为限定具体行为而设立,但其却难以事无巨细地对此进行社会治理,而遇到跨领域问题,如本文所研究的动物使用类非遗即是一例,一方面需要依赖这类法律的司法解释予以定性,另一方面或须借助相关法律,即“动物保护类法律”加以调整。然而,仅从《非遗公约》及相关非遗法律法规来看,独立约束非遗保护的法律法规既缺乏细节阐释,也少有与其他法律法规相对接的政策机制。
较之非遗保护,针对动物伦理的国际关注多与环境问题相关,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而在部分国家或地区,还将宠物和牲畜等动物纳入福利观照对象。正如前文所言,人类文化得以创造的基础本就离不开动物的支持,而采集狩猎生产模式、畜牧养殖业的发展、饮食烹饪技艺的生活传承以及竞技娱乐活动的多元开展,甚至族际战争、人生礼仪和祭祀典礼等都必须动物“在场”。此外,诸多动物(之名)还由谐音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为赋予各种象征寓意,如“喜上眉梢”“松鹤延年”“吉祥如意”“连年有余”“三阳开泰”等,而以十二生肖为代表的“动物群”则成为中国民众使用至今的重要计时工具。然而,随着人与动物关系的逐渐密切,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特别是在竞技娱乐、饮食烹饪及祭祀典礼等领域,选择何种动物并以何种手段使其远离伤亡带来的痛苦乃至绝灭危险,则成为人类进行伦理思考的核心要素。其实,古今中外的动物使用伦理并不止于哲学思辨,还在某些历史阶段创建过类似中国当代林草局和渔业局的官方机构。如封建时代用以管理山泽禽兽的“虞”“衡”部门,诸如《淮南子》《唐六典》《明史》等古代典籍还对渔猎等活动的限定状况进行了记述,(12)《淮南子》卷九《主术训》载:“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刘安.淮南子[M].杨有礼,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357;《唐六典·尚书工部》:“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交,陆禽孕育,喂兽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籍;秋实之登,不得焚燎。若虎豹豺狼之害,则不拘其时,听为槛阱,获则赏之,大小有差。”张九龄,等,著.唐六典全译[M].袁文兴,潘寅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241;《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志一》则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岁下诸司采捕……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若害兽,听为陷阱获之,赏有差。”张廷玉,等.明史(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60.就此民间社会也根据生产生活经验定下相应的习惯法原则(13)如鄂温克族就对出行狩猎的时间做出了规定——“讲究‘七不出,八不入’,即每月的7、17、27日不得离家出猎,8、18、28日不得收猎返家”。应文达.鄂温克族民间禁忌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不过,这些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相反还表现出强烈的族群差异性和时空局限性,因而面对极端动物使用,人们既从意识上进行反思,又借助行为艺术加以反抗。
如今,以儒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代表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态观,但作为当代学术理念及行为实践之指导的动物伦理观或动物福利观,则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为中国学者所推广,而吕碧城则是其中典型代表(14)参见熊慧颖.吕碧城戒杀护生观念及其对西方保护动物运动的传介[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王晓辉.“礼拜不鞭马”:清末民初国人对英国动物保护的认知及初步实践[J].全球史评论,2017,(2);朱英.“为什么要保护动物”——近代国人新动物观述论[J].浙江学刊,2023,(3).。尽管西方社会在动物伦理或动物福利的探讨上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但其核心理念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蒋劲松看来,西方动物保护经历了3个阶段的伦理深化,即(1)以人之生存为基础,“把动物作为资源和环境的一部分来保护”;(2)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目的,“把动物作为可以感知痛苦的生命来保护”;(3)“把动物作为与人类平等的生命来保护”,此以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动物解放”说和汤姆·里根(Tom Regan)“动物权利”说为代表。(15)蒋劲松.顺应天道,护生节用——儒家的动物保护观[EB/OL].https://mp.weixin.qq.com/s/fV2smSds8VcHdi5HrHyGCA,2021-11-12.相较于前两者,第三种表现得更为激进和彻底,且同当下颇为流行的素食主义密切关联,甚至有颠覆屠宰业和动物实验等既有社会制度的倾向。尽管这种伦理意识深刻影响了当代人的动物认知,但其实践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冲突得以发生的可能性。不过,作为万物之灵长,人类之于动物的各种行为又岂能缺少伦理依托。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忽略动物保护问题,放任人类对动物以及物种的滥捕滥杀和掠夺式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16)崔拴林.动物地位问题的法学与伦理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而立法限定(指导)人类行为则成为强化动物伦理,提升动物福利的重要举措。
基于动物保护的现实需要,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同中国一样不仅制定了一系列关涉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案,且为宠物和牲畜提供了有效生存的福利法保障,(17)参见宋伟.善待生灵——英国动物福利法律制度概要[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莽萍,徐雪莉.为动物立法——东亚动物福利法律汇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外动物福利法律法规汇编[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肖肖,李卫华.澳大利亚农场动物福利操作规范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但中国除香港和台湾外,尚未对后者作出全国性制度规范。不过,中国学者于近年也开展了一些立法讨论。如“一些学者赞成动物(权利)主体论,主张应在法律上赋予动物(权利)主体的地位”,他们认为“应基于‘大自然的主体性高于人的主体性’的视角承认动物的主体地位”,而“动物也具有‘绝对’的‘内在价值’”,故应“通过设立平等对待原则、权利内容差别原则、独立利益代表原则来建立动物主体制度”;虽然也有学者“从民事主体制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分配正义、程序正义、动物权利制度的可操作性、动物的法律‘物格’、动物客体论在规则适用和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等方面”提出与前者相反的“动物客体论”,但他们并不否认立法以规避某些极端行为的国家做法。(18)崔拴林.动物地位问题的法学与伦理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此外,以常纪文为代表的中国法学者不仅在研究如何立法,还亲自起草“动物福利法”文本以供国家立法机关参考。(19)常纪文.动物福利法:中国与欧盟之比较[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常纪文,Gill Michaels.动物保护法与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与各界争锋[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0.然而,这种立法愿望由于深受西方伦理思想影响而未被普遍认可,甚至在特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审议中,涉及“动物福利”的条款还被删除,且在后续的法条修订中一直未被纳入。(20)田雨,邹声文.关注立法:畜牧法草案删除有关“动物福利”的条款[EB/OL].https://www.gov.cn/zwhd/content_136421.htm,2005-12-24.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民众对这类理念的认知不足,更在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动物经济之于现实国情的产业功能,而不独为动物的社会属性。
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立法工作的持续推进,动物伦理观或动物福利观也逐渐为大众所知并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动物之于人类社会的实际作用赋予不同俗民个体或集体以不同的伦理理解,继而产生激烈的言语论辩甚至身体争斗。为了协调不同阵营的动物认知,通过立法以协调彼此关系,既是一条有效途径,也是统一不同思想的有力手段。但这种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动物保护策略,是否真能通过国家强制力加以限制,不仅要考量受保护动物的种类及措施(或言量刑标准),也要测算区域生态环境的自然承载力。更重要的是,人类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根本离不开动物,而动物也是当下诸多非遗实践的重要构成元素。然而,单从动物保护类法律法规来看,它们无一不是立足动物本身而制定的人类行为准则,故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出现涉及动物伦理的问题则在所难免。因此,作为进入国际视野的文化事象,立法保护非遗与立法保护动物并不是截然分立的两种人类行为,相反二者必须对接,甚至部分条文需要统一。
二、多元发展的柔性标准:动物使用类非遗项目的国际法表现
在历经20余年的非遗保护工作后,由动物使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虽愈发凸显,但国际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并未因此彻底改变。正如上文所言,作为人类文化表现形式的重要构成元素,动物在决定不同主权国家及其附属地区独特性的同时,也为处于相同或相似自然环境或社会结构中的不同族群,提供了解释不同主权国家及其附属地区的文化表现形式何以呈现某些一致性的参照,而这恰是教科文组织鼓励不同主权国家开展非遗实践联合申报的重要原因。截至2023年6月,教科文组织的195个成员国已有181个主权国家成为《非遗公约》的缔约国。不过,在每年一次的代表作项目申报过程中,《非遗公约》及其《操作指南》虽对缔约国的各类申报材料具有指导甚至约束功能,但缔约国对其所申报代表作项目的确定仍有来自“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文化自主权和自由选择权。而从历年提交的申报材料看,基于动物使用确定的代表作项目不仅每年都有所涉及,且大多凸显于农业生产领域,另有少量代表作项目涉及竞技或娱乐。
作为处理国家关系并规定国家间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非遗公约》及其伴生文件并无针对动物伦理的特别条款。然而,从操作层面看,动物伦理问题则被涵盖于《非遗公约》的非遗定义中。也就是说,《非遗公约》所界定的非遗必须满足“三个符合”,即“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G].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Z].2020:8(内部资料).此外,基于“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代表作项目之选择,也符合2015年教科文组织所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相关建议,尤其是第六条,即“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到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2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J].巴莫曲布嫫,张玲,译.民族文学研究,2016,(3).。因此,动物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现行国际人权文书。不过,这里的“动物”不应指称“所有”动物,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且不是涉及为国际社会统一认可的各类保护动物,特别是进入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23)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又称“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英文全称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an Natural Resource,简称IUCN。不定期发布的《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以及列入各国(地区)所制定的“动物分级保护名录”的动物。就此而论,《非遗公约》第三条“与其他国际文书的关系”第二点恰恰表明了此意。(24)《非遗公约》第三条“与其他国际文书的关系”指出:“本公约的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二)影响缔约国从其作为缔约方的任何有关知识产权或使用生物和生态资源的国际文书所获得的权利和所负有的义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G].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Z].2020:8(内部资料).换言之,非遗保护不能成为人类“无限”使用动物的实践支撑,尤其是那些涉及濒危野生动物的文化表现形式,如以象牙、犀角、玳瑁、盔犀鸟头等为原材料的传统手工技艺。
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际非遗保护事件,“彝族火把节”所指称的动物使用问题虽触发了人们对人类与动物之关系的伦理思考,但在这一事件出现前,动物使用并非相关代表作项目得以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直至2016年再度修订《操作指南》时方在动物使用问题上作出明示(详见第四部分)。截至2022年12月,共有676项非遗实践列入《〈非遗公约〉名录》,从这些代表作项目的名称及内容简介(25)对此,可从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处官网查询,网址为https://ich.unesco.org/en/lists。即可获知哪些项目涉及动物使用。不过,另有部分代表作项目虽未直接表露是否涉及动物使用,但申报材料依然暗含被缔约国刻意“遮蔽”的这一要素。这些代表作项目既为审查机构及政府间委员会所审定,又是受国际法认可并保护的人类文化表现形式。固然,我们可从历届政府间委员会的决议中看到相关代表作项目之所以被列入、退回或不予列入的最终表述,但除特殊原因外(26)例如,比利时阿尔斯特狂欢节在2019年政府间委员会常会期间被移出“代表作名录”。原因是因该遗产项目在近几年的巡游行列出现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成为与《非遗公约》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第一个反面例证。,并未因正常的动物使用(如饮食传统和仪式实践)产生异议。从入选《〈非遗公约〉名录》的遗产项目及优秀实践来看,涉及动物使用的各类文化表现形式也处于非遗五大领域的互涉之中,但其重心或细节却为我们提供了分类依据。就此可知,国际层面的动物使用类非遗大体可划分为六大类,即生产类、饮食类、仪式类、竞技/游戏类、扮演类以及其他类,而这也适用于中国四级名录的扩展型次级分类。
具体而言,生产类动物使用型是以渔猎、放牧、蓄养或售卖为主要生产(经济)模式或借助驯养动物以获取肉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济州海女(女性潜水人)文化”(27)韩国“济州海女(女性潜水人)文化”是以一群80多岁的妇女为主体,在不戴氧气面罩的情况下,潜入海下十余米处“收集诸如鲍鱼、海胆等贝类”,并以环保手段协助管理日常捕捞行为的生产文化。(韩国,2016)、“猎鹰训练术——一项活态人类遗产”(28)“猎鹰训练术——一项活态人类遗产”(Falconry, a living human heritage,下称“驯鹰术”)初于2010年为欧亚非11国联合申报,2016年增至18国,即阿联酋、叙利亚、奥地利、巴基斯坦、比利时、韩国、德国、法国、哈萨克斯坦、捷克、卡塔尔、蒙古、摩洛哥、葡萄牙、沙特、西班牙、匈牙利以及意大利,2021年又增加6个国家,即克罗地亚、爱尔兰、吉尔吉斯斯坦、荷兰、波兰和斯洛伐克,共计24国。(阿联酋等24国,2021)和“蚕桑与传统丝绸织造生产”(阿富汗等7国,2022)以及优秀实践“游牧运动——重拾遗产、弘扬多元”(吉尔吉斯斯坦,2021)等;饮食类动物使用型,即对从渔猎、放牧或驯养等方式中获取的肉食进行烹饪的技艺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类生活习俗和宴会等文化表现形式,如“和食——日本人的传统饮食文化,特别是为了庆祝新年”(2013)、“奥希抓饭——塔吉克斯坦传统膳食及其社会文化语境”(2016)和“新加坡小贩文化——多元文化城市背景下的社区餐饮和烹饪实践”(2020)等遗产项目;仪式类动物使用,乃以动物为牺牲或为渔猎、放牧、驯养等生产行为祈福,或为某一特定社会目的而举行仪式或仪式性活动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桑凯蒙——桑凯的集体捕鱼仪式”(马里,2009)和“劝诱骆驼仪式”(蒙古国,2015)等急需保护代表作项目以及《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马拉尼昂州的本巴牛文化”(巴西,2019)等。
就竞技/游戏类动物使用型而言,即以动物为对象,或借助动物以开展人力(包括智力和技术等)竞技,或借此进行大众娱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如“乔甘——阿塞拜疆共和国卡拉巴赫传统马背竞赛”(2013)等急需保护代表作项目和吉尔吉斯斯坦“阔克博如——传统赛马”(2017)以及阿联酋与阿曼联合申报的“赛骆驼,一种与骆驼相关的社会习俗和节日遗产”(2020)等《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扮演类动物使用型,即以动物为模仿对象(部分还会使用动物制品),并于特定活动予以展示的文化表现形式,此以欧美“狂欢节”为典型,如哥伦比亚“巴兰基亚狂欢节”(2008)、法国“格朗维勒狂欢节”(2016)和“比利牛斯山的熊庆典”(与安道尔联合申报,2022)等《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其他类动物使用型,乃包含动物使用(作为组成部分或要素)的文化表现形式,主要集中于2009年之前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后均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大部分“文化空间”,如约旦“佩特拉和瓦地伦的贝都人文化空间”、乌兹别克斯坦“博恩逊地区的文化空间”、越南“锣钲文化空间”以及摩洛哥“杰玛·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等。
通过类型释义及举例可知,以动物使用为外在表现形式的非遗实践大都被列入《代表作名录》,仅有少数隶属于《急需保护名录》,而在《优秀保护实践名册》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有1项。此外,扮演类动物使用型主要表现于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狂欢节或大型节庆活动,而其他类动物使用型则以2008~2009年转入《代表作名录》的“文化空间”为代表。从申报国或申报地区来看,欧、美、亚、非等均有表现,且单独申报远超联合申报;就所涉动物种类而言,欧美国家或地区对马“情有独钟”,即以马术为主要文化表现形式的代表作项目最抢眼,而中西亚及部分非洲国家亦较“爱”马。此外,牛、羊、鱼、虾、鹰、蛇、蚕、骆驼以及蜜蜂等也承载了具体非遗实践。不过,尽管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动物种类大都见于日常生活,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亦有部分为“野生”,或由“野生”转向“驯养”的动物,特别是“鹰”“蛇”等与牲畜有别的动物种类,这显然最具争议性。然而,这类以生产活动为基础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却未受到动物伦理的直接影响,且在联合申报国的持续增加中发挥了文化之于跨国合作的维系功能。
进一步讲,在生产、饮食、仪式和竞技/游戏类动物使用型中,“项目”有比较直观的名称表述,而扮演类和其他类动物使用型非遗实践则显得相对隐蔽,但其简介却昭示了“动物”的存在。如哥伦比亚“巴兰基亚狂欢节”就有“动物面具”;在匈牙利“莫哈奇的布索庆典——冬季面具狂欢节习俗”中,由人装扮而成的恐怖形象“布索”则“头戴木质面具、身披羊毛大斗篷”;法国“格朗维勒狂欢节”的形成与“当地繁荣的渔业(鳕鱼捕捞季)密不可分”;约旦“佩特拉和瓦地伦的贝都人文化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为“传统游牧文化及相关知识技能”,而“骆驼饲养”就是其中之一;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博恩逊地区的文化空间”中,就有在给婴儿施行割礼时“伴有斗羊和其他游戏”;越南“锣钲文化空间”存在“祭献小牛牺牲的仪式”,而摩洛哥“杰玛·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则有“耍蛇”表演。对应上文所述,相较于较早列入相应名录的遗产项目,后列入者的动物类型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在名称表述更为显性的同时,内容简介却有所隐藏,这或许就是“彝族火把节”提供的先见——不论申报文本、申报片,还是图片,都尽可能不把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使用加以视听呈现,但通过形式审查的遗产项目并没有影响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原貌”展示。然而,尽管“彝族火把节”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但后续遗产项目的种类不仅多元,且其审查标准的形式性,即只评价申报资料是否符合申报要求,(2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1~12段)[G].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Z].2020:24~26(内部资料).并不进行实地考察——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法——《非遗公约》的柔性特征。
就本质而言,以《非遗公约》为代表的非遗保护国际法,强调对“人”的观照(30)《非遗公约》“前言”对此作了详细说明,故此不再赘述。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G].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Z].2020:6~7(内部资料).,却少有对接动物保护类国际法的条款,而动物使用却是普遍存在的人类文化表现形式,这种实践可以单独存在于特定非遗项目中,也可作为构成元素融入相应的遗产项目。然而,当动物使用成为非遗保护过程的一个“问题”,单独立法下的“动物”和“非遗”或已很难调和。纵然《操作指南》于2016年新加一章,即“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但其重在指导缔约国如何处理涉及非遗的各项国内外社会事务,这当中固然包括动物使用伦理(详见第四部分)。然而,这一章在调整国与国或族群与族群的国际关系时,并未就“动物”和“非遗”的统一性以及后者的申报评审规则提出协调策略。不过,这种立法原则已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参考或方向。也就是说,“动物”和“非遗”不仅要在后者的“三个符合”,特别是“相互尊重的需要”下进行伦理约束,更需实现两类国际法的对接或在既有国际法——《非遗公约》(及《操作指南》)的基础上增加相关条款,如此方能更为有效地维系动物使用类非遗实践的存续力(viability)及其社会功能。
三、传承人群的认知差异:动物使用类非遗案件的国内法张力
动物的文化属性是鲜明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或族群)不与动物发生关联,纵然上文并未直接就具体国家或民族(或族群)的动物使用情况展开详细描述,但通过入选《〈非遗公约〉名录》的典型非遗实践亦可管窥其相应状态。上文曾言,立法保护动物是早于立法保护非遗的国际行为,且其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保护对象并不止于野生动物,还包括宠物和牲畜,而这在中国却是相对缺位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仅《非遗公约》尚有一些成员国至今没有缔约,动物保护类国际法同样存在不少尚未缔约的国家,而这种未能形成统一国际法行动的现象也就无法对尚未缔约的国家产生约束。因此,诸如部分国家的“捕鲸”习俗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也不会在教科文组织层面被列入任何《〈非遗公约〉名录》代表作名录,但这并不影响该国民众继续实践这种生产模式。另外,以休闲娱乐、神灵祭祀、食物获取等为目的的动物使用行为并不受制于前述国际法,且在国内也不完全为现行动物保护法所限制的现象更是多样。
虽然西学东渐为中国民众带来“动物伦理”这一现代性哲学理念,但这一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却遇到一定困难。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来自作为西学的“动物伦理”并未主动对接中国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则在于相关推介者抛弃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政治上“以人为本”,经济上“立国于农”,文化上“根基传承”。因此,尽管在“民主”“科学”的大旗下,清末民国时的知识分子也仅有部分关注到伦理之于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且未将之完全上升为“文明”。更何况占人口主体但未经受正规教育的广大民众,即便在民间“动物保护组织”日益增多且人口素质极速提升的当下,人们对动物伦理的认识却逐步分化为不同辩争阵营,而这种现象既表现于国际之间,更彰显在国家之内。虽然教科文组织曾于1993年接受韩国建议而设定“人类活财富”(142 EX/18)(31)按国际文化政策研究通行做法,本文所引国际工作文件(grey documents,即非正式出版物)可据文中所标文件代码从教科文组织正式文件系统(documents.un.org)和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unesdoc.unesco.org)获取。若非必要,后文不再赘言。,并由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2002年推出《建立人类活财富体系指南》(CLT-2002/SANS COTE),但在总结完同年4月举行的“人类活财富培训”(FIT/553/RAS/72/Final report)后,这一针对持有高超技艺者的国际保护行动即在2003年《非遗公约》出台时成为一项“前计划”(32)Living Human Treasures: a Former Programme of UNESCO[EB/OL].https://ich.unesco.org/en/living-human-treasures.。不过,为提升各缔约国在非遗保护中对“人”的关注度,时为非物质遗产处(Intangible Heritage Section)的教科文组织内设机构还是拟定了一份仅供缔约国参考的《建立国家“人类活财富”制度指南》(33)Guidelin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Living Human Treasures” Systems[EB/OL].https://ich.unesco.org/doc/src/00031-EN.pdf.。表面上看,“人类活财富”同中国所称“传承人”(34)“传承人”这一术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出现,但作为保护非遗的法定术语,则出现于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相似,但后者并不止于“传人”,还包含“承人”(巴莫曲布嫫的总结),故对动物使用伦理的差异性认识实则反映了“传承人群”的自觉分化。
同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动物使用类遗产项目一样,中国“四级名录体系”中的此类代表性项目亦不在少数。对此,林海聪立足“使用类型”,将中国动物使用类非遗实践分为“以动物为加工材料”“以动物为活动媒介”和“以动物为生产对象”3种,且从所选项目类别来看,中国动物使用类非遗实践依次集中于“传统技艺”“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传统戏剧”以及“传统美术”等领域。(35)林海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动物使用”的伦理困境[J].民族艺术,2016,(1).虽然这种分类与笔者对《〈非遗公约〉名录》的类型划分有所差异,但本质并无二致。更重要的是,动物使用类非遗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皆有分布,且同物资生产、节日节庆和祭祀仪式联系最紧密,这无疑与国际社会表现一致。同教科文组织不尽相同的是,在其关注到动物使用对非遗保护的影响并于《操作指南》的修订中加入相关章节后,中国至今未在这一问题上进行立法思考。在教科文组织层面,笔者尚未发现除“彝族火把节”外与国际法相关的动物使用类非遗事件,而这一项目的审查过程虽在“会上”(9.COM)有所辩论,但其并未上升到国际法庭的事实表明,动物使用之于非遗保护并不属于国际利益争端,且缺乏国际法依凭。不过,我们并不能否认相关缔约国没有发生因动物使用,而影响特定非遗实践的保护及其有序传承的法定案例,而中国亦有此类情形发生。
在《“动物保护”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一文中,笔者分别对传承于不同群体的3类省(市)级代表性项目——“猴戏”“狗肉”和“点翠”的法律间问题作出详细记述。尽管只有“猴戏”涉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而进入刑事领域,但后两者所引发的社会舆论无疑更值得反思,特别是由“狗肉”导致的各类行为艺术乃至“高速拦狗车”等极端事件,则因执法“双标”备受诟病。(36)孟令法.“动物保护”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来自“狗肉”“猴戏”与“点翠技艺”的法律思考[J].民族艺术,2016,(1).
在此三案尚未完全得以解决时,又出现涉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鹰的非遗刑事案件。据《中国环境报》报道,东海县“鹰猎技艺”(37)东海县“鹰猎技艺”于2013年9月被列入第五批连云港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因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某法等人违法收购苍鹰,而被连云港海州区人民法院判处缓刑并处罚金。根据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介绍,东海县“鹰猎技艺”除用于狩猎,还被赋予“玩”的属性,故其代表性传承人也被称为“资深玩鹰人”,而这或许正是其被列入“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领域的原因。(38)韩东良,张继龙,周静,等.“资深玩鹰人”也不能任性:因收购苍鹰,江苏东海3名被告人被判刑[N].中国环境报,2018-03-28(008).与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的驯鹰者被判罚不同,非代表性传承人的抖音主播因以“抖鹰”为题展示“纳西族驯鹰习俗”(39)“纳西族驯鹰习俗”于2017年6月被列入第四批云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民俗类。而受到行政处罚,但司法部门却未明确何人可以何种方式获得“驯养”资格(40)丽江同城网.传统与现实的碰撞,在玉龙雪山上玩“抖鹰”,合法吗?[EB/OL].https://k.sina.cn/article_2370746434_8d4eb842027009z0p.html,2018-08-30.;并非“乌拉满族鹰猎习俗”(41)2008年11月“乌拉满族鹰猎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民俗类。代表性传承人的杨某某则因私自捕鹰、驯鹰和鹰猎被刑事处罚,而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指出,仅有获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吉林市鹰猎文化传承协会”可以驯养并繁殖苍鹰。(42)王晓晨.保护野生动物,禁踩法律红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EB/OL].http://jlltqfy.e-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1/09/id/6286728.shtml,2021-09-26.通过环保部门及主审法院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应不难看出,他们并不完全反对传承“驯鹰术”,但强调必须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进行。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文化和旅游部令第3号)以及地方同类规章的规定可知,代表性传承人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但构成特定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群的个体却有很多。因此,面对“鹰”之来源的合法性以及驯养的普遍性问题,很难不引发人们对“非遗传承”与“玩鹰特权”的“无效”争议(43)任江波.消失的驯鹰人[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187883999831766&wfr=spider&for=pc,2022-01-06.,而这无疑也彰显了文化传统与动物保护的国家法矛盾。
除前述代表性项目外,尚有“民俗类”国家级代表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44)“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于2011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以及被列入“传统技艺”类的新乡市级代表性项目——“鹰猎”(45)“鹰猎”于2012年12月被列入第三批新乡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等,而其有序传承也不同程度受到司法行为以及民间组织的诟病。如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为代表的动物保护组织并不否认“驯鹰术”的文化价值,但它们出于动物保护的单一面向还是将之批判为“陋俗”,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简称《动保法》)等法律法规作为立论基础,从而在舆论上深度影响“驯鹰术”在中国的发展。(46)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中国绿会”“绿会”等,其不仅在百度、新浪、搜狐和头条等门户网注册专用账号,且开发官网http://www.cbcgdf.org/和“中国绿发会”微信公众号等。通过这些网络媒介,自2017年以来,相继发表《绿会秘书长:民俗不应成为违法的借口,为盗猎背黑锅》《志愿者反映吉林又一承传“鹰猎习俗基地”挂牌成立,陋习何时停止?》《“鹰猎”陋俗危害大,宜早日摒弃并作出合理合法改变》《绿会致函吉林市委、市政府:建议改变“鹰猎”陋俗,并提出3点改进意见》《盼早日解决“鹰猎”习俗不合理合法情况,绿会致函国家林业局》《河南新乡非遗鹰猎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宣传非法捕猎?》等网文。对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详请自查,此不赘述。通过上文之述可知,“驯鹰术”是一个世界性人类文化表现形式,且兼具物质生产和消遣娱乐等多重社会属性。尽管欧美国家亦有动物保护组织极力反对“驯鹰”行为,但相较于中国基于警示的刑事判决或行政处罚,前者似乎还仅停留于民间,是一种折射于动物伦理的纯思想争辩。或许受制于法律属性的不同,多数联合申报“驯鹰术”的亚非国家却将之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由是观之,虽然“驯鹰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基本一致,但其在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类型确认以及相应司法行为和民间辩争,却也体现了不同传承人群的差异性伦理认知。在笔者看来,与以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47)《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初由原林业部和农业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法条共同制定,1988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并于1989年1月14日由原林业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施行,此后经多次修订。现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乃2021年2月5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的调整本,内列野生动物980种和8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的“鹰”为基础形成的“驯鹰术”相比,由“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鸿茅药酒配制技艺”(48)“鸿茅药酒配制技艺”于2014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属“中医传统制剂方法”的扩展项目,申报地区为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保护单位为鸿茅药酒文化研究会。引发的司法事件,不仅涉及多个国家部门,且触发人们对这一制药传统的质疑,更在后续发展中引动社会各界对“动物保护法”甚至“刑法”的怀疑。可以说,“鸿茅药酒”的二次事件把非遗项目中的野生动物使用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具体来说,最初的“鸿茅药酒”事件源自一场发生于2017年12月底的因“名誉侵权”导致的跨省逮捕案件,此时仅是当事人质疑该传统医药的“夸大宣传”和“毒副作用”,但在2018年3月,网民“大王”于“春雨医生”网直接质疑“鸿茅药酒”所用原料——“海量”豹骨的来源是否合法,(49)大王.公然用濒危野生动物入药,鸿茅药酒底气何在?[EB/OL].https://www.chunyuyisheng.com/pc/article/120485/,2018-03-20.从而引来更大范围且持续至今的群体质疑。早在2006年3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下发《关于豹骨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中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已全面禁止从野外猎捕豹类和收购豹骨”,并制定“为避免药品生产企业的经济损失,对药品生产企业有库存的豹骨,准许其继续使用完毕”的缓冲条款。(50)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06年3月21日印发《关于豹骨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国食药监注〔2006〕118号)。然而,在鸿茅药酒生产企业——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两次回应中,均把“豹骨”来源解释为“购买”(51)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查整改报告(内鸿国药〔2018〕119号),2018年4月26日;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鸿药字〔2018〕147号”,2018年6月5日。具体内容此不赘述,详请自查。。其实,早在企业回应前,就有社会人士宁方刚于2018年4月16日实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致信询问“海量豹骨从哪里来”,(52)风华之羽.北大医学部博士再致国家药监局:“鸿茅药酒”海量豹骨从哪里来?[EB/OL].https://zhuanlan.zhihu.com/p/35824361,2018-04-18.而社会人士雷闯则向内蒙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公开鸿茅药酒配方中豹骨采购来源等相关资料”,但后者却在2018年5月29日的回复中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依法不予公开”,且同样将豹骨的来源定位于“购买”。(53)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5月29日向雷闯寄送《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食药监函〔2018〕95号)。此函具体内容此不赘述,详请自查。由此可见,“购买”显然违反前述部门规章,而这无疑也是该事件持续发酵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且直接凸显法律之于不同人群的差异性认知。
从现有国际法来看,豹在1973年就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54)包括马来云豹、云豹、花豹和雪豹4种。,而中国作为缔约国,于1988年将之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且为国家一级一等保护动物,至2008年又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位处近危物种(NT)行列。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显示,中国针对“动物犯罪”定下3种十分严苛的罪名,即“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和“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结合这起事件的各方回应,以及《关于豹骨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可知,2006年1月1日至今,任何涉“豹”行为都是“情节特别严重的”的犯罪。据此,“这种明显违背珍稀濒危动物利用常理、违反公约精神和国际国内法条款、不符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进入国家级名录是需慎重的,否则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合规性、合法性和严肃性。”(55)陈红雨.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物利用问题[J].学术评论,2019,(2).
中药对动物的使用是极为广泛的,而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传统知识,其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医疗功能。经“药智数据”的“中成药处方”数据库查询,即可发现大量涉及濒危野生动物的中成药。(56)如“虎骨药”13种、“豹骨药”42种、“熊胆药”109种、“羚羊角药”122种、“蛇药”366种、“鹿药”371种以及“麝香药”463种等。“药智数据”之“中成药处方”数据库,网址https://db.yaozh.com/chufang,2023年6月26日查询。面对如此多样的“动物药”,我们岂能仅关注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类文化表现形式,却不理会作为自然资源之动物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当这些野生动物因人类行为走向灭绝时,那些所谓“动物药”又怎能维护人体健康,而相应的制药技艺也只能“纸上得来终觉浅”,成为自然反制人类的一种有效手段。除了中药,传统技艺领域也是动物,特别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使用的“重灾区”,而饮食之外,工艺美术中的“象牙”“犀角”“玳瑁”“盔犀”“珊瑚”等显然不纯是自然“材料”,相反对它们的任一使用方式都是违法必究的犯罪行为。例如联合国大会专门于2015年7月30日通过《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的决议(57)倪红梅,顾震球.联大就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通过决议[EB/OL].http://www.rmzxb.com.cn/c/2015-07-31/544088.shtml,2015-07-31.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or World Wildlife Fund,缩写为WWF)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都在为保护大象奔走呼吁,他们希望借助国际立法以推动全面禁止象牙及其制品贸易。,而中国作为该决议的发起国之一,于2016年12月30日印发《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其中规定“2017年3月31日前先行停止一批象牙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2017年12月31日前全面停止”,并责令文化部门“积极引导象牙雕刻技艺转型”。(58)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16〕103号)[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3).由此可见,作为国家级代表性项目的“象牙雕刻”(59)2006年,由北京市崇文区和广东省广州市申报的“象牙雕刻”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保护单位分别是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和广州市大新象牙工艺厂;2014年,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申报的“常州象牙浅刻”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保护单位为常州剑波雅刻艺术品有限公司。,已不再符合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有违国家法律法规,显然是失去传承能力的文化表现形式。
从表面上看,列入中国“四级名录体系”的代表性项目并未全然产生行政或刑事问题,但前述相对典型且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例如不进行立法规避,显然会带来更大的伦理问题,甚至导致相关动物的灭绝。不过,涉及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依然需要厘清法律和常识的界限(60)如作为“大学生掏鸟窝被判十年”案的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2年4月废止,且为《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取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22,(4).,而后者即包含大量地方性传统知识。尽管部分由动物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尚未成为代表性项目,但这并不代表其未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而这其中既包括娱乐性“宠物”饲养和经济性“动物”养殖,也包含应对野生动物破坏农业生产的“猎捕”行为。就前者来说,宠物的当代发展早已突破猫狗等常见物种,甚至因“异宠”泛滥严重干扰区域生态平衡,而以鹦鹉等为代表的鸟类饲养就曾引发多起刑事案件。此外,动物养殖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野”与“非野”的模糊性界定也为此类生产活动带来阻碍;后者则是如何评估自然承载力之于野生动物数量对粮食安全和个体经济的影响,而野猪的区域泛滥即是典型。总之,以动物为要素形成的各类文化表现形式纵然有违现行“动物保护法”,但其非物质性却是鲜明的。据此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提倡动物伦理而否定这些人类创造,只是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则是我们必须考量的现实问题。
四、政策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联动
典型案例的粗线条书写虽然只能从侧面呈现非遗保护之于动物伦理的发生状态,但这种社会现实却彰显了文化治理与生活常识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矛盾交叉点。上文之述表明,以“彝族火把节”为代表的动物使用类遗产项目在国际非遗保护过程中或仅为个案,这同中国频繁出现的涉及动物使用的非遗案件,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有着显著差别。也就是说,尽管以法律为代表的国际国内政策均有直接针对非遗和动物的保护文本和措施,且均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但前者并未产生具有惩罚性的国际法争端,后者却在国内法的刑罚执行中体现了非遗法律法规与“动物法”的不可通约性。换言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相关判词或各方当事人的回应在认定涉案事象为非遗代表性项且并强调需依法报批驯养动物时,并未从涉案人员是否立足非遗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非遗传承进行审判,即重视“动物法”而忽略非遗法律法规。时至今日,面对层出不穷的动物使用类非遗案件,中国尚未对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而非遗法律法规在此过程中的缺位则凸显了立法保护非遗的弱势情形。然而,为了尽可能降低动物伦理对非遗保护的影响,以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则在既有国际文书的基础上做出了新思考。
如果仅从《非遗公约》来看,其约文表述即有多处涉及“自然”或“环境”的宏观话语,而在强调其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关联时,也确认了文化与生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二者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发挥作用的统一性。据此而论,尽管《非遗公约》没有任何条款直接涉足动物伦理,也未曾将动物伦理作为拟列入《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得以通过审查的显性标准,但非遗之于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功能却在非遗概念的“三个符合”,即(1)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2)符合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以及(3)顺应可持续发展中,隐含了何种非遗项目可被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基本原则。相较于(1)和(3)的客观性,(2)的主观性则让《代表作名录》的列入标准更难把握。然而,这一相对模糊的国际法表述,却成为各缔约国不得不面对的技术难题。尽管立足“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文化多样性是拟列入《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但如何看待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巨大争议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社区、群体或个人在面对文化冲突时的包容性心态,则是非遗保护过程中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而中国文化传统如何与世界接轨,并获得广泛理解和接受,更是重中之重。此外,“彝族火把节”虽为各缔约国申报相关代表作项目提供了“避险”参照,但在笔者看来,警惕欧洲中心主义的当代泛起也是必不可少的。
动物伦理在非遗保护中显然已成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横向问题,但在《非遗公约》条款,特别是第三条“与其他国际文书的关系”对“使用生物和生态资源”的表述尚未修订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减少其对遗产项目的申报影响。除缔约国主动调整申报用语,教科文组织也作出了积极回应——2016年第六届缔约国大会(6.GA)在修正《操作指南》时,于新加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中对“动物使用”问题作出了说明,其核心表述则集中于“6.1.1食品安全”和“6.3.1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而“6.1.2医疗保健”和“6.3.2环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等也不同程度隐含了动物伦理与非遗保护的生态互动功能。(6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178~179段;189~190段)[G].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Z].2020:52~53;57~58(内部资料).
笔者认为,6.1.1和6.3.1都突显了积累于人类生产生活以及认知自然和宇宙过程的“知识与实践”。就6.1.1来说,其所表述的“捕鱼、狩猎、放牧”无疑是涉及动物使用的人类行为,而其目的不仅是在保护相关非遗的基础上,确保人类的“食品安全和充足营养”,更是在保障人类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在6.3.1中,不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潜在作用,从而促进环境可持续性”,还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管理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无疑在更深广的层面将动物伦理纳入其中,而这种表述的目的则是在以非遗为代表的“经验”保护中维系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这些被置于国际法中的条款是否蕴含利用或借助动物以实现“竞技”或“娱乐”目的的“弦外之音”,尚不能随意揣测,毕竟缺乏更为细致的国际法释义。不过,从已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非遗实践可知,“竞技”和“娱乐”等非因“生存”或“信仰”等产生的人类文化表现形式,不仅没有受到全面“限制”,相反还有不少项目被直接冠以“竞技”或“娱乐”之名。虽然动物伦理已是不可回避的非遗保护横向问题,且在遗产项目申报中并未成为“必要”甚至“充分”条件,但任何缔约于动物保护类国际文书的《非遗公约》缔约国,其动物使用类遗产项目在实践过程中,亦不能违反这些国际文书以及本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非遗保护并非单纯保护非遗本身,而是一个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系统工程。作为一种环境表征或构成要素,不论畜禽动物,还是宠物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为非遗实践提供必要“材料”或“对象”时,理应得到相关“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协同保护。尽管“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出现相对晚近的学术概念,但其国际传播却直接下沉到了民间。现有资料表明,“可持续发展”最早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于1980年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提出,不仅是一个被视为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处理代际生存关系的路径和策略。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为“可持续发展”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则提出与前者相对一致的“可持续利用”概念,认为“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速度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下滑,保证其能够满足当代及后代的需求潜力”。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便是包括动物的有形之生物。
虽然“可持续”和“多样性”均源出生态学,但诸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表明,各种人类文化表现形式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随着国际社会对各类文化表现形式之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作用认知的加深,前者的相关表述为“文化多样性”概念的产生奠定了参照对象。毫无疑问,《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简称《多样性宣言》)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简称《多样性公约》)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而后者则从国际法层面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财富。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指导性原则之一。由此《多样性公约》将“文化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而且“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在笔者看来,通过实践介入《多样性宣言》和《多样性公约》的《非遗公约》,上承前者下起后者,而其“前言”所称非遗“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保护非遗就是“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则进一步彰显了三者的历时性关联。
据上笔者认为,非遗保护的理论基础离不开“可持续”和“多样性”的支撑,而随着两大理念的国际推广,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关系也愈发为世人认同,故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史以来首份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文书——《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了与之对接,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11月相继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而前者的核心内容则于2016年6月被修入《操作指南》,即上文所述“第六章”,2018年6月(13.COM)再次修订《操作指南》时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全面成果框架》。如今,教科文组织主导下的国际非遗保护也在跟进联合国系统正在全球开展的“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2020~2030年)”。总体而言,每一份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文书及其社会实践都蕴含着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协同观照,而两大国际政府间组织针对原本彼此分离的工作职责也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只不过教科文组织更为主动地跟踪联合国相关动态并及时调整自己的非遗保护策略,而这种国际政策的协同发展,也给予各缔约国重新思考包括动物伦理在内的一切“可持续”和“多样性”的契机。
相较于国际层面积极推进不同领域政策之于非遗保护的协同性,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则相对迟滞。上文之述表明,中国非遗保护中的动物伦理问题不仅十分突出,且所涉及的动物种类极为多样。然而,同国际社会对待动物使用类拟列入《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的态度有所差异的是,中国司法部门在弱化非遗法律法规的同时,强以“动物法”判罚相关人员,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否在前者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下从事传承活动亦不明确;在民间社会不论野生动物还是驯养动物(牲畜或宠物)更是常为“动保人士”加以道德审判,而“驯鹰术”的多国联合申报及其在中国司法过程中的遭遇则是说明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其实,查阅入选《〈非遗公约〉名录》的典型动物使用类非遗实践的申报书及其决议,即可知道各缔约国在申报相关项目名录时,其文本表述重在呈现人与动物的生活关系,而非直言其作为一种生物的经济价值或娱乐功能。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次申报则从项目名称的去“羊”化(由“马背叼羊比赛”改为“阔克博如——传统赛马”)到文本书写中“羊”的“偶像”化,均彰显了该国立足“尊重”原则以规避“生活现实”的策略。不过,这种情形的出现无疑有来自教科文组织基于“彝族火把节”所设定之隐形标准的影响,但在中国,即便出现大量涉及动物使用的非遗案件,也未促进文化部门对司法判决的思考。
不可否认,以法律法规为代表的动物类政策文本在中国正趋于体系化。目前,涉及动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渔业法》《生猪屠宰条例》以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而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的《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动物园管理规范》等也对动物使用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在国际非遗保护领域开始将动物伦理与非遗保护相对接时,中国的非遗法律法规和“动物法”依然走在相互独立甚至彼此分立的立法和司法道路上。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不论野生动物,还是畜禽水产,抑或伴侣动物,都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反映。保护生物多样性无疑是促进文化多样性动态生成的有效手段,但过度规训人类对生物的影响显然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中国针对动物使用类非遗案件的裁判基本是摒除文化属性的纯司法行为,这显然干扰了具体遗产项目的存续力及特定族群生活的正常运行。不过,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绝不能对动物伦理视而不见,相反如何促进两者的协同实践则是必然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如今,动物伦理之于非遗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但二者本就分立的局面则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变得愈发明显。虽然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是哪种动物传播了这一病毒或具有对该病毒的传播能力,但部分动物却在这一十分严峻的时段背负了更多“生命”之“危”。
自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后,中国各部门各领域均开启十分坚定的“禁野”活动。而与生产习俗密切相关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也迅速修订,这不仅影响到部分驯养技术相对成熟的特种养殖业的有序发展,是否把六畜之一的狗纳入其中的官方回应更是造就一场持续至今的舆论争辩。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据此制定的《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也进入紧急修订日程。经过两年多的意见征求和审议,前者于2022年12月3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后者则被更名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2023年6月30日公布。此外,涉疫冷链食品的检验检疫也愈发严格。总体来看,源自这场“疫情”的“动物法”修订过程基本是针对饮食习俗的,但这无疑也动摇了包括传统医药、传统技艺乃至传统体育、杂技与竞技(如马戏)等类别代表性项目的存续力。其实,在疫情肆虐的关键时段,欧美社会同样对养殖类野生动物下达“扑杀令”,而染疫之水貂则首当其冲。
尽管从教科文组织现有“《非遗公约》名录体系”中无法查到涉及水貂的项目,但这并不否认具有水貂养殖传统的欧美社会,其水貂养殖技术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皮草制作不具有非遗性。因此,当病毒在人与动物之间产生相互传播的危险时,我们岂能不重新思考人类对特种经济或奢侈消费的需求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疫情防控期间还出现一系列因人之“禁足”导致野生动物“进城”的事件,正如美国芝加哥都市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赛斯·马格尔(Seth Magle)所言:“这些现象可能在提醒着人类,动物们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不认为城市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它们的确是”(62)法兰瓷.疫情新现象:野生动物在封锁城市逛大街[EB/OL].https://grinews.cn/news/疫情新现象野生动物在封锁城市逛大街/,2020-03-31.。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然超越生存空间的限制。有研究表明,“全世界约60%的新发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疾病,而人畜共患疾病中超过70%源于野生动物。”(63)陈俊侠,连佳曼.新冠疫情应促使人们遵守野生动植物贸易政策——访《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秘书长伊沃妮·伊格罗[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174741898797126&wfr=spider&for=pc,2020-07-14.只要人类还与动物一起生活,人畜共患疾病就无法被彻底消灭,但人类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风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遵守各类现行国际和国内法。不过,人类对动物及其制品的消耗无处不在,故面对种群数量的降低,必然要创设一定的替代方案。如合法合规的发展动物驯养产业,(64)如我国原林业部(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就曾于1997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发布《黑熊养殖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林护通字〔1997〕56号)。但此间出现的动物伤害事件依然考量着人类的伦理道德,而由“活熊取胆”引发的社会舆论则是极具典型性的例证之一(65)参见张璐.“活熊取胆”风波的法律透视[J].中州学刊,2012,(4);杨通进.人对动物难道没有道德义务吗——以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为中心的讨论[J].探索与争鸣,2012,(5);姜燕.传播文明价值观,谨防以情绪化、戏剧化报道吸引眼球——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报道解析[J].新闻记者,2012,(6);郭欣,严火其,姜萍.科学知识社会学视阈下“活熊取胆”争论事件探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5)。。由此可见,即便没有入选任何类别(级别)的“非遗名录”,动物之于人类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也不再只是伦理或法律的单一面向。
就《非遗公约》来看,任何非遗实践都来自相关“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确定,因而社区、群体和个人有权决定是否“传承”或“放弃”这一或这类遗产项目。但保护非遗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同时也能从侧面助力生物多样性,因而作为非遗保护主体的政府有责任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上,明确哪些涉及动物的行为可被鼓励,哪些行为必须规避。换言之,立法保护动物和非遗不只为了惩罚违禁者,也是在引导社区居民的伦理道德。不过,非遗保护的中心部门虽在文化,但非遗本身并不止于文化的事实表明,其存续力仍需其他部门的鼎力协助。在笔者看来,尽管中国于2022年对“部级联席会”的参与部门进行了增加,(6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调整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国办函〔2022〕13号),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1月26日成文,2022年2月17日发布。但不可否认的是,未被列入名单的司法部门(公检法)、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民政部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也同非遗联系紧密,如跨地区运输马戏用野生动物既受管于公安部,也脱不开交通运输部。据此可知,针对非遗保护的跨部门协作既需扩大,也应纳入非国家部门的其他多元行动方,如民间组织(NGO)等。总之,非遗保护与动物伦理的关系极为复杂,针对二者的各类政策亦纷繁多样,但双方政策的协同发展不仅能助力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联动,更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结 语
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横向问题,动物伦理毫无疑问地成为保护非遗的重要影响要素。尽管在《非遗公约》出台的20年里,动物伦理并未真正成为非遗实践是否能通过审查的关键标准,也未彻底阻碍缔约国就相关遗产项目的成功申报,但自其为教科文组织发现以来,合理规避涉及动物使用的话语表述就成为各缔约国申报此类项目的常用做法。然而,以非遗为代表的文化多样性和以动物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在国际法层面显然是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但其在维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却是相互联动的整体。随着动物伦理对非遗保护影响的持续深入,教科文组织也逐渐意识到协调二者关系的重要性。尽管《非遗公约》的非遗定义已从“三个符合”的角度确定了“相互尊重”原则之于动物伦理的审查标准,但为了将这种相对隐含的表述更为直白地展现于各缔约国,并有效对接联合国各项“可持续发展行动”,教科文组织相继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两份指导性文件,还两度在《操作指南》中加入涉及动物的可持续发展内容,从而于国家层面赋予人们保护非遗的基本标准。由此可见,从国际法层面尽可能弥合动物伦理与非遗保护的分离状态,一直是教科文组织努力的重要方向。
同国际社会相似,中国不仅存在大量涉及动物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且有部分代表性项目与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遗产项目相同,如“驯鹰术”即是典型案例。不过,涉及非遗的司法案件表明,不论野生动物还是蓄养(野生)动物,不论用于祭祀食用还是欣赏娱乐,非遗法律法规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而非遗法律法规与“动物法”的分立状态,直至新冠疫情“结束”都未得到文化、农林和司法等部门的有效观照。更重要的是,“动物法”的订立和修正虽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维系提供了法治保障,却未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给予立法促进。此外,尽管保护动物以维系生态平衡的自然意识自古延今,但其在当代社会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彰显出些许矛盾,而上文所举例的诸多案例即是明证。进一步讲,现代动物伦理尚未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而部分“动保人士”的激进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作用。正如上文所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的共同作用下推进的。因此,作为生态环境之构成的动物和作为社会人文之组成的非遗,并非截然分开的两种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据此笔者认为,《非遗法》和“动物法”的未来修正必然要以二者的协同对接为准绳。
作为《非遗公约》的缔约国,又有“彝族火把节”为前例,中国理当更加明了动物伦理与非遗保护的关系,而分类实施动物使用类代表性项目保护的基础,则是对“四级名录体系”进行全面清查。正如朝戈金所言:“我们希望在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引入伦理分析的视角,并形成连续性讨论。这或许有利于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向度促进‘提高认识行动’,加强履约的能力建设,进而探索未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路径,厘清实践中的伦理挑战,进而规避伦理误区,并止步伦理禁区。”(67)朝戈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绎读与评骘[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5).而乌丙安在《非遗法》刚一出台,便提出“尽快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协调配合实施的有效机制”和“尽快制订有关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细则”的建议,而前者之于非遗保护和动物伦理的司法协同则具有决定性意义。(68)乌丙安.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两点建议[J].西北民族研究,2011,(2).对此,《“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文旅非遗发〔2021〕61号)已就“研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推动制定实施条例”作出说明。据此笔者认为,《非遗法》的修订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立法工程,既要广泛征集社会意见或建议,又要在文化部门的主导下,于现有部级联席会的基础上增加司法、林草、卫健、交通等部门,协商具体法条的精准表述,从而在保障非遗法律法规的法律效力时,尽快出台“非遗法实施条例”,进而提升其可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