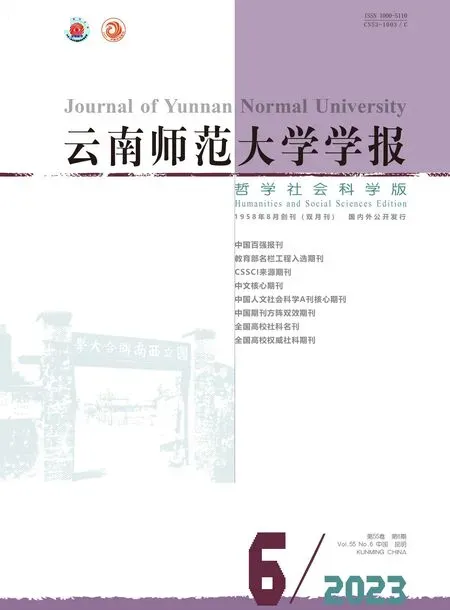格萨尔史诗传统的在地保护实践与社区内生动力*
央吉卓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03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2008年,该公约缔约国大会第4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简称“政府间委员会”)拟订的《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通过设立名录列入机制,为各缔约国保护其领土上存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规定了法律责任,也为国际社会保护人类共同遗产建立了国际合作的基线行动。
2009年9月,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4次会议期间,中国政府申报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Gesar epic tradition)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表作名录》)(1)Government of China. Nomination file No.00204 for Inscription of “Gesar epic tradition” in 2009 (4.COM)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EB/OL].https://ich.unesco.org/en/RL/gesar-epic-tradition-00204, n.d., accessed on May 26,2023.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卷宗可从以上网址获取,行文中或采取夹注方式,即(Nomination file No.00204),不再另作说明。,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一方面是对史诗传统传承现状和既往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又为新时期格萨尔保护的根本宗旨和工作思路指明了方向。此后,经过全国各利益攸关方14年的共同努力,该遗产项目的保护实践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为做好非遗系统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格萨(斯)尔史诗在内的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在国家层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而今正在迈向新时代新征程。
在《非遗公约》即将迎来其20周年华诞之际,我们不难注意到,截至2023年2月17日,已有181个国家加入该公约,不仅在国际层面牢固确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还同时确立了“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2)本文但凡仅出现“社区”,则是以俭省方式指代“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the communit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concerned,缩写为the CGIs,以下或统称为“社区”),同时涵盖三者之间互涉的主体间性。的核心作用(Resolution 9.GA 13, para.8)。(3)按国际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通行做法,本文举凡引述的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工作文件,均可按文中括注的文件代码从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unesdoc.unesco.org)获取。若非必要,行文中不再另作说明。因此,围绕“社区”这个关键词,探讨“格萨(斯)尔史诗传统”从基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学科化实践到进入非遗保护的遗产化进程,本文力图将“社区赋权”和“参与式发展”作为观察地方层面的社区行动机制,以期说明厚植人民至上的情怀与坚持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理念高度契合,而将扎根于乡土的村落、家族、贤能的社区力量充分融入非遗传承发展的在地化实践,不仅有助于服务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也有益于在基层民间将文化传承转化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问题导向:何谓“社区”又何以“社区”?
在讨论“社区”这个关键词之前,我们尚需通过回溯学术史以生发格萨尔史诗保护的主要路径。究其根本而言,非遗保护属于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的公有领域,由一整套法律法规、政策计划、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来推动,从国际法的以社区为基础到国内法的以人民为中心,也是对既往从学术研究资料着手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的继承和超越。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和各级政府持续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开展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可谓筚路蓝缕七十载。通过抢救性记录和重点保护,格萨尔史诗不仅在音影图文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在拓展研究视野、革新方法论和建设话语体系等方面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史诗资料学建设历程中,作为对沉寂10年并遭受严重冲击的现实的回应,确立了以抢救为重心的工作目标,对史诗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参与搜集、翻译、整理工作的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格萨尔史诗的内容属性和本体价值进行学理思考。这类基于文本进行分析阐发的学术探索影响深远,总体上成为贯穿20世纪下半叶的主要研究模式,从而在客观上形塑了“以文本为中心”的格萨尔史诗研究路径。
随着20世纪80年代相关工作的陆续恢复,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再次呈现蓬勃之势,但早期搜集整理成果出现严重损毁,叙事传统的存续力面临风险,尤其是口头史诗演述及其受众范围的萎缩日益凸显。恰在此时,扎巴老人、桑珠老人、才仁旺堆、玉梅等史诗艺人(后来代之以“演述人”)被史诗调查研究人员发现,他们迅速组织人员对几位演述人的口头文本进行了录音、记录和整理。彼时,几位演述人已不复盛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人亡歌息”的危险,因此格萨尔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抢救”。经各方参与者的不懈努力,跨越时空,时长可观且弥足珍贵的史诗口头演述本得以留存至今,而各地相继召开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说唱艺人研讨会”和“说唱艺人表彰会”等会议不仅高度认可了史诗演述人的价值和贡献,同时客观上提升了活态史诗传统的可见度。
世纪之交,正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遭遇新思想、新方法、新理论,倡导民间文学研究当“以演述为中心”,关注“活态性”,建构“文本与语境”对举的研究理路,酝酿学科范式转换的特殊时期。而此时,格萨尔工作中记录整理“民间艺人说唱本”的工作已开展逾10年,有关史诗演述人的生活史、演述曲目和演述文本等资料已相当丰富,学科范式转换与“说唱艺人”调查研究的热潮相互碰撞生发了新的学术增长点。时至今日,格萨尔史诗研究中“以艺人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不仅成果斐然且方兴未艾。
2004年12月,中国加入《非遗公约》。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施行。在近20年的历程中,国家层面的保护工作以“十六方针”为指引,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各级各类文化主管部门助推的保护策略,代表性传承人在其中主要扮演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从代表性项目到代表性传承人,史诗传统保护实践以行政认定和政策扶助为主,同时也鼓励传承人群体参与建档和保护保存工作。各地格萨尔工作在保护史诗传承人和呈现其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包括抄刻本、唐卡、雕塑、石刻、风物遗迹等)方面用力颇勤;国内非遗整体性保护理念和政策支持也促使史诗传统腹地的各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继落地。随着旅游业和文创产业的兴起,格萨尔史诗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象征成为地方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的衍生点之一,各利益攸关方纷纷参与到与史诗传统相关的“生产性保护”实践中,为当地社区和群体提供了可持续生计。科研机构一如既往地开展调研和出版学术成果,以此促进对格萨尔史诗的价值认定和面向公众的媒体推广。在此进程中,“格萨(斯)尔”史诗保护在国家层面也取得了诸多实绩。2006年和2014年,来自9个代表性社区的“格萨(斯)尔”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类别:民间文学;项目序号:27;项目编号:Ⅰ-27);2009年9月,“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4年,“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截至2018年,共有14位史诗演述人先后被国家文化主管部门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包括来自藏族的次仁占堆、才让旺堆、达哇扎巴、阿尼、桑珠、和明远、巴嘎、格日尖参、巴旦和才智,来自蒙古族的吕日甫、罗布生和金巴扎木苏,以及来自土族的王永福;2023年,“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总体上看“格萨(斯)尔史诗传统”的保护路径,前述两种传统工作模式似乎已因袭承制,并没有因其遗产化进程——从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到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换言之,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从非遗领域到学术领域,不论是偏重于文本还是专注于说唱艺人,都可以理解为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学术传统及其学科化导向在不同时段对文化政策及其实施路径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将“以文本为中心”和“以艺人为中心”的两种模式作为镜像,用以映射非遗保护的进程中格萨尔史诗的多样化在地实践,由此自下而上去探查非遗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那就需要回到“社区”这个关键词上来。
实际上,自《非遗公约》通过以来,“社区”这个凸显集体性的工作概念便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社区参与”则是保护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权利赋予。为此,《公约》第十五条“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要求“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地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非遗领域的学者们认为,无论是在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国际化保护行动中,还是在国家层面的体制机制中“社区”始终是根基性问题,其内涵和外延触及非遗保护的观念层面,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钩沉“社区”概念的语义渊源及其语用变化并非本文所求,已有不少学者围绕“社区”或“社区参与”等相关话题展开过跨学科探讨。本文旨在立足非遗保护的基本立场,将“社区”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反思此前相关工作和保护历程,进而探索新时期格萨尔史诗保护的路径。
那么在非遗保护领域中,何谓“社区”?又何以“社区”呢?尽管在《非遗公约》及其衍生的基本文件中并没有对社区作出确切界定,但细读《公约》序言和相关条款,其字里行间已经道出了“社区”的能指和所指。按《公约》第二条“定义”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G].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2020:7~8(内部资料).该定义实际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社区对其非遗有共同的价值认定;二是非遗对于社区而言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立足上述两个层面逆向推衍可知,对某一非遗项目有共同的价值认定,且围绕该遗产项目形成文化认同的人群即可被认定为社区的构成。(5)巴莫曲布嫫.非遗关键词:社区、群体和个人[C/OL].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俗学专业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线系列讲座第十五讲,2020年10月31日,腾讯会议号935 302 504.换言之,社区边界高度依赖于非遗项目的确认和界定,其“非固定性、非均质性以及指涉范畴的巨大弹性”(6)杨利慧.以社区为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政策中社区的地位及其界定[J].西北民族研究,2016,(4).,既彰显了非遗项目的共享性或曰包容性,同时也体现了遗产项目的代表性而非排他性。
翻查中国向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申报材料(Nomination file No.00204),在述及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现状时,主要列述了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所居住的农区和牧区,并将之作为整体上的代表性实践社区。一方面,这种表述策略充分彰显了史诗传统的代表性和共享性;另一方面,在社区参与的信息提供中,因采用自治区或省+具体地名的枚举法,虽然涉及来自5个自治区/省的18个具体地名,但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社区的非固定性和非均质性,从而难以用更具象化的细节说明传承、实践该遗产项目的社区多样性。不论怎样,我们可以从政府间委员会的决定(Decision 4.COM 13.14, para.2)来看该将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的支持性理据:
R.1:格萨(斯)尔史诗的世代相传得到了清晰的说明,该遗产项目为相关的几个民族社区提供了认同感和持续感;
R.2:将“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列入《代表作名录》将有助于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促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R.3:申报材料中描述的保护措施包括:巩固史诗传习和演述的文化空间,同时聚焦于研究和传承;
R.4:相关社区参与了申报进程,并提供了尊重其意愿且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明;
R.5:该项目已被列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管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由上可见,政府间委员会分别依据符合《非遗公约》定义、对名录的贡献、保护措施、社区参与、国家清单等5条列入标准(7)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G].2020:24~25(内部资料)。形成评审决定,其中特别述及该遗产项目之于“几个相关民族社区的认同感和持续感”,换言之,这里的认同是跨越族际的。而其他资料也显示,除了以民族、语言、职业、行业、行政区划、经济类型等外部视野来界定社区外,遗产项目的实践地似乎还可向内下沉,在传统社会结构的内部分层和当代实践方式上找到本地的社区观念。
实际上,在格萨尔史诗传统腹地就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勘查的社区类型或亚类型。例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德尔文部落”(dur-bud tsho-pa)就因其在当地被认为与格萨尔王族有渊源关系(该部落自称是格萨尔王族后裔)而备受重视,其史诗保护的多重实践在地方传统的支撑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已成为实践范型。该部落所在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德尔文”村也于2006年被命名为“格萨尔史诗文化村”。因而,“德尔文部落”史诗保护实践的成功与其多重身份认同(尤其是祖先认同)密切相关,这类借助特定身份认同确立保护主体地位的模式在史诗传统腹地并非孤例。这类保护模式甚至成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工作模型从而在传统腹地被不断复制。
有鉴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将身份认同视为格萨尔史诗传承和保护的核心要素,并认可缺乏身份认同则史诗传统的存续力必将面临威胁的观点?是否还有其他超越身份认同而存在的社区类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类社区的保护实践有何特征和意义?基于上述疑问,深入史诗传统腹地调查史诗传统保护的在地化实践变得尤为必要。2020年4月和8月,笔者两度前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开展田野调查以期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江西仲措:村落社区的自主实践与乡村振兴
“格萨(斯)尔史诗传统”跨民族、跨区域和跨语种的共享性及其影响力直观地体现在该遗产项目申报地区(或保护单位)的数量和覆盖面上。仅就藏族地区而言,参与史诗传统传承和保护实践的社区就已数量可观,江西村即为其中颇为典型的村落型社区。通过实地考察,这个村落为我们打开了理解非遗保护当立足社区的通衢,即坚守“以社区为中心”基本立场至关重要。
在当地藏语中,江西村称为“江西仲措”(gyam shis grong tsho),“江”意为具有岩石、岩洞、树木之地,“西”意为吉祥,“仲措”则为行政村。“该村因坐落在具有岩石、树林、河流和野生动物,景色宜人的吉祥之地而得名。”(8)尼玛才仁.玉树市乡镇村社地名文化释义[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9:278.江西村偏居小苏莽乡东南角,地貌以高山峡谷和山原地带为主,属以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该村东连本乡草格村和莫地村,南邻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面达乡格杂村和巴通村,西接囊谦县娘拉乡多伦多村和毛庄乡孜荣村,北连本乡扎秋村。江西村因下辖“江西林场”而为人所熟知。由于辖区土地90%属于林业保护区,林业资源丰富,因此江西村乃至小苏莽乡素有“天然氧吧”和“高原江南”的美誉,颇具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开发的潜力。然而,由于耕地和草场面积狭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9)江西村距小苏莽乡政府所在地98公里,距玉树市193公里,进村道路崎岖且以泥土路为主,三通一平工程(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尚未覆盖该村。且地处林业保护区,长期以来江西村经济低迷、劳动力流失、人口外流、缺乏特色产业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概而言之,头顶“省级贫困村”帽子,加之又缺乏特色产业的江西村曾是地方政府的心病。
其一,“嘎玛嘎哲”唐卡绘制技艺与产业振兴
玉树藏族自治州成立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于1987年7月。近20年的工作实绩,构筑了玉树州扶贫工作“开发地方资源,扶持优势产业”的总体框架和将养殖业、种植业作为重点扶持项目的整体思路。2010年随着“二纵三横”(10)“二纵三横”路网格局:即以州府结古镇为中心,以国道109线和214线“二纵”为依托,以清水河-曲麻莱-不冻泉公路,多拉马科-杂多-查吾拉公路,结古镇-治多县索加公路“三横”省道为主骨架。公路通车里程15793千米,其中国道482千米,省道2122千米,县道1543千米,乡道3257千米,专用道211千米,村道8178千米。参见玉树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玉树州志(1996~2015)[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202.路网布局的基本实现,玉树扶贫工作打破了“两大产业论”的格局,将商业和运输纳入了扶持项目总体规划。2015年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纵深推进,涉及汽车维修、烹饪中心、唐卡绘制和民族服饰制作等领域的扶贫产业园项目陆续落地并成为扶持对象。正是在上述历史进程和新时代背景下,迟迟未能摘帽的贫困村——“江西村”及其村办扫盲班和唐卡绘制技艺传习班进入了扶贫干部的视野。
2015年,在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江西村筹建了以“嘎玛嘎哲”唐卡绘制技艺为主要培训内容的“江西村惠牧职业培训学校”。立足建校元年回顾往昔,在此之前该培训学校依托村落自主力量已走过逾10年的曲折发展道路。据学校创办人益西介绍,江西村青壮年男性大多常年在外务工补贴家用,然而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文盲率较高,他们只能选择技术含量和薪酬双低的工作,而村内青年女性则大多选择外嫁(其中相当一部分女性属于早婚)。由于当地缺乏脱贫致富的客观条件,常年来江西村只能依靠政府的贫困补贴维持生活,收入结构单一。益西认为受教育程度低是造成贫困的主因,因此2005年他主动担负起为留守村内的青少年无偿教授藏语文的责任。从露天课堂到简易教室再到地震期间(11)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7.4级强震,全州6县不同程度受灾,震中玉树市受灾最为严重。的帐篷学校,这所由村民自发组建,集全村物力和人力的村办学校渐成规模,在校人数逐年递增。
办校数年后,学校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提高识读能力来降低村民外出务工压力的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村贫困问题,使务工者具备一技之长才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彼时,主要流传于藏区东部(主要指康巴地区(12)“康”是一个历史地理名称,是藏语“khams”的汉语音译,在旧时汉语文献中曾译作“喀木”或“巴尔喀木”,是中国“藏地三区”(卫藏、安多、康)之一。在汉语环境中,人们习惯于将它称作为“康区”“康巴地区”。康巴地区大致涵盖了今天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且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为核心申报地区的“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13)2006年,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申报的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被入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2008年,由西藏自治区昌都县申报的藏族唐卡(昌都嘎玛嘎赤画派)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媒体的宣传和弘扬下,几年间各类唐卡画院、唐卡绘制技艺培训中心和唐卡艺术传习基地纷纷涌现,各类展销会、展览会和画展中也频频出现唐卡展区,唐卡技艺的可见度得到有效提升的同时,相关从业者亦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回报。有鉴于此,学校将唐卡绘制技艺引入了日常课堂,与毗邻地区交流和沟通的便利性为聘请昌都和德格地区唐卡画师成为可能,而长期的藏语文训练又为学员掌握相关知识奠定了基础。
2011年,学校延请西藏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噶玛嘎孜画派第十代传人嘎玛德勒(1932年出生,籍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嘎玛乡)赴江西村亲授唐卡绘制技艺课程。此后,嘎玛德勒大师每年赴江西村授课成为惯例,其授课时间也从最初的几周延长至半年。为了及时解决学员的疑问,随地随时指导学员,学校又设法从昌都请来驻校教学的唐卡技艺老师旦增江措。经多位名师言传身教,学员的唐卡绘制技艺逐步提升,其中部分学员不仅能够独立完成颜料研磨配色、画笔制作择选、画布绷制打磨等基础备料工作,还能够绘制出符合法度且精美的唐卡画作。2015年玉树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正式授予该校“文化产业示范户”称号。2016年“江西村‘嘎玛嘎哲’唐卡绘画技艺”获准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年,玉树州群众艺术馆和玉树州非遗保护中心经实地考察,现场评估授予该校“玉树嘎玛嘎赤唐卡传承基地”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鼓励具备唐卡绘制技艺系统知识的学员前往昌都、德格和结古等地自主谋生,同时他们也可以继续留在学校作画,画作经多渠道外销,收入均归个人所有。然而,学员们通常会将部分收入自愿回馈学校,而这部分收入则成为新建和维修教室、画室、食堂和宿舍的资金来源之一。随着学校规模和知名度的提升,其生源从本村拓展到毗邻地区,且女学员占比逐年上升。据不完全统计,该校学员曾达到近百的规模,而他们的画作也获得了各地各级传承人的认可和赞赏。2017年,玉树州文联、玉树州文化局、玉树州书协共同授予该校“玉树地区‘嘎玛嘎哲’唐卡画派创作基地”称号,此后江西村在玉树乃至毗邻地区声名鹊起,当地政府将江西村树立为实践“精准扶贫”政策的模范典型,予以高度评价。近年来,当地主管部门立足实际,统筹规划,扶持该校成立了“玉树市福利唐卡绘画有限公司”。
其二,史诗人物系列唐卡与文化振兴
本文考察对象玉树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毗邻西藏昌都、四川德格和玉树市多个县乡,地处交通要冲,区位优势显著,文化资源丰富,可谓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腹心地区之一。据当地长老介绍,史诗演述传统曾在当地颇受民众喜爱。借阅、传抄乃至供奉史诗抄本的情况亦不鲜见。然而,随着劳动力流失和人口外流加剧,史诗传统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在江西惠牧职业培训学校就读的多位当地年轻学员均表示此前对史诗传统知之甚少,仅对史诗主人公和几位核心人物有些许了解。
2009年,随着中国政府申报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Gesar epic tradition)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表作名录》),史诗传统的可见度得到全面提升。包括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和手工技艺等在内的多种文化表现形式与此前格萨尔史诗“以艺人为中心”和“以文本为中心”的传承和保护模式之间的张力引起了多方讨论。挖掘、传承和保护史诗传统的多种实践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格萨尔石刻和壁画乃至唐卡绘制及其作品在各类文艺和商贸展销会中吸引受众驻足观赏和消费的盛况被媒体争相报道。2016年初,江西惠牧职业培训学校的决策者从延请地方耆老讲解地方风物传说、讲述史诗故事以及师生共读史诗书籍等举措入手,组织在校学员深入了解和学习史诗传统。随后,该校通过遴选技艺成熟的学员绘制史诗人物系列唐卡的工程正式启动。
史诗人物系列唐卡的工程历时数年,于2019年陆续完成绘制工作。同年8月,120幅史诗人物系列唐卡在“2019年玉树州唐卡文艺博览会”正式展出,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江西惠牧职业培训学校及其史诗传统保护实践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而采用噶玛嘎孜画派技艺所绘史诗人物系列唐卡画作不仅成为该校的“镇校之宝”,绘制史诗人物唐卡的相关知识和实践亦成为该校的特色课程。毋庸讳言,正是由于史诗人物系列唐卡绘制工程的启动和作品问世,江西惠牧职业培训学校才得以从众多唐卡画室、唐卡培训中心和传习基地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乃至毗邻地区振兴传统文化,发展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的典型个案。
自江西惠牧职业培训学校学员绘制的史诗人物系列唐卡展出并获得认可后,该校在课程中又陆续引入“岭仓”(格萨尔王族)曲调和舞蹈的课程学习内容。当地及毗邻地区的史诗演述人也纷纷获邀赴江西村现场演述,学校还为学员购买了大量史诗书籍和光碟卡带等学习资料,筹建“格萨尔藏戏团”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如今,学校通过求教地方长老和专业人士,根据史诗音乐排练出多支舞蹈,每逢节庆学员或自发或经学校组织在各类节庆场合表演歌舞,颇受民众欢迎。田野调查期间,课余时间学员围坐在画室前的草坪之上,探讨唐卡中史诗人物的绘制技巧和审美标准,谈噱史诗中具有戏剧张力的情节的情景,至今令笔者记忆犹新。诚如村民所言,几年间在江西村目之所见,言之所谈,身之所历皆关史诗,慕名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也逐年增加,村民收入结构趋于多元且稳步提升。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逐步规划并建立起来的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与中国行政区域基本对应,形成了“国家+省+市+县”金字塔型层级结构,非遗项目经过层层申报最终进入国家级名录,而在金字塔的底端则是体量庞大的以村落为单位的基层社区。村落作为关键性行动方,连接着非遗项目各个层面的利益攸关方,同时村落也是非遗在地赋权工作中通过多元行动方落实相关保护措施的重心。格萨尔史诗传统保护的江西村实践始于社区驱动,当地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先后参与其中,从而模塑了非遗保护视域下格萨尔史诗传承和保护实践的工作模式。这一模式体现了非遗保护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重要意义,彰显了唯有以社区为中心,才能实践非遗保护赋权青年、赋权女性以及让社区获益的“过程性保护”(14)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性保护:以饮食类非遗项目的清理与呈现为主线[R].中国饮食类非遗传承与保护课题组简报,2018,(2).目标和包容性发展的核心理念。
三、江西霍仓:家族社区的内生动力与文化传承
作为藏族社会结构的核心单元,“仓”(tshang)对探索和解析族群文化生成和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包括民俗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在内人文学科的相关研究并未对其给予足够重视。对“仓”内涵的探讨亦大多停留在将其视为最小社会单元即家户,阐释其在现代社会中类型和功能的嬗变等层面,未能从地方传统和本土视角出发,从历代垒成的诸义项出发,结合历时和共时语境对其能指和所指进行深入辨析,导致其在藏族传统和现代社会中的多重功能被遮蔽和忽略。
实际上,在藏族文化传统中“仓”具有特别的社会历史意涵。通过梳理从吐蕃时期(公元6~9世纪)以迄晚明的历史文献,笔者结合词源学和语文学分析工具,对“仓”(tshang)进行了系统考证和校雠,这里难以展开。文献分析结果表明,迟至明代,作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历史书写中频频复现的语词tshang其所指已经与共享以血缘为核心的多重认同的群体,即“家族”密切相连,此其一;其二,被认为血统高贵的家族与其世代所居的土地及属民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共生关系,以家族姓氏指代其所辖地区的情况不绝于史(15)藏族传统社会中的核心社会单元——部落(sde)是指由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成的集体。在藏族文化辐射区,一个部落一般由一个或若干(血缘相近)家族构成,因此藏文史籍中血统高贵的家族往往与相关部落之间也构成共生关系,以家族姓氏指代所属部落的情况亦并不鲜见。;其三,各级土司家族依据其所辖地域、属民以及纵横交错的家族关系网络维持和巩固各自的威荣(16)清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治藏策略,家族(尤其是血统高贵的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相关研究参见:(意)毕达克.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M].沈卫荣,宋黎明,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仓”的上述三重属性构成了家族社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内生动力的基石。
“江西霍仓”(个别史料中又写作“火仓”)为藏语gyam shis hor tshang的音译。作为专名,该词组由两部分组成,即作为修饰语的“江西霍”和作为中心语的“仓”。其中,修饰语又由地名——“江西”(gyam shis)和家族姓氏——“霍”(hor)两部分构成,从而形成双重修饰的语法结构。“仓”在该专名中占据语义核心地位。何谓“仓”?《藏汉大辞典》中“仓”的基本义为:家,寓所,巢穴(vjog svam sdod svi nang khyim)。与不同的修辞语组合,辞典罗列了若干以“仓”为中心语的偏正词组,如mi tshang(人家)、gnas tshang(寓所)、sbrang tshang(蜂巢)、jag tshang(匪窝)等。近现代意义上的“仓”,常常和指称姓氏的专名组合构成合成词“某仓”,其语义一般理解为“某家族”(或“某家”),如“岭仓”(gling tshang),意为格萨尔王室家族。
江西霍仓旧时驻牧江西(gyam shis)地区,即上文所涉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霍”(hor)为姓氏,以此为姓的家族在玉树地区(乃至毗邻地区)各县乡均有分布,但分布多地的霍氏家族均出自江西霍仓在当地为基本共识。据江西村然给寺(ra gad dgon)寺志和当地口碑资料记载,江西霍仓至少可以上溯18代,史称“霍仓十八代”(hor tshang mi rabs bco brgyad)。(17)被访谈人:益西(男,47岁,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村民,霍仓百长家族传人);访谈人:央吉卓玛;访谈地点;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霍仓百长家族官寨(家族府邸)旧址;访谈时间:2020年4月24日。换言之,历经数百年,“江西霍仓”在玉树(乃至毗邻地区)已形成支系庞大,分布区域广泛的共同体。
据史料记载,江西霍仓家族(hor tshang)历代族长充任当地土司,官拜百长(be ceng),隶属于玉树地区布庆百户长(bu chen be hu)。前文中提及的江西村惠牧职业培训学校创办人益西即为该家族成员。据益西介绍,该家族上溯8代均为当地土酋,至今霍仓百长(史籍中又写作江西百长gyam shis be ceng)(18)陈庆英.中国藏族部落[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30.的官寨(家族府邸)仍屹立在村中山丘高台之上。身处官寨举目眺望,河谷、山林和草场尽收眼底。因霍仓百长所辖地域广阔且当地自然资源丰富,常为毗邻土司滋扰,冲突时有发生。当地至今仍流传着霍仓百长家族骁勇善战,族人以一当百,战无不胜的地方传说。土司家族作为地方豪族,具有接受私塾和寺院教育的特权,因此族中不乏才德兼备者。霍仓百长家族历代族人中不乏画师、土陶师、铁匠师等善巧者以及熟悉并擅长讲述地方掌故的能人。
此外,据益西回忆,家中长辈和村内长老常以讲述和吟诵格萨尔史诗消闲作乐。在他幼年时期,官寨中还藏有若干格萨尔史诗手抄本,这些抄本被其族人视若珍宝,供于经阁之上,出借和传抄者甚众。据笔者所知,在史诗传统腹地,旧时地方豪族世家往往以收藏格萨尔写本(抄本、刻本)为好,并以此彰显家族地位和势力,互借互赠各自所藏写本亦成为土酋维系家族关系网络的手段之一。概言之,包括江西霍仓家族在内的土酋家族往往是传承和实践地方文化的集大成者。(19)被访谈人:益西(男,47岁,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村民,霍仓百长家族传人);访谈人:央吉卓玛;访谈地点;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霍仓百长家族官寨(家族府邸);访谈时间:2020年8月6日.
历史上,百长家族不仅掌握所辖地区地方资源的支配权和本土知识的解释权,同时也履行“守土御民”的职责和义务。时至今日,霍仓家族成员仍保有一份使命感(即个人层面上的情感依托)。益西无偿为村民扫盲,其兄长身为藏医,经常为村民无偿看诊并赠药,兄弟二人筹建职业培训学校,在自家宅基地建造校舍、宿舍和食堂,将政府下发的个人补贴款(政府为履行退牧还林、退牧还草的个体提供的补偿和补助)用于支付学校日常开支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皆为使命感使然。此外,霍仓家族在当地的声望和几代人铸造的家族关系网络又在无形中为其筹建培训学校,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等方面的保障。
尽管这里未能追索藏语“仓”(tshang)一词在世代交替中语义和语用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但不难发现:正是基于其作为基层社区的类型之一在藏族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发挥多种功能的基本认同,在非遗保护热潮的推动下,藏族地方社会中以“仓”作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实践主体的情况不乏其例。仅在青海玉树地区就有世代收藏和保护《大藏经》的“东仓”(ldong tshang,又称“东仓家族”)(20)东仓《大藏经》俗称“东仓五百部”,在藏族地区享有盛誉。据学者考证,东仓《大藏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民间收藏《大藏经》,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世代管理通天河渡口,掌管沿岸摆渡行业经营权,传承牛皮筏制作技艺的“直本仓”(gru dpon tshang,又称“直本仓家族”)以及世代从事格萨尔史诗缮写工作的抄本世家“增达仓”(vdzin mdav tshang,又称“增达仓家族”)等传统文化保护的关键性主体。(21)我们认为格萨尔史诗抄本和刻本在明清时期大量涌现以及进入文人视野并被载入多种著述也与彼时“仓”(家族)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密切相关。
近10年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倾全县之力挖掘、保护和发扬“嘎嘉洛文化”传统,也可以视为家族社区在本地史诗传承中自觉担责、积极作为的一个范例。在格萨尔叙事传统中“嘎嘉洛仓”(sga skya lo tshang)家族为格萨尔王王妃森姜珠姆的娘家,该家族因在当地富甲一方且颇具人望而得以与格萨尔王族联姻。在玉树乃至毗邻地区,治多县所在的广阔地域被认为是“嘎嘉洛仓”的发祥地,世居此地的民众也以拥有“嘎嘉洛仓后裔”的身份认同而自豪。有关“嘎嘉洛仓”历代成员,尤其是王妃珠姆的传说故事、风物遗迹和节日习俗在当地可谓俯拾皆是。在人们的信俗中,青海的扎陵湖、鄂陵湖、卓陵湖既是格萨尔王的寄魂湖,也是珠姆的寄魂湖,还是三大家族嘉洛仓、鄂洛仓、卓洛仓的寄魂湖。因而,以“仓”为史诗传承和保护发展的民间根基深深地根植于家族这一基层社区,也为当地保护三江源的高原生态和维系史诗叙事传统的文化生境厚植了内生性动力。
2023年8月,第四届全国嘎嘉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素有“长江之源 珠姆故里 英雄家园”的治多县举行。在长江源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中,嘉洛大帐成为格萨尔史诗演述的主场。据传,这顶帐篷已有千年历史,素有嘎嘉洛九扇天窗蓝翼龙帐之说,民间深信是珠姆降世人间的母帐。青梅让丁、慈诚嘉措和拉巴玉加等3位嘎嘉洛神授艺人以充满激情的说唱,展现他们对于长江源嘎嘉洛山水的礼赞和对嘉洛大帐的精彩诠释。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传承人济济一堂,围绕史诗格萨尔在治多县的传承和发展集思广益,也展示了多元行动方的协作网络与功能互补。全国格办主任诺布旺丹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嘎嘉洛文化学术交流会规模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学术成果丰硕、研讨议题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如今已经成为格萨尔学界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会上,治多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嘎嘉洛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还获颁“格萨尔文化保护传承基地”授牌仪式。(22)迅迅.第四届全国嘎嘉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万里长江第一县——治多县举行[EB/OL].https://k.sina.com.cn/article_1261543734_4b31a136001013eui.html,2023-08-23.而这一基于家族社区的文化传承也与格萨尔史诗的学术实践形成了有机榫接。同时,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今天,史诗的传统传承方式如何借助学术界等多元行动方的不同力量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四、益西堪布:本地贤能与文化协理人
社区具有非均质性特点,其表征为社区成员在身份、职能和分工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作为社区的本质属性之一,非均质性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社区在传统文化保护和实践中的内在活力。
实际上,在民间叙事学研究领域,学界早已注意到社区内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在地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方面存在的差异。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立足丰富的民间叙事传统,以搜集整理叙事文本为目的,与叙事传统的传承群体共同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彼时,参与调查搜集的学者发现并揭示了实践传统的群体类型(如积极传承者和消极传承者),并通过整合和汇编来自不同群体的多形态文本完成了集成工作。世纪之交,随着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个体才能及其实践与叙事传统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一大批个性鲜明,贡献突出的“故事讲述能手”“故事家”“故事篓子”“故事坛子”“文化专家”“地方知识精英”进入了学者视野。然而,无论是前期参与集成工作的实践群体,还是此后凭借个体贡献引发学术讨论的各类传承人,对于研究者而言他们的身份主要仍然是信息提供者,他们在传统文化保护和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未能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从而导致他们参与相关工作相对被动且迟滞。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实际上与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以政府为主导,文化主管部门助推和学者广泛参与的基本工作方法密切相关。在上述工作思路的指导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和实践者往往被置于保护链条的末端,从而低估了社区及其成员的多重价值。
近年来,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持续推进,非遗保护的核心理念和工作法则逐渐深入人心,社区及其成员在保护工作中的地位和功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建立和纵深发展即是非遗保护“以人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随着“格萨(斯)尔史诗传统”作为非遗项目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非遗保护基于包容性社会发展的倡议也得到了印证。除了代表性传承人和广大遗产持有者外,社区内身兼数职,集地方文化专家、传统实践者、文化协调者和经纪人等身份于一体的个体贤能涌现出来,在本地非遗项目管理、组织、策划、沟通和协调等实践中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本文考察对象玉树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毗邻西藏昌都、四川德格和玉树市多个县乡,地处交通要冲,区位优势显著,文化资源丰富,可谓藏族康巴文化腹心地区之一。然而,由于缺乏认识和经验,江西村在地理、自然和人文等方面的突出优势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各方关注。毋庸讳言,在江西村的脱贫致富和传统文化保护实践中,当地霍仓百长家族后裔——益西发挥了重要功能。
“江西村惠牧职业培训学校”创办人益西(yid shes)于1975年出生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小苏莽乡江西村霍仓家族(益西之母为当地霍仓末代百长独女,颇受当地民众敬重,现已93岁高龄)。益西于18岁在当地然给寺(ra gad dgon)出家为僧。在此之前,由于种种原因益西未能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但是通过自学和求教当地长老,他已具备藏文识读能力。入寺后,益西接受了寺院教育并得以游历藏族地区名寺胜迹,可谓经多见广。修行间隙,益西回村探望家人,有感于村民生活贫困,村内青年缺乏致富能力以及因村内人口外流导致地方传统文化难以为继的状况,于2005年离寺清修,自愿留守村中为青少年教授藏文,扫盲启智,并最终在各方协助扶持下创办“江西村惠牧职业培训学校”,与多元行动方形成功能互补,以文化协理人的身份深度参与新时期社区建设事业。
在江西村,村民尊称益西为“堪布”(mkhan po)(23)“堪布”一词是藏传佛教僧职称谓。担任这一僧职的高僧是藏传佛教寺院或寺院札仓(学院)的权威主持者。由于担任堪布这一僧职应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和培养僧才的素质以及延续佛法事业的能力,因而必须是寺院中德高望重的高僧,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职的僧人大都是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大德。,然而益西自2005年离开然给寺,全身心投入村落社区建设事业以来,至今未能重回寺院完成戒律及经典论著的学修。就此而言,由于未能获得藏传佛教修行及学位体系中的相应僧职,益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堪布”。然而,何以村民皆称呼益西为“堪布”呢?通过深度访谈,不难发现:益西善言,他不仅能将个人经历和家族历史娓娓道来,对地方传统和族群历史也如数家珍;益西善行,多年来他奔走呼吁,因地制宜,历经数年筹建职业培训学校,协力各方培养了一大批传统手工艺从业者;益西善思,他以国家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政策为依托,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及其纵深推进之契机,立足格萨尔史诗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协力各方开展江西村脱贫致富和传统文化保护实践,带领村民走上赋能脱贫之路。从地方知识储备、个体主观能动性和实际贡献出发,村民尊称益西为“堪布”可谓实至名归。
在《非遗公约》的框架内,社区、群体和个人(均为复数)是3个互涉主体。其中,社区因作为关键性主体参与遗产项目的确认、建档、维护、传承和振兴等一系列保护实践而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解读“社区”内涵、类型及功能的重要维度,个人及其所在群体在非遗保护实践中的角色功能也应当是相关讨论题中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所谓可持续发展,就其本旨而言是指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个体的传承人和实践者,他/她在身份、职业、认知水平、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其在保护实践中的行动效果。益西在江西村格萨尔史诗保护实践中充当了文化协理人的角色,通过在社区内部践行包容性发展的策略,个体差异化的实践方法得到了有效平衡,实现了地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村民致富和社区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社区”及其相关术语的理解和界定当注重单数的“传承人”,同时转向关注复数的传承人和实践者群体,“江西霍仓”的在地行动正是基于社区和群体的文化认同而开展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实践,可为当下代表性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基本行动路线。
结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4)《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9年7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25)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EB/OL].http://www.cppcc.gov.cn/zxww/2019/07/17/ARTI1563320837687103.shtml,2023-10-16.因此,为确保非遗的存续力,亦须在保护和传承之间找准发展的前行方向。
毋庸讳言,非遗过程性保护的工作法则和操作流程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保护提供了指导性实践方针,而立足于社区赋权并“以社区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不仅为此前格萨尔史诗保护工作提供了反思向度,在认识论层面也引发了一系列触及史诗传统知识再生产、存续和发展等根本问题的审思。在非遗保护领域,社区的界定高度依赖于遗产项目的逐级行政认定。由于社区在保护进程中当处于核心位置,因此对其能指和所指的理解关乎保护实践的效能和成败。就格萨尔史诗而言,无论是其资料学建设从搜集、翻译、整理到抢救、录音、记录、整理、翻译的过渡,还是其学术研究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艺人为中心”的发展,客观上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相关行动方为记录和研究史诗传统而采取的学科化举措。其间对该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传播的媒介载体重视有余,对史诗传统作为活态遗产的社区实践及其内生动力尚认识不足。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格萨尔史诗传统的在地保护实践凸显了社区的中心作用,为史诗传统这一活态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从江西仲措的村落实践到江西霍仓的家族实践,再到益西堪布的个人实践,作为藏族基层社区的3种行动选择和在地实践,不仅在史诗格萨尔的保护、振兴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向心力作用,也带动了与史诗传统相关的其他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当下的史诗传统保护实践更加需要坚持“以社区为重心”,激发传统传承方式的实践活力,让村落、家族和个人的努力形成合力并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此外,鉴于史诗流布之纵深,尚需引入更广泛、更贴地的社区参与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尤其是要本着维系史诗传统所在社区和群体的集体性互动和代际传承实践,让更多的本地社区和群体尤其是年轻人有机会从多元行动方的参与式发展中受益。与此同时,由社区驱动的在地保护实践,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主管部门的扶持,也需要专家、专业中心、科研机构、教育机构、新闻媒体机构以及其他社团组织的参与,各尽其职、各展所长,方能建立起持续性的功能互补型协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