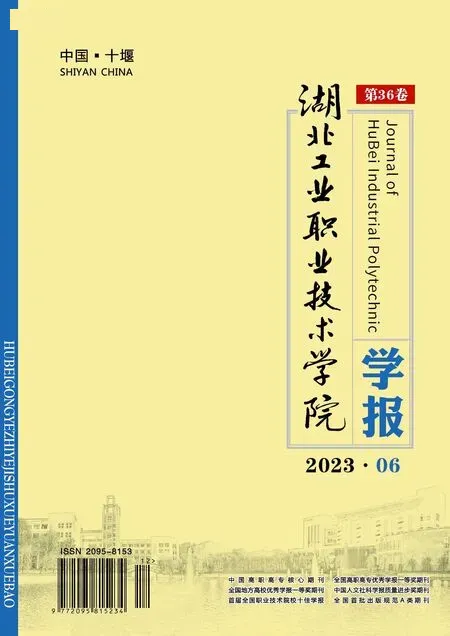反抗的忧郁与循环的阴影:《鲸鱼马戏团》的意象表达与历史之维
吴 赛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尼采曾疾呼:“上帝已死!”[1]近代科学与理性主义将上帝推下了人类信仰的山巅,只是在道德的荒原上奄奄一息,而在世纪转折点上,上帝更是被无情地彻底杀死,我们心里的天堂与地狱也随之消失。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的信念与道德逐渐失去意义,价值虚无与信仰危机随之急遽汹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上帝的“死亡”似乎也给予了我们去重新寻找和赋予自己生命意义的机会可能。贝拉·塔尔认同尼采的观念,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如何活这一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是什么。没有什么是不可冒犯的,除了生命本身。”[2]而他的影片《鲸鱼马戏团》便是站在上帝远去的世界云端,静默地俯瞰哀鸿的苦难,试图去探寻在这个“上帝已死”的世界里生命的质量。
一、匈牙利的历史:抗争与失意
匈牙利的近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悲剧史。它是怆痛与苦难的承受者,是被蹂躏与欺辱的不幸儿,但不可否认,它也是罪恶与悲剧的缔造者。匈牙利作为欧洲的十字路口,由于其地理位置的显赫,在历史上不断遭受异族的践踏与侵略。从16世纪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铮铮铁蹄下被占领,到两次世界大战遭受解体,接连不断的战乱使得这个国家饱经血雨与沧桑。1919年3月,匈牙利建立了继苏联之后的第二个社会主义政权,但是由于国内外经济封锁和军事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后,历时四个月崩溃。次年匈牙利作为一战战败国,与协约国签署《特里亚农条约》,该条约使得匈牙利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人口。而在二战期间,匈牙利加入德意日轴心国,成为纳粹的盟友,战后在苏联的控制下废除帝制,但是独裁与专制、恐怖与饥饿却接踵而至。随后匈牙利人民决意反抗苏联强加给自己的制度,爆发了十月革命。在苏联的暴力镇压中,2500名匈牙利百姓死亡,20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
纵览匈牙利的近代历史,匈牙利人民一直遭受着侵略与羞辱,他们也始终对苦难进行反抗,却似乎始终没有成功过。在漫长的战争与恐怖的氛围之中,真正承受民族苦难的就是这些底层的芸芸百姓。他们或许是为了集体而选择与某种强大的力量进行抗争,出于民族的名誉与国家的正义举起紧握的拳头。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不仅是苦难的最终承受者,同时也是被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他们的拳头被牵扯上芊芊长丝,如同木偶剧的傀儡,失去思考似地去建造了屹立人间的地狱大厦。因而,在一次次的抗争与失败的循环往复之中,一种独特的忧郁性格便深深地烙印在了匈牙利人民的集体灵魂深处,而这种独特的“反抗的忧郁”的性格,也便是贝拉·塔尔电影中每个人身上始终无法被抹去的痕迹和底色。
二、《鲸鱼马戏团》中的意象表达
贝拉·塔尔否认《鲸鱼马戏团》是一部政治寓言,并没有任何形而上的象征与意味,其中所表现的只有时间——以心理发展的时间历程去雕刻集体的存在感并去抚慰这些形象被风雨冲刷后的灵魂。《鲸鱼马戏团》并非只是一部去表现匈牙利的政治或是回溯民族历史的写实照片,影片的主题似乎隐藏在云层之上,关乎人性,关乎信仰,关乎时空以外。
(一)鲸鱼
出现在影片名称中的“鲸鱼”,可以说是整部影片最为重要的一个意象。影片的故事情节也是围绕鲸鱼而展开的——一条鲸鱼的到来打破了内陆小镇的宁静。除了亚诺什,人们都拒绝走进集装箱,去亲眼目睹这条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鲸鱼”。而面对这条突如其来的庞然大物,小镇居民充满了敌意与排斥,人们发起暴动,去袭击了小镇的医院。最终随着鲸鱼的离去,小镇重新恢复了往昔的静谧与安宁。
首先,在时间意义上,鲸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它见证了地球的演变、人类的诞生与进化,沉淀着关于历史的记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这条死去的鲸鱼所联系的,便是匈牙利过去被忽视或者说被遗忘的民族历史。偌大的历史就摆在他们的面前,无法被否定、被消灭,人们能做的只是去逃避,或是嫁祸于此。对于匈牙利人民而言,其历史是一部悲剧和屈辱的历史,它带给匈牙利人民更多的是一副沉重的镣铐与枷锁。面对被践踏和伤痕累累的过往,人们想到的是通过暴力去改变现实的面貌——科苏特宣读《独立宣言》是,1956年十月革命是,小镇的居民选择投掷火把冲向公共场所同样是如此。
此外,在文化意义上,《圣经·约拿书》中有着一则关于鲸鱼的故事:亚米太之子约拿受上帝之命,前往尼尼微大城去告诫作恶的人民。约拿却因为害怕而逃走,上帝便使其被一条鲸鱼所吞。约拿在鱼腹中忏悔,最终得到救赎而毅然决然前往充满堕落和罪恶之城。可以说,在影片中,那条被囚禁在集装箱里的鲸鱼与吞噬约拿的那条大鱼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共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条大鱼是上帝的所指。走进集装箱与鲸鱼对视的亚诺什便是在鱼腹中忏悔的约拿。特别是第二次亚诺什偷偷溜进集装箱看到鲸鱼后听到了马戏团长与王子的谎言后,他企图想要去唤醒丧失了理智的群众,就如同想要前往尼尼微大城去拯救堕落与罪恶的人们的约拿一样——只不过亚诺什是失败了的约拿,他没有实现救赎,而是在躁动的人之逆流中渐渐渺小,隐入黑夜。而这条死去的大鱼,也如同时刻清醒而冷静的上帝,他矗立在世界之外,俯瞰着人们进行各式各样的荒唐与失智,只是冷眼旁观地掂量关乎生命存在的重量。
(二)日食、纯律与十二平均律
影片伊始,醉酒的亚诺什在小酒馆中为人们表演了一出关于日食的戏:起初,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月亮围绕地球旋转,整个宇宙充满秩序与宁静。慢慢地在天体运动过程中,太阳、月亮与地球重合在一条水平线上,一切都陷入到绝望和恐惧之中——此时贝拉·塔尔的长镜头慢慢后移,直到吊灯进入画面的上方,光明再次出现——星体继续运动,黑暗逐渐消退,光明返还世界,宇宙重新井然,人们也再次获得安宁与和谐。最后,亚诺什在被当作醉酒之人赶出门口时,他如同先知般所言:“一切还未结束,一切也刚刚开始。”
贝拉·塔尔为何要通过一段长达11分钟的长镜头去表现这样一场似乎脱离主线情节的日食之戏呢?倘若“一切还没结束,一切也刚刚开始”,一切绝望后的宁静与惶恐前的和谐实现了时间上的勾连,那么,所有的暴力和杀戮是否也都并非只是一时的冲动与疯狂,而是历史的重复?这样一种“结束即开始”的历史观无疑给整部影片蒙上了一层悲观主义的面纱。起初醉酒之人的舞之蹈之,暗暗之中正在酝酿着又一次的动荡与抗争。影片最后,鲸鱼曝露在广场之上,疯狂被理智重新镇压,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就在不久之前弥漫的攻击、质疑、谩骂与背叛,而是在集体主义的盔甲之下,逃避了历史的罪责,成为了民众之中的一个组成分子,似乎一切都只是开始、结束、开始的历史必然。贝拉·塔尔面对人们沉陷在这种历史循环的泥沼之中,他试图站在一个接近天空的视角思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鲸鱼马戏团》的另一个名字是《残缺的和声》,影片中的音乐——纯律与十二平均律——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符号。唐德婶婶拜托亚诺什去恳请叔叔埃斯特尔组织小镇运动,亚诺什听到了叔叔谈论德国巴洛克音乐家安德烈亚斯·沃克曼斯特的音乐理论。沃克曼斯特是最早提倡平均律的音乐家,他将八度音阶分为十二个半步音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但是埃斯特尔认为,十二平均律是人们对于具有神性的音乐形式的亵渎和玷污,如其所言:“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他赞同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数学、音乐与星空是宇宙和谐联系的表现,大多数谐音和声是由简单正数比例的音调组合而成的。正如影片中所提到的,最初有音乐的时候,人们对于音乐怀有一种类似于宗教和信仰的崇尚敬畏,仅仅是在自然所拥有的音阶之间进行演奏和表达。
在这里,贝拉·塔尔试图对于“问题出在哪里?”进行作答。他借埃斯特尔之口指出,不十二平均律不仅不是人类的天才创造,反而控诉其是对于伟大神性的剥夺,是用人造的系统来取代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神性,是人的狂妄自大,是对宇宙的失敬亵渎。从这里我们可以进行适当延伸,埃斯特尔否定的,是由人矫揉创造的事物,正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去组织由人所构架的社会秩序,拒绝那些所谓的“伟大的”领袖们所创造的这个“色彩斑斓”的社会。贝拉·塔尔似乎是在说:问题是出在了人身上,正是人的理性造就了人的非理性,正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想的博弈造就了这个循环往复的人间地狱。
(三)王子和影子
王子是马戏团的特邀嘉宾。小镇居民购买一百福林的门票,便可以参观“世界上最大的鲸鱼”,并且聆听王子的演出。但是,亚诺什在第二次偷偷溜进集装箱的时候,得知了关于王子的真相——王子是马戏团团长一手培养的专门进行表演的“表演家”,并且在自己真正获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之后,企图挣脱马戏团团长的摆布,想要在演出时向观众演说具有煽动性的言论。
王子是影片中最后暴动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也正是因为他的言论,麻雀与蝼蚁似的人群涌进了小镇医院,殴打患者,破坏设施。可以说,具有言论权威或影响力的煽动者是使人们失去理智,走向疯狂的幕后元凶,而这些迷失了生活目标、失去理想与希望的平民,在一种被政治意识形态粉饰的魅惑之下,选择信服,选择屈从。而在匈牙利的历史中,这些平民在摘下面具,成为“暴民”之后,又再次戴上了面具,重新成为平民,依旧淹没的贫穷和痛苦的生活黑暗之中。当初的煽动者,或者说“暴民”背后的力量却获得了真实的利益。而贝拉·塔尔似乎走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影片中,王子从来没有正面出现过,他留给我们的仅仅是模糊的声音和投映在墙壁上斑驳的影子。我们对于他的形象完全是碎片的、支离的——那么我们看到的王子是真实的吗?或者说,他是否就是煽动暴动的真正的幕后元凶呢?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在场”出现在暴乱的小镇居民中。在大家被王子所煽动,为了一个看似裹挟理想与抱负的目标而一言不发的破坏医院后,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医院的长廊,他们的身体在灯光下被投射为充满恐怖和压抑气息的偌大阴影,横向穿过屏幕,最终在离去的广场上所有影子聚合在了一起。贝拉·塔尔曾解释《鲸鱼马戏团》中的行走:“人们走路的时候能够体现一种力量。”[3]同样的问题,贝拉·塔尔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看到的他们是真实的吗?或者说他们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吗?
或许,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关于王子、暴民的影子,乃至影片开始运输鲸鱼的集装箱的影子,来延伸至有关柏拉图洞穴的概念。柏拉图的洞穴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有关乎真实与虚假的理念世界——在其洞穴中,所有人被投映在墙壁上的影子所迷惑,并不知道所谓真实的世界为何物,而当从洞穴中走出的人发现真实的世界是另一番景象后,真实与虚假的痛苦思索便萦绕在了他的脑海之中,久久挥之不去。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提到:“因为摄影机,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了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4]回到《鲸鱼马戏团》,摄影机所记录下的那些大量关于影子的表现,所带来的正是某种程度上的不真实。深夜载着鲸鱼的卡车来到镇子里,卡车投映在墙壁上巨大的影子,似乎充满着某种未知的恐怖与威胁。而小镇的居民并没有走进集装箱,单凭影子就完全无条件地信服了一切——鲸鱼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可是人们依然对它抱有敌意。可以说,无论是运输鲸鱼的卡车的影子,还是王子的影子、暴民的影子,都是脱离了事物真实的存在。王子煽动性极强,吸引了众多的拥趸,但是他呈现给我们的又何尝不是一个畸形的影子?暴民肆无忌惮地发泄着暴力,施虐于更弱小者,但是那幽幽长廊里落寞离场的影子又是否也只是一群被摆布者和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呢?
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亚诺什是否就是第一个走出洞穴而了解真相的人呢?是否在影片中外面的世界便是那个装着鲸鱼的集装箱呢?亚诺什在无意间听到马戏团团长与王子的对话,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急于将集装箱内的真实告诉人们,告诉他们上帝的目光正冰冷地目睹着一切。可是人们没有相信或者说选择忽视亚诺什。警察局的警官、餐厅工作的女工、广场上密密麻麻游荡的人群,甚至是所谓依旧理智的音乐家都没有人愿意走出外面的世界,进入集装箱去看一看所谓真实的世界。当影片结束,集装箱破碎,死去的鲸鱼黯然沉默在广场上。诚如贝拉·塔尔所言:“真实的世界也会以幻觉的形式存在。”[5]或许真实就在人们眼前,亦或是真实离人们越来越远。无论如何,居民似乎达成了一种集体性的默契,依旧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等待着下一个“伟大”的操纵者来牵扯可以摆布自己的木偶之线。
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么真实在哪里呢?这场暴动的真正元凶又是谁呢?贝拉·塔尔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答案:当暴民的影子接踵穿过长廊,亚诺什看着他们,看着所谓的真相——可是他看向的是摄影机,暴民的位置是在摄影机之后——那堵横亘在我们与角色之间的墙被打破了,所谓的答案就在亚诺什的目光之中。
(四)赤裸的老人
汉娜·阿伦特曾提到一个概念:“恶的平庸化”(the benality of evil)。那些实施暴行、恶行的人,并没有残暴动机和恶的企图,他们只是和我们一样,是为生活而寻找目标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放弃了思考,而被某种掌握意识形态的煽动者所鼓动[6]。正如《鲸鱼马戏团》中那些在广场上游荡的、愤怒的“唐德婶婶们”,他们怀有良好的愿望,想要恢复秩序,创造和谐的环境。但是在失去独立判断能力之后,想要构造人间天堂的美好企图,最终却变成了人间地狱。那么,贝拉·塔尔是否对此自始至终是完全的悲观呢?
在影片表现的暴动之中,人们砸碎公共设施,施虐于更弱小的病人,将医院变成一片狼藉。但是,当这些“为了理想而反抗”的人民面对一个骨瘦如柴的全身赤裸的老人,面对可以唤起他们关于历史、关于血与泪、关于大屠杀的记忆的老人时,他们沉默地离开了。就像亚诺什在影片伊始所说的:“一切还没结束,一切也刚刚开始。”如今的所有暴力和杀戮并非只是一时的冲动和疯狂,而是也曾经真实地、一次次地发生在历史之中。但是当我们面对历史,被唤起的,似乎是被粉碎了的理智与温煦——我们似乎从这里隐约能够看到贝拉·塔尔对于历史和人民的一丝悲悯和些许善意。当每个人因为疯狂而堕入黑暗与深渊,可又与那些抹不去的记忆重逢,我们还是会停下脚步去吐露一声叹息,去感受曾经被施与的疼痛和如今正在跳动着的灼痛。
三、《鲸鱼马戏团》的主题意涵
《鲸鱼马戏团》并非只是一部去表现匈牙利的政治或是去回溯匈牙利民族历史的表层寓言。贝拉·塔尔将一种事物的“幻灭”秩序的正常失序和毁灭或疯狂的极端之间的亲密关系呈现为一部精美的浪漫童话[7]。首先,贝拉·塔尔通过影片所要表现的,是那些普通群众在失去希望后想要重新建立希望之时面对充满魅力的煽动者的盲从。这些“暴民”自认为找到了所谓的价值和意义,能够重新建立社会的秩序和自己的家园,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从而开始取代先前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后又将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可是,贝拉·塔尔告诉我们,那些进行反抗的“暴民”,他们虽然是为了自认为崇高的理想进行斗争,但是他们没有恶意初衷的行为却造成了一种恶的结果。而他们最后又恢复为“无辜”的平民,逃避了责任和惩戒,依旧贫穷、迷茫和痛苦。而当初的煽动者或者说背后的主使者,却获得了利益——但或许也只是暂时的。从而,我们便可以将这个小镇与匈牙利整个国家相映照,将喧嚣的夜晚与匈牙利的历史相勾连。
贝拉·塔尔之所以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电影大师”,他的立意要更为高远和深邃。那条大鱼睁着偌大而毫无波澜的眼睛冷眼旁观着所有的动荡与混乱,注视着雄火粼粼,注视着黑影斑斑——贝拉·塔尔以上帝的视角反观人类自己的行为,直指人类犯下的反复无常的暴力与杀戮,但又从这血雾的悲怆之中浇灌下了一场细雨绵绵的怜悯,滋润的是那些罪恶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