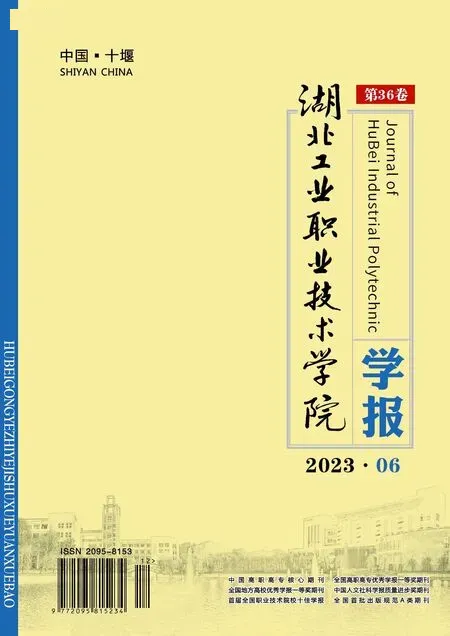论陈梦家新诗创作的突围和终止
张 茜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并称“新月派四大诗人”的陈梦家,二十岁以一本《梦家诗集》登上诗坛。在沈从文所说的新诗的“沉默期”中,他被看做“新诗里寂寞的火星”[1],胡适读罢其诗,认为“令人生大乐观”[1]。然而从已知的创作来看,自1928年1月发表第一首《可怜虫》,到1935年8月最后一部诗集《梦家存诗》出版,其创作热情仅仅持续了不过六七年的时间。现代文学史上转型为职业学者的不在少数,闻一多就曾记述一个时期诗人向古史的兴趣转移:“和玮德一起作诗的朋友,如大纲原是治本国史的,毓棠是治西洋史的,近来兼致力于本国史,孟家现在也在从古文字中追求古史。何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一个方向?我期待着早晚新诗定要展开一个新局面,玮德和他这几位朋友便是这局面的开拓者。”[2]但显然陈梦家的转型是与新诗的彻底割袍,此后他向着学术道路一去不回,几无诗作发表,也几无对于新诗创作的追念。着眼陈梦家由诗人到学者的转型个案,有利于梳理陈梦家的创作脉络,进一步丰富对新诗与古史研究复杂性关系的认知,窥探三十年代新诗发展的一角。
一、自我之“歌”:个体情感的张扬
作为后期新月派的代表诗人,陈梦家的新诗创作不同程度上受到闻一多、徐志摩两位前辈的影响,内容上多与自然、爱情等有关,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形式上则强调格律,“我们不怕格律。格律是圆,它使诗更显明,更美。形式是官感赏乐的外助。”[3]他在《新月诗选·序》中为新月诗友所作的评述,同样也涵括了自己的创作:“纵使我们小,小得如一粒沙子,我们也始终忠实于自己,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不做夸大的梦。我们全是年青人,如其正恋爱着,我们自然可以不羞惭的唱出我们的情歌。”[3]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诗人的心灵实在是一种贮藏器,收藏着无数种感觉、词句、意象。”经过生命前二十年的积蕴,陈梦家的情感喷薄出现在中央大学就读期间。五部爱情散文小说《某夕》《七重封印的梦》《一夜之梦》《五月》《不开花的春天》接连发表,同时一系列缠绵哀婉的情诗也不绝如缕、层出不殆。但在《悔与回》之后,或因恋情失败的刺激,或因关注重点的转移,“从诗文里看,1930 年底《梦家诗集》结集之后,陈梦家几乎没再写过这种热情、不安地期待亲密关系一类的诗。”[4]此外,陈梦家显然对它们持否定态度:“这些日子我自不能引以为光荣,因为可鄙弃的与耻辱的正多。”[5]作为“七年写诗的结账”的《梦家存诗》也未见收录这批作品。相对而言,同期的其他作品艺术性要稍高一些。
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
血红的酒里掺着深毒的花朵。
除掉我自己,我从来不曾埋怨过
那苍天──苍天也有它不赦的错。
……
我像在梦里还死抓着一把空想:
有人会听见我歌的半分声响。
(《自己的歌》节选)
这是一首抓碎心胸掏出的歌,“血红的酒”与“深毒的花朵”喻示着有极真诚浓郁的情感凝聚于其间。对陈梦家而言,抒情诗具有极强的共情能力,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用一颗心摇撼另一颗心,是他最欢喜的体裁:“伟大的叙事诗尽有它不朽的价值,但抒情诗给人的感动与不可忘记的灵魂的战栗,更能抱紧读者的心。诗人偶尔的感兴,竟许是影响人类的终古的情绪。”[3]
然而歌声“被人听见”却只可能是“梦里的空想”,以至于情感无处发泄只能被不断压缩再压缩,形成一声蕴含血泪而低徊哀切的长低音,沉重地奏响了命运的残酷无情:“挤在命运的磨盘里再不敢作声,有谁挺出身子挡住掌磨的人?”劳苦众生安身立命的方法,多的是忍耐少的是抗争,然而这究竟是懦弱还是生活的智慧?是为谁辛苦为谁甜?“在世界的谜里做了上帝的玩偶,最痛恨自己知道是一条刍狗。”“刍”,草也。“刍狗”,即古时用草编结成的狗形,供祭祀用,用完即丢弃,是极为卑琐微小之物。诗人直言不讳,道出人命危浅、生如草芥的真相。“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死生幻灭来来往往,人如虫堕网中无所遁形,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过这一生?
年轻的诗人思考着宿命、观照着自我。相较于前七节始终保持着的高亢浓郁的情感输出,到了第八节尖锐的剖白与控诉显然已开始收束,是诗人最后的哽咽哀声:“我是侥幸还留存着这一丝灵魂,吊我自己的丧,哭出一腔哀声;/那忘了自己的人都要不幸迷住,在跟别人的哭笑里再不会清苏。”诗人最后写下的这两行诗句:“我像在梦里还死抓着一把空想:/有人会听见我歌的半分声响”,是给自己留下的“光明的尾巴”。在认清生活之后却仍然敢于直面这惨痛的真相,即使是“空想”也仍然“死抓着”,何尝不是另一种英雄主义?正如陈梦家所说,即使小如沙砾,仍然应当自尊自重,忠实于自己,“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那么即使无人听见,也要固执地唱出真诚而坚定的自我之歌,在广袤的世界里辨识着微弱的回声、探询着自我的位置。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一朵野花》)
在个体急剧膨胀的二十年代,当诗坛高唱着“大写的人”,陈梦家却在荒原上发现了“一朵野花”。《梦家存诗》序言中的自陈表明了诗人对这首诗价值的肯定:“《一朵野花》是此集中最先完成的一首,它代表我不被熏着前的嫩。”[6]诗分两节,以野花的开落、生命的轮转来赞美一个忘记渺小、昂首微笑的倔强小生命,他聪明且自知、有梦但迷茫。诗人通过自然书写揭露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贫瘠的荒原上一朵孱弱的野花,倏忽开落就是一生走过。然而他从容接纳命运的安排,在无人之地向着太阳、望向青天,绽开自己微弱但不卑微的笑,感受生命的欢喜,书写自己的诗,做着自己的梦,哪怕容易忘掉。陈梦家所描摹的“这朵野花”透露出一种永静、平和的宗教气质,俨然是《圣经》中“野地里的百合花”意象的诗歌变体。“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马太福音6:26-28)”在无需思虑苦多的朴素慰藉之外,诗句还隐隐闪烁着存在主义自在、自为的思理:万物天生自然,野花自在的生命状态同样有赖于此。尽管在某种超越性的存在面前,己身的渺小昭然若揭,但“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传道书3:11)”诗人发觉生命的强力和奇迹:渺小之物,看似于生命荒原之中显得孱弱无力,但若能顺时进退、从容生长,亦能摆脱局限的久暂之别,走向永恒的美好与圆熟。
无独有偶,在陈梦家此后诸如《红果》《雁子》《生命》等诗篇中我们能发现更多自然界中的微小意象:秋日的雁子,等待着的红果,小小的红花,缸中的金鱼,微风中草叶的轻摇,掠过水面的燕子尾,流云和孤星,细雨和柔风,日光下露珠的闪耀……都如此渺小迷茫,做的梦却浩荡。陈梦家笔下的万物被放置于生死幻灭的自然法则之中,个体的有限性似乎吞噬了生命延展的可能,但当自身存在的局限开始显明,实际上一个更加广阔的生命空间也在同时被展开,我们可以期许在其中寻找到自我的平静和救赎,寻找到自我之歌。
二、推移之“影”:现实维度的增强
文集《你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飞》记录了1930年夏天陈梦家与方令孺之间的信件往来详情,两人也自此结下深厚友情。题名“文黛”与“彼得”取自于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的童话《彼得·潘》中的主人公。当二十岁的诗人在信中倾吐着父亲病重、毕业迷茫、生活困惑的种种时,奇妙的永无岛、不肯长大的男孩彼得·潘和体贴温柔的小母亲文黛则为他建造起一个抵御成长烦恼、摆脱成人社会枯索繁杂的美丽世界。在第二年夏天写给文黛的诗中,陈梦家依然抗拒着“明天”的到来,试图“飞”离现实的束缚:“不许提到明天/笑一声 依旧往天上飞。(《告诉文黛》)”然而抽象的命运我们尚可指控,借助文学想象逃离,具体的生活我们却无力反抗,只能一天一天走过。面对时间这无情的推手,诗人不得不承认,“风里面停不住永远的梦。(《嘤嘤两节》)”
1931年7月,陈梦家从中央大学毕业。脱离单纯的校园环境被抛入社会,一路努力唱着自我之歌的诗人在此诚实地表白着自己的茫然惶惑:“像一路风,我找不着自己的地方,在一流小河,一片叶子,和一架风车上我听见那些东西美丽和谐的声音,但从来没有寻到自己的歌。”[7]在1931年6月的《梦家诗集·再版序》中,陈梦家似乎是下定了决心,痛定思痛:“不该再容许我自己在没有着落和虚幻中推敲了,我要开始从事于在沉默里仔细观看这世界,不再无尽地表现我的穷乏。”[7]
是一棵树的影子,
一步一步它在移,
也许它有点欣喜,
也许它不大愿意。——
月亮自东往西。
最初它睡在泥地,
随后像是要站起,
慢慢它抱着树枝,
到了又倒在树底。——
月亮已经偏西。
(《影》)
1932年12月26日夜,陈梦家坐在海甸某一隅的桌前,回忆起几个月前的青岛往事,写下于青岛海滨的一次夜步所见。一棵树,树影推移着,诗人的观察之眼藏在物象背后。在月亮裹挟树影无止的变动之中,人被命运推着走的无奈之感展露无遗,树模糊的思绪和被动的姿态或许正可与诗人当时年轻迷茫的心遥相呼应。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然而就在一天之前的鸡鸣寺,志摩还在对陈梦家说着对未来的打算:“这样的生活,什么生活,这一回一定要下决心,彻底改变一下。”[5]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陈梦家投身前线,亲赴国难。参与了鲜血淋漓的肉搏战,目睹了沿着铁路逶迤数十里的难民队伍。时代的巨幕拉开,更让人觉察到世事的动荡微渺。如果说早期那些情感泛滥、缥缈哀切的自我书写,让诗人“常常感到自己的空虚,好像再没有理由往下写诗。”[7]那么此期友人离世的切身之痛、山河飘摇的家国之痛,还有毕业后从校园被抛掷到社会后无所着落的迷茫之感,或许让他看到听到了“更伟大更鲜明的颜色或是声音”[7]。
1932年3月,陈梦家到青岛,做闻一多的助教。在青岛期间,他完成了《在前线》四首的创作(《在蕴藻滨的战场上》《一个兵的墓铭》《老人》《哀息》),记录了战地所见。陈梦家在《梦家存诗·序》中曾回忆道:“《老人》有意摆脱形式羁绊,意识上也自觉满意,《影子》《小庙春景》已完全脱开这一切,经过了理性的沥滤。”[6]这种尝试其实早已有迹可循。在《诗刊》第四期“志摩纪念号”的叙语中,他就曾说:“很想把新诗的内容要更扩大。”《新月诗选·序》中他也提到:“格律在不影响于内容的程度上,我们要他。”“我们会把技巧和格律化成自己运用的一部。但是合理,情绪的原来空气的保存,以及诗的价值的估量,是运用技巧或格律的前提。”[3]陈梦家在延续新月派重格律的基础上,对形式的要求显然更宽泛,强调了诗质作为前提的必要,创见性地提升了内容的重要性。
也许他就要腐烂,
也许被人忘掉;——
但是他曾经站起,
为着别人死了!
(《一个兵的墓铭》)
比较来看,同样描写战场阵亡的士兵,《梦家诗集》中《古战场的夜》里诗人更多是为这无名的死尸扼腕唏嘘:“也猜不透你做了那一家英雄。”两军对阵剑拔弩张,似乎个个义愤填膺,但可叹的是或许直到死去的那一刻都没弄清是为了什么而死,“英雄”又如何,依旧无名无姓。不同于这种类似打抱不平的哀伤以及因“古战场”而生发的浮泛苍凉之感,《一个兵的墓铭》显露的是诗人在前线磋磨出的真真切切的知觉:“战争所磨砺的心”[8]和“可羞的不死”[8]。前线见闻拓展了诗人生命体验的维度,意境亦显博大。最后两句转折成为“提亮”整首诗的关键:或许肉身将要腐烂丧失,或许灵魂也将被弃毁遗忘,但君子论迹,当他站起扛下重责,我们便可以说,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转弯,他认识村上的路,
认识每一条河,每一块
石头和它多少的掌故:
多少人坐过的,死了。
……
他该走近那棵杨树了。
为什么他没有看见?
(《老人》节选)
而在《老人》一诗中,我们看见战火袭扰之中,故乡还可以凭借记忆重返,但也只能凭借记忆,因为一切已物是人非。到最后只剩下一棵杨树,勉强借以指认着从前,成为记忆的锚点。而当这棵古老的杨树也被摧毁,“老人”,同时也是诗人与读者乃至我们每个人,终于深切地意识到战争带来了什么——这是一场彻底的颠覆。过往的意象都在当下的现实中被摧毁,这样痛苦的记忆带来清晰的历史感,强烈地激活了诗人的民族意识。
战争的阴影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在1932年10月华北危急之时,陈梦家仍在疾呼一种“伟大的强烈的呼喊”,他认为在国难时刻尤其应该倾听“大众的哀泣”,把个人的感情化作全民族的感情,从而共同寻找复兴的希望。他在《秋天谈诗》中将新月派等浪漫诗歌斥为“个人颓废的呻吟”[9],把左翼诗歌批评为“假冒为群众的嘈杂”[9],而对于自己曾经的创作他同样不满:“现在我不愿自己也不愿别人做铁马儿,我们应该是风,是秋风。”[9]檐下的铁马只是随风而动,诗人却决心成为摇撼生命的秋风。如果说曾经的陈梦家衣衫落拓,以“一朵野花”的渺小之姿不卑不亢地叩问广袤宇宙,探询个体的位置,此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风雨飘摇,要求着个体的退场,从而推动历史的显豁、呼唤时代的真话,寻找着新诗突围的途径。
三、历史之“攀”:灵性突围的失败
1932年9月陈梦家进入燕京大学宗教系就读,后又拜入容庚先生门下读古文字研究生。从南京到青岛再到北平,从校园到社会再回校园,诗人的转向在不断的创作和变换的生活中慢慢浮现出一个轮廓。“长期的变换多离奇的生活,才是一首真实的诗”[7],诗人竟一语成谶。
翻开陈梦家的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丧歌》记述了一个无名乞丐在冬夜的寂寞死亡:“你的一生,你永远不变更的容忍/在穷困里,穷困里,作了一世穷人。”诗句中有关注,有刻画,有被渺小的死亡激发的同情与哀叹,但却没有更多的感触和阐发。就像这首诗的后记中,大半篇幅也只是纯然描述,只有最后这几句似乎要揭开什么,却又隔靴搔痒点到为止:“雪把这河山飘得太美丽了。但是这乞丐呢?他死了。”《马号》有着理想主义的光环:“这是英雄,英雄的事业,/杀的是弟兄,不是仇敌。”人人皆弟兄姊妹,诗人厌恶杀戮的心几乎单纯天真,杀戮背后的隐藏的复杂社会性却在这种悲哀中被冲淡。这里显露着作者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牧师的好儿子”,自幼浸淫于宗教的圣气灵光之中,陈梦家的早期文本明显闪烁着希伯来宗教的光晕,但“宗教对他并不是一种皈依诱惑,而是一种对生命奥秘的深切感悟、人格的自我塑造,是一种对宇宙神秘的体验、对超然之爱的崇敬。”[10]这种气质伴随诗人不断寻求新诗突围的历程,日渐沉潜入陈梦家的文学生命中,形成对“大爱”精神和生活“真诗”的推崇。
我攀上山岭,攀上悬崖;
攀住老死的野草,攀住荆刺的小苗;
我蹬住枯渴的石头,我往上走。
我觉得我自己,浩浩荡空;
后面我看不见,前面是三尺地;
我蹬住枯渴于石头,我往上走。
(《攀》)
山岭、悬崖都可攀援,野草、小苗、石头都可借力,诗人的勇往直前蕴含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将这看作是一条没有后退可言的路:“后面我看不见”,因此“登山望海”,唯有努力向前。故事中的彼得·潘最终长大,不再梦想着“飞”,而是依靠双手双脚向上“攀”。诗中记录下主体“我”永恒向上的姿态,定格了一个追寻的瞬间,正和他在《梦家存诗·序》最后的发愿相合:“我预备辩味一个亲切的合理的世界。”[6]
然而这场突围显然是失败了。事实上,自1934年陈梦家再次进入燕京大学后,他在学术成果频频发表的同时只有零星诗作问世,1935年《梦家存诗》后再无诗集出版,一种兴趣的转移正在发生。
按陈梦家自述,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古代宗教、神话和礼俗经由古文字学,之后转向了古史研究。这条路的起始或可追溯于青岛时期,“我记得在青岛的时候,晚间无事,我们两人手持一册,他常常吟诵古代诗人或外国诗人的诗篇。”[5]作为“闻门二家”之一的陈梦家,在这位贤师的影响下读了诗经、楚辞之类古人诗篇,还有外文诗。沉潜于旧体诗词和外国诗歌的体验使陈梦家颇为震撼,《铁马集后记》他这样说:“这册诗稿跟从我南北跑了两年半,我对它的爱心一天淡一天;自己多读些古人或异域人的诗篇,渐渐追悔五年来分行的事工,毕竟是壮夫不为的小技。”[8]
古典传统带给了诗人强烈的震动,他决心探索新诗道路的愿望也不幸受挫。1933年3月陈梦家在《论诗小札》中认为:“新诗现在走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大家似乎一天一天把自己可走的路逼狭了,人人都走在同一条旧路上。”[9]这指向的是新诗长久以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的日渐僵化,“内容千篇一律是抒情,形式是小诗。”[9]从前最爱“飞”、最爱抒情、最爱想象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现在转而反复重申着国家多难、民众遭劫的现状,强调应当寻找生活的“真诗”:“长在这混乱的漩涡中是幸福的,这里有最切身的材料,而我们正好经验着。眼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恶浊,总有一个门连着天堂的,无须乎飞上云霄去找——那会迷路的。”[9]诗人大胆质疑着当下的诗歌创作:“这时代本该再有一个杜甫出来的,为什么没有呢,也许是那些可以成为杜甫的不是迷路在天上,就是迷路在齐梁的旧辙上永远走不出来。”[9]那些“迷路在天上”的是还抱着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梦,而那些“迷路在齐梁的旧辙”的则是丢不开“采丽竞繁”的浮浅词藻和“兴寄都绝”的狭窄气象。
诗人痛心着“杜甫”在这个时代的失落,同时也失望于自己的创作尝试。1935年,在《梦家存诗》中,陈梦家为七年写诗生涯作了极清明的结账。“它们全在伤感中孕育成的,在发长的时期,遭受整齐的割裂,又掺杂了临时的外景。”[6]“这把锁链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6],在他看来,这样的诗,“伤感”而不是“情感”,“整齐”而不是“节奏”,“雕琢”而丧失“灵性”。于是诗人以构思一礼拜的《老人》达成对形式的有意摆脱,以理性滤沥挣开空泛抒情的窠臼。然而一写到长诗,诗人还是受到了“最大的丧胆”,他自称这是“造作时手臂上暴起的脉络”[6]。不同于小诗偶尔或可勉强运用单调的格律,长诗则会彻底暴露造字造句的局限,陷于凝滞、空洞、幼稚和矫情。
四、结语
当诗人之歌渐渐枯涩,日益成为“壮夫不为的小技”[7],灵性的努力突围也宣告失败,陈梦家最终选择以学术之刃破开新境界,从“最现代的文字”转向了“最古老的文字”。在陈梦家看来,若要完成新诗体的突破与创造,就必须更深刻地回到本国文化传统的脉络之中,寻求更具力度的意象,这便是向古史探寻。但是,如果说一开始诗人只是试图参考更多语料来寻找一种足以承托民族寓意的厚重意象,那么到最后,那些庞大悠远的古典情绪和古代文化则彻底抓住了他,推动陈梦家走向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型,自此他将个体融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试图再创造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