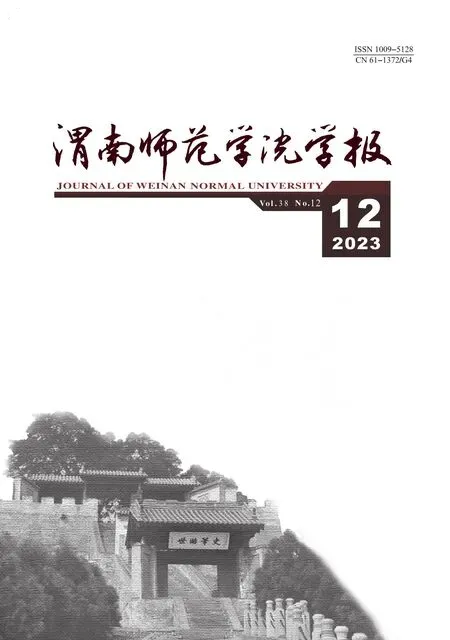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杨 玲,马皓斌
(兰州大学文学院,兰州 730000)
蒯通,本名蒯彻,《史记》《汉书》为避汉武帝讳,改“彻”为“通”。他是汉初策士的代表,上承战国策士遗风,深谙游说之道,辩才无双,曾被认为是《战国策》的编纂者[1];下涉汉初历史大变局,其三足鼎立之策若能奉行,重要性和影响力不亚于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清人姚苧田评价蒯通:“文在鲁连之上,品居王蠋之前。”[2]165鲁仲连、王蠋均是战国齐人,前者能说擅写,后者品行高洁。蒯通力压二者,其才其德于此可见。如此一位传奇人物,已有研究却多将蒯通作为韩信的附属,以蒯通言行印证韩信品格,考察韩信谋反事件的历史真相;或依据《史记》蒯通事迹,总结评价蒯通谋略辩才、策士风貌;或在分析马班异同时,将蒯通书写附为佐证史例;或关注蒯通故事由正史进入俗文学后发生的转变。少有研究注意到《史记》《汉书》后,《资治通鉴》也对其有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三部典籍在对蒯通的书写上存在着虽是细节,却至为关键、不容忽视的变化和差异。这些变化和差异直接推动了蒯通形象从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到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其加以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的著述特点、著述中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可以窥斑见豹,具体、细致地体察《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人物书写。
一、从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到乘时徼利之人
司马迁《史记》首记蒯通。秦末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张耳、陈余出谋划策,提出向北攻占赵地。陈胜故友武臣接受这一任务,迅速攻下赵地十城,剩余城池坚守,不肯轻易投降,范阳即其一。武臣决定强攻。大军压境,范阳令生死存亡之际,蒯通出场:
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3]3106
置身于秦末变局,蒯通洞见秦政权灭亡的必然性,因此主动出击,首先用“一吊一贺”的游说技巧引起范阳令注意,然后理智分析范阳令与百姓的矛盾,阐明据城坚守的危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范阳令相信自己可以解其困境,由此成功借力使力,代表范阳令去游说武臣。
面对武臣,蒯通首先声称有不战而胜、平定千里的妙计,引起武臣兴趣,在其追问下,蒯通顺势道出自己的计策:
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3]3107
蒯通认为,强攻,杀死范阳令,然后占领范阳城非上策。换一种做法:封官进赏范阳令,不仅可以轻松得到范阳城,而且也可以使其他地方官效仿范阳令,主动投降,如此则可以“传檄定赵”。蒯通的计策被武臣采纳,最终促成武臣不战而胜、蒯通辩才得以展示、百姓避免生灵涂炭的多赢结局。《史记》对这一过程详赡生动的叙述隐含了司马迁对蒯通其人其智的欣赏、赞许。
《汉书》承《史记》书写蒯通。班固将蒯通游说范阳令、武臣一事集中在《蒯伍江息夫传》,情节与《史记》大体相类,但是笔锋微调。
第一,《汉书》叙事语言有改笔补笔。其一是删。《史记》中,范阳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前有“秦法重”的前提,说明范阳令是迫于秦法严苛,不得已才伤化虐民。《汉书》删去“秦法重”,没有秦法的胁迫,范阳令上述举措则出于自愿,其形象也由此变为一个倚官仗势、任用职权、荼毒百姓的酷吏。蒯通帮助这样的人逃脱罪责甚至取得富贵,自己也有为虎作伥的嫌疑。其二是补。天下大乱,秦法不施,《史记》中“慈父孝子”争刃范阳令是为了“成其名”。《汉书》则是为了“复其怨而成其功名”[4]2159,补上“复其怨”三字强调了百姓在个人情感上与范阳令的誓不两立,也越发显得蒯通助纣为虐。其三是改。《史记》蒯通“闻”公之将死,前来献策。而《汉书》蒯通“闵”公之将死,方来救之,蒯通变为对话中的高位者,更易从心理上打击恫吓范阳令。此外,《汉书》蒯通对武信君的计谋之失也有夸大之嫌,《史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过”是“过分”,以武力攻城略地并非最优解。《汉书》改为“殆”,“危险”,指摘武信君的手段不是费力而是危殆了。《汉书》中的蒯通通过贬责他人、标榜自我,给自己的计谋加重砝码。
第二,《汉书》将《史记》中对话性内容改为人物独白。《史记》蒯通说服范阳令之后,直接面见武臣进行第二阶段的游说。但在《汉书》中,蒯通仍处于与范阳令对话的语境中,蒯通言“赵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问其死生,通且见武信君而说之,曰……彼将曰……臣因对曰”[4]2159,将预备游说武臣的话语和预测的情节走向先行向范阳令全盘托出。由此,《史记》献计范阳令和游说武臣两件实时发生的事,《汉书》将后一件改为预叙的形式,在蒯通劝服范阳令的一场对话中叙述完毕。预叙可以形成悬念,让读者产生一种心理期待,当预言变为现实,读者对谋划者智慧的赞服会更增一重。显然,《汉书》中事件的每一步都在蒯通预言中毫厘不差地进行着,《汉书》结尾又以“如通策焉”作结,果如所料,令人口服心服。
第三,《汉书》简化情节,突出对比。在蒯通申述计谋时,《史记》有“范阳少年”参与,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因为“范阳少年”变动性很大,他们既可杀范阳令以拒武信君,又可杀范阳令以应武信君,属于不可控因素,如此言说很容易让人找到逻辑漏洞。蒯通欲说服武信君将范阳令塑造成投降有利可图的例子,所以《汉书》蒯通不言“范阳少年”云云,而是紧紧抓住对待范阳令的两种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对比。同时,蒯通语言在《汉书》中更具文采和诱惑性。若是“范阳令先降而身死”,其他守城将士“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颜师古释“金城汤池”曰:“金以喻坚,汤喻沸不可近。”[4]2160比喻强调城池坚不可摧。而若是“范阳令先下而身富贵”,那么守城将士“必相率而降,犹如阪上走丸也”。斜坡上滚弹丸,颜师古曰:“言乘势便易。”[4]2160借势而为,毫不费力。《汉书》枝节的省略大大提升了因果关联速度,逻辑线索更加简单且结局对比明了。比喻又使得蒯通说辞节奏紧迫,落差增强,迫使范阳令、武臣惟策士之言是听。
《汉书》以上三种叙事策略使蒯通形象相比于《史记》发生明显变化。
从上文所论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蒯通深受战国策士影响,是一位有战国纵横家遗风的权变之士。他擅长虚拟事件,给自己的游说对象提供两种选择,并定向两个截然相反的结局,压迫听者思维。这种游说技巧类似于战国策士高频使用的对比之法。不仅如此,蒯通的言说内容也与战国策士相近。如他劝韩信背汉自立时曾说“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3]3164,与《战国策》所记陈轸游说秦王所言“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5]137相近,以至于杨宽先生认为:“看来蒯通曾经编辑和学习战国游说辞,这套话就是从陈轸那里学来的。”①杨宽先生在著作中提到上述言辞是“陈轸游说楚王”,考《战国策·秦策二》,陈轸是在与秦王对话中出现上述表达,应作“陈轸游说秦王”。详见杨宽《杨宽著作集古史探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74 页。相同的例子还有蒯通被刘邦质问和威胁时,以“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3]3168为自己开脱,这也正是《战国策》中貂勃回答安平君田单质疑时说的话。因此,司马迁在《田儋列传》中评议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3]3195。权变,即随机应变。司马迁在《苏秦列传》中说“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3]2749。在《张仪列传》中又说“三晋多权变之士”[3]2784。蒯通言行及成就与苏秦兄弟、张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迁所论道出了蒯通纵横权变之士的特点和原因。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子部纵横家类著录“《蒯子》五篇。名通”[4]1739,可证司马迁对蒯通的定位是恰当的。
与《史记》不同,《汉书》在书写蒯通时强调了他的智慧,锐化了他的计谋,使之拥有更大诱惑力,但同时通过突出范阳令的负面形象,给蒯通增加一重危险色彩,蒯通成为深不可测的奇士,难以掌控的辩士,为虎傅翼的谋士,他“一说而丧三俊”(烹郦食其,败田横,骄韩信),正是孔子严厉批判的“利口之覆邦家”[4]2189之人。班固甚至认为,蒯通没有被烹杀,不过是侥幸。
《通鉴》蒯通事迹基本采自《史记》《汉书》,对蒯通策士形象有所保留,除此之外,《资治通鉴》叙事语言中对蒯通说辞的删削改笔可以看出司马光眼中蒯通形象的另一面。《资治通鉴》省略了《史记》《汉书》中均有的“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这一蒯通表忠心的话语,也没有采用《汉书》蒯通所言“方今为足下计”(我为您出谋划策),而是继续保留《史记》的“诚能听臣之计”[6]347(假如能听我的计策)。变化虽小,但足以看出司马光对策士的态度,他们不过是一个在各方势力之间制衡算计,不论是非,从中谋利,择言为己,没有仁义、忠心可言的群体。这个判断是基于历史现实而言,诸侯国的存在是策士搅弄风云的前提。且从蒯通游说韩信不成,为避免牵连而“详狂为巫”,以及被捕后“狗固吠非其主”的辩解也可见他并非忠诚于韩信。司马光说韩信“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6]391,这也是他对蒯通的定位定性:一个胸无大志、心无是非的乘势获利者。
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采撷编排史料,生成了蒯通的三张面孔。书写是个人化行为,书写者常隐秘地将思想观念、情感立场表现于笔下,从蒯通形象的嬗递可以推究书写者的独特用心,如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
二、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书写体例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书写体例各不相同,而书写体例的选择会影响史书内部事件组织结构和人物塑造品评。
(一)《史记》以纪传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贯穿以人为中心的编纂理念。但是《史记》叙事过程中,为了事件的完整性,有时以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为叙事基点,已经有了纪事本末体的意味①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篇下》:“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 页。。
蒯通的游说生涯中,说服范阳令和武臣不过是他作为辩士小试牛刀,劝韩信背汉自立才是让他扬名立万、一举而为天下知的关键。司马迁考虑到蒯通献计的阅读效果,便将蒯通事迹向中心人物韩信的传记集中。这样处理,一方面可以保证重要历史事件的连贯完整,便于读者把握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这是纪事本末体最独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人物塑造有着相得益彰的效果。韩信对蒯通计谋弃置不用反映了韩信对刘邦的感恩与忠心,韩信结局和临死之叹也印证了蒯通的智慧和眼光,同一事件中的双方互为衬托,两相交涉中各自的言行举止互为对比,两人的个性形象都丰满起来。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淮阴侯列传》对蒯通的记述反映了他“此面”的性格特征,对于其“彼面”,司马迁采用“互见法”,本传略之,他传发之。《乐毅列传》中有一处《史记》独有,《汉书》《资治通鉴》缺失的文字:“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3]2941为何乐毅专传的“太史公曰”中会谈到蒯通的情感?
《报燕王书》是战国时期燕将乐毅回复燕惠王的信。信中乐毅详细回忆了燕惠王之父燕昭王的知遇之恩,君臣遇合的快意。同时申辩自己为了避祸而离燕投赵,隐晦地批评了燕惠王不察,不能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渗透着自己理想和抱负终不得实现的苦闷,惋惜中带有幽怨和愤懑,感情真挚,一片苦心。
蒯通泣涕,是情感上与乐毅产生共鸣。君臣不遇,贤主何寻?空有大计,奈何屡屡空置。随着韩信灭亡,自己纵横天下,三方博弈的抱负也就此消散在历史烟云中,“士不遇”的永恒困境一遍遍敲打着蒯通和司马迁的心灵。这是司马迁与乐毅和蒯通的共情。基于此,蒯通形象被涂上一层“士不遇”的困顿色彩,司马迁除了对蒯通其智的欣赏,对其人还有一种通忧共患的理解与同情。
欣赏、同情之余,司马迁对蒯通又颇有微词。他在《田儋列传》中说:“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3]3195蒯通为韩信提过两计,一是趁齐国田氏不备突袭齐国,韩信采纳而齐国乱;二是背汉自立,韩信未用卒灭亡。司马迁惋惜田横与韩信,因而批评蒯通之谋像一把利剑,挫伤众位英雄。司马迁对蒯通的态度是复杂的,且怜且责,青眼相看又责之切切。
在纪传体的大结构下,司马迁注重重要历史事件的连贯性,将与事件相关的历史人物言行集中在一起,蒯通书写的体例可以称之为纪传体和纪事本末写法的有机结合。同时通过“互见法”,在书中他处添补蒯通侧面,表达对蒯通复杂的情感倾向,与司马迁对蒯通“权变之士”的定位一致。《史记》蒯通书写体例的选择,兼顾事件的完整性、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和作者情感表达的充分性。
(二)《汉书》严守纪传体成法
《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下》中说:“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圆”指不拘成法、灵活变化,上述蒯通书写可见司马迁通纪传、纪事本末之长。而“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7]36,班固守纪传体成法,为蒯通立本传。
《汉书》的蒯通本传,在内容上将《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田儋列传》《淮阴侯列传》中蒯通的言辞事迹集中在一处。而在韩信等人的传记中,事涉蒯通,即只述梗概,以“语在通传”四字提示读者翻检《蒯伍江息夫传》。这一写法,一方面削弱韩信等人传记的可读性,文气亦不连贯;另一方面阅读之际前后翻阅补充,颇为烦琐。正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论:
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8]1440
其实,班固将蒯通与伍被、江充、息夫躬并列,打入另册,自有一番思虑。颜师古在《汉书》“列传”第一篇《陈胜项籍传》篇首注出作传原则:“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4]1785可见,通过“以类相从”的合传原则,班固认为四人是同类人。《汉书·叙传》称:“蒯通一说,三雄是败,覆郦骄韩,田横颠沛。被之拘系,乃成患害。充、躬罔极,交乱弘大。”[4]4250《蒯伍江息夫传》赞语说四人是“利口覆邦”的典型。可是,伍被、江充、息夫躬三人是在汉朝统一时期的“倾覆之徒”,蒯通游说时,天下尚未分明,难以定论他“覆”了谁的“邦”。班固以合传归类的方式强化了蒯通的负面形象,表达对蒯通的尤为不满与严厉批评。
但是,《汉书》单列蒯通传记,其生平轨迹得以完善。相较于《史记》,《汉书》在蒯通成功逃离刘邦后,增补了蒯通在统一的汉帝国时期的事迹。高祖统一天下后,曹参任齐相,蒯通做了曹参的宾客。蒯通经人建议,将东郭先生和梁石君两位隐士推荐给曹相国。蒯通运用寓言的方式,将两位隐士喻为守节不嫁的妇人,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劝谏曹相国以礼相待。[4]2166此处补笔或采自《韩诗外传》卷七。这段记述中,蒯通形象从口若悬河的辩士,变为曹参的侍从之臣。大一统的政治气候下,在各方势力中辗转的策士最终转变成为帝国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成为政治社会的稳定因子。《汉书》此笔有意彰显大一统政治的成功,与班固舍弃其父班彪续作《史记》的做法,改通史为断代史目的相同,“是一种‘宣汉’历史意识的体现”[9]396。
(三)《通鉴》编年体例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①《通鉴》是编年体例,但在书写的过程中取纪传之长补编年之短,借鉴纪传体史书追叙、补叙、带叙等叙事方法完善人物履历,带有一定纪传文学的特色。我们依旧能从时间脉络中勾连出人物的生平事迹,这也是《史记》《汉书》《通鉴》体例不同却能开展对比研究的内在原因。。蒯通事迹按照时间先后依次出现。编年体有简约和长于揭示历史大势的特点,司马光对蒯通言行多有删削,只有其行径影响重要事件转向、反映中心人物性格的时候才予以记载。
《史记》“游说武臣,传檄定赵”书写中,蒯通对范阳令一吊一贺的情节可以体现蒯通言语的魅力,进谏的智慧,《资治通鉴》删去。在司马光看来,武臣如何平定赵地,才是值得深究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余展现策士风采的细枝末节,不必采录,所以只保留蒯通对武臣的游说:
彻曰:“范阳令徐公,畏死而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则边地之城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君若赍臣侯印以授范阳令,使乘朱轮华毂,驱驰燕、赵之郊,即燕、赵城可无战而降矣。”[6]257
在说辞中,司马光进一步简化语言,将范阳令的性格、想法简略。蒯通向决策者武信君直接陈列出两种选择,用“君若……则……”“君若……即……”两组“措施—结果”型句式组合,言辞简省,少用“阪上走丸”等比喻夸张修辞。
蒯通作为司马光眼中的次要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主要事件的发展中伴随出场,次序清晰。只不过,他的存在是为了揭示武臣定赵的方式、韩信的并无反心、高祖的宽仁大度,而不再是《史记》《汉书》中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形象。《资治通鉴》后文蒯通仍被提及。《晋纪三十三》中幽州刺史辟闾浑参军张瑛为浑作檄,辞多不逊,南燕王德执之责备。张瑛神色自若,说:“浑之有臣,犹韩信之有蒯通。通遇汉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窃为不幸耳!”[6]3496指责南燕王德度量狭小。《陈纪二》陈宝应使人读《汉书》,听到蒯通游说韩信“相君之背,贵不可言”时,蹶然起坐,称赞蒯通智士。虞寄不赞同这种说法:“通一说杀三士,何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6]5220虞寄通过谴责蒯通之谋,试图打消陈宝应的谋逆之心。蒯通自身形象的丰满生动被《资治通鉴》忽视,立体感较《史记》大大削弱,缩减风化为一个关于谋臣劝反的符号,在史书中被一遍遍援引以论今。
三、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书写立场
司马迁和班固都生活在汉朝,且班固《汉书》对汉武帝前人物的书写以因袭《史记》为主,但是二书之蒯通却发生了从“权变之士”到“利口之覆邦家”的变化。这种变化何以产生?其原因何在?对比《史记》《汉书》关于刘邦与蒯通一段对话的书写,可以发现端倪。
蒯通劝韩信背汉自立,韩信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终为吕后、刘邦擒杀,临了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于女子之手!”因这句遗言,蒯通被诏捕至朝廷。接下来的情景,《史记》这样书写:
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3]3168
蒯通大方承认对韩信的策反,并认为若是韩信能听取,刘邦必不能轻易一统天下。刘邦闻此暴怒,下令烹杀蒯通。危急时刻,蒯通再次凭借口才化险为夷。《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对这一情景的书写与《史记》大体相同,但省略了“上怒曰亨之”前蒯通所言,也就是刘邦与蒯通对话的第一回合被删去。这虽是一小细节,却反映了班固的“天命观”。
《史记》中,司马迁借蒯通之口首次明确提出“逐鹿说”。蒯通在向刘邦描述秦末汉初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历史情势时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3]3168蒯通认为群雄并起,最强者获得最高统治地位,将刘邦得天下归功“人力”。这一逐鹿兴汉的观念承袭自战国以来“天命”坠地与“人”的发现的时代精神。[10]
与司马迁不同,班彪班固父子赞成“天命在汉”的说法。班彪《王命论》说:
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4]4208
班彪驳斥游士所谓“逐鹿说”为不自量力、觊觎神器的“瞽说”,认为天下神器只有得天命者才能获得,是天命而非人力决定谁将取胜。班固编纂《汉书》很大程度上应朝廷颂扬汉德、以示受命于天的需要[11]224-237,必然秉持“天命说”。既然天命兴汉,韩信便不足为患,蒯通之谋采用与否,对于刘邦一统天下何足道哉?正因班氏父子极为重视刘氏得天下的合理合法性,故而写作中处处留意,删去“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此类言论。
司马迁对天命持开放、探索态度,因此把“究天人之际”视为著述《史记》的宗旨之一。司马迁一方面质疑天命:“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257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天命有一定的可信度,《史记》中频见的相术应验书写可证。不过,“在天象人事的这种联系中,司马迁所强调的是人事对于天变的影响,即认为天象是人事的反应,而不是人事变化的根本和决定因素。是人间的事变引起了天象的变化,而不是天象的变化决定着人世的变化”[12],这就使得司马迁把注意力投注于“人”“人事”,而非天命。这一点从下面一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相近的书写可以看出。
韩信被封齐王,成为可以与项、刘任何一方相抗衡的势力之后,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于是极力劝说韩信据齐自立,与项、刘三分天下。其间谈到楚汉战争进入僵局,士卒疲惫、百姓蒙难时,《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有细节的差异。
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3]3162
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桀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锐气挫于险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罢极,无所归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贤圣,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4]2161
楚汉相争,战乱频频,百姓民不聊生,关于战争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史记》比《汉书》着墨更重。《史记》强调战争使“无罪之人”,即无辜卷入战争的平民百姓惨遭杀戮,父子老小暴尸荒野。《汉书》只是笼统带过,战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失所,百姓的惨状减弱,且不复《史记》的生动形象和感染力。后文《史记》所言“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整句着眼都在百姓。而《汉书》改为“百姓罢极,无所归命”,百姓疲惫不堪是因为没有君主可归依,立足点回到“命”,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由此,百姓的悲惨处境成为汉朝建立的铺垫。且《汉书》又删“怨望”二字,擦除百姓对刘、项长期战争的埋怨责备。如此可见,《史记》站在百姓立场,强调乱世百姓的苦楚;而《汉书》站在上层统治者立场,强调君主降世、拯救百姓于水火的急不可待。
司马迁多方游历,深入民间,与民众多有接触。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司马迁关注民情民生,情为民所系,在写作中透露出深厚的人民情怀。班固出身仕宦之家,又系外戚①参见范晔《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323 页。,与皇室关系密切,加之奉旨著书,故而刻意论证“汉得天统”,目光始终不离统治阶层。
《资治通鉴》与《史记》类似,没有用天命观说教,更加注重人事。司马光在《原命》中一方面说“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认为只有圣人才能通达精微难知的天道。另一方面却又说“是以圣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13]1402,洞悉天道的圣人治国的关键在人不在天。所以有学者言《资治通鉴》“言‘天人’,对天命,又信又疑,基本上撂在一边;对人事,大为关注,津津乐道”[14]。在同一事件的书写上,司马光的目光集中在百姓身上。
天下初发难也,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百姓罢极怨望,无所归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6]346
与上引《史记》《汉书》相比,《资治通鉴》省略“俊雄豪桀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熛至风起”[3]3162等天下大势的渲染,对于战争带给百姓的痛苦,《资治通鉴》基本采用《史记》说法,只是将《史记》强调无辜百姓受难的“天下无罪之人”改为“天下之人”,受难者的范围大大增加,反映出《资治通鉴》编纂者对于战争的反感和厌恶。后半句省略了楚汉军队锐气受挫、粮食缺乏的描写,百姓的“怨望”和“无所归倚”仍旧保留,着眼点上依从《史记》,关注民众的状况,只是写法上更加简洁。《资治通鉴》极为重视百姓视角,司马光认为国之休戚系于民,“国以民为本”[13]745,“夫民者,国之堂基也”[13]540,以民为鉴,民心向背可以反映治乱兴衰,故而百姓的生存图景一直保留在《资治通鉴》的叙事视野中。
或是平民百姓或是统治阶层的不同书写立场,影响了三位史学家的历史人物书写。班固《汉书》关注上层统治阶级,反对“逐鹿说”,以“天命说”强调汉得神器的历史必然,以百姓景况论证汉取天下的迫切。而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天命论”兴致寥寥,转向人民立场,目光始终不离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由此影响到三部经典对包括蒯通在内的人物书写。
四、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书写旨趣
作品是作者的言说,对作者书写旨趣的分析应是题中之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秉持各自旨趣书写历史人物,影响了对蒯通材料的剪裁安排和增删取舍。
相较《汉书》《资治通鉴》,《史记》对蒯通的书写最为细致,其原因除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著述宗旨,还有“附骥尾”的情怀。中国古人视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司马迁却看到闾巷之人即使努力砥行,依然很难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一鳞半爪、只言片语。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不愿、不能漠视草根阶层的光辉。史笔在手,他有一种自觉的承担,撰著中不掩“小”人物风采,使他们得以“附青云之士”[3]2574,留名青史。蒯通书写即一例。
《史记》对蒯通细致详赡的记载可见司马迁对其人文采智谋的欣赏,他不因蒯通曾是“谋逆之计”的发起人而不记或虽记却贬。他把最能展示蒯通才智的事迹附于《淮阴侯列传》,又借韩信遗言凸显蒯通在楚汉相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典型的“附骥尾”。如若司马迁也像班固,使蒯通和伍备、江充等人同传,后世又有几人知蒯通?司马迁写辩士、游士、商贾之士、侠客等非主流历史人物,彰显各色人物不同风貌,展现更加宏大的社会图景。《史记》也因司马迁“海纳百川”的史笔,包罗万象,以更宏通的视角观照人事的沉浮兴衰。
班彪、班固父子作为汉代文人,其著作《汉书》带有鲜明的“宣汉”意旨。“‘宣汉’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编纂思想的核心。”[15]从《汉书》的断代为史、汉承尧运、为尊者讳、渲染祥瑞等书写中都能体现班氏父子宣汉、崇汉的思想。在《汉书》中,“班固毫不厌烦地把他对汉王朝的崇敬与宣扬之情一遍又一遍的陈述出来”[16]40。而蒯通作为韩信、刘邦关系的挑拨者,自然是影响汉政权稳定的蠹虫,在书写中,其辞色的锋芒在《汉书》中耀眼可畏,字里行间闪露出危险的色彩,是“利口之覆邦家”的代表。
除了在书写中对蒯通警戒之外,班固还通过细微之处的改动以抬高刘邦地位。蒯通劝说韩信据齐自立、三分天下的说辞中,谈及战争环境下项羽、刘邦的所作所为,《史记》先言楚,后言汉,对项羽的叙述在刘邦前,符合当时灭秦战争和楚汉战争前期的力量贡献和实力对比。《汉书》直接将刘邦的作为移至项羽前面。《史记》称这场战争为“楚汉分争”,符合历史史实,当时相争的主力是以项羽为首的楚政权和以刘邦为首的汉政权,但是项羽、刘邦手下还各有依附的诸侯国。《汉书》改成“刘项分争”,隐退了其他小股势力,且在顺序先后上又将刘邦调至项羽前。崇汉意味自在其中。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以资治为旨归。这一点在其《进〈资治通鉴〉表》说得很清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挙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13]1646而宋神宗对《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期待进一步强化了此书“资治”宗旨。基于此,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蒯通的言辞做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为了劝说韩信反叛自立,用了“相面游说法”,这是被后代读者津津乐道的一个精彩情节,原文约一百八十余字,《资治通鉴》删改后不足八十字:
武涉已去,蒯彻知天下权在信,乃以相人之术说信曰:“仆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彻曰:“天下初发难也……”[6]346
《资治通鉴》删去了《史记》“贵贱在于骨法”的相术导论和私密性的所有描写,只将相术作为由头,以一问一答迅速切入蒯通策反的言论,使读者从相人之术的神异气氛中抽身出来,直面现实政治矛盾。司马光反对神怪迷信,自然不信相面,他认为蒯通在故弄玄虚,“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6]4809,虚妄之事无益资治,因此《资治通鉴》书写始终保持着祛魅的自觉。
在蒯通最后劝导韩信“机不可失”一段中,《资治通鉴》省略《史记》诸多语句(括号内为《资治通鉴》省略语句):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3]3164
可见,《史记》中蒯通奉承之言、不可甘于屈居臣位、“贵能行之”四喻,《资治通鉴》均省略。保留下来的只有关于抓住时机、早下决断的劝导。司马光本就认为策士说辞多夸张假饰,不足为取。且在教唆反叛之事上,书写时更注意尺度。《资治通鉴》开篇“臣光曰”即提出礼制思想“礼莫大于分”,“何谓分?君、臣是也”。司马光通过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说明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6]3。故而“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6]9511。蒯通的僭越之辞不合为臣之道。《史记》上文“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3]3164,《资治通鉴》亦省。司马光不想引起君臣之间的猜忌,必然要在书写上通过省略来消解君臣对立,弥合君臣关系。
综上,蒯通形象的嬗递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在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的制约下,采择史料、删削修润所致。《说文解字》释“史”曰:“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17]116所谓历史就是史官客观公正地记录下来的曾经存在、发生的人和事。既如此,三位史家所为是否违背了古人对历史的认识、对史官的要求?答案是否定的。
史学文本并非史料的堆砌,而是在文本书写中渗透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创造。《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8]745此即《春秋》笔法五例。钱钟书先生说:“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就史学之演进而言,‘五例’可征史家不徒纪事传人,又复垂戒致用。”[19]162“载笔之体”即如何书写历史,“载笔之用”即历史的功用。在钱先生看来,史家的责任不仅仅是纪事传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历史实现“惩恶而劝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更是将“史之为用”提升到“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20]281的高度。可见,在传统史官眼中,价值判断和意义创造比直录史实更加重要。也就是说,书写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被允许介入史录,史官修饰权力被承认,“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被准予。“点窜涂改”“陶铸群言”是史家应有的权利①章学诚《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34 页。。他们可以在广搜博览、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删改润饰,“即彼陈编,就我创制”②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8 页。,只要“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7]209。正是在这一认识下,后人评价《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2738,《汉书》“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21]1386,《资治通鉴》“兼收并蓄,不遗巨细”[22]237。所以,我们不必质疑、惊讶同一个蒯通何以在三部经典中有三副面孔。新历史主义提出“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前者提醒我们历史一旦书写成文本就是史料和作者的合作品,后者意味着“文本并非是一个超历史的审美客体,而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阶级、权力以及文化等语境的产物”[23]456。蒯通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经典中形象不断嬗递,是书写者受制于各自时代和自身因素的必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误读”,他们都对史料进行了二次叙述。得幸于前代经典的保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修改痕迹,并能从文本的书写中感受历史人物形象的演变,推知“变形”背后撰述者的史意文心。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的心血之作,蒯通形象的嬗递反映出他们均不甘于做纯粹的历史转述工具,体现出他们利用书写的权力裁决事件、臧否人物的努力。出于不同的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三位书写者剪裁、删拾、组织史料,最终生成不同的蒯通形象。读者通过对《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相关文本的比读、分析,不仅能够深切感受人物形象的变化,而且还可以以小见大,体悟书写者寄托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甚至是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