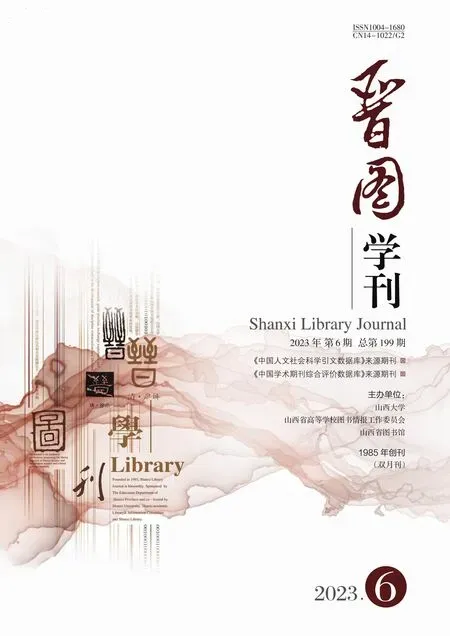论《四库全书总目》杂事小说的善本标准
郑丽梅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0 引言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总共收录杂事类小说86部(包括存目),在这86部杂事小说提要中,四库馆臣均作出或详或略、或高或低的评价,四库馆臣评估杂事小说优劣的标准至今仍龂龂难断。本文主要以梳理杂事小说提要为主,结合四库馆臣的小说评论,最后总结出《四库总目》杂事小说类的“善本”标准,并同版本学“善本”标准区分开来及窥探出四库馆臣的小说思想,以期裨益于相关研究。
在进行论述之前,很必要明确几个问题:一是本文的小说概念并非指由西方传入的小说之概念,而是取自《四库总目》的小说概念,即同班固的亦是本土的定义;二是本文的研究的范围仅限于四库馆臣对杂事小说类的提要部分,目的是对《四库总目》中杂事小说善本之标准进行总结,非《四库总目》对杂事小说类著录之标准的总结,故本文得出的结论无法保证符合杂事小说类以外的作品;三是关于善本,其概念是变动的而非固定的。
1 《四库总目》杂事小说之外的善本概念
关于古籍的善本概念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其当时所用的词语是“善书”而非“善本”,如《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注‘真,正也。留其正本’”[1]。可见在西汉已经注重辨伪,注重版本的择选,以正本为善书。而“善本”一词首次作为版本学概念乃昉自北宋。版本学上的善本,具有经过精细校对的概念,稀有而珍贵,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唐田弘正家庙碑》中提到:
“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2];北宋叶梦得认为唐前藏书多善本的原因,在于稀有且精校过,“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3]
再如《宋史卷二九四·列传第五三》载:
“北宋元祐四友”之一的王钦臣,即王仲至,“……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4]
据朱弁的《曲洧旧闻》所载,北宋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的藏书注重版本择选,且因宋之藏书经过其多次校对而受世人追捧,被称为“善本”:
“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5]
显而易见,北宋的善本的概念,指的是经过精校后的版本,受人追捧。到了南宋更是延续了这种善本观,认为善本是经过精校后的标本、基准,有供别本校对订正的作用,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淮南子》二十一卷时提及,其所藏的版本残缺而没有善本可供订正,“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洎南宋陈振孙,对于善本便有了更完善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其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中。除精校本之外,直斋还补充了足本、旧本等[6]。
自宋以降,人们对于善本的看法与宋代的善本观大同而小异。无论是清人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跋》提出的“四条善本标准”(1)[清]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跋》提出的四条善本的标准:一曰旧刻;二曰精本;三曰旧抄;四曰旧校。,还是张之洞的善本标准(2)[清]张之洞在《輶轩篇·语学篇》提出善本之义有三:一是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是精本(精校、精注);三是旧本(旧刻、旧钞)。,抑或是今人提出的“三性”(3)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三性”是指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流传较少的古籍。,均不出宋人之范围。虽关于善本的说法各式各样,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以上的善本观都透露出,善本作为一种经过精校的足本,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地位,它是最佳底本,是所有版本与之对齐的目标。
2 《四库总目》杂事小说的善本标准
“善本”一词在《四库总目》小说家中总共出现于4处,分别在《因话录》《唐语林》《东南纪闻》和《残本唐语林》的提要中,因《唐语林》和《残本唐语林》实际为一合本,故“善本”一词在小说家提要中真正只出现3次。
《因话录》:“……所载亦不免於缘饰。然其他实多可资考证者,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7]1839
《唐语林》:“前有之鸾自序,称所得非善本,其字画漫漶,篇次错乱,几不可读……”[7]1857
《东南纪闻》:“然大旨记述近实,持论近正,在说部之中犹为善本。”[7]1867
由此可知,真正的杂事小说“善本”在四库馆臣看来不仅仅指文献完好如初,更是指文献内容存在一定的史料价值、思想价值以及广见闻之价值,即更侧重文献的学术性,正如其在小说家序中写的“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通过对《四库总目》杂事小说类内容的梳理与归纳,《四库总目》杂事小说的“善本”标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点。
2.1 真:记述近实
在四库馆臣的杂事小说评语中,“补史之阙”“证史”“可资考证”等一系列与史相关的词语频繁出现,说明《四库总目》中的“小说”非如今所说的“小说”。前者是小道之说,街谈巷语,在四库馆臣看来,小说非正统之学,其存在大多是补史之阙,参合政史,更偏向史学而非文学;后者则是进行虚构化的文学,亦四库馆臣所不崇。如班固《汉书》对小说的解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四库总目》将小说家的分类及态度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四库总目》对班固《汉书》之小说家概念的体认,符合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
出于史学的角度,四库馆臣认为杂事小说的内容记述应该有所考证以接近实际,这一点是有关小说能成为善本和能被四库馆臣收录的关键。如《四库总目》对唐人赵璘的《因话录》部分内容就予以较高的评价,虽有谬误,“然其他实多可资考证者,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7]1839。四库馆臣评述小说家著述时云:
“唐、宋而後,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7]1838
唐宋之后的小说真假掺杂,《因话录》如是,然而因为它存在考证据实的内容居多,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因而能被四库馆臣称之为“善本”。除此,据《四库总目》所收录的杂事小说作品,虽不乏侈谈迂怪之作,但有史学价值的作品居多。
或有裨考证,杂事小说可作为史学的辅助性证据非直接证据,如:
《云溪友议》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7]1841;
《北梦琐言》者“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而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7]1845;
《南部新书》者“虽小说家言……,於考证尚属有裨”[7]1846。
此外,还有《王文正笔录》《水东日记》《乐郊私语》《投辖录》等。
“据之为证”“可资考证”“裨于考证”等批评词语的频繁出现,透露出了四库馆臣对杂事小说考据价值的侧重,认为杂事小说具有可作为考据的补充性佐证材料的文献价值。
或足以补史阙,杂事小说可作为史学的补充性文本,如:
《松窗杂录》者,“书中记唐明皇事颇详整可观……是亦足以补史阙”[7]1840;
《大唐传载》者,“所录唐公卿事迹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7]1867;
《唐言》者,“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7]1867;
《归潜志》者,“载天兴元年刘元规使北朝……皆足以补正史之阙”[7]1867。
此外,还有《高斋漫录》《珍席放谈》等。
或足以与史相参证,所谓“参证”即参考验证,与考证不同,以资相参的文献真假存疑,需要多个文献进行验证,杂事小说可作为史学的参考性验证。如:
《乐郊私语》者,“所记轶闻琐事,多近小说家言。然其中如杨额哲武林之捷,张士诚杉青之败,颇足与史传相参。所辨六里山天册碑……亦足资考证”[7]1869;
《中朝故事》者,“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固未尝不足以资参证也”[7]1843;
《金华子》者,“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其中……靡所不载,多足与正史相参证”[7]1843。
等等。
如此可见,四库馆臣划分的杂事小说是依附史学存在的,以服务史学为主,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这也证实四库馆臣对小说的考证据实方面十分看重。小说可以烦琐有瑕疵,但绝不能无裨于史,因而成为小说善本的关键一点,则是记述必须要极力接近真实而具有史学价值。
2.2 正:其论近正
《四库总目》作为一部官方目录,作品的存在与官方的价值取向关系颇深,被收录在内的作品不可背离正统思想,正如小说家序中所云,“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7]1834,小说不单单需要求真,还需要求正。根据《四库总目》所收录的杂事小说提要,此“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评论要公允;二是思想要雅正。此为杂事小说善本的第二点要求。
《四库总目》收录杂事小说中持论公允的,有如《儒林公议》:
“明悉掌故……其持论亦皆平允……书中虽於竦多恕词,而於富弼诸人竦所深嫉者,仍揄扬其美,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其心术醇正,亦不可及……儒者犹存直道,不以爱憎为是非也。”[7]1847
四库馆臣评论田况思想端正,认为其论说不以个人爱憎恩怨为转移,犹存儒者风范。再如:
《山房随笔》:“所记多宋末元初之事……所言良允”[7]1868;
电气自动化的发展,得益于近现代科技的进步与相关理论的出现,总体来看,电气自动化的发展主要受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枫窗小牍》:“其是非亦皆平允”。
此外,在苏辙《龙川略志》的提要中肯定了苏辙不以个人恩怨为转移的客观做法,并发出“此辙之所以为辙欤”的感叹,“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动辄归怨於君父。……”[7]1850
《四库总目》收录杂事小说中思想内容雅正的作品甚多,其中虽有内容猥杂者,然其论近正,亦不可因内容猥杂而废之,这主要是受到官学维护中央统治的思想影响。如《山居新语》的提要有云:
“记朱夫人、陈才人之殉节,记高丽女之守义,记樊时中之死事,则有裨於风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资劝戒者颇多。”[7]
四库馆臣认为《山居新语》里有“裨於风教”和“可资劝戒”的内容,“虽亦《辍耕录》之流……则胜之远矣。”
再如评《东斋记事》遵守伦理规范:
“其书多宋代祖宗美政,无所谓诽讪君父,得罪名教之语。”[7]1849
评《萍洲可谈》虽琐屑,但有助于风教:
“即轶闻琐事,亦往往有裨劝戒。”[7]
四库馆臣还认为:王定保《唐摭言》所记杂事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7]1842;《大唐新语》“取轶文旧事,有裨劝诫者”[7]1837;《教坊记》《唐国史补》《山房随笔》等等“有裨劝诫”“裨於风教”,均是存有雅正思想的小说,具有裨益社会风教的价值。
《四库》作为官修目录,“其论近正”除了受到官学维护中央统治的思想影响,还受到了孔子收录《诗》三百“思无邪”和“兴观群怨”说的思想影响,如《四库总目》收录的《随隐漫录》载南宋臣降君辱之惨时,流露出自己的怨愤之情,颇具《史记》“史蕴诗心”的发愤著书之风,四库官臣以之为说部中的佼佼者:
“……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惨,与所以致败之由,终无一言之显斥,犹有黍离诗人悱恻忠厚之遗,尤非他说部所及也。”[7]
还如论及《张氏可书》,称其意存鉴戒,以文载道:
“迨其晚岁,追述为书,不无沧桑今昔之感。故於徽宗时朝廷故实,纪录尤多,往往意存鉴戒。”[7]
有作者声誉欠佳,然其论近正者,亦不以人废之,如《青箱杂记》的作者吴处厚为人风评欠佳,但其论犹有可取之处:
“然处厚本工吟咏……皆绰有唐人格意。故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7]
其论近正的小说要么持论公允,要么史蕴雅正,要么二者兼备。具有寓劝诫、正世风的价值,是小说成为“善本”第二点要求,也是维护官方统治的要求,亦有孔子“思无邪”和“兴观群怨”说的影响。
2.3 博而简:材博言简
所谓“博而简”是指小说善本取材应广博,但叙事语言需简洁有条理,否则便落于猥杂琐碎的窠臼。《四库总目》所收录的杂事小说,内容庞杂,难以厘清内容类目,如关于《大唐新语》的收录分类,其“皆取轶文旧事有裨劝戒者”,“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7]1837。在比较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和李心传书时,四库馆臣采用明人王士禛的看法,“颇涉烦碎,不及李心传书”[7]1865,于是将李心传书归入史部,而将《四朝闻见录》列入小说家。据此可知,取材广博是小说家与他家的基本区别,取材广博可资采掇,具有广见闻的价值。如评以下作品,多以博材论之:
《西京杂记》:“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
《朝野佥载》:“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於见闻也”;
《独醒杂志》:“书中多纪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见闻”[7]1864。
等等。
“博”是小说的基础;“简”是善本小说的要点。取材广博者可置于小说类,然不可成为小说之“善本”。小说中的“善本”除了上述所需的“近真”和“近正”,还需要语言上的简洁有序,也就是说,善本小说与普通小说的区别在于,在取材广博的基础上,看它是否融“真”“正”“简”于一体。在《四库总目》中,陶宗仪的《辍耕录》4次被作为比较的劣方出现在其它小说的提要中,分别如下。
元孔齐撰,《至正直记》:“是书亦陶宗仪《辍耕录》之类,所记颇多猥琐……”[7]1891
宋周密撰,《癸辛杂识前集》:“而遗文佚事可资考据者实多,究在《辍耕录》之上。”[7]1866
元杨瑀撰,《山居新语》:“……则亦颇有助於考证。虽亦《辍耕录》之流,而视陶宗仪所记之猥杂,则胜之远矣。”[7]1868
元郑元祐撰,《遂昌杂录》:“其言皆笃厚质实,非《辍耕录》诸书捃拾冗杂者可比。”[7]1868
对于《辍耕录》的表述,四库馆臣多用“冗杂”“猥杂”“猥琐”“猥亵”等非褒义之词。再看看四库馆臣对《辍耕录》的提要评语:
“惟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颇乖著作之体。叶盛《水东日记》深病其所载猥亵,良非苛论。然其首尾赅贯,要为能留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宗仪练习旧章,元代朝野旧事,实借此书以存,而许其有裨史学。则虽瑜不掩瑕,固亦论古者所不废矣。”[7]1869
“瑜不掩瑕”一词将四库馆臣鄙夷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知,《辍耕录》在四库馆臣的心中居下品,是不被推崇的。对于内容烦琐复杂的小说,四库馆臣更倾向于简洁清朗的小说,如四库馆臣评价《异苑》时,称之“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一旦史家文献的内容过于烦琐,四库馆臣便会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如唐刘肃《大唐新语》便是因为《谐谑》一门的内容偏驳杂,四库馆臣称之“繁芜猥琐,自秽其书”[7]1837,于是退而求其次将其归入小说家类。至于《辍耕录》能被收录入内,是因为“其有裨史学”,据此可知,取材广博是小说的基本特点,而语言简洁则是“善本”小说的必要条件。
简言之,依四库馆臣看,真正的杂事小说善本是在取材广博的基础上,融“真”“正”“简”于一体的小说。杂事小说善本具有记述近实、其论近正和材博言简三大标准,是作为服务他者而存在的文献,或有裨于见闻,或有裨于史,或裨於风教和可资劝戒,具有很高的资料学术性。它只是作为一块“砖”去完善镶嵌“一栋房子”,而不可以独立成房。
3 结束语
基上述可知,在文献地位上,四库中的杂事小说善本不等同于其他善本,它的文献地位高低取决于它对史学的价值大小。其他善本是底本、标本,可作为直接依据,而四库馆臣眼中的杂事小说善本是校本、补充本,可作为参考依据,也就是在没有最佳选本的情况下,那么补充本就被需要了。
根据《四库总目》中杂事小说善本的标准和文献地位,善本小说与其说归于小说家类,还不如说属于史家类,当一个杂事小说同时满足了记述近实、其论近正和材博言简三大标准,那么其再也不是四库馆臣笔下的“小说”,而更像是一部庞大的纪事体史书,那么便可归于史部。主要原因在于,四库馆臣受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具有浓厚的笃实思想。除此,“小说”一词在四库馆臣那实际上含有贬义,此贬义是相对史家文献而言,如当四库馆臣批评小说的不好之处,有乖史家之体例时,常常使用“小说家言”“堕小说窠臼”“小说家猥琐之习”“小说习径”“小说习气,为自秽其书”等等。
由此可知,小说在四库馆臣看来非正统之文,而是史家的草稿或笔记,小说的存在依附于史学的存在,小说是为史学服务的。基于此小说观,在小说家的收录上,四库馆臣持较为宽容的态度,或不以人废书,或不以小疵废书,只要有裨于史学,即具有学术性便可收录在内,这也正体现了四库馆臣务实求真以有裨于史的小说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