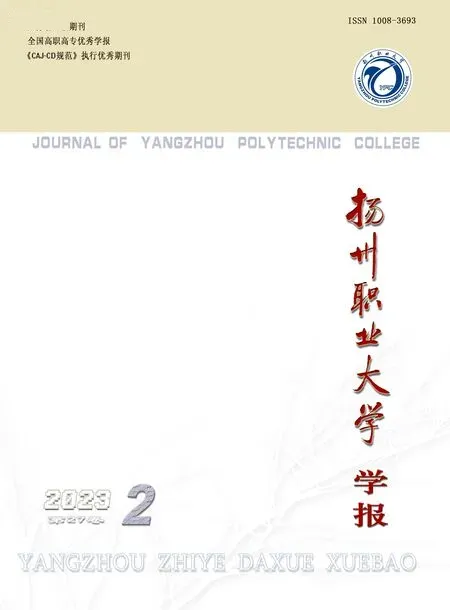辽金族际婚姻述略
方 舟
(扬州职业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9)
辽国和金国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具有历史上的承续关系,二者除了在时间上前后相接,在领土上有所重叠之外,在人口构成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民族成分多元、民族关系复杂的鲜明特征。区别于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上出现过的一些民族政权,辽金两国不仅存在时间更加长久,地域范围更加辽阔,而且政局较为稳固,社会较为安定,这些有利的外部因素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族际婚姻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与成果展现,它的发生机制、发展态势、存在形态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正因如此,对辽金族际婚姻情况加以考察,不失为一条加深对民族融合问题理解与认识的有效途径。
1 契丹族际婚姻
辽国契丹族姓氏惟耶律与萧,别无他者。另据《契丹国志》载:“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1]221依此而论,耶律便基本上只能与萧联姻,这显然是族际婚姻的不利因素。除此以外,辽国契丹族并未与其他民族人口大范围杂居,虽说统治者掳掠、征调外族人口迁徙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也只是让他们迁至某地后再行聚居。如易俗县为辽东渤海之民“尽迁于京北,置县居之”[2]300,长春县为“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2]304,宣州同为“开泰三年徒汉户置”[2]304,宗州为“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2]317。泰州(今黑龙江)的情况则更具代表性:“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2]304对于饱受侵扰的通化州民也仅仅是让其“近本族”加以保护而不与其杂居,其原因就在于契丹人并未随政权建立而改变本民族逐水草而居、游牧渔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居住环境必须是土地空旷、人烟稀少的森林草原,因而辽国时期并不存在契丹人口大量南迁的情况。这一点显然使得多数契丹人与农耕民族百姓之间的交流较少,也成为民间族际婚姻的极大障碍。然而也应该看到,虽然族内婚是契丹婚姻的主要面向,但契丹上层的族际婚姻却依然存在。
1.1 相对自由的辽国契丹男性族际婚姻
契丹男性族际婚姻比较自由,帝王纳娶外族女性无所禁忌,官员纳娶外族女性也基本不受限制。虽说辽国帝王依规须与后族婚配,但历代统治者中仍不乏大权在握而不尊祖训者。渤海国灭亡后便陆续有一些渤海降人后代成为帝王的婚配对象:辽景宗曾纳渤海妃,其姓名、生平不载,可能是平民或宫女出身[2]632;辽圣宗曾纳大氏,大为渤海国姓,应为王族后裔[2]635;天祚帝之妃萧瑟瑟同为渤海大氏人,其改姓情况不详[1]146。辽国宫廷中亦不乏汉族女性,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曾接受南唐李昪“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1]20;辽世宗攻克后晋大梁时得后唐宫人甄氏,宠遇甚厚,天禄元年(947)即位后册其为皇后,可见夫妇双方感情不差,这场婚姻也并非一定是出于胁迫[2]818;辽圣宗于开泰二年(1013)曾一次性纳“马氏为丽仪,耿氏为淑仪,尚寝白氏为昭仪,尚服李氏为顺仪,尚功艾氏为芳仪,尚仪孙氏为和仪”[2]120。耿氏“以良家子入选”,为汉族功勋耿崇美的孙女[3]119,属于通过遴选形式入宫的士族家庭女性。另五位来历不明,其中有四位在册妃之前已有女官阶,考虑到“澶渊之盟”(1005)达成未久,她们很可能是在辽宋战争中被俘后没入宫籍的汉族女性。此外,东丹王耶律倍也曾纳娶渤海王族大氏和右姓高氏[2]824-825,他作为原渤海国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被封为“人皇王”,自然可以像帝王那般不受限制地纳娶当地贵族女性。由此可知,辽国帝王的族际婚姻以权力为外部条件保障,以个人欲望为内在驱力,与历代帝王的婚姻情况并无差异。
帝王以外其他契丹官员的族际婚姻也没有过多障碍。辽国自太宗始便规定“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人仪,听与汉人婚姻”[2]35,考虑到官员职位的不断变更,就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契丹男性可以自由地与汉族女性通婚。如南府宰相耶律瑰引娶郑氏,其子耶律仁先又娶肃氏[4]751-752;鸿胪少卿耶律筠先后娶“清河郡夫人”张氏之女马枢哥、马省哥[4]637-638;静江军节度使萧孝忠纳“汉儿小娘子苏哥”[4]858;长宁宫汉儿渤海都部署使耶律庶几娶刘氏;耶律惯宁于霸州任上以墨太保为媒求得刘令公孙女寿哥夫人为妇[4]856-857,这些婚姻都无须征得辽国统治者允许,但其性质却存疑。马枢哥、马省哥出于官宦之家,刘寿哥为地方富户之女,她们的婚姻性质基本可以确定为以门第为基础的自然聘娶。其余女性则身世不载,根据宋人记载,辽国契丹权贵时有强娶民女的行为,以致于“幽蓟之女有姿质者,父母不令施粉白,弊衣而藏之”[5],因此不能排除她们是契丹官员权势胁迫下的民间女子。
1.2 以赐婚为主要形式的辽国契丹女性族际婚姻
统治者赐婚是辽国契丹女性族际婚姻的主要形式。辽太宗赐婚“北大王帐族女耶律氏”于通事高唐英[3]37,赐婚燕国公主于汉人枢密使刘珂[1]157;辽景宗赐婚渤海妃之女耶律淑哥于兴国军节度使卢俊[2]632;法天太后强逼耿元吉娶其妹晋国夫人萧氏[1]144;辽圣宗将昭仪白氏之女八哥、十哥、擘失分别下嫁进士刘三嘏、枢密直学士刘四端、奚王萧高九,将大氏女长寿下嫁渤海贵族大力秋[2]635-636,将景宗外孙女萧氏下嫁刘二玄[6]341。自统和四年(986)党项族李继迁归附起,辽国先后有三位公主嫁往西夏:辽圣宗将王子帐耶律襄之女下嫁西夏首领李继迁[2]1044,辽兴宗将兴平公主嫁给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2]1045,天祚帝将族女耶律南仙嫁给西夏国王李乾顺[2]1047。由于西夏是辽国的藩属国,因而公主外嫁的和亲也可以看作是赐婚的特殊形式。此外还有一些纳娶契丹女性的案例虽未明载,但依据非北主之命不得通婚外族的规定,也应该属于赐婚一类,或至少获得辽主的同意。如耿崇美与其子耿绍忠分别娶“卫国夫人耶律氏”与“北王之息女”[3]14,奉班祗候梁延敬娶东丹王子荆王耶律道隐女[4]542,临海军节度赵匡禹纳护卫相公萧某之女为继室[4]359,静江军节度使刘庆馀之妻为耶律氏[4]827,北枢密院敕留承应张恭谦之子张伸也曾纳娶耶律氏为妻[4]656。赐婚通常是一种以笼络人心为出发点的强制性恩遇,但当事双方可能因缺乏感情基础而婚姻质量不高,相关政治目的难以实现。如耶律淑哥因与卢俊不谐而“表请离婚”[2]632,刘三嘏因“与公主不谐”而奔宋,被遣返后遇害[2]900,大力秋因参与大延琳事而伏诛[2]635,兴平公主与李元昊不谐而死于西夏[2]1045,这些都反映出赐婚的局限性,至于法天太后仅仅为了满足其妹的欲望而挟权杀死耿元吉发妻的做法更是有悖人伦[1]144。
1.3 辽国契丹族际婚姻中的特殊情况
奚王族及玉田韩氏家族在辽国与契丹人频繁通婚,属于族际婚姻中的特殊情况。奚族在契丹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归附较早,且与契丹同出鲜卑宇文部之后[2]585,两者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因而在辽国享有与契丹同族的政治待遇。《金史》记载“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6]1052,述律氏为后族,因此奚贵族被赐予萧姓,其联姻对象为王族耶律氏。奚人萧韩家奴之母为耶律氏,其弟萧福延又娶耶律氏[3]131-132,其子萧忠信又娶耶律庆嗣之妹迪辇夫人[7]457-458。耶律惯宁曾先后求得神得奚王之女蒲里不夫人和挞里么奚王孙女骨欲夫人,骨欲夫人第三女又聘予孙里古奚王为妇[4]856-857。此外甚至还存在辽世宗之母、东丹王之妾柔贞皇后萧氏为奚族人的观点[8]。汉族韩知古家族同样因归附较早且功勋卓著,被辽国契丹人视为同族。这一契丹化的汉人家族世代以后族萧氏为通婚对象,特别是韩氏从第三代人韩德让开始被赐予国姓耶律[2]877,家族成员与后族的联姻关系便更加顺理成章。辽国韩氏七代人婚姻状况可考者59位,通婚对象73例,其中契丹萧氏占52例[9],这些数据正是联姻关系的有力表现。奚王族及玉田韩氏家族的成员既纳娶契丹女性,也嫁给契丹男性,人数较多且不受限制,在本质上属于披着族内婚外衣的族际婚姻。
1.4 金国时期的契丹族际婚姻
金灭辽后,少数契丹人随耶律大石前往西域,多数契丹人则成为金国的臣民,其中一部分战争中被俘的契丹女性成为金国的战利品,另一部分契丹上层继续与汉族、渤海、奚族保持婚姻关系。耶律氏嫁于靖康俘虏李浩,生女于五国城[10]256,侯氏嫁给耶律彻,为海陵王徒单皇后侍女[6]1000,这些可能是金国人主导的契汉婚配;礼部侍郎萧拱之妻妹耶律弥勒为张氏所生,当为契丹与汉族或渤海族之通婚[6]1002;耶律察八尝许嫁低阶武官奚人萧堂古带[6]1003,说明金国时期的契丹与奚族延续了通婚关系。东丹王家族在金国受到优待,并与汉族士族家庭保持着稳定的通婚关系,耶律履曾先后纳娶“岞山世胄之孙”郭氏和“名士杨昙之女”杨氏[4]3067-3068,长子耶律辩才娶靖氏[4]3060,次子耶律思忠娶郭氏[4]3044,三子耶律楚才先娶梁氏,降蒙后又娶苏轼四世孙苏氏[4]2841。除此以外,数量更多的契丹降人则被编入金国基层组织猛安谋克,并在随后经历了频繁的逃亡、分散、迁徙、征调。金太祖破东京后收编契丹降民,以讹里野领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6]654;耶律余睹于天会十年(1132)密结燕云地区契丹人起事,失败后部分契丹人“亡入夏国,及北奔沙漠”。皇统初年(1141),部分契丹人随女真屯田户“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11]278;大定二年(1162),耶律窝斡领导西北路契丹人起义失败,当地契丹猛安谋克被拆散混编入女真猛安谋克[6]86,并于大定十七年(1177)被征调至上京等路,以便“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6]1305。由于与女真紧张的民族关系,许多契丹人在金后期投奔蒙古,并在元朝完成了自身的民族融合。
2 女真族际婚姻
同为少数民族政权,金国女真族际婚姻的发生条件较辽国契丹族要好。一方面,区别于辽国的南北分治,金国统治者曾大量迁徙女真族人至中原地区,史载“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罗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结屯而起”[11]72,其数量高达40猛安,约96万口之多[12]。随居住环境改变的是生活方式,女真人不得不由原先的打渔狩猎转向农耕,并在屯田垦殖中与汉族人频繁交往。金国中期女真汉化已十分严重,许多人说汉语、着汉服、用汉姓,反映出封建经济、文化对固有习俗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金世宗曾下令女真人聚族而居,与汉人民户分开耕种,二者田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6]1077,但收效有限。另一方面,金国婚姻政策更加宽松,统治者大多对族际婚姻持包容和鼓励的态度。除世宗以外,统治者不曾对南迁女真人的通婚加以限制,章宗还曾采纳尚书省意见,令汉族平民与女真屯田户“递相婚姻”,甚至主动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6]184,进而促成了“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的局面[6]653。南宋官员蔡戡在分析金国民情时认为:“后来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彼方之情视其母尤亲,背其父之训。骄纵懦弱,习与性成,非复昔日女真也。”[13]这表明女真猛安谋克户与其他民族百姓结为婚姻、组建家庭、生育后代的情况客观存在,然而民间婚姻当事双方大多身名不显而难见经传,更加具体的情况难以寻得。现有史料中女真族际婚姻的相关信息主要集中于贵族官宦阶层。
2.1 掠夺性质的女真男性族际婚姻
区别于契丹立国之前与唐、五代时期的中原政权交往多年,女真直至建国之初还处于原始氏族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文明开化程度较低,掠夺婚便时有发生。据《松漠纪闻》载,辽末混同江附近有一小国名“嗢热”,部落杂处,各族混居,女真子弟往往依当地抢婚习俗先载妇女而归,有子后方携礼归宁。完颜希尹之子(名不详)与完颜固碖分别获得当地千户李靖的侄女与妹妹,而李靖“衣制皆如汉”,其二子“亦习进士举”[14]45-46。“嗢热”即宋太宗《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中之“乌舍”[15]10901,可知嗢热国当为渤海遗民建立,李氏家族应为渤海亡国后迁居于此的渤海族人。除此以外,金国前期的族际战争为掠夺婚提供了条件。如金灭辽时,石抹荣与其母忽土特满便为完颜希尹所获,忽土特满被纳为次室[6]1345,石抹即辽之述律氏,其母应为耶律氏;天祚帝女耶律馀里衍为完颜宗望所俘,后被金太祖赐为妻妾[6]1129;至于靖康中的赵宋宗室、宫人、百姓没入金国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多人被“分配”给金国宗室大臣为婢妾。掠夺婚甚至在帝王婚姻中也存在。金国皇后虽多出于“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6]1014,但妃嫔中不乏异族女性,其中一些人具有先被俘、后婚配的经历。如金太祖纳萧氏为妃[6]996,萧氏来历不详,当为契丹后族俘虏,金熙宗于皇统元年纳赵赛月、赵金姑为次妃,纳赵圆珠、赵串珠为夫人,次年又纳赵金奴为夫人,她们都是被俘北上的宋朝宗室女性[10]257。金国政权兴起于灭辽,大盛于征宋,战争中的异族女性俘虏便随之成为女真男性的婚配对象,而原始欲望驱动下具有掠夺性质的婚姻形式便成为金国前期女真族际婚姻的主要内容。随着战争消歇与政权文明程度的提升,掠夺婚在金国中期以后逐渐消失。
2.2 聘娶性质的女真男性族际婚姻
女真贵族男性在金国前期与渤海士族之间维持了相对稳定的通婚关系。金太祖天辅年间曾下令遴选东京士族家庭女子婚配宗室以广继嗣,东京辽阳为渤海故地,当地士族多为渤海族。辽阳李氏被选中后送入上京完颜宗辅邸,生金世宗完颜雍,追谥贞懿皇后;金世宗又纳张氏、李氏、大氏为妃。贞懿皇后与世宗妃张氏为葭莩亲,父讳雏讹只,而大姓为典型的渤海姓氏,据此可以推定她们为渤海族人[6]1008-1011。完颜宗干同样纳大氏,于天辅六年(1122)生完颜亮[6]59,又纳李氏生完颜充[6]1157,大氏和李氏来历不详,应为天辅年间被选中的渤海女性;完颜亮即位之前也曾纳大氏[6]1000,可能为其母娘家人。王室成员与渤海族之所以频繁联姻,除了因两族同为肃慎族系秣羯后裔之外,更多还因为二者在抗辽中结下的战斗情谊,正如辽太宗朝便有渤海人“亡入新罗、女直”[2]20。辽国末期又有大批渤海人叛辽附金,金太祖更是在兴兵之初就提出“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6]17。由于大兴国、李老僧等人参与完颜亮的政变[6]60,渤海族式微并逐渐淡出了金国宫廷。
汉族女性在金国中期以后成为女真男性的纳娶对象。据史料看,金国王室以非掠夺手段与汉族女性结为婚姻始于世宗朝。金世宗曾纳梁氏为昭仪[6]1011,其子完颜允恭又纳刘氏、田氏、王氏,刘氏生金宣宗,追谥昭圣皇后,田氏子完颜琮和完颜瓌善吟咏、书法、丹青、篆刻,王氏子完颜玠温厚好学[6]1365-1367,再加之四姓均不属渤海姓氏,可知四人当出自汉人士族家庭。章宗朝始,汉族女性更加频繁地婚配于金国王室。金章宗不仅纳资明夫人林氏[6]1367,欲立出身低微的李师儿为皇后,欲传位给贾氏、范氏尚未出生的孩子,还曾“诏诸王求民家子,以广继嗣”[6]1014-1017。卫绍王纳钦圣夫人袁氏[16],金宣宗即位前曾纳燕京民家女子庞氏及王氏姊妹,并立其妹为后,其姊生金哀宗,追谥明惠皇后[6]1017,另有丽妃史氏[6]1369,来历不详,这些汉族姓氏的出现正是金章宗诏令的回响。金王室与汉族女性的婚姻具有积极意义,这些女性通过延续血脉的方式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民族地位,而且使皇家血液中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基因,丰富了金国作为多民族政权的内涵。
王室成员以外,其他女真官员纳娶汉族女性的情况同样存在。太祖从弟曾孙完颜习捏娶郭氏,曾担任过义州节度副使,墓志记载其子完颜怀德“以宣宗兴定五年(1221)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秋六十”[4]3077,可知郭氏生子时为1161年,这场婚嫁发生于海陵王时期;完颜怀德又于世宗朝娶降臣郭药师之女孙,其本人一生只做过密州仓使、临淄县令这样的小官[4]3077,可知这一支宗室远亲在几代人的繁衍后早已边缘化,其与汉族官僚家庭联姻并不奇怪。同知镇戎军州事蒲鲜石鲁刺娶嘉议大夫王扩之女,王扩生前地位较显,他的其他女儿皆嫁于官僚之家[4]2925。蒲察元衡娶王氏,前者父祖皆封镇国上将军,后者为汉族世家、燕郡大族[4]2960-2961。由此可知,随着政权的封建化,政治联姻已经成为部分女真官员族际婚姻的重要考量因素。山东东路总管判官徒单喜僧娶沁州刺史李楫之女,李楫曾任山东东路劝农副使[4]2897,应该是在任期内与该路长官徒单喜僧相识而后嫁女于他,这表明两族人在同朝为官中难免接触频繁,双方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结为婚姻也是很有可能的。此外还有许多汉族女性的身份不详,如尼庞窟小汉娶蒙氏[17]158,奥屯世英娶张氏[17]175,完颜猪儿于娶尹氏[6]1877,夹谷斜烈娶殷氏[4]2962。这些女真男性大多职位不高,如尼庞窟小汉为“世宗朝护卫”,奥屯世英为“合水酒税监”,完颜猪儿“系出萧王”,其家族因参与海陵政变而被边缘化,夹谷斜烈在贞佑之乱中陷入蒙古并在那里娶妻,他们的配偶极有可能来自民间。由此可知,部分女真男性的配偶出自官僚士族,另一部分可能来自平民家庭,这些婚姻中固然不乏政治结盟和利益驱动,但同样蕴含着共处与交往中的民族互信,它们都有别于金国前期的掠夺婚,反映出中原婚俗对女真习俗的影响。
2.3 时势浮沉中的女真女性族际婚姻
金国女真女性较少嫁于外族,一方面是因为女真作为统治民族较其他民族地位要高,而女性作为被选择的一方又缺乏婚姻主导权;另一方面,金国统治者虽支持族际婚姻和民族融合,但出发点仍是女真化。就现存有限的案例看来,女真女性族际婚姻存在于海陵王时期和蒙古入侵中的金国后期。完颜亮依托外族对抗宗族,曾以奚人萧玉之子尚公主[6]1150,萧玉有功于政变,海陵赐婚无疑是出于笼络人心。区别于辽国较多地赐婚外族,金国驸马尽出本族,萧玉当属个例。石宗璧亦曾娶纥石烈氏,墓志记载他生于天庆四年(1114),任博平县尉时因镇压农民起义而获得高升[18]。博平位于山东西北部,为正隆间农民起义地区[6]72,石宗璧受海陵重用而纳娶女真贵族也不无可能。区别于辽国的迅速灭亡,金国由衰而亡经历了较长时间,从蒙古南侵直至亡国尚有二十年之久。随着宣宗南迁,金国失去了对河北、山东等地的实际控制,地方武装并起,游走于蒙古、金国乃至南宋之间。伴随土地丢失、政权动摇的还有女真民族地位的下降,一些乱世中的女真女性便成为汉族男性的婚配对象,如毕叔贤娶纳合氏[4]3101,史千世娶完颜氏[4]3569,史天泽娶纳合氏、穆延氏[19]。这些汉族男性皆为乱世豪强,有的甚至先后依附金、宋、蒙。如毕叔贤本为金国昭信校尉,于1219年随张林投靠南宋,又于1227年投降蒙古;史千世“居河津,占上籍”,金季曾组织当地百姓筑营垒、造甲兵以御侵扰,俨然地方割据头目,后于木华黎入山西时归附;史天泽于贞佑初年(1213)归降蒙古,元朝时作为开国功臣享受荣华。他们的配偶中除毕叔贤之妻被明确为“镇西军节度使思烈之女”以外,其余家世不载,当为流落北地的女真难民。贞佑之后,遭受战乱的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女真人不仅生计艰难,而且还因部分汉族人“睚眦种人”而面临生命危险[4]3077,因此部分女真女性嫁给汉族男性以求自保便可以理解。综上所述,女真女性的族际婚姻反映了民族地位浮沉,是金国政治与国运的表征。
3 契丹、女真以外的族际婚姻
契丹、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与汉族的通婚同样是辽金族际婚姻的组成部分。在婚姻政策方面,辽金统治者都不曾干预过本民族以外的族际婚姻;在风俗文化方面,部分民族间可能因历史上的接触与交流而习俗相近、相性较高;在地域环境方面,少数民族原本多为族内聚居,但国家政策、族际战争等因素往往使他们迁出故地而与外族混居,这就为族际交往创造了机会。
3.1 奚族族际婚姻
奚汉通婚发生较早,唐玄宗时奚族强盛、时反时附,统治者曾于开元、天宝年间施行和亲政策,如开元五年(717)嫁固安县主于李大酺,开元十四年(726)嫁东光公主于李鲁苏,天宝四年(745)嫁宜芳公主于李延宠[20],此后随奚族衰弱而终止。附辽以后,奚贵族被附于述律氏萧姓,不仅与契丹王族通婚,与契丹化的汉族韩氏间也有政治联姻,如韩德颙之女“适奚王府相之息”[21],韩雱金之女“适奚太师为夫人”[3]69。区别于奚族上层的频繁通婚,奚族民间多为族内婚。苏辙使辽时曾亲历中京地区的奚王府领地,称奚人崇尚暴力而不遵礼法,虽“遗民杂汉编”却“婚姻未许连”[22],可见辽国奚人虽与汉族混居,但民风习俗迥异,并且奚王可能也禁止通婚。当然,奚汉民间婚姻也仍有存在的空间,《黑山崇善碑题名》中归属“孔寨”的“孙奚婆”可能为汉族女性嫁给奚人后的称呼,归属“城子”的“刘公林、姐姐奚婆”则表明刘公林的姐姐嫁给奚人为妇[4]893-896。崇善碑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距奚王府所在的中京(现赤峰市)有一定距离,不排除部分流散在外的奚人因超出奚王管辖范围而不受其婚姻政策限制。除此以外,碑文中人名混杂而汉族姓氏占绝大多数,可见崇善碑所在地为当时汉族人口为主的民族混居地,处于绝对少数的奚人接受优势文化影响并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组建家庭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辽国灭亡以后,奚族降民被编为九猛安,“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6]657,世宗时部分奚族猛安谋克随斡罕起义失败,参与叛乱的奚族男性被杀,“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6]84,其余奚人被再次拆散迁徙至咸平、临潢、泰州等地务农[6]693。至此奚人被彻底打散,逐渐融合进女真和汉族,失去了自身作为民族实体的地位。
3.2 渤海族族际婚姻
渤海族汉化时间较早,汉化程度最高。大祚荣在回靺鞨故地建国前曾与营州的汉族人一同生活多年[23]4695,建国后又积极接受中原文化,被视为“与华夏同风者”[24]。除大姓之外,渤海姓与汉姓高度重合,不出“高、张、杨、窦、乌、李”,“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1]247,这就在客观上使得渤海人的民族身份不易区分。由于诸多相似,辽金政权常将渤海人与汉人归为一类来管理。辽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2]574,金国则“专置检法官二员,一员检断女直契丹等,一员检断汉儿渤海等”[25]。金熙宗诏令“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勃海同汉人”[6]47,金世宗诏令“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6]94,金章宗诏令“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6]682,这些举措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渤海人的民族身份认知。渤海人在辽国有过两次大范围迁徙:契丹灭渤海置东丹国,辽太宗于天显三年(928年)迁东丹民以实辽阳[2]20;太平十年(1030)大延琳起义失败,辽阳的渤海人进一步被迁徙至来、隰、迁、润等州[2]144。迁出辽东的渤海人多与汉人杂处,如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与汉民杂居,户四千”;定霸县“本抚余府强师县民”,“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散居京南”;潞县“本幽州潞县民”,“与渤海人杂处”;镇、防、维三州分居“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2]300-308。此外亦有汉族人迁入辽东与渤海人杂居,据《贾师训墓志铭》所载:“辽东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迄今数世无患。”[4]557墓主死于寿昌二年(1096),距渤海亡国已有170年,可见这一过程漫长而持续。金初渤海人被编为八猛安,皇统五年(1145)罢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6]654,至此渤海人进一步融入民间,与汉族百姓无异。文化趋同与杂居生活让渤海与汉族的通婚不会有太多障碍:高唐英之子高嵩“其先渤海郡人”,先娶“都承郦公之女”,后娶“曹州太保之女”石氏,其子高元又娶“天水赵公之第三女”[3]37-38;高为裘“娶天水阎氏、太原孙氏”,其祖先为“渤海国扶余府鱼谷县乌悊里人”[4]861-862,其子高泽又“娶彭城刘氏”,泽之女“适左班殿直、平昌孟三温”,高泽之子高永年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平昌孟湘”和“陇西李仲颙”[4]863。程延超为武吕郡人,其女嫁给“渤海郡高守凝提举”[4]850;进士毛端卿先娶同郡秦氏,后娶西京路转运使之女辽阳高氏[4]3200,进士史邦直也是初娶某氏,后娶某官之女辽东高氏[4]2989,他们的第二次婚姻皆为续娶,与渤海族一夫一妻的婚俗相符。
3.3 白霫族族际婚姻
与渤海族同样较早受到中原文明影响的还有白霫族。白霫原为铁勒十五部之一,属匈奴别种[26]3635,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该族于贞观年间归附唐朝,统治者列其地为寘颜州、居延州,并任命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23]4671。到了辽国时期,白霫人已经基本接受了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北宋使辽官员苏颂曾亲历白霫之地并留有诗篇:“拥传经过白霫东,依稀村落有乡风。食饴宛类吹箫市,逆旅时逢炀灶翁。渐使黔黎安畎亩,方知雨露徧华戎。朝廷涵养恩多少,岁岁轺车万里通。”[10]86当地村店旅社热闹,百姓以耕种为业,使用灶台生火,情景与中原无异。考虑到白霫与汉族混居的情况可能存在,那么两者之间的通婚就不可避免。随着部分白霫人在金国为官,他们也开始逐步融入汉族士人的交际圈。如白霫惠和人赵愿恭与白霫长兴人赵松石都与金国文人蔡松年有所交游,前者以科举入仕,后者则以幕僚起家[27]。元好问称金国官员中不乏“潢霫之人以门阀见推者”[4]2884,“潢水”为白霫三部之一[23]4671,可见当时部分白霫家族因多人为官已成为名门显贵。白霫家族从地方富户变为世家大族的起势途径当为科举,这从侧面说明白霫在与汉族的相处中已逐步形成崇儒兴教的风气。由于史料缺乏,现存白霫族际婚姻案例很少,但其中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辽国“白霫北原人”郑惟熙曾娶“渤海申相公女”,申姓不属渤海姓氏,当为后迁入的汉族人,其子郑恪又娶李氏[4]522-523。郑恪表弟梁援曾任户部使,与《梁援墓志》墓主当为一人,其母“郑氏”当为白霫人郑惟熙之姐妹,嫁于梁援之父宥州刺史梁仲方[4]542。郑恪之曾祖曾为官,其本人敏达博学,名列三甲,其姑适官宦之家,其子“皆隶进士业”,其碑铭则为“白霫布衣刘航字利川书”,可见白霫家族在辽国已与汉族频繁通婚,重教之风业已形成。历仕辽金的赵兴祥也应该有白霫血统,他曾在辽末“省亲于白霫”,在金熙宗朝以孝行闻名并获得“护视太子”的殊荣[6]1344-1345。综上所述,白霫与汉族的族际婚姻有着文化、价值认同的坚实基础,而相关案例载之甚少,很可能是由于辽金时期的许多白霫人与汉族人已难以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正表明民族间的高度融合。
3.4 回鹘族际婚姻
迁徙是回鹘族际婚姻的主要驱动因素。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于开成末年(840)灭亡,回鹘人四散迁徙,其中一部分随乌介可汗等人南迁至中国北部,并逐渐融入当地。会昌初年(841),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那颉军,歼灭、受降近九万人;会昌二年冬、三年春,特勤庞俱遮等七部三万众降于幽州并被发配诸道,另有特勤嗢没斯等五部降振武军;大中元年(847),乌介可汗部诣幽州降[26]3548。这些回鹘人在进入幽燕地区后有可能与当地人通婚。“大燕景城县人”陈万历仕后唐和辽,其面貌“虬发鹤颔,猿臂虎形”[4]37,上谷人耿崇美是辽初重臣,其“姿貌魁梧,面紫黑,蚪髭,赫怒之时,鬓毛如猬”[4]160,他们的相貌与汉族及东北土著民族差异明显,可能为汉人与回鹘人的后代。除南迁以外,另有贵族庞特勒带领十五部回鹘人西迁至今新疆、甘肃一带,并在当地先后建立民族政权[23]4664。宋大中祥符至天圣年间,甘州回鹘在西夏进攻下瓦解[15]10805-10807,这一时期有“卷发深目、浓眉虬髯”的回鹘人“入居秦川为熟户”,其民风开放,“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14]44-45。天会八年(1130)女真攻入陕西,次年初“泾原、熙河两路皆平”[6]41,部分回鹘人被迁往东北,金国后期官员马庆祥很可能为他们的后代。马庆祥本名习里吉斯,为“花门贵种”,族人曾“居临洮之狄道”,于“金兵略地陕右”时“尽室迁辽东”,随后被赦免遣散至净州天山占籍。天山因“近接边堡”而为“互市所在”,马氏家族凭耕种、畜牧成为富户,与周边汉族人多有接触,马庆祥的女婿杨氏便很可能为族际交往中结识的汉族人。除此以外,马氏族人重视教育:马庆祥通六国语言,泰和间以科举入仕,元光二年(1223)被俘后不屈殉国,当有祖辈教导之功;本人不仅“严于教子,动有成法,必使知远大者”,而且还承担丧父之甥的教育,“躬自教督,逾于所生”以为“它日起家之地”[4]3051-3053。由此可知,金国时期的部分回鹘人不仅摈弃了原有的婚姻陋俗,而且开始积极接受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族际婚姻的有力支撑。
4 结语
辽金族际婚姻的内容丰富,不仅参与民族众多,而且涉及阶层较广。这种局面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背景:一方面,统治者主导的移民与各族人民的自发性迁徙使得辽金地区的人口流动较为频繁,不同民族相遇、相处乃至交流、交往的几率有所提升,这种情况与相对宽松的婚姻政策一并成为有利于族际婚姻的外部客观条件;另一方面,统治阶层的征服与欲望、官宦士族的利益与结盟、习俗文化的接受与适应等因素作为内在主观条件同样为族际婚姻的发生提供了有力驱动。族际婚姻意味着族际共同体的生成,其不仅能够以血脉融合的方式固化民族融合的成果,而且能够影响当事双方的亲属、朋友、后代,在塑造民族个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着极强的辐射作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8],族际婚姻不仅为自在阶段的中华民族提供了有力注脚,而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与形成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