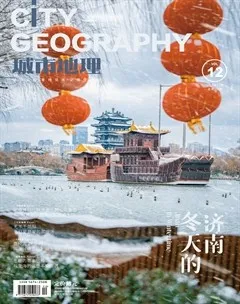大连往事:达里尼的深冬
谢谨言


穿过一条幽长的隧道,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打开车窗,外边的冷空气卷进了车里,如绒毛般轻盈的雪花落到了我的鼻尖,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
大连的冬天比起哈尔滨稍显温和,但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仍然十分寒冷。从学校出发,来到海边,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风呼啦呼啦地吹着,与南来的海风撞在一起,视线里到处都是玉屑纷飞狂舞,海面笼罩在茫茫的雪雾之中,眼前一片朦胧。人也困在这风雪之中,就这般等待黄昏的降临。
天渐渐暗去,夜空如眼前的玄色深海。正对着渤海,可以看到朦朦胧胧的跨海大橋,回头是高楼耸立的高新区。大厦上的灯光耀眼地闪烁着,散发着灯红酒绿的都市之气。但这场雪却让那些象征着金钱财富的大厦变得黯淡无光。在20 世纪90 年代,大连曾经被誉为“北方小香港”。市中心青泥洼桥聚集了许多外资企业,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整个城市开始陷入停滞。
从海边走回学校附近,人流量越来越稀少,周围的景象愈加灰暗,从汽车声中逃离,从广告霓虹灯下逃离,远离夹道堆满了积雪的道路,时间好像真的能暂停。直到走入幽深的小巷子里,看到空荡的小路边几处老房子亮着的灯,身上浓厚的都市气息才得以清除,重新回归到接地气的世俗里。环望四周,上世纪90 年代时这里是什么样子,现在好像就是什么样子。
至今仍然忘不了第一次来到大连时,热情好客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说,大连其实叫做“达里尼”,是俄国人起的名字,蕴含了“遥远的东方”的意思。起初我很诧异,这个极具有异域风情的名字是怎么变成“大连”的?后来,大学的第一堂课上,老师说起了大连的城市背景——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接管了达里尼。可是达里尼这个名字对日本人来说十分拗口,他们便把这里改称“大连”。
渐渐适应北方生活后,我对大连城市基础建设的了解也在一点点加深。1898 年,沙俄强占大连地区,在这里开辟新港,希望打造一个能够辐射东北亚的港口城市。在城市建设之初,沙俄提出了两个城市道路建设的设计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棋盘式”道路结构,第二种方案是“放射式”道路结构。最终,第二种方案得到了批准。由此,大连成为了极少数拥有欧洲古典主义城市建设风格的城市。
作为地标性建筑的尼古拉耶夫广场,就是今天的中山广场,这里是大连放射式道路的中心,也是大连城市建设的起点。中山广场向四周辐射出了十条主干道路,犹如一颗镶嵌在城市中心的明珠。最重要的官方公署、银行、各国领事馆就坐落在广场周边。道路的沥青下雨下雪都不会脏,沙俄统治时期从南俄罗斯运来的槐树和白杨树,如今也依旧分布于道路两侧。
在最辉煌的时候,“大连”这个名字可算是新颖别致,让每一个想要度蜜月的夫妻们心生向往。后来的这二十多年里,它渐渐成了一座普通海滨城市的名字,心向北上广的人们不会过多青睐。近几年,当地的年轻人心中有了一种难言的不安,在这种不安中,他们发现了大连的魅力和虚无:大连的魅力,是蓝天白云,是太阳在梦幻的夕霭中微微泛黄的样子,是落潮后广阔的沙滩以及鸣鹤鼻礁石;大连的虚无,在于每一个在这里出生的年轻人都知道,他们的使命就是离开这片土地。这种虚无,反过来又激发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留恋与执拗,想要做点什么来抖落这二十多年来的陈旧。于是,大连的虚无在年轻人的心中又酿成了一种即兴又强烈的复杂情愫。
每次离开大连,都不得不路过学校后门那条灰扑扑的巷子。巷子两旁,无论是彩色瓦屋顶、土黄色的墙壁,还是挂在门口闪着耀眼光彩的广告牌,都在日晒雨淋下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如果用口感来形容,就像是用俄罗斯裸麦做成的黢黑面包——每次走到这里时我都会这么想。失去了生气建筑的左右两侧,又盖着两三层高的杂居小屋,颜色灰暗。冬天时银杏树已经光秃秃的,盛满了积雪的树冠耷拉下来,擦过杂居小屋的房顶,宛如一柄沾满了白色颜料的巨大扫帚。即使离开大连时是绿树猗猗的夏天,可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还是下着大雪、眼前一片朦胧的深冬。
坦白来说,在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我认识到自己已把这里当作另一处故乡。四年的生活,令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做执着于土地。从遥远的西南来到这里,不过住了四个年头而已,但我见过了春天早早挂上花朵的榛树、夏天溶溶荡荡的大海、秋天白露满地的清晨、冬天雪后如玉的晴天。如今,这片土地似乎已成为我生命的土壤,居其间则心安,离开时则痛苦。
推己及人,身边那些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连的人,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可见一斑。失去了自己故乡的人,总想要重建一个故乡,东北饺子馆、大连海鲜烧烤等餐饮店在南方遍地开花,似乎就是最真实的写照。然而,将自己禁锢在舒适圈和回忆里是人的弱点。执着通常是一种力量,但执着也意味着终止。执着地把家乡的特色复制粘贴在另外一个城市,看起来可以找到寄托,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仍然会忍不住去怀念远在千里的那片海、那场大雪。
倘若离开大连,究竟是该留在新的城市,还是在功成名就后搬回故乡?至今,我仍然无法站在大连本地人的角度解答这个问题。
编辑+ 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