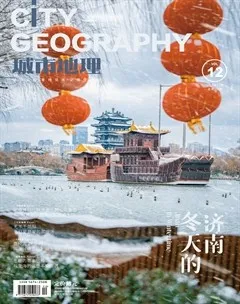著名小说家刘汀:在城的海啸里驶向彼岸

刘汀
小说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
对话刘汀
1. 刘汀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是内蒙古赤峰人,后来定居北京,在这样的变迁中,您是否有产生心态或者生活上的变化呢?
变化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这种变化不管是心态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成熟。这个成熟不是指生理意义上的成熟,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在老家乡村的那段时间,我正处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时我对于文学和生活的理解认知,也依然是相对幼稚的心态。但是自从我来到北京,从读书到毕业后在这儿工作、定居,已经有20 年,在这个过程中,我进行了一个自我的成熟。
我理解到我个人在群体中处在什么位置,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我所处的群体在整个中国的语境里,又处在什么位置,有什么样的特点;甚至再大一点,我们的民族、国家的文学或者文化,在整个世界无论是纵向的历史上还是横向的比较上,它应该有一个什么位置;再到更大一点,就是对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而言,它在宇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这是一个不断递进、不断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从乡下到城里生活之后,城市给予我的心态和生活上的核心的变化,就是让我不断地抛开原来的认识,不断地走向成熟。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远远没有结束的,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永远走在成熟过程中的变化。
2. 在北京接触文化圈数十载,您认为北京的文化氛围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具体是怎样的?
我觉得北京的文化氛围在我生活的二十年来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它依然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充满可能性的,甚至具有相当的平等性的文化空间。
基于北京的文化氛圍,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很多文人来了不愿意离开的地方,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需要太严苛或太充分的条件,就能够支撑无数文艺青年前来追梦,他们可能在某个网站当一个特别苦的小编辑,但是同时,他们也能够去完成自己那些有关文学的,甚至是艺术的、音乐的、绘画的理想。因为北京拥有最多的文化单位,最多的出版社,最多的网络空间,这些土壤在不断地滋养着所有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所以北京的文化形态,可能永远都达不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但它永远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实现理想的怀抱。
3. 每个作家都有一个精神原乡,请问您的精神原乡在哪里呢?
我想精神原乡并不局限在时间这个层面上,所以我的精神原乡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我的故乡。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对于我来说,具有一种地基性、基础性的建构作用。小时候在北方的乡村,我看到春天时人们栽种下庄稼,夏天它旺盛生长,秋天收获,到了冬天人们把它磨成米、面,做成食物吃下去,然后第二年春天又重复这个过程。在这样四季轮换播种收获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这个世界或许并不是人们口中“今天一定比昨天发展得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这样进化论式的方式存在。
另一个精神原乡是我阅读过的所有书籍,它们为我建构的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记得我读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时,是在大学一年级,我感觉到它特别吸引我,虽然我当时完全不理解它为什么好,但这个东西扎根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是何种刺激或者何种影响,浇灌了它、滋养了它、让它开花结果。当我到30 岁的时候,再重新去读这首诗,忽然发现我理解了它,这个理解可能只是我个人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成为了我精神层面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让我在之后很多人生的关键时刻,通过这首诗或者其他的作品来理解我的生活,理解自身。所以我觉得,精神原乡的意义可以生发成:我们借由这样一个精神储备,来面对我们后来的生活,后来的人生,后来的世界。
4. 您出版的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包含四个中篇小说,每一篇都写了一个跨越城市与乡村的当代女性,她们拥有不同的年龄和身份,在城乡之间漂泊奋斗。请问您创作这本小说集的初心是什么?
我最初的计划就是写以“梅兰竹菊”来命名的四个女性的故事,“梅兰竹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着特别高雅的气质,但这四种植物又各有它的含义,所以我的初心之一是想借用这个含义,来描述当代女性的不同气质和精神面貌;第二就是我写作的野心,想通过这四位女性,把当下这个时代最活跃的几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群体,做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呈现。
我选取的都是从乡村到城市,或者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漂泊、努力寻找生存空间的人物。因为这一类女性是我最为熟悉,也最为了解的,也是我最想去表现她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女性群体。
她们其实都有一定的原型,这个原型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群人。比如《人人都爱尹雪梅》里,主人公尹雪梅的原型就是我的母亲,在我的母亲来到城里带小孩的那两年,我发现还有许多和她生活环境相似的带娃的姥姥、奶奶,但在当代文学上,很少有专门表现这个群体形象的作品。
我的母亲是一个乡村的妇女,她到城里后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城市化,虽然她的自我在乡村社会里被封闭、被束缚,但在这个新的生长空间里,她依然顽强地向外面探出她的枝,去开她的花,去释放能量,义无反顾地展现生命里最具有活力的那一部分,尽管这个空间又短暂又狭窄。
5. 在您的文学作品中,城市生活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是不利于城市生活的。我是乡村长大的小孩,哪怕已经转为了城市户口,城市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既在又不在的地方。这是一种我们生活在这里,但我们的生活的根又似乎不在这里的状态,所以城市是我所有作品的故事发生地之一,但是它同时又像是一处海市蜃楼,我能看见它,但我并不身在其中,它是现实,但又是超现实。它的现实性在于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里,衣食住行都和城市发生关联,超现实性在于它不断地变化,哪怕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会偶然地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感到陌生,因为总有某个角落是我们无法触及的,所以它又永远具有一个超现实性的影响。
我特别愿意把我在小说里的城市描述成在汪洋大海中栖身的一艘船,我只是借由这艘船,抵达一个连我自己也并不清楚的彼岸。现在我们在大海中央,只能通过这艘船,也就是通过城市生活去面对一切暴风骤雨,面对一切浪花海啸,而最终抵达的彼岸是什么样的,无人知晓。
6. 在您看来,人的生活环境如何影响人的情感和思想?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生活环境对于我们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等思维方式都是有影响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是基础性的,它可能会发生调整,甚至发生变化,但是它的根本很难动摇。
现在回溯起来,在乡下生活时,我得到了一个“所见即所得”的认知,就是我们看见的庄稼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看见有几头牛走在街上,就是几头牛走在街上,他们不包含任何抒情,不包含任何隐喻,他们就是这个事物本身,任何乡村的事在最基本的伦理里面都是这样的,事物就是他们本身。这个道理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具有非常深刻的哲理性,我们有时候会被各种各样的附加的东西影响,但如果回到事物的本身去看待它,很多复杂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同时,城市生活也对我有很多思维方式上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开放的视野,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封闭的、安静的、田园的、保守的环境,它有一种自主性,但是城市生活更多的是流动性、变迁性以及宏观性。生活在城市,人们会意识到一切都是转瞬就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不会再期待永恒,不会再向往过于崇高或者过于宏大的东西,反而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些变化。
7.写小说需要有细腻的对生活的感知,但同时也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来建构虚拟的世界,请问您是怎样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我可以将写作者定义为对万事万物都过敏的人,并且不只是敏感,是过敏,对万事万物要有生理性的反应。就像我们碰到了一件过敏的东西或吃了过敏的食物,身体会起疹子,会发烧,甚至有的人会窒息,会死亡一样,作家是在精神上对万事万物过敏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是不需要主动去触碰它的,只要是经过它,精神就会有所提示,这件事情、这个人或者这个物品,很可能是具有文学意义的,这就是对生活的细腻感知。
想象力当然也是作为写作者最重要的能力。当我们看到了一则新闻,或者是在春天看到一朵花,我们会去感慨花的美丽,春天的美好,但是诗人或者作家,会用文学性的、艺术性的方式去留住转瞬即逝的花,尽管你也可以用照片去留住,但是它们永远只是表象,而不是我们看到它那一瞬的感觉。我觉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这样一个功能,我们为了装饰或者留住这朵花给我们的感受,需要给它一个花盆,有了花盆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建造一个空间,一个摆花的桌子,有了这个桌子,你再去看这朵花它依然是不够完善的,还需要给它搭建一栋房子,但是花在这栋房子里面同样是很孤单的,我们需要这个房子里有人走动、有生活气息,这样一点点往外延展,就是我们为了一朵花去建构了一个世界。
我觉得在文学作品里,现实和虚构的关系就如同花和世界,现实可能只是那朵转瞬即逝的花,而虚构就是要为这朵花建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甚至适合它死亡的世界。这个建造的世界的每一部分都需要真材实料,但这个世界本身又是虚构的。
8. 作为《人民文学》的副编审,您认为当代文学刊物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文学刊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特别火,书本,甚至好多刊物的发行量都达到了几百万册的状态,在那个时代,我们除了独自地呐喊之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尤其是刊物,还有一定量的书籍来表达情绪。当然,这是文学发展乃至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当时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的主要表达方式,因此非常兴盛。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媒体,甚至是全媒体、融媒体的时代,有无数种方式可以去表达情绪和意见,如朋友圈、拍视频、写段子等等。
但是刊物的发行并不是从此失去了意义。首先,我认为现在的文学刊物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守住文学性的底线。现在的所有媒介传播讲求的是传播性,看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转化成广告、转化成利润。文学刊物虽然发行量不大,它却帮我们守住了文学性的底线,最有质量的底线。
其次,它能够真正地帮助文学界甚至艺术界发现有潜质的新人。最后,我觉得刊物发行到现在依然很强大的作用,就是在文学传播中充当了文学鉴别师,在挑选作品,帮助文学作品经典化。我们可以看到畅销书排行榜上每年都有新书,但是这些书可能一两年后就没有人再想起,因为有新的书把它代替了。不过,有一部分被淘洗過的文学经典作品,可能每年销量并没有特别多,却永远有最富有智慧的大脑在阅读它。所以文学刊物在披沙拣金的过程中,可能就扮演了文学鉴别师这样一个角色。
编辑+ 冯艺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