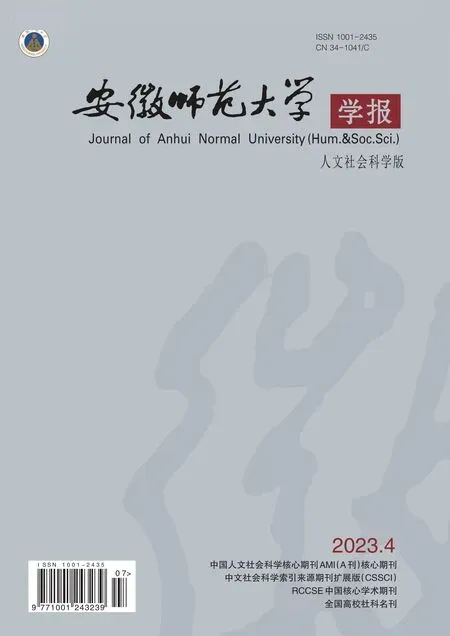“网红脸”的消费形式及其资本逻辑*
康 洁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一、“网红脸”现象的探讨与问题
“网红”(Online Celebrities)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网红”是指因借助网络传播而流行起来的受大众广泛关注的一切知名人士。狭义上的“网红”专指通过网络直播而出名的具有媒体消费价值的流量明星。根据网络技术升级换代的命名方式,“网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文字时代、图文时代、宽频时代。①沈霄、王国华、杨腾飞、钟声扬:《我国网红现象的发展历程、特征分析与治理对策》,《情报杂志》2016年第11期。在当前网络传播的宽频时代,“网红”传播的内容随着网络技术的提升,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正如杨国庆、陈敬良在《网络红人形象传播及其符号互动模式研究》一文中提出:“按时间顺序可将‘网红’传播内容分为文字、图片、视频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当前‘网红’的传播内容从个性化走向符号多元化。”②杨庆国、陈敬良:《网络红人形象传播及其符号互动模式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7期。许祥云、张茜从网络经济与文化的视角认为,“‘网红’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与消费文化现象,‘网红’的超强变现能力使得各类资本竞相追逐,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之下,‘网红’已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化链条”。③许祥云、张茜:《“网红”的发展逻辑及其负面效应的规避》,《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网红”背后的产业链是支撑他们持续走红的经济原因。从传统平面媒体的读者群到互联网时代的网民,表明了媒介方式、阅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符号互动方式的转变。本文所论及的“网红”与“网红脸”是指狭义层面的。
在“网红脸”的研究方面,吴斯以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为研究框架、以网红脸的流行为具体研究对象,从物质身体、文化身体和技术身体三个方面对网红脸的诞生及流行过程进行分析。④吴斯:《分裂与聚合: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身体研究——基于“网红脸”流行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杨一丹从全球化消费与身体政治的视角探讨“网红脸”的审美幻象,认为“网红脸”本质上是一种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范围的身体政治问题,而要改变人在日常美学实践中的异化问题,需要“以‘共同遭遇’为基础的无国界团结和良性互动,也许才是突破全球资本和右翼保守主义危险合谋的必由之路”。⑤杨一丹:《“人体炸弹”和“网红脸”——“去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体政治》,《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2期。文章还指出,人体炸弹与“网红脸”,尽管毫不相干,但从宏观背景上看,都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垄断资本运行模式下身体政治的产物。这种观点深刻反思了当代资本全球化运作所带来的身体政治的隐忧。
女权主义者同样介入了“网红脸”的研究,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把“网红脸”现象看作是纯粹的以男性为审美价值取向的身体消费行为,并借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业文化批判的立场,认为身体消费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陷阱。消费者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单向度的人”,“她们的身体被塑造为物化的身体,因此消费文化不具有社会正当性,甚至不具备合法性,是一种畸形的病态文化,应该加以价值疏导与社会控制”。⑥王蕾蕾:《论女性审美文化的社会控制》,《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3年第4期。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那些“被不少研究者诟病的都市消费文化及网络空间进一步物化了女性身体的现象,恰好是女性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代特征,女性的身体生命活动正成为一种更具主体性的审美活动或艺术表演”。⑦林树明:《大众消费文化与女性审美体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显然这种观点认为“网红脸”的身体消费,是女性的性别独立与审美主体性的明证,是反男权主义的女性集体无意识。这种观点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本雅明的观点,在工业文化消费时代中,消费者不完全是被动接受的,而是具有审美主体性的创造性个体。正如汪民安所指出的,“本雅明将马克思主义的重心置放到形象上面。工业经济与消费文化彼此埋藏在各自的形象中,经济就是借助于这样的文化现象得以表达的,它们并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区域”。⑧汪民安:《感官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网红脸”的身体消费既是经济现象又是文化现象,彼此相互生产与再生产。
随着韩剧热、化妆整形技术与各种电视选秀节目的兴起,大众流行文化逐渐出现一种消费“男色”的现象。原来父权制下单一的男性对女性的“观看”逐渐被男女双方相互“观看”的互动与双向模式所取代。尤其是在粉丝经济与流量经济的驱动下,“网红脸”的身体消费同样存在女性对男性的审美与判断。如今,从女性审美的觉醒时代到审美价值标准的多元化时代变迁中,不难察觉当代性别文化正在对女性审美价值标准实施重建。因此,“引导和树立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审美价值观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基础”。⑨曲凯音:《百年中国女性审美价值标准变迁的文化评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综上,本文拟从“网红脸”的消费形式出发,探讨网络流行文化中的“网红脸”的审美机制及其资本逻辑,反思当代青年时代脸谱的身体哲学意蕴,并提出无差别的“身体性”(corporeality)及其生命归旨对于日常审美活动的核心价值作用。
二、“网红脸”的消费形式
在信息技术化的生活美学时代,脸面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身份识别,其实体性、差异性在不断减弱,而它的虚拟性与同质性在增强。在身体消费观念的驱动下,脸面的颜值越来越受到青睐,它既是化妆整形技术追逐的对象,又是视像合成技术的产品。“网红脸”的消费形式主要表现为技术消费与身体消费。
(一)“网红脸”的技术消费
“网红脸”的技术消费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医疗整形的物理技术,虽然它与化妆有关,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化妆,而是通过诸如修眉、割眼皮、隆鼻、注射玻尿酸等使脸面发生美学意义上的更改。二是基于图像修整的身体视像化技术,脸面被电子技术二次处理,被各种美图软件所修改,并成为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交流与互动的符号。前者是技术对物质身体的改造,后者则是对图像身体的加工与修饰。这两种技术形式使“网红脸”成为当代社会脸谱体系中重要的“类型脸”,引领身体美学的时尚与潮流。
从社会审美舆论上看,同质性与符号化引发了人们对于“网红脸”缺乏个性、审美疲劳的诟病。一方面它并不被认为是审美主流,但另一方面从女性整容实践来看,脸面整容的聚类分析直接指向了“网红脸”。可见,“网红脸”并非盲从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其背后的美学观念仍有其科学理论与审美历史的基础。比如在欧洲,“十九世纪的男性人体外形被重构,挺腹缩肩的贵族气派被颠覆,而是流行起了‘布尔乔亚’式的挺胸收腹。女人的外形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即出现了追求‘挺胸、直背、收腹’外形美的新观念。”①[法]乔治·维加莱洛著,关虹译:《人体美丽史:文艺复兴——二十世纪》,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在玻尿酸技术没有出现之前,有的形体学家发明了一种脸部操,即借助“塔夫绸黏结剂”黏住的导线能调动脸的不同部位。这些部位接着被拉长,以迫使皮肤和肌肉变成所希望的状态。19世纪中叶以来,化妆品的研发及其工业生产开始大量出现,化妆的材料与工具层出不穷。日常化妆事务的新颖之处尤其在于改变了傅粉施朱的方式,“化妆不仅修正某种缺陷,还使人变得更加妩媚动人,更具有诱惑力。它甚至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迫使人人‘自己塑造自己’”。②[法]乔治·维加莱洛著,关虹译:《人体美丽史: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第140页。20 世纪初整形外科开始出现,这种尚不明确的外科分支试图医治丑陋和畸形。“但它昭示着一个行业,创造出一个词语‘美容护理’和一种商业范式——‘美容院’:为‘诊疗’设计的会客厅,在那里进行的一些‘矫正身体和脸部缺陷的治疗’”。③[法]乔治·维加莱洛著,关虹译:《人体美丽史: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第185页。这些化妆与整容的历史实践表明,对于脸部的护理与美化,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成为商业的运作领域。当代流行起来的“网红脸”,正是历史上的整形技术更新与美学观念演化的产物。当代流行起来“网红脸”最初是针对女性而言的,带有男性主义审美心态的性别美学观念,后来延伸到了男性整形美容的日常事务,以及跨性别之间的集体偏好。“网红脸”的性别固化观念开始淡化。从直播打赏、广告宣传、色情服务等领域来看,“网红脸”的市场寻租空间很大。在“网红脸”的身体技术市场,商家往往把脸面分部位进行“销售”,比如下巴、眼皮、鼻梁、眼睛、嘴唇、眉毛等,这些部位进入了当代美容院的整形外科手术的操作目录,并明码标价。“网红脸”的整形目标在于它的一种类型化、高颜值的参数标准,比如下巴的尖度,鼻梁的高度、嘴唇的厚度、眉毛的齐整度与对称性等。
通常情况下,“网红脸”在物质身体的基础上,经过美图技术与视像技术的再次修改,变成一种虚拟化的脸谱形象。基于医学生理学意义的身体并不是身体所谓的本真性的存在方式,尽管我们对它习以为常,但它仅仅是身体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网络的虚拟交流的基础也正是以‘虚拟身体’为特征的新的‘感觉’形式。”④姜宇辉:《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网红脸”的身体美学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助推因素:一是文化观念的渲染,二是身体技术的运用。即通过身体技术的教化使网民产生审美观念的趋同,而且,网络围观与视频直播可以使“网红脸”在互联网经济中获利与变现,促成了基于身体技术的网络新业态。“人的身体通过与一个电脑终端的联结而完全突破了自身的‘事实’层次的身体结构,在虚拟的世界层次,身体可以被随意地组织、想象。”①姜宇辉:《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第197页。“网红脸”成为当代青年偏好的时代脸谱,正是依靠审美观念的普及、身体技术的开发与网络推手的平台建设等综合性因素得以最终确立。这可概括为“观念先行+技术跟进+商业操作”的模式。即,首先通过关于脸面的科学化的美学观念,再辅助化妆、整形与修图等一系列的身体技术,最后形成一整套关于“网红脸”的商业运作模式。由此,“网红脸”从身体技术领域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微观经济学领域,转化为身体政治的表现领域。随着微电子学技术的兴起,“网红”拥有了更多的赋权与增殖空间,进而通过身体的电子技术的改观,出现了所谓“后人类”“新新人类”“合成人”等虚拟的身体。
(二)“网红脸”的身体消费
在信息技术的不同阶段,从图文时代的平面修图技术,到宽频时代的视像合成技术,“网红”们追求的主要不是现象学式的身体体验,而是技术性身体的诱惑价值,使身体成为市场营销的手段。“网红”试图以“网红脸”的审美效果来营销自己,进而设法使自身的脸面形象接近为大众审美所欢迎的“高级脸”的结果。“网红”关心的并非仅仅是“网红脸”的个体审美体验,更多的是网民的世俗眼光,即通过使用身体技术来迎合受众的审美心态以求达到市场营销的目的。“网红脸”体现了一种关于个体性与统一性的辩证法:一方面在专业的形象设计安排下,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网络推手尽可能把被助推的“网红”脸面改造成具有市场价值的个性化脸型;另一方面,整形产业以“韩流”为代表的美容文化为价值参照,造成了整形之后的脸面被指责为身体消费的产物,缺乏个体性特色与主体性的深度。尽管有些女权主义者声称,“网红脸”是实现个体审美体验、突破父权制的刻板脸谱形象的个性化形式,但同时又陷入了商业体制的符码化的生产程序。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那样,“在消费社会,生产是相互区别的,但是根据某些普遍范例及它们的编码,消费者就是在寻找自我独特性行为中的相互类同了”。②[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归根结底,网络消费体制之中“意义”的生产总是以一种“差异”的面貌出现的,“这种消费‘意义’自身的生产逻辑恰恰是从‘差异’出发而以‘统一性’终结”。③姜宇辉:《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第194页。
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剧与港剧通过银幕形象参与了时代脸谱的美学设计,在新世纪之后,韩剧参与了消费时代的脸谱形态学的指导性实践,它们通过影星创造脸谱美学的专有名词,并推广为化妆整形时尚的模板。总体而言,这是一种从“父权制度”到“影星制度”的脸谱美学的变迁。大多数传统女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身体观念纳入父权制的审美体系之中。但如今,化妆整形技术不仅让她们获得了生活美学上的满足,而且取得了审美心态上的愈疗效果,试图从技术论领域进入到生存美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脸面形象产生了,这种脸面使广大女性从父权制的脸谱形态学的僵化教条中解放出来,进入一种被推广者所宣称的自信、阳光、自由、时尚的身体形象之中。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在人体美丽观念上引领潮流,并制定了《海斯法》,“这部法律的制定者声称想控制美国的影像业,避免可能出现的不良行为,遂发明了‘大腿艺术’一词”。④[法]乔治·维加莱洛著,关虹译:《人体美丽史: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第221页。在20世纪末,韩国电影将人体美丽观念聚焦在脸部,进而导致了美容产业与电影工业的双重受益。
临行之前,阿东坐在床边跟阿里谈话。阿东说他要出差,要阿里在家乖乖听爸爸的话,不能吵闹。他回来给阿里带好吃的。阿东的话没有谈完,阿里便呼呼睡着了。
三、“网红脸”消费形式中的性别平等
在封建礼教的性别文化语境下,女性的性别美学屈从于家庭伦理学,女性通常在“贤妻良母”的父权制伦理角色中享受有限的审美主体性。对于女性而言,“一旦角色定位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她们就不再具有审美创造性,而只能处于父权体系的操纵之下”。①[美]简·盖洛普著,杨莉馨译:《通过身体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然而,从精神分析或集体无意识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父权制下的女性审美形象与社会矛盾,“中国女性的传统模式不断被刻板化,但刻板化的女性模式却与男性审美视角有很大的矛盾”。②焦杰:《传统女性的刻板模式与男性审美视角的矛盾——以中国古代姬妾妓娼现象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在于中国传统的“妻妾制”的家庭婚姻制度以及中国古代男性的娼妓消费现象。这种现象直到民主共和制的建立,以及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建立才开始松动。随着当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两性平等的身体美学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才逐渐变为现实。长期以来,“在父权制社会关系中,女人通常是无助的、失声的以及不被倾听的、被无视的群体,因此,当代美容术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美学实践,而且更是一种事关政治诉求的热点问题”。③Luna Dolezal,The(In)visible Body:Feminism,Phenomenology,and the Case of Cosmetic Surgery,Hypatia,no.2(2010),pp.357-375.换言之,正是以脸面为主导的身体消费促进了两性的平等,使传统女性从家务操持、生育繁衍、相夫教子等不受重视的女性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女性不仅开始宣示自身的身体主权及其审美意志,而且通过集体性的消费力量开始对男性的身体景观品头论足。这促成了两性之间社会审美的身体互动模式。女性从家庭责任体制中解放出来,走入了消费性的休闲领域。身体消费文化使女性的主体意识与审美愉悦得以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女性通过化妆、整形与修图技术,开始全方位、立体性地“建构女性的身体话语,将女体视为自我赋权的独特空间,流动而多变”。④林树明:《大众消费文化与女性审美体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女性从传统的社会分工体系与家务劳作空间中逐渐解放出来以后,她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发生了后现代方向的转变。原来的以工作与家务为主的时间体制与空间体制发生了动摇。女性的生活美学日常化了,她们的艺术实践并非只在正式的美术馆、音乐厅、学院讲堂等场所才能实现,而是广延到购物广场、美容院、电影院、健身中心等都市消费场所。这种离散性、个性化的审美空间,使女性身体审美的赋权得以确证,实现了两性生活的民主化。在消费市场的选择中,女性并非被动地接受与被观望,而是对身体技术的生产领域有引导与推动作用,女性旺盛的消费欲望与逐渐强大的经济能力同时主导了男性身体观念的转型、身体技术的创新与身体产品的生产。男性作为一种身体景观开始被女性所观望与凝视。
诚然,仍有一种女权主义者的声音,担心女性所谓的身体解放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消费意识形态的陷阱。她们认为,女性在父权制与男权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支配下,争取到的女性身体的解放,是一种资本主义民主消费的假象。女性的身体解放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身体束缚,即按照消费型身体文化逻辑的本质,女性身体仍是男性支配的“被凝视”的客体化身体,是由男性主宰的选美委员会的价值评判的产物。这种现象也造成了女性内部的价值撕裂,即老一辈女性由于跟不上身体消费的观念而被歧视,沦落为被边缘化的“油腻女”形象。传统消费观认为,消费是为了生产,即便是个性化、私人订制式的消费,仍然是以生产为目的,即通过无数的所谓个性化消费来促进工业生产的维系。这种以生产为目的的消费,制造的是现代都市以男性审美习惯为中心的女性形象。女性的身体被消费技术景观化了,供男人观看与欣赏。但另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消费同样具有女性的主体性向度,即“男色”身体的消费。在以身体消费为特征的都市叙事(电影、文学等)中,也包括女性对男人的主动审美。“网红脸”不专指女性,也指涉男性,正是女性的消费主体性使男性的脸面同样被身体技术所塑造。因此,随着以女性消费群体主导的“男色”消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男性主导的单一化的身体消费观。
“男色”的景观化与男性“网红”现象的兴起,与大众媒体渲染的流行文化是分不开的。在电视热剧、档期电影、电视选秀、网络直播视频等娱乐文化的助推下,“小鲜肉”“小奶狗”“男神”等成为女性主义的消费名词,他们吻合了女性消费群体对男性形象的构想,同时也被众多的男性本身所接纳。男性的颜值与面容遵循着女性的消费期待及其资本逻辑。如果说,早期的“小鲜肉”形象还不能被社会所普遍接受,通常被冠以“伪娘”“娘娘腔”等称谓,但到新世纪之后,随着娱乐消费的女性主义审美风潮的盛行,“小鲜肉”的美学形象逐渐被娱乐市场与流行文化所认可,体现了当代性别美学的审美趣味。男性“网红”在生活方式和爱好选择上,“他们喜欢用化妆品来美化自己的脸面,愿意为了保持良好的身形做健身和节食,更有甚者为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和女星一样进行除皱、瘦脸等手术”。①黄静:《“男色”消费与“小鲜肉”审美——近年银幕男性审美趋势探因》,《东南传播》2015年第4期。
2016 年的微博热搜排行榜数据显示,网络热度排名前十的有7 位男星,其中王俊凯、易烊千玺、鹿晗、王源等包揽了前六名,尤其是TFBOYS组合,到现在依然热度不减。②沈佳晨:《男色消费——影视娱乐语境下女性审美的一场狂欢》,《艺术科技》2018年第2期。这些男星的脸谱普遍呈现出一种阴柔、俊俏、中性化等特点,为“男色”消费市场确立了价值的风向标。男性的脸谱从原来的银幕形象中的“硬汉”“威猛”之美转向了信息化媒体形象中的“阴柔”“中性”之美。从20世纪80年代的史泰龙、施瓦辛格、高仓健、秦汉到90年代的“四大天王”、周润发、罗嘉良等,从2000年以后的F4、陆毅、陈坤再到近年充满手机屏幕的肖战、鹿晗、陈伟霆等“小鲜肉”类型的花样美男,可以窥见男性脸谱形象的变化及其消费市场的变迁规律。21世纪初以来,人体美学的观念开始在男女平等制度中建构日常实践方式,尤其是“男性选美大赛”改变了传统的男性健壮的形象,而注重的是外表的文雅和自我护理,男性美的提升,而不是强健的体魄。③[法]乔治·维加莱洛著,关虹译:《人体美丽史: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第230页。随着女性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男性选美尺度的女性法则的确立,职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男人的典型形象通常是,“出门时带一块秒表和一整套美容品,因为这是外表竞争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在两年内翻了一番的男性美容市场证实了对身体的真正崇拜”。④[法]乔治·维加莱洛著,关虹译:《人体美丽史: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第231页。这种驱动男性身体消费的力量既来自女性的消费意志,同时又存在于男性自身为迎合两性平等观念而产生的审美自觉。
四、“网红脸”消费的资本逻辑与哲学反思
“网红脸”是“网红”的脸谱标识。从表面上看,“网红”对于“网红脸”的消费现象,是“网红”的一种基于主体性的消费自觉。但就其实质而言,“网红脸”的出现与流行,有身体消费、营销策略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在起作用。因此,揭示“网红脸”消费的资本逻辑,并从身体哲学的视角反思“网红脸”的消费现象很有必要。
(一)资本逻辑
在互联网的话语生态中,身体被软件技术所修饰、被视像化以后,它的生理性在减弱而商业性在增强。身体的医学生理学转变成了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互联网通过各种信息技术建构了它自己的身体世界,并影响人们对身体的认知与信仰。日常生活的身体观发生了巨变,身体被代码化与符号化了。当“网红脸”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脸谱,并且它的化妆规范与形体参数介入日常生活的身体修饰时,身体已经被一种资本逻辑所束缚。身体作为工具参与社会利益交换,被视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谋求身份改变与阶层上升的一种符号。“网红脸”被视为一种颜值资本,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被看作是草根阶层突破阶层固化的一种身体工具,它是“网红”能够自主开发的为数不多的身体资源之一。但是,“网红”也存在工具性身体的悖论:“当她们用自己的身体突入现实的政治经济语境,试图打破现有的权力关系而在社会结构的松动中获益时,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抗本身就是被权力话语所塑造和规定的。”⑤杨一丹:《“人体炸弹”和“网红脸”——“去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体政治》,《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2期。换言之,正是由资本逻辑塑造的社会权力结构生产了身体的符号及其谱系,而不是通过诸如“网红脸”一样的脸谱改造术使身体实现了阶层的突围。实际上,身体技术是资本运作的应用领域,即什么样的身体经济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身体技术开发,包括实体性的医疗整形与虚拟性的身体修图。
从“网红脸”的审美观念的传播机制上看,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在制造“网红”与“网红脸”?“网红”现象是一种网络经济现象,还是一种娱乐文化现象?“网红”的脸谱是如何被消费意识及其背后资本逻辑所控制的?在一个身体主权自觉的时代,尽管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身体权利所抗争,但身体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身体总是具有其公共性维度,被公共视野中的社会现象所建构,也就是说,我的身体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①Judith Butler,Undoing Gender,Routledge,2004,p.21.对于网络公众人物的“网红”来说,那些影响他们审美取向的看不见的“他者”,成为弥散于身体消费旨趣的一种精神存在。“当它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似乎看见了许多包含在身体之中的可能性,而身体正是这些可能性的综合呈现方式。”②Maurice Merleau-Ponty,The World of Perception,Oliver Davies,Trans.,Routledge,2008,p.83.作为一种网络消费时代的脸谱形象,“网红脸”所折射的是由信息技术、市场营销与流行文化等多重因素相交织的消费机制。质言之,这种消费机制正是由于资本逻辑作用于人的日常身体实践的产物。
不过,有女权主义者强调,正是新媒体、自媒体解放了女性的身体,使身体不但没有成为现代工业生产“欲望”的终端,而是女性审美的表现领域。化妆技术、整形技术与修图软件工具,使女性的审美体验通过身体得以呈现。女性的身体不是男性欣赏的景观,而是自我实现的证明。“网红脸”并非像阿多诺声称的化妆与整形“工业文化”的产品,也并非像马尔库塞所声称的“单向度的人”的表现形式,相反,正是“网红脸”的存在,使女性变成了“多向度”“多元化”“个性化”的审美主体。网络技术使图像身体具有不断续写的可能,身体价值的“延异性”在增强。网络符码体系取代了日常生活语言。在网络虚拟的交往活动中,网民更倾向于用键盘组织语言与传递价值。格式化的键盘语言与数字化的视像表达,开启了不同于传统的身体观念、美学方式及其表达规则,实现了文字、声音与图像并存的身体呈现方式。
(二)哲学反思
互联网虚拟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经验方式,以至于哲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实在与现象、身体与心灵的关系,并开辟身体研究的新领域。“网红脸”的身体技术与审美取向,不得不引发人们对身体哲学甚至身份伦理的反思:我是谁?我为何被弄成了现在这种样子?我究竟被什么力量塑造?真实与虚幻的边界如何确知?体验身体(现象学身体)与技术身体(工具论身体)的关系如何?“网红脸”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日常生活的资本实践,还是一种全新的身体美学理念?等等。
通常来说,身体在西方思想史中有三种命运,这三种命运同样可以用来反思“网红脸”在身体哲学上的表现。一是自柏拉图之后,身体是意识发生的障碍,身体受制于形而上学的道德形式。所谓支配身体的理念,是世界知识的终极起源和最高价值,而身体则受制于灵魂的独断论之下。“正是理念,派生了现象,派生了多样性,派生了偶然性,派生了感官,派生了艺术,派生了身体。”③汪民安:《尼采与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网红脸”的出现显然对于打破脸谱的父权制与男权主义的审美形式、道德专制形式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二是在尼采之后,身体开始觉醒,成为主体的替身。“网红脸”成为跨性别审美主体的表征,促成了两性平等甚至性别多元化的审美格局。三是自莫里斯·梅洛-庞蒂、赫尔曼·斯密茨等身体现象学家之后,身体成为一种新型的意义源与意义生成体系的逻各斯,成为意义确知的可靠来源。在身体的现象学时代,“网红”只有突破工具性身体的束缚,在脸面审美实践中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同时把生命意义的核心价值定位于身体性,从一种体验性的身体深度上获取生命价值确证的通道,才能实现生活美学的个性化创造。
“我们认识到的‘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是‘虚构的世界’。”①[德]尼采著,贺骥译:《权力意志》,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页。而关于身体的新型“道德形式”只不过是“道德理性”重建的一种表现。如尼采所言,肯定身体的就是真实,否定身体的就是虚假;真理的标准在于权力意志的彰显,在于激发生命。面对“网红脸”带来的身体、资本与文化等方面的议题,我们需要重估身体正义、审美价值以及善恶伦理的标准。正义、价值、伦理并不是某种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规定,而是一种关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身体性描述。权力意志是身体性的,是生命的激情,同时也是情感性的与伦理性的。“网红脸”对于探究基于身体出发的各种存在的可能世界,激发“网红”的生活美学想象,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梅洛-庞蒂提出的“世界之肉”(The fresh of world)的观点,人对世界的知觉方式源自身体而不是意识。身体性的存在才是纯粹的、真实的、想象性的存在。“通过想象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放飞自我,并探究各种可能性的世界。”②James B. Steeves,The Virtual Body:Mealeau-Ponty's Early Philosophy of Imagination,Philosophy Today,no.4(2001),pp.370-379.反思“网红脸”消费现象背后的资本逻辑及其身体哲学,“人对世界的体验是通过与他者的身体性关系而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性把身体置于不断地接受与他者的社会互动过程中”。③Dylan Trigg,The Body of the Other:Intercorporealit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Agoraphobia,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no.3(2013),pp.413–429.“网红脸”正是在身体政治、身体技术与资本运作等多重领域的跨性别互动关系中流行起来,并将持续作用于当代脸谱的日常审美活动。
五、结 语
当代民众的脸面美学不仅折射了人们身体美学的观念史,而且赋予了脸谱的某些意识形态特征。比如,传统的父权制审美逻辑下女性鼻削、颧高、阔口大面的“克夫脸”,带有小资情调的上部略圆、下巴略尖、线条流畅的“瓜子脸”,具有新闻联播主持人脸型特质——轮廓柔和、圆润饱满、端庄大气的“国泰民安脸”,等等,它们构成了当代复杂的关于脸面审美解释权的争夺场景。在当代脸面审美的谱系里,“网红脸”无疑是最典型、最广普的一种类型,它是随着商业性的网络直播而兴起的一种新型脸面,是技术消费与身体消费的产物,其商业意味与资本逻辑更加突出。
“网红”们所热衷的身体消费并非仅仅创作出一种消费化的脸谱,准确地说,他(她)们正在从事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化妆整形的生活实践。“网红”通过修脸术与修图工具建构了消费时代的脸谱形态学。这种消费化的脸谱在摆脱父权制或男女性别二元论法则的同时,依然受制于本质主义、形式主义的身体美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身体现象学层面上的“真实的”生命意义。“网红脸”只不过对性别形象文化做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规划,结果可能导致“网红”们陷入了新一轮跨性别的脸谱美学较量的身体政治实践。无论从女性审美主体的觉醒,还是男女性别平等意识的形成,包括脸面、健身、养生等在内的身体消费,仍很有必要从身体哲学层面去反思:工具论身体只有转化为现象学身体,才能使当代青年的脸面审美在存在论意义上实现本真性的回归与生活美学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