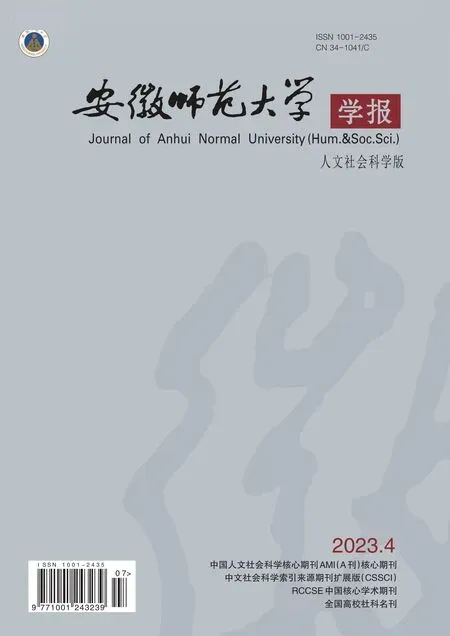皇权视域下清代赈捐事业的历史走向*
杨双利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24)
清代救灾力量多元,将筹赈来源与放赈主体分而观之,可为三类:官资官办,救灾物资和放赈活动由政府一力承担;民资官办,救灾物资来源于社会团体或个人,放赈活动则由政府统一协调和管理;民资民办,救灾物资与放赈活动皆系社会各阶层的团体与个人自发举办。“捐”是非官方资源参与救灾事业的主要方式,“劝捐”是清朝政府动员社会力量的一项重要手段,“捐”与“劝”的实践过程中饱含了皇权与民意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中,皇权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赈捐历史的演进轨迹,亦反映了王朝政治的盛衰变化。
为助力国家救灾事业而开展的赈捐活动主要是以捐纳和捐输两种方式实现的。①关于捐纳和捐输的异同,学界多有论及,江晓成在总结学界诸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思考和辨析(详见江晓成:《清代捐纳、捐输概念考辨》,《清史研究》2023年第2期)。捐纳、捐输之外,社会一般个人的私捐、私赈行为也常常受到官方的注意乃至重视,本文也将其纳入讨论的范围。因此,在许大龄、陈宽强、伍跃、吴四伍、江晓成关于清代捐纳、捐输制度的讨论中,赈捐都是备受关注的一项内容。②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陈宽强:《清代捐纳制度》,台北三民书店2014年版;吴四伍:《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江晓成:《清代捐输制度研究(1644-1850)》,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赵晓华专门就清代赈捐的方式、特点、发展历程、利弊得失及晚清赈捐的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进行了细致探讨。③赵晓华:《清代赈捐制度略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晚清的赈捐制度》,《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但由于研究重心的不同,学者们对赈捐这类特殊“捐”项所牵涉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救荒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没有展开分析,关于清代赈捐历史中皇权的态度及其影响亦乏详论。笔者从皇权视域出发,通过解析不同时期清廷对赈捐的态度及民意反馈,以期管窥王朝时代公共事业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④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国家权力与皇权本就难解难分。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顶峰时期,皇权对国家机器的支配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因此,文中所言国家、官方、清廷或某位皇帝的决策、政令、言论等一定程度上都可视为皇权意志的产物。
一、荒政不济与清初的劝捐策略
清初正处于15—19世纪近500年间最寒冷的17世纪,是气候史上典型的“低温多灾”时段。⑤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然而,历经明末大乱之后的清王朝百废待兴,不惟荒政制度不完善,财政方面也不宽裕,军需供应尚且捉襟见肘,更难承担起灾荒救济的重任。统计数据显示,顺治朝年均赈灾频次远远落后于清代其他时期,且主要集中在直隶地区。⑥据统计,整个清代267年赈济频次总数为27110,年平均赈济次数约为102次;顺治朝18年总计赈济频次94,年均赈济频次约5次,只是其中的一个零头,而且近2/3发生在直隶地区(计62次)。参见杨双利:《福惠天下:清代筹赈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56页。为此,清廷不得不通过劝捐办法极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救灾事业中来,以补官赈之不足。
顺治九年(1652),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赈捐热情,经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山东道御史王秉乾及户部科臣魏裔介先后奏请,清廷批准对赈捐行为给予奖励。由地方官将“乐输义助者汇造姓名”,送往户部登记备奖,给予“士绅、富民倡义助赈者”“以顶带、服色、纪录”。⑦《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七,《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2页;卷六八,第530页;卷六九,第543页。有学者认为,此次奖励赈捐之举表明清代奖励捐输赈济的政策已经初步形成。⑧江晓成:《清代捐输制度研究(1644-1850)》,第30页。顺治十年(1653)直隶水灾,清廷令地方官对捐输谷麦及减价出粜的殷实之家“酌量多寡,先给好义扁额及羊、酒、币、帛,以示旌表”。⑨《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二,《清实录》第3册,第643-644页。顺治十(1653)、十一(1654)、十二(1655)、十三(1656)、十四(1657)等年直隶连岁水灾,清廷倾注心力,不仅大量动用了皇家内帑,亦对对非官方赈捐有迫切需求和殷切希望。⑩《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七,《清实录》第3册,第607、608页;卷八一,第638页;卷八二,第643-644页;卷八九,第703页;卷九六,第753页;卷一〇三,第800页;卷一一三,第888页。期间,皇帝下诏对水旱灾害中“能赈恤全活五百人以上”的官员“核实纪录”,能活“千人以上者”“题请加级”;“乡绅、富民尚义出粟,全活贫民百人以上者”,令地方官给予旌劝。①《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四,《清实录》第3册,第663页。顺治十四(1657)、十七年(1660)再次强调,按前文所述政策奖劝赈捐。②《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〇八,《清实录》第3册,第848页;卷一三一,第1015页。继而,又“开准贡一途”,将“士民捐银赈济,能全活百人以上者,各照出身,量与录用”。③《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三七,《清实录》第3册,第1058页。虽然奖劝力度很大,但顺治时期民间捐赈者寥寥,数额亦不多,参与赈捐的主要是各级官员。以顺治十一年(1654)直隶广平府饥荒救济为例,民间殷实之家除“永年县故宦陈良贵之妻国氏捐杂粮二十五石”外“别无捐助者”,而大名道副使及广平府知府以下各官捐赈合计为1 400余两。为了激劝赈捐,上级官员不仅令永年县对陈良贵之妻给予“好义牌匾并羊、酒旌表”,对“未便给匾”的牧民之官亦承诺“量行奖励”。④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9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0909页。
朝廷对赈捐的迫切需求为官员晋升提供了机遇。操江巡抚蒋国柱因“捐赈宁国、太平水灾贫民”而加兵部尚书衔;湖广巡抚张长庚因捐赈饥民加兵部尚书衔,又因“捐赈武昌、汉阳二府饥民”加太子少保。⑤《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二〇,《清实录》第3册,第932页;卷一二四,第959页;卷一三二,第1018页。顺治末年,清廷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对吏治有负面影响。为“慎重名器”,对从前各部议定“文武各官捐助银米”给予纪录、加级、授官之例进行了修订,规定“嗣后凡捐助银米者,俱不必加级、授官,仍与纪录”,如“有应加恤赉者”,重新议定。⑥《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四,《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页。
虽然官员捐赈加级、授官之例被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再需要官员个人参与赈捐活动。在清廷看来,官员的赈捐行为不仅有助于弥补国家财政之不足,而且能在地方上起到显著的表率作用,以为民捐之倡。因此,康熙年间要求官员捐赈的现象仍然存在。康熙四年(1665)山东灾荒,除发给常平仓粟外,“谕地方官捐输赈济”。⑦《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一五,《清实录》第4册,第223页。康熙九年(1670)江南水灾,户部议定在正项钱粮不足的情况下“劝谕通省各官设法捐输”。⑧《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三三,《清实录》第4册,第450页。针对地方绅、商、富民开展的劝捐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息。康熙二十三年(1684)河南饥荒,谕令户部讨论“鼓励捐输”事宜;二十四年(1685)直隶饥荒,户部批准巡抚崔澄所请“劝谕捐输”办法;二十九年(1690)正月,对上年直隶受灾地方不能自备牛种的穷民,由巡抚督率有司劝捐救助。⑨《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卷一一四,《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6页;卷一二〇,第259页;卷一四四,第584页。然而,民间捐助本属个人自愿行为,官为劝捐虽然表达了清廷对民间力量的期望,却已有干预民心之嫌。更甚者,许多地方往往因官不得人而出现摊捐的过火行为,以致民怨久积。郑世元在《私赈谣》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康、雍之际地方官的劝捐实况:
昨闻飞檄来幽燕,官家漕米都回船。吾乡急公且好善,富人大户群助钱。乐输执簿沿门奏,点簿挨家米一斗。此虽善事何劳劝,多寡亦要随人愿。富家十石尔道多,贫家一斗将奈何?富家陈陈堆满屋,贫家一斗剜其肉。⑩[清]张应昌编:《清诗铎》(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40页。郑氏认为,民间私赈系自愿为之,不劳官家激劝。“官家漕米都回船”、“此虽善事何劳劝”等诗句表达的正是其对政府在灾荒救济中不动用官米,反而在民间社会无论贫富之家一律登门劝捐的不满。而“挨家米一斗”的摊捐方式已经背离了民间捐输的“义助”宗旨,给贫困之家造成了极大负担。这种过分激劝的情势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府救灾力量不足的实情。
捐输之外,清廷亦通过捐纳方式汲取救灾物资。康熙四年(1665)山东旱灾中,礼科给事中黏本盛奏请“酌定生监准贡条例,令生员、俊秀、富民等捐米备赈”。康熙帝谕令只将此条中“生员等捐助银米”一项停止,其余依议实行。①《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一五,《清实录》第4册,第231页。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二四,《清实录》第7册,第378页。嗣后,康熙朝救荒实践中屡有开捐事例。②相关事例参见陈宽强:《清代捐纳制度》,第109-119页。有学者统计,清初顺治、康熙两朝总共实施了64次捐纳,其中以筹资救灾为目的的赈捐就达23次,约占到40%。③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第349-350页。为了充分动员捐赈,清朝政府还制定了明确的报捐细则。康熙十八年(1679),关于捐纳助赈山东春旱的题报中细致开列了报捐和回馈的标准:
……在东省就近捐纳,则捐者必众。如现任文官有加级至一品者,捐粟二百石,准封三代;二三品者,捐粟一百石,准封两代。有参罚停升者,捐粟三百石,准行注销;未选之官,捐粟三百石,准其先用。童生捐粟一百石,准入学;生员捐粟一百石,准入监;廪捐一百石,增捐二百石,附捐三百石,准岁贡。待补完赈项,即行停止。如此则上不费而民得生养之资矣。④[清]张能麟:《救荒政略》,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2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53页。正如伍跃所指出的,捐纳是“政府出卖各种与做官有关的资格”来解决财政问题的一种方式。⑤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第1页。由于牵涉到铨选,清廷对开办捐纳往往持保守态度,康熙帝本人亦十分谨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赈济直隶、河南灾荒,九卿等决议在仓存米谷不敷的情况下“暂开捐例”,康熙认为“捐纳事例无益,不准行”。⑥《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卷一一四,《清实录》第5册,第189页。四十六年(1707)浙江旱灾中,浙抚奏请按照山东常平捐纳例开捐济赈,康熙批示按照江南例截漕赈灾即可,不必捐纳。⑦《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二三一,《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0页。关于地方官捐俸赈灾一事,康熙认为“皆虚名而已”,并无益处。他更强调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凡遇歉收之年,督抚等但据实速报,则或蠲赈、或停征,先期酌行,于百姓乃有裨益”。⑧《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二五四,《清实录》第6册,第513页。
康熙朝赈捐活动中暴露出的问题使继任的雍正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民间捐输“名曰乐捐,其实强派,累民不浅”。雍正二年(1724)上谕,“嗣后绅衿、富民情愿协助者,听其自行完纳”,并要求对官吏摊捐行为予以惩处。⑨《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一九,《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3页。至于官员个人的捐赈行为,雍正帝与乃父的态度一样:“纵将通省官员俸银捐助,为数亦属无几,有何裨益?”但他并不打击地方官员中“愿出己资捐助效力”者的积极性,只是对以往赈捐活动之后官员题请邀功的行为进行取缔。⑩《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一一,《清实录》第7册,第203-204页。关于捐纳一事,雍正表示,虽然“皇考曾屡言捐纳非美事”,但鉴于户部供支不济,仍不罢停。⑪《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一五,《清实录》第4册,第231页。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二四,《清实录》第7册,第378页。雍正朝因灾捐纳主要用在备荒仓储方面,临灾开捐并不多见,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清代前期捐纳奖叙标准常常为捐输所参考,从而更加激励了捐输行为。⑫江晓成:《清代捐输制度研究(1644-1850)》,第74-75页。这一点在雍正朝尤其突出。为了鼓励捐输,政府常常通过题匾的方式予以旌奖。雍正四年(1726),广东潮州府发生饥荒,近30余名生员因“自行义赈其乡”而获得来自朝廷的题匾奖励。紧接的雍正五年(1727)饥荒中,又有至少70余名绅士“捐米义赈”,受过旌奖的“诸人皆在其列”,“或平粜,或捐米,或分赈、共赈”。⑬[清]萧麟趾修、梅弈绍纂:《乾隆普宁县志》卷六,见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6册,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240、270-272页。雍正九年(1731)直隶、河南、山东旱灾救济中,为了杜绝虚冒滥奖,清廷参考捐纳条例,重新厘定捐输议叙规则:“地方绅衿、富户捐谷十石以上至三十石者,分别给以花红扁额;二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分别给以顶带。该地方捐谷至三千石以上,将地方官从优议叙。”①《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一〇七,《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1页。雍正十年(1732)直隶、山东旱灾救济中更为清楚地展现了赈捐奖励的多样性:“耆老、义民,量其捐谷多寡,或给匾额,或给顶带荣身;生监人等,或准作贡生;缙绅人等,或刻石书名,以为众劝;候补、候选有力之家,捐资多者加级,更多者照本职加衔。其地方官有能捐俸籴谷广行赈济者,量其所捐,分别议叙;有因公罚俸、降级停升者,准予开复。”②《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一一八,《清实录》第8册,第566页。
由于财政支绌和供应繁费,清前期在灾荒救济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赈捐。即便清廷早已认识到此法的诸多弊病,也没有停禁的打算。捐赈在弥补官赈之不足、解救饥民于倒悬的同时,也给参与其中的社会各阶层增添了经济负担。正如雍正十三年(1735)给户部的谕旨中所指出的,“各省从前办公,无项可动,上下共相捐应,官民并受其累”。③《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一五七,《清实录》第8册,第918页。
二、皇权国威与乾隆朝的赈捐限度
雍正朝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其后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清初各类赈捐活动中产生的诸种弊病也给后继者敲响了警钟。弘历甫登大宝,即历数雍正晚期频繁捐输之弊端,“对以乐善好施名义请奖捐输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再次强调了捐输的自愿原则”。④江晓成:《清代捐输制度研究(1644-1850)》,第99-100页。此后,清廷又以捐纳事例中浮费太多为由,将京师及各省捐纳之项全部议停,只留捐监一项收归户部,“以为各省一时岁歉赈济之用”。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 册,档案出版社1991 年版,第343 页;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39-40页。
作为皇权的代理人,地方官员执行皇权赋予的救荒任务是分所应当,但其私赈行为在乾隆朝是被严厉斥责的。乾隆八年(1743)夏季,贵州省米价昂贵,总督张广泗先令各属发仓谷减价平粜,并将鳏寡孤独等人户收入普济堂养赡。其后又提出,不敷之资“若州县力不能捐,臣等公同捐给,务使茕独不致失所”。此奏虽是为救饥而作,却遭到乾隆帝的批评。乾隆认为,“此等穷困之民,国家自应加恩惠养。其养赡之资,动用存公银两为是。若散给州县,令地方官捐资,岂朕保赤之意?”同时,他斥责张广泗“不识大体”,令内阁发上谕“申饬之”。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64页。这里面不仅体现了皇帝对国家养民能力的自信,更是表达了其对惠民之权操诸上的态度。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对顾琮奏请停办捐纳封典一事的态度,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了皇权的排他性。他批评顾琮此奏是“邀取声名”的行为,并严肃强调,是否停办捐纳系出自皇帝本人的意志,且经九卿会议讨论后做出的决定。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86-87页。他对地方官员和绅士办理赈务时是否有忠于朝廷、爱养黎民的诚心亦表示怀疑,以至于对他们时时表现出“代民谢恩”的态度生出厌恶的情绪。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南巡抚刘藻以本籍山东鱼台灾赈而上表题谢,上谕认为:
各省水旱灾伤,切轸朕念,赈周抚恤,每怀靡及。夫哺其赤子者,不可以言慈,自亦不知其慈也。向例,在京大学士、九卿等遇有本籍加恩之事,每连名奏谢,在籍绅士亦或有具呈该督抚代为题谢者,已属厌观。至外省督抚以桑梓沾恩,缮疏鸣谢,尤属非体。赈恤以为灾黎,岂因缙绅始沛恩施耶?是使绅士转得借以市惠闾阎,或且武断乡曲也。嗣后督抚等遇有本籍加恩之事,概不得具本题谢。著为令。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112-113页。乾隆帝强调,赈灾活动惠及的不只是官绅们的“桑梓”,更是“朕”的黎民。他很厌恶地方绅衿借皇权以为私用,或“市惠闾阎”,或“武断乡曲”。既不愿意“惠民之权”操之于地方,更不愿意地方民众为绅衿所制而影响皇权的发挥。
乾隆帝曾试图让地方官员明白,国家正项与民间捐助迥然有别,不应混为一谈。乾隆十七年(1752),山西蒲、解等属旱灾,巡抚阿思哈奏请将平阳绅衿、耆庶人等捐输银两就近解交河东道库,作为加赈时折放之用。乾隆帝严批阿思哈:
此奏殊为卑鄙错谬之至,朕实骇闻。直省偶遇偏灾,地方殷实之家乐善好施,或自出家廪积贮,或出己资籴运米石散给贫民,功令原所不禁。惟具数报官,量加优叙,以为闾阎任恤者劝耳,并非敛资贮库,借以助赈也。国家赈济、蠲缓,重者数百万两,少亦数十万两,悉动库帑正项,从无顾惜。地方富户所捐几何?贮库助赈,殊非体制。此端一开,则偏灾之地贫民既苦,艰食富户又令出资,国家抚恤灾黎何忍出此?深负朕痌瘝一体之意。阿思哈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捐银两著发还,听该绅衿等自行办理。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627-628页。他强调,将国家正项与民间捐助混为一谈是不合体制的,且国家赈蠲灾荒从不惜费,数额之巨,非民间捐助所及。政府对民间义举原则上不禁止,甚而“量加优叙”,只是为提倡民间互助而已,并不是要汲取民间力量以为官用。
乾隆十九年(1754)关于商人捐输报效军费的讨论中更为集中地表明了乾隆帝对当朝国力之自信及临时捐输的态度。该年,长芦盐政普福奏称,“芦东众商情愿捐银三十万两”充作军营赏需,更请援照此前商人报效“金川之例”为请。乾隆帝认为“此甚非是”,并说明了理由:
金川用兵,适当朕普免天下钱粮数千余万之后,又值江南水灾赈济抚恤需用过多。是以,于两淮、芦东、浙、闽等处各商之急公捐输者,不便阻其报效之忱,俯允所请。其实于军需所费何禆万一。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实……而近年以来,各省年谷顺成,仓储丰羡,即去秋淮、徐诸郡被水成灾,赈恤所需亦不下数百万。而每岁冬季,八旗兵丁诸赏赉按例举行,并不因西北军需于应用帑项稍存裁节之见。统计所费仍复有赢无绌,何至遽以商捐为请也?向来偶遇军兴、灾赈之事,不知轻重之人多思借以开例报捐。然果使筹饷、恤灾,动烦经划,则捐输踊跃,原属臣民忠爱之诚,而此时则殊可不必。况天地生财,贵于流通,库藏所积既多,而临事又复别筹取益,殊非用财大道,朕所不为。军需所费,边境借以流通,即内地商民亦均为有益。普福此奏所见甚小,著传旨申饬。恐各商复有踵而行之者,是用明降此,谆切晓谕,令内外诸臣共知朕意。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769页。
在他看来,此前军兴、灾赈事宜中臣民捐输报效,原属“忠爱之诚”,但“此时则殊可不必”。因为,“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实”,已经有能力支付这些巨额开销。待次年江南水灾时,普福再奏两淮盐商为救灾捐输赈款30万两,并表示商人自述“不敢仰邀议叙”,乾隆帝则给予了积极认可的态度。他认为“商人等谊敦桑梓,济急拯灾,好义可嘉,应予加恩议叙,以示优奖”,遂令两淮盐政“核明捐输确数,开具姓名,造册咨部,分别议叙”。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839页。前后两次看似迥异的态度,其实蕴含了同一种政治逻辑。前一项是军国大事,若吸收商捐,则不足以彰显国家实力,有损国威。后一项允许商人以“好义”之名捐输赈资,并非国家需要,而是皇权给予其一次表达“忠爱之诚”和“谊敦桑梓”的机会。因此,前后两次看似矛盾的态度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要充分体现本朝的盛世气象和皇帝的仁君形象。不仅要在国力上彰显出来,更是要从臣民对待国家的态度上体现出来。相比捐纳而言,乾隆帝更愿意接受臣民急公好义而不图奖叙的捐输行为,后者更能满足皇权对“忠”的政治伦理之要求及对“义”的社会风尚之提倡。
乾隆后期,皇权试图进一步强化官员处理公共事务时的国家意识。五十一年(1786),富勒浑所奏广东洋行商人捐输银30万两助赈江浙旱灾,以及李世杰因黄、运两河漫口的抚恤、善后事宜而奏请开办捐纳之例,都被乾隆帝严词拒斥。在发给前者的上谕中,乾隆帝表示,“上年江浙、河南、山东、湖广等处被旱地方较多,节次降旨蠲免,并不惜数百万帑金,以为灾黎赈恤之用。今富勒浑以商人潘文岩等愿捐银三十万两,辄以入奏,殊属见小”。他批评富勒浑作为封疆大吏不认真整顿地方,不思国家在各省赈灾方面先后拨发帑金“已盈数百万”,而对“商人些微捐助”即“意存见好”,“殊非朕委任之意”。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3册,第111页。显然,乾隆帝此谕并非要否定商捐的贡献,而是要官员明白自身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和皇权意志。在发给李世杰的上谕中,他明确表示“此奏断不可行”,并试图从皇权、国威的重要性和捐输、捐纳的弊端两个方面来强化官员的国家意识。他指出,以往国家军功、民政活动及目前户部库存都足以显示出国家之能力和皇权之胸怀,开捐毫无必要。而且,捐纳已经给选官制度造成诸多危害,对国家铨选和政府财政两无裨益。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3册,第328页。
乾隆一朝,对捐纳的运用非常谨慎,且后期有严禁之意,但并不排斥捐输,且对报效巨额款项的盐商“恩赏更加优厚”。③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盐商是乾隆朝捐输赈济的主要来源。根据陈锋和江晓成的统计,乾隆朝盐商赈济类捐输约计不到250万两,在乾隆朝盐商各类捐输项目中仅占6.3%,与乾隆朝国家正项灾赈开支更不可同日而语。④根据陈锋的统计,乾隆朝盐商捐输款项中,赈济类约计217.8万两;江晓成在此基础上又增补赈济捐输2例共32万两,总计约249.8万两。而江晓成统计的乾隆朝见于记载的盐商捐输总额约为3 946.3万两,赈济类约占6.3%。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220页;江晓成:《清乾嘉两朝盐商捐输数额新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又据统计显示,乾隆朝政府用在灾荒赈济方面开支,除去粮食不算,仅银钱开支折银至少在5 500万两以上。参见杨双利:《福惠天下:清代筹赈问题研究》,第66页。因此,乾隆时期的捐纳、捐输在备荒积谷方面虽有贡献,但在临时筹赈方面,数额和频次上都十分有限,被湮没在了密集的官赈活动中。⑤从赵晓华的统计中可知,乾隆朝因灾开办捐纳事例者,有乾隆七年(1742)两淮水旱、九年(1744)直隶旱灾、十一年(1746)两江水灾、十三年(1748)山东旱灾、十八年(1753)江苏水灾、二十二年(1757)两江水灾、二十六年(1761)黄河水灾等数次(赵晓华:《清代赈捐制度略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从江晓成所列举的灾赈捐输事例中可见,乾隆朝的因灾捐输活动中,捐输的数额大都不会很多,捐输人员的数量也屈指可数(江晓成:《清代捐输制度研究(1644-1850)》,第138-140页)。
三、财政危机与嘉、道以降赈捐活动的兴盛
乾、嘉之际,地方仓库亏空严重,制约了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应对能力。嘉庆初年,各省“遇有缓急需用之处,动辄请发内帑”。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页。镇压白莲教起义对于嘉庆朝政府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不惟军费要通过捐纳等手段来筹办⑦有学者指出,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所开川楚捐纳事例是清代捐例中规模最大、用银最多的一次。参见史志宏:《清代户部库银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灾荒赈济中亦大量使用捐输款项。据统计,嘉庆朝用于灾荒赈济的盐商捐输款额为117.8万两,这仅是直接用于赈济的款项。清朝中后期,由于河工失修、河患频发及财政萎缩,工赈日益成为灾荒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各类河工及其他水利方面的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工赈开支的。在江晓成的统计数据中,嘉庆朝盐商捐输款项用于黄河河工者为3 538万两,用于其他水利经费者76.6 万两,合计3 614.6 万两,占嘉庆朝盐商捐输总额的2/3 强。⑧江晓成:《清乾嘉两朝盐商捐输数额新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如果把其中的工赈开支计入灾赈开支,则嘉庆朝灾赈款项中仅来自盐商捐输的经费可能就已比肩国家正项开支,更不论其他捐收款项。⑨嘉庆朝赈灾动用国家正项银钱折银约在1 600余万两左右。参见杨双利:《福惠天下:清代筹赈问题研究》,第66页。
通过捐输报效获取的赈灾钱粮通常是由政府统一提调,往往先从国家仓库中挪垫应捐之数放赈,待捐款到位之后补还仓库。关于个人的私捐私赈,一些官员认为应当禁止,或者区别对待。嘉庆六年(1801)直隶水灾中,负责京师治安的步军统领明安奏称,“现在发帑赈济,而官民内有自出己资散给银米者,应请禁止”;以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的汪承霈也认为“官赈与私捐不应搀杂一处”。嘉庆帝不以为然,对明、汪二人的奏请予以驳斥,批评二人“俱属见小,不知政体”。他在上谕中连连发问:
试思官员等皆食禄于朝,稍有捐助,孰非公家之物?朕闻现在部员中即有查有圻、盛时彦等捐给银米之事,有何不合?至殷实商民受国家涵育深仁,积有余资,伊等乐善好施,更属美事。将来事毕后,尚当查明官员内有捐资较多者加恩甄叙,商民等亦应酌赏顶戴,或官给匾额,以示奖励。方嘉许之不暇,岂有转行禁止之理?若云官赈、私捐虑其搀杂,亦断无钦派大员等在彼散发口粮,而私捐之官民等率行争先散给之事。况官赈之外,又有私捐接济,饥民多得一分口食,岂不更资果腹耶?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239-240页。嘉庆帝认可私捐私赈的理由是,官员俸禄乃“公家之物”,捐资助赈系用公家之物赈国家之民,并无不合体制之处。商民捐赈则纯属“乐善好施”,更无不妥。显然,嘉庆帝的态度与乾隆时期迥然不同,而明安和汪承霈有此一奏则并非完全出于一己私见,实际上是受到乾隆时期流传下来的非难私捐私赈思维的影响。前面已经论道,乾隆帝十分在意对“惠民之权”的掌控,认为官绅等私捐私赈有借“惠民之权”操控地方的嫌疑,会影响到皇权的发挥。因此,他主张将官赈与民捐严格区分开来。嘉庆初年,一些旧臣的思想世界里延续了乾隆朝的惯习,甚至有官员因为处理私捐私赈问题而被御史弹劾。被弹劾的阎泰和在录口供时表态说,“我们放赈时,见有许多私赈,我于召见时曾经面奏不准与官赈夹杂,哪里还有叫他私捐的事”。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527页。嘉庆帝关于私赈私捐的一席分辩,又将各类赈捐都归为官方认可的灾荒救济手段,并大加鼓励。这既是嘉庆帝的个人见解,也是财政紧蹙下皇权的一丝变通,却为社会各阶层以“捐”的方式广泛参与救荒活动清除了思想和制度上的障碍。同时,对官员捐廉助赈行为仍然有一定限制。在辛酉水灾救赈时,河南巡抚颜检以河南与直隶毗连,奏请由河南各级官员捐廉一年、其本人捐廉两年“以佐工需”。嘉庆帝认为,赈灾、办工虽耗资甚多,但动辄让“通省司道府州俱请捐廉助公”则不成体统,谕令停止。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324-325页。嘉庆帝之所以不希望各级官员动辄捐廉助赈,是担心此举会导致养廉银丧失本初功能,继而兴起贪污腐败之风。嘉庆十六年(1811)江苏水灾,江南各省督抚、盐政、关差以及道、府、州、县等官纷纷请求捐廉助赈,亦被嘉庆帝严词驳回。他在给两江总督百龄的上谕中明确指出,“养廉之设,系为办公之用。若普行摊扣,在贤者自以急公奉上为重,不改廉政;而不肖者或因此借口多方巧取,其弊岂可胜言”?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6册,第511-512页。尽管嘉庆帝对捐廉助赈持谨慎态度,但仍然没有经受住财政窘境的考验。李喜霞的研究表明,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旱灾中,嘉庆帝劝谕地方大员要倡率属员捐廉助赈,以“补国帑所不逮”,全活灾黎,以“积德于身家”。⑤李喜霞:《养廉银与灾荒救济:以嘉庆十八年豫省灾荒为中心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嘉庆后期,绅、商、富民等社会各阶层的赈捐行为也愈发增多,这为其后道光朝大力推广赈捐办法营造了浓厚的氛围。⑥嘉庆十七年江南水灾,地方官员及商人等纷纷捐赈,受到朝廷的褒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77-78页);嘉庆十八年直隶旱灾,绅士等捐款助赈,直隶总督温承惠恳恩奖赏(同前第18册,第161页);嘉庆十八年陕西旱歉,地方绅民踊跃捐款,地方官按照捐款数额请奖(同前第19册,第358-359页);嘉庆十九年湖北匣商捐资助赈,又有绅商捐款十万余两赈济安徽灾歉(同前第19册,第331、788页);嘉庆二十五年江南灾荒,地方绅富踊跃捐款助赈,浙江巡抚认为其“较之官赈更为有益”(同前第25册,第463页)。据两淮盐政查明,自嘉庆十五年至二十二年,仅两淮商人捐输赈务、河工及军需银两就达1 700万两之多(同前第24册,第552-554页)。
道光时期,绅、商、富民在捐输赈灾方面的参与度大大增加。道光三年(1823)江苏水灾中,江宁、苏州两藩司所属绅、商、富民捐银达195 万余两之多。朝廷对捐数在300 两以下者,由本省酌给匾额奖赏;300两以上及数千上万两者,按照嘉庆十九年(1814)办过的赈捐奖励成案给予奖叙。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5页。道光十一年(1831)湖北水灾中,地方官“惟恐经费不敷”,向本地绅、商、富户“极力劝捐”,希望“一邑所捐能敷一邑之用”,捐项不敷再请官府发银赈济。②[清]周存义:《江邑救荒笔记》,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第3403-3404页。可见,赈捐在此时的救灾活动中已经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许多赈捐活动中,报捐人数越发增多。以该年江苏水灾为例,江宁藩司所属捐银在1 000两以上至5 000两以上者22名,300两以上者89名;苏州藩司所属捐银在1 000两以上至2 000两以上者9名,300两以上者52名。这还只是交由户部议叙的报捐人数,捐银在300两以下由地方酌给奖励的人数尚不包含在内。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95-96页。显然,地方政府已经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赈灾款项,才把筹赈寄托于民间赈捐活动上。不仅如此,许多地方的赈捐任务还须由地方官员以养廉银摊捐。道光十五年(1835),江西因连年水灾用过例银76 000余两,该省巡抚奏请循照旧案公摊还款,清廷给予批准。除巡抚及各司道捐银1万两外,余银66 066两由南昌等11 府及所属63 厅州县“按廉摊捐”,分作五年,“由藩司分别按月按季提扣养廉归款”,“免其造册报销”。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0册,第154页。可见,官员分摊捐款在一些地方已早有成例,而且形成“寅吃卯粮”的模式,将往后的养廉银都摊扣到赈款之中,为官僚制度的崩坏埋下了隐患。
朱浒指出,乾隆末年以至嘉庆时期,“以官民合作劝赈、分任赈济为主体内容的捐赈机制”“已运行得相当成熟”。⑤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嘉、道时期,赈捐地位的日益突出,使得劝捐成为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充分调动社会文化资源为赈捐活动助力,形成了如《海宁州劝赈唱和诗》这类独具特色的救荒文献。为了推动捐输赈灾,清廷不仅对捐输钱粮者给予奖励,对倡捐或劝捐成效显著的地方官吏亦给予充分的优奖,以激励他们在劝捐方面竭尽所能。道光三年(1823),浙江水灾赈务结束后,朝廷表示,除捐输钱粮的官、商、绅士给予奖叙外,对“劝导有方”的乌程县知县杨徳恒、归安县知县马伯乐等人亦给予奖叙。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157-158页。道光四年(1824)的安徽水灾中,对劝捐及办赈出力的知县、主簿、教谕、训导、典史等地方官吏近20余人给予“从优议叙”。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9册,第235页。之后,地方官吏因劝捐出力被给予奖叙的记载频繁地出现在道光朝的上谕中。
咸、同时期,国家财政的消耗日益严重。除战争赔款、河工修费等项外,又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又西北筹饷,不仅军费浩繁,而且作为财富之区的江南亦遭遇严重破坏,税收大幅度减少。灾荒赈济中,除直隶灾荒清廷尚能竭力拨款截漕外,对其他省份的灾荒几乎无能为力,地方的赈捐任务更为艰巨。同治五年(1866)江苏水灾,赈济、河工共需银30万两,搜罗江宁藩库所剩银两不足13万两,即使全部拨给,也不能敷用。为了早日筹得赈款,清廷敦促地方大员竭诚办理劝捐事宜,又提出“照筹饷新例递减二成报捐,并准其移荫子弟”。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同治六年(1867)陕西灾赈中,户部奏明由山西拨银6万两,四川、湖北各拨银7万两。然而,直至同治七年(1868)四月,除湖北筹解银1万两外,山西等省竟无分厘报解。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8册,第134-135页。
随着政府仓库钱粮的短绌及灾赈事务中对赈捐的越发倚重,加速了赈灾事务的地方化进程,官绅商民等社会各阶层逐渐成为救荒钱粮的主要来源,地方官吏愈发成为劝捐筹赈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此外,劝捐筹赈的任务已经不限于灾区官吏,也愈发广泛地涉及到非灾区的地方官吏。这种状况到光绪“丁戊奇荒”时已经十分突出。其时,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官吏参与到了为华北旱灾劝捐筹赈的事务中来。捐资来源则遍及社会各阶层,乃至海外的侨民。赈捐所获也成为此次灾荒中清廷办赈的主要财源,比动拨国家正项银钱的数额还要多出许多。然而,赈捐推行愈广,则捐力疲敝愈速。“丁戊奇荒”中,一些省份劝捐困难重重,不得已只能靠各级官吏凑捐或摊捐。有官员已经意识到“劝捐虽救急之策,而劝而又劝,难必捐而再捐”,遂提出“易捐为贷”的办法。理由是,“劝捐不如劝贷,捐则往而不返,惟慷慨好义者能之;贷则去而仍来,无损于己而有益于人,虽吝啬者亦可勉为拟仿”。①《奏为晋豫灾广赈繁请行分贷济赈方法办理事》(光绪四年四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5582-027。晚清捐务之难可想而知。显然,“丁戊奇荒”中的巨额捐款实际上是在透支全国捐力的情况下筹集起来的。
四、晚清义赈的崛起与官、义协作
在形成独具特色的“义赈”潮流以前,民间社会捐助赈灾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而“义赈”名称的出现也与民间捐助的长期积累不无关系。朱浒指出,“义赈”作为一个独立的词语最早出现在16世纪。那时的“义赈”主要是作为民间捐赈的一种褒称而存在。19世纪上半叶,义赈开始发展为一种特色的地方性救灾机制。到晚清光绪年间,义赈已经演变为一种超越了地方场域、独立于官赈之外的有组织、社会化的大型民间活动,并且“对官赈体制形成了强烈的制度性冲击”。②朱浒:《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则是义赈崛起的时代机遇。
“丁戊奇荒”期间,在义赈组织者们频繁穿梭于江南与华北之间的时候,清廷一面竭力调拨政府财力赈济灾区,一面如以往一样开办赈捐等局,督促地方官绅组织赈捐事宜,希望从社会各阶层中获得更多的助力。虽然清廷通过凑拨和开办赈捐的方式获得了巨额赈资,但其筹赈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进程也十分缓慢,以至于这笔巨款并没有在赈灾救民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效力。③参见杨双利:《福惠天下:清代筹赈问题研究》,第216-291页。因此,当李鸿章提出对光绪三年(1877)在江苏海州、山东青州等处,光绪四年(1878)在直隶河间及山西、河南等处广施赈济的上海果育善堂、广东东华善堂、浙江湖州仁济善堂、上海丝业会馆颁发匾额,以奖励其“急公好义、有裨荒政”的善举之时,清廷表示,该善堂、会馆等“向俱崇奉关帝神灵佑助,寅感实深,著南书房翰林恭书扁额四方”,交给李鸿章分发各善堂、会馆,令其悬挂在关帝,神前,“以答灵贶,而顺舆情”。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6页。显然,清廷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组织此时的赈灾活动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仍将他们视为崇尚关帝之“义”的传统民间捐助。奖励这种行为,一方面出于对民间社会倡议互助行为的提倡,另一方面是肯定他们在补充官赈不足上所做出的贡献。这其实也与义赈人士在自身认同方面的阶段性特征有关。“丁戊奇荒”时期,义赈人士仍然徘徊在“福报话语”和以“荒政”为话语对象的自我认同阶段⑤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405页。,与官方的沟通方面便不会显现出其与以往民间义举的差异。正是这种阶段性认知和做法,为义赈组织活动的开展赢取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为社会化赈济的逐渐壮大扫清了一些障碍。光绪五年(1879)六月底,官方对参与义赈的18家善会善堂颁给匾额嘉奖,正是在这样的互动氛围中产生的。⑥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171页。光绪六年(1880),当给事中郭从矩奏请将“丁戊奇荒”中“急公乐善”而“不求奖叙”的苏、杭等地善局首事姓名、事迹纂入各本籍志书中时,清廷欣然同意。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6册,第61页。显然,清廷认为,这类组织及其行为大有可用之处,不但有实济于国家,更可引用其事迹“以彰风化”。光绪七年(1881)十月,清廷又对奇荒期间集资助赈的“江苏生员谢家福著赏加国子监学正衔,廪生严作霖著赏加国子监助教衔,以示奖励”。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7册,第293页。至光绪九年(1883),山东水灾筹赈完毕后,义赈的主要领袖也大都出现在了官方的奖励名单中:
……直隶候补道盛宣怀、浙江候补道徐润、翰林院庶吉士沈善登、候选道郑官(观)应、补用道李培松、候选主事经元善、国子监学正谢家福、河南候补县丞杨家杲设法劝捐,不遗余力。拣选知县潘民表、候选训导严作霖、举人施则敬分赴利津、齐东、齐河等处核实散放,均属心存利济,见义勇为,著传旨嘉奖,以昭激劝。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9册,第326页。就在这份名单上报给朝廷的两个月前,义赈群体刚刚公布了其主要成员的构成,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四人以经理人的身份而成为义赈首脑。②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329页。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鉴于“江浙各官绅捐资助赈已历三年,为数甚巨”,周家楣、盛宣怀、施善昌、李培松、严作霖等义赈人士获得了“交部从优议叙”奖励,并被传旨与沈善登、徐润、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及其他江、浙、闽、粤官绅一体嘉奖。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12册,第87页。此后的官方文书中,对义赈人士的旌奖亦是不绝如缕。义赈组织紧锣密鼓的救灾实践和晚清政府的一再褒奖,助推了义赈声势的进一步壮大。清廷显然已经将义赈视为与官赈一样不可或缺的组织行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关于直隶灾情较重的玉田县灾赈问题的上谕中指出,该县因“官赈、义赈皆未推及,若不急筹勘抚,恐籽种尽绝,耕获无期”,遂令直督王文韶派员即速赈济。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1册,第46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人以“义赈动用官款,名实不副”为由,奏请禁止。清廷发上谕称:“京官办理义赈,自不应拨用官款,方昭核实。嗣后,官赈、义赈各专责成,用款毋得稍有牵混。至所称分认地段办理之处,著顺天府、直隶总督随时斟酌妥办”。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3册,第24页。此谕虽然意在讨论将官赈与义赈款项用度及办理事宜区分开来,但同时也非常明确地将二者等而视之。不惟款项用度上“各专责成”,亦试图以“分认地段”的办法将灾赈任务由官赈和义赈分别承担。而光绪二十四年(1898)江苏水灾中,有人陈奏将“官赈、义赈请归义绅严作霖总办”。清廷表示,“严作霖平素办赈均属妥协,该处赈务可否责成办理”,由督抚斟酌情形决定。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21页。在实际办赈活动中,清廷亦曾指示地方官协同绅士严作霖在灾区放赈。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27页。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陕西旱灾时,朝廷再度想要充分发挥义赈人士的作用,一方面请义赈元老严作霖“邀集同志来陕办理义赈”;一方面请“向办义赈均著成效”的施则敬、严信厚、周宝生等分头劝办义赈;又令熟悉上海商情的盛宣怀“劝募巨款,源源汇解”。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366页。可见,此时的灾荒赈济中,义赈群体不仅获得了朝廷的认可,而且清廷已经十分依赖义赈人士及其组织能力。
显然,清廷屡屡将灾赈任务“让渡”给义赈群体,与其自身财政状况的恶化和救荒能力的衰减密切相关。这一点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一道上谕中体现的极为明显。该年年初,由于内务府咨照户部补交光绪二十六(1900)、二十七(1901)两年进款20余万两,“以备宫中之用”,御史蒋式瑆即用“以崇俭德”的说辞向宫中进言。不料,上谕中却愤而斥之为“冒昧陈奏,实属昏谬糊涂”。原因在于,其时“各省水旱偏灾,立颁赈济,或随时体恤兵丁,优予赏给,亦皆出自内帑”。宫廷内帑“三节进奉各款每年不过十余万两”,皇帝及太后等“宫廷服御一切”已经“力从省约”,该御史却仍然以“崇尚俭德”为请,自然让宫廷之主难以接受。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8册,第39页。这道上谕清楚地表明,政府在灾赈事项方面已经难以为继,朝廷拨给的赈灾之资主要是来自于内廷的节省银两。这就无怪乎,每遇灾荒赈济,清廷便会极力鼓动义赈群体出资出力。无论其目的如何,官方邀集义赈群体来组织救灾工作,无疑为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参与救荒来表达自身的主体性提供了土壤,也为一些以救荒为目的或名头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壮大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此,不仅推动了救荒事业的社会化进程,而且大大推进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五、结 语
君主专制时代,受国家治理能力和皇权态度的影响,赈捐事业的境遇也因时而异。清初,财政竭蹙和荒政凋敝使得顺治朝政府不得不通过劝捐的方式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到救荒事业中来,以弥补官赈之不足。康、雍时期,由于赈捐实践中暴露出的诸种弊病,皇权一度对此持谨慎态度,但劝捐的活动并未停止,甚且出现过度激劝的行为。雍正财政改革造就的国库充裕新局面,为乾隆朝治国理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十足的底气。在乾隆帝看来,非官方的赈捐活动不仅缺乏必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皇权的发挥和国威的施展。乾隆初年即以弊端过多为由对捐输、捐纳的相关名目大加裁减。随后,清廷日益关注赈捐活动中所蕴藏的政治意涵:官绅的私捐私赈因带有“市惠闾阎”“武断乡曲”的嫌疑而被严厉斥责;商人的捐输行为则被认定为报效国家的“忠爱之诚”,不再敢于主动邀奖;一般民间捐助行为中所体现的“好义之风”被一再强调,以期达到充分彰显盛世气象的目的。乾、嘉之际,一度被压制的非官方力量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日益衰颓而出现反弹,嘉庆帝对私捐私赈一再表现出明显的认可态度。而后,救荒活动中对捐输钱粮的大规模运用则表明,社会力量参与救荒事业已经势不可挡。嘉、道以降,社会各阶层都已经广泛参与到赈捐活动中来,“劝捐”亦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政事。清政府试图通过制定明确的奖励政策乃至出售明码标价的政治资源来获取社会力量对政府活动的支持,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社会阶层则想要通过参与赈捐赢得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发展的诸多资源,晚清官僚制度的颓废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与此颇有关联。在官方主导的赈捐活动之外,以近代商人为主体的“义赈”力量迅速崛起,为晚清救荒事业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也对中国救荒事业的社会化起到了引路开道的作用。总之,清代赈捐处境的变化充分表明,皇权专制的王朝时代,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意愿和能力,而且与国家力量的盛衰及皇权态度的变化密切相连。当国家力量衰弱时,统治者不仅有可能让渡一部分权利给社会来发挥作用,甚且通过激劝的方式向社会求助。反之,国家经济强盛的时候,“惠民之权”操诸谁则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非官方力量想要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首先要征得官方的认可,至少不能与国家政治认同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