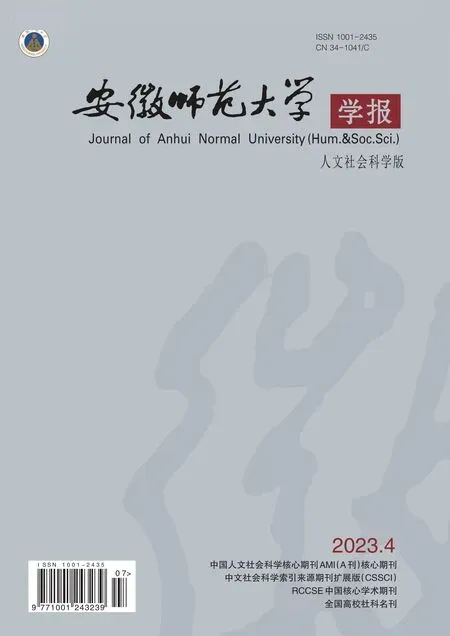新实用主义的阐释观订辩
——以罗蒂为焦点的考察*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州350001)
近些年来,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话题。在构建路径方面,文论界的共识是既要系统总结、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阐释学的理论资源,并结合时代语境、中国问题创造新的阐释学体系,也要适当参考、合理借鉴国外阐释学的理念与方法。截至目前,前一方面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而后一方面的工作则有待进一步细化、准确化。国外阐释学流派众多,十分庞杂,而以罗蒂为代表的美国新实用主义阐释学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阐释学常常被贴上“非理性”“非确定性”“反对公度”“极端相对主义”等标签。①参看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张江、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迈克·费瑟斯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张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揆诸罗蒂的阐释学思想面貌②关于罗蒂的阐释学思想,国外学术界围绕“从认识论到阐释学”(罗蒂1979年出版的专著《哲学和自然之镜》第7章)有过大量的讨论与争辩。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里奇认为罗蒂的阐释学是“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参见Vincent B.Leitch,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the 1930s,Routledge,2010,p.177.第二,瓦恩科(Geougia Warnke)提出了“罗蒂的民主主义阐释学”一说。参见Charles Guignon and David R.Hiley(eds.),Richard Ror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05.第三,帕尔默(Richard E.Palmer)强调罗蒂重视人文科学的语言、阐释与修辞三大转向,他的实用主义阐释学与德国阐释学之间联系密切。参见[美] 帕尔默:《解释学能给修辞学带来什么》,载[美] 沃尔特·约斯特、[美]迈克尔·J.海德编,黄旺译:《当代修辞学与解释学读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9-140页。第四,菲尔认为实用主义阐释学是罗蒂思想的重要遗产之一,这一阐释学否认任何非历史的阐释,而倾向于在共同体的对话中求得共识。参见István M.FEHÉR,Aspects of Rorty's Legacy:Pragmatism,Hermeneutics,Politics,Philobiblon:Transylvanian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Humanities,vol.18,no.1(2013),pp.58-67.第五,罗克莫尔反对罗蒂阐释学与认识论的对立,认为两者是相容的,因为认识论是阐释学的一种形式。参见Tom Rockmore,Gadamer,Rorty and Epistemology as Hermeneutics,Laval théologique et philosophique,vol.53,no.1(1997),pp.119-130.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其一,王治河将罗蒂的阐释学归入后现代阐释学,强调其反独断论与开放性、对话性的特征,并特别指出我们应当看到其“试图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努力”。参看王治河:《解释的游戏——当代西方的后现代解释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5页。王岳川也以赞赏的口吻指出罗蒂“新解释学”的特点是坚持差异性与相对性原则、注重对话,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眼光、新视界与新可能。参见王岳川:《当代西方美学主潮》,黄山书社2017年版,第86-87页。其二,乔国强认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阐释学既有浓烈的实用主义主义色彩,也有“典型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参看乔国强:《美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页。其三,王金福以罗蒂在“阐释与过度阐释”讨论会上的发言为依据,批评罗蒂陷入两难困境。参见王金福:《罗蒂难题:“你的文章是否说了些什么?”》,《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其四,同样是以上述讨论会发言为据,陆扬则将罗蒂反本质主义的阐释学列为四种阐释模式之一。参看陆扬:《论阐释的四种模式》,《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其五,汤拥华指出,罗蒂阐释学的“论题、概念与论证逻辑”,“需联系分析哲学方能理解到位”。参见汤拥华:《语言、真理与新实用主义的阐释学——以罗蒂对戴维森的解读为中心》,《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其六,王伟讨论了另一位新实用主义的代表舒斯特曼对罗蒂阐释学转向的批评,认为这一批评难以成立。参见王伟:《解释学转向:价值与论争》,《理论与现代化》2014年第6期。,可以发现,这些笼统的印象式标签是漫画式的,并未进入罗蒂阐释思想的内部肌理。
一、启蒙理性与交往理性
罗蒂之所以容易被人误解,自然与其颇具革命性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密切相关。罗蒂明确提出,实用主义的出发点是反表象主义:“信念是行为的习惯而不是表象实在的努力。根据这种信念观,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的问题。根据这种真理观,关于主体与客体、现象与实在的认识论问题可以由政治问题,即关于为哪些团体、为何种需要而从事研究的问题,取而代之。”③[美]罗蒂著,黄勇编译:《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序”第1页。这种反表象主义又被称为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美国化形态,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为表象实在凭借的是理性,所以,指责反表象是非理性的看起来顺理成章。罗蒂不惮于承认,依照那种区分表象与实在的理性观念,实用主义者无疑是非理性主义者。然而,“我们非理性主义者并不像动物那样口吐泡沫、举止粗鲁,我们只是简单地拒绝以某种方式谈话而已”,并试图以新的方式开展说服工作。④[美]罗蒂著,张国清译:《后形而上学希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罗蒂而言,表象实在的理性是传统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启蒙运动所赋予的一种可以接触实在、发现本质、探究真理的禀赋。就取代宗教权威的历史作用而言,这一理性有其积极意义。但它仍然信奉那些超越人类的东西,带有18世纪理性主义的最后残余,因此,罗蒂认为应该沿着启蒙运动反权威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行。如果说传统理性充当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纽带,架设了一座通向绝对实在的桥梁,那么,实用主义的理性则否认存在这种与实在相连的某种理性官能的运行。“对于我们‘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理性是在对话中养成的,我们视理性的含义为愿意探讨事物,倾听不同意见,试图达成和平的共识。理性并不是指能够由表及里地掌握科学实在或道德实在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具有理性就是有交谈能力,而不是屈从。”①[美] 罗蒂著,黄宗英等译:《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换句话说,从掌握内在本质的理性到致力于交谈的理性,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转换为后现代的对话理性,理性的范式或理性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巨大更迭。如此一来,先前非理性的指责就只能局限于旧有的框架或前提之中才能成立,而在新的衡量标准之下则变得没有意义。或者说,理性/非理性的旧式区分也不再有用。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自然科学都被视为传统理性的模范。正因如此,科学、理性、真理与客观性等概念经常被一起讨论,乃至相互等同,而科学家理所当然地成了人类与超人类之间进行联系的中间人。罗蒂认为,“如果理性意味着能够预先制定标准,那么将自然科学作为理性的范式是合理的”。②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6.问题在于,若是以这种尺度来衡量的话,整个人文学科就难免陷于非理性的境地。不言而喻,若要免除这种尴尬的局面,人文学科就需要另寻一种理性。如果说符合实在的理性是“较强的”理性观,那么,这则是一种“较弱的”理性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理智’或‘合理’,而不是‘有条不紊’。它列出了一系列道德美德:宽容、尊重周围人的意见、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武力。这些是文明社会的成员必须具备的美德,如果这个社会要持久的话。在这个‘理性’的意义上,这个词的意思更像是‘文明’,而不是‘有条不紊’。当这样解释时,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区别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特别的关系。”③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1,p.37.换句话说,理性不是追寻实在的一种能力,合乎理性也并非是指这一能力的运用,而是指可以商量的,是一种说服他人而非以强力服人的教养,这与以对话、交谈来阐释理性其实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说法。
罗蒂还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解释其推崇的后现代理性。具体说来,哈贝马斯区分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与“交往理性”:前者是柏拉图式的发明,它存在于个体心灵与事物性质间的固有本质之中;后者并非人类的自然天赋,而“只是当人们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讨论问题,争论直到达成一致,并遵守由此达成的协议时所存在的东西”。④Richard Rorty,Universalist Grandeur,Romantic Depth,Pragmatist Cunning,Diogenes,vol.51,no.2(2004),pp.129-140.以上两种不同的理性,意味着迥然相异的工作方式与知识生成模式。视理性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就是相信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能力,从而不需要交谈即可直接获取知识。相反,视理性为主体间交往的,就是把通过自由而非强制的交谈所获得的共识当作知识,它不需要借助实在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一方面,罗蒂同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认为这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把对非人标准的责任替换为对他人的责任,“把我们的视线从我们之上的无条件之物降低为文明周围的共同体”。⑤罗蒂著,孙伟平编,孙伟平等译:《罗蒂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页。另一方面,罗蒂又严厉批评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取向。这一取向鲜明地表现在哈贝马斯坚持相互理解的无条件性,坚持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有效性,坚持无扭曲的交往是意见的趋同过程。罗蒂明确反对这种非历史的“接近想象中的焦点”的看法,提出意见趋同是“越来越愿意与多元化共存”并且“停止要求普遍有效性”。⑥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67.
二、确定性与主体间性
在表象与实在的二元区分中,实在有着先验的确定性,而表象在持续接近实在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分有了这种确定性。因此,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背上非确定性的恶名并不为奇。应该看到的是,实用主义者摆脱了表象与实在框架下的确定性之后,紧接着就对确定性进行了重新界定。“我们认为‘理性的确定性’是争论中的胜利问题,而不是与已知对象的关系,我们将依靠对话者而不是我们的本能来解释这一现象。”⑦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156-157.即是说,确定性不再是与非人的现实加以对照的问题,而变为在人际之间开展对话的问题。与之相应的是,知识也不再是实在的镜像或映现,而是在持续对话中达成的暂时性共识或意见。如果说对照式的确定性是还原论与原子论的,抽离了社会实践,或者说,带有逃避世界的倾向,那么,对话式的确定性则是商谈论与整体论的,沉浸于社会实践。从对照到对话的变迁,显然是哲学观念的重大革新。罗蒂称这种实用主义为“认识论的行为主义”①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174.,它不再诉诸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或永恒不变的权威标准,不再试图找寻特殊的表象来证明论断,而是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论证,始终把证明看成是行为主义与整体论的,而且依赖于阐释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证明行为。
先验的确定性意味着先验的客观性,意味着不受人类具体社会环境制约的客观实在性。当人们追求这种客观性时,就会力图不与任何特定的事物关联起来,就不会尊重自己周围其他人的观点,也不会把自己当作某个阐释共同体的成员。罗蒂指出,这种自古希腊以来的客观主义文化传统预设了一种可以超越社会局限的共同性,一种非历史的人性。因此,这种传统把真理视为与实在相符。罗蒂敦促人们放弃这一形而上学的传统,认为应将客观性归结为协同性,从而无需劳神思索社会实践与社会之外的事物之间有何关系。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有助于人们刷新对客观性的认识,“客观性不是实在的内在本质的反映,而是主体间性”。②[美]罗蒂著,黄宗英等译:《哲学、文学和政治》,第206页。需要说明的是,这绝不应理解成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简单重述,而应理解为他们英雄所见略同。因为主体间性其实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杜威早在哈贝马斯之前就宣称,客观性的概念除了主体间的一致性之外没有其他东西,这种一致性通过对所有可用的假设和政策进行自由和开放的讨论而达成”。③Richard Rorty,Truth and Progress: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7.罗蒂传承了实用主义的主体间性思想,并在多部著作中进行屡屡申述。在他看来,“无论‘客观性’和‘超越性’的思想对我们的文化有什么好处,都可以通过一个既追求主体间的一致性又追求新颖性的共同体的理念来实现——一个杜威梦想的民主、进步、多元的共同体。如果一个人用我下面建议的方式把客观性重新解释为主体间性或团结,那么一个人就会放弃如何接触‘独立于心智和独立于语言的现实’的问题”。④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1,p.13.简而言之,“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对客观性的渴望并不是想要逃避自己所在共同体的限制,而只是想要尽可能多地达成主体间的一致,希望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指称范围”。⑤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1,p.23.与之紧密相关的是,“我们否认寻求客观真理是寻求与现实的对应,并敦促将其视为寻求尽可能广泛的主体间一致”。⑥Richard Rorty,Truth and Progress: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3,p.63.讨论自己与塞尔之间的争论时,罗蒂非常明确地表示:“塞尔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你不相信独立于心智的现实,你是否仍然可以相信并坚持客观性。站在我这一边的哲学家回答说,客观性不是一个与客体相对应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其他主体相结合的问题——除了主体间性之外,客观性没有别的东西。”⑦Richard Rorty,Truth and Progress: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3,pp.71-72.换言之,罗蒂眼中的客观性就是且只是主体间性。从表象实在的客观性转向主体间性的客观性,堪称实用主义的关键步骤。它专注于鲜明生动的实践,而对某种不变的形而上学对象则置之不理。这种转换既意味着参与对话者需要宽容对待彼此的意见,又意味着他们需要认真审视身临其境的繁复实践。所谓主体间性,是指通过自由与开放的讨论获得的主体之间的一致意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一致是“非强制一致”,“实用主义者将探究的目标(在任何文化领域)阐释为实现非强制一致与容忍分歧的适当混合(在该领域内,什么是适当的,通过试错来决定)”。⑧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1,p.41.换句话说,实用主义的客观性在追求一致性的同时,亦为差异性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在罗蒂看来,将客观性理解为主体间性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有助于重塑我们的研究内容,抛开那些过时的、没有意义的问题。譬如,某种表述是否符合实在、人类的世界之外有无非人的实体,如此等等。实际上,这种消解而非解决困扰前人问题的做法,着意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表述方式,恰恰彰显了罗蒂对其新实用主义哲学“治疗性”的定位。也即是说,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某一客体的描述多种多样,它们都不是与客体本质相互同一的描述。评判它们的优劣,要看其是否更好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适合社会实践的需要、是否为愈来愈多的人带来更大的幸福。二是有益于增强我们的敏感性,营造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抛弃了符合实在的客观真理之后,人们转而寻求的是最广泛可能的主体间的一致同意。于是,友好、宽容与可错主义精神将是每个参与者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他们将自己的忠诚给予为主体间性创造条件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除了自身的保护和自我完善、文明的维护和加强之外,不会有更高的目的”。①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1,p.45.
主体间性的客观性也引来了相对主义的尖锐批评。对罗蒂来说,区分、辨明相对主义的不同含义,可以让实用主义免受不少无妄之责。罗蒂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实用主义者应该反复申明:“没有任何柏拉图、康德和正统的有神论梦想的绝对,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观点和所有其他的观点一样好”,“它不意味着现在的一切都是任意的”。②[美]罗蒂著,黄宗英等译:《哲学、文学和政治》,第221页。这是一种加在实用主义头上的非常流行的、简单化的偏见。相对主义的第二种含义是“认为‘真’是一个多义词,即有多少证明的上下文就有多少意义的真”,罗蒂明确表示实用主义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因为真理在实用主义看来是单义词,“它同样适用于律师、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判断。给这些学科分配‘客观度’或‘强硬度’是没有意义的”。③Richard Rorty,"Science as Solidality",Johns Nelson,Allan Megill&Donald N.McCloskey(eds.),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The University of Wissconsin Press,1987,p.42.实用主义比较肯定的是相对主义的第三种含义,它“认为除了描述一个特定社会(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或另一个研究领域所适用的熟悉的证明正当性的程序外,对真理或合理性没有什么可说的”。④Richard Rorty,"Science as Solidality",Johns Nelson,Allan Megill&Donald N.McCloskey(eds.),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p.42.这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不过是主张我们的理解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实践、社会历史语境,没有任何中立的超越性基础而已。
三、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
罗蒂反对公度性的一面引人注目,经常被拿来作为负面的样板,至于他所反对的公度性是怎样的却被泛化或一概而论,而他主张公度性的另一面亦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略。因此,讨论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问题,需要厘清两者各自针对什么发言,不宜搅在一起以致于张冠李戴。其实,罗蒂反对的是认识论的可公度性,提倡的是阐释学的可公度性。具体来说,认识论代表了一种映现自然或表象实在的哲学知识观,渴望认识论即是渴望在限制与对照中获取知识,渴望能有一个赖以评判的抽象的最终基础。而阐释学则反对这种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想象,力主把认识论行为主义化,或者说,将认识论对接人们的实际行动,拉入生龙活虎的实践。可以发现,认识论与阐释学之间的这种区分,与传统的区分——前者分别以科学基础与人文科学基础为钻研对象——迥然相异。罗蒂赋予了认识论与阐释学以新的含义,对他而言,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⑤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学术史的维度上,阐释学这一概念包含着多个不同的流派,其中既有认识论的,亦有本体论的,它们表达着相异的诠释立场与主张。即是说,认识论阐释学亦是阐释学的内容之一。第二,有学者指出,罗蒂批评的上述认识论实质上是“现代性”或“现代的基础主义”认识论,这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论,而罗蒂并未将其与一般的认识论加以区分。因此,罗蒂的新型区分就遮蔽了如下事实:阐释学其实是新的认识论取代了旧的认识论,而并非对认识论本身的取代。换言之,阐释学从根本上说皆为认识论阐释学。参见[美]默罗阿德·韦斯特法尔著,吴德凯、何卫平等译:《韦斯特法尔:新康德主义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阐释学宛若认识论的“排毒药”。在认识论撤退或歇业之后留下的问题与文化空间,阐释学无意继续解决与填补。
罗蒂具体解释说,认识论认为“有一个永久中立的框架,哲学可以展示其‘结构’,即头脑要面对的对象,或约束探究的规则,是所有话语,或者至少是关于特定主题的每一种话语所共有的。因此,认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对给定话语的所有参与都是可公度的”,而可公度是指“能够根据一套规则,告诉我们如何在每一个诸陈述似乎冲突的点上,如何合理地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①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p.315-316.即是说,认识论的建立要求找到与他人共享的共同基础。罗蒂指出,回顾哲学的历史,这种基础有时被想象为在尘世之外,有时被想象为在人的内心,有时被想象为在语言之中,如此等等。尽管共同基础的形式有别,但它们都能为达成普遍的公度性提供有力保障。在认识论的构架中,哲学家扮演着文化监督者的角色。如同《理想国》中的哲学王那样,他知晓每一个人的所做作为、所思所想,知晓每一个人凭借的共同基础。因此,认识论所达成的一致不过是共同基础的外在表征,而共同体中的个体也由这种共同基础团结起来。相较而言,在阐释学的框架中,哲学家是对话中的协调者。“阐释学认为,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可能的对话中的线索,这场对话的前提是没有将说话者统一在一起的纪律矩阵,但只要对话持续,达成一致的希望就永远不会失去。”②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318.阐释学的一致不再依靠认识论钟爱的先在的共同基础,而是通过在具体社会中意见的充分对话与持续博弈来达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蒂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阐释学循环永不止歇。
如果说认识论的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意味着等级之分,可公度的是真正的客观的认知,而不可公度的则是主观的意见或趣味,那么,阐释学的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则只是对正常话语与异常话语的描述。“正常话语是在一系列约定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些约定包括什么是相关的贡献,什么是回答问题,什么是对答案有充分的论证或对其进行充分的批评。异常话语是指当某人加入到话语中时,不了解这些惯例或将其置于一边而所发生的事情。”③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320.对阐释学而言,一种话语之所以是可公度的,不是因为能够从中发现知识的本质,而是因为这种话语的实践较为长久,容易从中抽取共同的规约。依照这个衡量标准,不论是神学、道德还是文学批评领域,只要它有足够稳定的积淀,获得公度性就不是难事。相反,“在其他时期,例如福柯在近代欧洲思想史中发现的‘考古阶层’之间的过渡期,可能很难知道哪些科学家实际上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就像知道哪些画家注定不朽一样困难”。④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322.罗蒂将可公度与不可公度分别与正常话语与异常话语一一对应起来,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对异常话语的偏爱。如果说正常话语是传统话语,那么,异常话语则意味着创新话语,意味着超越时代的革命性思想。罗蒂特别提出,根据革命的哲学家对待不可公度性的不同态度,可将他们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仅把自己的创新话语与传统话语的不可公度性视为暂时的不便,并认为在创新话语被制度化之后,这一不便就可以自然消失。另一类是唯恐自己的创新话语被制度化,或者其创新话语能够与传统话语相公度。前一类哲学家以认识论为中心,是“系统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胡塞尔与罗素等。而后一类哲学家则以怀疑认识论为出发点,是“教化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后期海德格尔等。在罗蒂看来,“教化哲学不仅是异常的,而且是反应性的,仅当抗议通过某些特权描述的实体化而提出普遍公度的建议来结束对话的企图时,它才有意义”。⑤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377.也即是说,教化哲学反对的是正常话语的一劳永逸,或文化的独白、固化与僵化,反对的是普遍的公度性对创新话语有可能带来的阻碍或遏制,反对的是某一话语以透明地表征、再现现实来获得自己的特殊优越性。教化哲学强调话语是从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获取意义,强调话语的意义来自永不停息的对话过程,并致力于不断推进对话继续进行下去,从而不断产生新的再描述,而公度性就在这种对话与实践的过程中得以生成。
四、内在特征与关系特征
实用主义以治疗哲学自居,并未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历史主义等理论流派那样,衍生出一套备受关注的文学理论。尽管如此,实用主义对文学研究仍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其核心即是反本质主义。在接受拉格访谈时,罗蒂强调:“我认为,实用主义,无论是应用于民主政治实践,还是应用于文学批评,都恰恰是在准确地揭穿表象与实在、本质与偶然之间的区别。”①Richard Rorty,E.P.Ragg,Worlds or Words Apart?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for Literary Studies: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vol.26,no.2(2002),pp.369-396.正是通过反本质主义,“通过将一切事物视为贯穿始终的关系”②Christopher J.Voparil and Richard J.Bernstein(ed.),The Rorty Reade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0,p.425.,实用主义放弃了表象与实在之间以及类似的区分。只有理解了这种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才能真正明了罗蒂何以批判艾柯、赫什等理论家,何以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又何以常常被污名化。
罗蒂坦言,自己在阅读艾柯的小说《福柯的钟摆》时,发现艾柯对一些解码者——他们自命不凡地以为能从偶然中发现本质、能在表象的面纱下发现真象——冷嘲热讽,因此,他一度将艾柯当成了同路人。但当艾柯主张读者的意图映入眼帘时,他的同路感很快便烟消云散。因为艾柯严格区分了“阐释(interpreting)文本”和“使用(using)文本”,这让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殊难接受:“在我们看来,任何人对任何事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用它。解释某事,了解它,洞察它的本质等等,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而艾柯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仍然“坚持与赫希(E.D.Hirsch)在意义和含义之间的区别相类似的区别,即进入文本本身和将文本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之间的区别。这正是像我这样的反本质主义者所痛惜的那种区别——内在与外在、事物的非关系与关系特征之间的区别”。③Richard Rorty,"The Pragmatist's Progress",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Stefan Collini(ed.),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93-94.换言之,阐释不是从中找到某个深藏的内在本质,而是服务于特定研究目的的使用。对罗蒂来说,整个社会科学都应该这样阐释学化,从而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一旦涉及到使用,似乎就不可避免地会诱发随意阐释的棘手问题。但这种使用实际上不可能随心所欲,因为“任何事物,在被用于探究目的时,都是由一个意义之网‘构成’的”。④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Essays:1972-1980),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199.任何事物都是关系性的,没有任何非关系性的特征,它唯有在充当一个关系网络中的关系项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知识对象。如此说来,所谓的“使用”只能在纵横交错的意义网络中得以展开。不论是中规中矩的使用,还是惊世骇俗的阐释,都需要接受关系网络、意义网络的制约、把关与审核。
在关系网络中进行阐释,既适用于一整个文本,也适用于其中单独的一句话。这意味着不论是一句话还是一整个文本,都没有独立自足的意义,都或隐或显、或间接或直接地依赖于其他句子与其他文本。正因如此,当德里达“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句话被错误批判时,罗蒂强调“在其上下文中,它具有一种比敌意评论者通常赋予它的更具体和复杂的意义”。⑤Richard Rorty,"Deconstruction",Raman Seld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 Volume 8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74.也即是说,上下文或语境具有纠正意义偏差的能力与权限,这种纠正依赖的并非任何内在本性或本质之类的东西,并非潜藏在文本内部的先在意义,并非任何非关系性的本质性意义,而是作为文本关系网络一个个节点的比较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罗蒂所言的“上下文”与艾柯主张的“文本意图”既相似又不同。艾柯认为,证明一个文本意图的猜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来检验”。⑥Umberto Eco,"Overinterpreting Texts",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Stefan Collini(ed.),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p.65.而罗蒂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文本的连贯性在它被描述之前并不是它所具有的东西,就像我们将它们连接起来之前这些点不具有连贯性一样。”①Richard Rorty,"The Pragmatist's Progress",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Stefan Collini(ed.),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p.97.不难看出,同样都承认文本连贯性,但罗蒂认为它不是先在的,而是说它本身就是阐释的最后结果。因此,文本意图或文本连贯性不可能如艾柯设想的那样,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检验是否为过度阐释的标准。罗蒂对上下文的重视也再次说明,实用主义的使用或阐释绝不会走向放任自流。譬如,在当代的语境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的“小人”阐释为“小孩子”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但《论语》的上下文明显否定了这种理解。因为“小人”这一关系项总是与“君子”相对而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此等等。因此,“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中的一些理解,不见得就能顺利通过上下文或意义网络的审核。这并不妨碍阐释的多义性,虽然意义网络不会认可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淑女”阐释为野蛮霸道的女子,但却可以有选择地将美丽、年轻、温柔、优雅等诸多美好的品质加诸其身。
就整个文本而言,罗蒂认为“阅读文本是根据其他文本、人物、使人痴迷的人或物、零碎的信息或你所拥有的东西来阅读它们,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②Richard Rorty,"The Pragmatist's Progress",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Stefan Collini(ed.),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p.105.阅读不是和某个本质性的意义进行对照,而是借助现有的意义网络进行评价。或者说,意义就是关系网络暂定的配置,随着关系网络的延展,意义亦随之修订。因此,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应满足于“解释书籍的真正含义”或“评价被称为‘文学价值’的东西”,而应“花时间把书放在其他书的背景下,把人物放在其他人物的背景下”。③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80.换言之,文学批评就是在诸多作家作品之间进行比较与衡量。这种相互的、多向的重新定位与重新描述工作,在理论上始终保持着开放性,有助于在不断扩大、延展的视野中,在多重的关系网络中理解单一文本,从而获得更为立体也更为丰满的阐释。罗蒂的这种批评观或阐释观,使其自觉地与如下两种流行的批评范式相区分:一是“结构主义批评”,它相信更多地了解文本机制对文学批评至关重要;二是“后结构主义批评”,它认为发现或颠覆形而上学层级的存在必不可少。④Richard Rorty,"The Pragmatist's Progress",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Stefan Collini(ed.),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p.105.尽管了解文本的工作机制与形而上学等级秩序并非骈拇枝指,但知晓这些依然无法令人更接近文本的内在本质。如果说结构主义式的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落入了本质主义的窠臼,那么,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则是在反对本质主义的进程中表现得不够彻底,又因构筑自己的元叙事而加入了本质主义的队列。
五、结 语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阐释学反对表象与实在的本质主义区分,强调在关系网络中进行理解与阐释。这种反本质主义的阐释路径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彰显着后现代的交往理性。这一阐释学主张在对话中说服他人,将客观性理解为主体间性,它不会导致人们过度担忧的那般“怎么都行”。文本所处的关系网络既划出了阐释所能触及的弹性边界,约束着意义的生产,又配置了意义的暂时确定性。新实用主义阐释学可以为当前关于公共理性及公共阐释的讨论提供一些参照。
——意象阐释学的观念与方法》简介
——充满艺术的实用主义者Eva 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