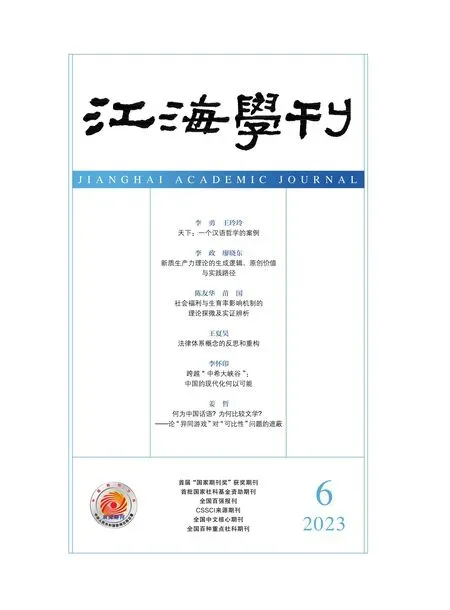停废科举之后
——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王亚飞
光绪二十九年(农历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廷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后文称癸卯学制),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近代学制,对近代中国的学术文教转型产生深刻影响。但正如周予同所说,癸卯学制“最足以引起吾人注意的,是对于经学的注重”,(1)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30页。既有研究已注意到其偏重旧学,尤其是强调经学的倾向,惟多从负面评价之。(2)在清季时人的表述中,常以“中学”(与西学相对)、“旧学”(与新学相对)指中国传统学问,不过“中学”有时是“中等学堂”的简称。为避免歧义,本文一律使用“旧学”,并不存价值判断。因该学制由张之洞主持拟定,其中的“《学务纲要》、经学各门及各学堂中国文学课程”更是由其“手定”而成,(3)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八,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73页。故时人对学章的异见和负面评议皆集矢于张之洞。后之研究者一般将癸卯学制的旧学色彩浓厚归咎于张之洞,这多少夸大了张氏在清季“新教育”中的话语权势,且有简化问题之嫌。
张之洞主持甚至直接参与拟定新学制,其间固然灌注了他的文教思想和学术理念,(4)许同莘就说癸卯学制“名虽学章,实公(张之洞)晚年学案也”。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八,第180页。但正如陆胤所提示的,既要“注重张之洞对政教事业的持久关怀”,又不可轻忽他“在‘京师’这一特殊环境下调停新旧的难处”。(5)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惟张之洞面临的难处和困境远不止于此。新式教育自兴办以来即弊端丛生,尤其是旧学在其中处于边缘位置,加之教授的效果不理想,使得学堂招致各方的批评,因此张之洞在新学章中安顿中西学时,必须尽力“调停新旧”;而清廷中央的办学方针,也是左右“新教育”进程的重要因素,其“旧学不可弃”的办学旨趣制约了新学制的中西学配置,却为既存研究相对忽略。
张之洞在厘定新学制时,试图将兴学堂、停科举二事并举;清廷在颁行癸卯学制的同时,也奏准了《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可见学堂与科举的关联。而目前关于停废科举的研究,往往忽略一个重要的关节:作为文化载体的旧学在科举罢除后的学堂时代如何传承?(6)既有关于停罢科举的研究多从以下角度切入:地方督抚和中央枢臣的合谋;清廷在制度层面设计了诸如保留举贡优拔生员考试、奖励学堂出身、为士子宽筹出路等善后措施;在趋新士人及其掌控的舆论鼓噪下,形成科举必废的强势意见等。毫无疑问,上述面相皆不同程度推动了科举的寿终正寝,惟忽略了学堂与科举互动的一面。相关研究可参阅: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戴鞍钢:《清末新政与科举停废》,《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2期;张仲民:《“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等。这不仅牵涉科举的罢废,也关乎学堂的兴办。如何安顿旧学实际是科举与学堂之争的焦点。职是之故,每每当清廷修订或颁行新的学制章程时,朝野新旧各方均注目于旧学各科的课程设置,张之洞拟定新学制也无法回避安顿旧学的问题。
在清季激进趋新已成主流的思想气候中,张之洞仍相当重视经学、“中国文学”等旧学,并将之置于显要位置,看似逆时代潮流而为,实则诊断出科举与学堂之争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在新制中提升旧学的比重,不失为当时调停新旧的务实之举。对上述相关问题的检讨,不仅有助于理解张之洞在规划新学制的旧学教育时的苦心和用意,又能从教育建制转型视阈下学科和知识衔接的层面审视兴学堂与停科举的勾连,从而增进对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和科举停罢进程的认识。
清季办学的中西纠葛
清末士人在面对国家的衰弱时,普遍认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7)张謇:《柳西草堂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四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6页。正如严复所说,自“中国维新以来,他议或有异同,乃至兴学,无贤不肖智愚,万喙一声,皆以为不可更缓”,(8)严复:《复旦公学募捐公启》,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形成了空前的办学共识。“新教育”既然承载着救亡图存的重任,于是兴学堂的同时废科举理应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和抉择,但实际上,质疑“新教育”和反对停罢科举的声音也同样弥漫朝野。这很大程度上皆与如何安顿中国传统旧学有关。若此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影响新学制的学科构建和知识配置,而且还整体制约从科举到学堂的转型。
当时趋新之风颇浓,叶昌炽即说“举世竞谈新学”,(9)叶昌炽著,王季烈编:《缘督庐日记钞》第3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甚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之势。(10)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1904年第3号。在这一风气的推助下,新式学堂亦走上偏重西学的途辙。以外语为例,当时的诸多学堂唯外语是尚,出现“都会之区,通商之埠,外国语学校到处林立”的局面。(11)《论中国教育宜急图改良之法》,《大公报》1904年12月10日,“论说”,第3版。不少办学者甚至认为,“西史”“地理”等西学,也“不过为练习方言起见”。(12)按:方言即外语,参见《痛哭中国学界之前途》,《大公报》1905年2月26日,“论说”,第2版。相形之下,学堂普遍不重视旧学。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湖南武冈的一位学生认为学堂的经学课程钟点甚少,每星期“仅占一次”,导致学生“虽云毕业而大旨未窥十一”,如此下去,“假如科举即废,学堂遍兴,天下之人才取于学校,天下之师范半出于大学堂,十年之后,中国之经学愈亡而不可复矣”。(13)李钟奇:《上学务大臣条议》,《湖南官报》1904年第603号,“专件”。学堂中的旧学被西学严重挤压,导致教授效果不理想。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湖北学务处总办郑孝胥在“考学堂汉文”时,发现学生“几无能成篇”。(14)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20页。
由于中西学的比例偏颇,致使时人对学堂有“专重西学,不重经学”的负面观感。(15)《科举不废之原因》,《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1903年10月4日,“纪事·内国之部”,第224页。学堂被斥为“洋学堂”,入学者则被目为“洋学生”。(16)《论学校亟宜注重国文》,《申报》1905年4月6日,第1—2版。山西士人刘大鹏甚至把学堂学生称为“外洋各国之民”。(17)刘大鹏著,乔志强标点:《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以“洋”冠名学堂和学生,适表明新学大行其道而旧学边缘化。蒯光典对此批评道,“人知学校之宜讲西学,而不知其必先中学也”。(18)蒯光典:《金粟斋遗集》卷六《议兵》,《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换言之,讲西学几乎是时人的“常识”,旧学则被视作不急之务而被轻忽。学堂本是承载图存救亡的希望所在,惟其办理不善,使得士人颇难取舍。曹元弼注意到时人对学堂的这种复杂心态:“方今扶危救否,发愤自立,莫急兴学。而一或不慎,又适以速天下大乱。抱薪救火,愈甚无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19)《曹元弼与黄绍箕书》(时间不详),俞天舒辑:《黄绍箕集》,《瑞安文史资料》第17辑,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版,第345页。
办学出现弊端,不仅使学堂招致负面观感,还影响士人对停罢科举的态度。学堂办理不善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他们担心罢废科举专重学堂将有“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的流弊。(20)张之洞:《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间,御史李芍华在向清廷奏递的条陈中,“力陈学堂之弊,万不足以得人才,且详陈科举之不可废”。(21)《大公报》1903年4月5日,“时事要闻”,第2版。三月,在京师大学堂教授史学、舆地的屠寄亦表示,“国家不变法,不废科举,学堂难于办得好”。(22)《寄(屠寄)致竹君(赵凤昌)》(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554页。同年闰五月初三日,陈黻宸在与孙宝瑄谈论“张之洞创议停罢科举”之是非时,认为“学校兴办不善,科举岂可骤废!”(2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册)(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三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81页。不难看出,学堂办理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停废科举的进程,而士人对学堂的非议多集中于其轻忽旧学。
而与此同时,科举有碍“新教育”的发展,几乎是时人的共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屡次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论及“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并请张氏“鼎力主持”废科举。(24)吴汝纶:《与张尚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37页。缪荃孙也因“科举不停,学校不兴”,而感叹“可惜时光”。(25)缪荃孙:《艺风堂书札·致金武祥(四十七)》,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2》,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在吴汝纶、缪荃孙的眼中,科举的存在阻滞了兴学的进程。在新式学堂弊端已初现的情形下,废科举与兴学堂之间形成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局。当时湖北学政胡鼎彝“考录遗才”时所命之题,或揭示出官方的两难:
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不废科举则学堂不兴,科举果可废欤?若专重学堂,则今日日本、上海游历学生猖狂悖谬,学堂又可恃欤?宜如何而去科举之弊、惩学生之奸,其策安在?(26)《命题卓识》,《申报》1903年9月24日。
尽管清廷已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布改书院、设学堂的上谕中,认定“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且从逻辑上言,“废科举、兴学堂,似宜人材辈出矣”,但学堂并未带来明显的“自强效益”,所见所闻反而是学堂办理的种种“不善”。尤其是“学子轻浮之习,比前较甚者,则以徒趋重新书,而置五经、四子书于脑后”,(28)郑观应:《答杨君弨伯、梁君敬若、何君阆樵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8页。这一当时普遍存在的“重西轻中”办学趋向,使得士人对学堂存有其偏重新学、荒废旧学的负面观感。
清季时人在面临学堂和科举的抉择时,实际是一种纠结而复杂的心态。在新学致用的主流认识下,中国旧学本已少有人问津,在新式学堂的传授情形也不乐观,若废科举而不对学堂的中西学比重进行调整,旧学势必进一步衰微。在旧学的安顿和讲授问题上,士人已对学堂形成负面观感,更因此而担心如遽废科举会为“舍孔孟而向西学”的风尚推波助澜。朝野士人对学堂办理成效的质疑和对旧学凋零的担忧,是后来张之洞在京修订学堂章程时遭遇的思想氛围。清廷在停废科举时也一度踟蹰难决,其考量之一即在于旧学的堪忧现状及其安顿问题。张之洞在拟定癸卯学制时的安排正切中了这个问题。
学堂课程不“远乎科举”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入京觐见,得旨应允,他于四月二十日抵京,直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出都。(29)张之洞此行入京,实抱着入参军机的希冀,但未能如愿,主持制定新学制,只“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学制的制定》,《河北学刊》2002年第6期。当张之洞尚在北上途中旅次于保定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即在慈禧太后面前“免冠顿首”,表示自己“有举学堂相让之意”。(30)《寄(屠寄)致竹君(赵凤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555页。张之洞抵京后,张百熙与另一管学大臣旗人荣庆于闰五月初三日以“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而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添派张氏会商学务。(31)张百熙等:《奏请添派重臣会商学务折》,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同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釐定”。(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9册(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日),第140页。荣庆也在当日记到,“学堂奏请派张督会商事务”。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日),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在湖北兴学有年的张之洞由此参与全国学务。张之洞修订的学章,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准颁布,是为癸卯学制。(33)应该指出的是,谕令只是要求张之洞会同两管学大臣修订学制,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下旬,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屠寄告诉赵凤昌,因张百熙、荣庆彼此不谐,“微有意见”,对学务均推诿不问,于是张之洞“独挥巨笔,改订章程,行且定矣”。《寄(屠寄)致竹君(赵凤昌)》(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560页。
在京厘定学制的张之洞以科举为兴学的障碍。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初致军机大臣瞿鸿禨的信中表示,“若非变通科举办法,稍示归重学堂之意,各省学堂安得大兴?”(34)张之洞:《致瞿子玖(十四)》(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九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6页。同年十一月,他在总结“奉旨兴办学堂已及两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时,更是将之归因于科举。张之洞指出,科举不停则士子皆以为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导致“人情不免观望”,“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35)张之洞:《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171页。科举为兴学障碍应是当时士人共同的观感。早在戊戌年间,即使声言“变法不能太骤”的翰林院编修徐兆玮却“独于学校一事,惟恐其不骤”,明确主张“非停止科举,不足以壹生童之趋向”。(36)徐兆玮:《与昭文令郁宪丞同年辞中西学社经董书》(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徐兆玮著,徐昂千点校,《虹隐楼诗文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6页。
而前引湖北学政胡鼎彝的考题中所言各种“学堂之弊”,同样成为“新教育”发展的障碍,张之洞对此也有洞见。当京师大学堂有学生致书湖北学生“会议生事”时,张之洞要求武昌知府梁鼎芬将原信速寄北京,以便查对笔迹,惩戒主事之人,并再三叮嘱梁氏要劝谕鄂省诸生“守法率教,专心力学”,以“保全湖北学生声名”,如此他在京即“有辞于排阻学堂诸人”。当时,东京、上海等地屡起“学潮”,京师大学堂“亦复嚣然不靖”,京朝官对学务“交口诟病,多方阻扰”,张之洞在京则极力与“当道诸公”斡旋,力劝“不可因噎废食”,以免“顽固者益得逞其阻力”,否则“天下学堂永无振兴之望”。(37)张之洞:《致武昌梁太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子刻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2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611—613页。
此时,张之洞力主将停罢科举和兴办学堂二事并举,但在二者之间,他明确以后者为重中之重。无论是停罢科举,还是剔除“学堂之弊”,皆是为推行“新教育”开道。旧学荒弃即为一种突出的“学堂之弊”,因此如若张之洞制定的新学制无法妥善安顿传统旧学,势必落人口实,停罢科举恐怕一时仍难以企及。如此一来,科举议废而不废,学堂谋兴而不兴,各方仍将在科举与学堂之争的牵扯中拉锯。反过来说,修订学章、规避学堂之弊也是在为停罢科举张本。正如关晓红所揭示,“只有减少兴学阻力,推进新式学务的发展,学堂育才取得显著成效,以此为前提,科举去留才会变得相对顺理成章”。(38)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01页。
前文已述,学堂办理不善,特别是“重西轻中”的办学趋向牵动着科举与学堂之争。新学制的中西学课程设置更是与此紧密相联。四川学政吴郁生即指出,若“使学堂课程远乎科举,则士不豫附;近乎科举,则其实无别于书院”。(39)《四川学政吴郁生奏请颁定学堂一定课程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82页。学堂课程的具体配置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同时处理好与学堂和科举的“远近”关系。对此,张之洞的思路是:学堂教育轻忽旧学已遭受士人的严重诟病,而科举又是推行“新教育”的阻碍,惟停废科举又会因担心旧学式微而引起守旧之士的激烈反对,但若新式学堂下旧学教育的目标和实际效果皆远优于科举时代,则既可减少维护科举者的理由,又能在相当程度上改观对学堂的负面评议,进而推动“新教育”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40)陆胤曾提示,张之洞坚持在新学制中增加经、史、“中国文学”内容,未尝没有为递减乃至停罢科举预做铺垫的用意(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第194页)。该思路对本文的写作颇有启发,但陆胤并未深入展开。更重要的是,张之洞重订学章时有意增加经史旧学的比重,既有借此减少停废科举阻力的目的,也有以此规避此前学堂轻忽旧学之弊的用意。张之洞曾公开表示,希望利用学堂这副“良药”,使“废科举一事自不费力”。(41)《大公报》1903年7月4日,“时事要闻”,第2版。若要毫不费力地废除科举,势必要妥善安顿好旧学。
秉承上述思路,张之洞在新学制中大幅提升经史旧学的地位和比重,并多次将修订新章的旧学教育作为停减科举的重要依据,而在述及癸卯学制的旧学教育时,更是以科举时代为参照,竭力彰显前者的目标和理想愿景皆远优于后者。这也就是吴郁生所提醒的学堂课程不可“远乎科举”。据朱贞研究,此前张百熙制定的壬寅学制“西”多于“中”,旧学并不显要,且经学的重要性也未得到体现,史学和文学的地位却有所提升;而张之洞主事时修订了壬寅学制中小学阶段的课时比重,经学课程明显增加,蒙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分别由1/6、1/6、3/37—3/38增加到2/5、1/3、1/4左右。(42)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张之洞的调整不可谓不大,不仅整体上提升旧学的比重,而且独标经学的地位,更创设经科大学,这在分科治学的癸卯学制中显属特异之举。除此而外,张之洞还对旧学的“讲读研求”之法有较此前更趋细密化的详尽设计。
在奏呈癸卯学制前,张之洞向军机大臣瞿鸿禨表示:
在不肯停减科举者,不过云学堂规矩未善,兴办未广,未必遽有人材,故不肯遽停科举。然现拟各学堂章程,注重中学根本,于防弊之法似已周密。(43)张之洞:《致瞿子玖(十四)》(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九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6页。
新学制“注重中学根本”正是反驳“不肯停减科举者”的重要依据。(44)张之洞在癸卯学制中通过强化管理、增加伦理教育等方式来体现其所谓“防弊之法”,也是力图彰显学堂“优胜”于科举,惟与本文讨论的主旨不甚相关,故对此不拟申论。而在大约同时的《请试办递减科举折》中,张之洞更特意指出:
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45)张之洞:《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171页。
张之洞原本试图将该折纳入新学制,但因枢臣意见参差而不果。(46)“本来《奏定学堂章程》中有《递减科举章程》”,但因诸枢臣对递减科举意见尚存参差,未尽一致,故张之洞决定将学章与《递减科举折》分别奏递,“科举单独附片,实源于此”(详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01页)。张之洞拟将《递减科举折》嵌入癸卯学制,正说明在京制定新学制的张之洞力图将罢废科举、兴办学堂二事并举,但最终分别奏陈,表明递减科举(进而废除之)在当时遭遇强大的阻力,这又进一步提示张之洞在学堂章程中提升旧学比重的“必要”。但该折仍在很大程度上与癸卯学制相互配合。张之洞在该折中之所以将新式学堂拔高到全面超越科举的程度,正因癸卯学制不仅“于中学尤为注重”,且对中学各科“包举靡遗”,实际上是力图从根本上否定科举继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又可消解科举停罢后“中学将无人肯讲”的疑惧。
在张之洞亲自拟定的《癸卯学制·学务纲要》中,“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条明确指出:
盖数十年来科目中人曾读“九经”而能讲解者,不过十分之二三。若照此章程(癸卯学制)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47)张之洞:《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3页。
在“学堂兼有科举所长”条也说:
凡诟病学堂者,盖误以为学堂专讲西学,不讲中学故也。现定各学堂课程,于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且讲读研求之法,皆有定程,较向业科举者尤加详备。查向来应举诸生,平日师无定程,不免泛骛,人事纷杂,亦多作辍,风檐试卷,取办临时。即以中学论,亦远不如学堂之有序而又有恒,是科举所尚之旧学,皆学堂诸生之所优为。学堂所增之新学,皆科举诸生之所未备。则学堂所出之人才,必远胜于科举之所得无疑矣。(48)张之洞:《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3—504页。
所谓“误以为学堂专讲西学,不讲中学”,适可与前文所述时人视学堂为“洋学堂”对读。张之洞针对此点立论,强调“科举所尚之旧学”,学堂无不优为。而张之洞放言“决无一荒经之人”“经学更可昌明”“学堂所出之人才,必远胜于科举”,多少有些悬想成分,意在通过夸大其词的方式塞反对学堂者和反对废科举者之口。从这种言说方式不难看出,张之洞意在通过标举“新教育”的优胜之处,以推动停罢科举,兴办学堂。
张之洞的苦心和用意并未逃过批评者的眼光。据在京参与学务的张鹤龄透露,张之洞与军机大臣王文韶因“裁减科举”一事而“大相龃龉”。(49)《张鹤龄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上海图书馆编:《盛宣怀档案选编》第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页。张之洞在初拟的奏稿中原本打算坦承王文韶的反对意见,但管学大臣张百熙却认为应删去“折内除大学士王某及与政务处王大臣会商意见相同两语”,可见在处置停废科举时的慎重。黄薇整理:《张百熙、瞿鸿禨往来书札(上)(113)》(时间不详),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对此,士人夏曾佑在报刊上发文称,张之洞力主废科举遭到王文韶的反对,却又在京师大学堂中添加“经史”课程,此举不过是将京师大学堂造成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翻版而已。(50)按:广雅书院为张之洞督粤时所办,两湖书院则为其在鄂督任上所办,均注重经史之学。他批评张之洞“有废科举之名,无废科举之实”,所谓“无废科举之实”,正是针对新学制中仍有经史旧学(且其比重较之前的学章有大幅提升)而言,他因此讥讽“竭力主持废科举”的张之洞与“竭力反对之”的王文韶实为“同志”,不必相煎太急。(51)夏曾佑:《论国家将以学堂为书院》(原载《中外日报》1903年10月6日),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在夏曾佑看来,张之洞一面主张废科举,另一面又在新式学堂中增加旧学课程的比重,显然互相抵牾,殊不知王文韶辈的意见才是理解这一吊诡行为的枢机。
除夏曾佑外,当时的趋新舆论也说癸卯学制“自初等(小学)至高等(小学),除《尔雅》、‘公穀’外,十三经已具其十。虽向之科举时代,专门读经者,中才亦所不及也”。(52)《教育杂谈》,《直隶教育杂志》1906年第19期,“杂谈”,第1A—2B页。宣统元年(1909),顾实更是借用“日人某诋我学堂为科举之变相”来抨击癸卯学制对读经的重视。(53)顾实:《论小学堂读经之谬》,《教育杂志》1909年第4期,“社说”,第58页。“以学堂为书院”“学堂为科举之变相”这些来自“对立方”的诘责,适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张之洞制定新学制时的思路和做法。在面临学堂课程“远乎科举”与“近乎科举”的两难抉择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旧学不可弃”与新学制的拟订
当停废科举之争尘埃落定后不久,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上发表文章,主张亟应修订颁行不及两年的癸卯学制。尽管此时罗振玉对新学制的批评实已相当尖锐,认为“章程早改订一日,早得一日之益”,不过他仍肯定张之洞拟定癸卯学制时“因科举未停,故窒碍之处甚多,其苦心结构,在科举教育并行之时,已称尽善”,(54)本段及下段关于罗振玉的论述,皆出自罗振玉:《学部设立后之教育管见》,《教育世界》1905年第110号,“论说”,第1—2页。实际上对张之洞面临“窒碍之处甚多”的处境抱有同情之理解。
罗振玉认为科举未废时本“已称尽善”的癸卯学制,不适宜于“专一育才于学校”的学堂时代。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得知“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后,虽也承认“科举在今日诚可罢”,但仍认为癸卯学制“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否则“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55)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罗、恽二人皆主张重订癸卯学制以因应后科举时代的学堂教育,但取向和思路却截然不同。
比较而言,罗振玉和恽毓鼎的意见显然一新一旧。张之洞通过拟定新学制以推动废科举、兴学堂,与趋新的罗振玉大体上为同道,只是罗氏走得较张之洞更远。有意思的是,在罗振玉看来还不够“新”的学堂章程,于恽毓鼎而言还不够“旧”,即使癸卯学制已全面地大幅提升经史旧学的比重,恽氏仍从“圣经贤传”的角度批评学堂章程“未妥善”。退一步说,如若张之洞在修订学章时并未提升旧学的比重(或提升的比重并未如此大),其将招致恽毓鼎辈的批判无疑要激烈得多,不难想见,新式学堂的兴办进程和罢废科举的历程也将更加曲折多磨。
显然,在无论是趋新者还是相对保守派看来,癸卯学制与其心中的目标均有不小的距离。当更趋新的一方逐渐掌握话语权势后,张之洞为推动教育改革而在新学制中对旧学做出的苦心安排,不但未得发覆,反而成为负面评议的集矢所在。实际上,自《劝学篇》刊行后不久,张之洞在趋新士人及其掌控的舆论中即愈来愈呈现出“守旧”的形象,而有关其晚年由趋新转向保守的评议对时人及后之研究者影响相当深远。(56)参见郭书愚:《“新旧交哄的激进时代”:以张之洞和存古学堂的“守旧”形象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张之洞在京修订学章时,对壬寅学制原拟旧学课程方案的重大变革,尤其是他对经学的注重,正是时人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也是其“守旧”形象的重要“证据”和渊源。但若以中立之心看,张之洞对癸卯学制的旧学课程实付出了极大心血,其力图构建一个远胜于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便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存在的意义,进而减少“新教育”推行的阻力和压力。此举虽从旧学入手,且对旧学有一定程度的偏重和倾斜,但若就其最终的落脚点和隐伏的理想愿景而言,或许可以说张之洞是在走“曲线趋新”之路。
张之洞此次在京为修订学堂章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门人许同莘就说,癸卯学制的“《学务纲要》、经学各门及各学堂中国文学课程,则公手定”。(57)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八,第173页。曾为张之洞幕僚的王国维也说,“今日之《奏定学校章程》,草创之者沔阳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而其中的经学、文学二科更是张之洞的“最得意之作”。(58)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0—31页。这在当时已广为人知。目前所见时人对学章无论正面或负面的评议皆系于张之洞一人。有意思的是,负面评议恰由张之洞的“最得意之作”而起。后之研究者一般将学章注重旧学的倾向完全视为张之洞的主张,这多少有些过于夸大张之洞在清季“新教育”中的话语权势。
学务作为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政事”之一,且“新教育”潜在的弊端和停罢科举可能导致旧学的进一步式微和士人的疏离,皆紧密关系到清廷政权的稳固,是当权者们极为关切的问题。在处理罢废科举与兴办学堂的问题上,慈禧太后持相当审慎的态度。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张之洞在觐见时即向慈禧太后“力陈科举不废学堂不兴之说”,她当时未置可否,而是谕令张之洞“下去会同大学堂拟一章程来看”。(59)《大公报》1903年6月10日,“时事要闻”,第3版。显然,她有所顾虑,如若在学堂章程尚未规划周全时即遽然停废科举,极有可能引起朝局震荡,于己不利。同时,科举的罢废和学堂的兴办在很大程度上以完备的新学制为转移。张之洞修订学堂章程时面临的压力可以想见。
至同年六月底仍有消息说,对于张之洞“屡争废科举”的举动,“皇太后均默然”。(60)《大公报》1903年8月21日,“时事要闻”,第2版。当时学堂章程尚未拟定妥善,应是慈禧太后对“争废科举”一直默然以对的重要原因。这些见诸报端的消息绝非无稽之谈。就在清廷颁行癸卯学制后的第二天,曾对学制章程“参酌审订数次”的张鹤龄,在一封致盛宣怀的私函中透露:“只因裁减科举一节,王相(文韶)持之甚坚,故迟迟至今始奏上耳。”(61)《张鹤龄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上海图书馆编:《盛宣怀档案选编》第91册,第402页。可见科举问题始终是牵扯新学制出奏的症结所在。后来张之洞竭力彰显癸卯学制注重旧学的特点,并将学堂与科举进行对照,强调学堂的旧学教育目标和前景皆远优于科举,如果考虑到慈禧太后的上述态度,张之洞此举既有针对维护科举者(如王文韶)及“排阻学堂诸人”的用意,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对慈禧太后上述顾虑和担忧的正面回应。
就在张之洞紧锣密鼓地草拟全国学堂章程时,舆论传出慈禧太后“于万机之暇,颇注意五经、四子等书”的消息。她要求将《书经浅说》绘图,用官话演说《孟子》,以便颁给学堂作为课本。(62)《注意经书》,《大公报》1903年9月30日,“时事要闻”,第3版。慈禧太后注重经书的举动,在科举与学堂之争相持不下时实有表态的作用,意在强调中国传统学问,尤其是经学在新旧教育制度转型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久历宦海的张之洞身在京城,对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态度和举动应有所察知。进而言之,张之洞在京主持修订学章,慈禧太后对旧学的态度无疑是其重要的考量。
实际上,“旧学不可弃”正是当时清廷最高统治者兴办教育的重要指针。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在召见即将赴日考察学务的湖北提学使黄绍箕等人时,就明确向其强调“旧学不可弃”。黄绍箕与张之洞颇为接近,次日即将在京召见情形悉数电知已回湖广总督本任的张之洞。(63)《京黄提学司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发、亥刻到),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106册,第632页。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十六日,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在京请训时,慈禧太后同样告诫傅氏:“学科自以中国学问为重,其洋文、算学等,不过稍求新知识,并未尝有大用处。”(64)傅增湘著,王会庵整理:《藏园笔记二篇》,《近代史资料》总8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页。慈禧太后对“洋文”“算学”等新学的定位和看法姑置不论,至少她明确认定学堂当以“中国学问为重”。这与她此前对废除科举的审慎、对经书的注意是一贯的。不难看出,慈禧太后对经史旧学的态度相当明朗而坚定。郭书愚在考察清季官方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时,也已经注意到慈禧太后对传统旧学的关注,与当时学部“较浓郁的趋新氛围”有明显距离。(65)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因此,或可退一步说,如果张之洞所拟癸卯学制对旧学的安顿远不及慈禧太后的预期,实则很难得到她的首肯而迅速颁行全国。易言之,慈禧太后对癸卯学制的旧学教育规划大体是肯定的(至少不反对)。
因此,当时人及后之研究者多将眼光聚焦在张之洞身上,进而把“新教育”在建制层面对旧学的注重完全归咎于张之洞时,实则忽略了清廷中央的兴学取向对张之洞的影响。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癸卯学制对旧学的注重及其对中西学的配置,也是慈禧太后等清廷统治者的办学态度和观念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张之洞的影响从癸卯学制中抹去,实际上,其中的不少建制皆延承着张之洞早年的办学努力和学术取向。(66)郭书愚、王亚飞:《“中体西用”之外的“参酌中用”:张之洞办学实务的前后沿承与嬗替》,《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癸卯学制之所以能冲破各方阻力,得以奏准颁行,显然与慈禧太后的肯定和支持分不开。或可说,其中隐含的办学倾向是清廷中央高层与张之洞等学制拟定者共同分享的兴学观念。
余 论
张之洞在癸卯学制中大幅提升旧学的比重,时论有谓其“以学堂为书院”“学堂为科举之变相”,后人也多视之为“守旧”“封建”。但实际上,此举或可视为当清季的教育改革在科举与学堂、新学与旧学纠缠难解时,张之洞的“因病而药”。当张之洞拟定新学制时,兴办有年的新式学堂“专重西学,不重经学”,被时人指为“洋学堂”,学生也被呼为“洋学生”;士人则担心科举停罢后“中学将无人肯讲”;清廷中央也秉持着“旧学不可弃”的办学旨趣。而大约一年以前,当张百熙奏进壬寅学制时,当轴诸公“多吹求”其中的“各种新学名目”。(67)《大公报》1902年8月26日,“时事要闻”,第3版。“新多于旧”的壬寅学制甫一颁布即遭到各方的反对,很快被弃置,这才有张之洞重行厘定之举,可谓殷鉴不远。如若不对此进行调适折中,张之洞难免要步张百熙的后尘。
提升旧学(尤其是经学)的地位和比重,看似逆势而为,实则诊断出科举与学堂之争的症结所在。张之洞的苦心安排,是以退为进的“曲线趋新”,也是调停新旧时的务实之举。何怀宏注意到,科举废除时各方“虽有种种忧虑担心,当时社会上总的反应却大致接近于是无声无息”,“似乎这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覆亡”。(68)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5页。就当时而言,张之洞所拟新学制“注重中学根本”,“于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建制极大地消解了科举停罢时的种种忧虑。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张之洞本一贯秉承“国家”高于“圣教”的取向,而癸卯学制作为一种落实其“中体西用”观念的制度,也把重心放置于“西学为用”上,进入学堂体制的旧学经其整合后,缩减了大量内容,显非传统故态。因此,张之洞是“以简化的方式保存传统”而非对旧学照单全收。(69)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1—141页。新学制中规划的旧学教育,已不可与其原本的样态同日而语,而是竭力采取“守约之法”,用意也在为可以“致用”的新学腾挪更多空间。也即是说,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的壬寅学制有大幅提升,但这均建立在学堂教育整体上以西学为重的前提之上。时人和后来者并未认识到张之洞的苦心孤诣。
尽管今人在述及清季的教育改革时,多将兴学堂、废科举并称,但在研究中难免顾此失彼,将之打为两橛。实际上,停科举与兴学堂是一体之两面。张之洞将兴办“新教育”和停罢科举并举,通过大幅提升经史旧学的地位和实际比重,既能借此减少全面兴办学堂的阻力,也可以此塞反对废除科举者之口。此举确曾在推动停废科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若由此引申来看,检讨清季颁行的历次学堂章程时,将停罢科举的具体进程纳入其中,注意其间的相互勾连,或许会给研究者理解学制拟定者对旧学的态度、偏重程度及其在学制中具体配置的差异提供新的视角。具体而言,在考察壬寅学制偏重西学而不重旧学的问题时,就应注意到其时主持者张百熙尚未真正虑及以学堂完全取代科举。易言之,张百熙并未打算把壬寅学制的出台作为科举停罢的依据,而是视之为科举的补充。二者并非替代关系。既然“科举与学堂并行”,科考作为“成功的阶梯”自可继续引导士子研求旧学,学堂教育则可更多偏向可以致中国于富强的西学,经史旧学也就不必占重要位置。
其实,张百熙对停废科举的态度是相当明晰的。当他受命为管学大臣后礼请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就对吴氏说:“今时虽孔孟复生,亦不能废科举。”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科举用策论,与学堂固一条鞭也”,(70)按:清廷已在此前(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发布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上谕。如此则已无废科举之必要。(71)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汝纶)年谱》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3),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壬寅学制规定逢乡、会试之期,学堂学生可请假与试,恰为入学者在科举与学堂之间的左右逢源开了方便之门。(72)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京师大学堂学生纷纷赴开封会试,在堂学生不过三十余人,“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学堂近闻》,《大公报》1903年9月10日,“中外近事·北京”,第3版。这进一步可佐证张百熙以学堂为科举之补充的思路。壬寅学制不重旧学,或可由此得到部分索解。
也就是说,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时,虽为学堂教育的发展规划了蓝图,但并未走到废除科举以“专重学堂”这一步。而后来张之洞修订学章时,则明显比张百熙走得更远,他努力以纳科举于学堂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惟当时新式学堂普遍偏重西学,科举停废后“中学将无人肯讲”的忧虑弥漫朝野,因而张之洞不得不在新学制中提升旧学的比重以因应之,这即是罗振玉所谓的“苦心结构”。探讨科举与学堂之争,要时刻注意二者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勾连,并将之“见之于行事”到具体的研究中。
需要说明的是,在趋新方面癸卯学制虽远不及此前的壬寅学制,但与西潮冲击前旧学涵盖的范围及其研求之法相比,进入癸卯学制的旧学内容已属“损之又损”,讲授方式也力求有别于过去。(73)张之洞曾在戊戌年间的《劝学篇》中系统阐述研读旧学的“简约之法”,但若将之与癸卯学制的相关内容对读,则会发现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在西学为重的时势下,简化旧学以传承之是其戊戌以降一贯的思想。尽管如此,新学制的颁行仍未挽回旧学式微的颓势。约两年后,张之洞即承认“奏定学章虽声明各学堂均须注重经学、国文,然风气所趋,科学既兴,旧日文学已渐就轻忽荒疏,十年以后中学必致颓废冺灭,实有道丧文敝之忧”,(74)张之洞:《致京学部荣中堂、严侍郎鉴并转孙中堂、张冶秋尚书》(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巳刻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37册,第451—452页。清廷因此又走上修订学堂章程的老路。
宣统年间,学部对癸卯学制中小学堂的课程进行了两次调整,惟其方向不是继续提升旧学的比重而是相反。(75)整体上如此,当时的调整相当细密,如旧学内部也有升降,尤其是经学的显要地位不再,而国文则明显上升。这样的调整显然与张之洞的上述忧虑相悖,而此时他为保存国粹也另辟蹊径,转而乞灵于专门性质的“存古学堂”。不过,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际,“救亡若救焚矣,生命第一,财货次之”,“周鼎商彝”“秦碑汉石”虽“非不重可宝也”,然其重要性远不及“生命财货”,(76)补青:《论教育思想之趋势》,《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6期,“论说”,第15—16页。故张之洞的反复擘画,难敌风气所趋,在当时终究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而与此同时,经过分科教学的条理后,旧学虽仍能在新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已“从整体一块被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科目课程”,其原有形态和价值难以维系。(77)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并进的问题,仍值得后人继续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