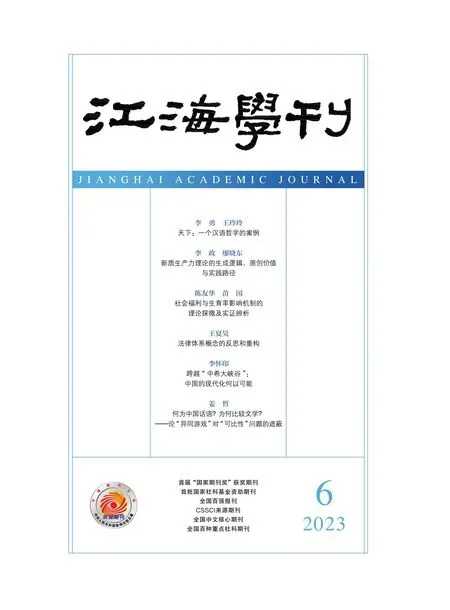天下:一个汉语哲学的案例*
李 勇 王玲玲
“汉语哲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韩水法认为,“汉语哲学的任务不是让哲学说汉语”,同时“汉语哲学主要不关涉实践领域的问题”。(1)韩水法:《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而孙向晨认为,汉语哲学是“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以及特有的概念规范”而进行的哲学活动。(2)孙向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汉语哲学比“中国哲学”这一概念要薄,不仅仅处理自先秦以来的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中国佛学等传统中国哲学史所处理的问题,还要处理中国哲学史以外的问题,诸如汉语本身的特征所引发的哲学思想。同时,汉语哲学又要比“中国的哲学”这一概念要薄。因为汉语哲学不仅在中国发生,还在任何讲汉语、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地方发生。此外,汉语哲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汉语的哲学”或者“用汉语表达的哲学”。很多在用汉语研究和写作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虽然确实是在用汉语这种语言研究诸多西方哲学的问题,诸如形而上学或者认识论上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外语的翻译的话,比如直接转译成英文,我们可能会发现,翻译出来的论著,估计也没有太多汉语思想的痕迹。
基于以上厘清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和“汉语的哲学”等概念的困难,本文认为,能够表达汉语哲学这一创新思路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出一个汉语哲学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说明,来自汉语语境的中国的哲学传统,有一些思想资源是独特的,可以凸显这个哲学传统面对人类普遍的问题,提供普遍的、有效的和独特的解决思路。当然,对这种案例说明的贡献可能有强的和弱的两种解读。强的解读可能会认为,这说明汉语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或者哲学方法,区别于诸如德语哲学、法语哲学、英语哲学等以语言划界的哲学传统,以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以区域划界的哲学传统等。弱的解读可能会认为,这至少说明汉语哲学传统中有独特的思想资源可以回应普遍的哲学问题。而如果汉语哲学中有诸多类似这样的思想资源的话,至少意味着这种哲学传统有其整体的独特性。
大多数提倡汉语哲学的学者力推对汉语哲学的强的解读。本文认为,只是根据案例来分析汉语哲学,进而为汉语哲学提供弱的解读,也可以为汉语哲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辩护。目前广义的汉语哲学研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例有“仁”“道”“天人合一”“民本”“天下”等诸多观念。本文选取“天下”观念,试图揭示该观念在广义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争中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对“天下”的讨论路径对其他汉语哲学的概念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对“天下”观念的讨论是在全球正义的背景下涌现的。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是过去几十年中关于全球正义和国际正义讨论的一个焦点。支持世界主义的学者认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国际秩序没有办法解决诸如全球气候变暖、饥荒和自然灾害等全球性的问题,更没有办法维持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支持民族主义的学者认为,剥离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任何构想都是乌托邦。而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确实呼唤某种关于全球正义和国际正义的新的理念。“天下”作为这样一种理念,有其特定的吸引力。本文将首先介绍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核心论证,指出其各自面临的问题,再引入“天下”的概念,并论证为什么天下可以为全球正义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并不是一个现当代的观念。“作为世界的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第欧根尼。近代哲学家康德求助于这个概念来构建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当代的学者诸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等人对此进行了系统性阐述。
世界主义与国际正义(international justice)和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这两个概念相关。国际正义一般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当有国家之间发生纷争的时候,国家利益的概念起了核心作用。与之相对,全球正义通常不是以国家为主体思考正义问题。全球正义处理的是公民个人是否对国界以外的他人承担某种类似于对同胞的责任。著名的后果主义者,诸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彼得·安格尔(Peter Unger)等人认为,我们面对那些国界以外的人的紧急需求,需要承担类似面对国人时的道德责任。
世界主义更多是和全球正义的概念相关,关注我们如何把自己看作一个国际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社会团体、民族、国家或者种族中的一员。世界主义者更多不是直接讨论如何解决全球饥荒或者地区战争等应用型问题,也不是讨论如何构建全球秩序等制度性问题,而是为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提供某种背景性的道德视角。比如在当下的欧洲难民问题上,因为世界主义者的平等主义承诺,对难民的接收就变成了一个基本的预设。因此,欧洲是否应该接收难民的讨论在世界主义者看来事实上被转换成了欧洲该如何更好地接收难民,以及如何在众多欧洲国家之间分配难民数量的问题。
世界主义的具体理论很多。不过,世界主义的众多理论似乎都呈现了涛慕思·博格(Thomas W. Pogge)所总结的三个特点:个人主义、普遍性和一般性。(3)Thomas W. Pogge, “Cosmopolitanism and Sovereignty”, Ethics, Vol.103, No.1, 1992, pp.48-49.世界主义强调个体而非民族国家才是全球正义关注的终极主体。同时,这种关注是普遍的,即宗教、性别和种族不应该造成任何差别。再次,这种关注是一般性的,即国界和民族身份不构成特殊性,国界内外的民众享受同样的正义标准和权利。
另外,对世界主义的辩护也有众多论证。如果对这些辩护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道德的和政治的。从道德的维度进行辩护,第一种路径强调人性的共同特征。诸如努斯鲍姆论证,人的尊严是没有等级的,是平等的。所有具有“基本道德学习和道德选择能力水平”的人都是具有尊严的。(4)Martha C. Nussbaum, The Cosmopolitan Tradition: An Noble but Flawed Ideal,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9, p.2.努斯鲍姆通过承认人的基本道德能力肯定普遍的人性和人的尊严,进而推出所有人都应得到这种尊严,国界不应该成为阻碍这种普遍尊重的障碍。第二种道德的辩护路径强调后果。彼得·辛格等人通过功利主义的预设,认为应该救助那些有紧急需求的人,国界、距离等都不应该是道德相关的考量。(5)Peter Singer,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7-158.第三种道德的辩护路径使用权利为基础的义务论论证。亨利·舒尔(Henry Shue)论证地球上每个人的生存权和人身安全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而世界主义恰恰是对这种权利的认同和承诺。(6)Henry Shue, Basic Righ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8.
除了从道德的维度对世界主义进行证成之外,还可以从政治的维度对世界主义进行辩护。政治的维度强调构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可以解决长久以来的战争、极端贫困、全球气候等问题。诸如博格论证,如果我们把自己对某一个区域性共同体的认同置于唯一重要的位置,肯定不利于以上威胁整个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的解决。(7)Thomas W. Pogge, “Cosmopolitanism and Sovereignty”, Ethics, Vol.103, No.1, 1992, pp.61-62.而且事实上,当下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已经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不正义的伤害。出于正义的要求,我们也应该接受世界主义的承诺。(8)Thomas W. Pogge, “Priorities of Global Justice”, Metaphilosophy, Vol.32, No.1/2, 2001, p.17.
世界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道德理念,确实非常美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范导性作用,而自古以来的大部分哲学家也都支持世界主义。不过世界主义也面临很多重要的反驳。
首先,世界主义违背了基本的人性。爱有差等是一个人性的基本事实。我们所有人都天然地关爱自己的家人、家乡和民族。世界主义要求我们忽视人性的这种基本事实,走向一种爱无差等的共同体。人性事实上对我们的道德有天然的限制和约束。违背人性事实的规范性是难以维系的,也无助于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其次,世界主义所坚持的某种全球范围的平等分配的实现依赖一种全球性的强制机制。分配正义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要求强力机构的存在。比如通过税收进行二次分配,就预设了税收机构及其成功履行功能的机制。但是,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税收机构和机制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一个全球政府的存在,强制机制便是空中楼阁。
最后,世界主义建立在特定的理想理论的基础之上,其对美好世界的描绘更多是一种乌托邦的理念。这种打破国界和区域差别的平等主义的世界观,脱离了人类社会的现实,无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纯粹是一种无根的理性设计,是一种空想。任何规范性的理论都应该建立在对人类现实和历史的承认的基础上。
总的看来,这些反驳的立足点更多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观。本文第二部分将重点讨论世界主义的对手——民族主义的观点和论证。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过,在与世界主义相对照的语境中,民族主义主要承诺我们对自己民族或者国家的某种特殊的责任。根据民族主义的代表学者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的论证,这种特殊的责任有如下来源。首先,民族认同是一个人的重要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构成了一个人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具有特殊的规范性价值。其次,民族认同也是个人社会福祉的重要部分。民族和国家边界是一个人享受特定福利的重要依据之一。再次,民族认同也是民族自决的重要依据。而民族自决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9)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0-11.
迈克尔·布莱克(Michael Blake)和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从分配和强制的意义上辩护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布莱克论证,分配正义的平等原则只有在一个强制的系统中才适用,而这种强制的系统就是国家。因此分配正义的平等原则只有在国家中才适用。而民族主义就是去捍卫这种意义上国家的重要性。(10)Michael Blake, Justic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04-105.内格尔认为,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互惠的共同体,而这也决定了其基本结构的社会规则具有强制性。同时,这种强制性可以保证免除随意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分配正义恰恰是这种强制性所实现的其中一个功能或者目标。(11)Thomas Nagel,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33, No.2, 2005, pp.128-129.
如果世界主义者真的关心所有人事实上的平等,按照以上民族主义的论证,至少在分配意义上要实现某种平等的话,这种分配只能在国家内部实现。在缺少强制力的国际社会中,承诺任何意义上的平等主义都是纸上谈兵。因为分配所涉及的关于税收等的强制手段,在世界主义的语境中是缺乏的。
不过,民族主义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民族主义似乎在分配正义上持相互冲突的观点。在国内,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坚持某种形式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强调民众之间的平等。但是,在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者似乎否定了这种分配正义,忽视了跨国界的民众之间的不平等。这种分配正义观念上的不一致,似乎蕴含了对平等的某种工具主义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分配平等就不具有内在价值。但是,大部分民族主义都宣称分配平等具有内在价值。
其次,当代的民族主义者一般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但是,这意味着那些国界之外的人权受到侵害的群体的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不过,民族主义者强调国界的规范性,他们无法或者不认为应该突破国界去保护那些个体的人权,因为对方国界决定了对方的某种民族自决的权利。很明显,民族主义者对国界的规范性的坚持和他们对人权普遍性的坚持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再次,现代的民族国家似乎既是全球问题的源头,也无法为一些棘手的全球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区域战争、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等,在目前的民族国家体系下,似乎没有出路。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对国界的规范性和民族自决权利的坚持,无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当然,前面关于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和人权的普遍性方面的困难,更多是纯粹理论性和概念性的。而解决全球问题的困难更多是实践性的。
天 下
如果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相互对立的理论难以令人满意的话,那么是否存在其他的全球正义的可能模型?本文接下来探讨天下作为一种全球正义理论的可能模型。
赵汀阳是较早提出天下观念的学者。他认为,在罗马帝国模型、大英帝国模型和美帝国模型之外,还有一种天下的模型。(12)Tingyang Zhao,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Tian-xia,天下)” , Social Identities, Vol.12, No.1, 2006, pp.38-39.根据赵汀阳的观点,儒家历史上的天下体系的制度化是从周朝开始的。“以小邦而居中原之主位的周朝政权面临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政治问题:如何‘以小治大’并且‘以一治众’?”(13)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周政权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发明一种政治制度,一种主要依靠制度吸引力而不是武力威慑的统治方式,以制度优势代替武力权威。”(14)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54页。而这种制度的创制包括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德治原则。
赵汀阳也指出,周朝的分封制度所预设的等级观念在现代社会很难实现。但这种天下体系所体现的“无外”的观念却是当代世界可以学习的。“根据‘无外’原则,只有整个世界形成内部化,才能达到天下大治。”(15)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82页。对赵来说,天下并不是“国家”,更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和一个世界社会。(16)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天下/帝国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性存在,但它允许按照各个地方分成许多‘国’,就是说,天下制度是共享的,但是各个地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独立的。”(1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53页。
赵汀阳的论述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天下的讨论。目前相关讨论可以被归纳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下观:以赵汀阳、白彤东、贝淡宁为代表的等级秩序的天下观和以许纪霖、刘擎等人为代表的非等级秩序的天下观。
赵汀阳对天下的整个讨论是建立在对老子观念的生发上的。“如果说西方对世界的思考是‘以国家衡量世界’,那么,中国的天下理论则是‘以世界衡量世界’——这是老子‘以天下观天下’这一原理的现代版。西方关于世界统一性的想象基于国际主义原则,基于‘之间关系(inter-ness)’观念而发展出来的世界性方案无非是联合国或其他类似的各种‘国际组织’,都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因此就很难通过联合国等方案来真正达到世界的完整性。”(1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32页。赵认为,这种天下秩序是等级的,是建立在新的夷夏之别的基础上的。
白彤东和贝淡宁也承认这种建立在等级差别基础上的天下秩序,这种等级不是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强弱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的文明和蛮夷之区别的基础之上的。(19)Tongdong Bai, 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87; Daniel A. Bell and Wang Pei, Just Hierar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129-142.不过,白彤东所建立的新天下体系,依然依靠(民族)国家:“新天下体系接受国家是世界的基本成员,并不寻求一个从天下或者世界政府开始的顶层体系。”(20)白彤东:《谁之天下?——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评估》,《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2期。
但是许纪霖、刘擎等人所提出的新天下观念,类似于某种现代民族国家平等基础上构建的国际秩序,希望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但是又不承认等级差等秩序。(21)参见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不过,在白彤东看来,许纪霖的工作,“虽然用了很多儒家的语言,但是其内容还是自由主义尤其是世界主义的全球秩序”。(22)白彤东:《谁之天下?——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评估》,《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2期。换句话说,这种平等基础上的天下观,本质上可能还是一种世界主义。
把天下观念理解成世界主义,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解读。比如刘悦笛指出,当今西方思想“没有关注到儒家的‘大同思想’对于世界主义的真正推进”。(23)刘悦笛:《大同世界与世界主义——兼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孔学堂》2017年第3期。虽然彭国翔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既与现代西方的‘cosmopolitanism’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足以解释现代西方‘cosmopolitanism’所欲处理的种种复杂课题”,但是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和他所理解的世界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有根的世界主义”。(24)彭国翔:《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孔子:思想与实践》,《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
如何理解天下?
赵汀阳、贝淡宁、白彤东、许纪霖、刘擎、刘悦笛和彭国翔等人为我们呈现了天下观念的多重维度和多样解释。赵汀阳、贝淡宁和白彤东把天下解读成一种等级秩序。许纪霖、刘擎、刘悦笛和彭国翔把天下解读成一种世界主义。那么,这里的天下在哲学的抽象意义上至少可以被还原成两种理解:一种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等级秩序,可以被称作某种国家主义;第二种是某种形式的世界主义。
按照第一种理解,在赵汀阳、贝淡宁和白彤东等人看来,天下绝不是世界主义。天下并不鼓励超越国界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某种平等主义。在天下的体系中,国家仍然是这个体系的基本单位。这种天下观和传统民族主义至少有两点区别。首先,在天下体系中,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被以文化为单位的国家所取代。国家被赋予了以文化正当性为基础的道德含义。有仁政王道的国家,也有暴政霸道的国家。其次,仁政王道的国家在这个体系中应该处于支配地位,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家庭、社群、国家等共同体仍然存在,爱有差等仍然得到承认。即使在这样的天下秩序中,国界仍然有其规范性效用。在这里,天下赋予了国家以道德的含义,同时国家之间在道德上是不平等的。
不过,天下这种国家主义和传统的民族主义相比,因为其所提倡的某种世界范围的道德秩序,更加强调我们对国界外其他民众的某种道德责任,因此,道德秩序和道德责任仍然是天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民族主义可能不会承诺这种特定的道德秩序和道德责任。传统的民族主义更加关注民族自决,每个民族因为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基于各自的资源和体制,决定了各自的发展。同时,在传统的民族主义看来,每个国家对他国没有很强的救助的道德责任,更多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援助。
与第一种理解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第二种理解,在许纪霖、刘擎、刘悦笛和彭国翔等人看来,天下是一种世界主义。在天下体系中,仁者爱人。超越国界的普遍仁爱具有核心的位置。是否承认爱有差等不是天下观念的核心,某种普世的仁爱是这种天下观念的核心。强调突破国界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是天下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世界范围的道德秩序则是这种道德责任和义务的基础。
很明显,被理解成是某种世界主义的天下观念与传统的世界主义相比,最大的区别不是这种世界主义的内容,即对国界外的民众具有某种兼爱的道德责任,而恰恰是这种世界主义的基础。传统的世界主义更多是建立在某种普遍的人的尊严或者权利的基础之上。天下观念则更多是建立在儒家仁爱、大同和天下为公等观念的基础之上。
世界主义理论在基础上的差别会对世界主义涉及的道德责任产生一定影响。通常来看,世界主义一般号召一种全球范围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模式。不仅仅种族、性别、宗教等不应该成为分配的相关因素,国籍这种运气也不应该成为分配的相关因素。换句话说,世界主义号召我们无差别地对待国界内外的个体。国界外的个体也应该享受国界内公民的诸多平等的地位和待遇。不过,以仁爱、大同和天下为公等观念构建的天下秩序并不要求这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方式。儒家宣扬的是大同理念,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分配方式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充足主义的理念。当所有人都有所终、所用、所长和所养时,就满足了天下为公的理念。这种理念并不号召某种极端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方式或要求消除财富的差距等。
那么,这里涉及的困难是,在以上两种对天下的理解中,我们应该接受哪种?本文认为,天下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而应是一套关于类似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该如何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理论模型。天下观念的基础还是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天下观念不是世界主义。
同时,天下观念所持有的“天下为公”“大同”等理念,也超越了传统民族主义所设置的边界。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只接受某种人道主义救助的观念,而不接受任何超出国界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分配正义不适用于国界之外。但是,天下观念是允许分配正义超出国界的。某种充足主义的分配方式蕴含在了天下为公和大同的理念之中。因此,纯粹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说,天下观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笔者是支持第一种对天下的理解的,即在某种国家主义的语境中理解天下体系。但是,本文所认同的天下观念与赵汀阳、贝淡宁和白彤东的理解存在如下几点区别。
首先,赵汀阳等人所理解的天下,强调等级秩序,仁政王道的大国支配其他诸国。本文不认同这种理解。这里涉及如何理解国家之间的区分,包括对国家道德属性的区分。这里有强的和弱的两种理解。根据强的理解,国家之间的道德属性的差别可以直接转换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对此,笔者并不认同。作一个类比,人和人之间存在道德属性的差异,有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素质一般的人,以及道德品质低下的人。笔者不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可以直接支配道德水平低于他的人。类似的,仁政王道的国家也不可以直接支配比其道德水准低的国家。这里就涉及弱的理解。根据弱的理解,国家之间的道德属性不可以直接转换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仁政王道的国家更多是处于一种范导性的位置,有引领带动的作用,但没有直接的支配权力。
其次,赵汀阳等人所理解的天下,并没有明确国家之间的分配模式。尤其是在贝淡宁、白彤东等人勾画的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中,更多强调仁政王道的大国对其他国家的支配作用。但是在分配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讲清楚具体的道德责任。笔者认为,在天下系统中,仁政王道的大国对其他国家是需要承担道德责任的,这种责任至少是在大同理念的指引下进行的,至少需要完成充足主义意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肯定不是平等主义的。儒家的天下为公和大同的理念不支持平等主义的分配模式。
为什么是天下?
如果天下观念不同于当代的世界主义和传统的民族主义,那么,相较于它们,天下观念有什么优越性?本文认为,这里有强和弱的两个论题。强的论题是,天下观念比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都要好,可以解决或者避免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或者主要问题,而且是现实可行的。弱的论题是,天下观念不同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思考全球正义的概念模式。弱的命题并不必然蕴含强的命题。但是,诸多天下主义者希望论证和支持的是强的论题。
如果想辩护强的论题,我们必须论证,天下观念不仅仅规避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而且是现实可行的。世界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人性的事实和实现正义所需的强制性手段。而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对国界外人群的忽视。那么,天下观念可以规避这些问题吗?
如前所述,世界主义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世界主义的承诺似乎忽视了人性的事实即爱有差等。我们对于家庭、社区、家乡和同胞等的特殊情感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些真实情感必然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但世界主义的爱无差等的承诺要求我们悬置或者弱化这一人性的事实。
类似的,世界主义要求废除国界对于正义观念的限制,这种预设本身具有乌托邦色彩。而这种乌托邦不是在纯粹实践操作意义上的乌托邦,而更多是一种违背基本人性意义上的乌托邦。废除国家类似于废除家庭,我们对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认同,很多时候是建立在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的。这种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居住地的变更,而是个人身份的一种深层次建构的需要。我们很难认同通过废除家庭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平等。类似的,我们也无法通过废除国家来实现公民之间的公平与平等。
天下观念承认爱有差等的事实,进而规避了世界主义所面临的以上的主要困难。另外,天下观念也规避了民族主义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即对国界外人群的忽视。天下观念建立在对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的认同基础之上,把整个世界纳入一种规范性的秩序之下。不打破我们对既定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同时在天下的规范性秩序下,我们识别出国界之外的他人和其他国家在一个秩序中的位置,由此,他们不仅仅是陌生人和竞争对手,也是共同体中的成员。
此外,天下观念也识别出了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之间竞争本质的理解,进而识别出了建立在民族国家关系之上的国际秩序的脆弱性。按照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利益合法性的理解,各个国家为各自的利益产生竞争甚至冲突是自然的结果。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诸多理解被限制在具有强制性的民族国家内部,那么,世界和平、平等与正义这些理念似乎在民族国家之间是无法实现的。
以上这种分析,使得天下观念似乎是某种版本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本文论述了天下观念不是世界主义,因为其承认民族国家或者类似的政治共同体是全球正义的基本单位。如果天下观念不打破我们对既定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的认同,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天下观念不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主义?
区分天下观念和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厘清天下观念下的世界秩序和民族主义视角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体,比如,澄清天下所呈现的世界秩序和联合国与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所体现的世界秩序的区别是什么。在赵汀阳看来,“联合国模式背后的哲学是对国际民主以及理性对话/交流理论的信念”。(25)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02页。在赵看来,这种程序公正的民主是无法达到实质工作的结果的,甚至产生可怕的结果。而天下背后的理念是一种“民心”概念。(2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02—103页。对赵汀阳这段话的一种延伸的理解是,天下的世界秩序不是通过民主的程序来建立的。换句话说,天下作为一种道德秩序,并不预设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进而在这种平等地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形成一种协商的国际组织或者共同体。
以上这种区分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种道德的世界秩序该如何形成?形成后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什么样的?本文认为,天下观念在第一个问题上并不需要做出某种承诺。一种道德的世界秩序可以通过协商之后形成,也可以通过强制的形式形成。当然,有人可能会指出,形成的程序直接决定这种国际秩序的合法性。然而,如果那些弱小的国家不同意某种强制形成的国际秩序,那么这种秩序对这些弱小的国家就没有规范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国际秩序的形成,并没有征求弱小国家的意见。同时,如果存在一种对全球长远发展有利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的获得,似乎并不依赖一种特定的民主程序。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道德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什么样的?我们很难给出具体的图景。不过,那些行仁政王道的大国,而不是某种军事和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帝国,在这种秩序中承担核心的作用。这些仁道的大国可以引领全球发展的方向,去攻克那些全球性的问题,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等困难。这种秩序肯定和目前的国际秩序差别很大。目前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二战之后帝国主义的一种秩序安排,和仁政王道相去甚远。
而这种道德的世界秩序的目的是天下大同,而不是某个或者某些国家支配全球的资源和市场。这种天下大同并不是世界主义所理解的全球的分配平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念是一种目的论的、至善主义的和充足主义的,而不是分配正义意义上的平等主义。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天下概念,说明了其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同时,解释了其在何种意义上规避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然,天下观念还面临很多概念和实践上的问题。诸如,在何种意义上,其不是理想主义的?天下观念的动机机制是什么?仁政王道的标准是什么?它和民族平等是否相冲突?这些问题不是本文的篇幅能够讨论清楚的,需要后续的讨论。
正是因为天下概念面临以上诸多问题,笔者并不认为我们当下可以辩护强的论题,即天下观念不仅仅规避了传统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而且是现实可行的。如果天下观念是现实可行的,我们不仅仅需要辨析天下观念的诸多细节,还需要回应其概念和实践上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的,涉及我们如何思考民族平等、跨国之间充足主义的落实等主题。我们当下只能辩护弱的论题,即天下观念不同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呈现出另外一种思考全球正义的概念模式。
结 论
天下作为一个汉语的概念,是一个特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和汉语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紧密相关。与西方世界中关于民族、国家和全球秩序的思维模式不同,汉语提出了不同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解决国际正义的路径。而这可以被理解为汉语哲学的一个案例。
除了“天下”以外,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汉语哲学的案例。诸如汉语中的“仁”,既不同于西方的“仁慈”(benevolence),也不同于西方的“关怀”(care),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体现一种品质性的特征,又具有关系性的特征。类似的,汉语中的“道”,既不同于西方的“真理”(truth),也不同于西方的“言说”(speech),汉语中的“道”似乎既具有某种本体论的特征,指称某种实存的、超越的东西,又具有认识论的特征,指称真的东西,同时也具有实践的维度。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汉语这种语言和哲学传统具有如此之多的独特性概念和理念。这些概念和理念是否可以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进而为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解决的思路,而这可能才是汉语哲学最重大的意义。汉语哲学的独特性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考古的发现或者语言学的描述,而应该更多作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思路,具有现实的、深刻的、普世的意义,进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