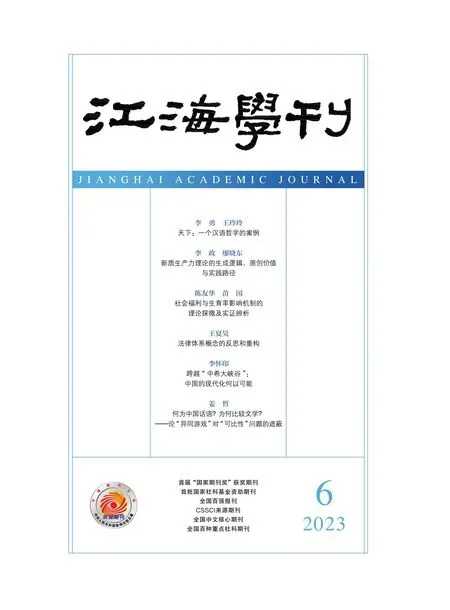论明末实学思想对理学家文学活动的影响*
——以东林学派陈龙正为例
李 琦 尹楚兵
晚明万历至崇祯时期是我国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东林学派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派。就理学内部的演进过程来看,阳明身后,王门盛极一时,并因对体用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分化为左右两派。时至晚明,东林学派因不满王学左派重本体、轻功夫之弊及与狂禅合流的倾向而再度推崇朱子学的正统地位,重新竖起“复兴程朱”的大旗,可以视作明代理学继明初朱子独尊和中期阳明崛起后的第三个阶段:“至明末,学者承王学末流向猖狂无忌惮一路发展、朱子学被掩蔽的现实,力倡实地做功夫。这种趋向渐渐发展为思想界的主流。”(1)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1页。就儒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由于王学左派最大的问题在于片面强调本体的“无善无恶”、认性为空,奢谈顿悟而蔑视践履,因此东林学派对此的纠正方式是强调本体的实有性和“性善”的本体地位,同时主张修悟并重,反对空谈本体,突出功夫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东林学派要求士人在重视修身的前提下积极入世,力求在朝堂与社会重塑儒家传统道德秩序,以此实现“学术救世”的抱负。可以看到,东林学派的学术宗旨带有明显的务实特点,因此被不少学者视作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源头,对顾炎武乃至颜李学派等清初实学家均有深远影响。(2)关于东林学派的实学特点及对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包括钱穆、李书增、步近智等学者都已有论述,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盖东林承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早有避虚归实之意。惟东林诸贤之所重在实行,而其后世变相乘,学者随时消息,相率以‘实学’为标榜。”详情可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李书增等:《中国明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0—1336页;步近智:《东林学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
陈龙正是东林学派最重要和特殊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师从学派领袖高攀龙,还承担了学派重要文献《高子遗书》的主要编纂工作。此外,陈龙正还是学派在明末最活跃的成员,崇祯时期,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学者都已去世,孙慎行、吴桂森、叶茂才等学者则年事已高,只有陈龙正、华允诚和吴钟峦三人正值壮年。而三人中尤以陈龙正的学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不仅继承了顾、高等学派前辈的主要思想,还依据明末具体的时代环境做出了革新。因此,如果东林学派因其“融合朱王”的特点可以被视作明代理学的总结者,那么陈龙正“以生生为宗,以人伦为重,以躬行实践为功夫,至于用世,大意盖为民而事君也”(3)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5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的思想则可以被视作东林学派的总结者,因此对他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典型价值。受明末严峻社会危机的影响,陈龙正更加重视学术的实用性,其思想的实学特点在东林学者中最为突出,其文学活动也沾溉了实学色彩。
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
实学对陈龙正文学思想产生的首要影响,是对文学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这是陈龙正与其他理学家的最大区别。在理学内部,“重道轻文”是自周敦颐以来学者对待文学的最大共识与根本准则,(4)在理学家的语境中,“重道轻文”之“文”并非专指文学,同样也包含语录、讲义在内的学术文章,但以“词章”和“诗文”为代表的文学无疑是“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林学派重要学者孙慎行就曾表示:“圣门道术,首言学文。虽非世文辞之文,而文辞未必非其流绪焉?”孙慎行:《玄晏斋集》,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60册,第50页。即便是少数文学造诣不凡的理学家也不例外。如陈龙正之师高攀龙虽长于诗歌,并因善于拟陶而被沈德潜盛赞“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5)沈德潜撰,王宏林笺注:《说诗晬语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但他本人也是“重道轻文”原则的坚定支持者。高攀龙明确主张“道本文末”,“德行废而任词章,既失其本矣”,(6)高攀龙著,尹楚兵辑校:《高攀龙全集》(上册),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577页。并对其弟高附骥“理七文一”的观念赞赏不已,“看书当七分理学,二分史学,一分诗文,方是会读书,方是会享清闲之乐”,(7)高攀龙著,尹楚兵辑校:《高攀龙全集》(中册),第930页。认为这是他“中年有大志”(8)高攀龙著,尹楚兵辑校:《高攀龙全集》(中册),第931页。的表现。而陈龙正虽然非常推崇高攀龙的学术成就,但对待文学的态度却与其有明显不同。他认为文学对理学、政治及社会治理和日常行为实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实用价值,应当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体现。
首先,就文道关系来看,陈龙正不仅继承了理学家“文以载道”的文道传统,还进一步加强了“文”在文道关系中的地位。“文以载道”将文隶属于“道”的统摄之下,文的唯一价值是为“道”服务,本质上仍是“重道轻文”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东林学者对“文以载道”的看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以高攀龙为代表,认为文虽可“载道”,但却是有限制的:“著述之事甚非学者所宜亟亟,不得已乃言之耳。一生学问有得力处,若无人可授,岂忍自私?只得公之后世,总亦出于不忍人之心,若文词何用?”(9)高攀龙著,尹楚兵辑校:《高攀龙全集》(上册),第320页。高攀龙认为文虽可“载道”,但“载道”未必一定要文,只有在“无人可授”的情况下,才需要用文章传承自己的学术思想。此外,高氏认可的载道之文是“著述”而非“文词”,也就是辩、讲义、会语等学术文章而非诗词等纯文学,前者地位明显高于后者。其二以冯从吾为代表,完全否定文有载道的可能,彻底消弭文学的一切价值:“文章可闻,而性道不可闻。性道原是不可闻的,若是可闻,便是文章,便不是性道矣。”(10)冯从吾著,刘学智、孙学功点校整理:《冯从吾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页。可以看出,多数东林学者在对待“文以载道”时,或进一步削弱文学在文道关系中的地位,或干脆否定文学具有载道的价值,总体呈现出扬道抑文的倾向。但陈龙正则明显不同。一方面,陈龙正认为文不仅可以载道,且道的唯一载体就是文。他在《巨手说》一文中表示:“然则天下莫巨于道,莫巨于心,而手为之次,手不过能文章耳。然道莫能载,而载道之器,必归文章,手同心之所托欤?撑乾坤,亘古今,亦惟兹手。”(11)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52页。陈龙正认为,“手”是天下除“道”以外最重要的事物,而“手”之所以重要,就是在于能写作文章,手能“撑乾坤,亘古今”,也就是文章能“撑乾坤,亘古今”。陈氏虽然仍将“文”统摄于“道”之下,但“文”的地位却已获得了大幅提高,成为了继“道”之外最重要的事物。另一方面,陈龙正不仅认可学术著作的载道能力,也认可包括诗文辞赋在内一切文体的载道能力。试看《阳明先生要书序例》一文:
钱氏定《传习录》外,则有文录,有外集,有别录,有续编,名目纷纠,义例杂出。据云:“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悔前之遗为外集。”及观其正,皆书也;其外,皆诗与传志也。岂书皆悟后之秘,而诗、传、志皆未透之说哉……又论学之书,虽在初年,列入正录,诗与传志,虽在晚年,亦入外集,是不论悟与未悟,醇与不醇,始终以体类分正外也,尤自失其初旨矣。(12)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93—595页。
此文表明陈龙正编纂《阳明先生要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对钱德洪等王门后人编纂王守仁文集时割裂其文学作品与理学思想关系的不满。在陈龙正看来,钱德洪以文体不同来界定“载道”与否的做法完全错误。著作能否“载道”,只取决于它创作于学者悟道前后。阳明早年所作的“论学之书”未必比晚年所作的“诗与传志”更能准确地反映其思想。如此,诗歌、传记等就不再完全是“小技”或“末流”,而是同语录、讲义一样具有“载道”的实用价值,地位明显得以提升。
其次,就文学与政治及社会的关系来看,陈龙正认为文学对政治乃至整体国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学的雅正靡邪与社会的兴盛衰败互相影响:“是故《典谟》世盛,《训诰》世治,《国策》世乱,《国语》世衰,文章与政治相表里。”(13)陈龙正:《几亭文录》,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1册,第106页。作为一名恪守程朱的理学家,陈龙正认为被儒家视作经典的《尚书》要胜过《战国策》和《国语》。因此《尚书》与三代治世相匹配,而《战国策》和《国语》则与混乱的春秋战国相匹配。仅从这一点来看,陈龙正的文学价值论似乎与自《毛诗大序》提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14)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页。以来儒家所持的“风雅正变”说并无不同,即文学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能力。但陈龙正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文学不仅可以反映现实,更可以干预现实:“而或者曰:‘文从世,世不从文。’则文之权太轻,而为文者之心不慎。夫令昼夜鼓舞于邪辞以希荣,恐幼学之邪心,直从文起矣。文移心,心移世,轻乎?重耶?”(15)陈龙正:《几亭文录》,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1册,第106—107页。他认为文学可以通过影响年轻学者心理的方式左右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强调文学对社会的实用价值,要求提升文学的地位。就这一点而言,陈龙正对文学价值的重视甚至与曹丕等文学家无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16)高步瀛选注,陈新点校:《魏晋文举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为东林学派乃至宋明理学家中少见。在各类文体中,陈龙正尤为重视诗歌的政治价值,诗歌在他看来不仅是学者和政治家的必备能力,还是连接学术与政治的纽带,具有重要地位:“学不以贯诗,不足以言学;诗不以贯政,不足以言诗。况诵诗则达政,政固诗中事也。诵者犹然,又况为诗者耶?”(17)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1册,第69页。
最后,就文学与日常生活实践,即言行关系来看,陈龙正一反理学家“行重言轻”的传统,强调言在日常生活各方面的重要性,主张“言行并重”。自孔子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以来,理学家在论及言行关系时几乎都以行为重。如许孚远认为:“今日之学,无有言论可以标揭,惟是一念纯诚,力行不懈,则此道自明。”(18)顾宪成著,李可心点校:《小心斋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页。而由于东林学者热衷于讲学,因此他们更担心因“重言”而落人口实,强调“行在言先”。如顾宪成就对孔子“先行后言”的观念赞赏不已:“讲学自孔子始。谓之讲,便容易落在口耳一边,故先行后言、慎言敏行之训,恒惓惓致意焉。”(19)顾宪成著,李可心点校:《小心斋札记》,第41页。而冯从吾更明确表示:“做人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20)冯从吾著,刘学智、孙学功点校整理:《冯从吾集》,第260页。可见“行重言轻”是他们的一致态度。陈龙正则与之有明显差别。他认可言的地位与价值,主张“言行并重”。试看与其子陈揆的对话:
揆问:“讷言耻言,言若此其轻;不学《诗》,无以言,言又何若此其重也?”曰:“言固有二,非行重而言轻也。讷且耻者,对躬行而为言。人情自舒所有,易至溢分,故加意收敛之,非轻之也。言出于学《诗》者,酬酢天下之言,事父事君,则敷奏以言,承顺以言,讽喻以言。当大事,则明理以言,抚众以言,摈使以言。出而治人,则折狱以言,屈敌以言。居恒亲友之间,则相规相劝以言。此之为言,所系甚重,而行且大半在言中矣。”(21)陈龙正:《几亭外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2册,第143—144页。
陈龙正首先反对“行重言轻”的观念,接着对儒家“讷言耻言”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全新解读。陈氏认为,孔子对言的“讷”与“耻”,目的在于约束和匡正不当言论,只是对言进行改造,而非贬低言的地位,更不是指“行重言轻”。这一点明显与许孚远、顾宪成、冯从吾等学者不同。最后,陈龙正从包括政治讽谏、教化百姓、治理社会和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肯定了言的实际价值,认为上述“酬酢天下之言”与践履实行已经没有本质差别,并特别提及了《诗经》对学言的重要意义。如此在陈龙正的思想体系中,“言”的地位就因其所具有的现实价值而大幅提高,“言行并重”也就成为可能。
实用原则指导下的文集编纂论
陈龙正虽然认可文学具有重要性,但归根结底仍旧是一位理学学者而非文学家。他之所以肯定并提高文学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希望发挥文学的实用价值,是一种实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纯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他对各类文集的编纂活动中。陈龙正一生编有大量文集,其中既有先贤名家所著,如《陶诗衍》《阳明先生要书》《朱子经说》;也有师长亲友所著,如《高子遗书》和《陶庵集》。在编纂上述文集的过程中,陈龙正以务求实用为原则,形成了具有实学色彩的编纂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陈龙正在编纂文集的过程中,以实用为选取诗文的最高标准,即编纂文集的目的具有实用性。陈龙正认为:“物无用,不如无是物;言无用,不如无是言。”(22)陈龙正:《几亭外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2册,第1页。在他看来,实用与否是判断文本价值的最高标准。比如在《阳明先生要书序例》中,他在文章开头便提出,本书编纂的目的是为了“欲使人人读而取益焉”;(23)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89页。并进一步表示,读者既要学习王守仁精深的理学思想,更要学习他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杰出成就:“惟阳明先生终身在事功中,终身以修德讲学为事。奏成功者,学助之也;居成功者,学为之也。观圣贤者观其用,曾谓用如先生,而尚非豁然闻道者耶?”(24)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89—590页。而当此书完成后,陈龙正更是不遗余力地向师友们宣传此书具有的现实价值,并希望获得推广。当他得知友人桂一章掌管山西学政时,甚至写信希望其能在山西官印此书,使三晋士人人手一本,以便更好地发挥此书的“救时”价值:“《阳明要书》奉教。此书救时之急务,心性经纶,以及文章,靡不概括,弟心力所用亦甚深甚微。乙亥,叶庆绳按东粤,蒙相信之至,已刻行彼中。若得年翁序其简端,就晋更刊官本,三晋良士,不下万人,使人人得印一部,熟读深体,其为裨益,胡可殚言?”(25)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66页。
此外,陈龙正对文学实用价值的追求还具有极端性。他不仅要求收集整理有用之文,还要删除无用或“有害”之文,通过“收”与“删”两方面的工作来确保传世之文的绝对实用性。出于这一目的,他甚至认为可以借鉴秦始皇焚书的部分做法,希望能举行一次全社会范围内的文集编纂工作,在收集“益世之书”的同时焚毁其余一切无用之文:
始皇焚烧经典,经典乃益世之书,如何可焚?焚之为大无道。今世诸书,除经传语录,明性教;史鉴典故,载治乱,备礼法;古名诗文,阐事情,此外尽可芟夷。第一宜焚者,淫词曲谱,第二通俗小说,第三则难言之文集是也。是宜分别去留,须妙选天下正大文人如刘向、韩愈、欧阳修之伦为总裁,择其有益世道人心者存之,其余惑世诬民之说,虽文采极艳,皆从删削,使今天下载籍约存百一。孔删诗书,去其十九,今文漫漶,非诗书比,又宜十之。(26)陈龙正:《几亭外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3册,第259—260页。
陈氏删定天下诸书的目的在于保存“益世道人心者”,删去“惑世诬民之说”,完全是出于实用原则考量的结果。他首先规定了不可焚毁的“益世之书”,包括经、史和部分名家诗文集;接着又罗列了必须焚毁的几类“有害”之书,主要指词集曲谱和通俗小说等俗文学;最后还推荐了执行删定天下诸书的负责人,即如韩愈、欧阳修一般人品高尚、学养精深的“正大文人”。可以看出,陈龙正要求删定天下诸书并非出于一时意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认真提出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陈龙正在此表现出了对俗文学的强烈敌意。他要求焚毁的三类书籍中,有两类可以归为俗文学。但如果结合其他文章则不难发现,陈龙正评判俗文学的根本标准,仍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如在《四子诗余序》中,陈龙正就表明不应以文体的雅俗来判断文学的价值,而是以实用与否为根本标准:“诗又降而有余,诗之尽,曲之初矣。然亦问其所存者何志,所赋者何意。若志存乎洁身,而意主乎移风,虽古昔先王,九歌是劝,皇极是训,足使辅翼而行,又何嫌乎体之降哉!”(27)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1册,第70—71页。可以看到,陈龙正看似对俗文学的态度前后矛盾,但其核心准则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艺术风格的雅俗,而在于是否能“洁身”“移风”,即是否具有提高个人修养和维护社会治理的能力。这无疑具有鲜明的实学特点。
其次,当确定所选的诗文具有实用价值后,陈龙正会通过各种方法强化文集的传播性和可接受性,以确保文集能流传得更广泛并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即编纂文集的手段同样具有实用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陈龙正对文集收录诗文的删选淘汰上。此处的删选与“删定天下诸书”又有不同,可视作针对已确定的“益世之书”的再筛选。陈龙正删选诗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两点,其一是删除“烦复”之文,以便于读者更易阅读和接受;其二是删除“诐邪”之文,确保文集可以最大程度上符合他对“有用”价值的要求。
就第一点来看,陈龙正在编纂《阳明先生要书》时,曾专门言及四点编纂原则,其中第三点即为“除繁”。尽管陈氏欣赏简洁干练的学人之笔,“词寡而理达,语约而味长,此学人之笔也”,(28)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95页。但他删减王守仁文章的主要目的却并非出于艺术追求,而是因读者具有“众厌而罕观”(29)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96页。的天性,故而需要通过删减缀文的方式加强文集的可接受性:“愚尝谓凡书一概混传,与不传无异。何则?众厌而罕观,则世不被是书之泽,而作者之神没也……余虽不敢删弃其篇次,遇一二烦复者,各以鄙意,与之节文,要使集无复篇,篇无复语。苟非切要,不复爱惜文辞。”(30)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96—597页。就第二点来看,既然陈龙正编选文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发挥文学的实用性,那么他自然要确保所选文章绝对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上文已经指出,陈龙正对于“惑世诬民”之书的态度极为严格。因此他所编选文集的作者大多为重要学者或亲友,已将“淫词曲谱”的作家排除在外。但即便如此,陈龙正仍要对他们的文章进行再筛选,确保一切偏离他价值标准的文章都被剔除在文集之外,这一点就连陈龙正的老师高攀龙、好友归子慕和偶像陶渊明都不能例外。如他在编纂《高子遗书》时,就删除了高攀龙大部分涉及党争的文章;(31)参见黄友灏:《高攀龙理学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明末清初高氏著作的编刻为中心》,《汉学研究》2014年第4期。而在编纂《陶庵集》时,又“遂用十日力,定存其三之二”,(32)陈龙正:《几亭文录》,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1册,第84页。对归子慕的诗文淘汰颇多;在编纂《陶诗衍》时,他认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除首篇外其余诸篇均为描写“世间不必有之物,不尽然之理”,不能识物明理,于世人无用,因此也一并删去。此外,陈氏曾编有丛书《皇明儒统》,收录包括胡居仁、陈献章、吕柟在内的明代著名理学家的文章、诗歌和语录。对于这些本朝理学大家,陈龙正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肯定这些前辈学者在儒学和事功方面的突出造诣,认为他们的诗文确有经世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理学家与东林学派,特别是陈师高攀龙的思想不尽相同,在陈龙正看来未免“大醇而小疵”。因此陈龙正在收集上述学者著述时,就不免有所删选:
象山、慈湖辈,直不幸而概传其说于后世。诐邪备见,系道者奚忍忘言?使宋元间复得如朱子者,删而泯之,后学之幸,未尝非二子之幸也。迩来诸家繁兴立说,无所不有,殊为斯道惧。惟存其是,与近是而未醇者,使后人读之,皆足以益身心而无复簧鼓其听睹。虽使目诸家皆醇儒正学,可也。成昔人之美,不敢开后人之误,余所窃附于君子之义焉。(33)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620—621页。
可以看到,陈龙正删选近世诸儒著述的目的,是为了使后人阅读后“足以益身心而无复簧鼓其听睹”,即确保读者从该文集中接受到的均为陈龙正认可的内容,以便充分发挥文集培育身心的实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还收录有少量背离程朱“正统”学脉的学者,主要为部分阳明后学。代表人物有浙中王门领袖王畿,泰州学派领袖王艮等人。浙中王门和泰州王门都属王学左派,是东林学派在学术领域的主要论敌。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学派领袖对其多有诟病:“吾辈试看龙溪之于利根断乎?未断乎?而汲汲以断名根为言,又恐利根愈活,则善根愈死,其为心术之害不小也。”(34)顾宪成撰,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361页。陈龙正同样对王畿、王艮有所批评,称其“栖心空寂”“寄迹儒门”。(35)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621页。但出于实用原则,陈龙正认为即便是王学左派同样有值得汲取之处:“凡留意讲学之人,必有所见,其所言亦必有合道者。”(36)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620页。因此,他主张“言不以人废”,(37)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623页。并在该书中收录王学左派文章中的“善者”,以期有助于后学:“惟择其善者存之,俾后世蒙其利,不受其害。”(38)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623页。在门户之风盛行的晚明,陈龙正能以务实用为主,跳脱学派藩篱,集百家之所长,可以视作实学思想对他产生的积极影响。
对“淡”的实学诠释与诗学实践
在各类文体中,陈龙正特别重视诗歌的实用价值。他的诗学思想和实践也带有鲜明的实学特点,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对“淡”的实学诠释上。“淡”是陈龙正最为青睐的诗歌风格,他酷爱陶诗淡泊自然、无所矫饰的审美旨趣:“其有声也为亮节,如风鹤云鸿,不以炼响得也;其色为素采,如积雪之有光,不以点染紫碧成也。”(39)陈龙正:《陶诗衍》,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2册,第181页。他认为王维、柳宗元二人于陶渊明“效之而不似”的原因就在于为诗过于注重字句安排,反而破坏了诗歌的淡泊之美:“王色色工致,固是唐调;柳以古博自矜,句造字刷,乏自然之致,且多以赋手作诗,其愈繁靡艰奥者,失之愈远。”(40)陈龙正:《陶诗衍》,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2册,第185页。可见其对淡泊诗风的追求。
与文学家不同的是,陈龙正并非仅将“淡”视作一种纯粹的审美风格,而是将其视作“道体”的存在状态和本质体现,也是一种具有社会和个人双重现实价值的理想之境。在理学思想体系中,本体论具有最高地位,“道体”“天理”“良知”“心性”等为学者对本体的不同指称。在理学家看来,以“道体”为代表的本体是先验且高度抽象的,无法用具体的言语表达,即“君子之道费而隐”。但在自然世界中运行的客观规律,则可以视作“道体”的表现形式。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陈龙正认为“淡”即为不矫饰,不造作,不经后天人力加工。它来源于自然,是对自然万物本初存在状态的理想描述,因此也就成为对“道体”的理想描述。学者通过体会“淡”,可以体悟“道体”在自然界的流转生化,即“入道”:“天然而淡者,淡即道也。意向于淡,则淡怀可以入道。”(41)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1册,第67页。需要注意的是,陈龙正并不认为“淡”就是清静无为,他不仅认可“淡”具有的学术价值,还认为“淡”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治理都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就社会层面来看,陈龙正认为“淡泊”之风有助于去除社会不良风气,完善社会治理:“烟霞之味,恒与道近,正为洗濯世氛,则理义敦笃耳。故淡泊者,道德经济之原。”(42)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5册,第246页。就个人层面来看,陈龙正认为学者一旦进入“淡泊”境界,就可以勘破生死:“人人恶死,细思为何?苟非系恋,即是恐怖。学者但得平生淡泊,一切嗜欲之乐,未尝耽溺,不觉其有味,则系恋自轻。”(43)陈龙正:《几亭外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2册,第36页。总之,在陈龙正的思想体系中,“淡”已经由一种审美风格扩展为具有本体论和境界论意义的学术概念,在理学研究、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方面都具有实用价值。
既然“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那么在陈龙正看来,诗歌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帮助作者和读者通过写作与阅读达到“淡”的境界。这种忽视诗歌艺术价值而追求实用价值的做法,可以视作实学思想对陈龙正诗学理论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只不过由于陈龙正理学家的独特身份,使他对诗歌实用价值的定义附加了更多的学术属性。尽管陈龙正为“淡”赋予了超越审美的价值与地位,但他也认可诗歌是最能体现“淡”内涵,营造“淡”意境的表现形式。在为好友卞子厚诗集《苍雪斋吟》所作的序文中,陈龙正表示:“(天然而淡者)此脉暮春咏归以来,《击壤》、白沙跻其巅矣。”(44)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1册,第67页。他不仅认为对淡的追求可以入道,还通过兼具理学大儒与著名诗人双重身份的邵雍与陈献章的例子表明,诗歌是学者营造淡泊之境、进而入道的良好媒介。而诗歌之所以有助于学者养成“淡泊”心境,在于它可以去除“嗜欲”。“嗜欲”在陈龙正的思想中并不单指对欲望的嗜好,而是一种对所有极端欲望的统称,是与“淡泊”最为对立的概念,也是学者入道和社会大同的最大障碍:“情欲是善恶统名,嗜欲有恶而无善。”(45)陈龙正:《几亭外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2册,第77页。“嗜欲既尔消融,自然思虑精微,义理充实,人伦日用到处妥当。”(46)陈龙正:《几亭外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2册,第373页。陈龙正认为,诗歌是去除“嗜欲”、恢复“淡泊”的最好工具,他曾专门作《诗以淡嗜欲》一文阐述这一理念:
诗总为淡人嗜欲而设,淇之上,洧之外,存以为戒。今人不知诗所从来,反其本原,拾其风韵,略负俊才,辄习淫趣。高若晋《子夜》,次若齐梁艳歌,下则元曲耳。助流连,增嗜欲,不师圣人之所法,而学圣人之所戒,栩栩乎犹以骚人韵客也,一口一笔必自宣其愚以示人,岂不哀哉!(47)陈龙正:《几亭外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2册,第330—331页。
在陈氏看来,诗歌创立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淡泊欲望,去除嗜欲。而如果仅仅如同南朝文人一般将其视作追求风韵、展示才华的手段,则完全背离了诗歌的初衷,是他所无法接受的。又如陈龙正在评价高攀龙的诗歌时,认为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淡雅似陶的诗风有助于学者去除嗜欲,恢复“清真”,而当学者恢复淡泊清真的本源后,自然可以在学术和事功上都取得斐然成果:“文字当垂,惟取益世。益世惟三:其一关切身心,其二开物成务,此易知也;三者,烟霞洒落,足以淡嗜好而资清真。理义从此实,故不身心而身心;才识从此浚,故不世务而世务。”(48)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73页。他特别在文章末尾再次强调这一点,希望读者能理解作者及编者的苦心,以便更好地发挥高诗的实用价值:“朴儒庄士,读至此便超迈一番;逸民韵客,思至此应精进一番。不然,有负作者,亦忝观者。”(49)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73页。可见陈龙正对诗歌“淡泊”价值的重视。
陈龙正诗学的核心思想,可总结为“诗总为淡人嗜欲而设”。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他主要通过提倡“淡泊无嗜欲”的人品和“以淡为美”的诗风来发挥诗歌去除嗜欲、恢复淡泊、进而载道致用的实用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陶诗衍》一书的编纂与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实践。陶渊明是陈龙正最为尊崇的文学家,他的诗歌整体明显体现出对陶诗的效仿。因此《陶诗衍》可以视作陈龙正对自己诗学思想的阐发:“通过对陶诗及后世学陶、效陶诗人诗作的评选,陈龙正完成了对陶诗接受体系的检视,也以此宣扬了他的诗学思想。”(50)邓富华:《明末陈龙正〈陶诗衍〉考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陶诗衍》虽为诗歌选集,但却并不重视分析研究诗歌遣词造句的艺术手法,而是注重从诗人的品行经历与诗歌的整体风格上做出评价:“不难发现,陈龙正对陶诗接受的问题已经转移到作者的品行与诗歌的风格上。”(51)邓富华:《明末陈龙正〈陶诗衍〉考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这与他“诗总为淡人嗜欲而设”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陈龙正在此书中对陶诗的评价极高,认为陶诗是“诗中孔门”,即中国古典诗歌的绝对正统:“诗宜以渊明为正宗,或云:‘诗家视陶,犹孔门视伯夷。’不知文章之有诗,已是伯夷一路也。咏歌性情,夷旷萧散,正风雅之本旨。陶为伯夷,谁为孔门。”(52)陈龙正:《陶诗衍》,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2册,第188—189页。可以看出,陈龙正之所以认陶诗为正统,根本原因就在于陶诗“咏歌性情,夷旷萧散”的特点符合《诗经》风雅的根本理念。而“夷旷萧散”正是“淡泊”在诗歌中常见的表现形式,也是陈龙正最为认可的诗歌风格。如他在评价《读山海经》首篇之“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一句时,就盛赞:“极平淡,何人道得?”(53)陈龙正:《陶诗衍》,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2册,第244页。陈氏推举陶诗为正统,并专门编选《陶诗衍》为之揄扬的目的,就在于希望更多人接受“以淡为美”的诗风,以期更广泛地实现诗歌去除嗜欲的价值。其次,《陶诗衍》下编收录后代众多著名类陶诗人的作品,并给予了评价。在这些诗人中,陈龙正将他们分为了“效之而偶似者”“效之而不似者”与“不效亦不似者”和“不效而似者”四类。其中最特殊的当属“不效亦不似者”,即孟浩然。在陈龙正看来,孟浩然本人不主动效陶,诗歌也与陶诗不似。但是他却将其收入《陶诗衍》,纳入陶诗正统谱系,说明他对孟浩然极为欣赏。而欣赏的原因在于孟浩然虽然在诗歌方面于陶渊明“不效亦不似”,但在品格性情和人生选择上却与陶相类,即不慕俗欲,以淡泊为终身追求:“不效亦不似,于浩然乎何取?盖其泪归青山,虽非恩怀荣禄,而终身隐遁,洒然有五柳之遗风。不然,唐世尚词,即见诮于世主,何难曳裾王公节度使间?亦其性近淡泊使之然也。”(54)陈龙正:《陶诗衍》,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2册,第187页。一般认为,孟浩然早年并非一心归隐,而是因诗遭玄宗放还后才寄心山野。但在陈龙正看来,孟浩然身怀大才,即便玄宗不取,游走于权贵之门获取荣华富贵也并非难事。而他却轻视世俗名利,不愿以诗才自售于显贵。这种淡泊不嗜欲的人生态度正是孟浩然和陶渊明最相似且最可贵的品格,也是陈龙正希望诗歌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因此,即便孟诗与陶诗不类,陈龙正依然将其视作诗歌正统予以弘扬。最后,《陶诗衍》最为推崇的诗人,除陶渊明外,当属“不效而似者”归子慕。陈龙正甚至表示《陶诗衍》就是因归子慕得名:“《陶诗衍》为归而名也。归诗何以无细评?归别有《陶庵集》于论之详也。”(55)陈龙正:《陶诗衍》,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2册,第337页。归子慕号陶庵,为归有光第五子,是陈龙正之师高攀龙和吴志远的挚友,平生酷爱陶渊明,在诗歌创作和日常生活中对其多有效仿。他屏居山村,“枕琴卧书,餐山茹水”,(56)高攀龙著,尹楚兵辑校:《高攀龙全集》(上册),第765页。颇具渊明遗风。陈龙正视归子慕为“淡泊无嗜欲”的典范。在《陶庵集序例》中,他认为归子慕“淡泊无嗜欲”的生活方式已经帮助他脱离了生死之苦,超越了周敦颐、程颢、邵雍等理学大家,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人生乐嗜欲,则死以失嗜欲为忧,生而乐,死而安,元纯居其常;生而乐,死而玩,康节游其偶。生而忧道,死而乐道,则于先生乎见之。从乐得玩者,得虽深,于圣人微异者也;从谨得乐者,所存虽未熟,与圣人大同者也。”(57)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0册,第565—566页。因此,《陶诗衍》对归子慕高度赞誉,旨在宣扬归子慕“淡泊无嗜欲”的诗歌与生活风格。
除了编纂《陶诗衍》外,陈龙正本人的诗歌创作也能体现出他对“诗总为淡人嗜欲而设”理念的实践。陈龙正酷爱作诗,《几亭全书》卷五十九、六十和《几亭续文录》卷八均为诗歌。这些诗歌多数都是以山水游记为题材,诗风淡雅自然,具有明显的“以淡为美”的特点。陈龙正认为自然山水有助于涤荡嗜欲,恢复淡泊:“烟霞之味,恒与道近,正为洗濯世氛,则理义敦笃耳。”(58)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5册,第246页。又说:“不涉道理,不涉事理,可以助人养心者,有三物:曰诗歌,曰乐音,曰山水。”(59)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05册,第246页。因此他特别热衷于创作山水诗,有《羁旅初归》《山游》《山行》《初入九锁山》《将入前溪》等。这些诗歌无一例外都营造了天然淡泊的意境,试看《初入九锁山》其三:
千山之内,一舟之上。舟小容膝,四达天敞。其俗可洗,其空可仰。载人以游,载天以往。(60)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1册,第211页。
《初入九锁山》全诗共七首,连贯地记叙了陈龙正在九锁山的游览过程。其中第三首描写了陈龙正经水路前往九锁山途中的所见。群山环绕的小河中,作者在露天小舟上抱膝而坐。仰望晴空,俯瞰碧水,人与自然浑然相融,塑造了淡泊天然的诗歌意境。而在这样淡雅的溪山风景中,世俗的欲望也被洗涤干净。类似的诗歌还有《将入前溪》:
来游适凉月,泉阿犹能翠。哑哑桨欲动,冉冉风当至。蝶鸟自得时,归鱼惬人意。新景永未腐,清赏待无事。襟致一超往,颜色洒然异。朴古真天游,涤除人间慧。(61)陈龙正:《几亭全书》,尹楚兵主编:《东林学派著作集成》第111册,第217页。
与《初入九锁山》其三相同,此诗同样描写了陈龙正泛舟旅行的经过。恰逢天气凉爽,作者乘舟出游,万籁俱寂,唯有桨声与风声阵阵。“蝶鸟自得时,归鱼惬人意”化用自《诗经·大雅·旱麓》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一句,意指万物各行其道,各得其所。作者非常喜欢如此质朴淡泊、天然清净的景色,认为它可以涤除世俗的烦恼与欲望。尽管两首诗描写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时节的景色,但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即语言质朴自然,塑造了淡泊雅致的诗歌意境,体现出了陈龙正“以淡为美”的诗歌审美倾向,是他“诗总为淡人嗜欲而设”诗学思想的体现。
作为一名生活在王朝易代时期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学者,陈龙正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实学特点,并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思想与实践。在过往的研究中,学界虽然已经注意到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但研究往往侧重于文学家群体。而以陈龙正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才是这场实学思潮的发起人与主导者。他们对实学思想的理解更为全面,受实学思想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因此,从实学角度出发对明末清初儒家学者的文学活动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探究这一时期儒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可以更为全面地展现当时学者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