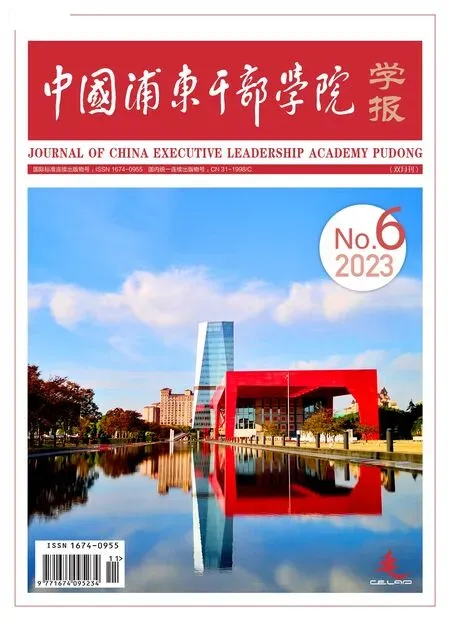《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研究导论
赵学清
(上海警备区 杨浦第四退休干部休养所,上海 200433)
从1930 年3 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中文译本出版以来,《资本论》在中国已经有90 多年的翻译和出版的历史。从《资本论》中文译本的出版时间、翻译内容、译著原本等方面考察,在《资本论》中文译本漫长的翻译出版过程中,产生了若干个《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但《资本论》中文首译本这个涉及《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史、传播史、研究史和文献学、阐释学、运用学等多领域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资学界足够的重视。现有的成果很少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即使在附带讲到这个问题时也都是大而化之,说法不一,缺少标准,不够严谨,甚至产生和流传了一些不太准确的共识①比如,现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1936 年出版的由侯外庐、王思华(分别署名玉枢、右铭)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册合订本是第一个完整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译本。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本文将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本文将提出《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界定标准并提出界定的初步意见,然后对研究这一问题的任务、意义和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引言。
一、《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认定原则
《资本论》及其手稿篇幅巨大,外文版本众多。从20 世纪30 年代起,我国一些学者和机构先后参与了《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事业。在漫长的《资本论》中文翻译出版过程中,出现了若干个依据不同外文版本、翻译不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的《资本论》中文译本,使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面临复杂的情况。在若干个中文译本中准确地认定《资本论》的中文首译本,首先需要简括地回顾一下《资本论》的中文翻译史。
(一)《资本论》中文翻译史述要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是《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出版后的第32 年,是《资本论》德文版理论部分三卷全部面世后的第5 年。在这一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在一篇译作中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思想。该刊第121 册发表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节译的《大同学》(原为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的《社会进化论》)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1]614虽然弄错了马克思的国籍,但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该刊第123 册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也。”[1]620①据资学专家徐洋考证,此段引文所依据的原文中的“资本”一词,原文为德文,用的是斜体字,指的就是《资本论》。参见徐洋:《〈资本论〉在中国的百年编译历程及现状》,《南开经济研究》2022 年第5 期。以《万国公报》的介绍为发端,作为人类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资本论》的思想开始在中国的大学和先进知识分子中传播。
《资本论》部分内容最早的中译文是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发表在1920 年10 月的上海《国民》月刊上,标题为《〈资本论〉自叙》。
1930 年3 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由陈启修(原名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内容包括第一篇的第一至第三章。陈启修的《资本论》中译本拉开了《资本论》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帷幕。陈启修原计划以十个分册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但不知何故,他在翻译出版了第一分册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潘冬舟(原名潘文郁)在遭受政治上的重大变故后于迷惘中逐渐认识到《资本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意义,于1932 年接着陈启修的译本继续翻译《资本论》。他同样计划以十个分册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1932 年8 月和1933 年1 月,北平东亚书局分别出版了由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第三分册。第二分册的内容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第三分册的内容是第一卷的第四篇。之后由于潘冬舟重新开始革命情报工作后不幸被捕并英勇就义,他的《资本论》翻译计划也戛然而止。
1932 年9 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由王慎明(原名王思华)和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内容包括第一篇至第三篇第七章。1936 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又出版了玉枢(即侯外庐)和右铭(即王思华)合译的中册(包括第三篇第八、第九章和第四篇)和下册(包括第五篇至第七篇),并出版了第一卷的合订本。自此,《资本论》第一卷接近全译的中文译本诞生了。以往资学界以为1936年出版的由玉枢和右铭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册合订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②如资学专家徐洋就持这样的观点。参见徐洋:《〈资本论〉及其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情况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 年第3 期。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玉枢、右铭译本在第23 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里少了极其重要的两节,即第三节《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和第四节《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③参见玉枢、右铭译:《资本论》第一卷(下册),世界名著译社1936 年版,第573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25—746 页。译者在第二节后加注括号解释说:“下缺两节译稿为蛮横的Gendarme 无理的检去。”[2]573但不管缺少译文的原因是什么,这两节内容是玉枢、右铭译本中所没有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重要论述正是在缺少的这两节当中。马克思在第四节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742相对过剩人口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指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743-744请问,缺少“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的相关译文,没有著名的“两极分化”论述的相关译文,这一译本还能称为第一个完整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吗?其实,除了缺少这两节外,玉枢、右铭译本在第23 章第五节《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中还缺少了C 节《流动人口》、D 节《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的内容。①参见玉枢、右铭译:《资本论》第一卷(下册),世界名著译社1936 年版,第597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65—774 页。玉枢、右铭译本缺少的这些部分,除了内容特别重要外,篇幅也不小。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的页码来计算,一共少了32 页,大约3 万字。所以,玉枢和右铭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本是不完整的第一卷全译本。
1934 年5 月,即潘冬舟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三分册之后、玉枢和右铭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册、下册之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吴半农翻译、千家驹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内容包括第一卷的第一、第二篇。虽然出版这个译本的出版社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社,但该译本在内容上并没有超过此前译本,故未形成较大影响。
《资本论》第一卷真正意义上的中文全译本和第二、第三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直到1938 年才出版。从1928 年开始,郭大力和王亚南先后投入到《资本论》三卷的翻译事业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38 年8—9 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1940 年5 月,郭大力校订《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而编制的包括1700 余处错误的详细勘误表,连同彭迪翻译的《资本生产物的商品》一文以《〈资本论〉补遗勘误》为名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 年,在哈尔滨解放区出版了根据勘误表修订的新版本。新中国成立后,郭大力和王亚南对他们的《资本论》中译本又进行了两次全面的修订。第一次修订本于1953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次修订本于1963—1966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40 年春,郭大力开始着手翻译考茨基编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该书在1949 年5 月先以“实践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一个月后又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
1955 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编译局开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译《全集》中文版。其中的第23 卷(1972 年 出 版)、第24 卷(1972 年 出 版)、第25 卷(1974 年出版)分别为《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第26 卷Ⅰ、Ⅱ、Ⅲ册(1972—1974 年出版)为《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1983 年,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自己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 年,中央编译局根据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中央编译局又依据MEGA2开始编译《全集》中文第二版,其中的第42 卷(2016 年出版)、第43 卷(2016 年 出 版)、第44 卷(2001 年 出 版)、第45 卷(2003 年出版)、第46 卷(2003 年出版)分别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卷法文版、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第二卷德文第二版和第三卷德文版的中译本。《剩余价值理论》的相关内容则以手稿的形式编入第33、第34、第35 卷中。
(二)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个原则
《资本论》在中国艰辛而曲折的翻译出版历程给界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提出了难题。在众多的《资本论》译本中,哪一本是中文首译本?是陈启修译本吗?当然是。从时间上看,陈启修译本无疑就是首译本。但是,从内容上看,陈启修译本仅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这只是《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一小部分;从翻译所依据的原本来看,陈启修译本依据的是考茨基德文国民版。考茨基版虽然有价值,但毕竟不是世界通行的德文第四版。所以,陈启修译本确实是《资本论》的中文首译本,但只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德文国民版内容的首译本。如果以上论述成立,陈启修译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首译本,那么以此类推,潘冬舟翻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分册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至第四篇内容的首译本……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如何界定的问题。在过去的《资本论》中国翻译史和传播史研究中,资学界还没有提出《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问题,因而《资本论》翻译史和传播史上的这个重要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甚至还存在和流传着一些不太准确的观点。笔者认为,研究《资本论》的中国翻译史、传播史、研究史、文献学、阐释学,以至于深化对“资学”的研究,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考证。
《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界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
一是时间的角度。所谓时间的角度,就是从时间上看,哪个中文版本的《资本论》翻译出版的时间在前,那个版本就是《资本论》的中文首译本,亦即时间在先原则。一般说来,在《资本论》翻译出版过程中翻译者都会有“争先”的意识,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分册的译者潘冬舟在其翻译过程中就明显地具有这种意识。在第三分册“译者言”中,他就提到王慎明和侯外庐的译本,指出其“在数量上虽然在今日还没有追上我译的前面,但据他们在广告上所发表的出版计划,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有着吸收较多助手的可能,以后或能追在我的译本之前面也未可知”。[4]2他表示“对于其余的部分,我们一定是尽量从速地继续出版”。[4]5由此可见翻译者对于出版时间的重视。出版社也非常重视出版时间,也会在版权页上体现这种“争先”意识,甚至精确到“日”。如1938 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当时并不知道国内有无其他出版社出版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文译本,所以在出版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时,就把出版时间精确到“日”。其确定的第一卷的出版时间为1938 年8 月31 日,第二卷的出版时间为1938 年9 月15 日,第三卷的出版时间为1938 年9月30 日。从出版时间来认定《资本论》的中文首译本,遵循的是时间在先原则。
二是内容的角度。《资本论》的篇幅非常庞大。从广义的角度看,《资本论》是一个卷帙浩繁的文献群,具体包括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马克思或恩格斯编辑或校译的各种外文版本,考茨基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德文国民版,考茨基整理编辑出版的德文版《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整理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俄文版两个版本,再加上数量庞大的《资本论》手稿,逾千万字。《资本论》的中文翻译,从一个人孤军奋战到有组织的联合作战,从20 世纪20 年代一直到目前,经过几代学者近百年的接力奋斗,作为文献群的《资本论》中文译本才基本出齐(目前尚有刊载《资本论》手稿的《全集》第二版第39、第40、第41 卷未出版)。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卷及其众多手稿并不是一个译者能够独立翻译完成的。众多学者的持续努力才使篇幅庞大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得以翻译成中文并正式出版。于是,从内容上看,谁翻译的《资本论》的那部分内容最先以书籍的形式正式出版,谁就是《资本论》那部分内容的中文首译者,这个版本就是《资本论》中文首译本。《资本论》的这部分内容已经由人翻译过,出过中文译本,则后来者对这部分内容的翻译就是再译,其版本就不是首译本。这是确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内容首译原则。如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分册,1930 年3 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其内容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过去没有人翻译过,也没有出版社出版过,则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理所当然就是《资本论》的中文首译本。又如,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其内容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至第四篇,分别于1932 年8 月、1933 年1 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二至第四篇的内容陈启修没有接着翻译,上海昆仑书店也没有继续出版,所以,潘冬舟所译的这部分内容是中文首译。由潘冬舟翻译、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理所当然地也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至第四篇内容的中文首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其第一篇已经由陈启修译过,第二至第四篇由潘冬舟译过,侯外庐、王思华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至第四篇就不是中文首译,其第五至第七篇才是首译,而他们译的第一卷作为一个整体,其版本也属于中文首译本。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则由于其内容已由陈启修、侯外庐和王思华翻译成中文出版,则不能算首译,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也不能算中文首译本。如此类推。
三是版本的角度。《资本论》有不同的原文版本,如第一卷就有马克思生前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德文第二版,马克思校订的法文版,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三版、德文第四版,恩格斯主持翻译的英文版等。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编辑出版和亲自校订的这些版本的主要内容虽然和通行本差别不是很大,但它们在《资本论》文献学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立的价值,因而这些版本的中文首译本的确定就不能简单地仅仅以内容为标准,还应该从版本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资本论》第四卷来说,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整理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不仅在内容编辑上存在差别,而且事实上就是不同的版本。所以,《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确定还必须考虑版本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编辑和校订的各种版本如果翻译成中文,应以出版时间和翻译内容为依据综合确定中文首译本。如中央编译局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中译本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中译本,虽然第一卷已经有多个中文译本,但从版本的角度看,它们仍然属于《资本论》某一外文版本的中文首译本。以《资本论》在文献学上有意义的版本为原本首次翻译为中文的可视为首译,其版本为中文首译本。这是确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版本首译原则。
二、《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初步认定
把时间在先原则、内容首译原则和版本首译原则综合起来考虑,检视《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可以基本确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情况如下。
1.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该译本于1930 年3 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其依据的原本是1928 年出版的考茨基德文国民版,参照了日本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河上肇和宫川实的日译本,内容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根据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陈启修译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中文首译本。
2.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该译本于1932 年8 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其依据的原本是1928 年出版的考茨基德文国民版,内容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第三篇。根据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潘冬舟译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第三篇的中文首译本。
3.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分册。该译本于1933 年1 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其依据的原本是1928 年出版的考茨基德文国民版,而内容是《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根据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分册潘冬舟译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的中文首译本。
4.玉枢(原名侯外庐)和右铭(原名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该译本于1936 年9 月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其依据的原本是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四版,同时参照英文、法文和日文等版本,内容是除第七篇第23 章的两节和两小节外的第一卷全部内容。该译本中,第五、第六篇和第七篇除第23 章的第三、第四节和第五节的C、D 两小节外的译文是中文首译,但由于该译本没有包含《资本论》第一卷全部内容,所以只能视为接近全译本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首译本,还不能看作完整意义上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首译本。
5.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该译本分别于1938 年8 月31 日、9 月15日和9 月30 日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依据的原本是“苏联1932—1934 年马恩列学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底本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5]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依据的原本不同于已经出版的陈启修译本、潘冬舟译本、玉枢和右铭译本依据的原本,且第23 章第三、第四节和第五节的C、D 两小节内容是中文首译,所以,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第一卷作为一个整体,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和中文首译本。其第二、第三卷译本全部符合时间在先、内容首译和版本首译三原则,更是当之无愧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中文首译本。
6.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该译本依据的原本是考茨基编辑的德文原版,内容为全部,由实践出版社1949 年出版。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符合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是《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的中文首译本。
7.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该译本依据的原本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6 卷,内容为全部,由人民出版社1972—1974 年出版。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符合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是《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中文首译本。
8.中央编译局根据法文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该译本依据的原本是马克思自己校订的、由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公司出版的法文版第一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出版。该译本符合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是马克思自己校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的中文首译本。
9.中央编译局根据德文第一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该译本依据的原本是“马克思亲自付印的《资本论》第一个版本即第一卷德文第一版”,[6]说明1内容为全部,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年出版。该译本符合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是马克思亲自付印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中文首译本。
此外,中央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第二卷,作为《全集》的第23、第24 卷于1972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三卷作为《全集》的第25卷于1974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单行本。这一版本依据的原本是《全集》德文版第23、第24、第25 卷。虽然中央编译局译本不是《资本论》的中文首译本,但它是在以往《资本论》译本尤其是在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基础上,集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大家的集体智慧而产生的权威版本。虽然按照认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三原则,中央编译局译本不是《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但它是研究其他中文首译本的坐标,对于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至于首次翻译出版的《资本论》手稿算不算《资本论》中文首译本,这一问题在这里暂不讨论。以上关于《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认定原则和认定意见仅仅属于个人初步研究心得,欢迎资学同行不吝赐教。
三、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任务
确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搞清《资本论》中文首译本译者的生平事迹。根据上文对《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初步界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译者有数十人。要搞清楚这些译者的自身情况、政治面貌、教育程度、主要经历,比如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翻译《资本论》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面对和解决了什么困难,译文的风格如何,译本有什么特点,等等。
二是搞清《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所依据的原本。《资本论》有不同的外文版本,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研究还要考察:中文首译本依据的原本是哪一种外文版本?译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外文版本?《资本论》的译者一般会在“序言”中对所依据的原本及选择的理由作出说明,如陈启修译本就在“译者序言”中明确地告诉读者,其依据的原本是考茨基编辑的1928 年德文国民版,选择这一版本的理由是它好于其他版本。而有的译者则没有对其所依据的原本作出说明,如潘冬舟译本,这就需要进行考证。在搞清翻译所依据的原本的同时,还可以顺带搞清译者翻译时所参考的外文版本。
三是分析《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中政治经济学术语和关键段落的翻译准确程度。《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通过科学抽象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范畴之间的转化、范畴之间的必然联系,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是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这一伟大革命必然伴随着专业术语的革命,出现了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利润、利润率、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利息、地租、绝对地租、级差地租等一系列专业术语。在政治经济学知识尚未在中国普及的时候,这些专业术语在《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中是如何被翻译的?这些译名有无受到别国译文的影响?各个《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对这些术语的翻译有什么不同,是怎样一步一步达到现在这种水平的?同时,《资本论》又是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块整钢,它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它还涉及哲学、政治学领域的专门术语,如辩证法、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所有制、阶级斗争、革命、经济社会形态等,涉及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社会革命运动的结论等。首译本中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范畴,同时还有哲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范畴穿插其间,主要以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为分析结论,因而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中这些范畴术语和关键结论的初始翻译状况及后来的完善,不仅对《资本论》翻译史、传播史研究有意义,更对《资本论》阐释学、研究史研究有意义。
四是分析《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中人名、地名和技术名词的翻译准确程度。《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牵涉大量的人名、地名、技术名词等。这些名词在《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中是如何被翻译的?存在什么问题?《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西学东渐的过程是相互交叉、相互伴随的,《资本论》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和技术名词也有一个逐步规范化的过程。除了由这个规范化的过程引起的问题外,各个译本本身的人名、地名和技术名词翻译还存在哪些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
五是分析《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中的误译、漏译的情况。要翻译如此重要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著作,译者往往受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译者还是在战火纷飞、国土沦丧这样的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事《资本论》翻译工作,缺乏足够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因而一些《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可能存在误译、漏译的情况。我们不应苛求这些译者,但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就必须发现和分析这些情况,搞清楚这些情况是如何在后来的译本中得到纠正的。
六是搞清《资本论》重要外文版本的中文译本的不同之处,理解《资本论》重要外文版本和中文首译本的价值。在我国《资本论》翻译史上,《资本论》第一卷有依据考茨基德文国民版、德文第四版、德文第一版、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版等外文版本翻译的中译本,第四卷有依据考茨基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全集》德文版《剩余价值理论》、历史考证版《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翻译的中译本,《资本论》手稿则被编入《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这些依据不同外文原本翻译的《资本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佐证,是研究《资本论》形成史的重要资料。考察这些重要外文版本的中译本的差异,理解《资本论》重要外文版本的价值,是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重要任务之一。
弄清上述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深化对《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认识,还有助于推动《资本论》翻译史、传播史、研究史、文献学、阐释学等资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当然,解决上述问题不是一个人、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资学界接续努力,不断探究。
四、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意义
(一)《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研究有助于深化《资本论》中国传播史研究
研究《资本论》中国传播史,就要梳理《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揭示《资本论》在中国传播的规律。研究《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必然要牵涉《资本论》中文首译本。过去《资本论》中国传播史研究对《资本论》中文首译本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也比较笼统。比如,对由陈启修最早翻译、上海昆仑书店最早出版(1930 年3 月)的《资本论》第一分册,直到2019 年才有一篇专门研究论文。而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是,谁第一次用中文翻译出版了《资本论》或《资本论》的不同部分?从《资本论》部分内容的翻译出版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部翻译出版,都有哪些人和机构是《资本论》的首译者和首先出版者?数百万字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翻译是如何从部分到全部、从“译稿”到完善的,其间经历过哪些曲折过程?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搞清《资本论》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弄清《资本论》首译本的译者和出版者,确定《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对以上这些和《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有关问题的回答将为深化《资本论》中国传播史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础。
(二)《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研究有助于深化《资本论》文献学研究
《资本论》在创作、形成、出版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文献,核心文献有:马克思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马克思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意见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恩格斯编辑的“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3]36的第一卷德文第四版;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遗稿整理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卷德文版;恩格斯主持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手稿和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稿等。《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所收入的著作和手稿就是《资本论》文献学所要研究的核心部分。其外围文献包括《全集》所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笔记、书信等,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及的主要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著作等。研究《资本论》,首先要掌握《资本论》文献。中国学者研究《资本论》文献学的理想条件是在掌握《资本论》基本思想的同时熟练掌握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所使用的主要语言,如德语、英语、法语等,并运用这些语言来研究《全集》历史考证版中的文献。但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这种理想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这样,就只能通过中文译本来掌握《资本论》的核心文献。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资本论》文献以及这些文献传入中国的初始状况。对比中文首译本和其他各个版本特别是完善本,就可以在了解《资本论》文献的同时全面掌握所研究的文献,推动《资本论》文献学研究。
(三)《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研究有助于深化《资本论》阐释学研究
研究《资本论》,首先就要明白掌握《资本论》的思想实质。《资本论》阐释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资本论》文献,准确阐释《资本论》的对象、方法、范畴、范畴间的关系、范畴的运动所反映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等。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只有借助于《资本论》的中文译本,才能阅读和研究《资本论》,阐释《资本论》。《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是中国人对《资本论》的最早理解和研究。而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可以发现中国人对《资本论》基本思想首次理解的程度,可以发现《资本论》中人名、地名、技术术语的初译和最终定译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名词术语和关键段落的不同翻译和最终定译间的发展过程。各中文首译本的译文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资本论》术语的不同理解,在对比中分析研究不同版本、不同译者的译文,可以明确这些术语的准确含义,为《资本论》阐释学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四)《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研究有助于深化《资本论》研究史研究
中国人对《资本论》的研究是从翻译《资本论》开始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资本论》的过程就是研究《资本论》的过程。只有对《资本论》的内容有准确的理解,才能把《资本论》从原文准确地译为中文。没有对《资本论》的初步研究,就无法翻译《资本论》。从《资本论》部分内容的首译到《资本论》全四卷的首译,从《资本论》部分手稿的首译到《资本论》全部手稿的首译,这个过程也是《资本论》研究史的一部分。潘冬舟烈士曾说过,对于《资本论》这样的重要著作来说,他翻译的只是“译稿”,而这些“译稿”却为最后的完善的译本提供了讨论研究的基础。与此同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也为学者和大众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大众通过中文首译本可以直接了解《资本论》的思想,研究《资本论》的理论,运用《资本论》的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学者和大众在阅读和研究中又会对翻译提出意见,尤其是懂外文的读者的意见会推动译本的完善。因此,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有助于推进和深化《资本论》研究史研究。
五、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方法
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没有捷径可走,首要的方法是熟读译文。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先要非常熟悉《资本论》通行本,在对通行本有一定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本一本地反复研读不同的《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在熟读《资本论》通行本和各个中文首译本的基础上,研究者的头脑里就会呈现出各个不同版本的影像,问题就会逐渐浮现出来。只有对《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烂熟于心,才谈得上研究。
其次是比较。在熟悉通行本和各个《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文本的基础上,就可以就上述提到的要解决的任务一个一个地进行互文性比较。比如,在《全集》本《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8而对于这段关于研究对象的论述,作为《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陈启修译本是如何翻译的呢?陈启修译本的译文是:“我在本书里面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那些与它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并交易关系。这些东西出现着的模范场所就是英国。”[7]167之后可以再看玉枢、右铭译本的翻译和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翻译。对比几个典型版本,尤其是和完善的《全集》本进行对比,马上就可以发现《资本论》这部分内容的中文首译本和《全集》本在名词术语上的重大差异。发现《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和《全集》本的差异,就为进一步的考证创造了条件。熟悉《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翻译原本的还可以进一步将译文和原文进行对照,不熟悉《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翻译原本的可以将各种版本的译文与《全集》本的译文进行比较,发现《资本论》中文首译本译文的长处和问题等。
最后是考证。比较的目的是发现问题,然后通过系统的考证来解决问题,得出结论。通过考证,可以发现《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存在的问题,概括出《资本论》中文首译本的特点,把握《资本论》中文首译本在推进《资本论》中译本完善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弄清其在《资本论》中国传播史上的地位。
研究《资本论》中文首译本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笔者将以《资本论》中文首译者为榜样,一步一步地展开研究,期望能够为繁荣资学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同样也期望资学界有兴趣的学者们一同参与,通过此项工作来推动资学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