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
陈振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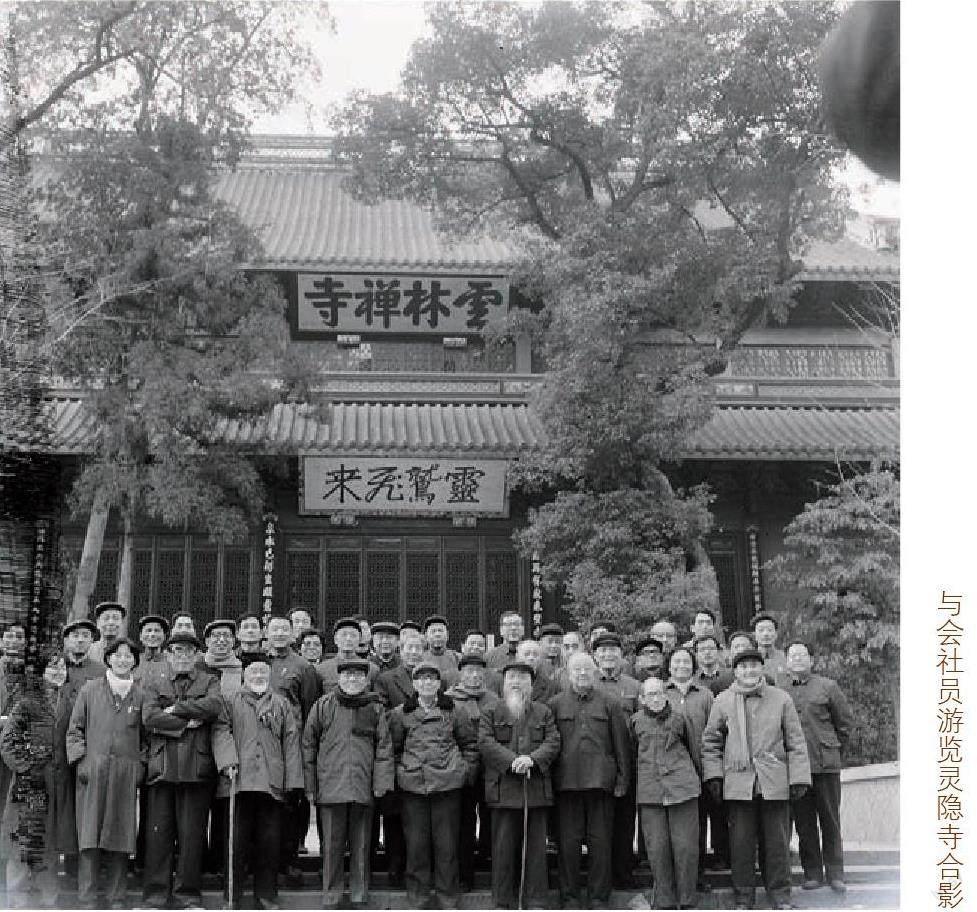
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以来重要学术活动如金石学、印学、书学与印学、国际印学论坛、国际印学峰会等方面学术研究的展开:西泠印社建社一百二十年,尤其是百年社庆以来二十年间的学术活动非常丰富多彩。我们原来对西泠印社的定位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保存金石的功能基本移交给了博物馆及文物管理委员会,西泠印社保留下来的就是『研究印学』。
当然,『研究印学』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因为大部分印社是研究篆刻实践。自从沙孟海先生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以后,提出要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所以我们对于『研究印学』这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双轨并行发展的;但相对而言比较重视理论的研究,包括篆刻学、古玺印学、书学,还有画学的研究。目前看来,西泠印社能够在这二十年里立于不败之地,为大家尊重和关注,其关键就在于它站在印学的制高点上。前期西泠印社的印学学术研讨会是五年举办一次,当时的出版条件及整个的学术氛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积累都不够,所以当时的学术水平在目前看来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在百年社庆以后,西泠印社印学理论研究研讨会的频率从五年一次变成一年一次,在最早的几年里甚至是一年两三次。这种频率的加速伴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改革开放,大量喜欢或者从事印学研究的人,忽然找到了西泠印社这样一个学术交流、发表的平台。我认为,当代印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与西泠印社贯彻沙孟海先生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非常吻合的,且从中获益匪浅。沙孟海先生本身是个学者,在书法学、篆刻学以及几乎所有与之相关的学术领域都有所涉及,而且都有比较好的成果。这就使得西泠印社在这些年里,其篆刻实践鹤立鸡群,印学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对于以前的各位社长前辈来说,今天西泠印社的发展,尤其是对学术方面的重视,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具体且唯一的发展特征。
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以后开始有『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每年或者几年一度举行的国际印学研讨会,以及印学专题研讨会,这三个架构差不多就构成了西泠印学这二十年来的发展脉络,这三个架构的层次也成为这二十年来重要学术活动的思想引领和专业拓展。我认为,这是西泠印社二十年来的重要学术活动,是我们给这二十年的发展交出了一份答卷,这份答卷在目前看来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其后,学术研究的内容又有所拓展。比如百年社庆以后,我们针对一九0四年西泠印社创社时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增加的『兼及书画』这三个宗旨,又做了一个前后的衔接,使其既有传统的来源,同时在新的发展时代又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新的思想和阐释。
关于『保存金石』,西泠印社在百年社庆以后特别提出要『重振金石学』。『保存金石』和『重振金石学』的区别其实很大。『保存金石』是关于博物馆及文物收藏、鉴定的学问,是以实物的交易或移置的方式为代表,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金石文物走向市场、走向交易这一行为,在国家的文物法里一开始是被禁止的。我记得当年沙孟海先生说,西泠印社『保存金石』这项功能已经移交给了博物馆及文物管理委员会,我们今后所能做的就是『研究印学』了。但篆刻和金石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强调,既然印石的实物属于文物,不能在民间私下交易与收藏,我们就开始做关于金石的学问,这也是『保存金石』的一种方式,于是就有了『重振金石学』这一理念。当然,这个理念的提出还有一个背景。民国以来,在新学科的架构之下,『金石学』这一学问已经消亡了,其中文字的部分进入古文字学,碑帖的部分进入书法的碑帖之学,器物的部分就进入了现在的考古学及古器物学,文字的叙述就进入了现在的古文字学及古文献学。『金石学』就此被分解到各个学科里面去了。
这样一来,鉴于『金石学』其本身作为一个『学』来说已经消亡了,但是它的内容在其他的学科里都有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西泠印社应该怎样做到『保存金石』?于是,我们就把『金石学』这一概念重新提出来。通过不断地实践,做到了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个是关于碑帖传拓和镌刻技术的复原。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碑、帖都可以用印刷来完成传播,所以传拓的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没有消亡,但在不断衰落。我们当时恢复的第一个研究就是碑帖的传拓和镌刻技术。
第二个是研究已经失传的青铜器全形拓。全形拓其实是在清代中期以后才慢慢开始发展起来的,这一技艺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上海兴旺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因为时势的关系又逐渐消亡了。所以我们又把青铜器全形拓(立体拓或者叫器物拓)技艺传承下来。
第三个是碑帖的题跋。当时特别提出了碑帖的题跋要有『五功』,即要有五种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碑帖的题跋需要五个不同的规则,以供人遵守。
第四个是器物拓的传播。譬如说砚铭、墨锭、玉器及文房都可以做器物拓。有个比较好的实践是和山东的淄砚进行合作,做了砚铭及其他文房用具的一些拓本。当然,汉代的砖瓦以及小型的画像砖等都包含其中。
第五个是『大众金石学』。这其实是倡导、推动金石学以加厚其社会基础。按照金石学的眼光来看,所有东西都可以拓,即『世间万物皆可拓』『世间无物不可拓』。比如椅背的雕花、床角的刻纹、陶瓷水缸上紋样以及窗纹、门楣等,所有生活中遇到的,甚至一个竹编都可以拓。在当时也办过一个展览,让喜欢金石学与金石传拓的人,都通过『重振金石学』找到自己的空间。我认为,这是关于『保存金石』,从保存金石文物到研究金石学所涉及的各个范围的发展。
再来说印学。原有的印学是指向明清篆刻,因为古玺印都属于收藏品。当然篆刻里也有一些研究古玺、金文的内容。我们现在以印学为核心,进行了比较充分地展开。比如从印学研究进入印学的使用,像是篆刻的器具以及印谱的制作等,就是印学的第一个展开。第二个展开是对印学做一个学术上的拓展。原本的印学因为是一种技艺的传授,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师父会什么就教学生什么,即传统意义上的『专攻一家』。以这样的方式,在师父和徒弟之间代代相传。当然,西泠印社这几十年来,在印学方面做了非常大的突破。每一次印社举办的印学评展,展览的征稿要求都会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自选动作』就是将自己印章最得意、最用心的一面展示出来;『规定动作』,比如刻出封泥、唐宋官印、元朱文、古玺印等一路风格的作品,每一年都出一个考题。一开始大家也会觉得有点纠结,因为某一个人可能刻元朱文刻得很好,让他刻古玺印一路就不一定擅长,或者遇到烂铜印、将军印等『规定动作』,会完全适应不了。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西泠印社在做的这项工作让一部分篆刻家觉得很难适应,但是十年过去,回过头来宏观地去看,就会发现西泠印社作为百年名社的引领作用,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
今天篆刻界的百花齐放,其实和西泠印社在百年社庆以后每一期篆刻征稿中的『规定项目』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形式,就是逼着篆刻家不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进行篆刻实践,还要去尝试一些自己不大熟悉的,甚至是从来没关注过的风格。这样的话,一个宏观的印学流派史和技法史,就被清晰地梳理出来了。这以后,浙派、邓石如皖派、黄牧甫金文或者吴昌硕石鼓文,还有古玺、巨印(烙马印),甚至还有多字印(一方印章十个字以上),都成为西泠印社当时考试的题目。通过每一年不同的考题,逼得篆刻家不再把篆刻简单看作是某一个很窄的领域的技艺传承,而把它看作是一个浩瀚的古印和篆刻世界的一种分布。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得去了解它,不一定是最擅长,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得知道篆刻有这么多的类型,而不只有我们擅长的类型。这个举措对于后来的篆刻家,包括今天的印坛,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可能刚开始有些篆刻家跟不上,但没关系,他后面慢慢就会有所体会,例如他原来只是刻邓石如风格的,忽然给他一方汉代的将军印,让他来试试看,一开始会觉得很陌生、不适应,但是他会慢慢开始觉得,其实印学实践的世界非常大,之前我们是自己没有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开始关注了,并且开始钻研了。这个是印学的,当然可能是篆刻实践这个部分的。
还有书学和印学之间的关系,西泠印社的国际印学峰会和论坛,也开始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当时西泠印社想要有所创新,设立了一个创新的目标,叫作世界印章史。当时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而篆刻都是古文字,它走出去也没人看得懂。所以西泠印社在举办国际印学峰会和印学论坛的时候,特别强调『世界性语言』,第一个是图像语言,第二个是外国文字的语言。这些文字、语言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印章史里面都有体现,图像语言如汉代的肖形印以及图形印等;至于非汉字的印章,如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西夏印,元代蒙古八思巴文印,一直到清代满文印等。但过去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分支,不重视,现在站在世界印章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印章有其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在做阿拉伯、古波斯、古希腊等图形和文字印章创作实践。这个方面其实是从研究开始的,我们在二0一六年曾经办过一场关于『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次接受挑战。到二0一八年,我们又办了一个『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个研讨会对于我们来说,其中的拓展和创新并不是拍拍脑袋瓜,而是有学理支撑的。这两个研讨会配套出版有一千多页、分上下两册的论文集,我们有信心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一直到今天,我们策划的『一带一路』和迎亚运风采的篆刻展,很多都是用图形元素来表现。所以,就金石学、印学和篆刻实践来说,『重振金石学』是恢复学理传统,然后列出了五个拓展领域和分支领域;印学是篆刻传统的实践,实践的部分其实就是十年来每次出一个新课题,像去年举办的『以篆入印——邓石如、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当代印风创作研究主题展』,梳理邓石如、徐三庚、赵之谦印风这一条脉络。这其实都属于一种引领,不是篆刻家会什么就提交什么,而是西泠印社作为百年名社,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引领作用。所以在传统的风格方面,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进。
然后是国际印学论坛和印学峰会,它们其实要强调的是『国际』。其时正逢国家的『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样的战略和政策,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开展『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世界图纹与印记』的研讨会。它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世界印章史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化自信,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而且是以印章的形式。所以,又有今年九月份西泠印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合作。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西泠印社所要表达的东西虽然是小众的,但也是有世界性的。如果我们都是用古文字刻印的话,其世界性就很有限,大部分人都看不懂。
所以西泠印社这二十年的活动,我把它理解为,第一个是『重振金石学』;第二个是对印学实践的引领,包括时代风格和流派技法;第三个是在国际印学方面的拓展,包括世界印章史、图形印和非汉字系统印章、世界图纹印记以及『一带一路』等几个区块的划分。印社举办的研讨会里面也有很多一流的文章,通过每一年秋季雅集时举办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基本上形成了一批以教授、硕博士为标杆的印学研究新兴力量。当然,西泠印社在学术论文评奖入社这一块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进行配合。
现在,以西泠印社为核心的印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形成,而且他们的水平并不亚于其他人文学科或者艺术学科。当然,我们还是要记住沙孟海先生提到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其中『国际』二字,我们过去的理解就是请几个外国学者带着论文来参会。但现在一想,以『世界图纹印记』研讨会为例,『国际』不是因为与会学者的『国际身份』,也不是一篇论文的『国际性』,而是指学者要走出去,要主動去寻找『国际』的新含义。同时,在印学实践方面,创作的印面内容都必须是『国际』的,既要有中国传统的核心,也要有国际的辐射面。在这方面,饶宗颐社长也特别提出要『播芳六合』『东学西渐』,中国的学问要往西方走,向西方推出。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创新和拓展,都是一些精神上的指引。因为西泠印社这些老先生长久地对于未来的洞察,我们才有机会来做这些事。
当然,除了印学实践与重要学术活动之外,西泠印社的组织架构,在其中也有非常多的配合,包括活动费用的支持,对新社员吸收的组织体制改革,以及每一年的社务活动等。可以说,没有这样的组织配合,很难在短短二十年里做这么四面出击式的改革。因为组织配合得非常融洽,所以这些活动都能推进。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就开始把很多的探索指向『大印学』。『大印学』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学科交叉』,一个是『文明交融』。当然,对于传统篆刻,我们也还是在持续地推进。『大印学』主要对这个学科顶层做一些设计,所以印学里面会有金石学。原先印学是『金石学』里很小的一部分,但现在用『大印学』的方式,『大印学』如果作为顶层设计,就会把金石学作为『大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的组合关系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只要在学理上有足够的支撑,那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创新,而且是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所以,这几个方面如果能够连起来,可以说西泠印社既有篆刻实践、理论研究,也有对观念的厘清。
西泠印社重要展览活动的开展:目前西泠印社的展览活动其实是非常密集的,包括好几个系列展。因为有孤山这样的一个印学圣地,所以除了大型的展览以外,还有很多各层次的展览。比如春秋两季雅集的大型展览,全国各地印社到孤山举办展览,还有各个印学的地域团队和人才集群到西泠印社来办展览等。当然也有很多个展、收藏展,以及西泠印社与其他的相关机构所举办的联展。这些展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学术性最强的应该是每一年秋季雅集的大展。当然春季雅集的展览也有很多,像去年举办的『以篆入印』展,今年在宁波的春季雅集,举办了涵盖已故的宁波籍和当代的宁波籍社员的『西泠印社宁波籍社员作品展』。西泠印社每年都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展览。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类型的展览,比如今年九月在黑龙江举行的『黑龙江籍社员作品展』,接下来在西安也会有一个四省社员的联展,还有如山东济宁访碑的活动等。通过这样的活动,西泠印社横向和各个专业机构,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展览在目前看来是西泠印社最活跃的一个部分。
尽管如此,西泠印社还是不断在琢磨、研究如何提升展览的学术高度,包括这次在宁波举办的『一带一路』图形印系列名家作品展。展览虽然遍地开花,但展览的学术含量更是西泠印社这样的百年名社所格外重视的,甚至要作为主要目标来研究。每一次展览能不能被记入历史,就像过去十年,西泠印社的篆刻评展向全国征稿,征稿每年出一个题目,十年下来,整个印学史的各种的样式、风格、技法、流派,被全部梳理了一遍,这在印学史里是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被提及的。那么今后,展览无非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广』,一个是『高』。『广』是我们有全国的机制,篆刻评展等各种各样的专题展;『高』是我们在展览方面还需要有一些新举措。
这段时间因为『大印学』的发展及『一带一路』『迎亚运』等契机,西泠印社在展览上其实已经有比较大的突破。展现给世人的,第一部分是有关亚运会的传统篆刻创作,内容包括十九届亚运会的口号,每一个运动项目的口号,每一届亚运会的基本理念和口号;第二部分就是图形印,以参与亚运会的四十五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为基准进行的印章创作,在宁波『一带一路』专题展,则是以一百五十二个国家和三十二个国际组织的文化基准来进行创作。
这是西泠印社这段时间在展览方面的创新,当然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新的尝试。以前西泠印社有很多重要展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如『中国历代印谱特展』『金石学发展与青铜器传拓(全形拓)精品展』,另外浙江在倡导宋韵文化,于是就有了『宋代金石学与印学特展』,更早的还有关于印章收藏史的展览等。当代的创作型展览是一个脉络,学术研究型展览又是一个脉络,把这几个脉络结合起来,其实就能看得出西泠印社的展览、创作、比赛、评展整体的架构。
西泠印社近三十来国际交流与拓展活动的展开:过去,西泠印社的国际交流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们派一个代表团,通过外事办公室出访希腊、意大利。这是西泠印社在那个时代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是现在的国际交流仅仅靠这种出访恐怕范围太小,所以我们开始倡导国际交流,亚运会就是我们抓住的一个机遇。
在国际交流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先解决理念问题,即『文明交融』。中国要有文化自信,但也要平等对待其他所有的文明,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交流。所以西泠印社在国际交流方面,有非常多原有的传统做法,也有现在比较新的做法。
中间还有一个拓展活动,即西泠印社与中国香港集古斋联合创办的香港『西泠学堂』,这个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关,西泠学堂的启动、开班以及后面由香港『西泠学堂』延伸到其他国家及地区,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澳门、台湾等。之所以会以香港『西泠学堂』为拓展,是因为它是饶宗颐社长和国家方面的领导人一起配合促成的一件事。饶宗颐先生登高一呼,使西泠学堂的国际拓展提高了水准。西泠学堂自二0一八年开班以来,每年在香港分春秋两季招生,开设国画、书法、篆刻三门课程,并且每年定期组织一次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游学活动。西泠印社与集古斋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与实践探索意义。
此外还有『百年西泠·中国印』海外系列展览,进一步扩大了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与力度。
西泠印社教育培训和社会公益的展开:西泠印社开展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如中国印学博物馆『印之爱』的公益活动,在十多年以前就开始了。最近五六年,最兴旺的是由西泠印社社员自发兴起的『西泠公益行』,就我所知,他们已经去到四川、青海、陕西、甘肃、贵州等地区,到目前为止有十余场。『西泠公益行』的可贵之处在于西泠印社只是发出了号召,分布在各省的西泠印社社员作为本地的文化名人,都自愿来参加西泠的公益活动。公益的概念,就是没有报酬,纯粹向社会付出的。但是这个部分完全不是西泠印社的社委会、党委要求,而是社员自发自觉地到西部文化不是太发达的地方去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去西安、甘肃,针对碑刻与简牍进行学习交流。所以,『西泠公益行』在目前看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讲求社会效益的活动,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活动是由我们的社员自发组织的。
教育培训方面,目前西泠印社也不断用新的课题来进行教育培训,多年来培养了很多的篆刻家。当然教育培训与社会公益的背后,还有西泠印社社委会、书画篆刻院之间的配套活动。所以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设有文物处、信息处、社团处、创研处等处室,其实这些处室本身是个机关,但是机关后面运作的平台,其实就是这么多的项目活动,项目多了,活动就办起来了。在社会公益和教育培训方面,今后还可以有更多的意义提升,包括在理論上证明其可行性。
目前看来,展览和学术研讨会是西泠印社的双轨。展览很多地方都在做,无非西泠印社是引领者,并且在西泠印社新的理念之下,展览会有更多的突破。除了展览以外,西泠印社一定要有学术研究的支撑,而在目前的专业团体里面,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和金石学研究,可能是支撑力最强、人才最多的。
所以如果把这些方面理顺,那么我们大概就能找到一个西泠印社的发展路径。另外,西泠印社社刊《西泠艺丛》,它不光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同时还是一个学术研究、交流的平台。我记得去年我们整理过一次社刊的专题,一期、两期可能没感觉,但很多期全部放在一起一看,还是洋洋大观。的确是二十年来没有虚度年华,还是做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专题,而且有些是别人都没做过的专题。所以在这个方面,从西泠印社所做的这么多事情,就能够看得出它具有唯一性。
现在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大家对金石学、碑帖学、印学,包括书法学、中国画学、诗词学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大环境的背后,最终决定社团的高度和含金量的,其实关键还是在于社团有什么样的思想支撑、学术支撑。西泠印社成就较高的原因是有思想引领,而且一旦有思想引领,它不是先做实践,而是先从理论上证明这件事的可行性,有学理支撑以后再来做实践,那就能从容不迫、神定气闲,每一件事情在还没启动的时候就可以做到非常有把握,知道应该怎么样往下走。这二十年来西泠印社的发展,其实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把这些内容再结合到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中,包括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七任社长,以及更早的四位创始人,就能看出今天西泠印社的全貌。当然除了四位创始人和七任社长以外,还有一些西泠印社当年的中坚力量,如陈伯衡、高络园、唐醉石、韩登安、葛昌楹、张鲁庵等,他们作为西泠印社的前辈,需要我们好好维护,甚至推仰,《西泠艺丛》社刊也都做过他们的专题。如果把这些展示出来,就能看到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的图卷,它是有血有肉、骨骼丰满的。西泠印社作为百年名社,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学术集体,它有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其功能更是要为这个时代的篆刻、印学、金石学树立标杆、建立高度、塑造品牌。它要作为引领,指明未来的方向,我觉得这一点目前的西泠印社已经做到了。它是在前面的引领者,而不是在现阶段的自我满足。
西泠印社始终在一个未知世界里等着你、启发你、带领你。这种引领对西泠印社来说,最近的概念就是『大印学』。篆刻家还在沉迷于自己的技巧的时候,西泠印社已经开始做世界印章史研究、文明交融、学科交叉等一系列事情。这些事情完成以后,就使得西泠印社在目前是獨一无二的,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也很难有其他人像我们做得这么专业、有高度。单独一个活动可能别人也做得不差,但是综合来看,西泠印社其思想观念的引领和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强有力的社委会的各个处室的工作,有编辑部的工作,还有几个机构互相之间的支撑,才能够把西泠印社做到目前大家来看是『高山仰止』的地位。我们现在看西泠印社四个创始人,再到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先生他们这一代,直至饶宗颐先生,都是『高山仰止』,也希望后继从事篆刻的中青年看西泠印社也是『高山仰止』——其实目前已经是这种情况。大家都认为孤山是圣地,都认为西泠印社令人『高山仰止』,这点其实是今天西泠印社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当然西泠印社的功能就是『为往圣继绝学』,金石学、金石传拓、印学、古玺印学、明清篆刻以及世界印章史,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绝学』,不『继』它就没了。当然我们一『继』,衍生出很多学术的大框架。所以对今天以及今后的西泠印社来说,『为往圣继绝学』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标杆,包括文物收藏,西泠印社还是在努力地按照自己的轨道走。『继绝学』中的很多『学』是消失了,比如『金石学』,所以西泠印社要把已经在中国的学科目录里面消亡的『金石学』重新恢复起来,并把一个非常庞大巍峨的、灿烂的金石学世界打造起来。我觉得这是西泠印社的『为往圣继绝学』,还包括青铜器全形拓的恢复,以及篆刻评展中的规定动作,这都是『绝学』。理论研究的『一带一路』还不是『绝学』,那是原来没有的『学』,是重新创造的『学』。
本文为作者访谈整理而成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西泠六子偕友8人书法艺术展
——读《中国印学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