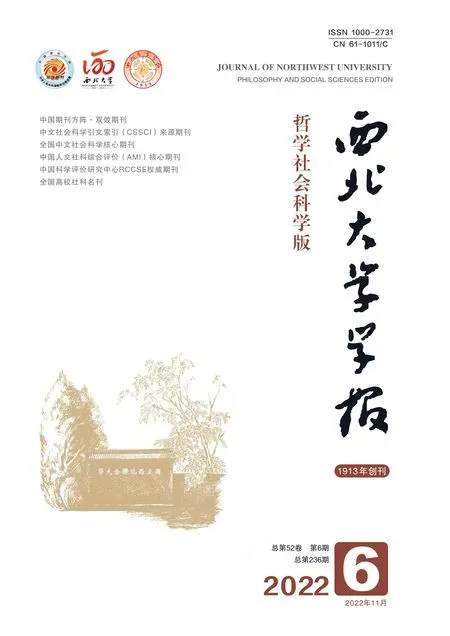学科交叉视野下的敦煌社会史研究及其展望
王晶波,马托弟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1900年敦煌文献的发现, 为世人打开了一扇回望中古敦煌的窗户,透过这扇窗口, 人们可以切实了解古代敦煌民众的生产生活、思想信仰、文化风俗,知道他们的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 信仰风尚、 民族构成的具体情状。 周一良曾说: “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 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1]456。 这些宝藏,为研究中古时期的敦煌乃至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直接资料。 张国刚在纪念敦煌石窟遗书发现百年之际, 特别指出敦煌文献在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 民间社会, 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帝王将相’的荣辱兴衰。 所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 特别是地域史、 人口史、 婚姻史、 家庭史等, 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 而敦煌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2]
除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珍贵文献,古代敦煌还以其丝路重镇的交通位置,汉胡杂居的民众,底层多元的文化,佛教石窟壁画内容的丰富以及长时段区域发展的社会,为今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古代西北地方社会的绝佳样本。这也就决定了有关敦煌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旨趣、内容范畴,还是理论方法、意义价值等方面,都天然地与社会史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无论自觉与否,敦煌研究的成果事实上也是敦煌社会研究的发展与体现。敦煌社会史以其百余年的研究实践,构成了中古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这门学科的发展进步,从资料、研究旨趣及理论方法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回顾百余年来敦煌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敦煌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受到了敦煌学整体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史研究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敦煌社会史的研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与态势。
一、近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与敦煌社会史研究的起步、发展
敦煌学研究开始之际,正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发生剧烈变革之时。两千年的专制王权统治结束,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科学、民主观念的提倡,动摇了传统思想与学术体系的基础。社会与学术的注意力,由原本偏重于经史与王朝政治,逐渐转向对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及思想的考察研究,反映中古敦煌社会与民众生活的敦煌文献恰逢其时公布于世,很快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09年至1949年,是敦煌学与敦煌社会史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敦煌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整体上是同步的。从内容看,敦煌学研究始于对藏经洞所出文献的考证与研究,虽然不少学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其中的传统经史典籍,但敦煌材料的多元性与世俗性,远远超出了传统经史之学的视野与范围,其新异内容多是人们前所未见,尤其是反映社会基层民众生活、思想及习俗的内容,很快就引起众多历史、文学、语言学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相关研究者中,那些较早接触西方学术思想、拥有更开阔学术视野的学者以及留学海外的学人,对此类民间社会材料及相关问题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这一阶段的研究,一方面是抄录、整理、刊布文献资料,编制文书目录;另一方面是利用这些新的社会史料,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史事、家庭户籍、土地乡里、教育、风俗及通俗文学、民族语言等方面展开研究。两个方面中,资料的整理与公布是基础,制约着相关研究的内容、方向与进展,而研究则又为材料提供意义,刺激着人们进一步寻找、查阅更多的敦煌写本,同时也推动敦煌学向前发展。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王国维等早期学者对敦煌史地、宗教、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兼具资料整理与研究考察两方面的工作性质,为后来者提供了典范。1924年,王国维率先利用罗振玉所藏敦煌户籍文书,结合传世史料,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3]74。
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的刘复(刘半农)抄录整理了法藏敦煌写本资料一百余种,按照性质分为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文字三类(三集),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1925年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印刷出版。他在前言中解释分类及理由时说,“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史的材料”,指出敦煌材料在认识了解古代社会、民俗、文学及语言方面的价值意义远远高出传统的经文,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开出一新天地”(1)刘复在前言中还对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新国学”研究加以申说:“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序来。”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页,21页。。这是“社会史”概念首次被引入敦煌学的范畴。刘复归入社会史的材料,涉及家宅田地、契约、诉讼、官事、婚姻、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等文献,表明了他对民间文献的内容与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与他看法一致,蔡元培在为其书所写序中指出,敦煌写本,尤其“各种杂文的写本”,“一是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的断片;一是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4]3,表明学界对于经、史、政治之外的敦煌世俗文献在考察当时社会状况及通俗文学中的意义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以专门研究社会经济史著称的《食货》半月刊专门收集了中、日书刊上有关敦煌的材料,整理刊印了《唐户籍簿丛辑》,陶希圣在前言中指出敦煌所出户籍、丁籍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可借此认识唐代的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情况(2)《食货半月刊》4卷5期,1936年版,第1页。另外关于该刊的发展及作用,可以参看朱守芬《〈食货半月刊〉与陶希圣》(《史林》2001年第4期)、阮兴《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和洪认清《〈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文。,《食货》上还发表不少利用敦煌资料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文章。
刘复之后,日本与中国有多位学者前往英法诸国查阅抄录敦煌文献,并展开相关研究,如狩野直喜、矢吹庆辉、那波利贞等,他们不仅关注敦煌的“杂文书”,也关注佛教疑伪经、寺院、社邑类文献,扩大了敦煌社会史的资料与研究范围。中国学者如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也先后至英法查阅抄录敦煌文献,出版多种叙录,并展开对敦煌历史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王重民1934年至1939年在法国考察法藏敦煌文献,除了完成《敦煌古籍叙录》,他还特别关注其中的俗文学内容,归国后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其他学者一道,校录出版了《敦煌变文集》。其后的数十年中,这本书一直是研究敦煌文学最基本的典籍。向达完成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回国后于1942年、1944年两次对敦煌进行了考察,从原本关注的俗文学方向,又转向敦煌历史、考古、石窟调查、文献考释等,“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路”[5]122。
陈寅恪运用敦煌文献中的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多种语言材料,开启了隋唐政治、佛教、文学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成为当时学术潮流的引领者[6]82。他在1930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时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7]236呼吁中国学者投身加入这一新的学术潮流当中。贺昌群也疾呼:“我们只要在这之中抓住一鳞半爪,也可以牵引起许多新问题。至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古文书以及多种语言的手写经卷的研究,那真是沃野千里,只待人开拓。”[8]58-59
在新文化运动及“白话文学史观”的影响下,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王国维、胡适、郑振铎、陈寅恪、刘复、向达、孙楷第、姜亮夫、任二北、潘重规、饶宗颐、季羡林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动反映中古民众生活与思想情感的敦煌变文、小说、曲辞、讲经文、话本等加以研究,从而开拓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片全新天地[9]169-170。奠定了中国民间文学史基础的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其中讲唱文学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敦煌俗文学资料为主要依据而完成的。
敦煌学研究一开始便具有国际性特点。中、日、法诸国学者在接触到敦煌文献伊始,便开始了相关研究与合作交流。这一特点,为后来的敦煌学树立了良好传统,也为其发展深入奠定了重要基础。与中国学者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英法等国学者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将敦煌学置于东方学、亚细亚学范畴之下,侧重于其他民族语言与宗教的研究,如伯希和、高梯奥、斯坦因对粟特与于阗及吐火罗语的考察;日本学者则在东洋学的视角下着重于中古敦煌社会历史、经济与宗教的考察,如内藤湖南、那波利贞、仁井田陞等人的研究。国外学者的敦煌学研究,一方面为后来敦煌社会史的研究奠定了语言考察、文献释读、理论建构方面的基础,成为后人研究方向的引领;另一方面,其成果也在国内引起对敦煌的更广泛的关注,掀起敦煌学研究的热潮,并为之提供了学术借鉴。
敦煌文献的发现及研究,不仅为认识中古社会及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对象,扩大了学术的视野与范围,同时也激发了人们进行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寻。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文献出土以及新学术观念输入的双重刺激和启示下产生的,它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建立的重要理论标志,也指导着敦煌学、敦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输入,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新史学”“新国学”“白话文运动”等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中外学术的合作交流,都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了敦煌社会史的发展,使得相关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相对较高的起点上。客观地看,在早期敦煌学的发展中,取得最大成就的领域无疑当属敦煌社会史,无论是对敦煌、河西区域史地的考察,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的剖析,还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的认识,通俗文学及艺术的发掘,民族语言的考证,都具有开拓性。
二、20世纪中后期敦煌社会史研究的不均衡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70年代,敦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即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与港台地区及外国相比,在研究的内容、范围、宗旨与特点上均有较大的不同。
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理论为指导,强调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社会、经济、土地、阶级关系诸问题成为大陆史学界研究的首要课题,有关均田制、租佃、赋役制度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者注重利用敦煌文献独有的原始材料,对敦煌户籍、均田制、赋役、租佃关系、农民生活等内容加以考察,如邓广铭、韩国磐、胡如雷、唐耕耦、王永兴等人对唐代土地与赋役制度的讨论,推进了对敦煌社会乃至中古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进一步认识与了解。成果数量虽不多,但在一些重要问题和局部研究上,都有一定的深入与推进,其中一些成果还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8]88。在获取资料不便的条件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力量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于1961年刊出,为更多研究者提供了可便捷利用的材料,推进了敦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同样,1957年英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片的获得以及60年代初《敦煌遗书索引》的出版,为大陆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敦煌俗文学是敦煌社会的产物,反映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社会风貌,是普通民众生活、思想、情感与艺术的真实反映,这些作品的内容主题契合当时面向工农兵的文艺政策与社会文化氛围,因此相关的敦煌俗文学研究在之前的基础上仍有所发展,但进步不大。主要工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期研究成果的结集出版,二是敦煌文学文献的校录整理。如周绍良、王重民、向达、王庆菽、任中敏等人校录整理的《敦煌变文集》《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汇录》等一系列重要敦煌文学作品集的相继出版。
1966年到1978年间, 中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 与中国大陆研究缓慢甚至停顿状态形成对照的, 是中国的港台地区与法国、 日本等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大都沿着之前的方向继续发展。 港台地区的敦煌社会史研究, 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推进了不少, 领域视野亦有拓展。 如苏莹辉、 饶宗颐等人对瓜沙史地及归义军历史的考察; 毛汉光从社会史角度对敦煌《姓氏录》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文献的考察; 罗宗涛依据敦煌变文材料从文学角度对敦煌社会风俗方面的研究[10], 推进了敦煌史地、 中古氏族、 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研究, 在港台地区及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饶宗颐《敦煌曲》、 潘重规《敦煌赋校录》从文学资料方面为敦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陈清香《北朝至隋唐间敦煌佛画的风俗》一文整理了敦煌壁画中的风俗资料, 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史料范围。 以上研究, 涉及敦煌及中古时代的历史、 宗教、 地理、 氏族、 风俗、 文学、 语言、 艺术等诸多方面。 这一阶段港台敦煌社会史研究的主力大多是1949年后由大陆迁徙而至者, 后期则陆续有新生力量加入。
国外学者的研究,以日本和法国为主,其敦煌学尤其是敦煌社会史的研究在此一阶段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领域宽阔,问题探讨深入,在敦煌历史、寺院经济、户籍契约、疑伪经、社会生活、历日法律、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如藤枝晃的一系列有关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政治史及敦煌石窟的长文,基本厘清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历史的发展概貌;竺沙雅章对敦煌社文书和寺户的研究,法国谢和耐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等,对中古敦煌寺院经济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薮内清和藤枝晃的敦煌历日研究,推进了对敦煌民众社会生活和信仰的认识;牧田谛亮《疑经研究》,利用敦煌文献系统研究佛教疑伪经,奠定了后人考察疑伪经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仁井田昇的法制史研究,池田温、金冈照光从生活、思想方面对敦煌民众社会生活的观照以及编入《西域文化研究》第二、第三册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中的论文,对敦煌与中古社会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
这一阶段中国的港台地区及国外敦煌社会史的研究,由于有材料获取上的便利,所以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将敦煌社会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这些进步为此后中国大陆敦煌学及社会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基础。
三、20世纪末期敦煌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发展
20世纪末期的20年,是敦煌学与敦煌社会史研究恢复与振兴的阶段。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往来重新恢复,学者们一方面接续起中断了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开辟出更多新的领域,注重培养新的研究人才,敦煌学与社会史的研究在经历了一个快速恢复的时段后,很快进入迅速发展的轨道。
与敦煌学的振兴发展相一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也进入快速恢复发展的阶段,并形成史学研究的一个热潮。既有关于研究对象、范畴、方法、意义的讨论,又有国外理论著作的译介,也有新领域、新视野的拓展,更有对问题的具体深入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中国社会史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可视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敦煌文献及敦煌学对社会史研究的贡献十分重要,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一书以及《敦煌文书与唐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唐朝住房面积小考》等文,便是在社会史研究思潮下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史的一个典范。
这一阶段,海内外不同机构所藏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以各种形式得到公布,为敦煌学研究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提供了更深厚的材料基础。学者们更从各自专业方向出发,从浩繁庞杂的敦煌文献中分类拣选出有关社会史的材料加以释录整理和研究,如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介绍并整理了社会经济文献;季羡林、习泽宗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书系中辑校出有关敦煌社邑、契约、天文历法、医药文书等类文献;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对各类世俗化佛教的愿文加以全面整理,这些分类整理成果不仅为敦煌社会史,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史不同方向与层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准确可靠的材料,奠定了从社会经济史、生活史、科技史与民间信仰等方面进一步研究的文献基础,同时,这些材料被辑录整理的本身,也是相关研究进展的结果和体现。
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便利,促进了国内敦煌学的发展。国外敦煌社会史研究的著作陆续被介绍进来,如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山本达郎主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日本《讲座敦煌》系列丛书,大多与社会史研究相关,其中《敦煌的社会》是研究敦煌中古社会的奠基之作;法国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考察了敦煌的民众经济、物质生活;戴仁、马克、茅甘、侯锦郎等人研究了中古时期的占卜与民众生活。
在敦煌社会文献分类校勘整理的基础上,受国外敦煌学发展成果及国内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影响,以及新时期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励[11]174,中国学界针对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了深入研究。施萍婷、李正宇、郑炳林、陆庆夫、荣新江、刘进宝等人的归义军史研究;李正宇、李并成、郑炳林的敦煌历史地理研究;齐陈骏、郑学檬、冻国栋的敦煌人口研究;杨际平、郝春文等对敦煌家庭、家族、僧尼生活的研究;宁可、郝春文等对敦煌基层组织社邑的研究;周一良、赵和平的书仪与社会礼俗研究;高国藩、谭蝉雪的民俗研究;黄正建、高启安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项楚、高明士、郑志明、郑阿财、朱凤玉等对敦煌教育、文学的研究;张涌泉、黄征等对敦煌俗语言的研究;高国藩、刘文英、郑炳林、黄正建等对敦煌占卜等文献的研究,共同开启了国内敦煌社会史研究的热潮。
在这个热潮中,姜伯勤在敦煌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其《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以敦煌文书为核心,对唐宋之际敦煌寺院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分礼仪、氏族、学校与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个专题对唐代敦煌社会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以礼仪为主线来构架并审视敦煌社会史,拓宽了唐代社会史研究的领域[12]769;《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通过艺术、宗教、礼乐三个维度来认识古代民族与社会,将敦煌社会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四、新世纪以来敦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新世纪以来,敦煌学与敦煌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在文献辑校整理继续推进并趋向细化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自觉结合其他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学的理论方法与视角,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同时开始反思敦煌学发展的理论及学科构建诸问题。因此,郝春文将这一段称为敦煌学的“转型期”。新世纪以来敦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一)敦煌社会生活与礼俗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13]395新世纪的敦煌社会史研究也同样将社会生活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基层组织,以及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民俗礼仪、疾病等内容作为研究对象,从更客观、详实的角度揭示了中古时期敦煌的民众生活内容风貌及其思想、信仰。
敦煌的人口、民族成分、家庭及妇女、儿童等内容,是研究敦煌史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郑炳林、郝二旭等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人口数量、民族成分、变化迁移,以及早期西汉移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陈丽萍、徐晓丽、石小英等从女性角度对敦煌妇女的生产生活、婚姻健康、家庭子女、经济、宗教信仰,包括政治参与、剃度出家、官司诉讼等情况进行了细致讨论;杨秀清则据文献记载与壁画图像,对敦煌地区儿童生活进行了梳理考察。
对敦煌家庭及基层组织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敦煌氏族大姓及社邑组织的考察上,如冯培红、陈菊霞等人对敦煌大族的研究;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则是自觉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从结构、功能的视角进行敦煌社邑研究的新成果。
日常生活研究方面,黄正建《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利用敦煌文献对唐代衣食住行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胡同庆、王义芝《敦煌古代衣食住行》梳理介绍了古代敦煌的衣饰、饮食、居住、出行等情况;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以及系列论文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民众饮食文化的诸多方面,构建起中古时期敦煌饮食文化的框架和体系。此外,谢静、竺小恩的敦煌服饰研究,杨森的敦煌家具研究,段小强、陈康、李重申等的敦煌体育研究,丛振的敦煌游艺活动考察,都综合利用文献记载与莫高窟壁画、塑像及考古资料,探讨了古代敦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礼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遵行的一般规范,主要体现于岁时节日、祭祀、丧葬仪式、婚姻嫁娶中的行事规范与仪节习俗。谭婵雪、吴丽娱、史睿、赵和平、高国藩等依据敦煌书仪及其他文献材料,对这些礼俗的具体内容、意义内涵及其演变进行了研究;马德、高国藩、梁丽玲等对妇女生育、乞子习俗进行了考察。
术数文化涉及民众思想、信仰与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期以来被视为封建迷信而加以摒弃。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开始从认识古代历史文化与民间信仰的角度,在法、日等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占卜文献及其文化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刘文英、黄正建、邓文宽、郑炳林、王爱和、王晶波、关长龙、陈于柱、王祥伟、金身佳、赵贞等人对敦煌占卜文献加以分类释录,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类占卜文化进行考察研究。黄正建率先对敦煌占卜文书加以分类梳理,并探讨占卜与唐五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其后,学者分别对敦煌的梦书、相书、易占、宅经、葬书、五兆卜法、禄命、占候等占卜文献进行校录整理与研究,对敦煌区域社会下占卜的种类、应用及趋吉避凶的社会心理,从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
有关生命、疾病与社会的考察是近年较受关注的论题,利用敦煌材料进行的多角度研究,极富特色。如高国藩对敦煌厌禳祛病巫术的探讨;圆空、于赓哲从疑伪经的传抄对唐代流行病的分析考察;陈于柱通过发病书对相关社会医疗问题的讨论;法国学者华澜对历日与身体关系的揭示,等等。陈明则依据敦煌文献,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敦煌的社会医疗问题,涉及疾病观、医疗观,民众的医学知识与传承,中外医学交流,古代敦煌的医疗资源及治疗、救护等问题。
(二)敦煌世俗化佛教与社会
尽管佛教类文献在敦煌文献占到绝大多数,但在21世纪之前,有关敦煌佛教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并不占重要地位,且多是外国学者在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对敦煌佛教及佛教文献的研究明显增多,如郝春文等人所言:“与上一阶段相比,转型期对敦煌佛教典籍的整理与研究,重点和视角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佛教典籍整理虽然仍在继续,但已经不再是重点。”[14]430这一阶段敦煌的佛教研究,既有与前阶段相同但更加系统地对佛教典籍文献的整理、考订、缀合、编目,又更多着眼于联系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社会实际,从佛经的抄写、流传、供养,疑伪经的内容与传播到僧尼生活、斋会仪式、丧葬礼俗,以及佛教讲唱、壁画艺术等众多方面,考察研究世俗化佛教在敦煌民众中的种种表现及特点。张总、尹富对地藏信仰的研究;王惠民、李小荣、张子开、赵晓星、党艳妮等对敦煌佛教信仰的考察;侯冲对斋会仪式的考察;魏郭辉、赵青山、朱瑶对敦煌抄经史及文献题记的梳理;方广锠、郑阿财、圆空、于赓哲、赵青山、张小艳、王孟等对敦煌疑伪经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刘亚丁、杨宝玉等对敦煌佛教灵验记的分析,郝春文、陈大为对归义军时期寺院及僧人的关注,都不约而同地将唐五代敦煌佛教视为一种“民众的信仰”或者在地的“世俗化”佛教而加以考察,且从各自角度揭示了中古时期世俗佛教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郝春文、陈大为《敦煌佛教与社会》;马德、王祥伟《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等论著,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方面研究的进步。
(三)吐蕃、粟特、回鹘、于阗等敦煌少数民族及其语言
敦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位置,使之成为古代文化交汇、民族聚居之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共同体”,同时“又构成了有别于内地的一个独特的地域社会”[2]。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居民中,汉族居多,其他民族亦不少,如吐蕃、粟特、于阗、回鹘等,有关这些民族历史文化及语言的研究亦是敦煌学以及敦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
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及相关系列论文,依据敦煌汉文藏文资料与传世文献,探讨了吐蕃时期的敦煌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活动以及唐蕃关系等问题,是这一阶段相关研究的代表[14]347。杨富学有关回鹘及摩尼教的研究成果不少。其中《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甘州回鹘宗教信仰考》等论述了有关回鹘宗教信仰及社会、经济、政治等内容,以及甘州回鹘王国建立后佛教取代摩尼教的历史情况。荣新江、姚崇新对中古时期传入中国的“三夷教”的情况与敦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荣氏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中所收文章,从多种角度讨论了丝绸之路及中古时期敦煌的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信仰问题;他和朱丽双有关于阗历史及于阗与敦煌关系的考察,亦富有开创性。
(四)敦煌石窟、壁画艺术与社会史
莫高窟是敦煌中古时期重要的公共社会活动场所,敦煌石窟及壁画艺术是敦煌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敦煌石窟和壁画研究表现出新的特点,即除了立足考古学、美术学、佛教史之外,也开始与历史学、特别是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比如马德、王祥伟《中古敦煌佛教与社会化略论》在全面考察佛教与敦煌社会的关系时,着重论述了石窟营建与敦煌社会的关系、石窟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前举郝春文、陈大为《敦煌佛教与社会》一书,也以一定篇幅讨论佛教洞窟与社会的关系;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等论著,虽立足于考古学,但在具体研究中将对洞窟、壁画的考察与敦煌佛教、吐蕃政权、归义军政权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了不同洞窟开凿创建时的具体政治及社会背景,讨论深入而富有突破。此外,作者有关壁画与经变的研究也同样结合历史学、宗教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具有启示性。
五、学科交叉视野下敦煌社会史的研究及其展望
综合回顾敦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百多年的敦煌社会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学术视野逐步扩大 早期研究视野多集中于传统学术所看重的内容与领域上,如敦煌的沿革、地理、经史典籍、民族、制度、文学、赋税、经济以及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关系等,在其后的研究中,逐渐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化细化的同时,也将视野扩大到敦煌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宗教信仰、民间风俗、文化艺术、基层组织、族群、名籍、日常生活、女性、艺术、娱乐,等等。凭借这些研究,将传世史料语焉不详或者付之阙如的社会史的内容具体翔实地构勒出来,填补了相关认识与研究的空白。
2.学术理念不断更新 就学术意义来说,早期还有一些研究者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的局限,不自觉地将自己工作的意义设定在为传统学术补缺与纠谬之上,给予经史文献以较多的关注。不过,随着新的西方学术理念的传入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学者很快认识到敦煌作为中古地方社会研究的样本意义,突破原有学术观念的束缚,将目光转向中古敦煌这样一个特定时空,以地域、基层、大众、民族、丝绸之路、生活、信仰、斋会仪式、个体等内容为关注对象,展开更细致深入的研究,并赋予这些研究以新的时代与学术意义,从而取得众多成果,不仅使敦煌学成为令人瞩目的一门新的世界性学科,也为中古社会史的发展给予了重要推动。
3.学术方法的综合运用 早期敦煌学研究者多受清代考据学影响,方法以考据为主,文献、史事、语言,学者多以敦煌文本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对照,旁征博引,加以考订。受敦煌文献、殷墟甲骨、其他民族语言文献发现的启示,王国维首先运用而经陈寅恪归纳的“二重证据法”,成为迄今仍在指导人们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理论之一。同时,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入,给中国社会史及敦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方法指导,学者综合运用多种学术方法进行研究,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学、考古学、地理学、心理学乃至建筑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用以考察研究敦煌的社会文化及其特点,这在新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富。
4.学科交叉特点明显,并且逐步突出 首先是研究材料的交叉。敦煌文献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多种语言、多种形式的复杂材料并存,汉语、胡语文献,石窟、壁画、考古遗存,这些同时产生并留存于4—14世纪的敦煌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之内的材料,互有关联,互为印证。汉语与胡语文献交叉,文字材料与石窟、壁画艺术及墓葬遗存交叉,共同构筑并反映着敦煌社会的各种面相与内涵。其次是研究领域与学科交叉。史学与文学、语言、佛教石窟艺术、宗教、民族学、科技、考古,等等,凡与敦煌研究相关的学科及其理论方法,均可交叉互鉴,针对敦煌社会及其内容进行综合研究。譬如有关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的研究,涉及社会、家庭、教育、婚姻、生育、子女、地位、财产、劳动、交往、信仰、服饰、装扮、族属、语言、礼仪等全方位的内容,既是有关女性历史生活状态及其所关联社会情境的考察,也有其心理、信仰及思想情感的分析,学者依据多方面材料(语言文字、洞窟壁画、考古发现)、运用多种学科理念方法从不同角度加以考察研究,对这一时期这一地域的女性有了较为完整和立体的认识。当然,这种学科交叉研究在不同的问题及领域上表现得并不平衡。
常建华在总结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时说:“中国社会史研究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学术理念的更新,而学术理念的更新与多元学术视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更新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仍是我们应努力的目标。”[13]396新世纪以来的敦煌社会史的研究实际,确实体现了他所强调的理念更新、研究视野扩大、学科交叉等各个方面的进展。虽然如此,基于目前敦煌学及敦煌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特点与趋势,敦煌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的研究在学科整体推进与综合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正如荣新江所指出,21世纪的敦煌学必须从文献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尽管目前有关的个案研究或某些专题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是缺乏综合研究[15]1。他所说的这种综合的研究,恰是历史学所追求的对整体历史的把握(3)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在解释《年鉴》杂志的创刊宗旨时指出: “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 其实并不存在。 只有作为整体的历史。 就其定义而言, 整体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敦煌社会史研究的推进恰是这种“整体的历史”的一种体现(相关论述可以参见余欣: 《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年版, 第6页)。。常建华也说:“社会史可以使历史丰满起来,具有整体性。从地域史追求历史的整体性,是把握‘多元而又高度整合’之传统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法。”[13]397
因此,在敦煌学各个方面均有重大进展的当下,如何将多学科的优势转化到敦煌重要社会问题的综合研究上来,通过对敦煌不同学科及研究成果的综合,进而认识唐五代宋初的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颇为值得期待的问题。就笔者所见,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第一,将敦煌社会史的研究与敦煌吐蕃史、归义军史、西北史地等已有研究结合。从敦煌社会文书的遗存情况来看,佛教文献、道教文献、“三夷教”文献甚至是衣食住行的相关资料都与政治有很大的关系,绝大多数资料是归义军官方组织编纂的文书,将政治史与社会文书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认识中古时期敦煌地域社会构成及其运行的整体情况。第二,将敦煌洞窟、壁画研究从考古学研究、艺术史研究视角转向历史学研究,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洞窟的营建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思想进一步联系起来,将洞窟壁画尤其是经变的研究与当时社会思想、信仰、心理联系起来,动态把握敦煌社会精神生态与价值取向。第三,将敦煌社会史的研究与中古中原王权政治的研究进一步联系起来,将吐蕃时期的敦煌与唐王朝关系研究结合起来,将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与不同阶段的中原王朝研究结合起来,将敦煌学置入整个中古史的研究范畴,进而通过敦煌了解整个中古时期的中国社会。第四,将敦煌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及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研究结合起来,将敦煌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放在“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视野下,以便真实呈现历史上敦煌的多元民族共同生活的面貌。期待今后敦煌研究者能更自觉更多元地借鉴与利用社会史及其他学科的视角与理论方法,社会史研究者也更多关注敦煌资料,进一步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推动敦煌社会史研究和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