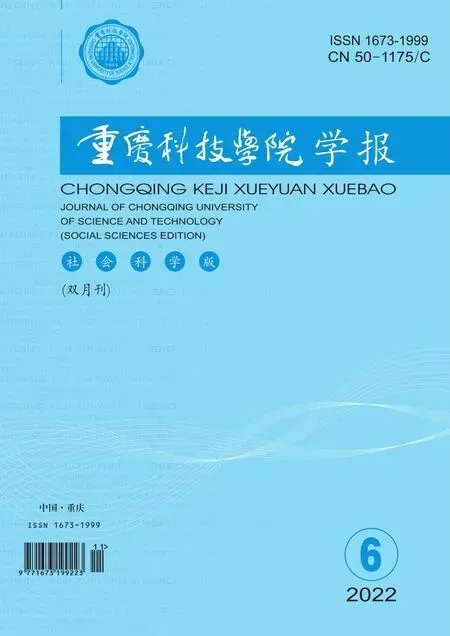秦汉时期侠士文化及其对传统武侠精神的影响
张 勇 郭玉成
(1.安徽工程大学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一、秦汉时期侠士来源
侠士和儒士是由先秦的士阶层分化而来。根据顾颉刚“古代学校即军政训练之所”的观点,士是需要学习射箭习武的,士大部分是武士,战国时期甚至“不与文士混”,彼此“自成一集团”。由于文武分列且彼此对立,因此“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可以总结为“儒重名誉,侠重义气”[1]327。子路之前也是一位仗剑行天下的侠士,后经孔子规劝而“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被视为由侠入儒的典型。当然,先秦时期士的培养内容本身就包含骑射,是训练具备一定军事能力的人才。春秋战国贵族垄断被打破,士阶层因为具有能文能武的技能而有更多的上升机会。“借恢复夏商周礼乐传统而成儒,协助当时有志之士一展抱负而成侠”,基本上可以概括后来文武分流的情况。历经战国养士之风,侠与权贵结成政治上的联盟,也产生出主宾知己般的个人感情。而到秦汉侠士下潜到中层官员和民间层面,出现了楼护、陈遵这样亦官亦侠的“官侠”,也出现了起于平民的布衣之侠,还有依仗权贵称霸一方而声名远播的豪侠,甚至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任意妄为仿效剑客而无视法律的“少年”,拿人钱财为人报仇的刺客组织。其深层的原因正是由于侠士信奉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图报心理,所推崇的道义只是基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情感,甚至超出社会法制限制范围[2]。
到了秦汉,武侠来源就变得多元复杂,不再只是由武士转换而来,拓展到了墨者、游民、平民,而真正由士阶层转化而来的武侠数量逐渐变少。
(一)战国没落的士阶层
先秦时期,侠多为士,被当时权贵所私养,被称为剑客、游侠。秦统一天下后,对于兵器进行了严格管制,士阶层文武分流,其中一部分下潜至民间,或任侠意气结交宾客,或与权贵相交通,由原先的庙堂之上转而进入街头巷尾。秦汉时期出现了很多布衣之侠。一方面,西汉政权的建立本身就验证了平民阶层在乱世具有上升为新贵的空间与可能;另一方面,西汉初期国家虽统一,但是各地分封诸王都有养士以显声势的风尚,而且其中主要的门客为武侠之辈,所以曾经的有武艺傍身的士在汉代仍能与权贵结交,实现自己侠士的理想和人生追求。
(二)潜入民间的墨者
墨家注重言行合一,乐于助人,不求回报,在行动准则上和侠士有着很近的联系。严格意义上讲,墨家士子本身就是士阶层,由于时局变动,尤其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墨家和其他学说流派一样逐渐衰弱。很多墨者本身就是侠士,逐渐潜入民间,不求政治主张得到当局政府的采纳,而继续救助困厄、广交志同道合的豪杰侠士,自身成为侠士也是自然的事情[3]。
(三)社会底层游民群体
由于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和战乱纷争导致了秦汉之际出现大量的游民,他们居无定所、无地可耕,聚集在一起为了生存,极易形成一种自发组织性的群体,做一些当时法律禁止的事情。其中还有一些平民,身处乱世,借助于自身孔武有力且勇猛果断的条件,广交朋友以谋求成就一番事业,改变自己身处社会底层的命运。跟随汉高祖刘邦的一群崇尚任侠风尚的“少年”,就是这样的侠士。
秦汉时期侠士的来源日趋多元,其身份复杂,也进一步证明了此时侠士这一群体已经呈现出其不完美的特点。他们可能秉承自己的为人行事准则,这种“单纯性和极端性就决定了其人性的闪光点和严重的缺陷并存”[4]。因此陈山推断,“侠的人格特质凸现出了人的共性——即英雄与魔鬼共存的复合体”[5]105。
二、秦汉时期侠士特征
秦统一天下后,收缴兵器铸成铜人以警示民众。然而秦朝的暴政导致天下民众不满,起义者风起云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遂致秦朝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依仗推崇“任侠”精神的平民豪士,战胜了代表旧贵族的项羽集团而取得天下,这是汉代侠士之风兴起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秦末汉初朝代更迭的动荡,距战国时代不远。对于侠士而言,由先秦时期伴随卿相左右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高度下潜到民间市井底层谋生,他们在动荡不定的时局下,寻求着解决现实生存问题和践行侠义理想的平衡。
(一)传统上将侠士分为三等
秦汉时期的游侠、任侠本身是复杂的群体,而秦汉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同身份武侠也基本呈现这样的差异[6]。清代曾国藩曾经将侠士分为三等:“布衣闾巷之侠、有土卿相之侠、暴豪恣欲之侠”。
布衣之侠,也称为“匹夫之侠”,是出身平民,且活动多集中在底层民间的侠。这些侠士相当于先秦时期的“隐士”,没有高贵的社会地位,多数不置业,也不事生产,但因为好“赈穷救急、脱人厄困为己任”,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声望。这些布衣之侠虽未直接参与政治纷争,但由于本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常被权贵所重视,并拉拢过来成为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例如:郭解被迁徙,甚至使得卫将军为之说情,前来送行的人“出千余万”,可知郭解是一个有很强号召力的侠士;与之相似的还有朱家、剧孟,虽然隐于民间,不求仕途,但是都得到当时权贵的高度重视。
卿相之侠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四公子“延引宾客,多至以千数”。到汉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卿相级别的侠几乎不存在了,而下移到一般官员,出现“侠官”和“官侠”。他们本身是官员,但具有侠士特立独行的个性,执意自己的行事准则,或与侠士肝胆相照,甚至敢于藏匿朝廷要犯,或不改任气豪情,常与剑客侠士聚集往来,例如季布、田叔。
暴豪恣欲之侠大多为一方豪强,在族人、宾客的支持下,为谋私利而聚集在一起。当然也有侠的“重诺言”“轻生死”的豪情,但同时也存在横行乡里的恶霸行径。如西汉灌夫,“喜任侠,重然诺,不好面谀”,同时“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陵贵戚而礼敬贫贱之士”,但“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从普通的对侠的认识来看,这一类侠的意味淡薄,几乎不能称其为“侠”,也有辱“武”的内涵;但是,从侠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和武侠人群性格特征的角度来看,这一类人群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7]。
(二)秦汉时期立体多面的侠士特征
西汉政权的建立本身就是以刘邦为代表的平民阶层中豪杰势力的胜利,而后这些政治新贵对于武侠阶层进行拉拢与渗透,以达到巩固其政权,稳定和解决其政治纷争的目的。汉代武侠开始与地方势力紧密结合,相互扶持,形成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豪强化群体。由于相互之间默认控制区域的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帮派组织的特征。秦汉时期的侠士拓展了战国时期侠士的生存内容,在先秦武侠蕴含的“宗强比周”“以睚眦杀人”的恶文化基础上增加了更多政治诉求和个人发展需求,汉代甚至出现了结党营私、横行乡里的豪侠群体,进一步让侠士的人格更加复杂化。
1.重诺轻死不问是非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总结侠的特点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秦末时期效力于项羽麾下的季布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侠士,为人守信重诺,甚至当时流传一句“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8]。但是侠士所信奉的行事原则有时与国家的法律相悖,甚至做出对抗官府法令的事,不是身处乱世简单地趋利避害以求生存,而是任侠意气往往不避生死,为知己可以赴死而“不还踵”。先秦时期的荆轲为太子丹而去刺杀秦王,田光为太子丹一句提醒而自杀以明志,都是这种游侠精神的体现。秦汉时期的侠士更多属于古人所说的任侠或豪侠,他们不论是否身居官位都依照自己的行事原则做事,有时甚至完全没有理性,甚至无视王法。郭解名声在外,一群侠士豪杰以其为自己的精神指引,有些或者受到郭解的帮助或救济,有些可能只是钦佩他本人。当郭解被官府勒令迁徙关中时,有人就杀当权者的儿子来发泄怨恨。当时有文人对郭解说句怨言,即被人暗杀。这些并不是郭解暗中指示或授意,全是出于这些“豪侠”对郭解的钦佩或感恩的情感。这种杀人不为私仇而为知己出头,虽完全不顾官府法令将自己行侠仗义凌驾在法律之上,为法理所不容,但必定和拿人钱财为其报仇的“刺客”不同。
2.任侠意气显名谋利
古代侠士往往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商业活动,而维持自己的生活需要钱财,收留帮助其他慕名而来的豪杰更需要大笔开销,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必然会穷困潦倒。但这些问题对于先秦从士阶层转变而来的侠士来说则不需要考虑,因为他们多被权贵所私养。但是,秦汉时期的侠士在成名之前本身需要生存,其成名之后还需要私养其他宾客,所以“求显名”也是为了进一步谋求私利的途径,这是身处乱世之秋的侠士出于现实问题的考虑而做出的选择。以郭解为例,在成名之前他也曾做过私铸货币的事情,以此获得大量的利益;名声远播之后,权贵往往赠予可观的钱财。虽说游侠以“家无余财”为荣,但是侠士往往并不会穷困潦倒。尤其是汉代,侠士不仅注重自己的名声,甚至有意识地显名于世,可以说是“追名逐利”。《史记·游侠列传》中记录鲁侠朱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在救助处于困顿的季布后,朱家名声远播。郭解的外甥被杀,他认为杀人者有道理竟然将其释放,因而获得极佳的声誉。对待“傲视”自己之人,托人免去差役,最终,“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帮忙调停复仇事件,仍将名声留给了当地贤豪,结果更加促使其侠名远播。这不仅是有意建立好名声,甚至本身就是追逐名利的表现,正如彭卫所言:“声誉也是一笔财富。”[9]
3.聚众任侠交结权贵
先秦时期,游侠、死士多为当权者私养,也是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力量。而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经历统一与动荡过程,很多侠士潜入民间,广交各种任侠、豪杰之士,有明显的组织化特点,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构成了威胁。到了汉代,出现了很多任侠与权贵、豪族结合,为侠士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如汉高祖时期的鲁侠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一度发展到“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的程度。广交权贵已经成为任侠群体自保和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手段。“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而在汝阳侯滕公和濮阳周氏等人的打点和求情下,季布得以赦免。郭解被当政者下令迁徙时,来送行的人“出千余万”,甚至大将军卫青也替他求情。汉武帝惊叹“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郭解的影响力波及关中,迁徙入关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这种排场和影响力较之先秦侠士,那是大得多。鲁迅总结先秦侠士“以死为终极目的”,而汉的大侠,“就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10]。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有意结交侠士群体,有政治斗争的需求,也有自身喜欢侠者的快意任侠风尚的原因。自郭解之后,很多侠士开始意识到与权贵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其进入高层社会的捷径,其中由侠入仕并最终位列九卿的楼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弃医任侠就是为积攒名声,在利用一道美味名菜获得当时外戚王氏五兄弟的青睐之后,运用能说会道的本领广交公卿大臣,竟被推荐成为广汉太守,后来在王莽时期立功,被封息乡侯。长安豪侠萭章与汉元帝宠臣石显勾结、汉宣帝宠臣陈遂的孙子陈遵“聚众任侠”,一时间侠群体中出现了与权贵相交往以求仕途发展的现象。当然,汉代与权贵结交而称霸一方的豪侠数量并不多,秦汉大多数的侠仍是处于民间底层,坚守着自战国游侠开始的行为准则。
三、秦汉时期侠士文化风尚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维持时间很短,随后进入秦汉过渡时期。秦汉之际时局动荡,平民阶层成为反抗暴秦的主力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好武力而推崇侠士的局面。一方面,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好武轻文”,权贵养士成为风尚,平民阶层中流行聘请剑客以解决私人恩怨的风气;另一方面,西汉初期的“兵民不分”,形成一定数量的具有战场经验且武力超群的平民群体,其中一部分转为不事生产而好仗剑聚结的侠士,形成豪杰侠士盛极一时的局面。秦汉武侠文化,承先秦之遗风,开武侠之新象,具体体现在对于先秦墨家、任侠和游侠精神的继承与开拓。
(一)不畏权贵专任意气:墨家风尚的遗留
墨家是先秦显学,墨子被称为“北方贤圣人”,他有一批组织性强、掌握精湛技艺且生死相随的追随者,称为“墨者”。墨者组织的首领叫“巨子”,是墨者的精神领袖。先秦时期很多人以当巨子为荣,而墨者都听命于巨子的号令。《庄子·天下篇》中说,“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在兼并战争不断的战国时期,墨家一边宣扬“兼爱、非攻”的理念,一边帮助弱小国家做防御工作。墨家子弟不辞辛苦在各国间奔走,“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11]。墨家“不畏强权”“舍身取义”的精神,影响了千百年来中华武侠文化的发展。秦汉时期,出现的一些对抗权贵且专任意气的侠士,影响了后世武侠文化的发展[12]。汉代兴起的具有组织性和集团化的豪侠,就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墨者组织的特点,只是这些豪侠已经从墨者心怀天下的精神信仰转变为追求名利的现实需要。墨家精神在秦汉侠士中得以继承,他们注重道义,为知己不仅一诺千金,而且可以为之赴死而没有丝毫犹豫。
(二)能立然诺尚气任侠:任侠风气的彰显
秦汉侠士既有“救死解厄而不惜拔刀相助”的侠义,也有“纵性横行至于对抗官府发令”的豪气。古人用“任侠”来概括这类侠士。《史记》中对于季布的描写为“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任侠之“任”,《史记·季布传》集解引用孟康的说法为“信交道曰任”,有司马迁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意思,汪涌豪指出还有引申的“放任、专任、擅任”的含义[1]51。
任侠之风气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权贵指使或聘请死士刺杀对手的事情时常发生。上行下效,这种“非正规的、不合法的暴力形式”自社会上层开始蔓延,也进一步助长了社会暴力倾向。上层社会为政治目的随意使用刺客、死士,民间为亲人报仇的“复仇”行为也被视为“孝”的一种。在春秋时期复仇行为只要到司法机关登记,就是无罪的[13]。依照钱大群的观点,复仇制度刚出现时,是被当局认同的,复仇成为在封建法治不够的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14]。而这种复仇现象到了汉代一度风行起来,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法治力度不够。而民间复仇事件频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任侠群体的发展。侠者自身对“诚信”看得非常重,尤其是具有组织化的任侠群体中的侠魁,继承了墨者的组织严谨和一诺千金的特征。任侠“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能立然诺”的行为也获得了民众的赞赏,“季布一诺,千金难求”的说法,更是反映出任侠守信重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信任。但随着秦汉时期统一国家建立后,出现了私德和公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重义轻死尚武好勇:游侠精神的遗风
秦汉时期由于侠士推崇尚武精神,社会底层也受到很大影响,一时间少年舞刀弄枪相互较力成为风尚,“重义轻死、好勇斗狠”为社会所推崇。侠者多意气,“重然诺,轻货财”,救人于厄难,重道义而轻生死。《史记·淮阴侯列传》记录了韩信受到“胯下之辱”的故事。少年挑衅“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当韩信俯下身子,众人“皆笑信,以为怯”。汉初尚武已经成为风气,由于刘邦“马上得天下”,自己平时就好武轻文,公卿都是“武力有功之臣”。当时,无论是权贵子弟还是普通平民,讲武习剑已成为时尚。章太炎总结说,汉时学者文人都习武练剑,有“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的说法[13]。汉代初期“兵民不分”,很多百姓休战时在田中耕种,遇到战时即从军打仗,因此民间有很多武艺高超的平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布衣之侠的形成。汉初分封诸王效仿战国的公子养士之风,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招宾客以千数”,梁孝王刘武招徕四方豪杰侠士。而西汉贵族也以养士为风尚,与战国养士不同,所招徕门客多为豪侠。甚至一些地方官员也私养剑客,如当时的河南尹何进所养剑客,曾经因为孔融看不起何进而欲刺杀孔融。
四、秦汉时期武侠文化对传统武侠精神的影响
(一)奠定武侠舍生取义的豪情,也显露好求显名的私欲
陈山认为汉代侠士文化以郭解为界,之前多是“救人厄困”,助人为乐,毫无私欲的正侠,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舍生取义豪情。秦汉之际由于时局动荡,游民大量增多,民间私人解决恩怨可雇佣任侠群体进行复仇,加之分封诸王养士成风尚,难免很多人利用“侠”的名号广交权贵或接受馈赠,然后达到进入仕途的目的或作为谋生手段。相对于先秦时期侠士多是一群行走于乱世而怀揣天下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秦汉之际,准确地说是汉代,侠士转为诉求现实,其后开始呈现求显名为私利,结党成帮的倾向,称之为“豪侠”。秦汉时期,武侠不仅有让人崇敬的豪情和不畏生死、执意任气的快意洒脱,也增加了好勇斗狠、结党营私、无视法纪的豪侠或侠魁的文化因子,而这些又滋养着习武者好场面、求名声、乐争斗的不良习性。这种将不求私欲以彰显正义与好名求利、争强好胜的矛盾性格集于一身的特征影响深远,“练得黄金技,货于帝王家”的说法正是习武之人以武功与侠名谋求个人发展的真实写照。
(二)延续武侠与权贵特殊关系,既有依靠又有对抗
中国侠士并不同于欧洲骑士那样只存在于一个特定时期,侠士文化在中国延续千百年而不断,其中不畏权贵、维护道义的精神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其本身受到不同时期民众的推崇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侠士精神也并没有像日本武士道那样成为一种职业操守,虽然中国侠士和日本武士的起源很相似,都是来源于士阶层,但是中国侠士文化和日本武士道所提倡的无条件的忠诚和服从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侠士自战国时期开始,就和自己所依附的权贵存在一种既相互依存也彼此独立的特殊关系。例如战国时期著名的孟尝君在其失势之时,大多数门客都相继离去,而在其重新获得权力后门客们又都回来投靠,且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惭愧[5]31-48。战国时期的士有着自己独立的个性,去与留并不是看重主家给予钱财的多少,而是更在意权贵对自己的态度,主家是否礼贤下士才是最重要的标准,这种关系更多地类似知己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的依附关系。由于平原君觉得门客的提议很是过分而不予采纳,随后半年之间门客相继离开过半,门客正是因为觉得平原君看轻自己而悄然离去。可以说,士所追求的是权贵对于自己的尊重和认可。秦汉时期的侠士延续了先秦侠士特立独行的行事标准,这种任意豪情不仅体现在其救人厄困不思回报、不吝钱财广结同道和轻死重诺的独特行事风格上,也体现在自己与权贵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上。虽然汉代豪侠有意识地借助权贵以达到入仕做官的目的,而且有一部分“官侠”更是身处名利场,但是仍然保持着敢冒生命危险对抗官府法令藏匿要犯、不顾个人仕途而为知己出头的侠义精神。这些任意侠气正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敬佩的原因。
秦汉侠士不仅在民间极富盛名,而且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促使当朝权贵也不惜放下上层阶级的架子主动与其结交。汉景帝时期,被委以军政重任的周亚夫接到平定动乱的任务从河南路过,途中遇见洛阳大侠剧孟,不由欣喜若狂,认为他就是稳定政局的重要人物。可见,不断壮大的侠士群体不只是依附于权贵在政治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价值,更是被当朝权贵视为需要拉拢结交的重要对象,甚至成为西汉王朝政治博弈的重要力量。当豪侠剧孟母亲去世时,来送丧的车辆上千,其中有不少都来自贵族官宦。此外,有些身处要职的权贵冒死藏匿朝廷缉拿的侠士,为保护自己敬重的侠士甚至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王莽时期的强弩将军孙建,将西河大侠漕中叔藏匿起来,当王莽问起来,他“请死”以拒,为了自己所钦佩的侠士甚至当面顶撞当权者。
五、结语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的《自叙》里写道:“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15]1386。中国武侠文化延绵数千年滋养着华夏儿女,那些守诺言、轻生死、为公利的事迹成为史家撰文立书和民众口口相传的传奇。这些为国家舍身取义,为知己死不还踵,为承诺至死不悔的精神曾经给予了多少人在乱世安身立命以指引[15]1386。在当下社会面临信任危机,全社会征信体系尚未健全,且成功评价标准单一的社会环境下,侠义精神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