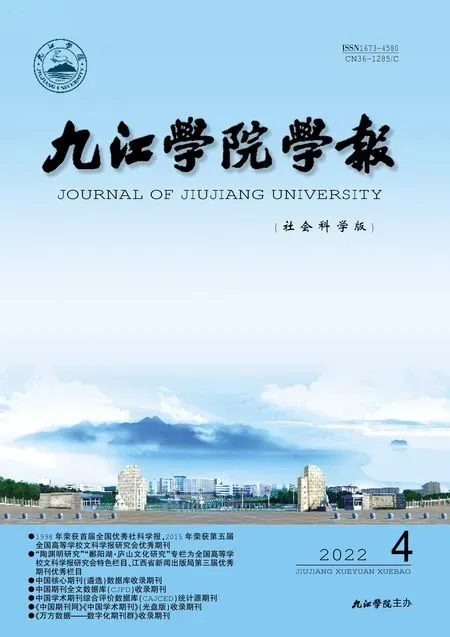困境、逃逸、救赎:班宇小说中的水意象探析
周 唯
(广州南方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广州 510970)
近年来,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在文坛崛起,这一批青年作家聚焦东北的历史与现实,书写了90年代末国企改制背景下两代东北人的困顿与突围,使东北叙事呈现出崭新的美学质地。其中,班宇的小说以独特的叙事形态和美学风格颇受瞩目。当下,学界对班宇小说的探讨多从主题、风格、叙事策略等角度展开,对小说中意象的分析还不够充分。笔者发现,在班宇已出版的两部小说集《冬泳》和《逍遥游》中,水意象的使用十分突出,不仅构成了沟渠、河流、湖水、游泳池等兼具物理性与隐喻性的空间形态,对于小说的主旨、叙事、风格和意境也起到了重要的表达作用。水既象征了大历史席卷下小人物的离散和困顿,也是个体自由与救赎的寄托。本文将着力于探究班宇小说水意象的内涵,以期提供新的阐释角度。
一、离散与困顿
班宇的小说大多以东北90年代末的国企改制为背景,在突如其来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中,一代人面临着生存与精神的双重考验。班宇在作品中大量表现故乡人的焦虑、恐惧与集体迷茫,小说情节也往往以失业、失踪、离异、重病、死亡、暴力犯罪为主要元素,表达了一种“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1]。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表述,以及人在大历史情境前被抛出常轨的无力与困顿,水意象起到了重要的表征作用。
在小说《梯形夕阳》中,作为变压器厂销售人员的“我”被派去电厂收账,几经周折收回的款项却被科长卷走,变压器厂依旧难逃破产的命运。小说中频繁使用的水意象表达了这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例如,“我”所观察到的小镇景观是这样的:“上方来的风卷入水里,激发不同方向的水浪,相互吞噬、碰撞,哗啦哗啦,像是很多人在说话。”[2]山雨欲来的危机感和不稳定感呼之欲出;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下,电厂也同样破败不堪、濒临崩溃,而电厂财务科的李薇却在背诵香港回归知识竞赛的试题,为的是赢回一张电褥子。在大时代的洪流面前,小人物的命运显得微渺而无力,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洪水”意象象征了这种历史的浪潮,人们相信此地今年将有大洪水来席,将一切淹没成海,李薇的梦境中也时常出现末日般的洪水景象:“水里还有蛇、羊和草,有一天还梦见你了,也在水里,离我本来挺近的,但怎么扑腾也游不过去,你伸着手也拽不到我,急得要死,后来一个浪从我俩中间打过来,你也消失不见了,就剩我自己,大雨浇得我睁不开眼睛。”[3]小说结尾,得知科长卷款私逃后的“我”走向河边,脑海中想到的是“一步一步迈入河中,让刺骨的水依次没过脚踝、大腿、双臂、脖颈乃至发梢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被溢出的洪水卷到半空之中,枕着浮冰、滚木,或者干脆骑在铁板上,从此告别一切过往的,会是什么样的人”[4]。在历史大潮的席卷下,人们被冲垮、席卷、淹没、吞噬,丧失了安稳的生活,与过往形成了巨大的断裂,从而迷失了自我身份的认同,成为无所依凭的孤独灵魂,只能在洪流中浮沉离散。正如论者所言,“那些试图涉渡的人群最终失去了上岸的可能性,永久地离散在东北漫长的冰河期之中。”[5]
与之相应,班宇常常在小说中以“困于水底”的表述隐喻充满无力感的普通个体情感结构与生存状态,小说《枪墓》以“元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对父子的命运,失业后的孙少军先后卖皮鞋、拉脚儿、卖面、兜售鞭炮,又历经了丧父和离异,几经挣扎却无法改变困苦的处境,他也确信自己已经被神灵抛弃:“耶稣没能认出我来,河边的不是我,我在水底。”[6]当“我”把孙程、孙少军父子的故事讲给刘柳听后,她觉得整个故事与自己的遭际相近,“上次你讲完,我还梦到过一次,跟我一起困在湖底,我们想上岸,但却不知该往哪里游,湖面结冰,太阳照在上面,金光四射,但里面却依旧很冷,四处都找不到出口。”[7]水意象形成的困顿感也贯穿了《夜莺湖》的叙事,对于“我”和苏丽而言,“水”曾经至少两次吞噬我们的亲友,“我”也一度想长眠水下,苏丽认为死去的弟弟会变为迷路的水鬼,“看着是往前游,其实没方向,”“回头不是岸,只有汪洋一片。”[8]“我”沉入劳动公园的泳池,任由一潭死水裹挟住自己,“双手向前扑去,奋力握向那些光线,却越沉越深。”[9]
整体而言,“困于水底”是班宇的东北叙事中常见的修辞,这一心理意象充分展现了一代人在历史错动时刻的精神困局与集体迷茫,他们并非没有在历史变革中努力寻找出路,但即便拼命往上游,也终究难逃被吞噬的命运。“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构成了班宇在叙事中不断回溯的历史起点和话语氛围,而水意象的使用则有效地实现了这一表达需求,也使小说萦绕着一种悲凉的、宿命般的美学氛围。
二、逃逸与突围
正如上文所述,班宇在小说中表现了一代东北人的困境,但他们的生活也绝非毫无生机可言,恰恰相反,故事里的主人公常常会在困顿之时迸发出生命的尊严、力量与诗意,无论是《盘锦豹子》中金刚怒目的孙旭庭,《肃杀》中摇旗呐喊的肖树斌,还是《空中道路》里吊车司机李承杰浪漫的城市构想,《安妮》中人们对于流星的寄托,许多人物身处困顿之中,却充满了逃逸的冲动、突围的能量和对自由的渴望。在这一表意维度中,以大海、暴雨等为代表的水意象象征着远方与自由,使小说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诗意,而以游泳池为空间载体、表现人物奋力游动或是跃入水中的书写,则表达了一种抗争的姿态和突围的精神。
班宇曾在创作谈《为了逃逸而书写》中提到了小说《逍遥游》,在他看来,许玲玲与好友的短途旅行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逸出”,“对很多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契机,但对于小说里的人物来说,已经拼尽全力,始终相互维护着,许多人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稍微丰富一些,并为此筋疲力尽。”[10]《逍遥游》里的许玲玲身患绝症,与生活处境同样艰难的发小谭娜、赵东阳同去秦皇岛,对于三人而言,这趟旅行已然是一种奢侈,但也是一种对于苦涩生活的抵御和逃逸。在小说中,水意象充分表达了主人公对自由和超越的渴望,例如,抵达山海关后,“我们俩步伐轻快,仿佛在水里游着,像是两条鱼。”[11]到了老龙头,许玲玲登上澄海楼,见到了宽广的大海,眼前的一切仿若庄子《逍遥游》的重现,这让她的心情得到了短暂的纾解。在这里,小说的景物描写充分外化了人物的心境:“有霞光从云中经过,此刻正照耀着我,金灿灿的,像黎明也像暮晚,让人直想落泪,直想被风带走,直想纵身一跃,游向深海,从此不再回头。”[12]原本沉重黯淡的生命骤然拨云见日,俨然一种超然的顿悟,最后,她收拾起所有的孤独和悲哀,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之中,完成了自己的“逍遥游”。水意象的使用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轻盈而超逸的美学效果,正如程永新对《逍遥游》的评价:“闪动着毫不刻意的诗性,贴着一群普通人卑微而沉重的生活,写出了生命隐约见底时的生机与飘逸。”[13]
大海意象在《工人村·超度》的故事结尾也有显现,失业后的李德龙和董四凤为假古董贩子老孙做完法事,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李德龙听着自己的摩托车发出平稳而踏实的突突声,他“想着自己是在开一艘船,海风,灯塔,浪花,礁石,在黑暗的前方,正等待着他逐一穿越,唯有彼岸才是搁浅之地”[14]。尽管生活困顿艰难,但在李德龙的想象中,他终将扬帆过海,抵达自由的彼岸,而那些搏斗或是撞击的痕迹,也正是生命独特性的印证,“在黑夜里,在海水里,他们正是凭着这些痕迹找到彼此,并重新依附在一起。”[15]水意象的使用令小说具备了一种理想和温情的光辉,也让读者窥见了“父一代”的真实面相与精神尊严,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逸”并非怯弱的逃避主义,而是终将回到生活本身,承受所有的苦难,重新出发。
《安妮》是班宇小说中颇具先锋色彩的一部,B与未婚妻即将结婚,但他似乎对此并无期待,循规蹈矩的生活也早已丧失了激情。在一次堵车中,B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个暴雨之夜,城市仿佛在雨水中漂浮起来,变成孤岛,但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试着让自己飞起来,在铁皮上滑行,然后飞在雨里,如鸟人一般,向下望去,那些车像一艘艘玩具船,在世界的澡盆里摇来荡去。”[16]水意象表达了人物的逃逸和超脱,B甚至拥有了一种飞翔的姿态和俯瞰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中,原本平常的世界变得陌生化,获得了一种超凡的诗意和跻身另一维度的可能。受到“逃逸”诱惑的B终于不告而别,他解脱了固有的自我,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人物面向困顿的另一种精神姿态是突围,在这一表意空间中,班宇常常以游泳池作为空间载体,表现人物奋力游动或是跃入水中的动作,以彰显其突围和抗争的精神。在《冬泳》《渠潮》《夜莺湖》等小说中,游泳池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出现,且往往是萧条、破败、污浊的景象,既象征着公共空间的消亡,也是人们溃败的生存状态的隐喻。但即便在这样死气沉沉的空间中,小说中的人物却时常有突破之举,例如《冬泳》中的描写,“池面如镜,双手划开,也像是在破冰”“我迈步上前,挺直身体,往下面跳,剧烈的风声灌满双耳,双臂入水,激起波浪,像要将池水分开”[17],呈现出突围的力量和精神。
三、死亡与救赎
在班宇的小说中,水意象也常常联系着暴力和死亡。逃逸和突围终究是艰难的,对于自由和超越的渴望甚至常常只能停留在想象中,班宇没有回避这种自救的失败,在《枪墓》《冬泳》《于洪》《夜莺湖》《渠潮》等作品中,作家书写了小人物奋力挣扎的徒劳,这些故事往往伴随着死亡事件的发生,但与此同时,死亡又指向了救赎的维度。在这种书写中,水意象的使用使小说兼具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质,呈现出独特的寓言结构和美学张力。
最为典型的文本是《冬泳》。小说中的“我”与隋菲因相亲结识,后互生好感,隋菲的前夫、社会混子东哥上门勒索,“我”用板砖将东哥拍倒,次日平静地同隋菲到卫工明渠祭奠隋菲亡父。行文至此,“我”一再隐晦的幽暗过往和小说的终局才得以揭示,“我”居然与卫工明渠失足少年和隋菲父亲的死密切相关,对于读者而言,此时的阅读期待或许是迎来一个解密的时刻,但文本却突然从现实主义跳接到了现代主义,“我”毫无预兆地开始脱下衣物,纵身跃入湖底,在水中,“我”见到了隋菲下落不明的父亲,甚至目睹被医生诊断不育的隋菲再度怀孕,并且出乎意料的是,表面上污浊不堪的卫工明渠实则干净清冽:“明渠里的水比看起来要更加清澈,竟然有酒的味道,甘醇浓烈,直冲头顶,令人迷醉,我的双眼刺痛,不断流出泪水。黑暗极大,两侧零星有光在闪,好像又有雪落下来,池底与水面之上同色,我扎进去又出来,眼前全是幽暗的幻影,我看见岸上有人向我跑来,像是隋菲,离我越近,反而越模糊,反而是她的身后,一切清晰无比,仿佛有星系升起,璀璨而温暖。”[18]在这里,水既代表了埋葬与死亡,令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而诡谲的色彩,但同时又指向了救赎,“我”跳入卫工明渠,逃离苦涩的生活和黯淡的内心,而在水中,“我”却逐渐摆脱了那些“幽暗的幻影”,希望的力量再度冉冉升起,使我在走向终结的同时也仿若获得重生。卫工明渠表面的污浊黏稠和内里的清澈温暖也形成了一层对比,仿若此岸与彼岸、真实与虚构的隐喻,它们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此岸的苦难内蕴含着彼岸的救赎,彼岸也同时完成了对现实的解脱,小说结尾弥漫着一种宗教般的理想主义色彩,“我”最终从水中“复活”:“我赤裸着身体,浮出水面,望向来路,并没有看见隋菲和她的女儿,云层稀薄,天空贫乏而黯淡,我一路走回去,没有看见树、灰烬、火光与星系,岸上除我之外,再无他人。”[19]
《冬泳》中出现的卫工明渠也同样出现在《渠潮》中,卫工明渠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沈阳的一条人工河,主要用于排放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既是沈阳人的“集体记忆”,也是班宇小说中鲜明的东北物象。小说中的明渠往往污浊不堪,且时常作为淹死人或抛尸的场所出现,因此,在论述水意象所指向的“死亡与救赎”意涵时,明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空间载体。
在小说《渠潮》中,李迢接连遭遇了母亲早逝、哥哥李漫打架伤人入狱、父亲失踪等密集的生命打击,哥哥被释后精神失常,李迢努力地帮助哥哥重建生活,却只等来了哥哥淹死在明渠中的噩耗。李漫同样失意悲苦,他勤学苦读,却连续三年高考失利,在经历了入狱、疯癫、家破人亡后,他纵身跳入卫工明渠,坚信只要身体随着明渠的水绕城一周,进入浑河,最后就可以流向大海,而到了那里,所有的人都会重新相逢:“我游到终点了,原来卫工明渠直通黄浦江,这里到处是帆船,漂得很慢,岸上的人都很有礼貌,……这里有一些旧相识,也有新朋友,人人不一样。”[20]卫工明渠的改造承载着城市繁盛的未来,它在梦中通向黄浦江,是爱情、希望,也是精神上的返乡[21],而“再次遇见”的表述也同样出现在《冬泳》的结尾,表明水既是人的葬身之地,又连通着另一个世界,使得以死亡作为终结的小说并不给人以压抑和沉重之感,而是展拓了苦难叙事和底层叙事的空间,使文本具有了一层超越的、悲悯的美学质地。正如张学昕所言:“他的叙述,虽然冷峻、荒寒、肃杀,但是潜隐在文字背后的却是干净、动人、温暖的内心和善良的情怀。以温情抵御‘肃杀’,抚慰、缓释精神创伤和人性的低迷,这也成为班宇叙事伦理和精神逻辑的起点。”[22]
四、结语
班宇的小说书写了90年代的东北集体记忆,为一代东北人的生存与精神造像,在班宇的东北叙事中,水意象起到了重要的表达作用,它既象征了历史的席卷与人的溃败、挣扎、离散和困顿,也是个体自由与救赎的寄托,水意象的使用结合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质,这一独特的表意模式也拓展了文本的表意空间与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