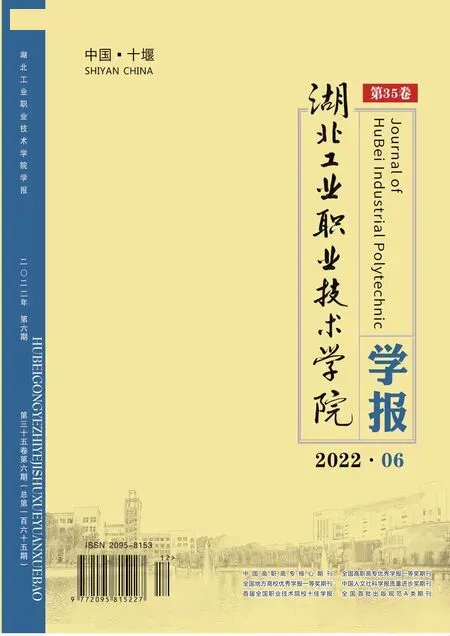论金圣叹的悲剧美批评思想
——以腰斩《水浒》《西厢》为例
李 莉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金圣叹作为明清著名的文学评点大家之一,他对于经典小说、戏曲的评点打破了明代以往的零散化、感悟化的批注式评点,推动了宏观整体式评点的诞生,具有高度理论概括性。金圣叹阅书无数,往往在作品之后设置总评,以便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解,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文论。因此,可从其评点中窥见金圣叹的文学思想。他的评点极具理论性和哲学性,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极好的推动。虽然现今有关金圣叹的文论研究极多,但因金圣叹的思想纷繁复杂,仍有部分文论还需后人仔细推敲。西方自古希腊开始,便有清晰的悲剧观,系统的悲剧批评理论。西方认为中国古代无悲剧,也无悲剧理论。其实不然,除去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悲剧外,还有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品,并且中国的悲剧思想也独有自身的特色,其中金圣叹的评点就蕴含丰富系统的悲剧理论。为了深入探究金圣叹的悲剧意识,现以金圣叹腰斩《西厢记》《水浒传》的两个评本为例,系统的分析其展现出来的悲剧美批评思想。
本文所采用金圣叹的悲剧概念与传统概念有所区别,既非传统教材中定义的广义的悲剧,也不是指狭义的悲剧。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或是艺术作品中所描述的悲剧过于宽泛,难以把握。而狭义的悲剧则是专指正面人物的失败或毁灭的戏剧艺术形式,所涉及的含义又过于狭隘,难以概括金圣叹所述的悲剧内容。因此,本文总结金圣叹的悲剧表述为:表现正面主人公失败或美好理想的毁灭;或是能揭露社会黑暗,展现统治阶级腐败与黑暗势力猖獗;又或是美好被破坏,现实难以扭转,努力皆是虚妄,内容严肃,格调崇高,能给人以警醒,给人心灵巨大震撼的文学艺术作品[1]。这样的悲剧概念正是从金圣叹腰斩《西厢记》《水浒传》的评本中能够得以体现。
一、金圣叹悲剧思想的溯源
纵观金圣叹的一生,不难发现,他与平常文人有极大不同,他从未踏上仕途,甚至生命最终也因其狂放怪诞的性格而草草收场。金圣叹一生动荡,因“哭苗案”被杀,终年54岁。学界认为明朝至万历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被称为晚明时期,可说其一生都生活于经历重大的变革时期,因此该时段对其的思维方式以及性格成长具有重大的影响。金圣叹腰斩《水浒》评本成书于崇祯末年,而金圣叹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成书于清顺治十三年,这两本书虽成书时期不同,但皆是作于金圣叹晚年思想成熟时期,而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金氏腰斩两书背后的悲剧思想就不得的分析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2]。但由于对金圣叹掌握史料的缺乏,难以从历史中得出形象立体的金圣叹,他将一生心血都融铸于文学评点中,由此我们可从其评点中窥探其个人经历及性格特征。
(一)金圣叹所处的时代背景
明末清初是一个衰败、动荡的时代,再加上这一时期的皇帝昏庸无道,宦官当权,民不聊生。经济日益萧条,外来思想的侵袭,导致社会环境异常活跃,但又缺少一定的秩序进行规范,导致整个市场混乱不堪。各地因官府的压迫,百姓不得不奋起反抗,暴乱丛生,社会动荡不安。并且当时各地边境也极不安定,后金的实力日益增长,都对明朝安定产生极大的威胁,让其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局之中。社会的动乱难免对当时的人们思想造成波动,特别是生活在重要文化要塞吴中地区的金圣叹所受冲击更为强烈。面对这样的社会,金氏的思想难免带有一丝悲天悯人,对社会的悲痛,对人民的悲悯无不冲刷他的思想,而这样的悲剧意识也渗透在其文学评论中,在其评点作品中时时刻刻的彰显出来。
明后期的君主多为无能之辈,致使当时的统治腐朽异常,官员贪污成风,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四处剥削百姓,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金圣叹的家乡苏州,更是因其为富饶之地,被压迫的格外严重,也爆发了无数斗争运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生存日益艰难,皇帝昏庸,官员暴戾,使得无数以出仕为目标的读书人终日笼罩在黑暗中。金圣叹当然难以避免,面对理想破灭,前途无望之际,他的内心自是充满无限失望与不甘,满腹才华无处施展,最终只能将悲伤倾吐于作品中。由此,在其批评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狂放”的文风,不难看出他腰斩两部作品背后的悲伤情感,对世俗进行不遗余力的讥讽斥责,对社会的满腔失望之情。
(二)儒释道思想的影响
金圣叹自幼便好读书,但对与科举相关的教育典籍却表现出极强的“抗拒”,他内心并未将世人视为圣书的儒家经典放于心中,正如其所言:“吾年十岁,方入私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每余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3]11由此不难看出,其对“四书五经”等书的“厌恶”心理。金圣叹虽对正统思想时时表现排斥,然而就其一生的大量的评点中传递的思想能够表明,他并不是毫无抱负之人,实则他一直都有着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只是无奈现实残酷,在其有感社会艰辛时,得不到当权者认可时,只能将满腔热情压抑隐藏,只能通过逃避来使得内心苦闷得以疏解。他看似十分排斥儒家思想,然而正是儒家“入世”思想在暗暗地影响他,让他有着“入世救国”之心,却难以实现,最终心中只能苦闷难耐,悲伤难抑。
金圣叹自小就学佛,劝人向善,对释、道二家中洒脱自由的思想十分向往,但同时他也认同儒家学说中的入世思想。金圣叹一面认为人生虚妄,生命短暂,一切皆为云烟;一面他却也认为好男儿应志在报国,建立一番功业,但他也排斥腐朽的官府生活。金圣叹所处的社会环境复杂,处于两朝交汇,思想混杂之际,这也导致其身上思想冗杂,儒、释、道思想的影子皆能在他的身上体现。所以金圣叹的思想本质是矛盾的,他既渴望佛道洒脱自由的生活,但又有着儒家所特有的积极入世的强烈冲动。正是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加上对现实的无望,使他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观情绪。
(三)史书写作思维的影响
自唐代古文运动后,《左传》《史记》等史书的写作方式与叙事手法也受到文人的鼎力推崇。中国的叙事文学也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史书写作注重纪实性,故采用史书的标准就与小说的虚构性形成天然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而然渗透于评点家们的评价中,金圣叹评《水浒传》时也难以避免。《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金圣叹就曾写有好几篇序来表达自己对于小说的看法。由此可分析,虽然金圣叹对小说的虚构性有一定的接受,但评点仍是带有对待史书的固定思维进行看待。这也导致他认为《水浒传》中不合时宜的情节应删去,对于人物的悲剧走向也应是符合历史,符合社会环境,而不应过度地凭空捏造。正如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不说鬼神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3]2由此不难看出,金圣叹虽认同小说的自由发挥,但并不赞同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4]。因此,金圣叹对于《西厢记》《水浒传》的腰斩则是有迹可循的,依循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实情,在他所处的社会中,百姓受苦,起义是必然,但他不愿宋江等人走向招安,于是给他们安排惊梦结局,让英雄人物有了更为悲壮的结局,比原先的结局更让人黯然神伤。相较《西厢记》原本的大团圆结局,金本的以梦为结,前程未卜则显得更为真实、凄凉,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终是难全,这是金圣叹对现实的客观书写,也是对社会悲剧的别样呈现,史书写作的真实性也在无形中影响他的悲剧思维,不是以往的小情小爱的悲,而是小人物苦苦挣扎依旧难逃命运轨迹的社会性悲剧;是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向前的悲剧。
二、金圣叹悲剧美批评理论
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多是感悟式、经验式的理论。它们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反应评点家在一定阶段对某一艺术问题的理解,但却难以从整体体现其艺术理论规范的自觉追求[1]。就悲剧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缺少如亚里士多德等所提出的规范化的悲剧定式,几乎每部悲剧都各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使得后人难以深入解读与研究古代批评家的悲剧理论。因此,我们需要从批评家的多方评点来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他们的悲剧美批评理论。
我国古代评论素有直面人生之传统,所谓“剧场即一世界”“古今一戏场”[5]等等,皆表明我国古代批评家的文论观念中难以割离的对现世人生的清醒认识。自晚明后,日益严峻的社会环境以及过度的文化禁锢,这种认识加剧批评家正视历史后内心清晰的感伤情绪和虚幻意识,形成一股浓浓的悲凉的悲剧观念。早在金圣叹之前,就已有批评家痛斥盛行的“大团圆”结局,并且明清的批评家认为应站在宇宙人生观的高度去看待悲剧,除激起人“恐惧”“怜悯”等情绪外,还应追求对“人生本质”的普世认识[5]。因此,以金圣叹为代表的明清批评家他们具有彻底的不妥协的悲剧观念,但金圣叹因其特殊的遭遇,其观念中还带有独有的佛老之学,“世事皆空”的虚幻悲凉之感,而这样的观念也体现在他进行作品评价中,由此,构建出独具特色的金圣叹的悲剧美批评理论。
(一)“无边苦事”现实论——主题悲剧观
《西厢记》结局之争,历来是评论界的一大热门话题。其中就有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主张止于《草桥惊梦》做悲剧结局的剧论家。就《西厢记》中崔、张爱情纠葛而言,金氏认为在其所处的现实世界中,妇女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因而此剧的悲剧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并且金本将原文中离经叛道的崔莺莺塑造成规矩懂礼的大家闺秀,以此来迎合小说封建礼教罪恶的悲剧主题。金圣叹选择对《西厢记》进行逐句评点批改,正是为了真实的反映封建社会的丑恶现实。他评点《西厢记》的核心思想就是“真实”,无论是真实的人物还是真实的生活,都是为了反映社会的真实。他选择删去第五本,将其变为一部引人深思的社会悲剧,正是因为其看透了封建礼法对人性的束缚与扼杀。结合起他自身经历,他早已明了在当时的社会想要通过科举改变自身的地位是徒劳之举。因此,现实早已决定张生与莺莺那动人心魄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无边苦事”。他们从相知相识到相爱,见面到结合却仍旧难以冲破现实那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对男女自由爱情的打压,最终只能走向分离。
金圣叹以悲结尾,抛弃过往的大团圆结局正是他看出来悲剧生成的必然性,崔张二人的悲剧于当时社会来说,是无解命题。这正是青年男女对真爱向往与落后的社会制度间难以调和的矛盾造成的。金氏认为《西厢记》的悲剧主题不仅是相爱男女被迫分离的爱情悲剧,更是封建压迫下人难以对抗的社会悲剧。他将《西厢记》的结局变为一场悲凉凄美的梦境,使得其悲剧主题更加增添几分“现实虚妄”的空无感。这样的主题悲剧观,是看透现实后,得出悲剧产生是人的个性发展与现实的冲突,是无力回天的社会悲剧,是金圣叹超越前人所独有的“无边苦事”现实论。
除在《西厢记》外,金圣叹同样选择腰斩《水浒传》,以“惊噩梦”为结局。这同样也是金圣叹面对恶浊人生,而欲所为却难所为的矛盾心理。金圣叹的惊噩梦结局,虽使得小说最后具有荒诞之感,但其背后却暗含一种更为现实的悲剧特征。小说原以农民起义为始,招安为结,但招安的安排本就不合情理,试问哪位皇帝能安然接受想要夺自己皇权之人,就算迫于现实,无可奈何下,又怎可能为其树碑立传,使其名留青史。显然,这样的结局是虚幻的,难以实现的,终究只是作者留下的光明期盼,但这样的光明却大大的削弱了原本的现实价值,这也是金圣叹悲剧观念里无法认同的。于是他改为以梦为结,虽是梦却更显真实,统治阶级难以接受宋江等人,而是选择将其屠杀殆尽,这不仅加重全书的悲剧意味,也更加凸显出现实中统治阶级与百姓间那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这更加凸显了金圣叹所提倡的主题悲剧观,这样悲剧观也使得作品的艺术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二)“黄粱一梦”虚空论——情节悲剧观
金圣叹的悲剧美批评思想主要就是体现在他对《西厢记》与《水浒传》的评点中。当中,他并未明确提出“悲剧”的概念,但他的悲剧思想却贯穿其中,除主题悲剧观外,金圣叹还特别注重情节悲剧观,以巧妙的情节结构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由此与主题的悲剧照相呼应,相辅相成。
正如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认为,人只是一种“非我”的存在,“我固非我也,非生之前,非我也;既去以后,又非我也”[6]2,人的现世存在只是一场虚妄,“从于一劫,乃至二劫三劫,遂经千劫”[6]173,终须“度脱”;而“度脱”的最佳办法就是“离别”,“自此一别,一切都别,萧然闲居,如梦还觉,身心轻安,不亦快乎”[6]175。他认为离别的尽头便是能够度脱,而悲离的结果就是对人生的一种大彻大悟。正如他评《西厢记》所云,作者必有“大悲生于其心,即有至理出乎其笔”[6]183,因此文中,金圣叹选择腰斩《西厢记》,通过“入梦是状元坊,出梦是草桥店”的结构,表现了主人公在悲痛、度脱后“自归于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6]189这一至理。
金圣叹在原本《西厢记》中删去“赖婚”一折中,张生对老夫人所说的“书中有女颜如玉”的话。在“哭宴”中,崔张二人哭别时,金本加入了老夫人要张生“唯以功名为念”的嘱咐,把张生对莺莺说的“小姐心里儿难念,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一段话改为“小姐放心,状元不是小姐家的,是谁家的?小生就此告别”。金氏将此情节改动的目的异常明显,就是为了突出不是状元郎,难娶崔家女,只有门当户对二人才有可能。这也与小说社会悲剧的主题相映合,现实从一开始就决定崔张二人的爱情难以撼动封建宗教制度,即使他们真心相爱,结局也早已从细节处得知,悲剧始自也是悲剧结[7]。金本从一早就安排二人爱情是一场虚幻梦境,从钟情至心心相许,只是严酷现实里美好的“梦境”,现实中的种种已然注定二人爱情难修正果。虽小说结局是梦,实则更符合二人最终的结局,二人之前的种种美好看似是现实,实则是封建社会下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美好幻象,更似梦。这个“梦境”就是礼教压迫下读书男女的“黄粱一梦”,表现出一切皆虚空,最终都是镜花水月。
《水浒传》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世俗的悲剧。百回本小说的最后一回,所描写的情节就是宋徽宗在李师师处休息时,与宋江、李逵梦中相遇的凄凉之景,呈现了幻象破灭后听天由命的悲凉绝唱。宋江只能在梦中表达自身的忠君之情,又只能由此才能得到皇帝的真情相待;“黑旋风”李逵再凶悍,也只能在梦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取得想要的成功。梦境与现实的鲜明对比,更是突出了命运难以改变的可笑感。虽然金氏删去之前的《水浒传》已然表现出大梦一场,万般努力皆是空的悲凉感。但也因后文的招安情节而大大削弱了全文的悲剧性,正如朱光潜所说的:“对悲剧造成致命伤的并不是邪恶,而是软弱。”宋江的软弱使得原本轰轰烈烈的起义造反,因招安而变得正义化,也因招安而变得悲惨。难以想象当年勇斗恶虎的武松,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的二人最后会真心皈依佛门,与残灯相伴。英雄武松断了一只手在寺庙中惶惶度日。这样的结局,看似是对众人壮志未酬的梦幻补偿,但更像是一场美丽的谎言,虚假的悲剧,悲则悲矣,却并不符合事实,与前文的情节发展并不连贯。金本并不认同这样的悲剧,他最讨厌百回本中宋江的就是其软弱性,于是他将情节大改,删去后面的情节,将最后一回改为所有人全部被砍头的“噩梦”。金圣叹在梁山事业顶峰时期选择以梦为结,正是因为他的内心是不想梁山好汉与正统之路更加渐行渐远,还不如让这一切变为一场英雄梦,大梦初醒,万事皆空,醒后万物皆无。高潮时落幕更是增添一种如梦如幻的幻灭感,使得全书的悲剧意味有了极大的升华,将个人的渺小命运与宇宙茫茫的无限进行联系思考,让人更叹荒凉[8]。作者将招安结局大改,何尝不是抒发人生如梦,感叹时代悲凉之感,这正是一种文人的悲观意识在情节中悄然体现。
(三)“理想破碎”人物论——人物悲剧观
金圣叹最擅用“生”与“扫”、“此来”与“彼来”、“渐”与“得”等联动情节发展的词来作为人物心理活动的链条,由此揭示出崔张二人的性格与命运不断搏斗的过程,并且,他还清晰地指出支配这个过程的乃是人物性格塑造下“不得不做”的必然规律。这就是说明主题悲剧与情节悲剧等故事的外在形态是由人物内心的性格悲剧为基础的。换言之,其实我们常说的戏剧冲突就是人物冲突,故事悲剧也是人物的悲剧。全书围绕主要人物出发,人物构建情节,情节突出主题,由此使得全书的悲剧意味得以展现。
金圣叹删改《西厢记》后,使得崔莺莺由敢爱敢恨的大小姐变为一个社会女性悲剧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对《西厢记》的批评往往是自批自改,可以说是他的再创作,他坚决地删除《西厢记》第三本,让莺莺成为一个悲剧性格的典型,从而反应出当时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并且张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寒门子弟难有出路的残酷现实,科举改变命运的故事已然成为过往,使得张生也增添几分理想破碎的凄凉感。金本选择全剧在张生赴试途中,由草桥惊梦的浓郁的悲剧气氛中结束。张生梦莺莺,醒来却身处荒郊野外,满目凄凉,别恨离愁掺杂于心,这种停留于悲凉气氛下却让故事戛然而止,一腔悲情难以诉说的悲剧比之大团圆结局更为深刻震撼。而崔张二人的人物塑造也更添几分真实感,在那样的时代,分别才应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二人经受了封建教育却仍觉醒自我,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渴求认同,不断地与命运对抗,与社会对抗,却只能以失败告终,让二人的形象塑造也更为丰满,印象深刻。
美梦像人生苦痛的一种别样补偿,但却难以引起人的哀痛与怜悯。正如大团圆结局虽给人以慰藉,却终究难让人记忆深刻,给人心理以沉痛一击。于是《西厢记》中,金圣叹选择腰斩第三本,《水浒传》金圣叹同样腰斩后几十回,留下七十回本。正是因为其不愿看到他所欣赏的水浒好汉走向回归之路,走向招安。如若招安与死亡是他们必选的两条路,那他宁愿他们轰轰烈烈的死,也不愿其窝窝囊囊的活。因为死代表正义的延伸,代表与命运顽强的抗争,代表命运终难战胜正义。这才能体现108位“杀身成仁”的凛然。金氏为书中人物塑造的皆是勇士,皆是豪杰。他最不愿看英雄末路,但他得尊重历史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宋江等人的覆灭不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某个阶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想在残酷现实面前的一次“悲壮”不可谓不令人心生震动。这正是金看透了悲剧生成的社会必然性,无论是崔张抑或是梁山好汉,在当时的社会,他们所追求的皆是虚妄,他不愿以传统价值观观照他们,却难以为他们安排更好的出路,于是以梦为结,虽是悲,但悲的壮烈,悲的动人,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安慰吧。
三、金圣叹悲剧美批评理论的价值
金圣叹的悲剧美批评理论对清朝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为清朝小说戏曲评点定了整体基调。无论是毛氏父子评《三国》抑或是脂砚斋为《石头记》所做评点,在形式与观点上皆带有金圣叹的影子。中国传统的评点中并没有“悲剧”的概念,向来只有“怨谱”“苦戏”之说。而金圣叹的悲剧思想则是对中国传统戏曲“苦戏”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虽“苦戏”注重对苦事的表现,但只局限于戏曲作品中,并未提高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金圣叹的悲剧美学思想则是注意到人的性格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认为造成悲剧的原因是社会。他对悲剧的认识是深刻的,虽具有他自己的主观认识,但他敏锐地察觉在当时的社会下个人力量的渺小,以及个人难以撼动封建宗教制度的可悲,人性虽觉醒却仍难在封建社会下散发,个人欲求的追逐与此要求难以实现的现实。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以此认识指导的悲剧美学批评理论,仍可以说的上是独一份,也对后人清晰地感悟悲剧以及对《西厢记》《水浒传》二作的艺术性也有了极大的加强。
(一)对清代评点家的影响
金圣叹评《西厢记》《水浒传》的悲剧美学的核心思想则是“真实”,重视社会的真实,人物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金本的《水浒》《西厢》所悲之处正在于其“真”,悲得真实、令人心碎。这种“真”让人感到震撼,而难以改变、无力回天的悲剧也让人流连忘返。作品描述的越真实,则越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金圣叹的悲剧观,重真实的思想则被李渔继承[9]。金氏不屑《西游记》这种表现虚幻情节的作品,李渔同是如此,他也认同金氏所提倡的能够默写现世人情的作品。金圣叹一反过往的大团圆结局也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清代的诸多评点家也多不满意悲剧作品中的喜剧结尾方式。以李渔为代表,他认为任何的艺术对生活描绘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只能做到相对的完美,很难达到极致与完全的状态。因此,李渔也是非常认同金氏腰斩两书后的悲剧结尾。除李渔外,金圣叹评《西厢记》的文论思想也被毛纶在评点《琵琶记》时被完美的继承下来。毛声山提出“无结之结”的观点则就是针对悲剧结局而言。毛氏认为欢含悲,合亦含离,一味勉强地制造大团圆结局只会违背自然之理。而这样不归于圆整的文论思想则与金氏的十分契合,由此可见,金圣叹的悲剧美批评理论对后世评点家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对读者阅读的正向激励
明清涌现无数才子佳人的小说、剧作,如被认为达到悲美境界的明末孟称舜的《娇红记》,同是反映封建制度扼杀青年男女真挚爱情的故事,书中却未曾描写任何主人公与封建家长的正面冲突,全书只有二人被毁灭的结果。面对罪恶的封建宗法婚姻制度,追求自身爱情的二人不是奋力抵抗,而是选择妥协,一味地适应这落后的婚姻制度。最终二人落得一个双双殉情的结局。而金本的《西厢记》一改原来的大团圆结局,不仅打破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虚假面具,更是将血淋淋残酷的现实摆在众人面前。并且他看到的是社会现实造成的青年男女的悲剧,他塑造了为追求自由爱情而与社会现实不断争斗的崔张二人,让二人的悲剧变得更为壮美崇高,这样的悲才能真正的唤醒浑浑噩噩的众人,看透虚伪封建制度的丑恶嘴脸。面对《水浒》,金圣叹的心是复杂的,一面他憎恶这样扰乱和平的战争,一面他同情悲苦的底层人民。矛盾的心理下迫使他看到后面他们被招安时,他是不认同的,是难以接受的。那样的悲剧是虚假的,他更想要的是壮烈的悲,才是真正令人深刻的“英雄悲剧”。看似都是失败的结局,众人的毁灭,但若以原书那般发展,虽得到虚假的安慰,却终是虚无。而虽改后看似“噩梦”,却仍能使人有更深领悟,带来毁灭之后真正永恒的胜利。因此,金圣叹的悲剧美批评理论才能使人真正认识悲剧,给人以警醒。
(三)对作品艺术性的加强
《西厢记》被誉为“北曲压卷”之作,自其诞生后就一直是元杂剧的代表作品。但《西厢记》虽一直备受文人墨客们推崇,却多是由心而发的感悟式夸赞,少有理论性的总结点评。因此,《西厢记》虽一直都有经典地位,在理论领域却难以站稳脚跟。直到金圣叹于顺治十三年完成对其的评点,才使得人们对于《西厢记》的经典性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并且金氏对《西厢记》的腰斩与改动,也使得原著中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变得合情合理,使其故事发展更为流畅。虽仍有许多人对金圣叹的改动带有争议,但不得不承认金氏的改动也将《西厢记》推向了更高的地位,难以比较金本与原本孰优孰劣,只能说金本的悲剧美学使得《西厢记》超越同时代的其余作品,一扫过往的大团圆结局,为整个文学发展带来更为崭新的方向,并且悲剧历来都被认为更加震撼人心,艺术性更高,让人更加记忆深刻,这何尝不是赋予《西厢记》蓬勃的生命活力,使其更加熠熠生辉。
在水浒流传的漫长历史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金圣叹的名字几乎与施耐庵一样重要,“腰斩”的《水浒传》在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闪烁着时代的光芒。无论是余氏本抑或是郭氏本,皆淹没于金本的光辉下。同一个故事,却在不同评点家手中呈现出不同的故事,金评本与过往百回本的本质差别,可能就体现在作者各自人生的不同价值观以及金氏渗透于其中的浓厚的悲剧意识。金圣叹以其独有的人生经历为本就闪耀的《水浒》名著更是添光溢彩,他让他心中正气豪情的英雄好汉走向毁灭,但却赋予他们更为崇高的人格,同样无从评说那一版本更好,只能说金圣叹以自身独有的悲剧观塑造了他眼中的水浒故事,使得后世读者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故事发展,也让这个故事的艺术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加深。
四、小结
金圣叹的悲剧美批评理论不仅是对当时大团圆情节的一大反叛,更是因其敏锐的认识到社会现实与个人意识觉醒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无论是《西厢记》还是《水浒传》究其本质都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悲剧。崔张的生离死别,水浒众人的“砍头”噩梦皆是那个社会环境下发展的必然真实。他的主题悲剧观、情节悲剧观、人物悲剧观都是围绕他清晰地认识人的追求、反叛与社会环境现实环境的冲突,想却不能才是悲剧产生的根源。因此,虽然他为两本书安排的“梦境”结局带有佛道的虚妄思想,但背后却仍旧隐藏着他对现世的清醒认识。他的这种悲剧观打破以往的沉迷于美感的悲剧思想,使悲剧理念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也对明清的悲剧观产生极大的冲击力,为后来的评点家带来巨大的影响,从侧面也为读者带来极好的正向激励,提高了作品整体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