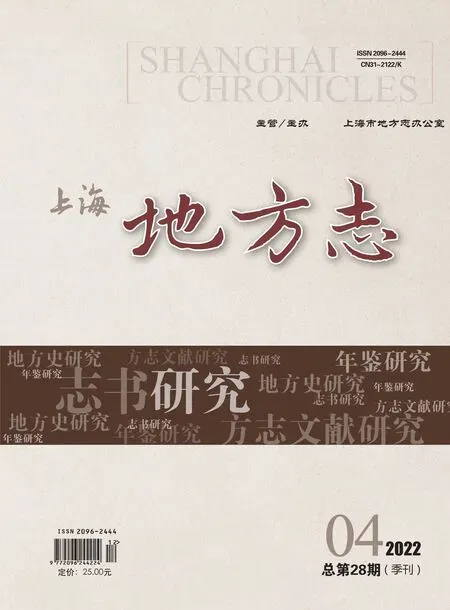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编纂方法略论
——以廉州方言为例
刘显钊
廉州话主要分布在广西合浦县大部分地区及邻近的浦北县南部和钦州市钦南区个别乡镇,是粤语钦廉片代表。广西北部湾地区(北海、钦州、防城港)的汉语方言中,廉州话是唯一一种同时被省、市、县三级志书记录音系的方言,如省级志书有两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市级志书有两轮《钦州市志》及《北海市志》,县级志书有《合浦县志》《浦北县志》《浦北县志(1991—2005)》《合浦县志(1991—2005)》。简单介绍过廉州话源流或语言面貌的志书还有《防城港市志》《廉州镇志》等。第三轮修志启动之际,有必要对第一、第二轮志书编纂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志书中的廉州话记载可谓总结提炼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编纂方法的典型案例。
汉语方言志的纂修向来是地方志部门的老大难问题,其专业性和复杂性常使非语言学专业背景的修志人员不敢触碰,多是外请专家编纂。方志学界对汉语方言志编纂方法的探讨文章相对其他专志而言较少。针对广西的情况展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合浦县新方志方言部分不可或缺的内容——语音、词汇和语法》①余毅忠:《合浦县新方志方言部分不可或缺的内容——语音、词汇和语法》,《珠乡史志》1988年第1期。《对方言志编写的建议》②关玉成:《对方言志编写的建议》,《广西地方志》1995年第4期。《方言志编纂中应该坚持的几项原则》③郭猛:《方言志编纂中应该坚持的几项原则》,《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1期。《简论广西市县志中语言志的得与失》④林亦、周祖亮:《简论广西市县志中语言志的得与失》,《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2期。《第二轮方言志编纂如何突出时代特征——基于对第二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编纂的思考》①陈曼平:《第二轮方言志编纂如何突出时代特征——基于对第二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编纂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期。《〈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续编)》②余瑾:《〈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续编)》,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广西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优秀成果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1—266页。《合浦县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与反思》③刘显钊:《合浦县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与反思》,《中国测绘》2022年第10期。等。
本文旨在于学界对广西的汉语方言志编纂方法研究的基础上,以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内容的得失为切入点,进一步提炼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的编纂方法。下文首先介绍广西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内容及编纂方法,接着在此基础上探讨广西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内容记载的优点与不足,最后对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提出具体的编纂方法建议。
一、广西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内容及编纂方法
广西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内容质量最高者当是作为专志的第一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因为第二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尚未出版,故下文在提及第一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时,直接省略“第一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出版于1998年,廉州话记载位于第一篇“白话(粤语)”第四章“钦廉片”,编纂者称之为“廉州白话”,主要内容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例句”三部分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7—252页。。全文使用语言学国际音标记录廉州话的读音,语音部分有“声韵调配合关系表”,重视收录看似“有音无字”的词,但没有20世纪80—90年代汉语方言研究论文常见的现代方言与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时代汉语读音对应规律叙述,而声韵调例字的数量则与同一时期的汉语方言研究论文一样为4个;词汇的选取范围和记录内容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制定的《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内容丰富而全面;语法例句部分将廉州话、普通话的句法进行比较,基本涵盖廉州话重要的语法特点。另外,“白话(粤语)”篇的概述部分简单涉及廉州话与南宁白话、梧州白话、玉林白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差异⑤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1页。,而《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第五篇“广西汉语方言字音对照”有包括廉州话在内的广西各汉语方言与中古音的一一对应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7—826页。,第六篇第二章“广西汉语方言及有关语言研究”有介绍此前学界对于廉州话的研究成果,但仅提到1987年蔡权在《方言》杂志发表的1篇论文,还把题目弄错了⑦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7—840页。。
《浦北县志》、《钦州市志》(2000年版)、《北海市志》的廉州话内容均出自陆善采之手,而《合浦县志》的廉州话内容不太可能是陆善采写的,他可能只是给过一些建议,这是学界很多人弄混的。《浦北县志》的廉州话记载分为“声母”“韵母”“声调”“常用词语举例”共4部分内容,全文使用国际音标记录廉州话的读音,正文前的概述介绍合浦县廉州话在浦北县得名“下路话”的缘由以及浦北县使用廉州话的人口分布范围及数量,但没有注明调查的方言点是哪个镇;声韵的例字仅有3个,声调的例字数量为4个;常用词语举例较为简单,且个别词语为书面语,参考价值不大⑧浦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浦北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83-784页。。《浦北县志》第二十四篇第三章“方言”在记载浦北县主要汉语方言后,附有“普通话、广州话与浦北县各种方言例句对照表”,实际对比内容只有3句语法例句⑨浦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浦北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4页。。
《钦州市志》(2000年版)的方言篇直接冠以“方言志”之名,形成“志中志”现象,这可能是沿袭传统方志体例所致。《钦州市志》(2000年版)的廉州话记载可分为“声韵调”“词语举例及语法例句”“犀牛脚镇廉州话与合浦县廉州话的区别”共三部分内容①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钦州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08—1313页。,全文使用国际音标记录廉州话的读音,正文前的概述交代为何命名为“犀牛脚廉州话”而不是依照母方言人群的自称“海獭话”;声韵调部分的例字数量不统一,大部分为3个,有介绍犀牛脚廉州话声韵调重要的发音特点以及犀牛脚廉州话和中古音的对应规律与普通话、广州话之不同;词语举例有谈到犀牛脚廉州话的特色词,涉及“有音无字”的情况;语法例句只有4句,其中3句不是口语;最后谈到作者认为的犀牛脚镇廉州话与合浦县廉州话语音、词汇的不同。《钦州市志》“方言志”文末还附有“普通话与钦州市各种方言例句读音对照表”“表现钦州市某些方言特点的顺口溜”②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钦州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37—1340页。。
《北海市志》的廉州话内容可分为“音系”“词汇例句”“佤话、海边话与廉州话的关系”共三部分③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0—1594页。,全文使用国际音标记录廉州话的读音,正文前的概述介绍廉州话使用人群的分布范围以及作者对于廉州话源流的看法;音系介绍内容的选取范围和《钦州市志》(2000年版)“犀牛脚廉州话”相似,但更为详细,然而声母例字数量较少,仅有2个;词汇的选取范围和记录内容有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制定的《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分为29个部类记录,不如专志全面,但作为通志足够丰富,远胜《钦州市志》(2000年版)“犀牛脚廉州话”;语法例句的记录范围是《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的缩略版,若非直接参考便是母本为同一份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提纲;“佤话、海边话与廉州话的关系”主要叙述佤话与廉州话的差别,并附有兴港镇南乐村田寮佤话词语举例,对于海边话与廉州话的异同一笔带过。
在《合浦县志》的评审版和正式版中,“方言”一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评审版即《合浦县志》“方言”原稿的作者是王宗孟④王宗孟:《廉州话的声韵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全文使用国际音标记录廉州话、山口军话、客家话的读音,附有“古今声调对照表”,将廉州话的声调与中古音的声调相对比⑤刘显钊:《合浦县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与反思》,《中国测绘》2022年第10期。。正式版最后采用徐子芳修改的“廉州话拼音方案”(创编者实为宋家东)记录廉州话,完全替换廉州话内容的原稿,周家干在徐子芳提供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又补充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军话、客家话因本地无人制定过拼音方案,《合浦县志》只能沿用原稿,是故最终《合浦县志》第六十三章“方言”的作者应为徐子芳、周家干、王宗孟。《合浦县志》第六十三章“方言”体例的前后矛盾常引起方言学界疑惑,因此这是一段必须要交代的历史。
《合浦县志》的廉州话记载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⑥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0—761页。,第六十三章“方言”的文末还附有“合浦县方言分布表”“合浦方言分布示意图”⑦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67—768页。。全文用“廉州话拼音方案”记录廉州话的读音,但“语音”附有声韵调与语言学国际音标的对应关系;声韵调例字过少,只有1个;对于语音特点的叙述详略得当,尤为值得肯定的是记廉州话的声调数量为8个;“词汇”不列词汇表,亦不随意举例,而是重点叙述语言接触现象及廉州话与普通话的异同;“语法”关注词形变化、词的复合、句法,不选择将廉州话、普通话进行例句比较。
《合浦县志(1991—2005)》编纂时,主编认为方言变化不大,直接沿用《合浦县志》相关内容,将章更名为“语言”,删去“合浦县方言分布表”“合浦方言分布示意图”,其他基本不做改动。不过,《合浦县志》印刷时,个别国际音标因为当年打印技术落后显示不出来,《合浦县志(1991—2005)》在照抄过程中,下意识认为那是空格,直接删去①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浦县志(1991—2005)》,方志出版社2019年,第741—754页。。《浦北县志(1991—2005)》对廉州话的记载基本沿袭《浦北县志》,仅作细节调整,声调例字使用编纂者宋家东于1960年为在合浦县总江公社推行廉州话注音识字扫盲而创编的《廉州话拼音方案》的声调例字“山河美丽谷麦熟”,琅琅上口,但全文国际音标排版时出现多处错误②浦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浦北县志(1991—2005)》,线装书局2018年,第591—593页。。
《钦州市志》(2018年版)的“方言”是重新制作的,该志记载钦州市的2种廉州话,全文用国际音标记录③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钦州市志》(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74—2214页。。一是“犀牛脚话”,内容分为“声韵调”“词汇举例”“语法例句”三部分,正文前的概述介绍使用该方言的人口分布范围及数量。《钦州市志》(2018年版)对犀牛脚镇廉州话的记载较为丰富,但声韵调例字太少,只有1个。且按照方言研究著作的通行做法,再次对同一方言进行调查理应换调查点,“海獭话”调查最好选择除犀牛脚镇以外的其他乡镇,但《钦州市志》(2018年版)不换,可能另有考虑。二是“麻佬话”,仅有声韵调及其特点的概括性介绍,正文前的概述提及“麻佬话”得名缘由及方言人群的分布范围。另外,“犀牛脚话”文前的“白话”概述有提到海獭话、廉州话、马留话、山话之间的关系。
《廉州镇志》没有公开出版,但方言学界的廉州话研究著述多有引用该志的廉州话内容,后文提及的个别值得商榷的说法源头即在此。《廉州镇志》不记录廉州话的音系,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廉州话的分布范围及使用人口,同时介绍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对于廉州话源流的观点。二为廉州话词语举例,但较为重要的亲属称谓不放在第三十七章“方言”,而放在第三十章“人口”,列有“称谓简表”,名“简”而不简,内容详尽,足可资鉴。另外,第三十七章“方言”又有“谚语”“俗语”“歇后语”三节,虽与第一节“廉州话”并列,但其实所述也是廉州话的语料,这部分内容反而比“廉州话”正文参考价值更大。
二、广西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内容的主要优点与不足
作为一部专志,《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对廉州话记载的准确性值得肯定,其内容及编纂方法充分体现方言学界对于方言志编修的主流观点。虽然作者记录的廉州话音系有值得商榷处,如将廉州话的声调数量记为7个,但作者已考虑到这些问题,内容中都有说明,可以说不是原则性问题,只是各派处理方法不同,能够自圆其说。其他同样是由语言学家参与编修的两轮《钦州市志》以及《浦北县志》《北海市志》,其“方言”内容的核心纂修理念无疑与《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殊途同归,只是常受限于通志所给的篇幅,未能充分实现。
《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的廉州话内容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将廉州话命名为“廉州白话”。纂修者认为民间通常将粤方言称为“白话”,廉州话是粤方言的一种。同时,这样命名或许还有志书体例整齐的考虑:廉州话位于“白话(粤语)”篇下。但说廉州话的人群一般不会将母方言称为“白话”。在合浦县居民日常语境中,“白话”指语音更为接近广州话的北海话、钦州话、南宁话等方言。近年来,一直有学者主张廉州话应该归属桂南平话④李连进:《平话的问题与认识》,李小凡、项梦冰主编:《承泽堂方言论丛》,语文出版社2014年,第20—33页。,除语言面貌的考虑外,母方言使用的自称也是重要依据。将廉州话命名为“廉州白话”,违背“名从主人”原则,容易使后来者忽略当地居民的文化心态,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浦北县志》、《钦州市志》(2000年版)、《北海市志》廉州话记载的核心内容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其优点与不足很大程度是因为编辑部肯给的篇幅不同。不过,有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双标:《北海市志》将廉州话视为狭义的廉州方言,广义的廉州方言还包括瓦话和海边话①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0—1594页。。这个说法独此一家,方言学界一般对广义和狭义的廉州方言的定义是:狭义的廉州方言指廉州镇的廉州话,广义的廉州方言包括其他乡镇说的廉州话②张丽红:《广西合浦县廉州方言语音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笔者经过研究后认为:鉴于有些瓦话方言点的使用者将母方言称为“廉州话”,且瓦话与廉州话的差异主要在声调调值,将瓦话归入廉州方言问题不大。“瓦话”因第一人称单数的读音近白话“瓦”字的读音而得名,这是“我”字上古汉语读音的摹写,一些著作为表明这是人称代词增加单人旁为“佤”,但这极容易被误解为佤族的语言,当不取。海边话虽然与廉州话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该方言并无廉州方言的重要特征词“低”(东西之意),母方言使用者也不认为自己说的是“廉州低”,不建议归入廉州方言。《北海市志》对“廉州方言”的界定其实是语言学家干预后的结果。相反,《浦北县志》却不将同样有廉州方言重要特征词“低”的小江话等浦北县汉语方言视为廉州方言的一种,令人困惑。
从对语言资源的关注及语料留存的角度来说,《浦北县志》、《钦州市志》(2000年版)的贡献值得肯定,这也是方言志相对方言研究著作的一个优势:方言研究专著容易受限于某位作者的时间及精力,往往只能抓“典型”。1987—2017年,合浦县廉州镇廉州话的音系被反复记录达10次之多,可能因为方言学界认为廉州镇是合浦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语音更“正宗”。若无《浦北县志》对浦北县廉州话的记录,恐怕浦北县廉州话的特色至今鲜有人关注。至于钦州市犀牛脚镇一带的廉州话,虽然得到学界关注,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地学者不知海獭话与廉州话是同一种方言之故。
《合浦县志》优点之一是记廉州话的声调为8个③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3—754页。,廉州话的第8个声调因为看似“有音无字”,在方言研究著述中常被省略,但从全面展示方言语言面貌的角度来说,第8个声调的记录是对语言事实的尊重。但提出“广府话演变说”值得商榷。该观点认为廉州话的前身是广东商人带来的广府话,依据是《廉州府志》“俗有四民”的记载④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0页。。道光《廉州府志》声称摘录自《大清一统志》⑤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3),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75页。⑥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下册),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50页。,现存史籍最早出现“俗有四民”的是明英宗天顺年间官修的《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称“俗有四民”摘录自宋代《合浦郡志》⑥,同样收录这段记载的《天下郡国利病书》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6),黄坤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88页。《大清一统志》⑧穆彰阿、潘锡恩:《大清一统志》(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52页。则分别称摘录自宋代《太平寰宇记》《廉州图经》。《太平寰宇记》至今仍有流传,内中并无“俗有四民”。而《合浦郡志》《廉州图经》今已散佚,无法得知具体内容。“广府话演变说”作为一种尚未成为学界共识的观点,实不应写入志书中,但后出的《北海市志》⑨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0页。《北海市铁山港区志》⑩北海市铁山港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铁山港区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页。仍然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合浦县志》的观点。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钦州市志》(2018年版)中,其在介绍“马留话”时写道:“马留话据说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留下的话,实际就是廉州话,廉州话地区大多有这种说法。”⑪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钦州市志》(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74页。事实上,古史记载的“马留人”是否存在有待商榷,即便确实存在,其使用的方言也与今日的廉州话无涉;古史记载并无明确提及“马留话”,这一说法更多见于今人著作;现实语境也没有“马留话”这种说法,仅有与之音近的“麻佬话”一称。就合浦县的情况而言,存在祖上是伏波将军马援部属传说的地方多将母方言称为“廉州话”(如廉州镇马江村),反倒是没有这类传说的地方把母方言称为“麻佬话”(如石康镇),这说明“马留人”的传说并非合浦县居民普遍的祖先记忆。而“麻佬话”的得名,可能反映合浦县麻类植物种植史,与马援无关①刘显钊:《广西沿海地区疍家族群问题初探》,《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4期。。
《钦州市志》(2018年版)“方言”还有一个问题是未对浦北县汉语方言展开充分调查,不知浦北县其实有2种自称为“麻佬话”的方言,在叙述时产生偏差。《钦州市志》(2018年版)将白石水镇麻佬话作为浦北县麻佬话的代表②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钦州市志》(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01页。,但这种方言在浦北县其他方言人群日常语境中常被视为“山话”,而语言面貌更接近合浦县石康镇麻佬话的那种粤方言主要分布在浦北县泉水、安石、石埇、张黄等镇,《浦北县志》称之为“下路话”,并注明这是龙镇、小江镇以北居民对廉州话的称呼③浦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浦北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83页。。
《廉州镇志》称廉州话使用人口约120万人。学界对于使用廉州话的人口数量的介绍基本引自《廉州镇志》。因为廉州话不是少数民族语言,而国内对汉语方言的使用人口一般少有专门统计,所以准确的人口数量无由得知。不过,根据《合浦年鉴(2021)》的记载来看,2020年合浦县主要使用廉州话的9个乡镇(廉州、党江、沙岗、星岛湖、西场、乌家、石湾、石康、常乐)的总人口为656632人④合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合浦年鉴(2021)》,线装书局2021年,第38页。,即使这些地方的居民全部说廉州话,离120万尚有很大差距,何况他们不可能都说廉州话,而合浦县外说廉州话的人口相对较少,可见1995年《廉州镇志》的“120万”之说没有相关人口统计的数据支持,不太严谨。
三、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编纂方法建议
方言学家和地方史志工作者在共同编纂方言志时,一个最大的理念分歧是:方言学家关心方言的语言面貌,主张撰写方言志只要将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正确并完整地记录下来即可,至于方言的源流不是研究重点。而地方史志工作者关心方言源流的探讨。笔者认为,方言的源流记载应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能将未有定论的内容如“广府话演变说”“马留话说”等写入志书。以廉州话的源流为例,现存古籍最早提及廉州话的是乾隆《廉州府志》⑤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2),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9页。,第三轮修志时也只能写“廉州话来源尚不可考,现存史籍最早记载廉州话者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成书的《廉州府志》。由此观之,最晚至清乾隆年间,廉州话已经形成”,更早的历史则不可妄论。尽管这一时间节点太晚,与廉州话语言面貌呈现出来的历史层次不符,但在没有其他佐证材料的情况下,方言志的纂修宁可保守一些。同时,乾隆《廉州府志》记载一批当时廉州话的用词,是廉州话历史的见证。其中,大部分词现在还在使用,但个别今已不用的可谓珍贵语料,第三轮志书应重点提及,以此完整衔接旧志。另外,第三轮修志还可以提及国家推广普通话对方言面貌的影响:廉州话本无“我比你大”这类说法,而是表达为“我大过你”,随着普通话影响的逐渐深入,合浦县的年轻人也说“我比你大”了⑥蔡权:《廉州话的形容词谓语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由此可观方言源流。
第三轮修志通志其他方言的记载可参考廉州话,正文前力图从旧志或其他史籍中寻找关于该方言的记载,叙述内容要以语料为依据,最好是旧时“小学”研究成果,切忌攀附没有明确指向的所谓方言人群历史记载,以此简明扼要地提及方言的源头;正文主要记录较为稳定的老派方言的语言面貌;正文后附有近年该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变化内容的简单介绍,即新派方言的重要特征,由此凸显这一方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
方言志要用语言学国际音标记录这点毋庸置疑,但笔者对于具体记载方法有不同主张。《第二轮方言志编纂如何突出时代特征——基于对第二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编纂的思考》认为:方言志编纂不能编成纯粹的语料库,也不能编成语言教科书、语言研究学术专著①陈曼平:《第二轮方言志编纂如何突出时代特征——基于对第二轮〈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编纂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期。。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广西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内容的编纂基本与方言研究著作无异,作为专志或许可行,但作为通志常受限于篇幅,无法全方位展示方言的声韵调系统、音变、内部差异、字音对照表等内容,即将方言进行共时和历时比较,若随意删减,支离破碎,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从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角度来看,笔者赞赏《合浦县志》“廉州方言”的最终框架,具体做法可改良为:记录音系前要标记所调查的方言点,便于学界利用志书时有迹可查,但不必注明发音合作人。方言志相对于方言研究著作的另一个优势是出于众人之手,在讨论时能够确定所述为该方言的普遍语音特点,尽量排除个体差异造成的记录偏颇,实现记载准确,在同样的研究领域体现志书体例的价值。像《中古日母字在廉州话中的演变研究》对“肉”字声母的分析,就是将个人语音带入研究,其实在廉州话中不具有典型性②陈建隆:《中古日母字在廉州话中的演变研究》,《贺州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方言的命名要尽可能尊重母方言人群的自称,廉州话另有一个名称“麻佬话”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然而,县城居民往往误解“麻佬话”是客家人对廉州话的蔑称,说廉州话的人群没有人如此称呼自己的母方言。其实,到合浦县北部的石湾、石康、常乐等镇工作过的干部就会发现,“麻佬话”正是当地人对母方言的自称,谁会蔑称自己呢?志书若选取这些点作调查,必须尊重方言人群的自称,为免产生歧义,可加注解说明。同时,不建议就甲方言与乙方言是否为同一种方言等细节问题发表意见。就北海市的情况来说,廉州话、瓦话、海边话宜分开记述,各自记录其语音、词汇、语法,充分反映其语言面貌,以供学界进行下一步深入研究三者间的关系。
“语音”不单独叙述方言与中古音的对应规律,而是寓之于声韵调例字中。方言学界现在观点认为过去选择4个声韵调例字过少,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方音与中古音的对应,目前有的著述选择6个或8个声韵调例字。笔者认为,通志的方言记载大可不必为了排版整齐,选择声韵调例字时拘泥于4个、6个或8个,而应穷尽一切来源,有多少个来源就记多少个。假若某声、某韵或某调只有一个音韵地位来源,也无须为凑够数量重复选择,如实记录即可。另外,声母、韵母、声调数量的记录要尊重语言事实,切忌为了音系简明而随意调整。对于看似有音无字的情况,不要妄论本字,或随便以同音字代替,而应“开天窗”(□),并在其后用国际音标注明读音。“开天窗”同样是为贯彻落实“述而不论”的修志原则,《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在这方面提供一个范例。“词汇”不列词汇表,重点叙述古汉语的留存、廉州话与其他语言的接触现象以及廉州话与普通话的同形异义和异形同义问题。“语法”不能单纯罗列大段例句,而要辅以词性、句法的介绍。第三轮修志通志其他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记录也可以参考上述做法。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地方史志工作者不要因方言志编修的专业性太强而觉得除邀请专家参与外别无他法。方言志的编纂既需要专家,也需要“杂家”。汉语方言学本质是一种“经验科学”,只是现在有些学者过于追求“计量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等新方法而忽略扎扎实实开展广泛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地方史志工作者长期生活在本地,他们对于本地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丰富感性认识,绝非外地学者在短时间的调查中所能获得的。如李蔚《童心旧梦:北海民俗与家园往事》记录不少北海白话的词汇、俗语、谚语以及基于这一语境下的各类北海民俗①李蔚:《童心旧梦:北海民俗与家园往事》,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尽管作者并非专业出身,词语条目的罗列较为随意,一些用语的记录用字也不太准确,但对于方言研究来说,语料的尽可能丰富永远是第一位的,李蔚的著作可谓研究北海市粤方言的重要参考。
此外,地方史志者不应过于痴迷方言源流的探讨,而应在其他与汉语方言志相关的地情基础工作有所作为。以使用廉州话的人口为例,虽然缺乏专门统计,但北海市的地方志机构可以根据本地廉州话分布地区的人口数量,结合钦州市及防城港市地方志机构提供的数据,得到较为准确的数字。不过,考虑到个人在家庭中可能同时以多种汉语方言为母方言,方言使用人口的统计不可能也没必要精确到个位数。
至于廉州话的使用范围及其在各地的自称、他称问题,也可以通过地方志机构之间的调查合作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2020年,钦州市犀牛脚镇官方出品一个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视频,所配字幕把当地的廉州话称为“海寮话”,而不是“海獭话”,或者其他常见的误写名称(海擦话、海查话、海察话)。这个写法笔者第一次看见,是否有依据值得研究。而广东廉江、吴川、电白一带的“海话”和廉州话有何关系,福建是否有廉州话的分布等问题的解决②余毅忠:《合浦县新方志方言部分不可或缺的内容——语音、词汇和语法》,《珠乡史志》1988年第1期。,更是需要各地地方志机构间的这种合作。方言学界在对某地方言展开调查前,首先参考的就是志书中方言的分布范围及使用人口,地方志的介绍应该力图做到准确,地方史志工作者更是要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