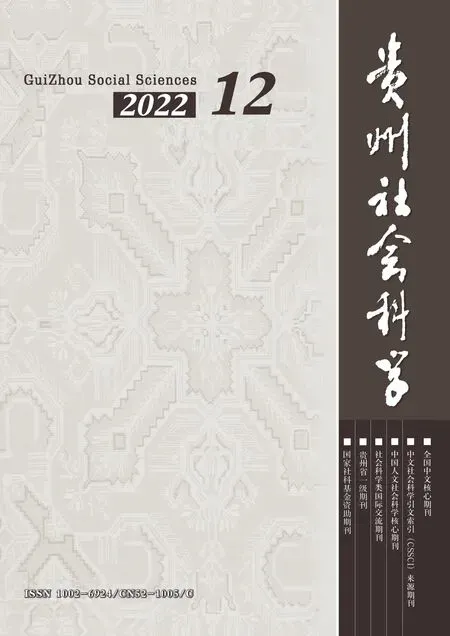斡旋与交涉
——客卿朝衡与8世纪中叶唐日关系的构建
张维薇 王 勇
(1.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2.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8)
8世纪中叶,伴随朝衡、①吉备真备等日本留学生的入唐及鉴真东渡的实现,7世纪后叶以来一度僵化的唐日关系得以逐渐重构,亦成就了唐日文化及人员交流历史上的顶峰时期。就目前中日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而言,遣唐使对于唐文化输入的意义无可厚非。②在唐日人员外交层面,聚焦于遣唐使人物群像的研究亦可谓层出不穷。③而事实上,在个案研究方面,尚可见可进一步挖掘的史实背景与相关文献,尤其在相关遣唐人员与同期唐日国交关系及东亚局势秩序等层面,尚有诸多问题有待继续探讨。
朝衡(阿倍仲麻吕)原以留学生身份随日本灵龟二年(717)第九次遣唐使④入唐,后“名成太学,官至客卿”。⑤侍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历任要职,终仕唐廷,是东亚古代历史上日籍人员在华从政的典型。“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⑥朝衡甚至可与东渡日本的鉴真齐名,誉“中日交涉史上之双壁”,是8世纪的东亚国际交流中关键乃至核心的人物。⑦朝衡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界的文献学实证考据。⑧但就目前而言,基于其相关诗文的研究则占据了主要比例。⑨相比国内学界以文本解析为主的研究思路,日本学界则侧重以诗文为线索考证并还原相关史实的细节。⑩然而,即便是“以诗证史”的视阙与方法论,依然存在着相对薄弱的层面与环节。事实上,除上述研究中涉及的点面以外,朝衡在同期唐日国交关系中的角色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留居长安五十余载、活跃于8世纪唐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学等多元领域的客卿,朝衡深度参与并实践了唐日国交层面的交涉与对话,见证了唐日关系的升温及文化外交、人员往来的顶峰。据此,拙文聚焦8世纪中叶唐日国交场域的相关活动,以天宝末年日本遣唐使所受殊遇、唐廷君臣外交诗赋中华夷观念的强化,朝衡的归国身份及使命等相关史实,窥析该人物在8世纪中叶唐日国交关系构建过程中的角色身份及唐王朝的对日立场与外交理念。
一、客卿朝衡的入唐及其在唐履职
朝衡于日本文武天皇二(698)年生于奈良近郊的贵族家庭,于日本灵龟二年(717)随遣唐使西渡入唐。同行的留学生中尚有吉备真备、大和长冈及沙门玄昉等人。赴唐留学的外籍学生至长安后,均入国子监。朝衡因其父阿倍船守在奈良朝的五品官位而别于其他同行的留学生,最终跻身太学。《旧唐书》东夷传曰:“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因其仰慕大唐文化而留居唐土,并取汉文名朝(晁)衡。朝衡卒业后经科考而留仕唐廷,入朝为官。王维诗言“名成太学、官至客卿”,描述的即是其登科后在唐为官的情形。《成寻所记入宋诸师传考》亦有载,“开元中有朝衡者。隶大学应举。仕至补阙。求归国。授捡挍秘书监放还”,可见朝衡科考入仕之途径。
至天宝末年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归国为止,朝衡历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左拾遺、左补阙、仪王友、秘书少监、卫尉少卿、秘书监、卫尉卿等职。而自安南漂流返唐后又再度仕唐,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节度使、光禄大夫等职。《新唐书》东夷传言“多所该职,久乃还”,日本朝廷评价其“显位斯升,英声已播”,是其在唐留学与官宦生涯的缩影。身为留学生和唐王朝客卿的朝衡,实际扮演了日本驻唐公使的角色,并为同期西渡入唐的使节和留学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便利与优遇。包佶诗言“九译藩君使”,亦可见其多次在唐日外交场合发挥沟通作用的事实。朝衡在8世纪中叶唐日国交场域的参与与斡旋,不仅彰显了文化移植期日本遣唐人员国际政治嗅觉的敏悟,在唐参政、议政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亦促进了主臣关系前提下唐日亲善国交关系的构建。
二、朝衡与8世纪中叶日本遣唐使在唐殊遇
8世纪中上叶,正值日本大量攫取唐文化的顶峰,亦成就了历史上唐日亲善关系的构建。朝衡经科考登第而入仕唐廷,历任校书、补阙、仪王友等职,于天宝末年擢任三品秘书监。杉本直治郎曾指出:“朝衡在唐五十余年之间,我国人至唐国者,大都受惠其斡旋之劳。”凭借在唐王朝的身份与地位,朝衡在同期唐日国交场域内进行充分交涉与斡旋,见证并亲历了唐王朝对日本遣唐使的优遇及对日本国际地位的认可,有效推进了同期日本东亚地位攀升与唐日亲善关系的升温。
天宝十一年(752)秋,由藤原清河所率第十二次遣唐使一行抵唐。《大日本史》记载:“胜宝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麻吕接之。”负责此次使团接待的,正是时任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的朝衡。同期日本奈良朝积极的对唐政策,从遣唐使国交活动中积极活跃的行为态度中不难得知。而得益于客卿朝衡的斡旋和举荐,此次日本遣唐使的访问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遣唐使在朝贺仪式等重要国交场合的座次问题。《日本国志》邻交志记载:“春正月,朔唐皇帝受诸蕃使朝贺于含元殿,敘新罗使东班在大食上清河等西班在吐蕃下,仲麻吕以为不宜班之后于新罗也,为之,请将军吴怀宝乃引清河与新罗使易位。”唐朝时期的东亚国际社会,各国遣唐使在拜朝仪式上的座次实为国际地位的体现。而事实证明,日本使节的座次高于新罗而位居东班之首,不仅得益于8世纪初以来开启文化外交、通过大量攫取唐文化之后自身国力的提高,尚有客卿朝衡从中斡旋这一重要因素。如此,不仅使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唐王朝的认可,亦意味着同期日本国际地位的攀升乃至东亚格局的局部调整。可以说,在8世纪日本对唐国交的构建及新东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客卿朝衡既是见证者,亦是实际的推动者。
天宝末年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国事访问期间,唐玄宗尚命朝衡引领其参观唐宫内府等秘所要地,其所受优待与厚遇亦可见一斑。《日本高僧传要文钞》记载:“又勅命朝衡领日本使于府库一切处。遍宥。至御披三教殿处。”可以说,对府库、三教殿等的见习,深化了日本使节对唐宫内府构造及大唐文化内涵的理解。客卿朝衡引领日本使节瞻观内府,不仅是唐朝对日本外交体制上的礼遇,亦是对宗主国国威及唐文化内涵的彰显。与此同时,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古麻吕、吉备真备等均受官职册封。《日本高僧传要文钞》记载:“大使藤原清河拜特进。副使大伴宿祢胡万拜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副使吉备朝臣真备拜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及卫尉卿。朝衡等致设也。”此次遣唐使被授予官爵者的人数及官品,在同期唐王朝对外藩使节的册封事例中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其所受诸官爵的册封乃“朝衡等致设”的事实,亦一再印证了朝衡对日本遣唐人员的积极举荐,及其在同期国交事务中的有效交涉与斡旋。
安积淡泊在《阿倍仲麻吕等传赞》中提及:“凡我使臣在彼者,例授官爵以之宠勚,其仲麻吕有间。”杉本直治郎亦指出,日使在唐期间受到如此破格恩典,无不是受朝衡的眷顾,进而向唐皇斡旋奏请的结果。森克己则认为,朝衡为后批次遣唐使的在唐事务极力斡旋,对日本文化之进步有间接之益。天宝末年日本遣唐使所受殊遇,折射出客卿朝衡在8世纪中叶唐日国交对话中的重要身份与角色。这不仅是唐朝对文化输入期的日本扶植、优遇政策的体现,亦预示了同期唐日国交亲善的深化,日本国际地位的攀升乃至东亚格局的调整。
三、诗赋外交与8世纪中叶唐朝的对日观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第十一次遣唐使来华之际,学成的朝衡按规应随其归国。但因其时任补阙之职,未能奏得唐廷许可,仅能待次批遣唐使的入唐。因而,天宝十一年(752)入唐的第十二次遣唐使在肩负聘请鉴真渡日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同时,实际亦肩负了召回客卿朝衡的重任。故此次遣唐使入唐之际,朝衡以故土“尚有亲老”为由而奏请归国,终得唐玄宗的许可而辞唐东归。
唐天宝十二年(753)秋第十二次遣唐使归国之际,唐廷特行盛大的送别宴。唐玄宗赋诗《送日本使》:“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吏部郎中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言:“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別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包佶诗《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言:“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九译蕃君使,千年圣主臣。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早识来朝岁,涂山玉帛均。”可以说,大唐君臣与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的此次诗赋外交,体现了8世纪东亚国交场域中最高规格的礼遇。
站在国交立场上的诗赋,透露了同期唐王朝的对日态度与政策,亦传达了对臣国日本的期许。“天中”这一称谓,是植根于唐统治者意识形态内的华夷观的流露。而王维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文中所见“帝乡”的自称,亦可谓异曲同工,均是对“天下中心”观的宣示与强化。而包佶诗中“上才”与“下国”的表述,则体现了唐朝对日观念范畴内对双方地位悬殊的认知,明示了唐日睦邻友好以华夷秩序及主臣关系为前提的基本理念。归根结底,唐统治者对于唐日关系的认知,始终以华夷秩序观为理论前提。而对于基于国际秩序的地位悬殊,日本亦持认同态度。另外,王维诗文中“异域”及诗序中“绝域”、“异姓之国”等称谓,亦可见唐朝统治者在基于“天下中心”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疆邻蕃地域歧视观的流露。
唐玄宗《送日本使》中言“王化远昭昭”,实际富含深刻的政治语义,既是唐王朝作为“华夏中心”的彰显与夸耀,亦是对朝衡等归国人员“播风弘道”、谕化邻蕃的期许,与王维“恢我王度,谕彼蕃臣”的表述呼应。而将对日观隐含于遣唐使归国的赠诗中,亦足见唐廷君臣的外交智慧及其在对外关系细节层面的应对。唐廷的诗赋外交,既是对朝衡等遣唐使在华夏文化传承、唐日国交构建过程中角色的肯定,亦有效传达了远播帝国威望、维护东亚秩序等层面的期望,在强化华夷观的同时,亦体现了儒家忠孝思想与伦理观念的灌输。
对于大唐君臣的诗赋赠别,朝衡曾以诗《衔命还国作》作为回赠。“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今枝二郎曾指出:“此诗吟咏了对大唐的恩德感怀,及其对故国的忠义。”而将唐土称为“国”,亦是身为两国臣子的双重身份,及其作为客卿在唐朝社会深度融入的体现。“侍臣”“明主”透露了朝衡思想意识中对儒家君臣观念的接纳,而“怀恩”“感义”则是忠孝伦理的体现。“天中恋明主”与《送日本使》中的“天中佳会朝”呼应,既迎合了唐朝统治者强化“华夏中心”地位的意愿,亦体现了对华夷秩序的认同与遵从。其朴实的叙述与情感流露足见其知恩与忠义及遣唐人员身上所普遍存在的慕华情结。可以说,8世纪中叶唐日亲善关系的升温是以华夷秩序为前提,并以唐朝的“维护”与日本的“认同”这一双方共识为基本运行模式。而在此过程中,客卿朝衡既是亲历者,亦是实践者。
四、朝衡的“赴日唐使”身份与唐日国交的构建
天宝十二年(753)秋,朝衡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归国。由《衔命还国作》的诗题可知,朝衡此次归国肩负了重大使命。《衔命还国作》一诗,亦作《衔命使本国》。朝衡在归国之际确奉唐玄宗之命,充当了赴日使者的角色。朝衡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日本的史实,历来被学界所公认。郭祝松曾明确指出,朝衡归国肩负了唐王朝赋予的使命。靳成诚亦曾指出其“以唐使身份赴日”的观点。直至唐天宝十二年(753)为止,朝衡在唐留学、任职近四十载,在其归国之际亦兼具唐朝赴日使臣、归国留学生、辞唐日籍官员等多元身份,肩负国事访问、敬问日皇、传达唐王朝对日政策立场的重任。
如前所述,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入唐,原本即肩负了召回客卿朝衡的重任。而时任三品秘书监的朝衡,其归国事宜亦须经唐朝官方的认可。因而,朝衡此次归国实际肩负唐玄宗“回聘”日本天皇的任务。而值得注意的是,朝衡于天宝十一年(752)擢四品上秘书少监兼卫尉卿,而在次年旋即擢任从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从唐朝官员的任职及升迁途径来看,即便是在当时的本土官员中亦不多见。朝衡擢任从三品官衔的天宝十二年(753),恰逢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国事访问期间,而此时的朝衡亦计划随其归国。一般认为,唐王朝将时任秘书少监的朝衡擢为从三品秘书监,是对其多年仕唐功绩的犒赏。与此同时,其擢升亦被认为与其归国时的“使者”身份有关。事实证明,唐朝官制中的赴外蕃使节由在任官员临时充任的情况居多。而由《唐会要》中所载若干官员的任职事例亦可知,充任外蕃押使或节度使的官员亦大凡具有三品以上的官品。故第十二次遣唐使团抵唐之际,唐朝旋即擢升朝衡为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应是册封其为赴日唐使的现实需要。
日本江户时期的儒者林罗山第四子林春德在《罗山先生文集》中载说:“《王维送朝衡序》云捧天皇敬问之诏,然则仲麻吕之出大唐也,齐来玄宗之勅简者必矣,非使本国之谓乎。”林春德认为,朝衡既是代表唐朝的名义出使日本,则不可称之为出使本国。可见,在日本近世儒者的观念中,存在将朝衡视为“唐籍”的认知倾向。亦有学者明确指出,身为客卿的朝衡,此次是代表自己所任职的异国出使自己的母国。笔者认为,朝衡此行的实质并非“出使”,而是“辞唐归国”。而“赴日使臣”的身份,是唐王朝在其归国之际为之所附的头衔。
而对于天宝十二年(753)朝衡辞唐归国时的身份,笔者亦曾指出,《衔命还国作》中所谓“衔命”,即是作为唐朝使者送还日本使归国。今枝二郎亦认为,既是衔命,朝衡即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归国,而是作为唐朝官员被赋予了“送客使”的任务和使命。通观整个遣唐使时代,出于不同的目的与初衷,唐日双方曾互派若干次送客使与迎客使。在送客使、迎客使为东亚国交礼仪的遣唐使时期,朝衡以送客使的名义陪护第十二次遣唐使团东归,不仅践行了他在唐日国交场域中的角色与身份,亦加固了唐日之间倾力共筑的亲善互信。
五、“怀敬问之诏”:国书携归的使命与唐日关系
天宝十二年(753)归国之际,朝衡辞别唐廷君臣,吟诵惜别祖州之诗。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文中“箧命赐之衣,怀敬问之诏”这一表述。可知朝衡在归国之际曾携唐玄宗所赐衣物,怀揣唐王朝至日本天皇的诏书,同时兼具了归国留学生、辞唐客卿、唐朝赴日使臣等多重身份。
在目前可考文献的范围内,并未见朝衡携归国书内容的相关记载。但据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的所载信息,天宝末年归国之际朝衡曾携带唐朝至日国书的事实实难否认。正如林春德所言:“齐来玄宗之勅简者必矣”。森公章以“敬问之诏”的表述剖析国书的性质,联系同期唐王朝对日观念、两国关系与地位的悬殊等层面,将该文书归为“皇帝敬问”类,并指出:“此类慰劳制书=‘皇帝(敬)问某’形式的诏书,对方地位应是优于论事敕书=‘敕某’形式诏书的对象,而又不同于对等关系国家之间的文书,但同属于唐朝皇帝下诏臣国的文书”。另一方面,唐王朝册封朝衡为赴日使臣即“赐衣”“赐印”的仪式很可能就是在前文所述的遣唐使送别宴上举行的。因而,唐玄宗《送日本使》所言“天中佳会朝”,除对第十二次遣唐使的赠别之外尚另有目的,即是对朝衡为赴日唐使的册封仪式。王维赠朝衡诗序言“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可见唐廷对其视如己出的态度,同时亦隐含了朝衡同为两国臣子的特殊身份。而这一身份亦与其携归国书、呈奏日皇的国交任务相协调。另外,亦可窥测在此册封仪式上,除前述“命赐之衣”以外,唐玄宗还另赐其“御印”等信物的史实。从朝衡怀揣的“敬问之诏”,足见唐王朝对日本主臣关系的宣示、华夷秩序观的强化及亲善关系的维系。
天宝十二年(753)秋,朝衡随第十二次遣唐使由苏州黄泗浦出港归国。此次东归,鉴真亦随之东渡。然而,他们所乘船只在阿尔奈波岛附近遭遇海难,后漂泊至安南都护府驩州境内。登岸后遭遇土著袭击,全船成员仅存命四人。朝衡归国之愿未遂,与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一行结伴返唐,并于天宝十三年(754)夏秋之际经由陆路回至长安。故可推测,朝衡所携国书抑或在安南滞留或辗转返唐的过程中遗损。即便对其倍加保护,亦因返唐后再度仕唐而未能将其及时携归。森公章亦认为,此“慰劳制书”或因藤原清河、朝衡的海难漂流而未被携至日本的可能性较高。但即便如此,朝衡在8世纪中叶唐日国交中的角色身份亦同样不能否认。
《新唐书》东夷传载:“天宝十二年,朝衡复入朝。”朝衡与藤原清河返唐后,二人均再次供职于唐廷。上元年间(760—761),朝衡被唐肃宗委任安南都护,赴安南都护府所在地宋平治政,并于永泰二年(766)以安南节度使身份平定因南邵势力东进所致的安南北境的蛮夷叛乱,对安史之乱后唐南部边藩的军政治理、疆域维安乃至东亚局势的平衡等层面,均具备特殊的历史意义。朝衡于唐大历二年(767)七月之前回至长安,归京后擢光禄大夫、北海郡开国公,并于大历五年(770)正月薧于长安,追赠正二品潞洲大都督。朝衡终仕唐廷,埋骨长安,虽未实现唐朝君臣所期冀的“传道经于绝域之人”,“致分器于异姓之国”,却可谓在实质上实践了日本驻唐使节的历史角色。
六、余 论
客卿朝衡在天宝末年唐日国交场域中的斡旋与交涉,诠释了8世纪中叶日本在唐人员外交活动的内涵。不仅是日籍人员在唐政务的参与,亦是对同期唐日关系、东亚形势深度洞察的体现。朝衡对第十二次日本遣唐使国事访问期间的引领举荐、在唐廷君臣“诗赋外交”的中的应对,及其归国之际的“唐使”身份和携归国书的史实,足见其在同期唐王朝对日外交中的关键性。得益于以朝衡等遣唐使关键人物的斡旋交涉,自7世纪后叶以来近乎僵化的唐日关系得以逐步升温,并重构起以“文化外交”为模式,以“亲善”为特征表象的新型国交关系。而局限于古代东亚秩序的唐日亲善,仍以唐王朝统治者长期致力维护的华夷观及主臣关系的存续为基本前提。
而事实上,得益于朝衡等极具涉外能力与政治嗅觉的遣唐使的斡旋交涉,唐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员外交亦因此而繁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朝衡、藤原清河等遣唐人员虽未如吉备真备等归国留学生那样最终成为唐文化的实际传播者,但就古代东亚文化交涉的角度而言,却成就了唐文化对外输出的“多元形式”,体现了日本在文化输入期力图与唐朝构筑友好关系的积极意愿,以及唐朝在维系与宣示华夷秩序的前提下对邻藩日本给予的帮扶与期许,可见文化“传播”与“渴求”的双向需求在国际政治与区域关系场域中的折射。
注 释:
①倍仲麻吕,留居唐土后更汉文名为朝衡,亦作晁衡。日本文献中多称阿倍仲麻吕,亦作安倍(朝臣)麻吕、安倍仲麿等,中国及越南文献中多称朝衡。
②参见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55年;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65年;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东野治之《遣唐使船》,朝日新闻社,1999年等相关著书。
③参见高木博《万叶的遣唐使船—遣唐使及其混血儿》,教育出版中心,1984年;王勇《唐眼中的遣唐使——混血儿的大唐帝国》,讲谈社,1995年。
④因计算方法不同,遣唐使的次数问题存在多种说法。本文据王勇、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大系》(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观点,将日本灵龟二年(717)的遣唐使视为第九次遣唐使。
⑥郭沫若,祝中日恢复邦交,《郭沫若选集》(卷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6页。
⑦张白影,阿倍仲麻吕研究,《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52—56页。
⑧代表研究有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育芳社,1940年;森下金二郎,阿倍仲麻吕(朝衡)事迹的校勘——试补遗、补注,《宫城学院女子大学研究论文集》1985年。
⑨代表研究有远田晤良,青海原—土佐日记阿倍仲麻吕歌,《比较文化论丛》,2006年;北住敏夫,阿倍仲麻吕天之原歌私考,《文学-语学》,1980年;黑川洋一,关于阿倍仲麻吕的诗,《文学》1975年第8期;陈子彬,中国唐代客卿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评介,《承德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郭祝崧,评《望乡诗》——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日本研究》1997年第1期。
⑩参见藏中进,鉴真渡海前后——阿倍仲麻吕在唐诗二首之周边,《神户外大论丛》1975年第3期;东城敏毅,阿倍仲麻吕在唐歌——作歌与传达,《日本文学论究》(54)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