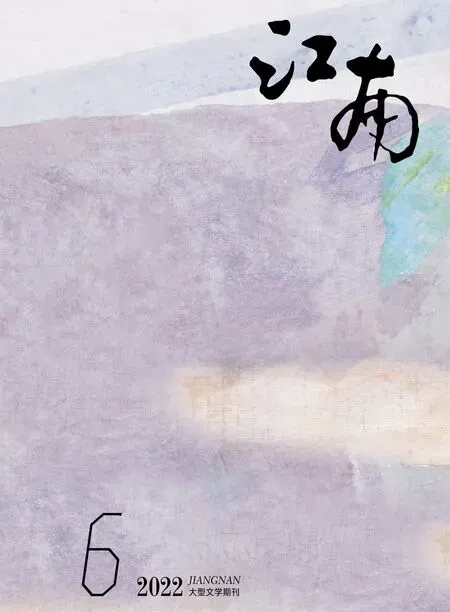瀑 布
□ 娜仁高娃
一
她,是银白水雾似的蜃楼。或者说,在干燥的地平线上徐徐飘浮的三片羽翼是她。我的望远镜对准着她,仿佛在静候热浪慢慢融化、吞噬她的结局。她穿着长裙,米白色的,大太阳下一闪一闪的。她沿着西热河北岸走,步履极慢,时不时弯腰捡拾什么,不厌其烦地踅来踅去。我跨坐在老榆树活着的粗枝上,用一端叉着铁片的削子削去死掉的树杈。这活儿很简单,没浪费我半个时辰。我有大把时间在树影的荫蔽下,远远地“跟踪”她。过了好久,她才走到我这边。
“巴格巴,这些是花鹊的旧巢,对吗?”她问。树下堆着喜鹊旧窝残骸,是我刚刚丢下去的。
“嗯。”
“这树已经死了一半,活着的一半也会死掉。”
我没有反驳。在戈壁野地,树的死亡一直在延续。与那些晒白的动物尸骨一样,用死亡的残留物来充填生命的摇篮。
“很多地方一个院子能繁衍成一座小村,这里不会那样,对吧?”
她向东看看,又向西看看说。她没有戴帽子,头发用花色头巾裹着堆到颅顶上,在我眼里,那模样赛似牛粪包。
“你直接叫我羊脸巴格巴,我习惯人们那么称呼我。”
“知道。”
她礼貌性地笑笑,眼睛却看着我胸前的望远镜。我轮番地抓着枝干滑下树,扛起一截断枝,转身走去。我的动作极快。我担心望远镜透露我先前的“心潮翻涌”。是的,心潮翻涌,一个中年男人沉寂多年的、游丝一般的心弦。我要降伏它突然的暗自轰鸣。
“巴格巴,你像一个远离喧嚣的隐居者。”
“呃——,我没有隐居。”
“感觉上是。”
斜斜的缓坡,一脚踩高,一脚踩低,人便来回摆动。两条影子,在眼皮下摇摆。有那么几次,两条影子叠到一起。那是爬坡时她踩到我的足印。
“巴格巴,你怎么一直不问我为什么又回来了?”她问道。
“你不是来捡石头的。”
我答非所问地回答。
“你有过女人吗?”
等两人走到屋西侧的柴垛旁后,她问道。
我没有应声,对着她的眼睛看。她避过脸,看看小山似的柴垛,又看看向东延伸至天边的秃山。眼神幽幽怨怨的,仿佛我把山上的树都扛回来了。三天前的偏午,她的眼神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们头一回照面。当时,我正在驼桩上抓驼毛。一峰脾性暴躁的母驼,我每抓一下,它便冲我吐口唾沫。不过我耐着性子,没有用鞭子抽它,也没有用绳子箍紧它的嘴。我也没发现有人靠近。当身后传来“您好!哦,糟糕,它唾了你一脸”时我扭头去看,便看见一个瘦长的女人,在晃眼的阳光下,一脸的惊讶与满眼的温和。
“您好,我们是来问路的,请问西热河是在这附近吗?”
“嗯。”
“嗨,老乡,西热河具体位置在哪儿?”
沙哑的嗓门。女人身后,一个方脸男人从车窗探出脑袋。
“就在那,你们刚走过。”
“哦,原来——,那就是西热河呀。”女人把语调拖长,脑袋从左到右地慢慢滑着,将视线内的干涸河床瞅个到底。我没再理会。从母驼后腰抓下一坨毛,母驼噗的一下,嘶嘶拉拉的唾液在空中飘飞。抓完了,回头看,两人已不见。临近傍晚,东边山下,一个黑点,悠悠地挨近。我认出是中午的车。车到水井旁停止。一会儿,女人径直走来。
“您好!晚上我俩在那边搭帐篷露宿,您若有空过来坐坐吧,聊聊天。我们有烤肉,还有酒。”
我没有拒绝。准确地讲,我想不出拒绝的理由。
“繁星、苍穹、宇宙,还有篝火、烤肉、红酒——,多么浪漫的荒野夏夜,是不是,亲爱的?”
男人一边在火堆上烤肉,一边脑袋朝天仰着说。
“等天完全黑了,你可以拍星轨。”女人说。眼睛向我瞟一眼,仿佛在说,请您不要嘲笑我们的一惊一乍。
“我们生来不是为了谴责彼此,而是为了深爱彼此。哦,愚蠢的人类,没有一颗星星会为你滑落。”
女人抿嘴一笑,对着我说:“他是我爱人,呃——,是个摄影师。”
“嗯。”
“我们还有黄酒和白酒,要不给您换一杯吧。”女人说。
我摇摇头,并举起杯表示感谢。我们用瓷杯喝酒。酒的味道真不错,只是有点甜。
“越来越多了,今晚它们都是我们的。”女人提高嗓门,有些突兀地说。
“只有其中一颗是你的。”男人说着,伸着胳膊递给我一串鸡翅,抹了酱的。
“老乡,味道还不错吧?”
“嗯。”
男人递给女人一串鸡翅,女人没有接,说了句谢谢,慢慢地呷着酒,向远处凝视。一会儿自言自语似的:“在这里,每一朵花都该有自己的名字。”
“这鬼地方哪有什么花。”男人呸地吐掉什么,转而递我一串说:“老乡,这是牛筋,车载冰箱里放了几天,不过不会走味的。在荒野烤肉,是我多年的梦想。呃,对了,老乡,怎么称呼您?”
“我叫羊脸巴格巴,巴格巴是我的名字,羊脸是老驼夫给我取的绰号。打小人们都这么叫我。”
“老驼夫一定很幽默。”
女人拦截男人话语似的轻咳一声,眼睛却依旧凝视着邈远。
天际,一脉高凸的黑屏障,那是阿拉格山。一声声老人呼唤什么似的声音从那里传来。
“听听——,什么在叫?”女人说。
“甭管是什么,你就全当幽灵在唱歌。”
“猫头鹰。”我说。
“在山那边——?”女人看着我问。
“嗯,夜里听起来会很近。”
“来,老乡,走一个。”男人举着杯,不过不等我举杯便大口喝下去半杯酒。男人有一头鬈发,比山上的褐色石头暗一些,应该是染过的。当他敞开嗓门大声说话时,发卷会抖动。他还时不时将手指插进去向后捋一捋。
月亮没出来。星辰炸开似的布满天空。我向我的屋子走去。酒没有上头,口腔里蓄着淡淡的甜味唾液。我没有与他俩道别,也没有邀请二人到家里做客。当三人简单摆手道别时,我仿佛成了他们的客人。四野悄寂。秃山呈暗紫色,河床变为淡红色。沙碛地浅白色被夏夜柔风抽走了颜色,浑然成蓝幽幽的一片。哧哧楚楚的,我踩出一路的干巴声响。小屋窗棂方方的,黑黑的,几只夜鸟扑突突地飞去。进了屋,我没有开灯。我站到窗户前,看着不远的透明的红和黄。那是他俩在各自的帐篷内挂了灯。
翌日,大太阳下一切照旧。井边,多了一拢烧透的灰堆,以及一对弧线似的车辙。车辙向着褐色阿拉格山、向着无云的碧空延伸。等到傍晚,山影依旧,夕阳依旧,温热的风依旧。我也依旧,只是手背多了半截火柴大的划伤。我坐在母亲留下的马扎上歇息。我很疲乏,白天我没有停止一刻的劳作。我本想早早爬上小床,可是我的眼睛却浮云似的瞟向水井那边。没一会儿,暮霭深沉,水井台不见了,我的眼睛依旧向那里飘浮。
第三天,与前几日一样,骄阳炙烤,热浪翻滚。我确定我已经忘记女人——,呃,还有她的丈夫。然而,等到夕阳下去,山影沉入大地后,我却鬼使神差地坐到马扎上凝望井口那边。其实,我没有回忆什么。我只是在凝望,单纯地凝望。脑海里一片空白。猫头鹰在叫,骆驼也在叫。野风从山坡滑下来,一阵沙沙声响。等到第四天晌午,也就是昨天,我在给驼羔灌祛暑药时女人却突然站在我跟前。驼羔扑腾,药液洒我一身。
“嚯咦,巴格巴,忙着呢?”
驼羔眼球上一条白柱,那是她。被我捕捉的身影。她的眼睛藏在墨镜后面,视觉上整张脸都藏在那后面。我随手拎起铜壶,咕咚咕咚几下,胸膛里一阵嚯嚯响。我的手浸过药液,毛糙糙的手长了绿苔似的。我把手蹭到衣服上。黑红的手背露出来。我粗粗地舒口气。面颊上辣辣的,我觉得那是汗粒正暗自狂欢地沁出毛孔,还有心脏,猛烈地撞击胸腔,仿佛也长出了脚。
“你不会是这么快就想不起我是谁了吧?”
我再次粗粗地舒口气,龇起牙。
“我和我爱人在山里迷路了,夜间我俩在山脚露宿。”
“哦。”
“我们没能找到——,嗯,我想,我们还是过来问问您比较好。他呢——,在那边拍图片,一会儿过来。”
“噢。”
“我嘛,随处走走,看见您在这边,我就过来了。”
“嗯——。”
“不会打扰到您吧?”
我摇摇头。
“呃,要不您先忙吧,我到河那边走走。”
“哦。”
等她走向河那边,我竟然逃离什么似的,匆匆灌完最后几勺药,扛起铁锹走向野地。同时我也在一种“揪耳朵吃肉”的自欺中带上望远镜。我想,这一切源自我在暮色下凝望水井那边时,我的“眼睛”遭受焦躁不安的折磨后,擅自向我的大脑发号施令:我要看到她。
二
我的屋子很小,只有里外两间。我的床也很小,只容我一个人翻腾。妹妹接走母亲前,母亲睡床,我睡外间靠窗的床。母亲走后我在里间睡。靠窗的床我用来堆放衣物。我不想把衣物堆到单人沙发上,因为吃饭时我坐沙发。
从野地回来进屋后,我邀请她坐到沙发上。不过她并没有马上坐上去。她站在屋中央,两条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仿佛放开了就会触到墙壁。她说,屋里好凉快。我说,一直都这样。屋顶,有一窝黄嘴燕崽。她仰着脸,满脸忘神地看着那窝雏鸟。她的裙摆上印着黄色花纹。花纹如蝴蝶羽翼——这是我的联想。我走到外面,阳光晃眼。一只走出幽暗洞穴站到山岗上的猛兽,会不会也觉得阳光比往常晃眼?这也是我的联想。干旱夏季大太阳下袒胸露背的野地,围拢着我。它们冬夜似的宁静,也围拢着我。真该有一场黄风,铺天盖地涌来,打破这死静。
“这里好安静。”
她站到我一旁。
顺着河床地,一辆车左拧右拐地驶近,并且很快到了门口。男人的鬈发、男人的方下巴、男人有些抽搐的面颊——都探出来了。她迎了过去,说:“哦,你终于回来了。”
“那边风景真不赖,我拍到刺猬了。”
男人大声说着,眼睛却盯着我。我向驼群走去。两人说着什么,我没听清。或者说,我根本就没听。半个时辰后,我逐一放开埋到地上的驼桩绳索。驼羔和母驼混为一体,发出嘈杂的动物声响。一会儿,整个驼群向西离去。他俩追着拍照。等驼群进了大片的灌木丛,两人折了回来。这空当,我换了外套,洗净了脸和手臂。
我备了晚餐,一锅风干牛肉,一叠醋泡沙葱,还有一瓶高度白酒。夕阳温和,河对岸秃山缓坡染了一层金黄。
“老乡,明天就劳驾您了。”男人举起杯,用一双毫无笑意的眼神看着我说。
“明天有雨。”我说。
“会下雨吗?”她问。
“只能是明天了,后天我们还有事。”男人将杯里的酒一仰而尽。男人的鬈发整体向后倒去,我想,那是男人驾车时一直在大开车窗。
“不碍事。”我说。
夜里,屋前两个蘑菇似的帐包。男人的呼噜声,夜鸟的鸣啭,山野的低吟,都飘过敞开的窗户传来。我在我的小床上,侧身躺着。对面墙壁,嵌入墙壁的母亲用来供绿度母的壁龛蒙着薄纱。我看着那里。感觉绿度母微闭的眼睑满是笑意。一阵扑突突,烟囱飞进来一只鸟。嗖嗖地飞,飞出凉飕飕的风。月亮上来了,窗外一片银白。闷燥燥的。躺柜上有笛子,我想吹吹笛子。我还想到外面走走,去看看秃山被月色渲染的样子。树木变黑后的样子。栅栏延伸至天边的样子。河床盐碱地泛白的样子。灰兔啃食草茎的样子。黄狐狸到井边汲水的样子。羊蛇扯着布满花斑身子逃去的样子。刺猬扑在母羊胯下吮吸羊奶的样子。跳鼠一弓一弓地飞奔过沙碛地的样子。还有草地黑鼠爬仓房窗台的诡谲样。它的尾巴上有鳞片,月下会散发出磷火一样的光。听说它也偷酒喝。嗯,对,应该整一杯。我下了地,赤着腿,赤着臂。嘎吱,里间的门被我拉开。我忘了它会响。我站住。我的肌肉瞬间绷紧。我瞅见我的胸脯高凸,哦,这就是我的生活赏赐我的奖励。酒在沙发一侧的壁橱内。又一声嘎吱,这次是壁橱的门。呼噜声戛然而止。一会儿继续响起。拎着酒瓶,空出一条胳膊,抬起门板,我想这回它不会嘎吱一声了。不过,它还是轻微地嘎吱一声。呼噜声依旧。
大大地下一口,陈酒,太辣。
又一口,辣味淡去。齿缝里酸涩涩的。
黛色山岗,浓雾氤氲。山脚有河,棕色水流,湍急。她扑在裸岩上。湿漉漉的好几条胳膊,那都是她的。一条一条地伸缩,犹如蜘蛛的腿。她在吃力地往上爬。风很大,她的裙摆抖动,要被掀去了。她张大嘴,像是在呼喊。一个男人,有张黑黑的脸,树一样站着,看她。
我醒了。发现梦里跑到山上见了她。外面正在下雨。天色已亮,雨脚密密麻麻地攀爬着窗户玻璃。从开着的窗户潲进来的雨水,在地上洇出一小片黑影。河床那边一片朦胧。对面的山坡隐在雨中。檐口扯下亮亮的水绳。这是一场没有雷声的暴雨。头涨得痛,胸腔里油腻腻的。我走了出去。屋前,有了血管似的交叉的水流。她在车里。男人披着雨衣,骂骂咧咧地抖落帐篷。水珠儿四溅。男人浅色牛仔裤半截湿透了,鞋子也是。头发耷拉下来,显得方脸更方了。
我去抖落另一个,抖净了拖进屋里。
“该死的雨。”男人嘟哝道。他面颊上红彤彤的,那是一半生气,一半宿酒未醒。
一次漫长的早茶。雨脚噗噗突突地踩着屋顶。屋内屋外此起彼伏的沙沙响。她抬头看看椽木上的雏鸟。男人也跟着看。她坐在沙发上,双腿拢回身下,裹着薄毯。头发垂下来,一头马鬃似的长发。
“雨停了,咱就出发。”男人说。
“嗯。”我应道。
我坐在马扎上。马扎很旧了,得用小腿撑着。男人坐在床沿,背对着窗户,黑乎乎的,乍看像一尊铜塑,那种在喇嘛庙里常有的。
“巴格巴,那是你吗?”
她看着壁上的旧照片问道。
“嗯,中间的是我母亲,个头小的是我妹妹。”
“八十年代的老照片了。”男人说。
“嗯。”我顿了顿,觉着男人匆匆瞥我一眼的眼神充满了冷峻的光芒。于是我接着说:“照的时候我的鼻腔里塞了羊粪蛋,那会儿我经常流鼻涕——,塞进了就掏不出来了。”
“鼻涕怎么可能堵住。”男人干巴巴地说着脱掉了鞋子,米色袜子脏兮兮的。
“后来我母亲用细棍抠出来的,羊粪蛋都烂掉了。”
她笑了,笑声很轻微,一手摁着额头,一手端着茶碗,明显是极力忍着大笑。
“我妹妹用羊粪蛋串起项链戴在脖子上,我用驼粪蛋串起佛珠念经,照片上能看到。”我说。
“哦哦,是吗?我还以为脖子上的是珊瑚之类的。”她说。
男人拎起鞋子啪啪地撞击,声音听起来很刺耳。屋里顿时陷入一种令人难堪的宁静。一会儿,三个人同时向窗外望去。
“抓过毛的骆驼会不会怕雨?”她突然说。
我摇摇头。她听了,把身子后倾,靠着高出肩头的沙发。那里黑亮亮的,那是我的汗液留下的污垢。
“怎么可能,骆驼那么大,甭说一场暴雨,就是三九天的白毛风都奈何不了它们。”
又是一阵突然而至的沉默。三人轮番看着窗外,仿佛都在暗自祈祷雨能快速停止。燕子嚯嚯地飞,雏鸟啾啾叫。一种潮乎乎的死寂慢慢地灌得叫人很不舒服。
“老乡,你们是不是每年都会祭拜那尊石人,呃,那个名叫‘阿布石’的——?”男人问道。
“嗯,每年都会。”
“你也是?”
“嗯。”
“巴格巴,祭拜石人算是一种年代长远的乡俗,是吧?”她问。
“嗯。”
“其实吧,草原深处的墓地石人多数是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有的更久远,石器时代的。”男人扭头看了看老婆——她,继续说:“考古的研究过新疆阿勒泰那边的,还有蒙古高原那边的,有的三五个在一起,猜测是古代某个王者或者首领的墓碑。”
“不全是墓碑。”她说。
“书上是那么讲的。”
“我跟你讲过,有的就不是。”她的语调些许地提高。
男人听了,沉默着,一双冷峻的眼神从她脸上滑过。我突然觉得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才会偶尔露出那种眼神。
终于,雨停了。
在几乎没有交流的情况下,三人挤进车里。车沿着雨后泥泞的河滩地前行。涸死的河床活了过来。浑浊的泥河,吞吐着泡沫,急促促地流淌。她把车窗大开,潮乎乎的风扫进来,身上麻麻的。男人不停地提速,车时不时打滑,不过她没提醒男人要当心点。我也没有。她在看远处。我在回想夜里的梦。路不远,来不及回忆完整的梦境便到了山口。三人徒步向山口走去。山口足足有一里地宽,西热河从那里甩着身子喷涌而来。一小群骆驼被山洪分开,一拨在这边,一拨在那边,隔着山洪相互哀鸣。越走地势越高,越陡,人影越小。我在前面走,她随后,男人尾在后面。男人拍了好些图片。
“该死的,到处是烂泥,好累。”
当三人攀至半山腰稍作歇息时,男人说。他双手叉着腰,胸口一起一落。发肿的单眼皮红红的,像是用手背狠狠地揉搓过。
“好壮观——,我的天,太美了。”她说。
褐色山岗被雨水冲刷后颜色变深。云层近乎贴着山头飘浮。灰色云变成薄薄的天纱,那后面是拳头似的鼓起的、灿白的,我们当地人称之为老云的白云。
“哟呵——,还有多远,老乡?”
“前面拐过去就是,那边,挨着那棵挂着经幡的神树。”
“就在那儿啊,前天我还以为是什么——,就没靠近,原来是神树啊。”男人懊恼地说。
“假如滑下去,会不会被山洪卷走?”她问。
“那当然,你仔细瞅瞅——,牛大的石头,呃,那个——,白色的,那可是石头。”男人指着山沟说。
“水不会很深,但是会撞到石头上。”我说。
“真够倒霉的,早知道就在跟前,那天咱俩就该往深处走走。”男人故意拦截我的话似的说。
“那天的风景可没有今天这么壮观。”她说着取下披在肩头上的头巾,开始整理头发。
“得有仪式感。”她说。很快,颅顶上的牛粪包恢复了原样。
“走吧。”男人说。
我没有挪脚。
“你不去吗?”她问。
“我就不去了,我在这儿等你们。”
“也是,你是当地人嘛。”
两人一同向挨近山脚的神树那边去。走出几步,男人猛地回头看看我,我想我有些痴痴地目送她的眼神被他捕捉到了。
头天夜里,我已经把“阿布石”的传说讲给了他俩。我讲得很粗略,完全没有母亲当初讲给我时那么令人动容。
“鞭子宁达是个魁梧而勇猛的男人,虽然他是个土匪,但他不会掳掠穷人。在阿拉格山最险峻、最隐秘的地方有他容身的山洞。洞里铺了老虎皮,他就在那上面睡觉。他有一匹枣红马,从十里地之外听到主人的口哨后便能疾奔而来。人们听到马蹄声,就会说,哦,那是我们鞭子宁达的神骏。他还是个神枪手,如果秃鹫想叼走他的猎物,他会一枪打烂秃鹫的脑袋。不过,他可从来没有猎杀过秃鹫,一个都没有。因为他说他的父亲是秃鹫。后来呀,他爱上了黑脸台吉的小夫人。豁勒嘿(语气词,类似可怜的),悲剧从那一刻开始。黑脸台吉是阿拉格山最富裕的人。富人家的女人,自然是很美丽。不过,这位美丽的夫人也爱上了鞭子宁达。有一次,在一个黄尘漫天的春日,鞭子宁达到黑脸台吉家掳走了小夫人。但是,黑脸台吉追到山里。很不幸,鞭子宁达被台吉的护兵抓到了,关进地窖里,还把他的双腿砍断了。黑脸台吉是想活活折磨死他。哦,苍天保佑!最后,我们的鞭子宁达还是逃走了。再后来,他找人用石头雕出自己的模样,立在阿拉格山里,好让小夫人经常到山里看他。”
在那个幼小年纪,我是不会追问小夫人的结局,不过母亲还是告诉了我。
“其实吧,黑脸台吉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并没有狠狠地惩罚小夫人,只是从她头发上坠起两条长长的木棍,那是一种很古老的惩罚。这种古老的惩罚就是新娘头戴上的西部格(名词,早期鄂尔多斯妇女头戴上用布缠绕的木棒)的来源。”
“那得多疼。”
“豁勒嘿,这个并没有浇灭小夫人心头的念想,她总是蹒跚着走到山里看望心上人。”
“鞭子宁达不是变成石头了吗?”
“那又怎么样,小夫人眼里它就是他。小夫人还生了三个小孩,不过孩子都夭折了。”
我不确定当时我有没有联想那三个孩子是“阿布石”的。
“苦命的女人,最后疯了。”
“疯了?额吉,小夫人疯了?”
“是啊,三个孩子夭折后,小夫人的舅舅让她嫁给了别人。后来她就疯了,嫁过去后再没有生小孩。”
夜里,当我把传说大致讲完后,她说了句:“多么凄美的爱情。”
“那算什么爱情,纯粹勾当。”男人说。他酡红的脸奇怪地抽搐着,眉头也硬邦邦地鼓起。
她没有应声,只是轻轻地叹口气,仿佛把心头的话化作一缕气吐了出去。也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把整个传说如母亲一样娓娓道来,好让她沉浸在无尽的遐想中。因为,窗外的夜色是那样的宁静与幽暗。
这是一个应该有传说与炉火的仲夏夜。
三
水汽蒸腾,刀刃似的条状阳光从云缝间直射山腰。她刚好走在那里。须臾,阳光崩离四散,她走入灰蒙蒙的水雾。男人走在她身后,一手执着随手捡来的木杖。禽鸟飞来飞去,山谷间满是它们的鸣叫。偶尔,风从山谷间旋起,飕飕地摇动稀疏的灌木丛。
“嗨,老乡,与我想象的没多大差别,大理石造的,足足有两米高,左臂垂下,握着鞭子。右臂打弯,持着一石碗,我冲那碗放了枚银币。这个土匪——,腰带还是雕花纹的。”
男人喘着粗气说,裤脚鞋子沾了泥垢,仿佛刚从泥沼里抽出来的。
“不要这么讲,亲爱的。”
“本来就是嘛。”
“别乱讲,咱俩刚刚给他磕过头的,你真没必要这么讲。”她近乎哀求似的说。她站在低处,说话时仰起脸,整个人后倾,如果风再大一些,她会跌落至山沟。
“嗨,老婆,他假如真能给我带来好运,呃,一个胖儿子——,或者一个鬈发丫头,那我叫他爹都可以。没什么,认一个土匪当爹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哈哈,妈的,真不该选个大雨天爬山。”
我转身欲走,她突然说:“巴格巴,你说的瀑布呢?”
“哪来的什么瀑布?”男人摆弄着相机,随手拍了几张图片。
“昨晚他讲过的。”
“不远,就在前面,两里地。”我说。
“带我们去吧。”她说。
“哦,老婆,不就是个瀑布嘛,不会很神奇的。”
“我想去看看。”
阳光忽地洒满山谷,身上有了暖意。不过很快又被浮云挡去了。
“你忘了,巴格巴讲过一个名叫阿弩达尔的女人生了二十三个孩子,就是因为祭拜过‘阿布石’,而且还……”
“的确是个奇迹。”
“她生那么多孩子,是因为喝过瀑布的水。”
“哦,我的老婆,不要相信那些哄小孩的话。你听听,瀑布在嚎哭。哈哈——,听听就够了,你又不是没见过瀑布,你说呢?”
“你不想去就下山吧。”她顿了顿,继续说:“你俩都下去吧,我不怕迷路。”
她转身走去。
“呃,老乡,永远不要小瞧一个满心想当母亲的女人愿望。”男人自嘲似的抓抓乱蓬蓬的头发,跟了过去。
周围尽是碎石,仿佛这里曾经发生过石头与石头的战争,大石头吞掉小石头,嚼碎,啐吐一地。
“这山里一定有岩羊、盘羊之类的,是吧,老乡?”
男人见我远远地尾在他后面,停住,大声问。
“有,不多。”我也提高了嗓门。
“砰砰——,呵,那得多过瘾。”男人挥臂比划着说。她已经走远了,沿山坡的一簇簇灌木差不多隐去了她的背影。等到太阳完全挣脱出所有的浮云,我们也到了瀑布偏北的山腰。再往前就是两山相遇的交界处。浑浊的水流从那里造出巨响喷泻,仿佛用轰响向我们告示它们正从囚禁地逃离。
“老婆,你仔细瞅瞅,真的就是个暴雨带来的山洪。”
男人显然懒得拍照,只是见她出神地凝望,慢腾腾地咔嚓几下。
水流扯出约十多米的水身,重重地摔进褐色山窝,被羊绒似的泡沫覆盖。在水流的冲击下,泡沫不停地堆积,颤动。
“它不会经常有,对吧?”她说。她并没有回头看我,不过我还是回了一句:“嗯,下雨后才会有。”
“它的名字叫‘阿布的瀑布’,是不是?”
“这边的老人们那么称呼。”
“你有多久没见到了?”她扭过头来看我。
“三四年——,不过,去年也有过,只是一股子小溪。”
“天旱了它就会断流,这很明显嘛。戈壁荒山嘛,十年九旱。”男人从一旁说。
已经是偏午时分,云层不断地从天际涌来。山沟,清幽幽的水雾渐渐散尽,稀疏的树木浸染过油似的发亮。鼻腔、胸腔里凉凉的,我大口大口地吸气呼气,仿佛这样才能降伏我躯体内不断暗涌的激荡。它们的源头是她,这点我毫不怀疑。
她——我在心底默念,毫不避讳。
“巴格巴,你见过她的样子吗?就是阿弩达尔。”
“没有,我也是听我母亲讲的。”
“一个活了七十多岁的女人,一个生下二十三个孩子的女人,没有经历过众目睽睽下的——,呃,众目睽睽下的矜持,故作的矜持,那该多好。”
也不知为何,我竟然向前踱了几步,几乎站到她身边了。
“山那边有个名叫‘母宫’的山洞,一旁有早年人们用来打猎的石墙,还有阿拉格庙烧毁的遗迹。”我说。我确定,有那么几瞬间我忘记男人的存在了。
“真该去看看。”
“老婆,算了,没什么奇特的。”
突然,她用手掌拢着嘴,呜地高喊。不一会儿,山谷传来隐隐的回响。又一下,很漫长的呜——。听着那缓缓消散的回响我莫名地笑了。她放下手,冲着我笑。
“我可以带你们去。”我说。
男人盯着我看,面无表情。那神情与四周满眼毫无生气的、僵硬的裸岩一样,越来越阴沉。
“不会很远,对吗?”
她说着扭过头来看我。一双无畏的眼神,是她这个四十多岁女人隐形的触角。此刻,它们正向我慢慢地延伸。我没有躲闪。
猛烈的、急促的、笨拙的——,撞击,男人的拳头落在我脑袋一侧。我向后趔趄着站稳,没觉着疼,只觉整个脑袋瞬间被泥浆灌满了,灌得死死的,闷闷的。又一下。这次比头一个弱一些。我向后撤出几步。男人的面孔,沦为一张铁青色的死人脸。我没有动。我的拳头已握紧,指关节在嘎巴脆响。我听到了。她没有尖叫,也没有阻止。眼神里也没有慌乱与惊讶。她依次看了看男人,看了看我,扭头看了看瀑布,或者更远的山峦,然后缄默着向来路走去。
男人啐了口唾沫,弯腰,弓背,向我扑来。
我也迎了过去。
云在旋转。山峰在旋转。树木在旋转。铁青的死人脸,凑过来,蓬乱的鬈发颤栗。耳朵根撞到什么,火辣辣的光,闪一下,不见。四条胳膊和四条腿纠缠着,混为一体,顺着山坡滑下去。骂娘的咒骂,粗野的咆哮,在四处回响。沁血的牙齿,惨白的石头,厚厚的嘴唇,憋红的面孔——都是男人的。挠心的撕裂声。肩头凉凉的,纽扣在崩裂中飞去。
须臾,我看到鬈发与草屑缠在一起,遮住半张铁青色的死人脸。我跨坐在男人身上,用膝盖顶住他的一条胳膊,另一条被我的一条胳膊扭着。我空出一条胳膊摁住男人的嘴。现在,铁青的死人脸上只有一双烧红的眼。
“你听。”我说。
男人奋力地扭动着硬撅撅的身躯,我感觉骑了一匹马。
“该死的——,听!”
烧红的眼睛瞪圆,变小,变成一条缝。
“瀑布在嚎叫——,呃,该死的牛犊子——,女人的呻吟。哪有那么多传说。”
男人停止踢腾。
我松开了手。
“那个女人……”我站起,吐唾沫。
“那个生了二十三个小孩的女人,家里有老母亲,帐篷太小,夜晚又太短暂,你知道的——,她和她男人每次都——,都在这边——。”
男人坐起,揉着拳头,哼哼地吐唾沫。
我转身走去。走出几步,顿住,回头看着男人,说:“我也有过老婆,只是很年轻就死了。还有,那个石人是我的父亲。我母亲那么告诉我的。”
路过石人时,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驻足看看他。他背对着我。原本灰色大理石身躯被雨水浸泡着变成浅酱色,微微地向一侧倾斜,视觉上,仿佛要结束长长久久的站立,来场不停歇的远足,或者伸开双臂,向某个匆匆路过的人挥挥手。
一种昏沉而沙哑的、戏谑而鄙夷的男人笑声,从我确定不了的方向隐隐地传来。我猜,是石人在笑。从我看不见的地方,正俯瞰着我。而他这般神迹似的存在,陪伴我多年。在我七八岁的某个冬夜,我和母亲赶着羊群路过这里。那天下了大雪,山头从雪层探出脑袋,黑乎乎地悬在半空,犹如无数个巨人正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天空阴沉,四周灰蒙,他孤零零地、黑黢黢地出现在前方。见他堵住去路,我用羊鞭啪地给了他一下。啪啪——,母亲的鞭子落在我身上。我逃去。在疾跑中,我听到一种从未听到过的笑声:沙哑与昏沉,戏谑中带着疼爱。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回忆时感觉到的。等到走出山口,母亲突然对我说,他是你的父亲。我说,是所有人的父亲。母亲说,不,是你的。我说,是死了的人的父亲。母亲的鞭子又啪啪落在我身上。
啪啪——,鞭子声响越来越清晰。
嘿嘿,笑声模糊。
她的背影出现在山口。
我折身,绕道向山的阴面走去。等我回到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躺着,敞身躺着。风从窗户吹进来,掀起壁龛上的蒙纱,一起一落。一种低吟的,类似于强力忍着哭泣的,而又有些歇斯底里的、悠长的喊声,遥遥地,穿过山野,搅动着云层,扫荡着荒野枯枝败叶,犹如弥天黄尘,翻滚,席卷每一粒砂砾,每一个烟囱,掀翻柴垛、木栅栏、人影、马鬃——哦,她的长发。她张大嘴,微闭着眼,一声声低唱,嗯,她在唱歌。一个蹩脚长调歌手打马穿过草原时,往往会发出那种歌声。
哦,她在低吟。
一个女人敞着身,在天地间,在瀑布的轰鸣中发出激昂的歌声。那是生命在经历自我的酝酿。
我的老婆曾发出过那样的声音。
那个女人一定也发出过。
她也应该发出。
呃,结束了,仅属于我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无趣、安宁、简单的生活,被一阵锐利的风扫荡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