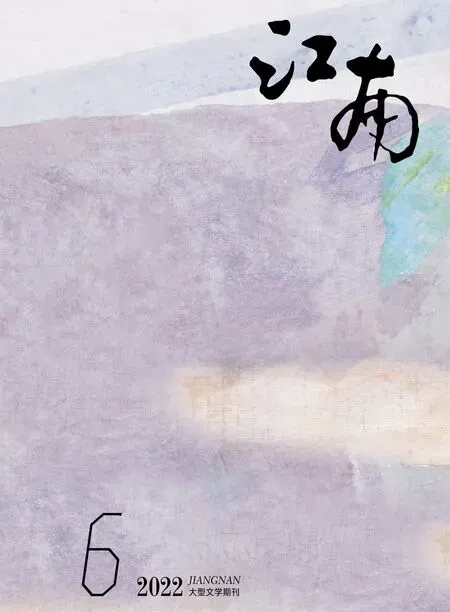临安、宋词及文学流变
□ 谢宗玉
一
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杭州我不是第一次来,只是这回我才知道,临安竟然还在。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临安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自南宋灭亡后,就跟着烟消云散了。我不知道,湮灭在历史风烟中的,只是一个花繁叶茂的幻影,而临安之根,自西晋太康元年以来,一直都在。
历史课本中的那个临安府,是南宋时期才有的。先有临安县。再之前,叫临水县,后因县东南有临安山,遂于公元280年,改名为临安县。公元1996年,改县为市。公元2017年,并入杭州市,为临安区。现在我要去的新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实践点,正是在临安区的某个山村。
北宋末年,靖康兵败,徽钦北掳,赵构作为钦宗赵桓的异母兄弟,在南京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也就是宋高宗。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初春,金兵突袭扬州,赵构仓皇出逃,南渡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作为“行在所”,即天子巡行所到的地方。公元1132年,赵构深感复国无望,汴京远矣,只好于半羞半愧中,定都临安府,守着半壁江山,度过了他安逸的一生,享年80岁,是乱世中唯一的长寿帝王。
临安,临时安居之地也。建炎朝廷以临安作为都城名,可谓煞费苦心。当时杭州下辖八九个县,临安县只是其中一个。将县名升作都城名。一是为拉拢当地民心。杭州曾是吴越国的大本营,最后一任吴越王钱弘俶虽于公元978年纳土归宋,但从吴越国开创者钱镠王以来,钱氏毕竟在这片土地上盘踞了近百年,影响力还在。用钱氏故乡临安作为都城名,跟《百家姓》将钱姓排名第二一样,都有对吴越钱氏抚勉的意思。现在强龙过境,虽是半流亡状态,也请地头蛇莫起他念。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名词暗含北归之意,民众固所愿也。最初南宋人们都觉得定都杭州不过是暂时的,来日终究会还都汴京。
然而,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人,每有直捣黄龙之势,就被赵构、秦桧之流急急召回。岳飞岳云父子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于风波亭,酿成千古遗恨。
除秦桧外,很少有人懂得宋高宗的心理,若王师北定中原,迎回徽钦二宗,那他赵构又该往何处去?为了一己之私心,全然不顾半壁江山在疼痛。所以临安一词,从定都开始,就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可怜了中原那些日盼夜望的冤魂野鬼,可惜了江南那些壮怀激烈的碧血丹心。
公元1276年,元蒙铁蹄踏碎江南,三吴都会饱受兵燹之祸,复归汴州的梦想,只能永远留在仁人志士的心中。随后三年,文天祥血战被俘,陆秀夫抱着8岁儿皇在崖山蹈海,至此南宋灭亡,神州陆沉,“临时安居”亦不可得矣!
南宋之后,临安一词便成了千百年来华夏儿女们心中的隐痛,后人则哀叹“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曾寄托了无数人美好愿景的临安,也成了“偏安一隅”的代名词。
回头想想,若岳飞等人北定成功,那临安一词无疑会被中华儿女视作悬梁刺股、卧薪尝胆后的“凯旋门”。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因为失败,同样意思的一个名词,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往小里说,是南宋小朝廷玷污了一个美好的汉词。往大里说,则是整个民族让一个无辜的汉词蒙羞了。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二
枕着残山破水而眠的赵构,塞耳不听中原百姓的凄厉呼号,掩眼不看南渡之路的斑斑血泪,蒙心不顾万里江山的水深火热,他甚至都忘了自己还有五个二到四岁不等的亲生女儿,也一同被掳去了。他置帝王、父亲、儿子和弟弟的职责于不顾,一生醉心于书法,著有煌煌大典《翰墨志》,亦有墨宝《草书洛神赋》传世。
在《翰墨志》中,他沾沾自喜写道:“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型,而心之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又说,“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取舍,至若禊帖,测之益深,拟之益严,以至成诵。”看了这些话,想起他身负的血海深仇,真恨不得能一口痰,从时光的遂道里吐进去,喷他一脸。
后人评价,赵构书法博采众长,融汇贯通,独创一体,俨然大家。其艺术成就直追书法瘦金体创始人,也就是他的父亲宋徽宗。网上则有文章称,“赵构的勤奋足为今日学子之楷模”。我呵呵笑了,两耳不闻山河破,一心只摹百家书,便是宋高宗的真实写照。如果艺术真的神圣到了可以置天下苍生于不顾,那么赵氏父子或可成为今日学子之楷模。然而,不能为社稷苍生服务的艺术,又有何用哉?更何况,政治这门艺术,才是赵氏父子的必修课,书法和绘画,只应该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就好比一个马上要面临决定命运大考的中学生,却沉迷于《王者荣耀》,日以继夜,没完没了地操练,终于成了史上最快最强通关者。现在,这个通关者要被钦定为青年学子之楷模,这让无数焚膏继晷、刻苦钻研学问的孩子们情何以堪?
这个比方,还不是十分确切。毕竟真能成为《王者荣耀》最强通关者,一辈子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可即便如此,也别把他当作榜样,就像我不赞同把打台球的丁俊晖当作青年楷模一样。据说他在中学期间经常逃课,跑出去玩球。他的成功毕竟是孤例,无法复制。
赵氏父子,明知大厦将倾,无数亲人臣民都要葬身于这断壁残垣中,身上压着“急寻大木柱长天”的重任,可他们却偏偏去做“自闭皇宫练书法”之闲事。还莫说,赵氏父子的定力真让人佩服,身处煎釜,竟还能静心沉醉于私趣之中。可谓“朝得书道,夕死可矣”。
活了八十岁的宋高宗,在自己五十五岁时,禅位给了自己养子。年富力强的他,摆脱了困危时局和繁琐政务后,再不必受笔下所言的“大利害相妨”,从此“未始一日舍笔墨”,终于将自己的书法推到一个崭新台阶。
与他们父子俩遥相呼应的,则是宋朝文人。宋朝文人凭藉宋词,把汉字意境之美发挥到了极致。著名词人张孝祥描写洞庭的观感,完全可以移来概括宋词之美:“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汉字之美,在宋词里多一分则嫌多,少一分则嫌少,并且不含一丝尘杂。美得让人喉涩眼湿,电流肺腑,却难以言表。
然而,正是要保持这份纯粹的美,很多糙词粗字、琐事俗务都入不了宋词的法眼。头颅、污血、断肢、哀号、饿殍、白骨……这些在宋朝常见的事物,统统被排斥在清洁宋词之外。宋词常用词则是:香腮、白衣、春水、秋月、新绿、柳绵、宝马、雕鞍、兰舟、薄衾、清霜、泪眼、秋千……
这些年,为练普通话,我在车子里放了一叠宋词碟片,开车在路上,我都会随听随念。听得久了,念得多了,对少年时奉为心灵至宝的宋词,竟生了厌倦之心。就那么几百汉词,几十种意象,竟撑起了整个宋朝的主流文学。这样互相模仿、彼此抄袭的无骨之物,居然把年少的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以致多年后还在婉约病里兜兜转转,大好男儿,竟有宋文人纤靡柔弱之心,半辈子都走不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心灵困境,正是这种自怜自艾的意绪,多少阻隔了我对经世致用之道勇猛精进的学习态势。
呔!宋词这样的审美旨趣,即便艺术造诣深不可测,于我又有何益哉?于国又有何益哉?于宋朝千万民众又有何益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无形之中,宋词竟成了一种青楼文学、一种亡国文学。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宋词若不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若是革命救亡文学占了主流,宋朝会不会这样惨淡收场呢?
是的,宋词也有豪放派。可豪放派占不到宋词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完全被遮蔽了。“柳郎中词,只合二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对此评价,据说苏轼为之绝倒。可是,观遍花红柳绿地,咿呀吟唱者,尽二八佳人,哪有虬须怒张的关西大汉?
更何况,大多数豪放派词人,也是单纯为豪放而豪放。对字词一样有严苛的挑选,“刀剑箭马”即便能入宋词,也是刀不入肉,剑不饮血,箭不穿身,马不踏骨。一切都那么光鲜亮丽,像在舞台表演。要么是言志的奇丽想象,要么是抒怀的华美梦境。豪放之词,更多的是为彰显自己的品性风骨。
甚至,还有用豪放的景致和事物,做出了婉约的词儿。比如《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此词对将士的软化功能,不啻于韩信的“四面楚歌”。而就算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之句,也透着深深的无奈感。典型的厌战反战之词。可群狼环伺,战争免无可免,避无可避,作为军营主帅的范仲淹,实在不可为了文章意境之凄美,而让戍疆士卒产生厌战之悲观情绪啊。
能与“社会水深火热、百姓流离失所”境况相匹配的宋词,只有一首,便是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饮毛茹血,虽审美不佳,可这才是抗战文学的标配。悲催的宋朝从建国以来,就被辽、西夏、金、蒙先后蚕食鲸吞三百余年,江山一残再残,民生一衰再衰,这时只有喊打喊杀、武装到牙齿的革命文学,才配得上这段血泪史,才可能挽回一颓再颓的危局。可惜的是,宋朝文人同赵氏父子一样,沉醉在风清月白的艺术梦中不愿醒来。偎红依绿的柳永更是以一曲《望海潮》引得金主完颜亮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去一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美景。
柳永若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是该羞愤而吼,还是该仰天而笑?想必柳永同赵构一样,会是后种心态吧?一词差点亡城啊,文字的魅力,被自己发挥到了极致,足以让柳氏后人夸耀千秋万代。
只不知柳永有没想过,当金蒙挥刀南侵时,会不会将其子孙族人的头颅全部收割去?正如宋高宗有没想过,自己写了那么多自以为可流传久远的墨宝,国破之后,会不会付之一炬,不留一字?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民族文艺的得失成败,得看它能为民族的发展、文明的进程、民众的活力提供多少精神动能啊,而不是像龚自珍《病梅馆记》里批判的那样,纯粹为审美而审美,最后将艺术变成靡淫心灵的精神鸦片。
宋明之悲剧,华夏之殷鉴。等到上世纪初叶,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亡国灭种之危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一大批左翼文人,再不肯在至暗时刻让文学缺席于社会主流。他们选择听从时代的号角将令,将文学变为匕首投枪,变作警世恒言和喻世明言,杀向敌人,唤警民众,在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中,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伟力。
三
让中华民族含羞的“临安”,终于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科技腾飞,洗刷掉了身上的羞耻印痕。“临安”不再是临时安居之地,而成了人们真正“临水临山安居”的乐土。非但临安是这样,整个杭州,包括汴京在内的大江南北都是这样的。
四海九州,内无忧患,外无侵凌,都成了人们安居乐业之地。昔日南宋人由“临安”之名而兴匡扶天下之志,共产党人在几百年后,帮他们实现了。今日之临安,说是中华民族精神意义上的衣锦还乡之地,也不为过。
现在,我以文学人的身份,来到浙江,看遍了杭州的高端和大气,也领略了临安的低调与轻奢。湖光山色与现代化文明融合在一起,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淡妆浓抹总相宜。若是柳七重生,定会发现,如果文明没有止境,那么繁华也是没有止境的。一茬一茬的人,可以如急流飞瀑般地老去消失,而古老的文明,在科技的助推下,将永远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算不上“豪奢”一词的标配,现在的豪奢,是八百年前的宋朝人想象不出的。
这个时候,中国作协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中国新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第一个文学实践点。我觉得其中的意味,令人深思。
那么,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时候?
当然是指纯文学日渐式微、与大众渐行渐远、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时候。
而这个地方——临安,则可以看作是“词殇”之地。把第一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实践点,设在此地,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我们知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之所以会发生流变,是因为文学在不断向民间下沉,是因为旧的文学形式日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越来越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新的文学形式会比旧的文学形式更接近民间,因此也拥有更多读者,更为民众喜闻乐见。即便是在“蛮蒙原本不读书”的元朝,以演唱形式流传的元曲剧,其受众面也比只在达官、文人和贵商中流行的宋词要宽广得多。
美到极致的宋词,非但宋朝的老百姓欣赏不了,就是放在现在的中学课本里,大多数学子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囫囵吞枣地背诵,并不能充分体会其中意境。我家就有理工儿郎一枚,凡课本里要求背诵的词文,他都背得出来,但若跟他探讨宋词的美学、汉字的风流,那就是对牛弹琴了。他的背诵,不过是牛嚼牡丹罢了。
现在我不妨粗粗梳理一下这种文学流变的轨迹。
唐诗是败给了风气。群狼环伺的宋朝,居然一开始就有躺平“竞豪奢”的风尚。也许是天下纷扰久了,全民厌战。也许是因为突然黄袍加身,江山得来太容易,然后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上层有了享乐之心,以享乐为目标的商业便异军突起,兴旺发达,一种比唐诗更通俗、更纯净、更能让人卖弄煽情的新文体,便有了滋生的温床。
宋词则败给了刀兵。再繁华的商业,再锦绣的江山,再绝美的宋词,如果没有脊梁般的骨头拱卫,没有钢筋般的拳头守护,也不过是夜空中绚烂的烟花而已,说没有,也就没有了。
元曲应该是败给了资本。庞然大物般的元朝,文艺却呈现萧山瘦水之姿,当明朝资本扩张、技术革命后,造纸和印刷术都得到极大提高,洛阳永远不会纸贵了,几个铜板就可以购得一沓纸来写写,购得一册书来翻翻。片言只字,再不能满足人们群众的阅读需求了。章回体小说这时闪亮登场。从此历史上终于有文人,不再需要投靠皇上、权贵、豪门、旺商、艳妓、剧班,单凭手中一支笔,直接卖文谋生了。书商就在冯梦龙们的家门口等着,写几章就印一册,卖出去多少,就分多少红利(版税)。
明清小说则是败给了西方思潮与东方革命。当亡国灭种之危局再次来临,几乎所有仁人志士都不再相信中国社会传统的构架、制度、思想与文化。他们引进西方思想,掀起东方革命。所以,严格说来,白话文的兴起,算不上文体上的求新,而是思想上的变革。明清白话文小说,在语言文体上,与五四后的小说并无多大差别,而其主旨、核心、题材、结构、情节及写作手法,则完全不同了。被打上人文主义烙印的新文学,与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是相契相融的。将个人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灌输他们平等、自由、博爱的理念,唤醒他们的欲望和热情,让他们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正是民众有了追求尊严和自由之心,中国社会也就拥有了翻天覆地的可能性。
新世纪以来的纯文学则是败给了科技。
如果网络不出现,我们似乎已经相信,中国民众的阅读兴趣已被世界同化,跟西方再没有任何区别了。然而,等网络章回体小说兴起后,我们这才发现,被西方文艺思潮浸淫了这么多年的中国老百姓,其实仍有属于自己的强大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而这种趣味习惯则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学以及“仿西文学”之所以在内陆大行其道,是自上而下的风潮所致:政策学西,权威尊西,作家仿西,青年向西。因为没有选择,或者说,选择权不在自己手中,中国民众不得不看西方文学或仿西文学。
网络文学经过二十年来的不断探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众逛网站,浏览自媒体,仿佛进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购物超市。样品多了,也就可以真正遵循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这时谁有市场,谁有发展潜力,一目了然,大数据是骗不了人的。
由纸质到网络,就好比由竹简到纸张,对社会,对民众来说,都是一个无需犹豫的选择。网络已经呈现出了要将整个人类文明都包罗进去的态势,这个时候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最紧要的一步,就是紧跟时代步伐,给文学松绑,把小池塘里的鱼虾,全部汇入网络的汪洋大海中来,以期它们能成巨鲸、化飞龙,这才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前提。
换句话说,黄河都改道了,黄河治理监察指挥所,就得移步到新道上来,如果还在旧道,对着干涸河床里的黄沙,研究未来洪水可能的泛滥,那就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跟古代那个刻舟求剑的人,没有半点区别。
网游八荒,络通千载。网络以它前沿、快捷、兼容、共享、方便的特质,未来将成为所有文明的集中地,文学更不会例外。网络是一个能让人快速试错纠错的地方,作家与读者可以直接互动。读者的喜好,作家能第一时间得知。读者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家的创作中来。
在网络,作家能迅速了解民众与时俱进的哀乐和愿望,懂得终身学习才是灵魂跟上脚步的奥秘,知晓科技是进入日新月异社会的钥匙,明白文明要向前发展,向历史找经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向未来找预案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通晓这个时代心灵的惶然、梦境的惊悚、思绪的茫然,绝大多数来自于对未来科技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预估不足。
知道了这些,作家们也就能找到与民众共鸣共振的题材。他们赓续东方“文以载道”的传统,不再以深度挖掘人性为创作的核心目标,而是以及时聚焦社会为创作的内在动能。“经世致用”的奋斗历程越来越成为时下成功作家的创作主题,这不但契合中国当前快马加鞭的建设理念,也符合民众勤劳致富的世俗需求。很显然,我们已拥有了一大群能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文艺群体。
这个时候,中国作协又把临安作为中国文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第一个实践点,可谓匠心独具,意义深远。我真心希望,新世纪文学能够借助科技的翅膀,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一起腾飞,共同辉煌。
很显然,发展的科技在不停改变社会的结构,新领域、新群体、新生活层出不穷,紧跟着,新体验、新情感、新矛盾、新观念、新伦理、新道德随之诞生。所以,作家重点要深入的,是由科技文明所带来的新生活。把这类生活的社会态势和运行奥秘,以及其中的甜酸苦辣和爱恨情仇,深刻而艺术地再现出来,最能起到和谐社会、抚慰人心的作用,这才称得上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好作品。
同样,我们要扎根的人民,主流也应该是时代的弄潮儿。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哀乐与愁喜,已与现代科技文明牵连甚广、搅和日深。是啊!临安的变化,杭州的变化,中国的变化,这一切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魔术和幻景。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所有这一切,都浸透了人们群众力争上游的血汗和大浪淘沙的痛楚,以及浮沉难料的哀愁。
新世纪文学,绝不能像宋词缺席民族的深重苦难一样,而缺席民族的悄然崛起。绝不能像宋词缺席社会的水深火热一样,而缺席时代的热火朝天。
懂得了这些,这次“国之大者·生态临安”的文学活动,我不想写一篇湖光山色掠影的旅游散文去交卷。而是想借此时机,借此地名,反思汉语及中国文学在历史中所出现的偏差,剖析新文学群体兴起的必然性,探讨正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文学的未来之态。
我很期待,从临安出发,中国文学能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快马加鞭,赶上时代的变化节奏,接轨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真正讲好属于中国的故事。如蝴蝶挣脱蛹茧,从此一个令人心驰神迷的文学新形象,将翩跹于这个无与伦比的新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