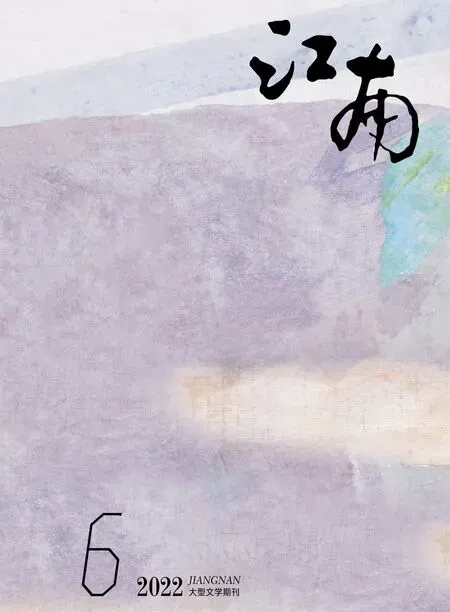玩味玲珑
——也说苏东坡其人其事
□ 潘庆平
在临安拥城而立的玲珑山,有卧龙山寺驻其南坡。山寺不大,却长年香客不绝,烟火绕缭之状不亚于径山、天目。因为宋代名家苏东坡曾登临此山,给这里平添一抹文化色彩,留下“苏公祠”“学士松”“三休亭”“醉眠石”“琴操墓”这些“遗物”,皆是宋韵文化的尤物,让玲珑山出落为一处人文风景名胜地。遇见当下的宋韵文化热,正好可作为一个话题用来玩味,抑或也是一种寻寻觅觅。其间,我们不难发觉玲珑山因为“绑架”了苏东坡才鲜亮起来。这些观赏的尤物浸润着苏东坡的品行格致向世人招展,因缘于爱屋及乌,对苏东坡的崇敬与爱戴演化为对山中景物的钟爱,玲珑山才有了哄然不歇的文化魅力。玲珑尤物的造作充满匠心,一件件都谋划得与苏东坡的精气神悄然相通,信手拈它来玩味,都会幡然彻悟,大有其乐无穷的美感。
苏公祠
《玲珑山志》称“苏公文忠祠”。建于何时?无文字记载,毁于何日?亦无明确时序。而徐映璞的《玲珑山志》说,明万历二十八年(1580)一个叫照启的和尚 ,募缘修庙,从苏公祠废墟里挖掘出的三尊石像,分别是苏轼、佛印、黄庭坚。这三尊石像由时任临安县知事的禇栋重新立在新修的苏公祠里。禇栋是外地人,参加万历八年的科举考试,考绩不错,排名得了个第40名,派到临安来任县官。他是个读书人,懂得这三个石像的分量,惺惺相惜,也夹杂一份崇尚才学的情怀,很认真地把三具石像扶起来,安放在复建的苏公祠内。但世事多舛,新苏公祠建成后又毁于兵燹,三尊石像复遭掩埋。乾隆五十五年(1790),有个叫刘田的地方绅士发兴重修苏公祠,重刻了一块苏公像碑镶嵌在屋墙内,而那三尊圆雕移到三休亭里。把三休亭改称为“三贤祠”。后来时运不济,兵祸又起,苏公祠、三贤亭统统被毁,那三尊石像弄得无头无手,沦为残石。还好,嵌在墙上的线刻苏公像还在,人们又从废墟里把它挖了出来。进入民国后,玲珑山寺庙得到扩建,因寺庙位于吟龙坞,将此前的“圆觉大殿”改为正式寺庙,取名“卧龙寺”。本有的苏公祠也恢复起来,只不过新建的苏公祠规模大不如前,只是那方带有石像的刻碑却很醒目地立在祠内中堂。徐映璞对此有记述:“近人重建小舍,若村里社庙然,嵌列碑石于内,虽曰简陋,亦不啻告朔饩羊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到寺庙里来“破四旧”,砸碎了很多古物,偏偏这尊线刻像被一位老人偷偷藏了起来,躲过一劫。
房屋被毁,苏东坡线刻像却保存了下来,我怀疑是一种天意。
苏东坡作为一个老百姓爱戴的士大夫,他的为人处事在历代民间都被传颂,把石刻像传承下来,宛若把苏东坡的魂魄保存了下来。在苏东坡的思想理念里,以民为本的观念十分浓烈。他走马上任来杭州当知州,正好遇上大旱,老百姓无水缺粮。他直接上谏,请求朝廷开仓拨出救济粮。他发动杭州居民掘井取水,共渡难关,杭州百井坊就是那时建成的。“当官多为民作主”这已经是苏东坡在仕途上的一种自律。这样的官宦,老百姓当然拥护。玲珑山开发山径,巧妙地设计出带有苏东坡故事的“学士松”“醉眠石”“苏公祠”等景物,这是一种期待的表达,是众黎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历经千年的线刻像得以传承,是老百姓文化心理的实证体现。苏东坡在玲珑山上的“手书”“手栽”未必都是史实,而苏东坡在祠宇里的尊位虽是影子却实实在在。
学士松
端详佛印坪前的那株学士松,十分令人生疑,如果当真是苏学士亲手所栽,那它至少有1100多年的生命了。千年古树不可能没有超常的老态。如今能见到的这棵学士松或许也是玲珑山造景的后来尤物。首先,“学士”的称谓用在苏东坡身上恰当不过,而松树的挺拔正好可以和苏东坡的人格风骨相应。苏东坡赞赏松树的品质由来已久——依依古松子,郁郁绿毛身。每长须成节,明年渐庇人——庇人,则是苏东坡所赞赏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松如庇人。
弟弟苏辙曾在甘肃平凉任职,那里有一个柳湖,他写了一首七言古诗:
柳湖万柳作云屯,种时乱插不须根。
根如卧蛇身合抱,仰视不见蜩蝉喧。
开花三月乱飞雪,过墙度水无复还。
穷高极远风力尽,弃坠泥土颜色昏。
偶然直堕湖中水,化为浮萍轻且繁。
随波上下去无定,物性不改天使然。
南山老松长百尺,根入石底蛟龙蟠。
秋深叶上露如雨,倾流入土明珠圆。
乘春发生叶短短,根大如指长而坚。
神农尝药最上品,气力直压钟乳温。
物生禀受久已异,世俗何始分愚贤。
此湖是宋神宗时,一位姓蔡的知州“引暖泉为湖,环湖植柳,建避暑阁于其中”,是官宦之需的产物,苏东坡当然不以为然。弟弟写的这首诗,明显地“扬松抑柳”,正中哥哥之意。苏轼向来鄙薄柳花的浮浪而喜爱松性的坚实,他的这种嗜好与他的志向吻合。他二十一岁出川应试,得了个“总分第二”,宋神宗把他留在朝廷做治理国家的大事,偏偏碰上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就是改革,当然会出现利益的调整。苏东坡发现新政固然不错,但有点操之过急,比如推行“青苗法”,老百姓很有意见。他认为放慢节奏让老百姓理解了再来施行,效果会更好。他就公开地向新政派陈述自己的观点,明说“激进”了没有什么好处。改革派认为这是苏东坡反对新政,就整他,到皇帝那里告黑状。苏东坡很自信,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动摇。改革派威吓他要撵他走,苏东坡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走就走!过于激进搞新政,他就是不同意。苏东坡就这样离开朝廷,贬为杭州通判。四十二岁那年,乌台诗案爆发,他被流放惠州、儋州。有后人分析,这是他那刚正不阿的脾气所招来的横祸。改革派当权时,苏东坡对他们的激进做法作过抨击,充当改革派的“仇人”。后来,形势变了,原来的保守派掌权,改革派受到打压,苏东坡又说不能全盘推翻改革派的变法,又成了保守派施政的“障碍”。保守派来了个“乌台诗案”,封了这位大学士的嘴,将他逐出皇宫,蒙受苦难。
苏东坡心底坦然,像经风历雨的青松一样立在老百姓的心中。刚正不阿的青松是他的影子,老百姓喜欢,玲珑山也喜欢。
三休亭
三休亭的演变《玲珑山志》上有所记载,原先陈列在苏公祠里的苏轼、佛印和黄庭坚三尊石像,明代时搬移到三休亭,三休亭改称为“三贤祠”。“三贤祠”则是苏东坡结交三位佛教朋友的展示。佛印是宋时的高僧,《玲珑山志》载,他曾来玲珑山圆觉大殿里讲过经,大殿前面的岗地就叫佛印坪。苏东坡与佛印交往很深,在江苏任徐州太守时,他去金山拜访佛印,结为好友,不但在诗歌上有唱和,在佛理的钻研上也都很认真。但佛印是高僧,苏东坡并不是佛教徒,他俩的关系比较微妙,理念上的差异也很明显。佛学界有一个《佛与牛粪》的流传故事:有一次,东坡到金山寺与佛印一起坐禅。坐了一个多时辰,东坡觉得身心通畅,内外舒坦,便忍不住问佛印:“禅师,你看我坐禅的样子如何?”佛印看了一下东坡,点头赞道:“像一尊佛。”东坡非常高兴,佛印随口也问东坡:“你看我的坐姿如何?”苏东坡揶揄地说:“像一堆牛粪!”佛印听了,并不动气,只是置之一笑。东坡高兴地回到家,告诉苏小妹说:“我今天赢了佛印禅师!”苏小妹颇不以为然地说:“哥哥,其实今天你输了。佛印禅师心中有佛,看什么都是佛,所以才看你也是佛;而你心中只有牛粪,所以才看禅师是牛粪。”这就是苏东坡与佛印参禅的差异。
佛学讲究“出世”,主张看破红尘,逃离现实;但苏东坡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他的三观本质是“入世”,孜孜以求的是饱读诗书,走仕途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史学家认为苏东坡“信奉佛教”并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是大儒家,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人生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不讲这个。当然他崇尚佛道,主张多读经,通佛理,也广结佛友。这完全与他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是时代潮流促使他成了佛学的大居士。有资料说,苏轼到凤翔县去任签判时,接触了一些佛教朋友,写了一部论佛、崇佛的书,叫《凤翔八观》。这本书受到好多人的夸奖,促使他与潜心佛学挂上了钩。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要结交一些佛教朋友,每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先到当地的寺庙走访交游。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第三天就去找西湖边的两个住持和尚德惠、德思,和他们写诗、宴饮。很快乐地就把被贬出京都的懊恼排除了。据专家考证,苏东坡 一生交游的僧人很多,光是能一同去游山玩水的就有十多人。比如了元佛印、南华重辩、龙井辩才、海月慧辩等。他在徐州任职时,结识金山寺的佛印。佛印深究佛理,为人又十分坦荡,与苏东坡的君子之交,成了不少文人笔下的佛教界趣事加以传扬。把他们俩再加上黄庭坚合为“三贤”,在玲珑山辟个可供奉的瞻仰处,给苏东坡崇尚佛学的人格演绎得更贴实更生动,给玲珑山的佛教文化注入极大活力。因为有过“三贤祠”的营建。有人断言苏东坡与佛印、黄山谷结伴来到玲珑山,也有说三位高人怜悯琴操这个弱女子特地登山探看。这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推想。正规的史籍上并无记载。臆想出三人同行,修筑一座“三贤祠”却像人心所向,倒也不亦乐乎。
琴操墓
苏东坡三度琴操是否确有其事?琴操是否确有其人?是个可再作考证有待解答的谜。如果把琴操这个人物认定为“确有其人”,那么琴操出家、墓葬玲珑山的事是否确有其事?就成了另外一个待解之谜。只是作为一处既成名胜、作为一处公众认定的物事,它的文化价值就不能小觑。
最早说起琴操受苏东坡点化一事的是北宋小说家方勺。他是湖州人,与苏东坡相熟,常常一起游山玩水。他科考中举,封了官,但觉得束缚,就辞官不干,专做乡贤过日子。他擅长写笔记小说,是著名的唐宋史料文学作家。他有一部笔记小说集叫《泊宅编》,里面写了不少当时的士大夫的故事,苏东坡点化琴操的这件事,就是《泊宅编》里的一篇。因为方勺写得很有感染力,又写的是苏东坡,很快得到流传。唐宋时的印刷业不发达,口头说说的故事只能是口头流传。到了明代晚期,苏东坡与琴操的故事就有刻印本,特别是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又把它编入他的笔记小说《枣林杂俎》,影响就大大扩展。苏东坡是历史名人,他与琴操的交往也很浪漫,不少人以此为乐,纷纷转载到自己的文稿里,后来还被编成杂剧《眉山秀》和《红莲债》等等。在临安和杭州的地方志书里,也能查阅到这件事的“蛛丝马迹”。《咸淳临安志》、明清的《临安县志》里都有琴操故事的记载,但记载之余往往会加上“或是传说”之类的一句话。
说“琴操墓葬玲珑山”未必属实,理由两条:一是如此佛门大事,如今能查阅到的古籍都没有原始记录,《玲珑山志》《临安县志》也只有墓名,没有事由的出处;二是文革中造反派砸开墓穴,里面空无一物。琴操墓是真是假,显然令人生疑。前面说过。不论真假,琴操墓作为古遗的文化价值客观存在。当年策划在玲珑山设置琴操墓的创意,深谙民间同情弱者的悲悯情怀,一个大文豪与一个弱女子的故事,以二十四岁的琴操了断终身为结局,这是人间悲剧,把琴操安排成“削发为尼”,又把她的坟墓埋在玲珑山,为苏东坡登临玲珑山的情由给出合理解释,故事讲圆了,而且,玲珑山有这一座琴操墓,更能召唤人们的悲悯情怀,客观上也是对苏东坡的一种赞赏。
醉眠石
徐映璞的《玲珑山志》载:“醉眠石,涧水之旁,有石砥平,能容坐卧。上端榜书醉眠石三大字。”明代童以登的万历《玲珑山志》也载:“醉眠石,在合涧泉旁。横陈路侧,平滑如床。相传苏长公尝醉卧于此,宛然入梦,为涛声惊醒,高卧枕流,真快事也。”在新编的《玲珑山志》轶闻篇里收录了一个《苏轼醉眠石》的故事。说是苏东坡来临安观政,在高陆的府衙里与时任县令的同科进士苏舜举喝了一通酒。酒后上山,酒性发作,醉眠在这块醉眠石上。志书上的文字记载是否真实,一直来有人怀疑。民国二十三年(1934),郁达夫到玲珑山写过一篇游记,其中一段:“东坡究竟有没有在此上醉眠过,且不去管他,但石上的三字,与离此石不远的岩壁上的‘九折岩’三字,以及‘何年僵立两苍龙’的那一首律诗,相传都是东坡的手笔,我非考古金石家,私自想想这些古迹,还是认它作真的好,假冒风雅比之焚琴煮鹤,究竟要有趣一点。”很显然,郁达夫对这个“苏东坡手笔”的说法内心并不苟同。其实,从风景区造景的常用套路上说,玲珑山借题发挥,把苏东坡来过玲珑山的确实经历视作是本山的资源,最大化地开发它利用它完全是合理的,毕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仅仅是放大而已,而且就故事而言,正是张扬了苏东坡豁达、大度、随遇而安的人格品质。